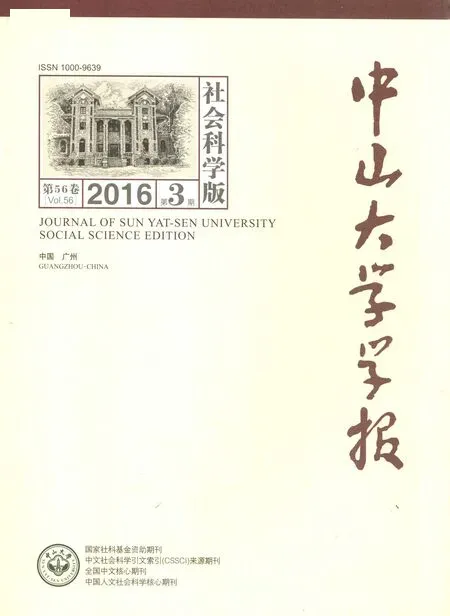普兰丁格的“保证”学说与当代儒学创新*
孙 清 海
普兰丁格的“保证”学说与当代儒学创新*
孙 清 海
摘要:美国著名哲学家普兰丁格提出的“保证”学说,旨在为基督教提供宗教认识论上的依据,同时可以成为当代儒学创新的重要契机。鉴于基督教与儒学思想的不同,“保证”学说自然不能直接生搬硬套,而需针对儒学的特点进行积极的改造。倪培民的有益尝试启发人们:儒学的复兴与创新,离不开学术层面的争鸣与争辩。
关键词:普兰丁格; “保证”学说; 儒学创新; 倪培民
当今多元文明并立,儒学的复兴与创新需要借助“他山之石”,以更好地反思、重整、更新自身,适应新形势下人们的精神需求。本文借助美国基督教哲学家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目前国内对Plantinga 的翻译,有普兰丁格、普兰亭格、普兰廷伽、柏亭格等译法。本文据北京大学邢滔滔、徐向东等教授的译法,引文尊重倪培民先生的原译,特此说明。)的“保证”学说,通过对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比较,尝试给出儒家式的“保证”定义,以期为儒家思想寻求宗教认识论上的理由或根据。与此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有前辈学者已经对此话题进行过讨论。其中最有洞见的当属美国华裔学者倪培民先生(以下简称倪先生)所做的开创性研究。故而笔者拟借助倪先生的若干观点作为主线,进而提出自己的评论,让更多学界同仁共同来探讨儒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才能真正创新。
倪先生的文章题为《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以下简称倪文)*[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3—192页。。“于女安乎”语出《论语》17:21:“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期可已矣。’子曰:‘食乎稻,衣乎锦,于女安乎?’曰:‘安。’”作者引用这段话,重点强调的是“安”字——心安、内心平静之意,以此表明儒家思想与普兰丁格的思想存在深刻的区别,但经过改造之后,仍然可以为我所用。文章的主旨是从儒家的角度对普兰丁格的理论做出一个回应,旨在引起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及各宗教传统之间更深入的对话,而最精彩的是给出了颇具中国儒学特色的“保证”定义。
一、普兰丁格与“保证”学说
普兰丁格是当今美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全美基督教哲学的领军人物”。普兰丁格一生的学术成就,最突出的就是建立了以“保证”为核心的认识论思想体系。赵敦华曾评价:“这种‘保证’既有恰当的用途,又有正当的理由,还有真理的感受。”*赵敦华:《关于warrant一词的意义和翻译说明》,[美]普兰丁格著,邢滔滔、徐向东等译:《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前言。普兰丁格正是通过“保证”把知识论的其他要素整合在一起,同时把保证立场用于对其基督教信念的捍卫之中。因其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改革宗的特点,故而被冠之以“改革宗认识论”(Reformed Epistemology)。
什么叫作保证?简单来说,保证就是“将知识与纯粹真信念分离开的一种属性或量”*Plantinga,Alvin. Warrant: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3.,其实质就是使得真信念成为知识的一种性质。具体含义是:“一个信念对一个人S是有保证,只有当那个信念在S这里是由恰当实施其功能的认知官能,在一个相对于S类型的认知官能来说是合适的环境中,按照一个朝向真理的设计蓝图而产生出来的。”*Plantinga,Alvin.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156,Chapter 6 to Chapter 8.这个定义中有四个条件尤为重要,分别是设计蓝图、恰当功能、适宜环境、朝向真理。
保证的第一个条件是设计蓝图。“形体健全,能恰当实施其功能的人类具有一套规格——而且是特别复杂且高度连接的规格……我们可以把这些规格或设计说明称之为‘设计蓝图’。”*Plantinga, Alvin. 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21,p.4,p.4,p.17.我们知道,就像人身上的消化器官或呼吸系统一样,人的认知官能可能运行得很好,也可能运行得很差。它们可能会发生功能障碍或者恰当实施其功能,所以,对认知官能的理解首先要求它有一个范式或者标准,规定了它正常运转、不发生功能障碍时呈现出来的样子。这个范式或标准就是“设计蓝图”。
保证的第二个条件是恰当功能。普兰丁格认为,从一个人的信念形成过程来看,首先要求的是认知者的认知机制能够恰当地实施其功能。《保证与恰当功能》一开头就强调:“要保证我的认知装备,我的信念形成或信念保持的器官或能力不会遭受这种功能障碍(malfunction)。”*Plantinga, Alvin. 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21,p.4,p.4,p.17.比如,如果一个人患有白内障,眼睛的视网膜就变得模糊,它们不能恰当地实施其功能,所以这个人看不清楚;心脏肌肉如果缺少弹性可以引起左心室的功能障碍;而饮酒或嗑药可能会引起认知功能紊乱等*Plantinga, Alvin. 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21,p.4,p.4,p.17.。
保证的第三个条件是适宜环境。简单来说,它是适合认知官能发挥其功能的环境。或者说,这种环境必须是某种人的官能为此而被设计的。例如,人的肺部本来是在空气流通正常的情况下用来呼吸的,而不是用来在密封或水下的环境中呼吸的。
保证的第四个条件是朝向真理。“保证”的形成还需要一个特别的条件,那就是设计蓝图必须指向真的信念(be aimed at producing true beliefs),即“朝向真理”。设计蓝图不但管束着信念的产生,而且也要朝向真理。人的认知官能需要按照设计蓝图发挥作用,而设计蓝图以产生真信念为其目的。普兰丁格强调:“管束该信念产生的设计蓝图的部件必须是这样的:即由认知官能根据该部件且在适宜的环境中恰当实施其功能所产生的信念是真的或逼真的(true or verisimilitudinous)。”*Plantinga, Alvin. 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21,p.4,p.4,p.17.
普兰丁格精心建立“保证”学说,目的在于“护教”,即为了论证基督教信念在理智上或合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在《有保证的基督教信念》一书中,普兰丁格的中心论点是基督教信念是有保证的,因为它符合保证的“四大条件”:基督教信念是在适宜的认知环境中,根据一种设计蓝图,由可以恰当实施其功能的认知官能产生的,并且成功地朝向真理,故而,基督教信念可以成为知识*Plantinga,Alvin.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156,Chapter 6 to Chapter 8.。由于经典的基督教信念分为有神论部分和独特的救赎部分,所以普兰丁格建立了两种模型来论证经典的基督教信念是有保证的。首先,他根据托马斯·阿奎那和约翰·加尔文的共同主张,建立了阿奎那/加尔文模型,即A/C模型,由此证明有神论信念是可以得到保证的。这个模型的核心是:神圣感应是作为我们认识上帝的认知官能,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恰当实施其功能,产生有关上帝的真信念。其次,他建立了扩展的A/C模型,来论证基督教信念的独特部分,即圣子耶稣的救赎信念也是有保证的。其中心思想是上帝安排了一个三重认知过程,即圣经、圣灵的内在引导和信心。这三重认知过程的恰当实施其功能,在合适的环境中产生朝向真理的信念,所以基督教的救赎信念也是有保证的,足以构成知识,从而也使得基督教信念具有恰当基础性*Plantinga,Alvin.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s , Chapter 8.。这样,普兰丁格的“保证”学说成功地为基督教信念在知识论上赢得一席之地,有效达到了“护教”的目的。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我们的思考重点是:儒家思想是否具有同样的“保证”作用?普兰丁格的“保证”学说是否可以为儒学创新提供借鉴或启示?
二、基督教与儒家的区别
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具有“异质性”的特点,故而,我们绝不能完全照搬普兰丁格的“保证”思想,否则会有东施效颦之嫌。对比而言,两种思想的不同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超越的外在和入世的内在;第二,认知和功夫。具体来说,基督教信念最重要的特征是有一位超越的外在,即上帝。普兰丁格的整个思想其实都是围绕基督教信念中的“上帝”和“耶稣——上帝之子”所展开的,这是外在的超越。面对这个外在的超越,我们该如何认识呢?基督教提出“信”。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信任情感基础上接受上帝才行,于是“信”就成为外在的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基督教特别强调“信”作为一种情感在认识论中的作用。参见谢文郁:《道路与真理——解读〈约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为什么要“信”,或者这种“信”有理由或有根据吗?普兰丁格的“保证”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儒家在“超越”问题上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根据倪先生的说法,儒家虽然也相信“天”,但是,天却没有基督教“上帝”那样高高在上的超越位置,而是表现为“人们周围的一切自然,甚至人们自己”*[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3,173,172,172,175,171页。,于是就有了“天意就表现在民意之中”*[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3,173,172,172,175,171页。,“天”跟“人”“民”之间表现为蕴涵关系——民之所归就是天命之的表现,民之所叛就是天讨之的证据。这样,儒家和基督教信念的不同之处显示出来了:相对于基督教的超越外在,儒家表现为“内在超越性”。比如,在“于女安乎”的对话中,孔子问宰我的意思是:不管你的父母的亡灵是否存在,你吃着稻米,穿着锦罗,自己心安否? 这样,“孔子不是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外在的神灵,而是引向个人自己内在的道德情感,要求人们作自身内在的精神性的反思。通过这种反思所得到的,不是有关外在存在的知识或关于对外在神灵的信念是否符合理性的结论,而是有关自己应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知识,也就是生活之道”*[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3,173,172,172,175,171页。,或者说,对儒家来说,一个人是否对神灵有知识或理性的信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是否能够得到安宁。 所以,孔子实际上“把对外在超越的认知问题转变为内在的道德反思”*[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3,173,172,172,175,171页。。
至此,笔者认为倪先生的观察非常准确而到位。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和儒家的“内在超越”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但是,笔者不太同意倪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如果一个儒者能感受到普兰亭格所说的那种通过神灵的内在施教和由上帝的爱印刻在心里的直接经验,那么他也可以接受有关上帝存在的信念,从而成为一个儒家基督徒。虽然这两种信仰之间需要一些磨合,但并无根本的冲突。”*[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3,173,172,172,175,171页。虽然倪先生用的是假设条件句,但做出这样的论断仍值得商榷。
首先,儒家是否能接受“神灵的内在施教”(即“圣灵的内在引导”)?倪先生在“超越的外在和入世的内在”一节开头第一句话就已经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即“孔子本人对鬼神和灵魂不死的问题抱怀疑论的态度”,其根据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也就是“他不对他所不知的事情做任何猜测和假设”*[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3,173,172,172,175,171页。。普兰丁格所论述的“圣灵的内在引导”,从基督徒的生存上来说,就是要建立在基督徒的“信任”情感上,没有信任,根本就无从圣灵之说。所以,一个是怀疑态度,一个要求信任情感,生存出发点不同,怎么会没有根本冲突呢?
其次,即使儒家“与时俱进”接受了“上帝存在的信念”,他们是否接受了基督教的核心信念——救赎呢?否则,他们为什么被称为“儒家基督徒”呢?根据普兰丁格的论述,基督教信念包括有神论信念和基督教独特的部分,即耶稣作为圣子对人类的救赎。即使儒家接受了上帝存在的信念,但是不接受基督教的圣子救赎,那么,他们可能只是儒家式的犹太教徒甚至巴哈伊教徒甚至伊斯兰教徒。也就是说,是否接受基督教的救赎观,是决定儒家基督徒配不配称为“基督徒”的标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参见[芬兰]黄保罗著、周永译:《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如果不能接受,儒家和基督教势必产生根本的冲突:儒家讲的“救赎”其实是教化,即“诚之”的过程;基督教的救赎是指上帝之子的“道成肉身”,即以圣子耶稣的无罪之身“除去(或背负)”所有信徒的罪孽。
最后,如果儒家接受上帝存在、圣子的救赎和圣灵的内在引导,那么,他们称为“儒家基督徒”就名副其实了;但是如果不接受,或者仅仅接受上帝存在的信念,那么,这个称号就有点名不符实,顶多是“基督徒式的儒家”,亦即本质上还是儒家,但接受基督教的部分观点而不是全部。
此外,倪先生对普兰丁格思想的解读也有些瑕疵。比如,倪文关于孔子对“天”的认识和普兰丁格说的通过“神觉”(即神圣感应)得到的上帝知识两者之间具有若干重要的相同点,并说:“首先,它们都不通过任何间接的证据或论证,分解和综合,不基于任何概念,而直接揭示于人的心灵。”*[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5,176,176—177,177,177,181页。对于这个论断,笔者认为:“不通过任何间接的证据或论证,分解和综合”这种表述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不基于任何概念”则不能成立。普兰丁格的“神觉”(神圣感应)难道不是概念吗?“圣灵的内在引导”“保证”“恰当功能”“设计蓝图”,哪一个不是靠概念表达呢?概念表达需要遵循一定的概念定义原则,普兰丁格分析哲学的方法恰恰特别重视对“概念”的分析。儒家是不是不重视概念呢?显然也不是。比如,孔子对于“天”、对于“礼”、对于“仁”以及“诚”等都有自己的定义方式,虽然这种定义方式跟西方哲学的要求并不相同。宗教哲学关心的就是宗教知识中的概念表达,而概念表达自然有其固定的定义原则,比如,概念之间必须遵循无矛盾原则等。所以,倪文“不基于概念”的说法值得商榷。
基督教与儒家的区别还体现在“认知与功夫”上。以普兰丁格的“保证”理论为参照系,我们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儒家对于内在的“天”或“天命”的知识,能否在某种意义上有“保证”?倪文认为: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儒家对天命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主体的长期修炼才能得到”*[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5,176,176—177,177,177,181页。。对此,儒家需要有“艺术家的天赋和后天的勤学苦练”。基于此,倪文把儒家的这种认识论归到“德性认识论”的框架下来讨论,其基本特点就是“通过认知主体的德性来规范认识论,并规定信念的合理性,而非如传统认识论那样从信念本身的性质去探讨认识论”*[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5,176,176—177,177,177,181页。。以此角度为基点来看,儒家所期望的“心安”是一种境界,是人的修养功夫达到一定层次以后形成的一种深层的道德意识和素质。对此,倪先生说:“他的目标直接是人的完善和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目标要求个人充分地体认(不仅仅是智力上或甚至是情感上的认识)包括仁、义、礼、智、信在内的各种德性。”*[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5,176,176—177,177,177,181页。“体认”是一种功夫论的修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仅是要得到某种信念,而且是对信念的充分认同,一种‘达’和‘通’的自由境界”*[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5,176,176—177,177,177,181页。。这样一来,儒家对天命的认识就超出了认识论中的“真”与“假”的范畴,直接涉及道德领域的“对”与“错”、“好”与“恶”的领域。我们显然不能再用“真”来考察儒家信念是否具有保证,而是要有这种信念“是否有效”的考虑。为什么要将“有效性”作为儒家信念保证的条件呢?倪先生对此的说法是“功法的保证离不开有效性”*[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75,176,176—177,177,177,181页。。这是儒家功夫论所要求的,它并不求“真”,而是看你这种修养的“功夫”有没有效果。但是仅仅靠功效还不行,因为即使像孔子那样的圣人,他也会在生存中经历时运不济、功效不显的时候,于是孔子才有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所以,儒家的“保证”与功效有关,但不能简单归结为功效。
笔者认为,倪先生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他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信念的差异。普兰丁格认为:人对上帝的认识是通过“神圣感应”和“圣灵的内在引导”来进行的,主动权在上帝那里,人是被动的接收者,所以,从逻辑上说,圣灵随时可能降临在某人身上,从而让人认识上帝;并且基督教追求的是对上帝的心思意念,重在对上帝的“认知”,而认知的目标就是“真”或“假”;而儒家追求的是“境界论”,重在对信念的“体认”,于是功夫论成了自身修养的必由之路,这也决定了该过程需要长期的积淀。修养的“有效性”就成为儒家信念是否具有“保证”的关键一环。倪先生把孔子的思想归到“德性认识论”的框架下讨论,也匠心独运。但笔者的疑问是,孔子追求的境界是“心安”,内心宁静,在他的认识体系中,自己认定了一个道德领域的目标,然后通过修养达到了这个境界,才能心“安”,但这个道德领域的“对”与“错”、“好”与“恶”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普兰丁格的“上帝”是真理,是至善,是其信念的指向,但是儒家的“安”要在什么程度上才是安呢?比如,倪先生举例说:“如果我有一种原初的恶的情感,比如,自私或希望别人都比我差,通过某种修炼以后它成了不可抗拒的,并且相反的感觉对我来说显得荒谬,而认同这种情感使我觉得心‘安’理得,儒家可以说,因为这个信念没有达己达人的功效,所以它不能被看作是有‘保证’的。”*[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81—182,182,183,183,186页。如果这个人的修炼目标自一开始就是“恶”的,而他自己浑然不知,坚持修养,以至于炉火纯青,那么,这种功夫论修养是不是明显就“南辕北辙”了?所以,道德领域的“对”与“错”、“好”与“恶”只能是在一种共识或传统意义上认定的标准下才能判断,并不能以个人的喜好作为标准。倪先生对此应该有更多更深入的表述。
三、儒家思想是否具有“保证”?
倪文还注意到基督教和儒家具有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区别,力图重新审视普兰丁格的“保证”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儒家所能接受的“保证”概念。
第一,从设计蓝图看。倪文认为,普兰丁格使用这个术语并不妥当,因为给人的印象是“预先假定了产生有保证的信念的官能必须是由一个有意志有智慧的创造主所设计制作的”*[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81—182,182,183,183,186页。。他认为:儒家所讲的人“心”可以作为官能,因为它既可以是自然生成的,也可能是人长期修炼的结果;而且,“由于心比口对人来说更为核心和根本,更体现人与禽兽的不同”*[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81—182,182,183,183,186页。。
第二,从朝向真理看。对于朝向真理的“设计目的”而言,倪文认为,可以按照儒家的思想把这个术语改成“生成的目标(the ends of becoming)”,这样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原因在于“目标”一词,既可以表达有目的的意志,也可以指自然生成之物的本性或自然倾向,而“生成”一词进一步明确这目标指的就是动态的趋向。“这样就不一定是预先存在的某种本质,它还可以包括经主体自我抉择而体认,经过学习、修炼而生成的内容。当然,这样的表述也允许基督教的信奉者把事物的生成目标看作是神的设计目的。”*[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81—182,182,183,183,186页。换句话说,这样的术语改动,既能迎合儒家的功夫论,又能适应基督教的设计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设计目的”涉及外在的超验的设计者,所以无法经验地直接获知;而事物的生成目标则在经验世界之中,是可能通过经验或多或少得到验证的。
第三,从适宜环境看。根据儒家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最适合于人求得至善、达己达人的环境。在儒家看来,人心对于天命的认识或体认天命,也有环境的要求。这种环境既有自然环境(如“夜间诸缘放下,尘虑不起之时,人更容易深入内心”),又有社会环境(如“孟母三迁,择邻而居,为的是寻找适合孟子成长的环境”);但更重要的是指社会环境,包括内修和外交两个方面。“儒家的‘慎独’决非孤绝超伦的特性的追求,而是通向普遍人性之中的实在的精神性的修炼方法,是从个人内在中‘转出’普遍性、共通性的途径。反过来说,越深入到社会中也就越能洞见人性,成就人性的完善。”*[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81—182,182,183,183,186页。通过这样的解释,倪文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把合适的环境作为其信念的保证条件,但这里的“保证”类似“功法指导”,即“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条件,就不可能有对天命的充分体认”。
第四,从恰当功能看。在普兰丁格看来,它指的是认知官能的不失常。倪文认为,普兰丁格所使用的神圣感应作为认知官能本身就是无法确认的,而且,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其功能是否正常。儒家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儒家的“心”指的是广义的认知、感觉和意志官能,而“心”的恰当功能的发挥,“恰好可以用儒家的一个核心概念‘诚’字来表达。人心之达到‘诚’和‘尽其心’的境界,就是它恰当发挥其功能的状态”*[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87,187,191,191,191,189页。。
经过分析,倪文给出了儒家式的保证信念,其大致表述为:“一个信念只有当它是其目标就是为了体认达己达人的天命而成功生成的人心(无论是自然的生成还是修炼的结果)在必要的环境条件下在‘诚’的意义上恰当地发挥其功能所产生的,才是有保证的。”*[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87,187,191,191,191,189页。很明显,这个儒家式的“保证”概念更强调主体性,而不是符合论意义上的客观性,体现出儒家和基督教的根本区别。
笔者认为,倪文以普兰丁格“保证”学说的四大条件为参照,依据儒家的特点对其进行相对本土化的“改造”,一方面把握住了儒家的人“心”作为体认官能(相对于普氏的认知官能),指出其目标是“为了体认达己达人的天命”(相对于朝向真理);另一方面强调了合适环境(既包括慎独式的内修,又包括深入社会的外交),恰当功能体现为在“诚”的意义上恰当发挥其功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儒家特色的“保证”概念,既强调了儒家的主体性,又体现了其功夫论的目标。要说缺点,这个定义未免过于笼统。比如,“达己达人的天命”“必要的环境条件”等表达非常模糊,要让别人接受,还需精雕细琢才行。毕竟,普兰丁格对这四大条件都给予了充分的解释和说明,这也是其“分析哲学”方法论的要求。此外,“在‘诚’的意义上恰当发挥其功能”,什么是“诚”的意义?为什么要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恰当发挥其功能?如果解释不清,势必让人疑惑。我们把它们当作问题抛出,希望得到更多儒家学者的关注。
四、宗教的多元主义和对话
倪文还谈到宗教多元和对话问题。普兰丁格是排他主义者,并把排他主义理解为:有一种人在对其他宗教及其信仰者的智力、道德、精神境界等有充分认识和反思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认为任何与他的宗教不相兼容的信念是错的。为此他遭受了很多批评,然而,他没有回避别的宗教信仰者对他的挑战,而是积极回应。倪文则认为:虽然“儒家学者在总体上仍然缺乏和别的宗教传统展开积极对话的动机和兴趣”*[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87,187,191,191,191,189页。,但“儒家思想的基础允许它比其他一些宗教文明更容易进入积极的对话”*[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87,187,191,191,191,189页。。这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开放的自我批判”。倪先生认为:孔子“从来不把自己当做先知先觉的‘教主’或者‘天’的代言人……他也不声称自己永远正确,他能坦承己过,并身体力行地‘过勿惮改’”*[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87,187,191,191,191,189页。。这种“开放的自我批判精神”不是单纯的自我否定,而是更新自己、成就自己,是儒家“为己之学”的一部分。
笔者赞同倪文对普兰丁格排他立场的分析。很明显,倪文体会到普兰丁格为什么持宗教排他主义的原因:“仅仅是在面对不同的信仰体系中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一定是反理性的。”*[美]倪培民:《于女安乎——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前揭书,第187,187,191,191,191,189页。换句话说,普兰丁格的“排他主义”旨在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固守我的宗教信念的前提下,为宗教对话寻找一个“理性”的解释。只要能够对于来自其他宗教的挑战给出合理的解释,我就不必放弃自己的宗教立场。放弃自己的宗教信念毕竟等于放弃自己的生存方式,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因而,只要我能够在“标”——“理性”上来解释其他宗教,我就可以不伤害我的“本”——宗教情感,从而不损害我的生存*关于普兰丁格的“排他主义”,参见孙清海:《多元与排他:生存视角下的宗教对话的可能性问题》,《基督教思想评论》第18辑(2014年),第197—206页。。
倪先生认为儒家属于例外,原因在于儒家的开放性或包容性。也就是说,儒家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是那么强烈,认为自己有可能是错的,并且常有“自我批判”精神。如果真如倪先生预测的那样,儒耶对话就简单得多了。比如,儒教徒和基督徒相遇,双方各自坦承自己的信仰立场。儒教徒“虚怀若谷”,静静倾听,并能积极思考:这个基督徒论述的角度的确给我们儒家以新的内容,或许我们儒家的确该在这个方面(比如基督教的救赎观念)有所改进。这种谦虚的包容态度和“开放性的批判精神”,一定会使儒家不断吸收新的因素和新的血液,不断更新自己。基督徒也会静静倾听来自儒家的意见,但他会思考: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今天通过儒教徒对我说话,到底对我的生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上帝通过这个儒教徒对我的严厉批评,到底要对我说什么呢?这样,他会把来自儒家的意见纳入自己的信仰体系之中。这样的宗教对话是在固守自己的宗教情感的前提下,在理性层面上寻求解释。
但是,环顾现实,倪先生的设想过于乐观。原因何在?蒋梦麟对于佛教和基督教入华的不同情况,有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中国的,耶稣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蒋梦麟:《西潮》,沈阳:辽宁出版社,1997年,第2页。。“炮弹上的耶稣”形象深入人心:基督教是伴随中国近代的屈辱史传入的,“洋教”的帽子到现在也没完全摘去;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于基督教的强势传入和“排他主义”的立场深表反感,“保卫中华文化”的忧虑意识被激发起来,基督教与儒家在文化差异、政治秩序及主权意识等方面都存在张力和冲突*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台北:久大文化,1992年,第116页。,更加剧了这种忧患意识。黄保罗曾谈到儒耶对话目前面临的四大障碍,包括神学层面(一元论的天人合一)、信仰层面(基督宗教是精神鸦片)、政治层面(基督宗教是政治稳定的隐患)、伦理层面(基督宗教的上帝概念与儒家伦理的冲突)*[芬兰]黄保罗著、周永译:《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前揭书,第242—262页。。这些观点虽是一己之见,但比较全面地诊断了儒耶对话的症结所在。病因找到了,“药方”在哪里?这值得每一个关注宗教对话、关注中国人自身生存的专家学者共同深思!
总结起来,倪先生对普兰丁格的保证思想做了儒家式的回应。他从“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认知与功夫”“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宗教多元主义与对话”等四个方面指出了基督教与儒家的不同特点,并且针对普兰丁格提出的保证的四大条件,相应提出了儒家的观点,并给出儒家式的“保证”概念。倪文的结尾说,他的回应是一个探讨的过程,而不是终极的结论。从儒学的复兴与创新离不开哲学、宗教等层面的争鸣与争辩看,本文更是探讨,而不是结论——结论只存在于人们寻找文化家园、信仰真谛的永恒思考之中。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赵洪艳】
*收稿日期:2015—10—16
作者简介:孙清海,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济南 25001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