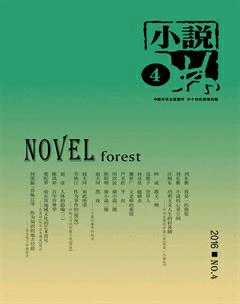百年许粤华
陈凤翚
关注缘由
关注许粤华女士的原因,是她和黄源结婚后,留有两男两女,女孩一死,一找不到下落。存世仅为两个儿子。长子黄伊凡,是我多年同事和朋友,又住前后院,是近邻,多有往来。
黄伊凡做人低调,极少谈及家庭。问及其父黄源时,往往淡然一笑了之,更绝少谈到母亲许粤华女士。
我在阅读中,从鲁迅、巴金诸多文学巨匠乃至东北作家群作家二萧的文字里,常常遇到许粤华名字和行止,多为片段,语焉不详,难以串联在一起。伊凡赠书《黄源文集》(1-7),《鲁迅致黄源书信手迹》《黄源影集》《黄源回忆录》,仔细阅读,反复琢磨,又参照巴金等人文字,许粤华一生曲折跌宕的经历,便不时萦绕脑际,其人生遭际,也是时代的折射,历史的照影。
2010年伊凡从美国发回邮件说,此次专程赴美,看望母亲,还传来几幅照片,留下他们母子相聚的幸福微笑。次年许粤华女士即告别人世。从1911年出生, 到2011年5月16日逝世,恰好走过人生一百年。百年称为“人瑞”,已经难得。对已过八旬的伊凡来说,仍然悲痛不已,他对异父同母的妹妹黎慰之说:“惊悉妈妈去世了。妈妈百岁高龄,有你们在跟前,她是带着欢笑、无忧无虑地走的。我这次来美,有幸看到了她的笑容,听到了她的歌声和对我的呼唤,有幸在今年的母亲节发了最后一个贺卡,我发贺卡的时候就曾想,妈妈还能收到我几个这样的贺卡呀…… 才几天,她真的平静安然地走了。现在我没有妈妈了!”我仿佛看到伊凡凄苦的面孔!
2013年一个夏日晚上,伊凡送来《黄源楼适夷通信集》上下册,我们随即交谈起来,我又问及伊凡母亲,那天伊凡谈兴甚佳,印象最深刻者,是伊凡强调,母亲信教,是为精神安宁,心灵平静。这或许可以解读许粤华后半生。
送走伊凡,我在灯下反复思索,许粤华已经走进历史。虽然没有黄源和黎烈文那样声名显赫,且早早淡出文坛,皈依宗教,希望被忘记。可是,当翻开二十世纪波澜壮阔历史,那位曾经驰骋文坛多年,王西彦赞誉为“性格上温柔,为人通达,言谈风趣,人们都喜欢和她接近,她是那种赢得别人善意和好感的妇女”,这位编辑、散文家、翻译家,影像依稀可辨,她不应该被遗忘。
鲁迅赞誉
许粤华,笔名雨田,浙江海盐人。她是著名英美文学翻译家许天虹胞妹,也是一位编辑、翻译家、散文家。
黄源(笔名河清)和许天虹同学,常到许家,有机会与许粤华相识。1926年,许粤华毕业于嘉兴秀州女中,在海盐城隍庙女子高等小学教书。黄、许因相识而相恋。经许父母认同,于1929年夏结婚。这是一对志同道合,自我选择的美满婚姻。他们的写作也进入最佳时期。
为攻读日语,许粤华1935年夏到次年8月,去日本留学一年。回国后,在吴朗西、巴金、伍禅、陆蠡等人创办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参加《少年读物》(半月刊)编辑、校对工作。
此间,许粤华发表译作有:日本鹿地亘的《鲁迅的回忆》,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秋田雨雀的《高尔基之死》,高尔基的《海燕》等等。
因为黄源和鲁迅关系密切,许粤华也和黄源一样尊敬鲁迅,热爱鲁迅,来往较多。
鲁迅先生生前不止一次提及许粤华,称颂同为翻译家的雨田甘为夫君黄源“作嫁衣裳”的贤妻之举——为代鲁迅主编《译文》杂志的黄源先生夜以继日誊抄稿件。鲁迅还说:“雨田的字比你(河清)的要好!”翻阅《鲁迅日记》:1935年7月11日,1936年3月22日,4月7日和24日,9月2日,五次提及“雨田”。
《鲁迅书信集》有致许粤华信件。那时她在日本留学,1936年鲁迅曾写信托她代购想要的书刊:
粤华先生:
顷收到来信并《世界文学全集》一本。我并非要研究霍氏作品,不过为了解释几幅绘画,必须看一看《织工》,所以有这一本已经敷用,不要原文全集,也不要别种译本了。
英译《昆虫记》并非急需,不必特地搜寻,只要便中看见时买下就好。德译本未曾见过,大约也是全部十本,如每本不过三四元,请代购得寄下,并随时留心缺本,有则购寄为荷。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三月二十一日
鲁迅葬礼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伟大鲁迅逝世。《黄源回忆录》记载,清早,内山书店的伙计送来鲁迅逝世的噩耗后,黄源即偕同妻子许粤华急速起身,坐上报丧汽车,顺路带上萧军,赶往大陆新饰的鲁迅家中,直奔二楼,鲁迅先生已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此时宋庆龄、冯雪峰、周建人、许广平正在三楼商议治丧委员会名单。当天下午,鲁迅先生的遗体移至万国殡仪馆。三整夜都由胡风、黄源、许粤华和萧军在殡仪馆值夜守灵。
胡风《关于鲁迅的丧事情况——我所经历的》说:只剩下我和黄源、雨田(许粤华笔名)、萧军四人负责照料守夜,就在遗体前面地毯上打地铺睡……治丧处事实上由我负责,但并没有任何名义。工作人员,只有黄源、雨田和萧军在殡仪馆经常在一起,但没有任何的名义……我领的一包钱是当作零用支出,由雨田记账。黄源、许粤华、萧军等同为“鲁迅先生治丧办事处”三十多名成员之一,许粤华参加鲁迅丧事的全过程。
黄源说:“鲁迅遗体从家里移到殡仪馆后,萧军跪在殡仪馆里的时候,我和夫人许粤华,萧军,还有胡风,四个人。第一夜在殡仪馆里可能还有周文。”
《痛别鲁迅》记载,送别鲁迅那一刻,许多人在许广平和海婴后面沉默而悲哀地送行,“雨田的哭泣声打破了沉默,忍不住的悲痛袭上心来,送行人哭成一团……”
在编辑《鲁迅纪念集》时,许粤华负责“函电的选录、签名、丧仪等统计”工作。
许粤华是为鲁迅守夜、送别乃至编辑纪念集的少有的女性之一。
中途分手
战乱,给黄源和许粤华婚姻带来不幸。除去离别与逃难外,还有道路的选择,终至婚姻破裂,最后分手。
鲁迅逝世后,黄与许本来计划到乍浦,闭门译作。中途却遇到麻烦。送别他们的萧乾,赠给许粤华一本《抗日歌曲集》,竟为当地所禁,一再盘查追问。他们无法在那样环境下工作,再次回上海,仍想继续闭门译书。
此时,“七七事变”,战事爆发,许粤华回老家海盐。又逢黄源父亲逝世,也回老家办理丧事。战火步步紧逼,一家七口(老祖母,母亲,妻子,三个孩子,最小女儿海伦刚刚三岁),需要迁往乡下,黄源先把家眷送到祖母娘家——吴家浜。从此,他们一家开始漫长逃难生活。
先和姨家、舅家共三十多口人转移到萧山,黄源母亲提出:“一家人分两块好,你,粤华和伊凡三个人走。我和一个孙子,一个孙女留萧山。”
黄源和许粤华带着伊凡,经南昌到长沙。在那里生一女婴,因无力抚养,四天后送给育婴堂(解放后也没有找到)。他们又商定,许粤华和伊凡留在长沙。黄源再回萧山,寻找母亲。
黄源没有找到家人,妹妹也失去联系。黄源遂走上抗日前线。1937年11月10日在《赴火线去——临别给亲友家族》说:“粤,你最了解我,我不必絮絮多说。我只希望你产后休息一时,也能上前线来。”
黄源去前线,无力顾及家事。许粤华1938年去广州,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工作,当时,巴金、章靳以也在那里。广州连遭日机轰炸,秋天,许粤华带着伊凡从香港去上海,留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伊凡念小学。
1939年4月,闽西北万山丛中小城永安,涌现一批新闻出版机构,其中佼佼者便是改进出版社,黎烈文应省长陈仪之约,主编综合性政论刊物《改进》,吸引大批有名望的学者、作家、记者如郭沫若、巴金、老舍、艾青、朱自清、冯雪峰、何其芳、马寅初、胡愈之、戈宝权、章乃器、宋之的、萧乾、范长江等等,《改进》还刊登译文,出版“苏联建设介绍专号”等。
1940年春,许粤华致信黎烈文,要求参加改进出版社工作,得到赞同。她把伊凡送到浙江嵊县农村祖母处,安顿好即南下,去永安,找到黎烈文,参加改进出版社,出任《现代儿童》(月刊)主编。
1941年1月“皖南事变”,黄源经过九死一生,终于突围。 1941年4月中旬,黄源到上海等待安排去苏北时,收到已在福建的许粤华来信说:我们离别已数年,各自找到生活的所在,今后彼此分离各走各的路吧,永别了吧。
黄源收到信后,也发一回信:你的宣告分离的永别信收到了,我永远感激你。我们曾有过十年春天的幸福,但幸福被战乱打碎,被迫分离,现在我只能尊重你的自由。我邀你同去的地方,并不是现存的福地,需要艰苦的创业,你不去也就罢了。我唯一可告慰的是鲁迅逝世后,国难又当头,我终于找到了那条正确的道路,我将继续地走下去。永别了。
许粤华的两个儿子,在离乱中,由祖母和姑姑照料,备尝艰辛,读完大学,他们的姑母为抚养他们,终生未婚。
我想,处于战乱年代,关山阻隔,长久分离,他们分手或许是一种无奈选择,今天的人们会理解。
远走台湾
黎烈文(1904-1972)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曾主编《申报》 “自由谈”,得到鲁迅、巴金等著名作家大力支持。鲁迅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所有文章,皆经黎烈文手刊出。
黎烈文原配夫人严冰之生黎念之后病逝,八年后和许粤华结合。
1946年春,黎烈文应台湾省长陈仪之邀,去台湾,曾担任台湾省编译馆编纂,《台湾新生报》副社长,台湾省训练团高级班国文讲师等职,执教二十余年。
许粤华随黎到台湾,继续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翻译有日文版《“台湾”乡镇之研究》、《十七世纪荷兰人在台湾的探金事业》等,并在《公论报》副刊《日月潭》等刊物发表散文。
巴金《怀念烈文》否定黎烈文是“反动文人”一说,也涉及许粤华。1947年初夏,巴金“到过台北,去过黎家”,“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夫人)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文中还说:“雨田也搞点翻译,偶尔写一两篇小说,我离开台北回到上海后,烈文、雨田常有信来。”
旅台三十年,黎烈文虽多次受到政治牵连,为当局传讯、审查,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节操。
当年有一份报道说:“晚报报道黎先生卧病的消息以后,曾经有些机关派人前往送钱,深知黎先生为人的黎太太怎样说也不接受。……我觉得这正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风范。”这里透露出许粤华的人格与操守。
黎烈文于台湾逝世后,许粤华随两子一女到美国定居。从此淡出中国文坛。
许粤华悉心照料严冰之留下长子黎念之,还有亲生的女儿黎慰之,次子黎忍之。她精心培养三个孩子。
长子黎念之,是化工分离专家。他是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90年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1996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8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获得被誉为化学工业界诺贝尔奖的普金奖章,他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获此殊荣的华人。2001年荣获世界化工大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1998年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友谊奖。黎念之一直铭记父母饮水思源教诲,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关心国内科技事业的发展。
黎慰之,黎忍之也在美国读书,获博士学位,可谓学有所成。
皈依宗教
五十年代初,许粤华皈依耶稣教。
从她的自述及信件里,可知她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她多次说:开始信主以来,不但确知我将来的去处,而且日常生活中也有平安喜乐。
1986年4月11日信里说:真是逝水年华,你我都已是望八老人了。兄已七十有九,大概孩子们一番孝心,邀请二老去北京度八十大寿吧?我年轻时多病,自忖活不到四十,信耶稣后很少忧虑,今年也已活到七十五,而且精神还相当好,可以和年轻人一样地上街购物并挤公共汽车。
1992年1月16日信中说:我虽未改换名字,但过去的我早已与基督同钉同埋,如今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的青年时代是因偏行己路而非常痛苦的,实在不堪回首! 若不是五十年代起信了耶稣,若不是因信获得她复活的生命而成了新造的人,我早已不在人间了。我与“过去”已完全断绝关系,请恕我不再谈那些伤心事。
许粤华一生,饱经战祸,家人离散,与儿女生离死别,感情折磨,精神伤害,人世冷暖,种种煎熬,作为感情丰富的女性,怎样摆脱?正如伊凡所说,她皈依宗教,无非摆脱精神痛苦,以求心理平衡。
世纪聚首
许粤华虽然笃信宗教,却依然怀念故国以及亲人与故旧。
1989年,许粤华携女儿黎慰之,回国访亲探友。这时许粤华离开大陆已近半个世纪。
黄源没有忘记许粤华,《黄源文集》多次提及。1981年3月9日,致巴金信中说:“粤华已有信给伊林,我还没有给她写信……”
这一年的6月17日,黄源给匡达人信中说:“你去美国,能会到许粤华,我非常高兴,感谢。我们只是因战事而分离的。我想托你带一点儿龙井茶叶给她。月底前设法送到你处。”
6月24日再次写信说:“托我女婿送上二罐龙井茶,烦请你带给许粤华”,“请你多问候她。我们只因战争(我去新四军了)而分离的,现在虽则各自成家,但谁也没有负谁。请你多了解她在美的一些情况,你回国后,我专诚(程)去看你,了解她的情况。致粤华短简,请面交。”
6月26日又写信说:“托我女婿周赫雄送上信和茶叶,谅已收到吧。兹将许粤华地址抄奉,如不远,有便请走一趟,万分感激。”
9月28日再次写信:“首先谢谢你为我效劳,虽没有会见粤华,但已将她的近况告知,非常感谢。我也不敢再打扰她。她给我一信,托巴金转交的,也是这个意思,只要她生活和健康都很好,我挂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许粤华回国后,有两次集会,值得一说。
一次是和巴金相会。黄源和黎烈文,都是巴金挚友,许粤华又在巴金办的出版社有共事之缘,自然也是巴金的好友。许粤华1989年到上海,会见巴金。黄源回忆说:“杭州正是春夏之交,蓝天碧水,翠柳飘舞,百花齐放。我的前妻许粤华由女儿黎慰之陪同,回到阔别半个世纪之久的祖国,看望儿子和旅游。”他们先到华东医院看望老巴金。巴金和他们一起参加了鲁迅的丧事。老朋友重逢,气氛非常热烈,许粤华的几个子女也在场。当时除了聊天、谈往事之外,许粤华还很想说服老巴金皈依到“主”的脚下。她恳切地说:“老朋友,你看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就是还缺一样,你没有主;有了主,一切就都完美了……”老巴金始终笑着,却没有答应。
后来巴金给许粤华一封信说:“我想得到,你不满意我,不肯伏倒在‘主的面前,向他求救,我甚至不相信神的存在!对,你不能说服我,但是我不会同你辩论,我尊敬你,因此我也尊敬你的信仰。我愿意受苦,是因为我愿意通过受苦来净化心灵,却不需要谁赐给我幸福。事实上这幸福靠要求是得不到的。正相反,我若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美好的东西献出来,献给别人,我就会得到幸福。”最后说:“我有我的‘主,那就是人民,那就是人类。”
一次是和黄源夫妇见面。《黄源回忆录》说:“她们的到来,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大家热情接待”,“在杭州住了几天,我和一熔给她们送花,请她们吃饭,和她们谈天,慰之还到我家中来看藏书。我给她们提供一些黎烈文的资料。”“我和粤华彼此都进入高龄,我们把她作为老朋友,向她们介绍新中国的许多情况,帮助她们了解国情。大家共同度过了一周难得的愉快时间。她看了新中国,看到两个儿子也都大学毕业有了工作,有美满的家庭,也放心了,高高兴兴地回去。”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为了迎接分别近半个世纪的母亲,伊凡请假从哈尔滨到上海同弟弟伊林一起去机场去接她。当时正遭遇“六四”,陪同她在上海拜访巴金、吴朗西夫妇等老朋友后,费尽心机,买了三套车票,历经艰险才到杭州;原本她还打算同伊凡一起北上,来哈尔滨看看他的家,也只好作罢,不得不改道从杭州经香港直接回美。
那次见面他们母子的感情波澜、内心的激荡,不言而喻。许粤华返回美国后,写信给陈瑜清说:“只是此番我和慰之回来为期太短,实在不胜遗憾!”在这些遗憾里,肯定包括哈尔滨没有成行,和儿子相处时间不够。
遗 著
许粤华出版的书籍:
译作《书的故事》(新生命书局出版, 1931年12月),《十诫》(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0年3月),短篇集《罪》(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 1941年11月)。
战前在上海《译文》上发表有日本鹿地亘作《鲁迅的回忆》和内山完造作《鲁迅先生》(新二卷,第一期, 1936年9月);秋田雨雀作《高尔基之死》和苏联M·高尔基作《海燕》(新一卷,第一期, 1936年6月);昇曙梦作《普式庚与拜伦主义》和中条百合子作《玛克沁·高尔基的一生》(新二卷,第二期)等。
她在福建永安翻译出版谢德林寓言《诚实的野兔》,盖达尔《白季迦的秘密》多种。
她的散文成就较大,如《母亲》《雨》和追念陆蠡的散文《期待着你回来》等,大多描写自然景物,倾诉心灵乐曲。她以细微妍丽的文笔追溯自己的童年生活,反刍人生,她善于运用景色和氛围烘托寂寥及怀念的心情,文笔工整精致,富有节奏感,同抒情旋律相适应。
去台湾后,也翻译了有关日文版《台湾乡镇之研究》《十七世纪荷兰人在台湾的探金事业》等文章,并在《公论报》副刊《日月潭》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