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印度人与中国人形象
张之燕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7)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印度人与中国人形象
张之燕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7)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多处出现过印度人和中国人。二者皆为富有的化身,同时也被赋予卑贱狡猾和欺诈性等反面色彩。英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一方面想与印度拉近距离以追求财富,另一方面又惧其诱惑性与危险性,所以将其与欺诈性相联系。中国人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尤其是《第十二夜》中是正面的,可是却被18世纪Steevens等学者注解为小偷和骗子之流。究其原因,一是一些词语存在多义性,如cunning,dexterous等常被用来形容中国人的词语含有多义性,容易被人片面地解读和利用;二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Cataian”本身具有模糊性;三是特殊时期一些人心存偏见乃至别有用心,从Steevens的注解可见一斑。综而观之,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形象是西方人基于自身利益对二者进行的想象和曲解。
莎士比亚 中国人 印度人 富有 欺诈
莎士比亚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不但美洲大陆被发现,而且遥远的东亚诸国在西方人眼中也不再只是梦幻般遥远的国度。在这个连伊丽莎白女王都想写信给中国皇帝的时代,作为文学乃至文化大师的莎士比亚也很自然地在其作品中涉及到了一些南亚、东亚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形象研究即为本文的重心。
“Indian”一词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出现过八次。包括“India”在内的相关的词语也多次出现。与“Indian”相比,“Chinese”一词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从未出现过,而相关的单词“China”出现过一次,可是指涉的并非中国,而是瓷器。不过,莎士比亚倒是在其《第十二夜》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提到过“Cataian”,它指的是“契丹人”,蒙古语中的契丹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等同于“Chinese”。在方平主编的《第十二夜》译本中,“Cataian”就被译作为“中国人”。本文也将“Cataian”等同于中国人,并基于此来勘探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印度人与中国人形象。
一、印度人:富有、虔诚、执迷、卑贱且有欺骗性
“Indian”在八个文本中出现过,其中有三个指涉印度人,另外五个很有可能指的是美洲印第安人。这源于哥伦布的一个错误认知。哥伦布探险时发现了美洲大陆却不自知,而把它误认作印度,因此就把当地人称为“Indian”,以后便以讹传讹。后来为了区分印度人和美洲“Indian”,便有了“东印度人”和“西印度人”之称,西印度人也即现在我们所称呼的印第安人。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剧中福斯塔夫就提到过东印度与西印度。
本文要分析的“Indian”是印度人,但是因为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Indian所指仍然含混难辨,其作品里的Indian有时可能也是指印第安人。不过,由于英国已经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与印度交往更多,莎士比亚文本中的Indian指涉印度的可能性更大。
从“India”和“Indies”所在文本的语境来看,印度是一个珠玉宝石琳琅满目的富有国度。不管是东印度还是西印度,他们在欧洲人眼中都是遍地黄金之所,是取之不尽的金矿。掌管家庭财务的培琪夫人与福德夫人即被福斯塔夫视为东印度和西印度,他贪婪地打着两位夫人的算盘,说道:“我要去接管她们俩人的全部富源,她们俩人便是我的两个国库;她们一个是东印度,一个是西印度,我就在这两地之间开辟我的生财大道。”①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卷第493页。本文参考的是朱生豪与方平的译本,当取一种翻译的时候,默认的是朱生豪的版本。福斯塔夫将富有的夫人们比作东西印度形象地折射了当时整个英国社会对东西印度的想象,也不乏觊觎与垂涎。
“Indian”一词也多处指涉印度的富裕。除此之外,Indian所在的三个语境构筑的印度人也有另外几种特征,即虔诚、执迷、卑贱且有欺骗性。《终成眷属》中海伦娜的话语昭显了印度人虔诚和执迷的特征。
原文:


朱生豪版:
海伦娜:我知道我的爱是没有希望的徒劳,可是在这罗网一样千孔万眼的筛子里,依然把我如水般的深情灌注下去,永远不感到枯涸。我正像印度教徒一样虔信而执迷,我崇拜着太阳,它的光辉虽然也照到它的信徒的身上,却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②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卷第405页。以下再次引用此译本时仅在引文后标出卷数和页码。(第2卷,405)
方平版:我正像印第安人,错误中也一样虔诚;我崇拜太阳,它照耀在它的信徒的身上,却一点也不理解信徒的心。(461)
这是海伦娜向罗西昂伯爵夫人吐露她对夫人之子贝特兰的爱慕时所说的一番话。她将自己对他的爱比作太阳,而她自己则似一个虔诚的印度人,爱恋着无视她的爱的太阳。“错误”可能从某种程度上也暗示印度人执迷的特性。朱生豪将“Indian”译为“印度教徒”,而方平却将其译为“印第安人”。正如前文所述,根据历史语境,笔者更倾向于朱生豪的翻译,将其视为印度人。虔诚和执迷也隐含着一份不为他人理解的执迷不悔。这里,海伦娜作为一名女性,一名“像印度教徒一样虔信而执迷”的女性崇拜着太阳般的男性,不但体现了当时女性相对卑贱的附属物般的地位,也很可能隐射了印度在权力关系中所处的类似的从属地位。
如果说从海伦娜的话语中来推断印度处于卑贱地位有牵强之嫌的话,那么《奥赛罗》中的一段话多少能澄清这种嫌疑。
原文:

朱生豪版:
奥赛罗:你们应该说我是一个在恋爱上不智而过于深情的人;一个不容易发生嫉妒,可是一旦被人煽动以后,就会感到极度烦恼的人;一个像那种糊涂的印度人一般,把一颗比他整个部落所有的财产更贵重的珍珠随手抛弃的人。(第5卷,512)
方平版:
奥赛罗:这样,你们就得说:这一个人用情太深,却又不善于用情;这个人不容易嫉妒,可是一旦起了疑心,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个人就像那些愚蠢的印度人,把一颗珍珠随手扔了,想不到它的价值胜过了他整个部落。(519)
方平将“the base Indian”中的“base”一词译为“愚蠢的”,朱生豪也将其译为类似的词语,即“糊涂的”,笔者认为除了此层含义之外,“base”一词还含有“低贱”之意。因为在“Like the base Indian,threw a pearl away/Richer than all his tribe”这句话中,印度人处于和珍珠的对比关系之中,既然珍珠很贵重,那么印度人不免就是低贱的,更何况“base”一词本身就有“低贱”之意。不管“base”究竟何所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它是一个贬义词,显示对印度人某种程度的嘲讽和歧视。这种歧视和偏见在《威尼斯商人》中亦有体现。
原文:

朱生豪版:
巴萨尼奥所以装饰不过是一道把船只诱进凶涛险浪的怒海中去的陷人的海岸,又像是遮掩着一个黑丑蛮女的一道美丽的面幕,总而言之,它是狡诈的世人用来欺诱智士的似是而非的真理。(第1卷,436-7)
方平版:
巴珊尼 所以说,“打扮”好比那陷人的海岸把船只引进了风紧浪高的海洋;像鲜艳的面巾罩着印度的美女。一句话,这些都是狡猾的圈套;以假乱真,好蒙蔽最聪明的人。(第3卷,73-4)
巴萨尼奥使用了一个平行结构,将“Thus ornament is but the guiled shore/To a most dangerous sea”与“the beauteous scarf/Veiling an Indian beauty”并置,从中,读者可以看到对应关系。外在的装饰被视为引诱船只进入险境的“陷人的海岸”,“美丽的面幕”被比作“陷人的海岸”,那么被比作“凶涛险浪的怒海”的“Indian beauty”必不会是一个美好的形象。方平将其直译为“印度的美女”,朱生豪则根据语境将其意译为“黑丑蛮女”。即便不是“黑丑蛮女”,从平行结构、对比关系和比喻来看,“Indian beauty”无疑也是具有贬义的,是与真正的美女背道而驰的一个形象。从“The seeming truth which cunning times put on/To entrap the wisest”这句归纳性的话语可以看出,至少此处“印度的美女”具有不美、危险性和欺诈性三个特点。这是审美差异所致吗?笔者认为,“印度的美女”所暗含的这些特征不是客观存在的,她是被西方观察者审视的一个客体,一个他者,这些特征是审视者基于自己的理解、利益乃至偏见赋予客体的。
不管是《皆大欢喜》中虔诚而执迷的印度人,还是《奥赛罗》中愚蠢低贱的印度人,抑或是《威尼斯商人》中黑丑且有欺诈性的“印度的美女”,他们都不是指涉某个具体的印度人,而是泛指印度人,且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贬低和歧视的意味。按照萨义德《东方学》中体现的观点,19世纪所有有关印度的学术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都被一些显而易见的政治事实所玷染、所控制、所侵犯。①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页。其实有关印度的学术知识被政治事实所玷染的情况不止存在于19世纪,莎士比亚关于印度的知识也无疑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事实所影响。譬如,英国成立的东印度公司为其了解印度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一方面,印度作为绽放异彩的他者,其丰富的物产资源等使其极具吸引力,另一方面,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认识的加深,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发现其差强人意甚或愚蠢低贱的一面。黑丑且有欺诈性的“印度的美女”也许并不只是指涉印度的美女,她更像是一个隐喻,隐喻一个神秘富有但又潜具危险性的国度。这些对印度的多维度的认知,包括偏见,在伊丽莎白时代不断传播,当然也就多多少少地浸染到一代大师莎士比亚。
其实,很多东方国家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被观照、审视的他者,也是一面镜子,镜子里映照的其实是西方人对他者的想象,而非他者本身,所以镜子里呈现的时而是天使形象,时而是恶魔形象,大多时候既是天使亦是恶魔。《威尼斯商人》中的“Indian beauty”理应是天使,却被勾勒为潜在的恶魔——理应是“印度的美女”,却又同时被赋予诱惑性和危险性的特征,这种特征甚至淹没颠覆其美丽性,使其转而变为“黑丑蛮女”。从某种程度上被恶魔化的不止是印度人,中国人也未曾幸免,只不过中国人的形象经历了一个被丑化的过程,从伊丽莎白时代的正面为主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反面为主。
二、中国人:富有与美德并具,灵巧与狡猾莫辨
如前所述,“Cataian”一词在莎士比亚著作里出现过两次,即《第十二夜》与《温莎的风流娘儿们》。②在早期英语文本中,仅“Cathay”一词就有十多种变体,包括“Cathaie”,“Cathaye”,“Cathaio”,“Cathai”,“Cataya”,“Catay”,“Catai”,“Kythay”,“Katay”and“Kithai”等,所以在有的版本里读者看到Cathaian的拼写方式也不足为怪。Cataian准确来说,指的是蒙古语中的契丹人,可是方平和朱生豪的翻译却大相径庭。方平将其译为“中国人”而朱生豪则译之为“骗人虫”。不过,朱生豪将“Cataian”视为骗人虫也不是闭门造车,他极有可能受到西方莎学专家的影响。18世纪编著莎士比亚作品的著名学者 George Steevens曾把Cataian标注为“小偷”,“恶棍”,以及“骗子”,在稍长的版本里还这样标注:中国人(古时候被称为Cataians)据说是手指灵巧的族裔里最手巧的(译者注:多婉转地指称小偷或骗子);③William Shakespeare,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the Johnson-Steevens edition,1995,P.265.Robert Nares更为激进,他直接将中国人与“手指灵巧的偷窃”相提并论。④Robert Nares,A Glossary;Or Collection of Words,Phrases,Names,and Allusions to Customs,Proverbs,etc.,London:R. Triphook,1822,P.77.Nares的标注已被牛津大辞典收录,对后世的影响可想而知。究竟孰对孰错,谁的注解和翻译更接近原文?笔者结合文本的语境和时代语境来分析。
先看《第十二夜》中“Cataian”出现的文本语境。
原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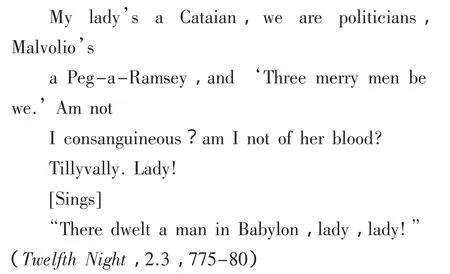
朱生豪版
托比:小姐是个骗人虫;我们是些阴谋家;马伏里奥是拉姆西的佩格姑娘;我们是三个快活的人。我不是同宗吗?我不是她的族人吗?胡说八道,姑娘!巴比伦有一个人,姑娘,姑娘!
小丑:要命,这位骑士真会开玩笑。
方平版
托比:伯爵小姐是个中国人,只当她说话是假的;我们一帮子可是机灵的政客呢,马伏里奥算得上什么东西!(唱)咱们是三个快乐人——我不是嫡系的叔父吗?我跟她不是有血缘关系吗?叽里咕噜什么呀,姑娘!(唱)巴比伦住着一个男儿汉,姑娘,姑娘。
托比口中的“My lady”即是他的侄女奥丽维雅。“My lady's a Cataian”说明奥丽维雅的形象即为中国人的形象。从剧本可以看出,她是一个集美德、美貌以及富有于一身的女子。无论是品格高洁的奥西诺公爵还是她的仆人都视其为美貌与智慧并举的高贵女子,托比与其无冤无仇,何况还是她的叔父,他会认为自己的侄女是“骗人虫”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再来看看“Cataian”的时代语境。
John Mandeville在 Here Begynneth a lytell Treatyse or Book中提到“Cathay是一个美好且富有”的国度;①John Mandeville,Here Begynneth a lytell Treatyse or Book,Westminster,1499,P.79.Freère Hayton把它描述成“世界上最高贵而又富有的王国”;②Frère Hayton,Here Begynneth a Lytell Cronycle,1520,P.1.Pietro Martie d'Anghiera将其与“伟大富有的帝国”以及“文明且无法言喻的富裕”相联系。③Pietro Martie d'Anghiera,“The Preface to the Reader”,in The Decades of the NeweWorlde or West India,1555.此外,Cathay也常常被赋予“有秩序”、“美德”、“优秀的管理”等美好特征。至于中国人,Freère Hayton也写到:“居住在中国的人叫做中国人,他们中间有很多貌美容俊的男人和女人。”④Frère Hayton,Here Begynneth a Lytell Cronycle,1520,P.1.Louis Leroy也赞誉中国人的智慧与勤奋。⑤Louis Leroy,Of the Interchangeble Course,or Variety of Things in the Whole World,translated fromFrench to English by Robert Ashley,1594,P.49.总体看来,中国及中国人在早期英语文本中的主导形象是积极光明的。根据格林布拉特所主张的新历史主义理论,笔者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同时代及之前其他历史文本中的中国人形象有相关性。中国人形象也似一种社会能量,在不同的文本里流动,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认知的变化而不断变迁。早期英语文本中的中国人形象和《第十二夜》中奥丽维雅的形象完全契合也正印证了新历史主义的一些观点。那么富有和具有美德的中国人何以被视为小偷、骗子乃至恶棍呢?
这至少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一些词语存在多义性,如cunning,dexterous。二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Cataian”形象具有模糊性。三是特殊时期一些人别有用心,从Steevens的注解可见一斑。另外,一些无知者不乏偏见和歧视。
第一,一些词语存在多义性和模糊性。前文在论述中国人具有富有和美德这两个特征时,也引用了Steevens与Nares的话,Steevens指出“中国人(古时候被称为Cataians)据说是手指灵巧的族裔里最手巧的(the most dexterous of all the nimble-finger'd tribe)。”而Nares则直接指明中国人“手指灵巧的偷窃”(the dexterous thieving of those people)。他们用到的形容词都是dexterous。这个词具有“手巧”“敏捷”“利落”等意思,本身并非贬义词。在18世纪之前的一些文本里,中国人经常被描述为心灵手巧的机智聪慧的民族,常常是被羡慕的对象。Dexterous常常是当作褒义词来赞誉中国人的心灵手巧和匠心独具。但是dexterous若与其他词搭配,就会变成诸如Steevens 和Nares笔下具有嘲讽意味的贬义词了。类似的词还有“cunning”等。“cunning”一词既有“巧妙的”和“可爱的”之意,也有“狡猾的”意思。Frère Hayton曾盛赞中国人在艺术和手工艺方面的匠心独造与心思缜密。①Frère Hayton,Here Begynneth a Lytell Cronycle,(London,1520),P.1.Thomas Elyot也曾用“cunning artificer”来感叹中国人手艺的精湛。但是,如果“cunning artificer”脱离了语境,就很有可能被人解读为“狡猾的手工艺人”。可见,一词多义性和词义的模糊性为日后一些学者断章取义留下了可能性。
第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Cataian”形象具有模糊性。在此剧中,培琪说道“I will not believe such a Cataian”。原文和译文如下:
原版

朱生豪版
培琪(旁白):“面包干酪”?这家伙缠七夹八的,不知在讲些什么!
……
培琪: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一个啰里啰唆莫名其妙的家伙。
……
培琪:尽管城里的牧师称赞他是真正的男子汉,我就不相信这种狗东西的话。
方平版
裴琪(自语):“我有自己的胃口”,听他说的!这家伙满口怪话,叫英国人都听不懂英国话了。……
裴琪(自语):我还从没碰见过这么个说话拿腔拿调、装腔作势的流氓。
……
裴琪(自语):我可不能相信这种“卡瑞人”,尽管城里的牧师还说他是个好人
朱生豪根据上下文将“I will not believe such a Cataian”中的Cataian意译为“狗东西”,正如他在《第十二夜》中将其译为“骗人虫”一样,贬义气息浓郁。此处,“Cataian”被质疑,确实含有贬义,但是这种质疑并不一定指中国人,即使是中国人,也不一定属实。首先,这种质疑可能是对中国人存不存在的一种怀疑。China(中国)与Cathay(契丹)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只是处于不同的时间点上,但是,包括利玛窦和弥尔顿在内的很多声名远播的著名学者都曾错误地将其视为两个国度,更是有人质疑Cathay的存在。如果Cathay不存在,那么居于此地的Cathaian也就同样不存在。另外,英国包括女王在内的皇室成员都曾出巨资资助过探险家和商人来中国,可是他们要么无功而返,要么命丧大海,因此都没能到达中国,这就导致很多人对中国这个国家是否存在有所质疑,这种对中国的怀疑有时也就迁移到了中国人身上。所以,在一些眼见为实者眼中,“I will not believe such a Cataian”也可以理解为:我才不相信有中国人这样无中生有的事呢,言下之意,中国人的存在是不可信的,尼姆的话也是不可信的,培琪的妻子背叛他也是无中生有的事,并不可信。其次,在培琪的眼中,尼姆是一个“说话拿腔拿调、装腔作势”的流氓,他质疑的或许就是其说话的腔调。相信自己的妻子,还是相信一个“说话拿腔拿调、装腔作势”的人?培琪选择相信妻子怀疑尼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我们也间接地知道,牧师称赞他为真正的男子汉,并且尼姆跟培琪和福德所说的话确实是实话,所以事实上他并不是骗子。只不过此刻尼姆缺席,根据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话语权掌握在培琪手中,但是掌握话语权的人说的并非都是事实真相。所以,培琪不相信尼姆,不代表尼姆就是骗子。一些人不相信中国人,不代表中国人就是骗子或小偷。
四是特殊时期一些人别有用心或心存偏见和歧视。譬如,Steevens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Cataian作注时,将其视为小偷和骗子,不但时代倒错地用他所处的18世纪的中国人形象来解读莎士比亚时代的中国人形象,而且断章取义地搜罗例证。正如Timothy Billings指出,Steevens曾“脱离语境地引用只言片语并将之当作又一份证据呈示给信任他的读者”。①TimothyBillings,“CaterwaulingCataians”, Shakespeare Quarterly.54.1(2003),P.28.譬如,他从The Pedler's Prophecy中引用了一段话“在印度的东部,他们借助大海和洪水来行窃”,并将“他们”视为中国人,以此将中国人和偷盗的行为联系起来,可是事实是,他只引用了一部分,而把主语“旅行者”省掉了,完整的句子是,“这些旅行者在印度的东部,他们借助大海和洪水来行窃”。②Chang Y.Z.,“Whoand What Were the Cathayans?”Studies in Philosophy,xxxiii.2(1936),203ff.所以真正被指摘的偷盗者是旅行在印度东部的游客,其中多数来自西方。③笔者在“My Lady's a Cataian:Cataian in Twelfth Night”一文中也指出过Steevens的断章取义性,详见Notes and Queries,2013年9月,第418-419页。
另外,对中国有直接了解的多是传教士、商人以及游客,其他人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是通过口口相传或是别人的撰述,虚构性淹没真实性的情况比比皆是。一旦有专家对此进行注解,后人便奉之为圭臬,视之为真理。无怪乎牛津大辞典以及中国的翻译大家也在译作中受之影响,将Cataian视为“骗人虫”和“狗东西”等负面形象。
三、结语
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他者,在具有探险和交流欲望乃至占有欲望的西方人眼中,保守被动的东方国家都像是话语权缺失的他者,其形象任由西方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想象和夸大。正如李勇所言,“从异国形象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想象主体的处境,而不是被想象的异国他者的境况”④李勇:《西欧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印度和中国皆被视为富有的国度,因而激起了英国人强烈的交流欲望乃至觊觎之心。对财富的追求本身无可厚非,但基于自身利益而丑化其他民族的行为则不妥。从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印度人被视为虔诚富有的民族,但是立足于西方人欲接触印度又怕遭遇危险的矛盾心理来看,印度人似一个极具诱惑性的美女,其可能具有的危险性使其形象大打折扣,恶魔性淹没天使性。
莎士比亚作品里的中国人形象在《第十二夜》里明显是积极正面的,集美德、美好、富有与聪颖于一体,但是这样的形象竟也被西方学者灌之以小偷和骗子。《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中国人指涉模糊,既可能指中国人,也可能指英国人,也可能暗指乌托邦性,因为,如前所述,很多人对中国是否存在心存质疑,甚至视之为乌托邦,莫尔的《乌托邦》即有中国的影子。不管《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Cataian具体指涉什么,根据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跟小偷和骗子是不相干的。后世的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或有意或无意地通过置换法将其视为小偷和骗子之流。这些置换法包括时间置换、文字语义置换和主题置换。
此处的时间置换即时代倒置,Steevens等将维多利亚时代中国人偏负面的形象时代倒错地放置到莎士比亚生活的伊丽莎白时代,然后指出“时至今日他们还是这副德行”。⑤William Shakespeare,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the Johnson-Steevens edition,1995,P.265.文字语义置换,即将dexterous,cunning,sharper等既具有褒义词义又具有贬义词义的词语贬义性地解读,忽视其褒义性浓郁的语境,可谓断章取义。如前文所述,Steevens等也通过断章取义来置换主体。可见,西方的中国形象,包括英国的中国形象“对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⑥周宁、周云龙:《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跨文化形象学的访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此文的目的之一即是通过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的分析,矫正莎士比亚作品中被歪曲的中国人形象,尽可能地还原其真实面目。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形势日益明显的新世纪,东西方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如果东西方都以深沉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慷慨博大的胸怀去欣赏异域文化而非特意疏远和敌视他者,①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页。如果中西方学者都像钱钟书一样笃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那么我们就不但能不带偏见地研究世界文化,倾心地欣赏世界文学,而且能真正助力东西方民族的交流与对话,实现世界共同繁荣与和谐发展。
(责任编辑:徐澍)
The Images of Indian and Chinese in Shakespeare's Works
ZHANG Zhi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The Indian and the Cataian appear many times in Shakespeare's works.They are believed to be rich and yet base and cunning.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reasons contributing to it.Firstly,the word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including cunning and dexterous have multiple meanings,which could be interpreted partially by some people for some purposes.Secondly,the image of the Cataian in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is vague.Thirdly,some people harbor prejudice or even ulterior motives which can be seen from Steevens's annotation.Generally speaking,the images of the Chinese and the Indian actually are kind of imagination and distortion based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West.
Shakespeare;Cataian;Indian;rich;cunning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项目“1473-1700年间英语文本中的中国形象”(2014EWY004)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早期英文图书中的中国形象”(14PJC025)的阶段性成果,亦受到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张之燕(1983-),女,安徽合肥人,讲师,硕导,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
I1
A
1008-7672(2016)03-004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