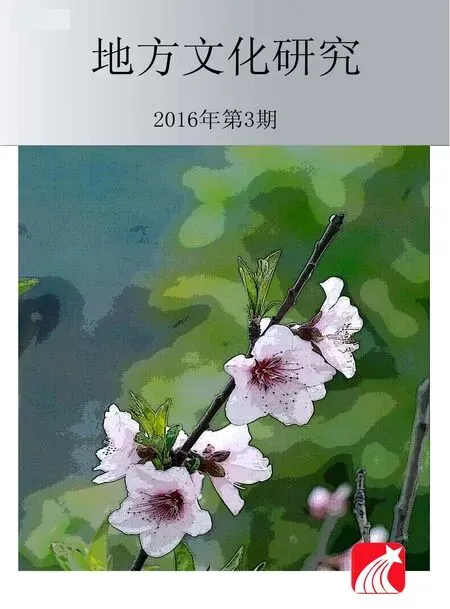滇南地方社会、彝族祖先记忆与文化认同——基于地方志和彝汉文碑记的考察
邱运胜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广东 广州,510665)
滇南地方社会、彝族祖先记忆与文化认同——基于地方志和彝汉文碑记的考察
邱运胜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广东 广州,510665)
藏缅语族、壮侗语族族群先民曾是历史上滇南的人群分布主体。元代以降,滇南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儒学随之兴起。地方志显示,明清两代,滇南儒家文化一度繁盛,对彝族传统文化的涵化影响较为显著。清乾隆年间,彝族尼苏人当中的一支,在族群精英的操持下,由普姓“恢复”为孔姓。《族谱明辨纪略》、《孔卓墓志铭》、《则旧孔氏汉彝文碑记》等彝汉文碑记成为孔姓彝族人建构孔子祖先记忆的重要资源。通过分析以上碑记资料,描述该族群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和维系彝族族群认同的努力。孔姓彝族人的个案是滇南地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反映。
明清时期;滇南;彝族;孔氏;儒家文化;文化认同
如果以云南作为一个整体,在当地人的地理观念中,“滇南”或“南滇”,通常倾向于指称如今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所在范围。地处云南之南的滇南地区,有着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在中国历史上“中心”与“边缘”持续的社会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异常丰富的族群文化多样性。这些族群文化,既有为滇南各世居族群所创造和共享,又持续地受到来自外界文化的影响,包括元代之后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渗入。滇南的族群文化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多种语言、宗教、生计方式的并存。自古以来,频繁的文化互动和族群间的竞争与妥协,形成了当下滇南地区“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分布格局,族群间的文化互动和文化涵化极为频密。历史学、民族学研究已经确证,彝语支民族先民乃是元明清时期汉族人大举进入之前滇南地区的主体族群之一。彝语支民族先民在滇南世代繁衍,不仅创造了本族群的语言、文字、宗教、天文、历法、文学、艺术,而且形成了自身的政治、社会、权力、军事管理制度,自成一套社会文化体系。这些文明创造均详略不一地在彝文文献中得以留存,并且提供了不同于汉文文献的关于滇南地方社会历史的解释。彝文文献对于理解滇南地方史,特别是元代之前族群互动的历史面向和社会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曾于2013年5月至10月,在滇南建水、石屏、元阳、开远等地从事过较为集中的田野调查,主要围绕彝族尼苏人(nip su pho)当中姓孔的一支族群的祖先记忆与族群认同进行民族志研究。孔姓彝族人是认同孔子为祖先,共享由“汉人融入彝人”的集体记忆,同时又始终维系彝族认同的族群。调查期间,笔者收集了一些汉文、彝汉文碑刻、墓志铭资料。这些资料是孔姓彝族人从古至今建构孔子祖先记忆、表述集体归属感、增强家族凝聚力的主要资源,从文本与语境的分析角度,可以窥探到滇南地方社会元明以降的社会变迁进程、彝族传统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汉文化的融合及涵化过程、彝族先民因应历史剧变所做出的合理化解释与认同抉择。本文将从滇南地方社会文化多样性格局的生成过程出发,对上述资料进行粗略呈现和分析。
一、滇南地方社会与文化多样性
云南红河流域两岸的哀牢山脉是一处多族群聚居的区域。从民族史学的角度来区分,在这一高山耸立、河谷纵横的复杂的地理单元中,主要分布着百越、氐羌部落的诸多世居族群,汉文史籍中常以“摆夷”、“东爨乌蛮”来指称这些古代族群。地方志文献对这一区域的描述,也频频出现“极边”、“极南”、“瘴疠之地”的词汇,这些表述内容充斥着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古代知识精英对“华夏边缘”的想象。彝族先民乃是滇南历史上的主体族群之一。纳楼土司作为彝族三大土司之一,其政治演变史,起于南诏,终于民国,是滇南彝族历史的一个缩影。据《蛮书校注》卷四《名类第四》记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①(唐)樊绰撰:《蛮书校注》,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2页。“步头”,指的是今天的建水一带。宋大理国取南诏而代之时,曾经借助过东爨“乌蛮三十七部”的军事力量。大理国统治爨地后,曾以“部”作为行政单位。统治者通过与白鹿部、罗婺部、华竹部等三十七部首领会盟的方式,颁赐职赏,把它们纳入统治范围。三十七部当中的纳楼部,其领地则主要在如今的建水周边地区。②易谋远:《彝族史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4-575页。
元代,红河流域首度被蒙古人强大的军事力量纳入到中央王权的控制版图之内,从此开始了逐步深入的行政管制。元代的临安路设于通海,以此为中心,治理南滇。有明一代,大量汉族人口不断南迁,政治中心也随之继续南移,从而有了位于今建水的临安府的建置。关于临安府的建置沿革,可参见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的叙述:
临安府,《禹贡》梁州徼外地,古句町国。汉武开西南夷,置句町县,属牂牁郡。后汉仍属牂牁郡。蜀汉属兴古郡,晋以后因之。梁末废。唐为羁縻柯州地,天宝末没于南诏,置通海郡都督府。宋时大理改为通海节度,寻改秀山郡,又改为通海郡。其后蛮酋互相侵夺。元宪宗六年内附,置阿僰部万户,至元八年改为南路,十三年改为临安路。明洪武十六年改为临安府。领州五、县五、长官司九。府南邻交趾,北拱会城,为滇南之上阃,作边陲之保障。③(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94-5095页。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直到元宪宗六年(1256年),元朝政权在通海置千户所,管辖滇南。滇南地区才得以“内附”,接受“王化”,被正式纳入到中央王权的统辖范围之内。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又改通海千户所为通海县,属临安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王朝在建水设立临安府。④建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建水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8页。建水作为临安府的府治,相应地设立了建水州的建置。建水旋即成为滇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纳楼土司在与临安府的角力、周旋过程中,其实际控制范围也经历了由北向南的沿革。临安府兴盛的文教制度与纳楼普氏土司的雄厚实力,都曾对当地的世居族群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和当地少数族群文化共同构建了滇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的格局,在多元文化的合力作用之下,无论是作为后来者的汉民族,还是原住民族群,都会无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建水自元代设立庙学以来,明清两代儒学教育的发展、儒家文化的传播达到鼎盛,被誉为“南滇邹鲁”、“文献名邦”,建水、石屏两地“士秀而文”,其民风“已与中州同若”。有关建水的人文风尚,清代雍正九年(1731年)修纂的《建水县志》有如下描述:
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衣冠礼庆与中州埒,号诗书。郡人多畏法,少有不平。宁众不争,多爱清雅。敬老崇文,婚礼近古。俗喜向学,士子讲习维勤。人才蔚起,科第盛于诸郡。⑤(清)祝宏等纂修:清雍正九年《建水县志》(1731),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重印本),汉口道新印书馆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56页。
元代以前的石屏地区,是当地世居族群生息繁衍的地方。明清之际,大量汉族人口迁入到当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清康熙年间的《石屏州志》对于汉族人口进入之前和之后的变化情况,有如下记述:
石屏,旧为荒远之地,多诸种倮彝。自元时内附,风气渐开。及明初置州牧,宣政教,以化导之。复设石屏、宝秀二屯。屯军皆江南北人,与土著之民错杂而居,由是,熏陶渐染,习俗丕变,文物冠裳,彬彬与中州侔矣。①(清)程封纂修: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1673),佘孟良标点注释,石屏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91年版,第53页。
建水、石屏所属的临安府的庙学,始于元至元二十二年 (1285)。临安府文庙又于泰定二年(1325)由佥事杨祚增建。至正十年(1350)平章王维勤、教授邵嗣宗继修。明清两代又经过五十多次增修扩建,以至成为云南文庙之冠,属全国大型文庙之一。②杨丰编著:《教育圣地:滇南邹鲁》,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建水州学亦设于文庙府学之内。明清两代,建水共出文武进士109名,次于昆明、大理;出文武举人1273名,仅次于昆明。③同上注,第43页。石屏县的儒学教育亦兴起于元代,逐渐成为临安府众州县庙学中较为繁盛的一处。石屏文庙始建于元至正年间,历来为临安府石屏州县学所在之地。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石屏州志》中的《重修学宫记》对于石屏的儒学兴盛有如下记载:
石屏为句町名胜,学宫起自元时,及明初重建,渐加开拓,踵事增华。于是规模宏敞,较他州为最。三百年来,士之由科日升,庸者百余人。西南文物于斯称极盛已。④(清)程封纂修: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1673),佘孟良标点注释,石屏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91年版,第216页。
根据《石屏县志》统计,明清两代,石屏共出现文进士65人,其中入院翰林院者16人次,武进士11人,文武举人638人。⑤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石屏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8页。儒学教育的繁盛,也影响了当地的非汉族族群,少数民族的青年才俊也不乏登甲榜者。清乾隆年间的《石屏州志》记录了儒学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士喜向学,讲习维勤。妇人习女红,勤纺织,每深夜犹闻机杼之声。……至山寨夷众皆居茅屋土莝,语言、服饰、婚丧、饮食,犹仍旧习。其英俊者习诗书,学文章,游泮者岁不乏人,现有登甲榜者。非圣朝文件之隆,曷克臻此。⑥(清)管学宣修纂:乾隆二十四年《石屏州志》(1759)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1页。
在石屏县众多进士当中,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第三甲第四十一名进士李云程系出自彝人家庭。⑦杨开达:《论云南清代彝族教育家文论家李云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26-31页。儒学教育的发展对滇南地方社会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文教成就上,更加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习俗风化。直至近代,儒家文化在石屏城依然有着显赫的地位。民国抗战时期,曾在石屏一中任教的江苏籍文人缪崇群(1907-1945)在其散文集《石屏随笔》中描述了当时石屏古城内的景象:
我欣喜地走进城里去作第一次的巡礼。整齐的道路,大都是用方石铺成的。十字路口和大街上有几座颇为巍峨的牌坊,虽然有些陈旧了,但他的匠工是异常考究而精细。人家的门头上,几乎触目都是一些匾额:“文魁”、“武举”、“太史第”、“观察第”、“经济科博士”、“父子同科”……那向东朝阳的一道城门楼上还有一块很大的横额,写着四个大字:“文献名邦”。我想到这个不平凡的城,原来就有着她的光荣的台衔。⑧缪崇群:《石屏随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作为文风兴盛的古名邦,面积不大的石屏古城内,至今还保留着石屏文庙、古城门、护城河、石屏风、袁嘉谷故居、老县衙、清真寺、个碧石铁路之石屏火车站⑨个碧石铁路是近代滇南企业家筹资,自主修建的铁路。1913年开工建设,至1936年全线竣工。采用寸轨(轨距600毫米)运行,全长为104公里,途经今红河州的个旧、碧色寨(蒙自)、临安(建水)、石屏等地。参见:和中孚:《个碧石铁路:云南人引为自豪的寸轨铁路》,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石屏一中内的企鹤楼、珠泉等大量名胜古迹。县城南面的焕文公园内,赫然耸立着状元楼、焕文塔等古建筑。两处建筑室内的图片展,向世人展示了石屏在古代文教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城郊有着“云南第一村”之称的石屏县宝秀镇郑营村,陈氏宗祠、郑氏宗祠等清代古建筑保留完好。这些汉族军屯后裔修建的规模宏大的宗祠,表明石屏等地的宗族文化是较为繁盛的。无论是有着“滇南邹鲁”之誉的建水,还是文献名邦石屏,明清时期都曾在文教和儒家思想传播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对当地多民族互动、交往的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认同孔子作为祖先的孔姓彝族人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孔姓彝族人既共享着孔子祖先记忆又具有彝族族群认同的认同表述模式是滇南地区儒家文化与彝族族群文化长期互动产生的结果。
二、彝汉文碑记与祖先记忆表述
滇南一带的孔姓彝族人都追认他们的第一代直系祖先是安葬于建水县官厅镇大凹子村附近山坳的孔载物。笔者曾到大凹子实地了解了几座孔家祖坟的情况。大凹子附近的地貌石漠化明显,岩石裸露地表,是一个缺水严重的村子。孔氏祖坟位于村子东北方向,坐南朝北分布着三处坟茔,分别是一世祖孔载物与妻子孙太君合葬墓、二世祖孔一德及其妻子赵太君的坟墓。三座墓葬直径约300cm,墓碑高160cm,目前左右两侧立有华表及一对石狮,华表顶部的装饰已脱落在一侧的地上。孔载物墓有《族谱明辨纪略》、孔一德墓有《尊谕辟论族规》铭文。三墓立于明嘉靖元年(1522年),墓志铭为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重修墓时所撰。《族谱明辨纪略》为清乾隆乙酉(1765年)科乡进士孔宗圣所撰,叙述了一世祖孔载物从南京,经贵州普安州①杨丰编著:《教育圣地:滇南邹鲁》,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来到云南的经过:
族之有谱,犹国之有乘也。乘以纪累朝之始终,谱以传阖族之源流,二者为家国之切要焉。观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木本水源,物且有然,而况人乎哉?追溯始祖,原是姓孔名厚,乃山东籍贯,南京应天府人也。曾荐贤书仕于黔之普安州。奈时逢改革,岁荒民变,甚至兵火延年,于祖有碍,不得已改姓普,由黔入滇至临潜居。孰意方出天罗旋入地网,倏值流贼作乱,吾祖乃旧逃奔。偶适此地,见山势盘桓,林木幽静,爰立宫室遂家焉,自此始祖厚娶孙氏,生二世祖一德;二世祖娶妻赵氏,生三世祖七人,分派七房。迄今子姓蕃昌,瓜瓞联绵,采芹折桂者代不乏其人。搃因先祖累积而成者。思我始祖仕于普安州,是由建业而入黔也。避乱而出忘,由黔而入滇也。卜居大凹子,弃繁华而爱清雅也。独是祖宗事绩,难以详尽。而族谱之源,乃承先启后之要。
兹为孔普两姓因辨明之。孙宗圣于乾隆乙酉科叨蒙祖宗默佑,己登乡荐赴京会试。寓于黔中,访我宗支。见有姓孔者,相叙及族谱,其人答曰:“我族谱由海岱而入于建业,虽南京人也,本山东籍也。先祖姓孔名厚者仕于普安州,闻知避乱入滇,未审落籍何处。”试考其备细,乃一组之孙,方知先祖姓孔,良非虚也。又知山东籍贯,洵不诬也。于戯!系出一脉,居分两地;人虽散处,谊属同宗。倘非先祖之灵验,其谁能知。且先祖曾仕普安州,间有以普为姓者,又以普安州为祖之姓名者。或又曰:“普是真姓,孔乃冒姓也。”若然,真是姓普则姓之矣,又何乐而姓孔乎?要之:先祖姓普不得已也,今复姓孔不忘本也。特辨明而敬述之,俾后世知所由来矣。特叙。
乾隆乙酉科乡进士,兵部侯推守备、后世孙宗圣敬题。②《族谱明辨纪略》是孔氏先贤清乾隆乙酉科(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乡进士孔宗圣(时周)所撰。《纪略》原文出自建水县官厅镇大凹子村孔氏先祖孔厚(载物)之墓志铭碑刻,本文附录转引自石屏县续修孔子世家谱指导小组:《石屏县孔子世家谱》,内部资料,2003年版,第35页。
孔宗圣撰写的《族谱明辨纪略》显示,一世祖孔载物籍贯山东,南京应天府人,曾被举荐到贵州普安州(今六盘水)做官,遭遇民变,隐姓埋名,奔逃到云南,选择大凹子作为安身之所,并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在孔载物之子孔一德的墓碑上,有其七位子嗣的姓名,分别为孔卓、孔哲、孔杰、孔长、孔槐、孔溥、孔豪。长子孔卓的墓葬在石屏县坝心镇孔家村的西北角,墓碑上也刻有一篇墓志铭,记录了孔一德长子孔卓从大凹子迁出的情况:
盖闻木无本者枝不茂,水无源者流不长。穷本溯源,后裔之所以报本追远也。吾孔氏祖自山东分派,迁入南京,越有历年,由南京又分派入黔之普安州越有年。自古在昔,遐哉邈乎,不可复识矣。惟始祖厚公由黔之普安州入滇,择居于临阳之大凹子,娶始祖妣孙氏,生二世祖一德公;公娶妣赵氏,生三世祖七人;长卓、次哲、三杰、四长、五槐、六溥、七豪。卓公始由大凹子迁居大坡,继由大坡迁居垤莫。及卒,卜葬于垤莫之右畔。经今历数传矣。而宗支朴茂,子姓蕃昌,想亦祖功宗德庇荫之所致也。夫爱人怀树,甘棠且犹勿剪;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况兹瓜瓞所兴实肇于斯者乎。爰镌诸石,以垂不朽。
大明嘉靖十三年葬
至大清乾隆甲戊年安碑
今道光二十八年一阳月初九日阖族重修①《孔卓墓志铭》是孔氏家族三始祖孔卓墓葬碑刻上的铭文。该墓葬位于石屏县坝心镇底莫村委会孔家村后山。本文附录转引自石屏县续修孔子世家谱指导小组:《石屏县孔子世家谱》,内部资料,2003年版,第40页。
乾隆二十三年冬月吉旦
在开远市小龙潭镇则旧村,笔者见到一处修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的孔荣昌墓地。这座墓地坐北朝南,单独在村子西侧的山坡之上,正前方数米远有风化程度较大的石狮一对,其中一只破损严重。这座墓葬的彝文和汉文铭文各有一篇,是为滇南彝族传统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相互融合的佐证。现将汉文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世系序
从来物本采大,人本采祖,本追远,所以传后世而继承者也。余始祖山东人氏,至今世远,年渺□不可知。但有高祖□世清,曾祖父之父孔李二妣,李氏生二子,余居二,生子三女四,孙则继续焉。余幼攻书史,未获成名,为铺役所累。然负性好游,索山水,得异人传授而卜得一穴,以妥先灵。不觉余年古稀,又卜一穴,系庚龙入首,作酉山印,向佳城。但余不敏,不敢上承先志,下遗子孙,或后之贤者欤。所宗其所不肖者□,亦识所从也。以是为序。
皇清待赠显考孔公讳荣昌之墓②孔荣昌墓葬位于开远市小龙潭镇则旧村委会则旧村。《则旧孔氏汉彝文碑记》采用彝、汉双文撰写。转引自开远市小龙潭办事处志编纂委员会编:《开远市小龙潭志》,内部资料,2002年版,第365页。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
在孔姓彝族人的集体记忆中,他们与普氏家族有着很深的渊源。为了把最先迁入云南的始祖为何隐姓埋名、由孔姓改为普姓的做法解释得更加合理,如今的孔姓彝族人认为,孔氏汉族祖先逃难到彝族地区,迫于彝族纳楼土司的压力,于是选择将姓氏改为普姓,从而与普氏土司同姓,可以免受欺凌。然而与之相应的,对于乾隆年间的举人孔宗圣为何要进行“族谱明辨”的动因,孔姓彝族人却归结为,这是“不忘本”的体现,本就是孔姓,无奈姓了普,“恢复”姓孔理所应当。根据调查获得的直接证据表明,孔姓彝族人曾由普姓改为孔姓是客观事实。对此,孔姓彝族人成员内部也均有一致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笔者实地了解的情况,在彝族尼苏人当中,同宗同源却不同姓的家族,远非孔普二姓一例。2012年12月,笔者在建水县官厅镇苍台村调查时了解到,该村的李姓家族是从元阳县马街镇迁入苍台的。据传,老祖辈为躲避派丁,用松球破开,兄弟各拿一瓣,分为马、李、白三姓,如今已经发展为四十多家,彼此之间虽然姓氏不同,但人们都相互认可是近亲关系。后来,李姓又分为大树李、四甲李、启甲李三支。大树李因为上门入赘等原因,又分为杨、王、李三姓,相互之间不通婚,实行家族外婚制。在石屏县坝心镇底莫村委会里长冲、大坡、羊街村等地,同是李姓家族,却被人们分为“张何李”、“白马李”两支,前三姓与后三姓都是同一家族,共享同一字辈。笔者在该村委会水塘寨村见到一“张何李”共用家庙民国四年(1915年)碑记上有如下记叙:
原我始祖张启恩,本属南京应天府人也。因滇逆扰,奉谕讨逆至滇,故为云南临安建水之籍,择邻于陆姜之处,徙于湾子寨邑而居,所生三子,长曰张世硕,次曰何世动,三曰李世崇,森森然改为三家,同胞异姓。原如何是也,窃赖我祖忠于朝廷,从戎立有剿叛之功,终不失子孙繁盛,是以三家之后……虽各一方,事同一体,骨肉之义尚在,共建宗祠于此水塘祭奠焉……①碑记内容引自石屏县坝心镇底莫村委会水塘寨村“张何李”三姓家庙民国四年(1905年)碑记《清白传家》。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
根据彝族各个家族后人之口述,所谓“同胞异姓”主要有旧时为躲避抓丁,兄弟改姓以及不同姓氏联合起来,壮大势力等两个原因。彝族尼苏人其他姓氏的情况,也许能为理解孔普二姓之间的关系提供某种参照。
三、“由汉变彝”与文化认同建构
滇南地区的儒学教育和儒家文化的传播,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到了乾隆年间可谓到达了鼎盛。与此同时,中央王权在当地的统治也愈发稳固,从而有了“改土归流”的实施,红河流域最大的土司彝族纳楼普氏土司尽管因其庞大的势力,没有遭遇“改流”,但其控制范围已经明显向红河南岸转移。对于主要生活在红河北岸的孔姓彝族人来说,大体上已经不再受纳楼普氏土司的直接管控,相反,清代中叶年间的孔姓彝族人已经从山区逐渐向海拔较低的半山区迁徙,与汉文化的接触也达到了空前的境地。从地方社会历史进程来看,孔姓彝族人“族谱明辨”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做出的由当时的精英主导的“恢复”孔姓行动。
调查发现,孔姓彝族人对彝族尼苏人的族群认同意识是明确的,人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在认同汉族与认同彝族之间的分歧或不同情境下的认同选择。孔姓彝族人在同其他族群交往、互动时,利用具有独特性的族群文化来表述尼苏彝族的身份。对于孔姓彝族人的祖先记忆,本文的基本理论假设是彝族尼苏人当中的一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由原本的彝族姓氏“普姓”改为“孔姓”,以在族群竞争中获得某种有利于自身的文化资本。然而,孔姓彝族人自身的表述却是,他们原本出自山东孔氏,融入了彝族普氏,之后改回孔姓是对孔姓的“恢复”。“由普改孔”与“由孔改普,再改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同模式。孔姓彝族人由普姓改为孔姓的经过,已经为碑刻文献资料和口述材料所证实。“由汉变彝”的认同表述与来自中原的汉文化和当地其他族群文化之间的文化互动有着直接的关联。本文将孔姓彝族人祖先记忆的表述内容,即祖先来自山东曲阜孔氏,并由汉人变成了彝人,视为一种彝族尼苏人对儒家文化的文化认同,所谓的“孔子后裔”是一种文化表述符号,它并不指涉汉族或彝族等特定的族群身份。孔姓彝族人的认同表述实践也是表明,他们并未因为认同了孔子作为祖先,而去积极建构对汉民族的族群认同意识,而是始终维系着对彝族尼苏人的认同。
实际上,在村落社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彝族民族成分的意义并非具有显著的重要性,人们依然以尼苏人自居,以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同属于彝族的其他支系族群,例如仆拉人等。山区的孔姓彝族人至今仍完好地保留了尼苏彝语,即彝语南部方言。会不会讲尼苏话,是人们区分本族群与其他族群的重要依据。彝族传统社会的毕摩信仰,仍然在彝族尼苏人的人生仪礼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并且与汉族人的“道士”相区别。彝族尼苏人珍爱本族群的传统服饰,在山区村寨的劳动场合以及日常生活中都能见到。人们外出旅游,到了景区也要特意换上尼苏服饰,合影留念。无论是节庆活动,还是休闲娱乐,传统的彝族烟盒舞更是人们不可或缺的文艺形式。语言、毕摩信仰、传统服饰及烟盒舞,都是彝族尼苏人区分于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成为山区孔姓彝族人建构族群认同可资利用的文化内容。
孔姓彝族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孔子祖先认同的同时,还不同程度地共享着彝族尼苏支系的文化与认同意识,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彝族”这样一种相对固定的民族成分。虽然为了对如今的族群现状给出一个尽量合理化的解释,孔姓彝族人生产出了各种“由汉族融入彝族”的身份表述,但是,人们并未向民族事务主管部门提出要求恢复为汉族的政治性的诉求。相反,在村落社区生活的日常实践中,孔姓彝族人认同彝族尼苏人,始终保持着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周遭其他族群之间互动的边界。从族群研究的意义上说,孔姓彝族人无疑可以将之作为一个具有彝族尼苏人族群性的群体。由此可见,孔姓彝族人是一个既有彝族尼苏人认同意识,又具有孔子祖先记忆的族群。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和当地少数族群文化共同构建了滇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的格局,在多元文化的合力作用之下,无论是作为后来者的汉民族,还是原住民族群,都会无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多样性的影响。认同孔子作为祖先的孔姓彝族人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孔姓彝族人既共享着孔子祖先记忆又具有彝族族群认同的认同表述模式是滇南地区儒家文化与彝族族群文化长期互动产生的结果。本文以为,儒家文化与当地彝族传统文化长期交汇、并行,互相影响、涵化的历史过程,才是孔姓彝族人建构孔子祖先记忆行为背后的社会脉络。从根本上来说,孔姓彝族人对彝族尼苏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和对孔氏远祖孔子的祖先记忆所产生的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是红河流域滇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的真实体现。
四、结 语
事实上,孔姓彝族当中的普通成员,对于彝族身份以及认同祖先孔子的真正意义并非时刻都在关注着。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祖先崇敬的对象,通常只限于自家近几代的祖先以及对村寨开基祖先的祭祀。笔者在此引述一位孔姓彝族族群精英的原话,颇具代表性。他对笔者说:“我们姓孔,是孔子的后代,但我们现在是彝族。有时,也会被人讽刺、奚落,说汉人怎么就变成了彝人。但是,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导致的。我们孔家的祖先是伟大的,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共融性,是个胸怀博大的群体。民族的融合性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对彝族身份不自卑,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是一种荣耀。我们大度、宽容,整个中华民族是大度、宽容的。彝族接纳了我们的祖先。”这是笔者调查期间,听到的孔氏精英人士最具总结性的观点,这种不乏见地的看法,会在多大程度上建构孔姓彝族人今后的认同模式以及会对当下人为固定化的民族身份边界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值得关注的是,当下孔姓彝族人对彝族尼苏人族群认同建构方面,却并未发现孔氏族群精英的身影。与之相反,孔姓彝族人当中的普通成员却尤其看重彝族尼苏人的族群文化,在多族群交错杂居的社会环境下,与其他族群的人保持身份认同上“自我”与“他者”的边界。简而言之,孔姓彝族人普通族群成员仍在恪守彝族尼苏人的族群认同意识,而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族群话语的孔氏精英却在实践着对“孔子后裔”的建构。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仍在持续,这或许是今后仍值得继续关注的问题之一。
附图:

图1: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重修孔姓彝族人一世祖孔载物孙太君合葬墓

图2:清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重修孔姓彝族人三世祖孔卓墓及维护墓葬的孔氏族人

图3:清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孔荣昌彝汉文碑记墓
(责任编辑:刘丽)
Local Society of Yunnan,Memory of Yi's Ancestors and Cultural Identity——On the Local Records and Inscriptions on the Yi's Chinese Languages
Qiu Yunsheng
(College of Nationalities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510665)
Ancestors of Tibetan-Burmese and Zhuang-Dong Family ethnic groups were the subject of southern Yunnan ethnic groups in history.South area of Yunnan form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central dynasty governance along with the rise of Confucianism since Yuan Dynasty.Chorography shows that the Confucian culture flourished and occurred significantly acculturation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Yi people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Under operation of ethnic elite,branch of the Yi(Nip su pho)reverted surname form Pu to Kong in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Record of Genealogy Discernment”,“Kong Zhuo Epitaph”,and“Yi-Chinese Character Inscription of Kong in Zejiu”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Kong Yi for 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ancestral memorie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 inscription data,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thnic groups’endeavor not only to express the identity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but also to maintain the ethnic identity of Yi people.The case of Kong Yi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southern Yunnan local social.
Ming and Qing Dynasties;Southern Yunnan;Yi people;Kong Clan;Confucian Culture;Cultural Identity
K892.27
A
1008-7354(2016)03-0048-08
邱运胜(1985-),男,江西鄱阳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本文为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文化融合背景下的滇南彝族祖先记忆研究”(项目批准编号:16YJC850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