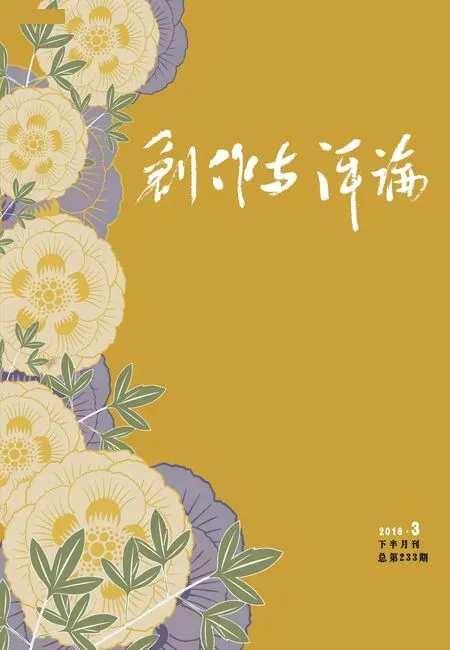作为方法论的和美学的『王小波』
——从房伟的『王小波研究』谈起
○梁鸿
作为方法论的和美学的『王小波』
——从房伟的『王小波研究』谈起
○梁鸿
199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或者说愿意阅读文学的年青人,有几个没有爱上过王小波?也许中年之后会遗忘,会批判,会有所疑问,但是,在青春最为激荡,最容易被宏大话语制约,最容易被“理想”“时代”“梦想”之类的词语所鼓动的时候,读到王小波,那是怎样的一种震动、震惊,或豁然开朗?
那天真而蛮荒的想象力,举重若轻的反讽意味,性与政治的微妙辩证,它们组合成一种充满趣味和独特审美的文学语言,以最轻盈的方式穿透哪怕是最坚固的内心,让你感受到人类存在的真相和时代精神内部的荒谬。而对于最缺乏个人意志和精神自由之感的当代中国人来说,那个“打不死的小强”,那个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刻——被严刑拷打,跳楼自杀,游行示众——也依然挺立的“小和尚”,犹如一个巨大的尖形碑,以滑稽而又庄严的方式给我们展现了生命的顽强和自由的美感。
房伟在他的《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三联书店)中称王小波为“坏孩子”,这一说法虽然是感性的,但却形象地把王小波与时代的关系,王小波存在的基本位置给展示了出来。他不按常理出牌,他挑战、嘲弄权威,他不负责任,任性耍赖,在人人义正辞严的时候,他却想着陈清扬的身体,在全国上下火红一片,都在大炼钢铁之时,他却把它想像为一场怪异抽象的战争,在贺先生不堪其辱愤而跳楼的悲惨时刻,他却注意到贺先生的“小和尚”依然是挺直的。他总是能够看到那些板着的面孔背后的漏洞,并且,就像一个班级的坏学生一样,还生尽千方百计让其它同学也看到那些漏洞,而全班同学发出的明了的哄笑声就是对他最大的奖赏。这“哄笑声”贯穿了王小波的所有创作。它是一种嘲弄,一种去蔽,对密布于我们生活内部的思想的突然陌生化,进而达到一种质疑——对最基本的概念、行动和观念的质疑。而由于它的感性基础,这一质疑变得真实、有力,几乎达到一种澄清,很难再被遮蔽。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性”作为一种自然的元素,它与个人、生命力、自由相关,所相对应的是束缚、集体、政治、制度。“小和尚”不分时候、不分地点挺直在那里,既嬉笑怒骂、悲惨无比,又为所欲为,不听使唤,哪怕是跳楼死亡,它也还在那里表演自己。王小波凭着直感找到反时代核心话语的核心话语,围绕着此,喋喋不休,反复叙述,最后形成一种审美和美学,并拥有强大的消解和反抗力量。
这无疑是一种教育,关于个体生命,关于人类存在的限度,关于理性与经验关系的教育。阅读王小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是一场关于启蒙的旅程。这与“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还略有不同。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启蒙更多地在于启发民智,让大家从愚弱中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危机,是一种族群意识的警醒,里面包含着对个人权利的认知,在王小波的“启蒙”里,以“族群”为名义的革命与权力恰恰正是需要反思的,他让你看到革命、权威、道德如何以“正义”“集体”的名义摧毁个人,让你看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点自然性及这一自然性的力量。
自1997年王小波去世以后,“王小波热”一浪超过一浪,先是思想文化界,精英媒体界,然后是文学界,最后到达大众文学爱好者和青年一代那里(这个排序本身很有意味),中间还有王小波的爱人,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推波助澜,关于王小波的一切——哪怕是他最不经意的一个动作和最私人的性爱(李银河最近推出传记详细写到两人的性爱方式),似乎都已经被大家熟知,并被广泛讨论。
为一个已经被分析过度的作家写传记,应该是一件很冒风险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全媒时代,掌握、收集资料,探听故人的看法,寻找传主生活过的地方,探查民间的声音,似乎都不是难事,这就意味着,揭密式的、生平式的传记都已经没有多大价值。这给传记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正是在这一层面,房伟的《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房伟打通了双重自我身份所产生的多重知识路径和美学路径。通读全书,可以看到,房伟仍然以王小波的生平为纲——为寻找一丁点的蛛丝马迹,房伟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了一切可以穷尽的人,去了一切可能去的地方,有半年时间,为了约到北京与王小波相关的人,房伟在北京租了间房子,随时待命。但是,他并非止于揭密式的描述,而是如抽丝般地梳理出王小波小说美学中的经验来源和知识来源,他做的是一种倒置式的和互证式的阐释,即,首先要对作家创作中的美学风格、思想方式和精神特征有最根本的把握,然后,通过对作家生平的回溯和探秘,找到其来源和生成方式。
这样的写法和结构方法,首先需要传记作者对作家作品有深刻的领悟和独特的认识。在此角度下,房伟充分发挥了他的专业优势。作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房伟不但对王小波小说进行理论探讨,从王小波的接受学、美学和比较学等多个层面进行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学术专著①,同时,作为一名作家,在创作上,房伟也全方位实践并探索王小波的美学思想。2012年房伟出版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在这部小说里,房伟让当代和古代两重时空同时并存,以一种王小波式的狂欢化、杂揉的语言对当代世界内部的虚空和荒诞进行了书写,但是,它的多义性语言和黑色幽默却又是房伟自己独异的风格。这其中,自然有对王小波致敬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出,房伟把王小波的美学风格作为一种实验,既实践它,又创造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弹性空间的形式。
这正是王小波的核心:从来不提供固定的真理式的思想,他更乐于提出一种思维的方法和精神的形态,沿着这一方法和形态,每个人都会达到自己的方向。它强调一种通向真理的方法论,而非真理本身。
从房伟关于王小波小说的论述和自己的创作可以看出,他对这个作家的精神世界,对这个作家在当代中的位置及背后的象征性意义,对作家的美学风格,都有极具创见性的理解,能够看到隐藏在作家作品中的多条路径。同时,你也可以感受到,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房伟有真正的欣赏和进一步探索的热望。对于房伟来说,王小波是通向越来越深、越来越宽广的远方。
以学术研究为起点,再回到传记研究,房伟要探讨的是,王小波的作品,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意象从哪里来。
在《三十而立》中,王小波写道,“你能告诉我这只猫的意义吗?还有那墙头上的花饰?从一团杂乱中,一个轮廓慢慢走出来。然后我要找出一些响亮的句子,像月光一样干净……”“古旧的房子老是引发我的遐想,走着走着身边空无一人。这是一个故事,一个谜,要慢慢参透。”
一个普通的读者读到这些话,可能很轻松地就滑过去了,只是不错的句子而已。但是,房伟却没有放过,反而从最简单的词语“墙头上的花饰”入手,回到王小波成长的生活空间和历史场景中,去寻找这句话的来源,并且,由此出发,对王小波小说中的大量物质性词语进行分析,进而阐释其中的修辞风格和美学意味。
在第二章“顽童时代——孤独的‘坏孩子’”中,房伟以“墙头上的花饰”为起点,对王小波的成长空间进行了地理学和谱系式的考察。他追溯到王小波的祖辈父辈,作为大地主的祖父和作为革命青年及学者的父亲,他们的生活方式、性格生成及命运轨迹,最后,回到王小波童年时代的“铁狮子一号”:
该楼的主体是灰砖石结构,楼面上镶着很多花纹和浮雕,样式繁多,对称而华美,有花和叶子,也有类似中国古典传说中的夔龙等形象的图案。主楼的大门是木质拱形黑木门,显得非常大气;副楼则有很多拱形回廊,绿色的立柱,以及造型欧化的路灯。……主楼和副楼相通,门窗和出入口很多,办公楼下还有很多地下室,这些地下室,四通八达,“曲径通幽”,给人以阴森神秘的感觉,据说当年的日伪特务机关,在此还设有水牢。王小平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这里的水牢和王小波小说的“钟楼情结”。……相比较红色北京的革命化空间,铁一号是“暧昧”的空间设置。作为革命者的后代,王小波及其同代人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生活环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和成方街不同,“铁一号”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少了一点杂乱和粗鄙的快乐,多了几分厚重的文化气息。更特别的是,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政治空间,“铁一号”对儿童的成长心理而言,却更多体现为“神秘”的艺术气息。曾经的辉煌,现实的衰败,两相对比,生发出一种历史“幽灵”般的神秘主义力量。②
由此,房伟认为,“铁狮子一号因此恰成为一种‘暧昧’的存在。它的样式造型、内涵意义,都是‘非革命的’,然而,它也并全不革命的‘对立空间’。在它被中性化的外表下,展现出来的却恰是‘革命之外’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丰富和复杂性。”这一成长的环境和空间,无疑会影响到作家日后的创作观和创作美学风格倾向,王小波小说中对“革命”的叛逆和反思,审美的复杂性,可能都与童年的生活经验和空间特征有关。也正如房伟所言,“王小波的成长空间,是一种革命北京的‘大院文化’。这种大院文化,既有别于王朔、姜文式的‘部队大院文化’,也有别于传统的‘市民胡同文化’。它属于革命北京时空中,国家事业单位、高校团体的独特空间。它既是革命北京的‘体制内产物’,又有一定的知识分子气息,对‘军事化的大院’有一定的疏离与反思。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一个体制内红色知识分子家庭诞生的王小波,最终形成了对‘革命北京’的深切反思。”③
以房伟的分析,我们返过来,再重新读“墙头上的花饰”,可能就不会觉得它只是一个苍白、陈腐的词语,而包含着一个幽微的空间,这一空间与大时代如火如荼的革命空间呈现一种出错位的存在。这些“陈腐的、阴暗的”物质化词语在王小波文本的大量使用,无疑增强了这一“幽微空间”的力量,并最终与“革命空间”形成对抗性和某种拆解作用,并形成一种美学风格。这也是我们在阅读王小波小说时,虽然明明知道他在写“革命”和“革命时代”,但又总感觉他的“革命”和“革命时代”和那一革命完全不同的基本原因。他会让你犹疑,让你颇费思量,进而产生思维上的晃动和真正的思考。
房伟非常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在这本书中,房伟对王小波小说里面最细微元素的来源都作了细致探讨,这不单是对作家创作细节的把握,也是对小说美学元素的还原,犹如密径,唯有仔细探察的人才能够发现。
再譬如,王小波在《革命时代的爱情》中描述“大炼钢铁”的情形,“我顺着那些砖墙,走到了学校的东操场,这里有好多巨人来来去去,头上戴着盔帽,手里拿着长枪。我还记得天是紫色的,有一个声音老从天上下来,要把耳膜撕裂,所以我时时站下来,捂住耳朵,把声音堵在外面。”
这显然是一个儿童视角,与王小波本人的童年经历相一致。1958年的人民大学的操场,和其他地方一样,也工作着无数个小高炉和炒钢炉。整个北京也陷入了“大炼钢铁”的狂欢。王小波以儿童眼光来看这一场宏大的运动,头盔,长枪,巨人,这都是典型的童话式意象,也有着堂吉诃德式的夸张与滑稽,而紫色的天空,则成了梦境的代表,这些描述自然地把“大炼钢铁”变形化和夸张化。房伟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处理方式,它有效避免了生硬的说教和概念植入,将理性精神与美学超越结合一体,也避免了新时期以来形成的文学规范在意识形态和美学特征上的制囿……铁狮子一号阴森恐怖的地牢已潜伏到了记忆深处,而废弃的高炉遗址,成为王小波有关成长记忆的隐秘圣地。这里有童年的幻想,也有隐秘的伤害,这里有紫色的天空,巨人,长枪,钢铁。而这些东西,像流星一般出现在历史,又很快被遗弃与遗忘,成为历史的幽灵。”④而这些,也正是王小波小说美学的基本底色:怪诞、夸张和狂欢。
从作家对词语的使用,回到作家的成长环境,再从作家的成长环境回到对词语的分析和美学的形成,房伟这样一种回环往复的考察,包含着对作家心理和性格成长的探秘,但更多的却使我们对王小波的世界有更加感性的和深刻的理解。
这样一种空间性的探讨,从学理上讲,并非完全是一种对位的关系,因为并非什么环境下一定生长出来什么人,而是同一环境下一定生长出不同的人。但它又具有意义,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作家成长内部的多种路径。
从整体而言,《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不只是研究王小波的美学和成长,其实也是回到那个时代,重新还原历史语境,探察那个时代的多条通道。以王小波为契机,房伟也在探讨政治与人的冲突,生命的顽强与自我的选择,进而探讨文学以何种方式来达到一种澄清。
王小波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可能被所有读者和研究者注意到。每每涉及此,王小波总是犀利尖刻,一针见血,但这一点,并非来自于皇天知识的培训,而来自于作者对人类自身经验的重视和肯定。这与他前面写“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感觉是相一致的。真正的理性其实很简单,尤其是对于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来说,就是“回到常识”。王小波的杂文里有一个“奶奶”的意象,即经验和常识的象征。
他自己曾公开宣称对智力和理性更感兴趣,这一观点也常常使王小波面临质疑,认为他有很强的精英主义倾向。但是,如果把王小波放置到一个大的语境之中,就明白,这句话,几乎是一种呐喊,背后有对我们这一国度最为匮乏的思维的焦虑。他的思想里有复杂的辩证成份。同时,最应该注意的,也是王小波最重要的地方,即,他对于所有事物的说理都并非是斩钉截铁的,他只是通过艺术的形象来传达。这样,他所呈现出的艺术形象往往大于他想要传达的,他的句子随时随地充满着这样的“溢出”,让你有更多向度的感受与思考。也许,这正是文学的基本魅力。纯粹的说理很难达到这样的多重方向。
房伟对此的分析也很有意味。他没有纠缠于王小波的“理性”是什么,没有试图帮读者去确认王小波的正确性,而是依然回到文本中,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在文学中的呈现方式,“对王小波而言,大跃进运动成为其树立文学内涵和美学原则的一个出发点。正是大跃进运动,让王小波看到了理性缺失的荒诞。有趣的是,尽管王小波在杂文中,不厌其烦地以大跃进为例,讲解科学理性对中国人思维的重要性,但小说中有关大跃进的印象,却成了一些更为悖论化的美学形象,所有那些荒诞景观,都以‘儿童狂想’的美学形式出现。狂想之中,儿童对生命的好奇和对奇观场景的探究,都在历史的荒诞之中,显现出了宿命般的美学魅力。一方面,历史的荒诞成为理性缺失的反证,革命因违背常识付出沉重代价;另一方面,荒诞的历史,又成为某种独特的现代美学景观,并被儿童视角赋予了‘奇幻’的生命激情”⑤。“革命活动”变为“荒诞景观”,“大炼钢铁”则成了一场虚无怪诞的狂欢,这一意义指向本身就是一种批判和消解,这是王小波的美学形式所产生的力量。可以说房伟始终抓住经验、生活与美学之间的关系对王小波进行分析,这使得他的结论可靠,让人信服,同时,又能够跟随着王小波回到时代深处,重新去把握时代的内在脉络。
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既是一本作家的传记,同时,也借王小波的方法和美学,对中国当代思想史进行溯源式的回顾和梳理。王小波并非只是本体,还是方法论。
作为一个传记作者,他和传主之间到底该是怎样的距离和关系?有人说,传记作者太爱传主容易形成误区,容易讳疾忌医,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热爱,又如何能够如考古一般,匍匐在灰尘里,一点点找遗落在时间和空间深处的线索?不管如何,作为王小波热爱者的房伟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理性和严谨,没有过于夸大王小波的文学意义,也没有夸大王小波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的行为及行为背后的意义。譬如王小波的辞职。房伟认为,这一行为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世的行为。王小波1992年从人民大学辞去教职,并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房伟在文中考察了同时期其他作家的辞职情况,南京作家韩东、吴晨骏、朱文都在同时期辞了职。辞职当然是某种精神的显现,但同时,也并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实际上,1990年代初期,“自由撰稿人”“下海”这样的词语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是今天难以想像的,它已然形成某种潜流和象征。并且,稿费的增加和报纸杂志的商业化,都给自由撰稿人的生存带来一定空间。当然,相伴随的,就是写作上的自由度和独立性。这样客观的、深入历史语境的考察和结论并不会损伤王小波的独立性,相反,它能够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时代内部的精神状态。它是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所得,同时,也是对王小波形象的恰当叙事和还原。王小波是革命星空下的那个“坏孩子”,有他成长的空间、语境和特殊的话语形态,这些也造就了他写作的基本内容。以此为起点,他把握时代、政治、人性和文学,他是在一定历史空间中所诞生的叛逆者和破坏者。
在最后一章里,房伟以非常客观和冷峻的笔法对王小波死之后的“王小波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媒体、文青、李银河、书商等如何共同参与,掀起了旷日持久的“造神”运动,而那些否定、批评王小波的声音又如何此消彼长,始终存在。对此,房伟认为,“无论喜欢还是讨厌,王小波在我们的社会,正在变成一个‘神话’被超越,在他身上,负载了太多复杂的社会信息,也负载了太多怨恨、愤怒、喜爱、沉静与悲伤。”这一“造神”运动对于王小波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还很难判断。但毫无疑问,房伟的《革命星空的“坏孩子”——王小波传》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具有独立价值的通向王小波世界的道路。
注释:
①《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王小波形象接受境遇考察》,《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新华文摘》摘编);《杂文历史小说:穿越历史和现实悖论的一种可能——论鲁迅<故事新编>与王小波的历史小说》,《东岳论丛》2006年第6期;《在革命的星空下-王小波小说的“革命+恋爱”模式》,《东岳论丛》2012年第2期;《笑忘红尘顽童梦》,《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31日(《新华文摘》摘编);《从强者的突围到顽童的想象——鲁迅与王小波之比较分析》,《文艺争鸣》2003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论王小波小说的三重形象》,《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另类目光与另类的生存——王小波同性爱题材小说研究》,《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论王小波小说叙述视角“复古”与“创新”》,《兰州学刊》2008年第7期;《个人主义与群体否定——论鲁迅、王小波文化逻辑之异同》,《艺术广角》2007年第5期。专著《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世纪末语境下的王小波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②③④⑤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6页、第112页、第34-35页、第32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