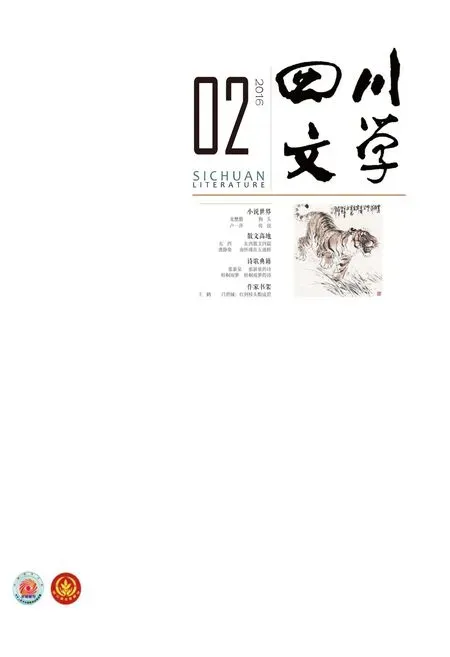传说
卢一萍
传说
卢一萍
一
大家把压缩干粮和雪梨罐头填进肚子,跨上了军马。虽然在漫漫长冬中苦熬的军马都很瘦,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雄健、骏逸,但大家第一次骑马,都有些激动。
分给我的是一匹白马。它是那些马中最瘦的,瘦得只有个骨架,当风敲打它骨头的时候,就能听到金属似的声响。这使我不忍心骑它,觉得会随时把它压趴下去。我打量着它,倒想扛着它走。
雪光映照着雪原,有如白昼,不时传来一声狼嗥。它凄厉的嗥叫使高原显得更加寒冷,我不由得把皮大衣往紧里裹了裹。
人马都喘着粗气,夜里听来像是高原在喘息。
到达克克吐鲁克已是夜里两点。边防连的营院镶嵌在一座冰峰下面。冰峰被雪光从黛蓝色的夜空中勾勒出来,边缘有些发蓝,如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刃,旁边点缀着几颗闪亮的寒星和一勾冷月。
营房里亮着灯,战士们涌出来欢迎我们。这些被大雪围困了五个多月的官兵把我们拥进会议室后,就激动地鼓掌。他们一直在等着我们。我们这些陌生的面孔使他们感到自己与外界有了联系。他们用那因与世外隔绝太久而显得有些呆滞的目光死盯着我们,一遍遍地打量,好像我们是花枝招展、风情万种的骚娘们儿。
因为高山反应,我一夜未能入睡。新兵们大多没有睡好。我们的眼圈发黑,眼晴发红。
吃了早饭,连长把我叫去。他最多二十八九岁,但我惊奇地发现没有戴军帽的他,头已秃顶。他黑铁般的脸衬托着他的秃顶,异常白亮。他掩饰性地捋了捋不多的头发,点了支烟,深吸了一口,问道:“说说看,你有什么特长?”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我突然想起了那匹白马,为了不让他失望,就答非所问地敷衍道:“我喜欢马。”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负责养马,连队的军马都交给你。”
“什么?”
“就这样吧。”连长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完,闭上了嘴。
我就这样成了克克吐鲁克边防连的军马饲养员,成了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马倌。
临离开连部时,我忍不住停住了,回转身去。连长马上问:“你还有事?”
“连长,能不能请问一下,克克吐鲁克,它是什么意思?”
“哈哈,这个……这个克克吐鲁克就是克克吐鲁克,它的意思,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
我搬进了马厩旁的小房子里。老马倌带了我一段时间,我从他那里学会了铡马草、配马料、钉马掌、剪马鬃、冲马厩、套马等“专业知识”。
每当我赶着马群出去放牧的时候,我都在寻找着来时在路上对克克吐鲁克的想象,但我没有找到一点与想象相符的地方,连狼嗥声都很难听见。
想到这里,我更加迫切地想知道它的意思了。我拽住了一个志愿兵:“老兵,你说说看,克克吐鲁克是不是死亡之地的意思啊?”
他严肃地摇摇头,说:“我们只把它当一个地名,管它的屌意思干什么!”
我又问别人,他们都不知道。
二
五月缓缓地到来,春天已被省略,阳光似乎是一夜间变得暖和起来的。我赶着马群走到雪峰下时,听到了大地在阳光里解冻时发出的巨大声响。
冰消雪融。不久,雪线便撤到了山腰上,营地前那片不大的草原上,萌出了浅浅的绿意。
我每天赶着马群,顺着喀喇秋库尔河放牧它们。
谁都注意到了,我从没把马群赶进营地前那块叫“可可吐鲁克”的小小草原。
没有了冰雪的衬托,营院便融进了那古老的、寸草不生的黑褐色山体里。那块绿色的草地便成了这里全部的美和生机。别的地方,都显得狰狞,它们虎视眈眈,似要把那美和生机一口吞噬。
从偶尔传来的牧歌声中,我已知道塔吉克老乡正骑着马,赶着羊群和牦牛从河川游牧而来。
我看着马群安详地吃草,任由风吹乱它们的长鬃。那匹皮包骨头的白马变化最快,它已经长上了膘,显露出了骏逸的风采。
我成了一个自由的牧马人,只是这种自由是由孤寂陪伴的。那时,我便唱歌,从小时学的儿歌开始唱,一直唱到最近学会的队列歌曲。那匹白马听到我的歌声,会常常抬起头来望我,像是在聆听着。有时,它会走到我的身边,停住,眨着宝石般的眼晴。不久后的一天上午,好像是受到了我歌声的召唤,我忽然听到了动人的歌声:
“江格拉克草原的野花散发着芳香,
我心爱的人儿他在何方?
我骑着马儿四处寻找,
找遍了高原的每一座毡房。
“喀喇秋库尔河怀着忧伤,
我来到了克克吐鲁克的山岗上,
我看到他骑着骏马,
像我心中的马塔尔汗一样。”
那是那个女孩子的歌声,那歌声是突然响起的,就在不远的地方。她竟然是用汉语唱的。那声音显然是高原孕育的,那么旷远、高拔、清亮,像这高原本身一样干净、辽阔。而那歌唱者呼出的每一缕气息都清晰可闻,使你能感觉到生命和爱那永恒的光亮。如果世世代代没有在这里生活,就不可能有那样的嗓音。
我像被一种古老的东西击中了,有一种晕眩,有一种沉醉。
歌声停止了,余音还在雪山间萦绕。天上的雄鹰一动不动,悬浮在雪山上;两只盘羊偎依着站在苍黑的巉岩上面,好像在庆幸它们中的一个没有远离。它们和我一样,沉醉在她的歌声里。
我循着声音,用目光搜寻那唱歌的人。但她好像在躲着我。我向她的歌声靠近一点,她就会离我远一点。我只能听见她的歌声,却看不见她在什么地方。
三
接连好几天,我都听到她在唱这首歌。
最后,我都把这首歌学会了,才看到了她。正如我料想的那样,她是一个姑娘,一个塔吉克姑娘。
我看到她的那天,她站在高岗后面一个小小的山岗上,岗顶一侧有几朵残雪,四周是高耸的冰峰,脚下是一小群散落的羊群。她头上包着红色的头巾,身上穿着红色的长裙,骑在一匹枣红马上,看起来,像一簇正在燃烧的火。她像是早就看到了我。我看她时,她朝我很响地甩了一下马鞭。然后,马儿载着她,一颠一颠地下了山岗,我再也看不见她了。
我感到一种与高原一样古老的忧郁,突然弥漫在了这晴朗、空阔的天地里。
那天,她再也没有出现过,她像是被那个山岗藏起来了。
第二天,我也没有看见她,只远远地听见了她的歌声。
第三天,我看见那个山岗侧面的残雪已经化掉了,我忍不住赶着马群向下游走去。
第四天,我看见她仍骑在那匹马上,风把她的裙裾和头巾拂起,向我相反的方向飘扬着。
我的心安静了,觉得受了抚慰一般,我坐在河边,看着哗哗东流的钢蓝色的河水发呆。
我不知道白马是多久离开我的,也不知它多久把姑娘那匹枣红马引了过来。它鞍辔齐备,只是没了那个有云雀般动人歌喉的骑手。
白马朝我得意地“咴咴”嘶鸣一声,像在炫耀它的魅力。
而我不知该不该把她的马给她送回去。
红马紧随白马,悠闲地吃着草,像是已经相识了很多年。
一会儿,她的身影出现了,她骑在另一匹光背的黑马上。在离我十几步远的地方,她跳下了马。黑马转身“得得”跑回马群。她微笑着,朝我走来。我看见了她帽子上的花很好看—那一定是她自己绣的,那些花儿正在开放,好像可以闻到花香;看到她背后金黄色的发辫上缀满了亮闪闪的银饰,一直拖到她凹陷的腰肢下;她的臀部那么紧凑,微微向上翘着;她的双腿修长,脚步轻盈;随着风和脚步飘动的裙子,使她看上去像会飘然飞去。我突然想,她要是能飞离这里,飞离克克吐鲁克这个苦寒之地,飞到云朵外的仙界之中,我定会满心欢喜。
她走近了,我看清了她红黑的脸蛋,蓝色的眼晴,薄薄的嘴唇。她看看我,又看看那两匹马,然后害羞地径直向那匹白马走去。
但我仍然蹲在河边,一只手仍然浸在河水里。我都忘记站起来了。
我担心白马认生,会伤了她,才猛地站了起来。而她已在抚摸白马优美的脖颈,白马则温顺地舔着她有巴旦姆花纹的毡靴,好像早已和她相识。
我在军裤上擦干了湿漉漉的、冰凉的右手,走过去看见她的脸正贴在白马脸上。
那个时刻,高原显得格外安静,只能听见风从高处掠过的声音,一只不知名的鸟儿从一棵芨芨草后面突然飞起,箭一样射向碧蓝的天空,把一声短促的鸣叫拉得很长。
我垂手立在她的身后。
好久,她如同刚从梦中醒来,看见我,羞涩地低下了头。
“这真是一匹好马。”她说。她的汉语有些生硬,但格外悦耳。
我点点头。
“它叫什么名字啊?”
“它没有名字,它是军马,只有编号,看,就烙在它的屁股上,81号。”
她好奇地转过头,看了看缎子一样光滑的马屁股,“哦,真的烙了一个编号,不过,这么好的马,应该有个名字。”她已不像原先那么羞涩了,嫣然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问有些腼腆的我,“那,你是军人,不会只有编号没有名字吧?”
我忍不住笑了。“我叫卢一萍。”
“卢、一、萍。”她像要把这个名字铭刻在自己的声音里,把每个字都使劲重复了一遍。
“你是克克吐鲁克边防连的?”
“是的,我是今年刚来的。”
“我叫巴娜玛柯。”
“我没想到你会用汉语唱歌。”
“我在县城读过书,前年,也就是我该读高二的时候,我爸爸得了重病,就辍学回来放羊了,不然,我今年都该考大学了。”说到这里,她很难过,“爸爸到喀什去看了好几次病,用了很多钱,但还是没有好转。你看,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家的羊卖得只剩下这么一点了。”
我看了一眼她家那剩下的三十来只羊,安慰她说:“你爸爸的病很快就会好的,等他的病好了,你还可以继续去上学。”
“我很想上学,但我今年都十八岁了。”她伤心地说。
四
老马倌年底就要复员了,他常常到营地前那片小小的草原上去,一坐就是半天。一个夏天下来,那片草原一直绿着。牧草虽然长不高,但已有厚厚的一层,像一床丝绒地毯。我一直希望那块草地能开满鲜花,但转眼高原的夏天就要过去了,连阳光灿烂的白天也有了寒意,所以,我也就不指望了。
有一天下午,老马倌让我陪他到草原上去坐坐,我默默地答应了。
他用报纸一边卷着莫合烟,一边说:“我看你最近一段时间像丢了魂儿似的,回到连里也很少说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连忙掩饰:“班长,没有,啥事也没有!”
“没有就好,你一定要好好干,干好了,说不定也能像我一样,捞个士官干干。”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你放心!”
“我相信你能干好。”他说完,把卷好的莫合烟递给我。
我说:“你知道,我不会抽烟。”
“抽一支没事的,你出去牧马,有时候好几天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抽烟,抽烟可以解闷。你就学学吧,抽了,我就告诉你克克吐鲁克的意思。”
我一听,赶紧接过烟,说:“班长,你快告诉我吧。”
他把烟给我点上,自己也慢条斯理地卷好一支,点上,悠悠地吸了一口,把烟吐在夕阳里,看着烟慢慢消散,望了一眼被晚晖映照得绯红的雪山,叹息了一声,嘴唇变得颤抖起来,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终于用颤抖的声音说:“我问过好几个塔吉克老乡,他们都说,克克吐鲁克……从塔吉克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开满……鲜花的地方……”
“开满鲜花的地方?”
“是的,开满……鲜花……的地方……”他说完,把头埋在膝盖上,突然抽泣起来。
知道了克克吐鲁克这个地名的意思,我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变得更加偏远、孤寂了。我认为那些塔吉克老乡肯定理解错了,即使是对的,那么,这个地方属于瓦罕走廊,在瓦罕语中,它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还挨近克什米尔,那么,它在乌尔都语中又是什么意思呢?说不定它是一个遗落在这里的古突厥语单词,或一个早已消亡的部落的语言,可能就是“鬼地方”的意思—因为在驻帕米尔高原这个边防团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这里海拔最高,含氧量最低,自然条件最恶劣,大家一直把它叫做“一号监狱”。
“开满鲜花的地方,这简直就是一个反讽!”我在心里说。
我决定去问问她。这里一直是她家的夏牧场,她一定知道克克吐鲁克是什么意思。
没有想到,她的回答和那些塔吉克老乡的回答是一样的。
“可是,这个边防连设在这里已经五十多年了,连里的官兵连一朵花的影子也没有看见。”
“那么高的地方,是不会有花开,但克克吐鲁克,就是那个意思。那里的花,就开在这个名字里。”
五
从那以后,我就好久没有见到她。我曾翻过明铁盖达坂,沿着喀喇秋库尔河去寻找她。我一直走到了喀喇秋库尔河和塔什库尔干河交汇的地方,也没有看到她的影子。她和她的羊群都像梦一样消失了,我最后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遇到过她。
有一天,终于传来了她的歌声,我第一次听到她的歌声有些伤感:
“珍珠离海就会失去光芒,
百灵关进笼子仍为玫瑰歌唱;
痴心的人儿纵使身陷炼狱啊,
燃烧的心儿仍献给对方……”
我骑马跑过去,刚把白马勒住,就问她:“呵,巴娜玛柯,这么久你都到哪里去啦?”
“有一些事情,我爸爸叫我回了一趟冬窝子。”我觉得她心事重重的,正想问她,她已转了话题,她高兴地接着说,“我去给你的白马寻找名字去了,在江格拉克,我给你的白马找到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我知道江格拉克离这里有好几个马站的路程,我想到她离开这里,原来是做这件事去了,放心了许多,我说,“那么,巴娜玛柯,你快些告诉我,你为它找到了什么好名字?”
“兴干。”
“兴干?它是什么意思呢?”
“这名字来源于我们塔吉克人的一个传说。说是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位国王的女儿,名叫莱丽。她非常漂亮,鹰见了她常常忘了飞翔,雪豹见了她也记不起奔跑;所有的小伙子都跟在她身后把情歌唱,不远万里来求婚的人更是没有断过,但她只爱牧马人马塔尔汗。不幸的是,她的国王父亲根本看不起他。
“马塔尔汗的马群中有匹叫兴干的神马,洁白得像雪一样。国王想得到那匹神马,但神马只听马塔尔汗的话,国王想尽了办法也抓不住它。没有办法,国王答应,只要马塔尔汗把神马给他,他就把莱丽嫁给他。马塔尔汗信以为真,把神马给了国王。国王得到神马后,却把马塔尔汗抓起来,关进了牢房。
“神马知道后,挣脱装饰着宝石的马缰,摧毁了国王的监狱,救出了自己的主人,然后又与国王请来的巫师搏斗,把巫师和国王压在了江格拉克的一座山下,而神马也被巫师的咒语定在了那座山的石壁上。
“马塔尔汗获救后,带着莱丽往北逃去,最后在幽静的克克吐鲁克安居下来,过上了恩爱幸福的生活。他们死后,马塔尔汗化作了慕士塔格雪峰,莱丽化作了卡拉库勒湖,他们至今还相依相伴,没有分离。而那匹白马至今还在江格拉克东边的半山上。远远看去,它与你的白马一模一样。”
“这传说真美,这白马的名字也非常美。”我说完,就叫了一声“兴干”,它好像知道自己就该叫这个名字,抬起头,前蹄腾空,欢快地嘶鸣了一声。
巴娜玛柯很高兴,她走到白马身边,用手梳理着它飞扬的鬃毛,好久,才说:“我很喜欢这匹白马,我可以骑骑它吗?”
“当然可以,它自从来到克克吐鲁克,还没有驮载过女骑手呢。”我爽快地答应了,“不过,我得给它装上马鞍。”
“不用的!”她高兴地跨上了白马的光背,抓着白马的长鬃,一磕毡靴,白马和她如一道红白相间的闪电,转瞬不见了。
过了好久,她才骑着白马返回来,在白马踏起的雪沫里激动地跳下马,说:“兴干真像那匹神马。”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双眸中闪烁着泪光。
六
营房前那块草原已变得金黄,那里依旧没有花开。
有一天早饭后,我正要把马从马厩里赶出来,老马倌突然从外面冲进来,激动地说:“草原上……草原上的花开了,快……你……快跟我去看看!”他的声音都沙哑了。
我想他肯定是希望那草原开满鲜花想疯了。我说:“那里草都枯黄了,怎么会有花开呢?”
但他拉着我,硬把我拽到了草原上。我果然看见有一团跳跃的红色!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屏住了呼吸,疯了般扑过去,我发现那是用一方头巾扎成的花朵。
—那是巴娜玛柯的头巾!
我哽咽着说:“这是……这里开放的惟一的花朵……”
老马倌早已泪流满面。“真不知道……这花……该叫什么名字。”
“巴娜玛柯,巴娜玛柯……这朵花的名字叫巴娜玛柯……”我喃喃地说。
这朵用头巾扎的花一定是她今天一大早放在这里的。我把马赶到河谷里,就赶紧去找她。
在明铁盖达坂下,我看到她一个人信马由缰,正沿着喀喇秋库尔河谷往回走,我看见她长辫上的银饰闪闪发光。她好像没有听见白马急促的马蹄声,也没有回头。我赶上去,和她并驾齐驱时,她才转过头来,对我微微笑了笑。
“巴娜玛柯,那朵花真好看。”
“但那里只有一朵花。”
“一朵花就够了,因为它永不凋谢。”
“但就是那样的花,有一天也会枯萎的。”她有些忧郁地说,然后,转过头来,问我,“你喜欢克克吐鲁克吗?
“还说不上喜欢,也许呆久了就会喜欢一点。”
“等你喜欢上了那个地方,那里就会一年四季开满鲜花。但那些花儿是开在心里的。”
“那么,克克吐鲁克应该是一个属于内心的名字。”
“是的。只有开在心里的花儿,才永远都不会凋零。”她的眼睛有些潮湿。“你知道吗?我的名字是从我们的一首歌里来的,你想听吗?”
“当然想。”
“那我就唱给你听,冬天就要来了,我们不久就要搬到冬窝子里去,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唱歌了。”她说完,就唱了起来—
“巴娜玛柯要出嫁了,
马儿要送她到远方;
克克吐鲁克的小伙子啊,
望着她的背影把心伤……”
她唱完这首歌,像赌气似地,使劲抽了一鞭胯下的红马,顺着河谷,一阵风似地跑远了。
七
从那以后,我更想见到她。但整个喀喇秋库尔河谷空荡荡的,只有越来越寒冷的风在河谷里游荡。
冬天就在四周潜伏着,这里一旦封山,我要到明年开山的时候才能见到她了,想到这里,我觉得十分难受,忍不住骑着白马,游牧着马群,向喀喇秋库尔河的下游走去。我又一次来到了喀喇秋库尔河和塔什库尔干河交汇的地方,但我连她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我在那一带徘徊。我常常骑着我的白马,爬到附近一座山上去,向四方眺望。但我只看到了四合的重重雪山,只看到了慕士塔格峰烟云缭绕的身影,只看到了塔什库尔干河两岸金色的草原,只看到了散落在草原上的、不知是谁家的白色毡帐和一朵一朵暗褐色的羊群。
那些天,我感觉自己像个穿着军装的野人。饿了,就拾点柴火,用随身携带的小高压锅煮点方便面、热点军用罐头吃,渴了,就喝喀喇秋库尔河的河水,困了,就钻进睡袋里睡一觉。我把马拌着,让它们在这一带吃草,准备在这里等她。虽然我作为军马饲养员,可以在荒野中过夜,但我是第一次在外面呆了这么久。
玻璃似的河水已经变瘦了,河里已结了冰。雪线已逼近河谷,高原的每个角落都做好了迎接第一场新雪的准备。
头天晚上我冻得没有睡着,我捡来被夏季的河水冲到河岸上的枯枝,烧了一堆火,偎着火堆,呆了一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梦见一朵白云承载着巴娜玛柯和她的羊群,飘到了我的梦里。我高兴得醒了过来。没有太阳,蓝色的天空已变成了铅灰色。我像一头冬眠的熊,从睡袋里爬出来。我先望了望天空,看了看那些快速飘浮的云。我在云上没有看见她。我想,我该归队了。但我不死心,我涉过了塔什库尔干河,骑马来到了靠近中巴公路的荒原上,再往前走,就是达布达尔了。马路上已看不到车辆,只有络绎不绝的从夏牧场迁往冬牧场的牧人。他们把五颜六色的家和家里的一切驮在骆驼背上,男人骑着马,带着骑着牦牛怀抱小孩的女人和骑着毛驴、抱着羊羔的老人,赶着肥硕的羊群,缓慢地行进着,像一支奇怪的大军。
我骑马站在公路边的土坎上,看着一家一家人从我脚下经过。眼看太阳就要偏西了,我还没有看见她,正在失望的时候,我胯下的白马突然嘶鸣了一声,然后,我听到了远处另一匹马的嘶鸣,我循声望去,看见她和她的羊群像一个新梦一样,重新出现了,我高兴得勒转马头,向她飞奔而去。
她看见我,连忙勒马等我。我一跑拢,她就问我:“冬天已经来了,你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想……”
我突然有些害羞,正想着该怎么回答她时,一匹马向我们跑了过来,马鞍两边各有一条细瘦的腿,由于马是昂头奔跑的,我没有看见那人的身子。待马跑到了我的跟前,马被勒住,马头垂下去啃草时,我才看见了那人短粗的上半身。他的脸也是又短又瘦的,一副尖锐的鹰钩鼻几乎占去了半张脸。他在马背上不吭气,只是死死地盯着巴娜玛柯。
巴娜玛柯指着他,对我说:“这是我的丈夫,我上一次离开你不久就和他成亲了。他们家的羊多,我爸爸的病需要用羊换钱。”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穿着已经变了,她的辫梢饰有丝穗,脖子上戴着用珍珠和银子做成的项链,胸前佩戴着叫做“阿勒卡”的圆形大银饰,库勒塔帽子上装饰着珍珠和玛瑙。这已是一个已婚女人的装束。我像个傻子,僵在马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天就要下大雪了,你赶快回连队去吧,这里离连队要走好久呢。”她说完,想对我笑一笑,但没有笑出来。她转身追赶羊群去了。那的确是很大一群羊,至少有三百只。
八
大雪已使克克吐鲁克与世隔绝。有一天,我正吹着鹰笛,连长过来了。连长说,走吧,大家正讲故事呢,你也进去讲一个。
我讲了巴娜玛柯讲给我的关于神马的传说。
有几个老兵听后,“哧”地笑了。连长说:“你小子瞎编呢。”
我说:“我是亲自听一个塔吉克老乡讲的。”
“你肯定在瞎编,那个传说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连长说完,就讲述起来,“我告诉你正版的传说是怎样的。说是很久以前,塔什库尔干地面上本没有这么多雪山,到处都是鲜花盛开的草原。圣徒阿里就住在草原上。他有一匹心爱的白马,那是他的坐骑。平日白马在草地上吃草,悠闲地奔跑。不料心怀妒意的魔鬼设下毒计,使白马在阿库达姆草原误吃毒草,昏昏睡去,未能按时返回,结果误了阿里的大事。阿里很生气,变了好多座大山,压在草原上,并将白马化作白石,置于一座山的山腰,以示儆惩,并将魔鬼藏身的阿库达姆草原化成了不毛之地,然后愤然离去。从此,这里一改原貌,成了苦寒的山区。哈哈,这才是兴干神马的传说,这里的乡亲一直都是这么讲述的,《塔吉克民间故事集》里也有这个故事,连队的阅览室就有这本书,不信你去看看”
我听后,愣了半晌,然后,走出连队俱乐部,冲进马厩,抱着白马的脖颈,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