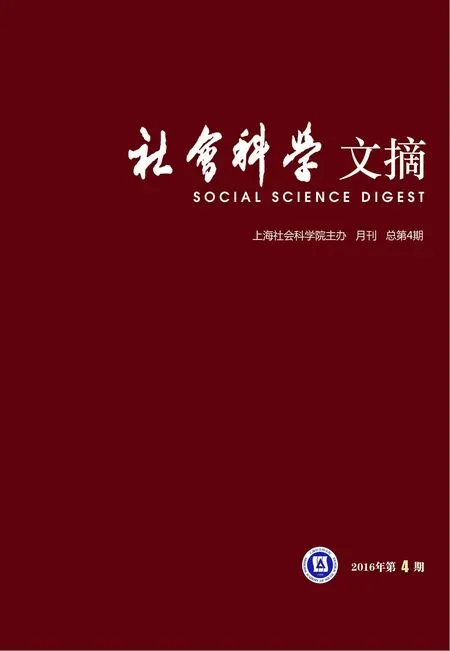现代性批判及其限度
——对几种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质疑
文/成林 谌中和
现代性批判及其限度
——对几种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质疑
文/成林 谌中和
现代性不是完满性,它当然可以批判。但现代性批判并不天然正确,它有其无法逃匿的限度。鉴此,本文将质疑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工业文明中的生产、消费和所谓文化工业的一些批判,认为这些流传久远、几被视为楷模的现代性批判在逻辑完备性与现实合理性等方面均有明显欠缺。
卢卡奇所谓“可计算性和合理化原则”的生产
卢卡奇对现代工业生产批判激烈,但他剑锋所指,却伤害了科技进步条件下所必然要求的劳动组织原则,比如理性与效率、精细的分工等等。按卢卡奇的逻辑,社会生产力水平越是提高,劳动组织原则就越是反动,劳动者就变得越是异化。即是说,人的异化随着科技理性的进步而愈演愈烈。卢卡奇认为机器大生产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罪责:首先,工业生产体系具有严密的分工和内在规律,它是由“可计算性”的效率原则所决定的。其次,科技进步使人和人的关系转而为物和物的关系所掩盖,物的价值不断上升而人的价值不断下降。最后,工业生产体系把遵循机器规律的行为尊奉为一种责任伦理,使人形成操作性的思维方式,从而丧失了把握社会总体和本质的能力。
但是,其一,分工是效率的必然要求,而效率是自由的基本前提。把服从分工的要求看作一种异化,其现实合理性何在确实让人无法理解。难道只有每个人都完成一切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其主体地位才不至丧失?难道只有更加落后的分工、更加迟钝的工具和更加辛劳的生活才能确保人的主体地位?难道和产品的整体联系不是表现在最终对产品的占有和支配上,不是表现为日益增多的闲暇时间,而是主要表现在对产品的制作上?
其二,难道有任何一种生产劳动不是由“可计算性”效率原则决定的而是可以根本不计效率的吗?就连雇佣劳动者也永远都在计算效率,他很清楚没有效率就没有工资收入。如果他的工资收入和效率不成比例,那就应该批判制度安排,而不是批判“可计算性”的效率原则本身。就是说,在这里,政治哲学应该关心的问题永远只是“谁的效率”,而不是它无权过问的任何东西。
其三,所谓颠倒人与物的关系,无非只是说人与人的直接依赖关系现在采取了物作为中介而演变成一种普遍的交换关系了。马克思充分肯定这是一种进步,因为这至少意味着赤裸裸的对人的直接践踏减弱了,人的自主性有所增强,尽管这种自主性依然隐藏在物的背后。如果一种批判的内在逻辑反而要求减少自由总量的生产而去强调失去物质基础的虚幻的主体性,就像对“物的依赖关系”这种进步所作的指责那样,那确实无法让人接受。
其四,“由操作性思维方式生成的责任伦理”是否确实会导致人们丧失卢卡奇所谓“把握社会总体和本质”的能力?如果把握社会总体和本质的能力不是某种神秘的东西而只不过就是追求真理和更加美好生活的能力,那么人们没有理由因为对机器规律的遵从就不去反诘制度创设和不去要求更多的自主性,也并不必然因为局部的机械劳动就只能养成操作性而不是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最近300年的世界历史实际上证明了这一点。
对所谓“可计算性和合理化原则”的那种伤及科技理性的批判是虚无的,因为这种批判要么混淆了遵从规律和坚持主体性的关系,要么颠倒了自由生产和制度分配的关系,从而内在地要求降低效率也即减少自由总量,这最终只会使得人的主体性丧失得越来越多。
所谓“消费社会”和“虚假的需求”
据鲍德里亚所言,由于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西方世界由此进入到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是一个堕落的坏的社会,因为消费社会的消费不再仅仅具有满足人们基本生理需要的功能,它还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意义,比方身份的认同、自我价值的确证(包括炫耀)等等。这种消费再也不那么纯洁了,它变成了感官放纵和物欲横流,人们沉醉于被商业广告操纵的消费狂欢中而丧失了自我和批判精神。马尔库塞还特意提出了“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这对概念,指出资本和利益集团为了追逐利润,不仅不去利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财富促使人们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且还通过广告等大众媒体控制和支配了人们的需求,造成了对人的“额外压抑”。因为这种需求并不是人的真实需求,而是服从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虚假需求,其内容和方向都是被资本所操纵的,其核心是把追逐物质生活享受作为幸福和自由来体验,它最终必然导致人们异化成为只知道追逐物质生活享受而丧失对自由和解放等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
鲍德里亚和马尔库塞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在对资本逐利本性及有意无意间消蚀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揭露等方面,确有睿智及独到处。但是,还应当看到:消费和需求的功能从来就不只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个人或集体的生命意义”理所当然就应该包括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的确证。史前时代的远祖,即使佩戴鸟羽头饰,不也在追求某种自我价值的确证和身份认同吗?除非一个人贫困到置办不起任何衣物,否则他的穿着就一定不只是为了御寒与遮羞,他就一定还想获得某种体面,这当然就是生命的重要意义之一,也是自由的题中必然之义。这样的消费不是丧失了自我,反而正是自由能力增强的表现,反而正是自我的有力确证,除非鲍德里亚们理解的自由纯粹只是某种神秘的精神生活或禁欲主义。
以资本主义批判为己任的鲍德里亚或马尔库塞们,当他们将消费社会带来的平等趋向和自由进步批判为被特定利益所操纵的病象时,当他们以某种方式要求回归清教式的“储蓄、劳动、遗产”等内在的禁欲主张时,他们是否察觉到了,这种批判反而比消费主义更有可能“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
人们之所以能被控制和被支配,只不过因为人们需要适应环境以追求更多自由,因为离开任何环境控制的那种自由决不存在。但我们不能控制一个根本不能控制的东西,资本家的广告之所以能够控制人们的消费,那只是因为人们本来就想消费。人们通过消费确证自我的价值,并且也通过消费让更多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除了变态的浪费、不必要和幼稚的炫富、完全不考虑购买力的自杀式消费等情形,这里没有太多需要批判的地方。
“消费社会”是一个准确的并有思想意义的提炼吗?难道更多更好的消费不是只能建立在更多更好的生产之基础上吗?难道更多更好的生产和消费不是标识着自由的进步反而标识着自由的萎缩吗?以此观之,如果所谓消费社会确实是真的,那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坏的社会,而所谓虚假的需求归根结底其实也并不虚假。因为,只要没有专制权力剥夺人们的自主性,只要社会是开放的和信息公开的,就不会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虚假的需求。
所谓“文化工业”
法兰克福学派在国内学界造成持久影响的“文化工业论”有如下几个主要思想:
其一,认为文化工业用其大众消费的无批判性本质,实现了对精神生活的全面控制。但大众文化并非真的毫无批判和照单全收,只不过那种批判或许缺乏条理与系统性,很多时候或许还是“理性的狡计”在起主导作用。
其二,认为文化工业把人的兴趣处理成肤浅庸俗的失去个性的时尚。但如果我们依然相信人的理性和反思性,肤浅庸俗和失去个性的时尚就既不会持久也不会控制得了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倾心的时尚,包括一些文化精英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追捧。但精英们可能并不认为追捧法兰克福学派也只是一种时尚,其在本质上和另一群人追捧某首歌曲没有区别。也许马尔库塞或哈贝马斯真正的关切在于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时尚乃是基于资本强权的压迫,而不是自由意志的理性选择,就像他们把科学技术也看作某种乐于被人服从的意识形态并且总在制造“虚假的需求”一样。这种泛意识形态指控看起来很有新意,但其内在逻辑推演开来,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置身于意识形态批判之外了。
其三,认为文化工业抽空了精神生活的内敛、反省、沉思等内在活动,使精神生活平面化和物像化,从而丧失了应有的内在丰富性。这个指控对人的精神生活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似乎在成为老庄之前人们就不配享有精神生活。文化工业并不包办代替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一个人也完全可以选择回避文化工业的某些影响。它也并没有通过某种专制使得所有的人都别无选择,它没有规定只能收看电视剧、相亲节目而不能阅读哲学。相反,它把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展示出来让人评价和选择,它完全可以培养沉思,只要一个人真的愿意沉思。它让那些毫无沉思习惯的人也可以比从前得到更加充分的信息,从而使得更加深刻的反省成为可能。
如果学术思想本来就应该关怀现实,那么笔者必须指出,当下中国经济需要更多更好的可计算性和效率原则,需要更强劲的消费而不是农业时代那种顽固的储蓄观念,需要真正繁荣发达的文化工业。中国不是欧洲和美国,它有自己特殊的烦恼和关切。离开生活实践的真实语境去讨论别人的烦恼并把它们看作自己的烦恼,这种情形与学术奴性相去不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自《哲学动态》2016年第3期;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4XZX00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13YJA720003)的阶段性成果,并受浙江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研究创新”团队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