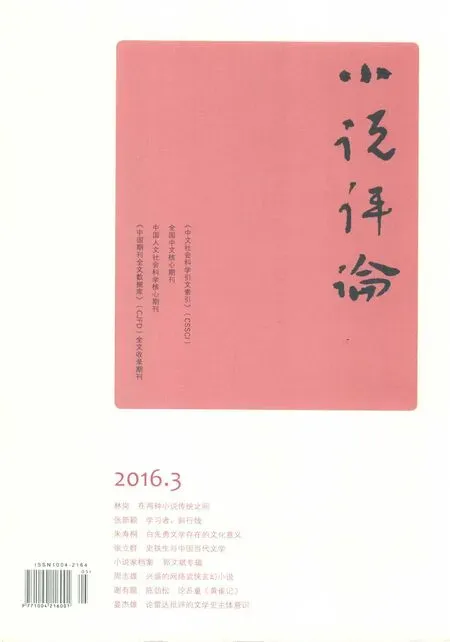郭文斌论
田 频
郭文斌论
田 频
回归、重建“精神家园”,是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愈渐强烈的精神需求。对理想家园的憧憬和寻找,是文学责无旁贷的责任,也是五四以来鲁迅等知识分子一直苦苦追寻的“乌托邦”梦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应该让自己成为“烛照人类前行的灯火”。这盏“灯火”在宁夏作家——郭文斌笔下得到了传承。
“安详”哲学——回归之路
作为地球上万物之灵长的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关注自己的命运,探索自己心灵世界的奥秘。中外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就是因为它们给人类提供了一片精神的绿洲,让在空虚和孤独中精神漂泊的人们得以重回“精神家园”。所谓“精神家园”,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精神支撑功能的精神文化系统,它是人类灵魂的港湾和精神的栖息之地。然而曾几何时,这块圣洁的“精神家园”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逐渐沦丧,以至难以寻觅。现代工业文明的先进成果,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日渐空虚:暴力、乱伦、抢劫等丑恶现象愈见加剧,人类正面临交流的失语和精神上的危机。当现代化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席卷着世界每一个角落时,当物质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时,人们该以何种方式寄托精神,滋养灵魂?如何回到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郭文斌用他的“安详”哲学为我们搭建了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康庄大道。
郭文斌于2006年提出“安详”哲学,他的作品《寻找安详》,如天籁般纯净安详,被誉为具有安妥灵魂、温暖人心的力量。 何谓“安详”?正如郭文斌在作品中描述,“安详是一种不需要条件作保障的快乐,它是一种根本快乐、永恒快乐、深度快乐。旨在帮助现代人找回丢失的幸福,让人们在最朴素、最平常的生活中找到并体会生命最大的快乐。安详既是生命的方向,也是生命的目的。它既可以让富者贵,也可以让贫者尊。它是对人的终级关怀。”说到底,“安详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①这里的“家”,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精神家园”,安详是通往此地最近的路。对安详的理解,浸透着作家对生命的体悟,凝聚着作家对人生的哲思,体现了一个行者在经过心灵的万重苦旅之后的灿烂涅槃。隐含在文字背后的安详的力量,如黑夜闪烁的星光,将带领那些迷失了方向且正在困境中迷茫、徘徊的跋涉者走出心灵的沼泽,为他们照亮回家的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承志用他一部辉煌壮烈的民族史诗——《心灵史》,让世人认识了哲合忍耶这个生长于西北大地上的穷人宗教教派。通过他们勇于牺牲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张承志为自己找到了心灵栖息的港湾。同样以西北大地为创作背景,郭文斌用他“洋溢着浓浓艾香”的“小说节日史”创作体系,让世人阅读到了同属于西北大地上的一种诗意的美好,并借助“安详”哲学,一步一步将现代人带入寻找人类最终的灵魂归属地——“精神家园”。
最初提出“安详”哲学,用郭文斌自己的话说,“纯属客串”。在2006年前后的一段日子,他发现传媒上的主要位置多是关于“天灾人祸”的报道,触目惊心。于是他不停地思索这个地球到底怎么了?最终得出结论:天灾是因为大地失去了安详,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了安详。针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弊病,郭文斌提出了“安详”哲学。但是不久他发现自己的“安详学”如空中楼阁,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做支撑。于是,郭文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诸如《论语》《弟子规》《了凡四训》等经典的研习,并且密切联系现实生活,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完善了“安详”哲学。在《寻找安详》一书中,郭文斌用“给、守、勤、静、信”五字箴言指引人们怎样才能走进安详,获得安详。“给”就是劝说人们要奉献自己,回报社会。融化“自我”这块坚冰,清除这一通往安详道路的最大的障碍。“守”是让心归到本位,让行归于伦常。通俗来讲,就是回到“现场”。“现场感”的提出,是获得安详的一个重要方法。“现场感”意即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或者说的话中,是一种身心全然在场又被“感”的状态,“这时”“这事”同时和“身”“心”“感”发生关联。只有拥有“现场感”,我们才能把生命变成和谐,把生活变成诗意,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和安详。“勤”意味着行动力,它强调的是从生活中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中的每一个细节做起,不放过每一个因缘。“静”不仅是一种生命力,还是一种跟踪力、观照力、觉察力,更是一种回家的方式,是一叶可以带着我们回家的美丽扁舟。拥有“静”,我们才能感受到世界的富有和美丽,才能获得和谐和幸福。“信”,是道德,是伦理,是因缘,是程序,它要求人们去行善。通过郭文斌的解读,读者领悟到获得安详的途径:“通过‘给’,我们把心路腾开,把心的空间放大,从‘小我’转变到‘大我’;通过‘守’,我们回到现场,回到本质,回到根;通过‘勤’,我们给自己不断‘升级’,同时不给习气以空间和机会;通过‘静’,我们的心湖能够映照明月,能够明察秋毫;通过‘信’,我们的心得到大定。”②最终,通过“给、守、勤、静、信”,我们走进安详,获得安详。
故乡——“精神家园”的地基
书写故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幅员辽阔,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长期影响,形成各地特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当作家描写自己故乡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把故乡的地方特色表现出来,故乡既是作家们的写作资源和思想资源,同时也是其在写作方式上的自觉追求。这类以故乡为创作母题的小说,以其丰富真实的生活内容、绚丽多姿的地方色彩,赢得读者的青睐。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沈从文,用他绚丽多姿的笔触向世人描绘了一个神秘、绮丽、野蛮的湘西世界。另外还有赵树理的“山西小说”,贾平凹的“商州小说”,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等,都书写了他们各自迥异的故乡。郭文斌继承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书写故乡的传统,在书写故乡西海固时,有别于人们对于西海固贫瘠、落后的固有印象。他最想突出的是西海固人们对生活美好、诗意的追求。汪曾祺曾说,“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③郭文斌用他的小说实践着使世界更诗化的梦想。他对记忆中的故乡“提纯”,用优美、诗意的笔调来滋润故乡西海固这片干涸的土地,旨在把西海固作为构建自己“精神家园”的地基,在自己的文学王国中建立一个超然淡泊、宁静和谐、充满爱和安详的世外桃源。
对于“精神家园”的寻找,鲁迅作为一个启蒙者,选择的是往前走,有着“绝不转回去”的决绝;而郭文斌却选择了回归,把找寻的目光投向了生他、养他的故乡。郭文斌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以故乡——西海固为背景,书写故乡的事和故乡的人,浓厚的故乡情结,一直贯穿在他的主要作品中。如作者曾发表的《吉祥如意》《大年》《开花的牙》《永远的堡子》等作品,都是描写发生在这片充满诗情画意的土地之上的故事。郭文斌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人类不宜生存之地——西海固度过的。西海固位于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其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贫穷、饥饿、灾荒伴随着西海固人的成长历程。长久以来,作家们对西海固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的书写是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他们用自己的笔描写着西海固“贫甲天下”“苦甲天下”“旱甲天下”的景象。然而郭文斌在描写故乡西海固时,却秉持着一种温暖平和的情怀,对西海固苦难的自然生存背景的描写提升到了一种祥和的文化生存状态,使得他笔下的西海固充满了安详与温暖。虽然西海固人生活在贫瘠的黄土地上,生活在过年才能吃到白面馒头的村子,但是就是在这样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人们心中没有对苦难的抱怨和仇恨,作品中洋溢着的是自给自足的快乐、天人合一的安详。正如郭文斌所说:“对于西海固,大多数人只抓住了它‘尖锐’的一面,‘苦’和‘烈’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没有看到她深藏不露的‘微笑’。当然也就不能表达她的博大、神秘、宁静和安详。培育了西海固连同西海固文学的,不是‘尖锐’,也不是‘苦’和‘烈’,而是一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④他用平和的心态触摸、感受着隐藏于生活深层中的温暖和真实,在生活的苦难、困顿中发现美好和温情;在物质的贫乏、窘迫中寻觅真诚和诗意。
郭文斌结合自己的童年记忆和文学经验写出了对故乡西海固的热爱,对生活的理解,以及苦中作乐的生命激情和乐观情绪。在《大年》这篇小说中,郭文斌细细地回味了一家子过年的情境:
爹说,等你娘来了一块儿吃。五月六月就到厨房去叫娘。娘说,我正忙着呢,你们先吃吧。六月一把拽了娘的后襟子,把娘拽到上房里。娘说,我刚才把些馍馍渣子吃了。爹说,年三十么,一块吃吧。爹说这话时,五月端了一碗饭给娘,娘不好意思地接过,看了看,给爹说,我给你拨一些吧,我吃不完这些。爹说,你就吃吧。五月和六月跟上说,你就吃吧。说着,一人端起一碗长面,预备赛跑似的等爹和娘动筷子。⑤
这段关于童年往事的温暖回忆文字,让阅读者感到既辛酸又欣慰。大年中的这一家人,面对着物质资料极度短缺的现实,却相濡以沫,相互关心,沉浸在无与伦比的快乐当中,浓浓的亲情在困顿的生活面前显得尤为可贵。郭文斌写故乡西海固的苦难生活时,秉持着一颗温暖平和的情怀与超越此在的心态,在面对这些生存的苦难时,“苦而不痛,难而不畏”,把这些苦难视为人生存之“常”,以平静的笔触描述着这片土地上惯常的生存为艰。“贫穷就是贫穷,它不可爱,但也不可怕,人们可以而且能够像享受富足一样享受贫穷。贫穷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人们只能接受它,歌颂与诅咒都无济于事。”⑥这句话道出了郭文斌对贫穷独特的诠释,面对贫穷和苦难,郭文斌不仅写出了惊人的美好,更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命真谛的思考。基于这样的生命观,郭文斌的作品就具有了内在性、深刻性和超越性的特点。在苦难面前,作者没有被打倒或被文学异化,反而在创作之中开放出美丽和幸福的花朵,使深重的生命有了轻松的飞扬,这就是郭文斌不同于别的作家带给人们的震撼。
把故乡西海固作为“精神家园”的地基,作者不仅仅是出于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在这里,也是一种叙事策略,他引领人们走向归乡之路,回归本源,去寻觅生命原初的光亮。通过作家的笔,让消失了的宁静安详重新浮现,让曾经的美好永驻心田。故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乡,而是作者有意搭建的具有复杂意象和多重视角审视下的精神世界,它是郭文斌心目中人性最后的救赎地的象征,也是人类灵魂最后的栖息地。郭文斌在这种诗意美学的创造中达到了对生命的回归与超越,在淳朴、安详的西海固上,为人们重建了一个安详、和谐的“精神家园”。
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的梁柱
郭文斌并没有简单停留在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上,在把自己的故乡作为“精神家园”的地基同时,他把关注的视角直接潜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中,从民族之根中汲取养分,来建设“精神家园”的梁柱。如果说沈从文是用“爱”和“美”来搭建自己的“希腊小庙”,那么郭文斌则是用“安详”哲学为指引,用“传统文化”为梁柱,在故土之上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
郭文斌不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推崇者,对于传统文化,他始终怀着崇尚和敬畏之心。在其作品中,读者随时可以发现关于传统文化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之根,儒、释、道三家文化是其构成体系中的主流部分。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李泽厚所言,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起了任何思想学说所难以比拟匹敌的巨大作用。”⑦郭文斌创作的乡土题材的小说,渗透着浓厚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内容。长篇小说《农历》,全篇都洋溢着浓浓的儒家情怀。作者在小说情节植入了大量儒家文化思想及教育内容,爹对五月、六月的教育多选取儒家的文化信条。比如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慎终须尽三年孝,追远常怀一片心”;“非礼勿视”等等 ,体现了儒家价值伦理体系在乡土民间所起到的道德规范的重要作用,也使得小说自然显出浓厚的道德力量,让读者不由得追怀起孔子所向往和推崇的礼乐时代。此外,郭文斌的小说更多时候是呈现出儒、释、道三者互为融合的文化蕴涵:仁爱谦恭的儒家、顿悟超脱的禅家、逍遥自得的道家,三者皆融会贯通于作品之中。在《水随天去》这篇小说中,通过描写父亲水上行从正常到怪异,以至最后离家出走的反常行为,追问了生命的真谛,探索了人类挣脱物质和精神束缚的可能性:禅宗的顿悟是否可以使人们放弃“现实之有”,进入“精神之无”?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集儒、释、道三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传承,他的生存哲学与人生观游走于三家文化的长廊中,可以说,是三家文化共同塑造了父亲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父亲的仁爱、超脱等性格的塑造,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梦幻的面纱,传统文化也随之焕发出令人迷醉的光芒。
与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并驾齐驱影响、滋养着世世代代华夏子孙心灵的当属传统节日。这些年复一年、一成不变的传统节日风俗,用它自身神奇的力量,滋养着一个民族的血肉,支撑着人类的“精神家园”。优美、温馨的传统节日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而且在过节这种喜庆的氛围中,让人们体会到与当今世俗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感受到民俗的独特魅力。从最开始的《大年》,到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吉祥如意》,再到入围茅盾文学奖的《农历》,传统节日在郭文斌笔下获得了全新的生命演绎,他将自己的乡土生存经验集中表现在带有浓郁农耕文化气息的年节中,用文学的形式对传统节日做考量,逐步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形成了“小说节日史”的创作体系。
长篇小说《农历》,由十五个传统节日组成,书中按照时间顺序,以细腻明快的笔法,从新年的第一个节日“元宵节”一直写到年尾的“大年”,把各个节日中的纪念活动、程序、步骤等一一细细描写,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传统节日民俗的多彩风貌,堪称一部魅力四射的乡村文化百科全书。比如“元宵”要用荞面和荞杆做明心灯、吃长面、献月神;“干节”要燎干、打干梢、扬灰;“龙节”不能动针线、要换夹衣、围仓、剃头、敲梁劝鼠、炒豌豆;“清明”要买纸、做针线、上坟;“小满”要吃苦苦菜、稳麦穗;“端午”要发甜醅、门上插柳条、供神、采艾、佩戴红绳及香包;“七巧”要给牛找嫩草、给牛洗澡、晒书;“中元”要敬神唱戏、游村、还愿;“中秋”要下梨、挖土豆、烙月饼、献月神;“重阳”要抢山头、祭神、诵《孝经》;“寒节”要给已故的祖先烧送寒衣;“冬至”要祭神、吃饺子、守水、制《九九消寒图》、制画板;“腊八”要喝粥、供粥;“大年”要写对联、贴春联、上坟、祭神、泼撒、分年、贴窗花、守夜;“上九”灶火出庄,要请神、游庙等等。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传统节日中的点点滴滴,富有民族繁衍生息的厚重感,营造了一种小世界安稳吉祥的氛围。郭文斌对民俗的理解和运用,印证了户晓辉的论断,“民俗长期充当了寻求本真之物的一个工具,满足了逃避现代性的渴望。”⑧他用文学的形式切入乡村文化的根基与血脉,铺展出一幅生机勃勃的中国乡村文化长卷,完整细致而又充满风趣典雅地对民俗节日进行了回忆,引发人们重新关注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真正存在价值,进而对现代生活下人性异化现象做出思考和反思,重新唤起民俗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如童谣般的安魂曲为现代疲惫流浪的人建造精神的故乡,帮助迷惘、孤独的现代人找到心灵安放的栖息之所。
五月、六月这两个精灵般的孩童的参与,使得作品中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变得越发鲜活,充满了人间情趣和俗世风情。作者巧妙地用五月、六月相互诘问的方式展开叙述:“六月问,水为啥不争?因为水是君子啊。啥是君子啊?君子就是不争的人啊。那孔子的七十二位弟子都是水做的?哈哈,应该吧?”⑨再如:“忏悔就是洗心对不对?六月问。五月直起身来,看着六月。六月说,爹说手拿了脏东西要洗手,眼睛看了脏东西要洗眼,那心想了脏东西也要洗心吗?五月说,对啊,很对啊,赶快把你的心掏出来洗啊。”⑩这些看似简单、幼稚的对话,从这对未经尘世污染的姐弟俩口中说出,却蕴含着非常值得追索和深入研究的内容。这里,作者借用五月、六月的诘问,从少年这个人生最美好的时段切入古老、坚韧的乡村文化,引领人们更加深入思考人生,从而关注心灵的安放意义。郭文斌的作品有意淡化故事与情节,远离政治和时代,却汇入中国主流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民俗文化的静水深流,使人“感动得落泪”。《农历》描绘的只是西北地区一处乡村风俗画,但它讲述的却是生命的潜流和文化的根基。作者不遗余力地去展示故乡的民俗节日,婚丧嫁娶、礼仪节庆、吃喝拉撒等日常生活细节,并把这一切都放置在一个天人合一的世外桃源之中,为世人营造了乡土记忆中吸引着人们回归并重建的“精神家园”。
简言之,郭文斌的文学作品,具有清新脱俗的气质和感人至深的力量;“渗透着对青春生命,对黄土地上的生存图景,对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意义的现代思考。”⑪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没有苦难与悲痛,也没有欲望与暴力,只有人类苦苦追寻的快乐与安详。他怀着一颗赤诚的文学之心,用他独有的感性,坚守着纯净的文学理想,捍卫着文学的尊严与神圣,以“安详”哲学为路径,深入到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根脉之中,体会生命的本真意义。在遥远而偏僻的中国西北一隅,以传统文化为梁柱,为人类重建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让人类旅行已久的心在“安详”哲学的带领下找到回家的路。
田 频 暨南大学
注释:
①②郭文斌:《寻找安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第30页。
③汪曾祺:《使这个世界更诗化》,读书,1994年第10期。
④郭文斌:《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⑤⑨⑩郭文斌:《农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300页、258页、77页。
⑥史佳丽、郭文斌:《含泪的微笑》,文艺报,2004年6月8日第2版。
⑦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⑧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⑪钟正平:《苦难生存中的灵魂救赎》,当代文坛,2000年第6期,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