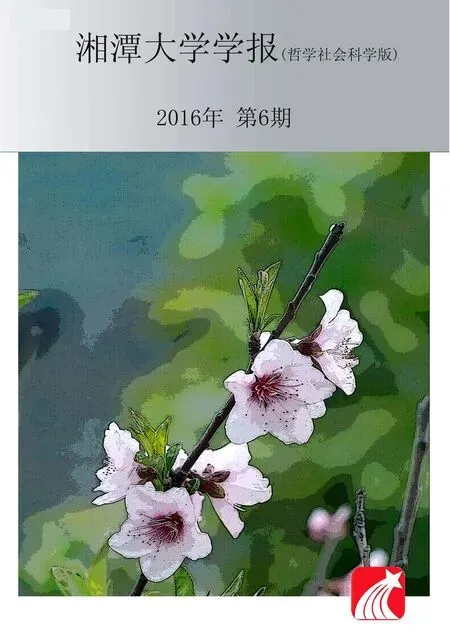语感的向度
——以“五四”诗歌翻译为例*
汤富华
(武汉纺织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0)
语感的向度
——以“五四”诗歌翻译为例*
汤富华
(武汉纺织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0)
语感范畴在人文学科领域鲜有理论介入,但现有的探讨还停留于感觉层面,大多是一种心理的表述。事实上语感的内涵不能只局限于语言的本能感觉(intuition),还有人们对语言的知识体系构建(sense)。语感的更高层次应该是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美的一种感觉(feel),即诗感。诗感是跨语言的,诗歌翻译就给出许多的印证。“五四”译诗催生了中国新诗,从而导致文学的整体革命,其效度与译者的双语语感能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语感的翻译向度与诗学向度分别做出阐述并详述了语感养成的内部机制。
语感范畴;翻译向度;诗学向度
语感范畴通常被人们口头提到,但鲜有人对之进行严肃的学科追问。语感不是指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感觉,而是指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产生的一种系统的感觉,这种感觉叫“语感”。
一、语感的内涵
语感的现象指语言行事的一种系统的感觉。叶圣陶、夏丐尊等在上世纪上半叶从语文教学实践中提出了语感现象。近些年,我国语文界及外语界的学者纷纷对语感范畴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探索,已有多篇论文论对语感范畴进行定义,从内涵、外延、表征以及语感养成等进行了尝试性的描述。但研究者们没有对语感范畴从系统论、结构论、关联论及本质内容等进行学科探索。语音音位方面的学说更是没有碰触,到目前为止有关语感范畴研究的博士论文不超过5篇,而且多半是教育心理学领域的论文,语言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几乎没有。
语感研究常被人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有些人甚至要求用统计测量的方法来定论,完全否定思辨研究途径。笔者认为,个人的感觉必须是从个人心里的感觉中去寻找。语感也是如此,只能从使用语言时记忆里寻找语感的蛛丝马迹。科学或绝对的科学只是一个目标而已。量子力学的“不可准确测量定律”就已经告诉我们,试图用统计测量方法得出语感的定论只是一个幼稚的想法而已。但我们始终感觉语感是存在的,而且它始终在引导着我们与人说话交流。那么语感到底是什么?
语感就是学习者多方位接触某种语言及其相关文化而产生的一种规律性的感觉。[1]22同时,语感也是语言的使用者对于某一种语言的各种场景的使用所具备的一种默认能力。而语能是一种语言全方位的使用能力,从层级来判断,它包含了表层与深层的能力。
在乔姆斯基眼里语言习得是心理学的事情,语言学习成为了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而韩礼德认为语言是社会学的范畴。语言学习成了语言发展(language development)。韩礼德观点表明了人是怎们通过语言活动而从个人变为了社会的一分子。[2]14
在二语习得理论中语感范畴不是普适的,语感应该分为母语语感与二语语感。[3]151语能(competence)不涉及更多具象,而是泛指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使用能力,我们说某个人语言表达能力不行时,我们会说“He is very poor in language competence”。当然日常口语会话不会这么讲,会说‘He is a little shy’,来指代他语言表达欠佳。语感则指的是语言活动的发生器,也可以说就是语言的生成器。到目前为止,它的原理对于语言学界来说还是一个谜。
母语语感是一种本能,相当于直觉(intuition),而二语语感则是一种知识的结构图式(sense),是可以有意识地去建构的,而母语语感是天生养成的。二语语感是可以当做知识训练而成的。[4]2-4
然而,语感的机制是什么,要素是什么,心理的又是什么?总之,语感概念非常复杂,难以着手。因为,研究者很难摆脱用语言谈语言的窠臼。到现在为止,语感范畴研究还没有重大突破,“语感”还是一个没有找到的“黑匣子”。
二、语感的养成
1.语感的结构与层次
如前所述,语感的辨析如借用英文词语会更加清晰。笔者认为,语感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本能的母语语感(intuition),这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一个是二语语感(sense),可以靠知识体系构建,可以培养而成。二是诗感,对语言美的感念(feel)。
诗感是语感的最高层次,诗感相当于人对艺术美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个体在语言艺术上的最高鉴赏力。笔者认为这种感觉即是个人的一种艺术鉴赏力,也是一种道的感应,这个道就是诗道,相当于茶道、书道。我们不妨借用古人严羽的定义来了解这个道德奥秘。
在《沧浪诗话》中严羽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5]26说到底“妙悟”就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产物。东方人讲究心境的宁静,静则生慧,而禅的智慧是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品质。它既是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对佛教文化的中国解读,也是佛家文化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具体说,诗道也就是“月下僧敲门”还是“月下僧推门”之间的一种游离。美就在于此,诗道的奥妙也在于此。人们所形成的这种诗感或者人们共同认可的诗道就是在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中沉淀下来的。
诗感的深层结构其实就是诗歌的观念。而中西诗学观自古就存有差异,但最终得以消解,翻译成了功臣,不同文本的交换与理解也就成为现实。翻译的功能有如此之大,其深层原因是翻译的颠覆力所致,而翻译的颠覆力就是语言的颠覆力。语言的诗功能通过翻译这个滤光镜发出缤纷的色彩。借助于诗学,语感的解析将会给出更为清晰明了的答案,通过翻译案列的分析,语感的表层与深层结构都将较为清楚地示例。
2.语感养成的模型
我们试图从语言学的途径解读语言能力及其背后的语感机制,从结构与形态来探索语感获得的捷径。笔者认同克拉申(Stephen D.Krashen)关于二语习得理论体系,其中自然路径(natural order)“可理解输入假设”以及“日进制”(I+1)[6]10-30的观点特别具有解释力。克拉申的“I+1”是指可理解的输入,也就是程度比学习者本人目前的水平稍高一点难度,从而让学习者能够接受。如果学习资料太难,则意味着超出学习者的接受能力,久而久之,学习者会自动放弃。这也就能解释许多人不能坚持学习一门外语的原因。
克拉申认为,第二语言的成功是习得(acquiered)的不是学得(learned)的。学习者应该全方位浸泡在目的语里,包括与语言相关的文化知识。
我们认为,二语学习者应该避免像学母语那样来学习第二语言。因为,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那是不可能复制的一种学习模型。母语学习是一种本能还原的样态。二语学习则是完全的知识学习,语感是不可以“兼容”的。具有日语语感的人要想获得汉语语感必须得从头来。
最近微信群里有一篇鼓励学习者以积极的心态参与会话活动的文章,其中一句话非常有说服力,外语教育应该是“Light the fire in stead of filling up the pail”。所以,还是谚语说得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们对什么感兴趣了,那么这门功课就有救了。语感的养成图示如下:

当然语感养成的绝对成因是无法完全还原的。只是我们将感性的知识与先天的本能有机地综合起来思考,则语感的原型显得容易理解了。
二语习得理论与实践始终难以有力地统一起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理清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的本质差别。虽然都是语言学习,但路径与效果完全不同。一个是本能的还原,也就是人的语言习得机制(LAD)的还原,二语习得包括外语学习只能是知识(sense)体系的建构, 而这种语感因人而异,有的人语言能力强,有的人则差。
母语学习指的是人从一出生就夜以继日地学习一门语言,而且是不知情的情况,是全社会来帮助养成的。换句话说,人不能说话则不能生存。聋哑盲人也得靠语言生存,即使是盲人也靠母语盲文来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二语习得或外语学习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就人类依赖语言的程度来说,母语是必需品,二语(外语)是奢侈品。当母语将所有的人一网打尽的时候,这种语言能力几乎就是一种本能,一种生存的本能。
关于学习过程,克拉申提到学习者本身就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Accuracy of self-correctness)。[6]104学习者自己知道自己目前的水平,因而只有他自己能判断什么学习是可理解输入(comprehensive input),[6]10因为路子对了,也就自动进入量变引起质变的路数,恰恰最能使得习得者走上语言习得的自然路径“natural route”。如此,二语习得中所需的语能与语感就获得了,自然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程式。
关于学习效度,克拉申甚至认为“在实际二语习得的过程中,二语习得理论以及应用语言学理论都不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语感。学习的效果在边学边会中产生”。[6]1以此来看语感的养成可能并不复杂。
至于语能与语感能力,一般来说,学习者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大多学习者的语感能力大多是边工作边学边自我完善,属于一种自主学习。贺拉斯对于语言的能力或者说一个诗人的语言能力在《诗艺》里有提及,强调诗艺的形成既要靠天赋还要靠勤奋。[7]158中国民间则强调“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量变引起质变在中国甚至是一个信念,这里实际上指的是要培养语言的最高形式,即诗的感觉:诗感,而这种感觉的形成应该是内化了的知识结构。关于这点,个人的自我意识起重要作用。严羽批判北宋的诗不是好诗,因为那是学而成的。[5]1想必严羽批的是北宋的诗多有模仿之气,无那种应是天上来的诗感或发自内心的对语言美的感念。
三、语感的翻译向度
很显然,用语言的语词去解读语感现象会过于抽象。通常,我们通过翻译、朗诵、写作、会话及辩论等语言活动来分析语言的重要范畴:语感。
翻译是语言转换的活动。但它毕竟是语言内的“跳动”,而这种跳动的能力背后就是语感。翻译领域的语言信息将会提供较为全面的语感信息图谱。
卡特福德(Catford)曾断言“翻译就是语言之间的变换活动,从一个语言文本转换成另一个文本”。[8]1这容易让我们觉得翻译就是什么东西简单地在语言之间移动而已,至于是什么在移动,我们是不得而知的。罗斯特(Robert Frost) 称:“诗歌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两种断言使得我们必须面对翻译的表层及其深层意义。[9]27
按卡德福的意思翻译是语言的转换, 真实情况是这样吗?翻译过程中遗失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只能是什么?
这些问题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翻译或转换的实体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它是语言承载的社会符号:语义。而语义转换则要求译者必定要有基本的翻译诠释力,这种力量就是一个人对翻译所涉及的双语语能与语感能力。它包含了人们对语言的基本理解力与语言的诗功能的深沉理解,除了语言的因素,还有诗学的因素甚至政治的因素。
翻译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处理能力,一个译者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将源语译成目的语。因此,翻译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诠释力。它牵涉到译者的双语能力,而这种以语言能力为主的能力未必是纯语言的,它还含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译者的双语能力总有一个是不及另一个的。也就是说译者对双语的语感是不匹配的。多半是母语好很多,外语差一大截。如果这样,翻译又是怎样发生的?所谓的对等又是如何可能的?翻译的深层结构到底是什么?
㉑㉒㉓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124、120页。
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无论什么翻译,对于译者来说,语言的能力是必须具备的,而且是双语的语言能力。我们暂且称之为“language competence”,[10]101乔姆斯基借用这个词来表达语言使用者使用一门语言的能力。他同时也使用了“performance”来表达说话人的具体语言表达,相当于索绪尔的 “parole”(utterance)概念,很显然人们会将语能(langauge competence)与语感(luanguage sense)两个词语弄混。如果我们将之层级化,那么语能是大于语感的。实际运用中不存在没有语感的语能,他们是相互依赖的,那么语感究竟是什么呢?
译者从事的语言活动说到底是一种很强的主体行为。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译者决定翻译的技巧及用词造句。一切翻译活动都是自主行为。客观地讲,译者的翻译行为因为双语的语能与语感不匹配,他只能进行无法逾越的活动,那就是:改写。而改写在翻译活动不再属于语言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尽管它是由于语感不够而导致的。因而一种改写的自主意识自然地产生了。
笔者曾在80年代给一家合成洗涤剂厂生产线做现场翻译,该生产线是从意大利进口的一氧化璜中和设备,说明书很多是英语写的,可是还有不少是意大利语写的。这种情况毫无办法翻译,只有借助现场的意大利专家从意大利语译成英语,再译成汉语。对于这种情况不是“资本主义企业”仗恃技术优势故意写成意大利语,或者说与权利话语没有关系。意大利专家的解释是负责该翻译的技术人员英语与意大利语语感不对称,到某些语句翻译不来时便顺手写成了意大利语,而且意大利语与英语同是印欧语系,基本差不多,就这样马虎应付了。这就是典型的因为语能与语感能力达不到匹配而发生的改写。
勒弗维尔(Lefevere)[11]41-50论述了改写与权力甚至操控有必然关系。笔者认为改写与权力的关系并不大。作为民间自发的翻译活动,改写的因果关系更多是语感能力所致。它也是译者一种自主的反应,无关乎政治。当然,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层面权力决定翻译的内容,不在此展开讨论。
四、语感的诗学向度
雅可布逊(Jakobson)断言:“诗学关注的是什么使得言语产品成了艺术品”,并称“诗学是语言学的一支”。[12]63按他的说法诗学关注的仍然是语言的问题。实际上,翻译的诗学问题还是语言问题,只不过是语言学的问题。对于语言问题,我们分析的是语言的各种功能,而诗学关注的是它何以如此。同时,诗感或者说诗道的探索都可沿着语言学路径出发并找寻其归宿,语感的诗学向度也就是语言的诗功能是何以生效的。
外语教育所提到的语感是可以像知识般地获得,它是一种任务型的学习模式,而母语语感是另一个话题。译者在双语语感不能匹配时,他自己是有策略的。行业间多半采取不成文的“母语优先”制,也就是翻译的目的语一定是母语。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作为最终的语言成品只有写成了母语才是合符语感的,才有可读性。如果译者将外语作为目的语,则连基本的语言可读性都没有达标。其中的原因仍然是语感问题。这种“母语优先”的做法,使得译者在理解原著上有很大的偏差,以至于翻译作品到最后成了改写品。
我国翻译史上就有卞之琳对李金发毫不留情的批评:“中文写作里处处夹杂了法文的李诗人竟连原诗的表层意思都不懂,也不理诗中的规范语法、普通格律,把它译得牛头不对马嘴,结果不知所云。”[13]186
李金发翻译了大量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作品,同时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也创作了不少异国风采的新诗,这种误译的结果使得不懂外语的读者以为李金发译的诗就是象征主义诗歌,尽管许多诗人贬低其文学才能,但他毕竟开创了中国象征主义诗歌新篇章,正如卞之琳如上所云:“李金发以他离奇的诗创作加翻译无意中为新诗现代化另外跨出了一条路。”[13]59-60
实际上,他们的议论焦点问题还是语感问题,李金发的成功在于他引进了中国诗坛没有的一种语体与语感,或者说一种语言的感念,这种感念唤醒了人们对语言美的追求与渴望。用象征主义的话说是李金发的翻译诗作或改写让读者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歪打正着地“应和”了,但从形而下的“器”来看,李金发的翻译“牛头不对马嘴”确实不符合诗歌的诗学要求,李金发的作品最后没有像徐志摩、郭沫若等人那样走入寻常百姓的“诗话”中,可能是李金发的双语语感没有过关,也就是诗感不美。
“五四”译诗不仅将不同的语体、语感、语式带进中国,它还消解了千年的旧体裁、旧文字还有旧的诗歌感念。“五四”译诗成功催生新诗的发生,其中成功的译者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卓越的双语语感能力使得他们的译诗非常轻松地被读者所接纳。从这点看,“五四”译诗成功催生新诗,译者的语感能力起了大作用。
翻译作为语言的属性,却超越了语言的功用,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的桥梁,也是人类意义的调和剂。因为,翻译的出现,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得以思想互文,人们通过语言进入了他族的心灵。
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916年12月,胡适在他二十五岁生日时填了一首《沁园春》的自寿词,[14]18可是到了1917年他却在《新青年》率先发表了用白话翻译的蒂斯代尔的诗《关不住了》。发表的时间相隔不过一年,但选用的语言则完全不同,一个是文言文而另一个是白话。显然,胡适身上也显出了一个旧文人与传统的决裂的矛盾。
两种不同的语言自然代表着两种完全不等同的诗学观念,个体对诗的感觉也迥然不同,但胡适坚持了白话的路子并坚决走文字革命的道路。这时他果断地放弃了他自小练就的文言文字功底,而选择了不是很熟悉的白话翻译,这个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也许是白话文学那种自由自在,不加拘束的自由浪漫的文气与诗感驱使着胡适勇往直前进行文学革命。
说到底,诗歌作品必须是艺术品。读者可能解释不清,但他们的鉴赏心理非常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还在传播,人们还能朗朗上口,其原因就是徐志摩的诗句有美好的诗感,而这正是他的双语语感能力所致。而李金发已没几个人熟悉了,恐怕只有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才记得这位“翻译家”了,至于他的作品则更是无人能想起。
如帕兹(Paz)所言 “翻译造就诗人”,[15]1徐志摩良好的双语语感能力与文学素养使得他的翻译下笔如有神。他首先是一个诗歌翻译家,继而发展成了才情四射的诗人。当我们仔细阅读徐志摩翻译的译诗《歌》与创作诗《偶然》时,我们会发现,徐志摩的诗句很多是从他的译诗传变而来。如译诗《歌》里的“假如你愿意,请记着我, 要是你甘心,忘了我。”[16]199就被徐志摩复制于《偶然》一诗中,且有很重的模仿痕迹:“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16]102
诗歌翻译激发了徐志摩的诗歌才情,他的创作诗歌“《再别康桥》不仅有物我交融、情景长存的意境,更有那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的美意。…… 《再别康桥》展示的既不是拜伦式的英雄激情也不是‘百岁光阴一梦蝶’式虚无、苍白无力的呻吟。徐志摩的诗歌展示的是一种我看自然,自然近,我看人,人与我亲的美境,一种回归生命本体的超然感受”。[16]55-57
胡适、郭沫若、李金发、徐志摩等新诗先驱前后奋斗二十余年,通过诗歌翻译身体力行实验各类新诗的写作,完成了新诗草创、发展与成熟的过程,终成气候。在翻译的招牌下,新的文体、新的文字及新的诗感也逐渐在中国诗坛落脚成熟,一种全新的审美形式悄然形成。
在追溯中国新诗的发生时,我们始终会关注到一个永远甩不掉的“他者”,即:翻译带来的文化异质。当目标语文化环境中充满了“非常见的”的词语以及新的语体、新的语式,新的语感自然而然随处可见可闻。这也恰好回答了雅柯布逊的发问“什么使得言语作品成了艺术品?”同时照应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格言:“使用奇字,风格显得高雅而不平凡”。[9]77以此,语言的语感问题通过翻译的滤光镜而逐渐显出本色。不仅仅是语言层面,诗学层面,它更是社会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向度。
四、结语
在关注语感的向度时,我们可以对其深层结构继续发问,进一步关注语感的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探索。同时,更多将精力放在语感的本质、结构形态及其功能与效应上。
诗感在语言的使用中,特别是语言的诗功能中属于一种什么样态?产生艺术效果的是诗功能还是诗感?翻译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而语言的生发器就是语感与语能。
语感的向度追问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语言的逻辑程式。“五四”译诗的历史事件终将置放于一个辩证的、发展的与全面的视野。译者对于双语的语能与语感把握才是翻译活动的第一要义。能译不等于可译,接下来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则会折射出更多的哲学追问。
[1] 汤富华.语感范畴与语言策略[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2).
[2] Halliday, M.A.K.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2001.
[3]汤富华,华敏.“语言发展”观与与语感知识论[J].湘潭大学学报,2015(6).
[4]汤富华.语感与语感本能[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4).
[5]严羽.沧浪诗话[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6] Krashen ,Stephen D.Principle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xford: Pergamon Press ,Ltd.1982.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M].罗念生,杨翰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 Catford, 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9] Gentzler, 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0] Chomsky, N.New Horizon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11] Andrew Lefevere,ed.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A Source Book[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2]Jakobson, R.Linguistics and Poetics , In Krystyna Pomorska & Stephen Rudy.(eds.).Language in Literature[M].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87.
[13] 卞之琳.五四以来翻译对于中国新诗的功过[J].译林,1989(5).
[14] 胡适.尝试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5] Willis Barnstone, Poetics of Translation[M].New He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 徐志摩.徐志摩经典[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7.
[17] 汤富华.翻译诗学的语言向度—论中国新诗的发生[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熊先兰
On the Research of Dimensions of Language Sense——A Case Study of May 4thPoetry Translation
TANG Fu-hua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Hubei430200,China)
Seldom is any theorectical approach made towards langauge sense category.Most of them, if any,are still feel-oriented feelings and mental expressions related to the above-mentioned topic.In fact,connotations of intuition or language sense are not limited by intuition which is an instinct.They are also related to systemic structural buildings when people learn languages.This paper puts forth a feel, which is above intuition or snese.It is a poetic feel, a feel for the beauty of languages.Poetic feel is compatible to languages, translation of poetry proves for itself.Chinese May 4thPoetry Translation brought forth the birth of New Poetry and also the New Literature Revolution.Its’ validity has much to do with the translators’ bilingual competence or langauge sense.An illustration is made of the institution of langauge sense nurturing.
language sense category;translation dimension; the poetic tendency
2016-08-01
汤富华(1962—),男,湖南邵阳人。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翻译诗学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项目“基于语感训练模式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培育研究”(编号:GPA115040);湖北省2015年度教育规划重点项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语感范畴研究”(编号:2015GA023)阶段性成果。
H319.3
A
1001-5981(2016)06-013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