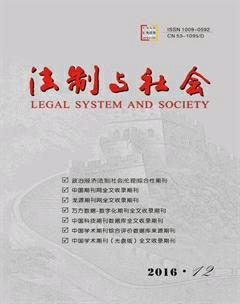略论“不道”罪之司法适用
付崔+晓宁
摘 要 在中国古代的重罪中,“不道”罪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罪名之一,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道”罪的演变分为发展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并且“不道”罪涵盖着广泛的内容,并非“十恶”中限定的范围。本文意在探究“不道”罪在司法适用中的不同表现。
关键词 政治性 犯罪 不道 十恶 唐律
作者简介:付崔、晓宁,武汉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009
“不道”罪从汉代起被广泛运用到司法中,虽同为“不道”罪,但是针对不同的犯罪情形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自《北齐律》始,“不道”罪成为“重罪十条”之一。尔后,在隋朝《开皇律》中。更成为“十恶”之一,接着被《唐律疏议》所继承。自此,“不道”罪的形态基本完成,纳入“十恶”重罪。随着《唐律疏议》的颁布和执行,直至清末止的一千多年来,“不道”罪的法定内容基本保持不变。
学界对于“不道”罪的相关分析和考察汗牛充栋,沈家本先生经过分析与“不道”罪相关的一系列律文和案例,认为“不道”罪并非固定的概念,“不道”罪在应用上也并无定则可循 。日本学者大庭修对汉代“不道”罪进行系统的研究,观点精当。他认为汉代“不道”罪并非毫无“定则”可循,在应用“不道”罪时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 。笔者认为大庭修对于分析“不道”罪在汉代的适用十分清晰和完整。此外,国内学者崔永东在大庭修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了汉代的“不道”罪已经包含了“不孝”罪名 。还有国内学者梁文生论证,认为“不道”罪乃指使用巫术手段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 。从“不道”罪演变的路径进行分析,可以得知“不道”罪是由政治性犯罪逐渐向暴力性犯罪过渡并最终定型,那么为什么“不道”罪存在此种演变形式呢?上述学者的分析极少论及“不道”罪演变的原因和意义,笔者将围绕这一角度展开探讨。
一、 “不道”罪的形成和发展
(一)“道”字与中国古代法律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罪的体系中,“不道”罪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罪名,对于“道”的法律意义的解读深刻影响了“不道”罪在法律中的定型、成型。
1.“道”字的语义及根源:
要理解“不道”的演化,首先应从“道”的辨析入手。凡是自主上路的,作“蹈”解;如果是引人上路,则作“导”解。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道,所行道也。从辶、首。一达谓之道。”《康熙字典》云:“道:《诗·小雅》周道如砥。《前汉· 董仲舒传》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书·大禹谟》道心惟微,又顺也。”可见,“道”本指人行之路。
“道”字后来的语义的演进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远古时期人们相信巫师能够通神灵,接祖先 ,这些通神的技术和方法就被称为“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某一时期出现了统治阶层,统治者通过垄断巫术,来证明自己权威的来源,遂把人间一切现象的发生归根于天,而只有自己才能真正与上天交流,以统治百姓。 后世的儒家继承了这一思想,在儒家观念中,“儒家将‘天神圣化,作为一种政治之术,是试图赋予‘天以最高地位,最高权威,使‘天成为最高的立法者,从而建立一种‘天子受命于天的权力格局。” 故而“天道”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秩序权威性的代表。
2.“不道”的法律概念:
在封建帝制之下,统治者所宣扬的“道”,是指儒家“道统”之“道”。其核心内容即是出自于《书·大禹谟》中的“十六字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中的“道”意为能够保障社会政治过程稳定运行的价值体系,也就是保障皇权的至高无上以及确立稳固的中央集权所需要的价值体系,正是基于此皇权才获得了其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一价值体系狭义上是对皇帝的忠诚,对皇权的维护;广义上就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伦理道德。故违背此价值体系的犯罪行为即被定义为“不道”。因此,“不道”罪的产生与政治领域中“道”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对于统治权威的挑衅和侵犯,构成了“不道”罪最初的形态。
(二)“不道”罪的形成及其早期的包容性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汉代时“不道”罪开始作为一个严重的罪名而频繁出现在司法活动当中。大庭修在《秦汉法制史研究》中对“不道”罪的阐述清晰而完整,分析了不道罪适用的一般准则,“不道”有其固定的指向,这种指向有两条脉络。第一,指侵害君权的行为,即违背“天道”的行为。构成“不道”罪的危害行为,后果最严重、适用最普遍的是“大逆”。大逆”行为构成了对君主统治地位直接的威胁,严重违背了国家伦理,因此“大逆”成为“不道”罪中罪严重的行为。这一类“不道”罪主要包括取代现在的天子或加害天子的企图和行为,如《汉书卷四五 列传第一五》载:“躬母圣,坐祠灶祝诅上,大逆不道。圣弃市,妻充汉与家属徙合浦。”破坏宗庙,如《史记·吴王濞列传》载:“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危害天子后嗣的企图和行为,如《汉书·宣帝纪》载:“……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谋毒太子,欲危宗庙。逆乱不道,咸其辜”。“悖逆”、“逆乱”或折“大逆”,都无疑把重点放在“逆”字上,这类“不道”罪被判处诛杀、要斩及“夷三族”等刑。第二,指丧失人伦的行为,即违背“人道”的行为。“律:杀不辜一家三人为不道。” 即杀害无辜的一家三人为“不道”。又有:“侯德嗣,鸿嘉三年,坐弟与后母乱,共杀兄,德知不举,不道,下狱病死。” 成陵侯德的家中有乱伦之丑行,他得知而不报,就被定为“不道”,那么可以肯定内乱行为本身也在“不道”之列。
(三)“不道”罪中谋反罪的分立
从魏晋始,“不道”罪的罪名体系处于不断的整合之中,曹魏制定《新律》时,将“谋反大逆”罪与非谋反的“大逆不道”罪作出了明确的区别,并规定“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而将其他罪名从“不道”罪中清除出去。《宋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时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朱起母彭家饮酒还,因得病,吐蛊虫十余枚。临死语妻张,死后刳腹出病。后张手自破视,五藏悉糜碎。”在此案中,法官认为张氏剖开丈夫的遗体,唐赐的儿子唐副不阻拦,都构成犯罪。但是当时法律规定:伤害死人,判徒刑四年;妻子伤害丈夫,判徒刑五年;儿子不孝顺父母,判死刑,都不符合本案的条例,所以不能以法律进行判决。经过讨论后,诏书采纳了顾觊之的意见:“法移路尸,犹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当以大理为断,谓副为不孝,张同不道。”此案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制的情况下,判决“以不道论”,充分体现了魏晋司法理念的转变,“不道”在罪名体系中的定位已从政治性犯罪转向违背天道甚至人道的犯罪。中国古代的身体观深受道家观念的影响,认为个体之“人”与大自然之“道”有及其密切的关联,强调人的生命状态应当顺应自然之“道”。
《北齐律》首次提出“重罪十条”:一日反逆,二日大逆,三日叛,四日降,五日恶逆,六日不道,七日不敬,八日不孝,九日不义,十日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将违反国家伦理的重罪和违犯宗族伦理等罪行从“不道”罪中彻底分化出来,使之成为特别的罪名,列入重罪十条之中。“不道”罪的法定含义此时仅剩下汉代的使用残酷手段杀人,违反人类道德底线的犯罪行为。
在《北齐律》的基础上,隋开皇元年, 制定新律:“又置十恶之条, 多采后齐之制, 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 二曰谋大逆, 三曰谋叛, 四曰恶逆, 五曰不道, 六曰大不敬, 七曰不孝, 八曰不睦, 九曰不义, 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 虽会赦犹除名。 ”《开皇律》中十恶的主要内容均来自《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其中“十恶”的内容沿袭了《开皇律》,“不道”罪至唐代最终定型。通过总结可知“十恶”重罪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危害封建皇权的;第二类是破坏伦理秩序;第三类是违反人类底线即“不道”。不道罪即杀同一家无死罪的三口人,或者是将人杀死后肢解;通过制造和使用从有害昆虫处获得的邪毒(“造畜蛊毒”)杀人、以符咒害人以及将被迷惑之魂强加于人(“厌魅”)。《宋刑统》对“不道”做出了相同的规定。由此可见,《唐律疏议》对于“不道”的规定是系统而完善的,唐以前的任何立法均不能与其相比。
(四)“不道”罪的演变路径
汉代“不道”罪关于“大逆”的法律规定所要保护的法益是封建专制统治,触犯此罪要遭受及其严重的惩罚。由前文分析,“道”的最初的法律意义包含国家伦理和家族伦理,因此“大逆”和“内乱”的罪行属“不道”。此外,“杀一家无辜者三人为不道”的法律规定体现了,“道”的法律意义在汉代已经包含人类的道德底线,因此将违背人伦的残忍的暴力行为认定为“不道”罪。可见在汉代关于“不道”罪的立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十分广泛的,除了超个人的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还包括个人的生命法益。
章太炎先生曾考证:“汉律非专刑书,盖与《周官》、《礼经》相邻,自唐朝开始律才专为刑书”。《汉律》内容繁杂,并非专门的律典。遇到疑难案件,往往是逐级向上汇报请示,直至天子,这种自由裁量的做法,必然带来“不道”罪适用范围极广的后果。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不道”罪这一适用范围极广的罪名,以口袋罪的形式存在,将众多具备社会危害性,违背“道”的行为纳入“不道”罪的范畴进行处罚。至西汉后期,“不道”罪已经包含了数十种不同的犯罪行为,无论是罪名的区分还是刑罚等级的划分方面,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司法上的混乱,以至于当时有人抨击道:“不道无正法,以所犯剧易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 ”无论从罪名分类还是刑罚等级的区分来看讲,由于汉代“不道”罪包含的内容如此之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司法实践的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对“不道”这一概念重新进行界定、对其内容加以厘清。
从曹魏制定《新律》至《唐律疏议》的制定,最终完成了“不道”罪有繁至简的过程,在“十恶”中明确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谋反,指预谋危害社稷;谋大逆,指预谋毁坏宗庙、山陵和宫殿;谋叛,指预谋背叛国家投靠敌伪。《唐律》“十恶”中的“三谋”重罪,是危害皇权的及其严重的政治犯罪,前文分析可知,“三谋”罪从汉代“不道”罪中“大逆”分离演变而来,最终成为和“不道”罪并列的重罪。“不道”罪,最终在立法上限定为使用特别残忍的手段杀人,违背正道的犯罪行为。之所以在疏议中载明“不道”罪的适用情况,就在于这些杀人方式严重地践踏了人类的尊严,违反了人性的底线。因此,将“不道”罪化繁为简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体现了立法的成熟化和精确化。
二、“不道”罪的犯罪构成
对于“不道”罪的认识,离不开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清晰把握,对于任何一个罪名的解释和运用,都必须从其规范的目的出发。考量“不道”罪的构成要件,要从其背后的法益出发。
(一)“不道”罪的犯罪主体
“不道”罪的犯罪主体在演化的过程中有所改变,汉代的“不道”罪以政治性犯罪为主,而特殊犯罪要求犯罪主体必须有特殊的身份。因此此时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多为和政权存在紧密联系的人,如朝廷官员、皇亲国戚等,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有机会做出危害皇权和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后来“不道”罪逐渐演化为违背人伦的暴力犯罪,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主体不再限于和政权存在紧密联系的人,而扩大到一般主体。
(二)“不道”罪的犯罪对象
犯罪对象是指主体的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具体的人或物,因为犯罪行为一般也要通过该具体的人或物的侵害而侵害对应的社会关系。对“不道”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构成“不道”罪的犯罪客体是犯罪人因实施了违背“道”的犯罪行为而侵害的社会秩序。同犯罪主体相似,“不道”罪的犯罪客体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有所演变。“不道”罪由特定的犯罪对象构成,在政治性犯罪下,“不道”罪的犯罪客体为至高无上的皇权、有序的封建统治秩序,犯罪对象为皇帝、皇嗣及与皇权紧密相关的宗庙等。后“不道”罪经过不断的演变在唐律中固定下来,从此以后犯罪客体表现为受法律保护的他人的生命权、稳定的社会公共秩序、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但是在对于犯罪对象的认定上,依然要做出具体的区分,对犯罪对象的身份进行排除。当犯罪的主观方面和犯罪主体相同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对犯罪对象的进行区别,如相同的犯罪行为厌魅,犯罪对象是皇帝或尊长时,明显不能以“不道”罪论处,而要分别定为谋反和恶逆。
(三)“不道”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不道”罪的犯罪主观方面根据不同的情况表现也有所不同。在前文中,将“不道”罪分为违背臣子之道的犯罪和违背人伦之道的犯罪。对于违背臣子之道的犯罪,可以称之为政治性犯罪,无论是后果严重的“大逆”、还是刑罚较轻的“祅言”、“诽谤”这一类言语犯罪,不要求行为人有主观的故意,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或者是过失,只要客观上造成可能危害皇权、破坏统治秩序的后果,就会被定为“不道”罪。另一类违背人伦之道的犯罪,经过演变最终在《唐律》中确定为“十恶”中的“不道”罪,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正是因为“不道”所对应的杀人方式过于残忍,犯罪人在实施犯罪的主观故意已经超越了人性底线,所以才将“不道”从一般的杀人罪中抽离出来进行特别的规定。
(四)“不道”罪的犯罪客观方面
前文中已经分析,在政治性行为下的“不道”罪,不要求行为人的故意,但是要求行为人有“谋逆”、“谋反”、“祅言”等行为,造成可能危害封建统治的结果。对于此类犯罪的危害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罪名的认定与统治者的主观感受直接相关,尤其是冒犯君主权威的感受,在不同的外界环境下都会有所不同,量刑轻重往往以统治者所认为的危害程度为标准,这种危害可能是现实的危害,也可能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危害。因此在此种情形下,“不道”罪为行为犯。经过演变成熟后的“不道”罪,危害行为和结果都具有确定性,行为人一定实施了“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的行为,并造成了使用残酷手段剥夺他人生命、扰乱正常社会公共秩序、违反社会伦理秩序的危害后果,因此“不道”罪在这种情形下是结果犯。
三、“不道”罪存在的必要性及法文化角度的分析
“不道”罪是中国古代刑事制度的重要内容,通过梳理可以看出“不道”罪在整个发展期中,其演变模式表现为由繁至简的过渡。并且随着犯罪手段发展,“不道”罪中的相关规定也在不断地完善,如明清增加“采生折割人”条款。中国古代刑法以工具主义为中心,由此而言,对于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等方面,“不道”罪的存在是十分有意义的。完善的制度设计或许是不存在的,符合当时的立法旨意,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制度设计,则已相对完备,“不道”罪可谓如此,现代刑法在诸多方面仍值得借鉴。
(一)保护法益的需要
“不道”罪在制定初期,是立足于当时刑法罪名单一的状况,为了应对实践中出现的众多犯罪行为所设立的口袋罪名。汉代“不道”罪的刑法定位就是刑法的兜底罪名,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将法无规定的犯罪行为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不道”罪在当时是为了对刑法中未规定的具备可罚性的行为进行规制,这种立法思想对现代刑法具有一定的启示,即刑法要重视法益保护的原则,注重对法益的保护。虽然口袋罪的立法模式不值得提倡,但重视法益保护的立场值得提倡。刑法应当是为法益保护服务的,现代刑法更应当重视对法益的保护程度,但这种保护不能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因此,现代刑法在立法时应当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社会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刑事立法,只有这样才能完善刑法体系对于法益的保护。
(二)有关加重情节规定的需要
现代刑法中在犯罪中有加重情节和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即在行为出现了恶性极大的行为或者结果时,法律会加大对这种行为的处罚力度。比如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这种行为不同于构成基本犯的一般犯罪行为,具有更加严重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因此应当在法定基本型的基础上加重处罚。“不道”罪的定义经过演化后稳定下来,即仅限于那些违反人道的残忍杀人行为,对适用严重的违反人道的方法杀人的行为进行加重处罚,并且将这种违背人道的杀人行为的内涵做了详细的规定,包括支解人,采生折割人,造畜蛊毒、厌魅等手段。我国刑法中很多关于加重情节的法律条文中仅以“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形式予以规定,易造成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加重情节程度的难题。因此,在加重情节的立法活动中,应当尽量在条文中采用详尽的方式归纳加重情节,才能对加重情节做出更合适的处罚,更好的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三)“不道”罪的法文化分析
法律文化在指令意义上归属观念范畴。它是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和法律实施的总体特征的综合,它通过评判,选择和制约作用,引导法律制度的创作和运作,影响法律思维的进行,控制法律的实施,指导着一切有关法律的活动,使其在总的结果上呈现出民族文化的特征。 虽然“不道”罪经历了分化和演变,但是其最初的法律含义在后来的封建王朝中都被保留并固定下来。
有关“不道”罪最初的法律含义之一是违反国家伦理的犯罪行为,它从“不道”罪中分化并发展成为“十恶”中的多项独立的重罪。从法律文化的传统来看,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形式,而中国古代基本法在权力来源上表现为皇帝的个人集权,政治权力的最大特征是一元性权威,而法律则是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工具,因此,企图颠覆政权的犯罪行为就成为及其严重的犯罪行为。
“不道”罪最终演变成为手段特别残忍的杀人犯罪,而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以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来统一人们的价值观,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仁”为道德的核心,是理想人格内在,是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最高准则。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人类的文明进程,就是一段不断摆脱野蛮、嗜血、暴力的历史,人类在漫长的文明修养中也慢慢积淀同情之心、恻隐之念和善良之风,正常人对于血腥的场景会有天然的厌恶和排斥。因此,“不道”罪中“残忍”的本质,就在于它挑战了人类的善良风尚和尊严底线。
四、 结语
通过以上对“不道”罪的演变、犯罪构成和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分析,可知“不道”罪是具有中国法律文化色彩的法律制度,在历史进程中完成了由繁至简的演化,实现了法益保护的精确化。从这项制度里,我们可以看出一元权力观、人性本善论等封建统治者利用并宣扬的社会观念,而这些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基因和沉淀。研究“不道”罪,其实就在很大程度上窥见了传统法制背后的文化基因,进而比较透彻的理解传统法制的本质。这为今天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都会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的作用,正所谓“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注释: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汉律拾遗.中华书局.1985.1415-1424.
[日]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14-118.
崔永东.《王杖十简》与《王杖诏书令册》法律思想研究——兼及“不道”罪考辨.法学研究.1999(2).
梁文生.“不道”罪的特质——法律文化视角下的解释.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6(2).
李泽厚.说自然人化.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130.
梁文生.“不道”罪源流考.河北法学.2010(2).
余荣根.道统与法统.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7.
《汉书·翟方进传》.
《汉书·王子候表》.
魏道明.汉代的不道罪与大逆不道罪.青海社会科学.2003(2).
《隋书》卷25 《刑法志》.
《汉书·陈汤传》.
陈晓枫主编.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