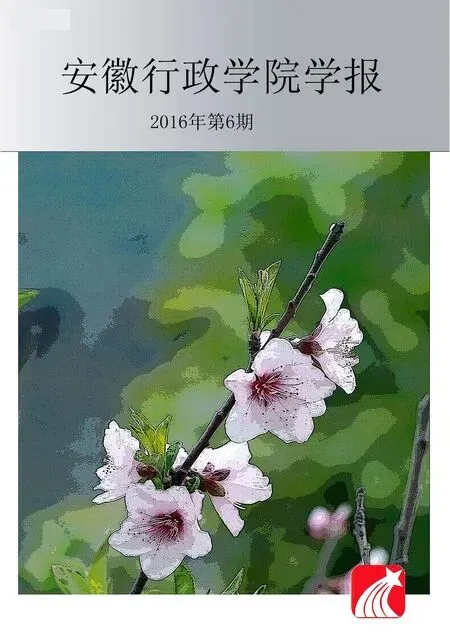多源流分析模式下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影响研究
陈瑞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多源流分析模式下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影响研究
陈瑞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政策议程的建立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逻辑起点和前提。多源流分析模式中“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汇合,开启“政策之窗”的机理,为探寻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影响提供了分析框架。多源流分析模式视角下,基于我国当前的公共政策实践,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信息集散、事件聚焦,触发问题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助推政策流;权力转移、利益诉求,伴奏政治流;聚焦整合、不失时机,开启政策之窗。
多源流分析模式;网络舆情;政策议程
约翰·W·金登(John W Kingdon)基于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科恩(Michael D Cohen)、奥尔森(Johan G Olsen)等人提出的“垃圾桶模式”而提出的多源流分析模式,是后现代政策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式之一,以“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以及“政策之窗”的开启为切入点,对政策议程设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基于多源流分析模式,结合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实践,探析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有助于把握公共权力和政府职能公共政策化同网络舆情的关系,厘清网络舆情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关系,提升公共政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水平。
一、网络舆情背景下的政策议程设置
保罗·A·萨巴蒂尔(Paul A Sabatier)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包括如下几个过程:界定问题,并提交给政府,由政府寻求解决的途径;政府组织形成若干备选方案,并选择政策方案;方案得以实施、评估和修正”[1]。托马斯·R·戴伊(Thomas R Dye)“把政策过程看作一系列的政治活动——问题确认、议程设定、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以及政策评估”[2]13。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和戴维·伊(David Easton)将政策议程称为“看门”(gatekeeping),即对输入到政治系统的要求要经过“看门人”检查。政策议程的设置处于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在公共权力和政府职能日益公共政策化的背景下,政府的职能活动要更加体现公共性、回应公众需要和适应政策环境,不论是政策过程的形式还是内容都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当代公共管理的新发展更加凸显政策议程在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性,“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而对议事日程设置的影响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3]。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新发展以及网民数量不断增加,网络日益成为网民自由、便捷、集中交流的超大“舆论场”,集散信息、放大舆论、串联散落于个体的资源,网络舆情也因此越来越成为人们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的“晴雨表”、“方向标”和“显示器”。以网络为载体,网络舆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网络舆情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通过影响政策议程设置来实现。一方面,网络的崛起促使政策议程设置由精英主义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转变,促进公众参与政策过程,提高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另一方面,网络所具有的相对匿名性、随意性则会将理性和非理性的信息交融、情感宣泄放大、加速,网上与网下重叠,虚拟与现实交织,网络舆情可能会引发政策议程设置的被动性、应急性、短期性等问题。
二、相关研究的回顾
国外学者关于舆情、舆论对政策议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分析大众传媒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展开,总体认为影响明显,但是,其实质性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马克思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在《议程设置——大众传媒与舆论》中提出,传播媒介的报道与公众对于某一事情的认识和关注度之间是成正比的,传播媒介越是对某一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和宣传,公众对该问题的感知程度就越高。约翰·W·金登认为,“大众传播媒体的确对公共舆论议程具有明显的影响”,“总体上说,新闻媒体不是对议程产生独立的影响,而是报道政府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媒体通过“在政策共同体内部充当一种沟通者的角色”和“对一些在其他地方业已开始的活动进行夸张性报道”来影响政策议程[4]71-74。托马斯·R·戴伊把大众传媒对决策的影响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为决策者发现问题并设定议程;第二,围绕政策问题,影响别人的态度和价值观;第三,改变投票者和决策者的行为[2]34-36。迈克尔·豪利特(Michael Howlett)认为,作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政府在一定问题和解决方案上的偏好选择,但大众传媒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应该被夸大的[5]。
国内学者关于互联网及其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分析网络及其网络舆情的新发展,基于政策系统同环境之间的互动,以及案例分析开展。朱亚鹏基于互联网的新发展,通过对“肝胆相照”论坛对政策议程设定的影响的案例研究,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工具性价值体现为推动政策议程设定的民主化,其价值理性上与协商民主的精神具有契合度[6]。陈姣娥以立法进程为例,分析网络时代公民自媒体激活政策沉淀、助推焦点事件、触发公共政策议程的现象,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的政策议程设置是单向性的“自上而下”方式,而网络时代背景下“自下而上”的政策议程设置显著增多,焦点事件能够推动政策问题的暴露,提出政策议程设置的“自媒体触发模式”[7]。陈国营认为,网络舆论产生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地方政府或官员迫于形象、政绩、稳定等方面压力,进而对网络回应,便产生政策行动[8]。鲁先锋认为,在网络情境下,公共决策机构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输入——转化——输出”关系具体表现为网络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的互动转化关系,而“政策议程与网络公共领域之间的脱配也导致了政策议程设置的被动性、应急性和非理性等问题”[9]。刘倩基于多源流分析模式探讨了自媒体对政策议程的影响:自媒体能够推动公众主动介入问题流建构和政策备选方案设计;加速和扩散舆论、激发国民情绪,推动政策议程设置进程;促进焦点事件不断出现,为政府之窗开启提供契
机[10]。
关于多源流理论模式的中国适用性问题,学者还是达成了一定共识:多源流理论模式对于分析中国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其适用度也是有限的。甄智君基于多源流理论,从《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制定过程探究了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途径,认为“多源流理论不仅适用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及政治体制,而且也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实践,同时对中国政策制定也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11]。文宏、崔铁认为,多源流模型适用于我国公共政策实践存在四个方面的“水土不服”:其一,封闭的决策体系使得各种要素源流有相互杂糅互动的趋势;其二,决策权力的集中导致政治家的偏好可以直接左右议程的输出;其三,制度化沟通渠道的缺失使民众的利益表达呈抗争式的特点;其四,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指引下,焦点事件在议程设置中的作用尤为凸显,焦点事件后的“临时拍板”现象屡见不鲜[12]。
三、政策议程的多源流分析模式机理
1995年,美国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提出了多源流分析模型,认为在政策系统中存在着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种不同的源流。问题流中,不是所有“在社会四处漂流”的问题都能够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从而上升到政策议程,政府内部及其周围的人们“注意到了一些问题并且也忽略了另一些问题”[4]113,只有当问题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才能被识别。指标、焦点事件、政策系统的反馈等问题引起政府官员的关注,而问题流中,预算则具有促进或者约束作用。政策流中,政策共同体——由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4]148——各自都有自己中意的想法或打算,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兜售、推销自己的思想,经过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来“软化”可能持抵制态度的政策共同体,得到共识的备选方案和政策建议就得以保留。“政治溪流中包括像国民情绪的摇摆不定、公共舆论的变化莫测、行政当局的更换、党派或意识形态在国会中分布状况的改变以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样的因素。这条溪流中实践的发生往往不依赖于问题溪流和建议溪流”[4]109。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彼此独立,在某一关键时间点上汇合到一起,从而打开“政策之窗”,问题就会被提上政策议程。政策之窗是指“政策建议的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办法的机会,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4]209。政治溪流变化或是紧迫性事件最能够开启“政策之窗”,然而,“政策之窗”并不经常打开,而且打开时间不长,所以,政策建议的倡导者需要抓住并利用“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促使自己的政策主张与问题流、政治流相结合,以便进入政策议程。在约翰·W·金登看来,多源流分析模式中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是互不依赖、相互独立的,之间的关联也只能说成是“松散的联合”。多源流分析模式对政策议程设置进行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以及“三流汇合”开启“政策之窗”的过程分析,改变了传统的政策理论基于因果关系分析的不足,对于政策议程设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探讨多源流分析模式下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必须从我国公共政策实践出发,明确其适用度和解释力。当前我国的公共政策实践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我国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还是以内在创始模型和动员模型为主,外在创始模型的影响力还较为有限,多源流模式中“政治流”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居于突出地位;第二,由于社会治理中刚性维稳思维盛行,绩效考核中的“一票否决”制,制度化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群众被迫选择非制度化、体制外和非理性的抗争式维权,以及官员的“届别机会主义”倾向和道德风险,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以“特事特办”、“急事先办”、“绿色通道”、“领导批示”、“临时拍板”等形式直接触发政策议程,绕开了多源流理论模式预设的议程设置机理和程序。从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实践出发,找到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之间的明确界线是困难的,政策问题界定、政策建议、政策方案、大众舆论、利益诉求等往往呈交织和协奏的态势。然而,模型的意义在于简化复杂的现实,以简洁直观的形式揭示模型指向物内在的固有联系和基本规律,帮助认识、解释和预测现实。从多源流分析模型和公共政策实践出发,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集散、事件聚焦,触发问题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助推政策流;权力转移、利益诉求,伴奏政治流;聚焦整合、不失时机,开启政策之窗。

图1 网络舆情背景下的多源流政策议程模型
四、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分析
(一)信息集散、事件聚焦,触发问题流
“问题流”其实是一个政策问题界定的过程,旨在分析为什么有些问题能够得到决策者的关注而其他的问题却没有,“政策问题认定和政策议程设置既是一个客观形成过程,更是一个主观构建的过程”[8]。问题界定的客观形成方面,主要体现在问题所涉及的领域和严重程度:在民生民权、公权失范、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涉及官民关系、警民关系、城乡关系、劳资关系、贫富关系、医患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往往引发规模较大的网络舆情,社会问题与这些领域的社会关系越密切越能体现其严重程度,也就能够更容易引起决策者的关注。问题的主观性建构则体现在:网民、公众、学者、决策者等政策共同体对问题、政策具有不同的认知和偏好;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能够吸引决策者的关注,决策者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网络舆情事件严重性的认识,对于网络舆情能否促成公共政策问题具有显著影响。
当前,为数众多的网民、规模庞大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发展迅猛的网络媒体,直接承载着社会问题的投射,拓展了网络舆情反映社会问题、社情民意以及大众舆论的广度和深度。以网络舆情为载体的社会问题就会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成为网络公共舆情问题,网络媒体又通过对参与政策过程各方的影响,将公共舆情问题注入公共政策过程。第一,信息集散方面,作为“方向标”、“晴雨表”和“显示器”的网络舆情,提高了公众对信息获取能力,扩展了其认识社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网络媒体及网络舆情的新发展,以微博、微信、QQ、客户端等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兴起带来了一个“人人即媒体”和“大众麦克风”网络舆情新趋势。互联网的新发展大大扩展了公众获取、发送、分享信息的渠道,逐步消解和打破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壁垒。通过网络民主强化公共政策的民主化价值,互联网也提升了决策者觉察和研判社会问题的能力。第二,事件聚焦方面,从网络舆情传播的角度看,网民越多、网络基础设施越发达,网络舆情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和呈现的强度就越高,网络舆情对于政策系统识别和界定政策问题的作用就越明显。互联网基础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网民数量激增、移动上网常态化、即时通信异军突起、搜索引擎规模庞大、网络谣言传播形势严峻、舆论场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等网络舆情传播新特点,进一步强化了网络舆情的地位,促使社会问题走进政策系统成为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够进入政策议程。一些关涉公权失范、公众利益受损、环境破坏等的问题长期不能进入政策议程,问题不断累积,潜伏于问题的风险也悄然增加,一经“撕开一道口子”便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2008年的贵州瓮安县“6·28”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和2011年郭美美事件就是典型例证。网络在群体性事件酝酿和触发中扮演的助推作用较为突出。当然,网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网络舆情问题并不一定都理应成为政策问题。网络舆情问题到底是短期麻烦和棘手问题,还是重要的政策问题,还需要审慎考量和研判。现实中,网民对网络舆情信息的把握不充分、不准确,对正常的政策过程施加不必要的约束和影响;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压力分散,且信息显得糊糊而庞杂,网络舆情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给政策议程带来不利影响。
(二)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助推政策流
“政策流”主要是指某一社会问题得到政策系统关注后,政策共同体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形成备选方案的过程。政策流中,网络媒体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共同体,参与政策建议的形成,或是为其他的政策共同体之间沟通和交流提供平台、信息支持,进而形成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政策建议并不一定都能形成备选方案,政策共同体之间对政策建议进行反复的讨论、劝说、修正后再完善,经过此“软化”过程,获得共识的政策建议才能成为备选方案。在政策建议提出及其“软化”过程中:第一,以互联网为载体,网络舆情推动社会问题能够跨越时间、空间而被阐释、认知、讨论、澄清和批判,实现了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第二,由于低门槛、低成本、相对匿名性等特点,互联网实现了对散见于网民个体的智慧、精力、时间、诉求、意见、建议、期待、诉求整合,搭建一个庞大的“云智慧”平台,网络舆情对政策方案形成、政策建议完善的影响得以强化;第三,网络舆情以其强大的信息优势将政策问题及其政策建议结合,推进政策流的进程。当然,一项转化为备选方案的政策建议必须符合相应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技术可行性、在政策共同体内的价值可接受性、可承受的费用、预期的公众默认以及在民选决策者中间被接受的合理机会”[4]165,否则政策建议需要修订后再进行“软化”。政策建议转化为备选方案的部分标准是专业化指标,而政策建议的产生、讨论以及重新修订大多是在由专业人员构成的政策中进行,公众对此的知晓度和实质性参与毕竟是有限度的,网络公共领域以及网络舆情对政策备选方案的影响也是不容夸大的。
网络问政于民的实践方兴未艾,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日益常态化,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日益突出,政策议程设置对社会问题的觉察更加全面、及时和有效,政策建议和方案的形成聚合了更加广泛的“民情”、“民智”、“民意”和“共识”。中国政府网于2014年3月1日开设“我向总理说句话”栏目,参与过网民留言办理的有36个国务院相关部门和9个省份,办理事项235件,截至2015年2月27日共收到留言12.1万余条,其中有效留言近9万条,成为进一步听取网民对政府工作意见建议的窗口[13]。中国政府网于2015年1月22日起联合6家网站发起的“2015政府工作报告我来写——我为政府工作献一策”活动以来,广受社会关注,网民反响强烈,截至2015年1月29日12点,接收建言总数9 577条,专题页面访问量210万。中国政府网则建立了直通车渠道,会把优秀的意见建议直接送给报告起草组负责人[14]。这些都是网络舆情聚合广泛民智、凝聚社会共识以及进行政策建议“软化”的鲜明体现。
(三)权力转移、利益诉求,伴奏政治流
政治流中包括国民情绪的摇摆不定、公共舆论的变化莫测、行政当局的更换、党派或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及利益集团的博弈。“网络技术的变革实现了公共领域的权力转移,一种扁平化的虚拟组织结构为公民参与和行动博弈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和交往平台”[15]。互联网的新发展,规模庞大的网民和日益兴盛的网络公共领域,使得网络舆情日益成为影响政策议程的重要变量。网络公共领域的“零壁垒”、“广覆盖”、“去中心”、“大众化”的特点,以及近来的网络监督、网络反腐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倒逼效应,强化了网民的“软权力”,助推了网民的“集体行动”,消解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排斥的阻滞,议程设置“草根性”特点越来越明显,政策议程设置权力有向网络公共领域转移的可能和趋势,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也得以拓展。当然,在网络媒体上制造、传递、分享的各种信息中,既包含有对客观问题的描述,也有对问题的主观认识和各种利益诉求。网络舆情自身所承载的权力转移、价值判断、利益诉求,既是对国民情绪和公共舆论的反映,也在自觉不自觉地传递、分享和放大,强调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必要性,促使某一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强势的利益团体可能通过自身强大的优势地位将其利益诉求通过网络舆情加以粉饰、渲染,甚至扭曲舆论,试图将其利益诉求输入政策系统,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置。
党和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一方面是在回应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将强化了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影响。网络舆情伴奏政治流,表达、回应和调协各方利益诉求,推动了政策议程的设置。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运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网络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
(四)聚焦整合、不失时机,开启政策之窗
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在某一时间点汇合到一起,社会问题得以识别和界定,政策建议和备选方案获得政策共同体的共识,各种政治力量赋予机会,“政策之窗”就此开启。换言之,“政策之窗”的开启,是问题源、政策流和政治流经量变,发生质变,进而触发政策议程。在这一时机,“社会问题——网络舆情公共问题——政策问题”之间实现流畅转换,问题的识别与界定、问题解决的必要性、问题解决的建议方案、各政治力量对问题解决的意向得到了有效的聚合。网络舆情通过网络公共领域弥合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之间的张力,充当“三流”汇合的纽带和粘合剂。互联网将分散于广大网民个体身上的观点、诉求、情绪等调动和整合起来,社会活动或社会问题才能得以通过网络舆情引发政策效应,强化网络公共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以互联网为载体,网络舆情事件的涉事主体、政策共同体以及关于社会问题的情绪态度等都聚焦于当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经由网络公共领域变成了网络公共问题,而网络舆情的传播、演变又将网络公共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
从2002年首发于广东地区的非典疫情,到《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编制提上议程,其过程中也是一个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汇合,政策之窗开启的典型例证。其中,网络舆情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疫情发生初期应对和处置不当,首发广东的非典随即扩散到全国24个省区市,问题流开启;“非典”期间,北京8家网络媒体从2003年4月23日至6月24日旅游解禁,有关“非典”新闻发布累计达到11.67万条,共制作有关“非典”防治专题90多个,专题页面浏览量累计约9.03亿人次[16];与此同时,对非典的恐慌情绪也在传播,专家学者、媒体官员都对非典应对和处置进行了大量的剖析和反思。最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编制理所应当地被提上议程:2005年1月26日通过、2006年1月8日发布并实施。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了井喷式的网络舆情,直接导致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促使政府在3个月时间内迅速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出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也是网络舆情触发政策议程的又一典型例证。
五、结 语
随着互联网产生并由Web1.0升级到Web2.0,网络已然崛起为重要的公共领域,公众已经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特别是大数据、物联网、自媒体、云计算、微博、微信等新鲜词汇走进大众视野,“人人即媒体”、“大众麦克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网络时代已经到来,网络舆情的地位和影响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网民数量的剧增日益凸显。网络及其传媒的新发展强化了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多源流分析模式为探析网络舆情触发政策议程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网络和网络舆情的新发展既打破了信息沟通和利益诉求的壁垒,也带来了新的“数字鸿沟”;网络舆情中理性与感性并存、真实与虚假合流、公开与遮掩同行、写实与扭曲交织。政策主体应该具备互联思维,正确研判和有效回应网络舆情,实现网络舆情与政策议程良性互动,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一是提高觉察社会问题和网络舆情的灵敏性,适应公共管理实践的新变化;二是健全和完善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渠道,有效回应各方利益诉求,提升公共政策的民主价值;三是通过网络媒体和网络舆情凝聚社会共识、整合各方智慧,提高政策议程设置的科学化水平;四是坚持政治系统的主导性,保持政策议程设置必要的独立性和选择性;五是,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优化和改进“临时拍板”等形式的危机决策。
[1]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彭宗超,钟开斌,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3.
[2]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谢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Peter Bachrach,Morton Baratz.Two Faces of Power.[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2(4)947-952.
[4]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第二版.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迈克尔·豪利特.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网[M].庞诗,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101.
[6]朱亚鹏.网络社会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定模式的转型——基于“肝胆相照”论坛的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59-166.
[7]陈姣娥,王国华.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机制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1):28-33.
[8]陈国营.网络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基于压力模式的角度[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1):117-123.
[9]鲁先锋.网络背景下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4:I-II.
[10]刘倩.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J].电子政务,2013(9):14-19.
[11]甄智君.从制定《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看中国政策议程设置途径——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10(1):59-67.
[12]文宏,崔铁.中国决策情境下的多源流模型及其优化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5):12-19.
[13]中国政府网.“我向总理说句话”开设一年收到留言12万多条[EB/OL].(2015-03-03)[2015-03-22].http://www.gov.cn/xinwen/2015-03/03/content_282447 4.htm.
[14]中国政府网发起“2015政府工作报告我来写”活动.[EB/OL](2015-01-30)[2015-03-22].http://www.sh.xinhuanet.com/2015-01/30/c_133957718.htm.
[15]陈潭,胡项连.网络公共领域的成长[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23-28.
[16]闵大洪.2003年的中国网络媒体与网络传播孙志刚事件掀起“网络舆论年”[EB/OL].(2014-04-15)[2015-03-23].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41 5/c40606-24898329-3.html.
Study on Influe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n the Policy Agenda in the View of Multiple-Streams Theory Model
CHEN Rui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genda setting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premise of social problems solving.It is the mechanism of problem stream,policy stream and political stream converged to a point,and then the policy window opened that is based on multiplestreams theory model.This model provides an effectiv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u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n the policy agenda.In the view of multiple-streams theory model,based on the policy practice in current China,these influences reflect in four aspects:firstly,driving problem stream through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atch concerns.Secondly,promoting policy stream by drawing upon all useful opinions and collective wisdom and efforts.Thirdly,enhancing political stream with transferring government power and strengthening interests demand.Lastly,focusing on integration,seizing the opportunity,and opening the policy window.
multiple-streams theory model;network public opinion;public policy agenda
D63-31;C916
A
1674-8638(2016)06-0034-06
[责任编辑:姜玲玲]
2016-06-14
2015年度云南大学笹川基金项目(15KT204)
陈瑞(1990-),女,云南师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与教育管理。
10.13454/j.issn.1674-8638.2016.0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