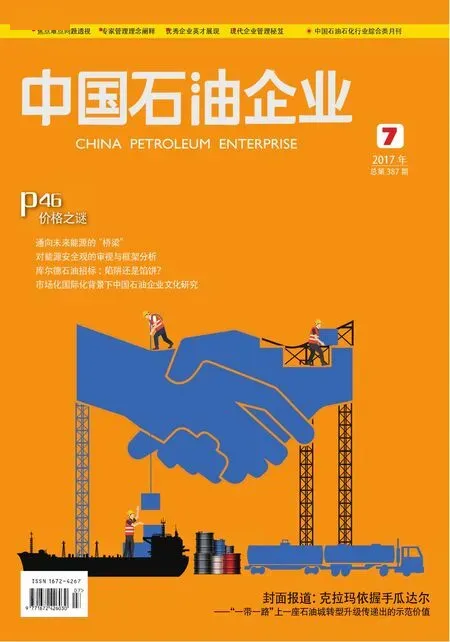对能源安全观的审视与框架分析
□ 文/林益楷 王亚莘
对能源安全观的审视与框架分析
□ 文/林益楷 王亚莘
能源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在经历一战、二战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对能源获取的“恐惧”,成为所有能源消费国的“心头之痛”。随着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日益攀升,能源安全问题已上升为国家的重要课题。如何看待能源安全领域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观点之争,如何审视中国的能源安全状况,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本文尝试进行分析与探讨。
两种能源安全观之辩
国际能源界对实现能源安全的路径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在《21世纪能源安全挑战》一书中,盖尔·勒夫特和安妮·科林梳理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
现实主义者认为,油气作为一种可完全耗竭的能源资源,其战略价值大于市场价值,能源可能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国与国之间要依靠竞争和战争才能获取资源。因此,石油的争夺注定将是一场“零和博弈”,国家间的合作虽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缓解这一属性,但不可能完全回避竞争。理想主义者则认为,没有世界的能源安全就没有一国的能源安全。石油和天然气都属于全球性的交易商品,完全可以按照市场机制来运行,这依赖于全球不同国家、公司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合作。追求能源安全可以通过减少需求、扩大国内能源供应、能源供应多元化、拓展全球贸易和投资来实现。著名的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曾说过:“真正的能源安全是不再做能源独立的白日梦,而是相互依赖支持。”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能源安全观背后,实际上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在能源安全领域的折射。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的核心内容是冲突与合作,或者说是战争与和平。政治现实主义此前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从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到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和根本特征,认为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而达成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
随着全球能源生产和供应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石油生产贸易机制已发生深刻变化。石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日益彰显,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能源署(IEA)等组织先后诞生并相互角力,跨国能源开发与供应商(卖方)和国际资本(买方)的作用也在加强,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市场博弈。有人认为,石油安全早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能源供应充足的范畴,而是一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彼此相互影响的能源系统性风险。全球化时代能源输出国与能源进口国之间关系的实质是相互依赖,没有稳定的进口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出口。
几个关键问题的辨析
一是能源安全是否等同于能源独立?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几任总统,如尼克松、卡特、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曾提出过能源独立的概念。随着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兴起,有机构预测美国到2030年会实现能源独立。然而,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能源独立不是指能源供应只靠自己、不靠别人,形成封闭的自我循环经济圈,能源独立更多是一种美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思想,它的核心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有利条件,通过增加本土油气供应、鼓励节能增效、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等措施,从而建设一个有利于美国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二是能源供需双方谁更强势?对很多国家来说,传统能源安全的概念就是需求安全。自从石油成为主流能源以来,石油消费国似乎先天处于弱势。然而,从20世纪后半叶几次国际油价下跌可以发现,如果石油供应中断,不仅将威胁到石油消费国的利益,对产油国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当乌克兰危机爆发之时,国际舆论普遍担心俄罗斯会切断输欧天然气阀门,但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俄罗斯比欧洲更依赖天然气出口带来的收入(目前俄罗斯70%的预算来自油气出口)。
三是产油国是否希望油价越高越好?石油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价格安全。价格上涨对能源资源供应国来讲是否就是大好事呢?恐怕未必。从经济上看,当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短期内产油国可能会获得额外的石油收益,但长期看也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而全球经济减速会带来石油需求减少,导致价格大幅下跌。从能源替代上看,石油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必然会引发能源节约技术研发和寻找替代能源进程的加速,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从而降低能源消费,影响整个石油行业的发展。
四是爆发石油战争的可能性?在石油供需稳定的形势下,所有与石油生产相关的参与者都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一旦打破这种稳定局面,对谁都是无益的。能源研究学者费特维斯认为,由于正常购买石油的成本要低于发动战争夺取能源的成本,因此发动能源战争是徒劳的。目前,中国75%的石油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一些人担心马六甲运输通道是中国能源安全的“心腹之患”,但有些学者并不认为“马六甲困境”是一个真实的命题,其理由是亚太各国能源、经济对于该航线高度依赖,一旦在马六甲海峡出现通航困难,受影响的将不单是中国的能源安全,更会影响整个亚太、甚至世界的经济安全。
中国能源是否安全?
从石油对外依存度看,根据管理学“木桶效应”理论,一个国家的能源是否安全,实际上最终取决于最不安全的那种能源,而不是整体能源。油气供应安全是中国能源安全的“短板”,根据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报告,201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6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上升至32.2%。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高于美国,且呈持续攀升态势,业界预计2020年将超过70%,2030年将超过80%。反观美国,近年其石油对外依存度在不断下降,美国目前已是煤炭和天然气出口国,而石油进口量也在逐年下降,美国石油液体能源(含石油、液化天然气和乙醇汽油等)对外依赖度从2005年的60%,下降到2014年的26%。中美两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反差,势必影响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全球能源安全态势。
从能源供应多元化看,2014年中国从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沙特、安哥拉、伊朗、伊拉克、苏丹、阿曼6个国家进口原油超过总进口量的60%,进口石油90%以上需要从海上船运,其中80%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长距离石油运输存在较高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而美国石油进口正逐步从中东转移至自家“后院”。2014年美国从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周边国家进口石油占比达41%(加上中南美洲占比达58%)。对美国来说,从周边地区进口石油,无论从能源运输成本、运输安全等方面都有优越性,其“舍远求近”的石油进口多元化策略值得中国学习。
从能源消费结构上看,尽管中国整体能源供应是安全的,但是能源消费结构非常不合理。2013年,煤炭占整个中国能源消费比重是67.5%,石油占比17.8%,天然气是5.1%,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次能源消费仍以煤为主,迟迟无法进入油气时代,不仅导致国内整体能源利用效率不高,还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在美国2013年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36.7%,天然气占29.6%,煤炭占20.1%,相较其2005年的能源结构(石油占40.27%,天然气占22.5%,煤炭占22.73%)更加合理,尽管依然以化石能源为主,但石油、煤炭等传统高碳能源所占比重正在减少,天然气比重得到较大提高。美国从“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的过渡取得比较大的成效,而中国能源发展“去碳化”进程则面临很大的挑战。
从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可持续看,当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整体偏低,2000-2011年间能源弹性系数平均为0.77(其中2003年和2004年竟达1.43和1.6),而发达国家一般不超过0.5。此外,中国能源消费强度高,2011年我国GDP约占世界的8.6%,但能源消耗约占世界的19.3%,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美国的2.4倍,日本的4.4倍。有专家认为,中国之所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过去10年来,美国在提高能效方面领先中国。
实现中国能源安全的路径选择
下一步,中国应充分借鉴美国实施“全方位能源战略”的战略设想(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发布《“全方位”能源战略——通向经济可持续增长之路》),大力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为实现国家能源安全创造更好的条件。
一是坚定推进多元化战略,强化能源“战略买家”角色。考虑到国内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禀赋的“短板”,油气供应安全将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需要着力关注的领域。中国应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坚定不移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推进石油供应多元化,构筑起网状、链式的能源供应体系。在巩固好非洲、中东等传统油气供应地的同时,强化在能源供给新重镇的“战略买家”角色:更加关注中亚和近邻俄罗斯,以能源合作为纽带,扩展自身能源供应安全与对方经济发展的战略交集;根据全球“能源生产重心西移”的趋势——墨西哥国内油气领域开放步伐加快,拉美地区的巴西等国近年处于油气大发现阶段,应抓住机遇,在生产过剩的“全球油价再平衡”短暂战略窗口期,继续深化与中南美洲相关国家的能源合作,使之成为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稳定来源,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博弈能力。
二是做好油气行业“战略简法”,释放制度红利。美国通过市场机制,推进能源革命,增加了国内油气产量,降低了石油进口依赖度,减少了贸易赤字,促进了就业,提升了美国国内能源安全。我国在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时明确提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当前,油气市场发育不足、市场参与主体较少是我国能源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因而,要本着“在全产业链引入竞争”的思路,做好油气行业“战略简法”,简化不必要的行政规制,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与竞争机制在能源生产与消费中的作用,坚持由市场形成能源价格,通过在上下游各领域逐步放宽准入、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探索实施混合所有制等多种途径,进一步激发石油市场活力。
三是推进结构能效并举措施,升级能源安全“战略匹配”。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根据政策目标调整,中国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心也开始从追求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的能源供应战略匹配,到追求安全、高效和清洁能源供应战略匹配的重大转变。美国目前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已低于1970年的50%水平,我国政府做出了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40%-45%的承诺,必须在提高能效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四是激活“亚投行”能源安全“周边外交”角色,实现能源基建战略牵引。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取得巨大进展,未来,“亚投行”也势必承担其能源角色。中国应积极借力“亚投行”,以跨国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为契机,重新战略性调整周边能源安全形势。首先,借力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改造升级既有的中国及周边区域的能源基础设施,确保能源基建“存量”安全可靠。其次,协调区域内跨国能源基建规划,实现能源基建“增量”有利布局。再次,在能源安全角度,整合“亚投行”机制与“一带一路”战略,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内,拓展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纵深空间。
五是积极介入全球能源金融体系,担当虚拟能源资本市场战略交易方。当前,伴随国际金融创新快速发展,能源金融衍生品成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一环,亦成为影响国际石油供给关系、造成价格波动的核心因素之一。因而,中国加强能源安全建设,需要更加创造性地介入由于自身起步较晚,还依旧陌生的全球能源金融市场:近期看,函待加强对国际能源金融市场的深度参与,在期货市场、证券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等金融市场中,熟悉规则、对冲风险、配置资源、锻炼人才,提高资本市场博弈能力;远期看,需要建设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能源金融交易中心,以期逐步形成可与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能源金融市场制衡的能力,从而维护全球能源金融市场的多元稳定。
(林益楷: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高级经济师;王亚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