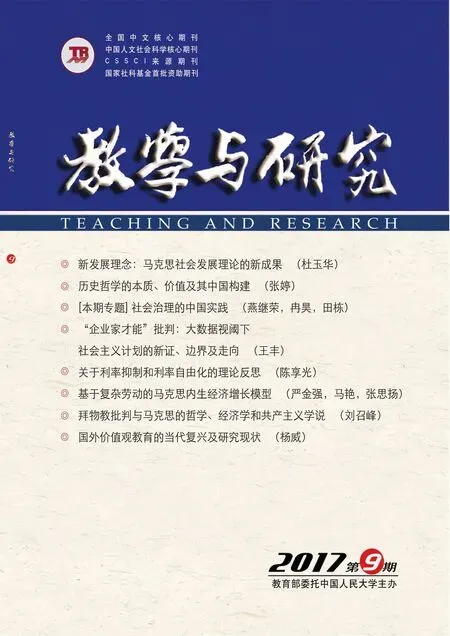社区治理中的党政同构效用
——基于北京市三个社区工作实践的对比分析*
社区治理中的党政同构效用
——基于北京市三个社区工作实践的对比分析*
田栋
社区治理;党政同构;治理能力;支持机制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城市管理体制逐渐从“单位制”向更具活力和多样性的“社区制”转变。社会流动的加剧和城市新社区的快速建立,使城市居民居住空间和工作空间的分离成为常态,从而带来一系列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社区管理内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居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开始上升,相应而来,社区管理体制也在适应这种变化进行大范围变革。“治理”取代“管理”成为社区建设的根本价值目标。但为适应社区形态变化而出现的社区“治理”机制,依然沿袭自计划时代开始的党政同构模式,但与以往相比,党政同构模式在社区治理中的运作机制及其效用出现变化。基于以上判断,本文从治理概念的内涵出发,选取三个社区进行对比分析,试图绘制北京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图景;通过对于现状的具体分析,寻求影响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序 言
从规范研究的角度来看,治理概念强调居民与国家正式制度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亦即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共生共治关系。“治理”既有传统意义上政府对居民的单向管理,也有居民参与社会建设和公共管理过程的内容。在我国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治理概念的提出需要国家正式组织(党的组织体系、政府组织)在理念、机制方面进行全方位转变以适应社会形式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从国家制度的层面对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出更高的改革要求。社区组织作为国家正式组织中与民众互动最为频繁、直接面对民众诉求的基层组织,“在实现党对社会有效整合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1]其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是影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因素。社区党组织作为党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在居民自治基础上依靠自身的组织优势有效扩充了国家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领导核心作用。在应对城市新阶层兴起所带来的系列挑战过程中,以社区党组织为主体的社区治理架构、社区基层组织的工作运行机制、社区党员/积极分子对基层组织的支持机制、疏离社区党组织的党员/居民自组织活动共同形成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基于上述判断,在有关部门帮助下结合研究需要,选取海淀区西三旗街道F社区、丰台区宛平城街道C社区和西城区月坛街道S社区三个具有典型性的社区来对比分析,其中S社区作为西城区选报的优秀社区,代表具有单位制属性的熟人社区;F社区是近年来形成的新建社区,城市新阶层居民较多;C社区代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村改居新建社区。
一、社区治理架构:社区治理中的基层组织
社区治理的主体包含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两个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是居民行使宪法赋予的自治权和民主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权力的法定组织。居委会成员由居民选举产生。同时在社区中,社区党组织作为执政党在基层的末梢,按照《党章》规定,是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的领导核心。两者在权力关系方面具有显著区别,居委会是自下而上的居民赋权,而社区党组织是执政党自上而下的组织赋权;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与农村类似,城市社区同样出现“以选举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变量被嵌入到‘自上而下’的权威结构之中,从而形成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逻辑的相互并存”的状况。[2]为解决两种权力关系可能的冲突与不协调,在社区工作实践中,北京市采取的办法是建立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的组织同构模式,即在组织关系上,两者都要接受街道组织的领导。社区党组织接受街道党(工)委领导,居委会在街道办事处指导下开展工作。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居委会主任的状况较为常见。
在调研的三个社区中,居委会主任都由所在社区党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担任;但居委会成员并不完全是党员。按照《关于北京市第九届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的规定,北京市“提倡和鼓励按照民主程序将社区党组织负责人推选为社区居民选举委员会主任,将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将社区党组织成员选举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力图“实现每个社区居民委员会中都有党员的目标”。因此,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的组织同构不仅体现在领导层面的兼任,也体现在两者内部成员的交叉任职。通常情况下,每个社区都存在社区党委/党支部成员担任居委会委员职务的状况。在调研的三个社区中,每个居委会中都有一半以上的委员是社区党组织成员;其中西三旗街道F社区居委会7名成员全部是社区党员。
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的组织同构决定了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社区党组织书记通常由上级组织提名产生,近年来为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社区党组织书记也要经由社区党员的选举产生。在实践中,上级提名的党组织书记都能够在选举中当选。不仅如此,在居委会选举中,社区党支部书记也能够当选居委会主任。在调研访谈中,丰台区的一位组工干部谈到在她从事工作的十年里,“无论是社区党支部选举还是居委会选举,还没有遇到过组织提名的人选在选举中落选的状况”*访谈,丰台区某街道组织部长,2014年10月11日。。这从侧面反映了即使存在研究者担心的居民选举自主性增多的状况,执政党的组织意图还是能够顺利得到实现。这体现了执政党在社区仍具有高水平的动员能力。
二、社区党组织工作运行机制:动员能力的差别化
社区党组织与居民自治组织的组织同构决定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两者工作步骤和工作目标的同一性。居委会承担的维持治安、公共安全、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等职能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事实上由于在现行体制中存在的“压力型”特征,社区居委会日益成为上级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承接大量来自上级组织的交办事项,特别是近年来在社区中广泛推行的“网格化管理”工作,进一步加重了居委会在网格管理中的行政化色彩。但是由于居委会自身人力、物力、财力均较为有限,而承接的上级组织交办事项却比较多,能力、资源的不匹配造成居委会必须依靠社区党组织去动员社区党员参与社区治理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因此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在社区层面被社区党组织动员而进行广泛参与的居民大多数是社区党员*社区党员指居住在本社区、组织关系在社区的居民党员。。
例如在西城区月坛街道S社区,9 540名居民中共有党员2 500余人,其中组织关系在社区的党员有257人;依靠社区党委下辖的三个支部和支部下属的党员楼门长队伍,建立起高效的社区党员支持机制,很多具体工作要在社区党员的协同之下去完成。比如登记流动人口信息、完成人口普查工作、在党和国家重大活动时期维持社会治安等工作都要依靠社区党员队伍来参与,以弥补人力的不足。按照社区党委成员W某的说法:“日常工作的开展依靠居委会这几个人远远不够,不必说上级要来检查评比的任务事项有多少,仅仅是处理日常居民之间的纠纷,靠居委会7、8个人都做不完”*访谈,西城区S社区党委,2014年11月3日。。这种状况在调研的其他社区同样存在。在调研期间恰逢C社区刚刚完成一项中央领导出席的重大政治活动的保障工作;按照上级政府要求,C社区要全面清查活动周边地区居民建筑,排查安全隐患;工作细致事项要求中就有“街面不能出现猫、狗等蓄养动物”。在有限的期限内完成入户排查工作并劝说居民管理好家养动物,必须依靠社区党员去完成。按照C社区干部的说法:“没有社区党员帮助工作,这项任务就不可能完成”*访谈,丰台区C社区工作人员,2014年10月11日。。街道组工部门负责人在谈到此事时也认为:“C社区党支部在日常工作中就比较注意发挥社区党员的作用,愈是到重大活动时期,这种作用的发挥就至关重要”*访谈,丰台区某街道组织部长,2014年10月11日。。
两者人员的高度重合性也决定了很难严格区分社区工作究竟是由党组织开展还是居委会开展,实际上在社区中无论是居民本身还是社区工作人员都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区分。在访谈中不只一位社区居民认为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是同一组织,按照一位居民(非党员)的说法:这两个组织“应该是一家”*访谈,海淀区F社区居民,2014年10月17日。,而一位社区居委会成员(同时也是社区支部成员)认为“工作都是我们做的,不管是开展党务活动还是居委会工作,只要是上级要求的,都要靠我们去做”*访谈,海淀区F社区干部,2014年10月17日。。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说法说明在社区,日常工作的开展并没有严格区别各自组织的工作范围。这样的做法可能出于节省成本的需要,在经费有限的状况下似乎没有必要重复开展社区活动。但这种做法同时也隐含不利的一面,社区党组织并没有主动将自身角色从社区工作中分离,这对于培育社区党员的党员意识、强化社区党组织动员能力,进而提升治理能力的目标是不利的。
比如在海淀区的两个中产阶层较多的社区进行的调研发现,有相当比例社区党员很少参加社区党组织活动,对于党组织的号召、要求并不积极。在这些不愿参加社区党组织活动的社区党员中,一些人曾经参加过次数有限的由居委会组织的活动,一些人在社区居民自组织活动中比较活跃,不但参与活动而且主动组织活动。在谈到没有积极履行党员义务、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的原因时,一位30岁党员的回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首先是平时就很少与居委会打交道,也不了解社区党组织开展过哪些组织活动”;而自己参加的社区活动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体育活动和休闲活动”*访谈,海淀区F社区党员,2014年10月18日。。对于这种党员疏离社区党组织的状况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加以解释(例如活动吸引力不够、缺少时间参与),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解释,都可以确定社区党组织自身角色的不清晰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理想状况下,支部组织与辖区党员之间联结的紧密度应高于社区组织与非党员居民的联结紧密度;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总体而言,依照调研社区的现实情况,社区党组织工作机制具有两方面显著特征。一方面,社区干部对自身工作的评价都比较高,认为社区工作成绩很多。在人力、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完成街道交办的各项行政任务、处理解决社区内部各类利益冲突、完成重大活动期间的各种政治任务并不容易。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社区党员和积极分子的踊跃支持。另一方面,社区中还存在着一些党员对社区活动参与不积极、游离于社区党组织之外的现象,特别是社区中知识化程度较高、收入水平较高、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年轻党员,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的热情不高,更乐于参与社区自组织活动。这种社区工作“一头冷一头热”的状况,在一些干部看来主要是由于“社区活动对青年人吸引力不足”,一位街道组织部长谈到“时代发展变化这么快,五六十岁的社区干部和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之间兴趣点肯定不同,年轻人喜欢的,这些老年人可能都不懂得到底是什么”*访谈,丰台区某街道组织部长,2014年10月11日。。
三、社区党组织支持机制:社区党员/积极分子的角色
社区内不同群体对社区党组织活动的参与程度不同说明社区党组织在不同群体间存在着差别化的动员能力。调研发现,在社区中能够积极参与活动的人群是与社区干部同年龄段的退休人员群体。在月坛街道S社区,由于多数社区党员是国家部委的退休干部,其中51%的党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社区党组织根据这种情况着力发展社区学习活动,动员老干部参与社区讲堂,并通过社区讲堂进一步开发老年人较为喜欢的健康知识讲座等社区活动,从而达到带动整个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目标。在西三旗街道F社区,存在很多退休后从外地来到北京照顾家庭第三代的老年居民,社区党组织根据这些居民空闲时间多、融入本地社区意愿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组建楼门党员小组,发动在社区中比较活跃的外地来京退休党员担任党员小组组长,通过这种建立平台的做法充分使用这些外地来京党员的社会资本*外来党员的同乡关系、邻里关系、以及共同参与小区活动的经历都是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来源。,在外来人口中快速建立了社区活动的参与基础。
搭建平台,开展适合居民特点的社区活动是强化动员能力的关键;但要保证活动开展的长效化,让社区党员、积极分子能够长期保持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并非易事。为增强社区党员和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活动、支持社区组织目标的积极性,进一步强化动员能力,社区党组织会在不违反规定的条件下,尽可能为积极分子提供各种优先享受公共服务的便利机会;或直接给予资金补贴。享受低保、困难救济金和慰问金、供暖费用报销、公租房申请等社区组织能够主导的公共服务对一些居民特别是生活存在困难的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困难党员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社区党组织开展的社会志愿活动如每季度都要进行的“学雷锋”志愿日、创建文明城区期间的道路治安维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基本上都要依靠社区内的低保户和退休党员来完成。
对社区党员、积极分子进行利益激励来鼓励他们参加社区活动仅仅依靠社区组织有限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在调研中了解到,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能够利用各自的工作需要向上级组织申请新的资金弥补经费缺口,社区中的居民自组织协会例如妇女协会、志愿者联合会也能够在社区党组织指导下从主管机构如妇联、民政部门争取到相当比例的活动经费。这些计划外的经费通常会由社区党组织在相关部门监督下使用到各种社区活动中。社区干部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好,能够兼顾实现满足居民需要和开展参与度高的居民活动两大目标;无论是对居民,还是对于社区党组织、上级部门来说,“这些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解决了大问题”*访谈,海淀区F社区干部,2014年10月17日。。
上述做法对于具有较强资金议价能力的社区而言是高效便捷的塑造居民支持的重要手段;但对于议价能力有限的社区而言,当向上级部门争取的经费有限时,社区党组织会创造性寻找、建立新的资金提供方式来争取社区党员、积极分子的支持。例如在C社区,由于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新建立的“村改居”社区,农民上楼之后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并不容易。失业人口较多的现实对于社区党组织来说无疑是加大了开展工作的难度。针对这种情况,社区党支部基于解决失业人口就业问题的需要,注册成立物业保洁公司,吸纳社区内的失业人口在公司中就业。在社区党支部的坚持下上级街道组织出于扶危济困的考虑帮助该公司在辖区内扩张业务范围,保证该公司能够获得长期的稳定盈利。在具备稳定收益的基础上,社区党支部依靠物业保洁公司在社区内开展更多的居民服务项目,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党组织的动员能力。
这种依托自身能力建立社区党员、积极分子支持机制的方法区别于其他社区依靠上级部门资金援助塑造居民支持的工作机制,但在最终目标即获得居民认同方面是一致的。两种做法的共同特点是建立利益关系来联结党组织与居民,但这种利益关系并非是通俗意义上的金钱关系;无论是居民获得低保还是像在C社区那样获得工作机会,本质上都是将社区组织所代表的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保障形式重新合法化”,[3](P75)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党组织能够塑造支持机制,强化动员能力,扩大社区居民、至少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居民的政治认同。
四、疏离社区活动的居民和社区自发组织活动
在社区党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西城区S社区和丰台区C社区,社区治理能够成功的关键是两个社区都有针对性地结合社区党员实际开展活动。对于这些老年人口较多、空闲时间较多的社区而言,同处五六十岁年龄段的社区干部更能够挖掘居民的需要,也更容易建立支持机制。但对于城市新建商品房社区党组织而言,面对的情况与前述类型社区有很大不同。在商品房社区中,很多居民接受过高等教育、收入水平和综合素质都比较高;相应地也具有较高水平的权利意识。对于个人利益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并且善于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合法权益。要在这一群体中塑造、强化社区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对于知识结构老化、工作方式较为传统的社区干部来说并非易事。
例如在F社区,作为2009年建立的商品房小区,居民大多属于在京接受高等教育后留京工作的“新北京人”。这些居民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非常积极,在参与社区事务方面具有较高的自主性。据了解,F社区在2009年开始陆续有居民开始入住,在收房过程中因开发商所建立的小区设施标准与售房时宣传承诺不一致而引发大量业主不满;自2010年起该社区连续发生居民自发组织的权益维护活动,例如在小区周边拉扯表达诉求的横幅、向新闻媒体寻求关注、在开发商售楼处和物业公司所在地开展集体抗议活动,这些行动的出现迫使开发商按照承诺重新改造小区设施。但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并未就此消解。在随后两年中,围绕小区地下车库停车收费问题,居民寻求各种表达渠道抗议收费违法,不但到街道办事处直接表达诉求,而且向区价格主管部门发函要求公开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在这些活动当中,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社区组织角色较为尴尬。有社区干部坦承居民的合法抗议活动有其“合理性”,社区党组织试图居中调和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但收效甚微,因为感觉“很难和这些年轻人打交道,他们口才好、水平高,对法律、政策的理解比我们好”*访谈,海淀区F社区工作人员,2014年10月17日。。在这种状况下,社区党组织的合理做法是尽可能降低居民抗争活动的广度和烈度;但是由于社区党组织在居民与开发商的利益关系中只能扮演第三方角色,依靠传统的群众工作方法来达到消除不稳定因素、排解居民抗争活动的目标时,效果并不理想。
F社区的案例说明,当居民具有较强的权益意识并积极以抗争活动的形式来争取合法权利的实现时,以社区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治理架构并不能对新情况进行有效应对。“居民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减弱”,社区党组织“能够达到的基层整合效果将越来越减弱”。[4]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社区治理架构内生的结构性矛盾,即作为“基层战斗堡垒”的社区党组织代表着国家权力对于基层社区的控制与渗透*“渗透”是国家能力理论的代表性概念。在国家能力理论中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覆盖、控制、渗透是实现国家能力的基础。详情可参见: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而作为“居民利益代言人”的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在理论上应是居民权利的汇合点。在社区自治发育尚不完全,国家权力所追求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目标与居民利益取向所要实现的权利诉求目标出现不协调状况时,“控制”与“自治”两个目标的不一致就会在现有社区治理架构中出现内生的结构性矛盾。
这种矛盾的存在意味着本应代表居民利益的居委会在应对居民抗争活动时必须优先考虑社区党组织追求稳定的政治目标。因此在现实工作中,居委会由于不能完全实现居民的利益要求而逐渐丧失居民“信任”。居委会被认为是“国家”的,而不是“居民”的。这种认识会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预期,居民会选择远离社区组织,并尽可能以自组织活动的形式在社区治理架构之外寻求自身权益的实现。
对于这些疏离社区活动的居民而言,较高的生活水平决定了他们并不需要通过社区组织去寻求“社会保障”,因此社区党组织同时也丧失了运用自身资源塑造居民支持的手段;也就无法有效动员社区党员带动居民参与。F社区在经历数次维权活动后,在居民中出现稳定的社区自组织活动平台。社区居民建立了自己的社区论坛,在论坛中广泛交流社区信息、组织邻里活动;一些权益意识较强的居民开始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力图通过居民自身的力量去建立业委会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F社区代表国家权力的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影响力显然要低于其他社区。在访谈中有社区干部承认居民选择成立业委会意味着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不信任,但他同时认为按照有关规定业委会必须在街道的指导下才能成立,在缺乏社区居委会支持的条件下,街道不会批准成立业委会。这一说法在一位社区自组织活动的组织者那里得到印证,他也认为业委会成立在资料齐全、已经满足法定条件的基础上迟迟不能得到批准是因为“没有得到居委会支持”。显然,在现有的社区治理架构中,权力与权利的共生关系还是一种理想,社区共治的局面从现实来看尚有距离。
五、结论:问题与建议
在治理能力视阈下,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建立“以集体所有成员都尊重的共同标准为基础”[3](P212)的国家正式组织与全体居民共同参与的社区共治格局。其中,既要有国家正式组织(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所代表的国家权力“贯穿”、“渗透”社区居民社会的一面,同时也要有社区居民反向“支持”、“信任”、“参与”社区治理的一面。在现行社区治理架构中,国家权力向居民社会的贯穿经由社区组织工作在基层社区的全覆盖和一系列技术化手段诸如网格化管理体系的建立而得到实现;困难在于从反向建立由“国家”所确立而且能够得到居民认同的社区事务“共同标准”,从而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对国家正式组织的支持和信任。
在构建社区共治格局的过程中,社区党组织所具有的依靠组织优势动员党员参与的支持机制对于从反向建立居民对国家正式组织的支持和信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党员的领导能够拓宽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依靠党员的政治忠诚和提供社会保障的形式,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党员中塑造支持机制、强化动员能力。西城区S社区和丰台区C社区的案例都充分说明这种做法能够行之有效。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上述两个社区的成功主要来自于由社区居民构成所决定的居民需求能够被社区组织识别并加以满足。S社区退休党员居民较多、C社区失业人口较多的现实情况使得社区党组织能够提供针对性强的工作内容来满足居民需要,从而建立反向的支持关系。当在社区中不再存在符合社区党组织组织优势的情况时,例如在F社区所出现的情况,社区党组织是否具备构建反向支持的能力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随着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类似S社区和C社区这种带有传统体制遗存的社区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类似F社区这样居民具有较高权利意识的新建社区。怎样有效面对新情况,如何结合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优势、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构建社区共治格局,需要全方位寻求提升社区党组织治理能力的有效方法。结合调研中对三个社区差异化对比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强化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的领导核心作用,始终坚持将党建引领作为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围绕国家权力与居民权利之间的不协调,有学者建议进一步分离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各自的工作职能,强化居委会自治功能。从理论角度来看,强化居委会自治功能始终是国家制度所鼓励的建设方向,但问题是是否需要弱化社区党组织在社区事务中的领导作用。从现有制度安排的框架来看,社区党组织是国家权力贯穿基层社会的重要一环,是代表国家权力嵌入社会治理的正式组织;同时也是实现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在社区强化自治功能,实现居民利益诉求并不排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相反更需要社区党组织在实现居民自治的过程中主动来引导居民自治与国家目标相吻合。因此需要调整的是理念、方法、机制,而不是制度本身。
二是进一步强化社区党组织动员能力,在加强以政治忠诚和社会保障形式动员退休党员、困难党员和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的同时,强化对社区党员动员的力度和广度;尤其是提升对城市新阶层居民中党员的动员效果。社区党组织的动员能力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基层社会的独特优势,在推进社区治理建设的过程中,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应不断保持并增强。建议进一步加强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服务和工作的力度,通过各领域、各部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的方式增强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量和动员能力;探索社区党组织与在职党员所属单位对社区党员的双评议机制,对于党员意识薄弱、疏离社区党组织的社区党员要出台教育帮扶办法;鼓励能力突出、综合素质较强的社区党员加入各种社区内的新社会组织,强化动员基础。
三是加强社区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年轻化”色彩。能够建立符合年轻居民需求、引起兴趣的社区活动是推进居民参与的基础;而社区党组织人员的兴趣偏好、能力素质是决定社区活动方式的重要因素。当前在传统社区中退休人员比例高,工作易开展;在新建社区,依靠年龄较大的社区干部开展社区活动较为困难。应进一步选拔年轻党员充实社区工作,建立工作机制鼓励机关单位年轻党员到社区挂职锻炼;进一步拓展基层社区干部的晋升渠道,职级待遇方面应加大倾斜力度,增强社区工作对年轻党员的吸引力;使社区能够“选到人、留住人”。
四是进一步创新机制,引导外部力量参加社区治理。政府部门力量、社会力量都是增强社会治理效果、弥补社区组织力量不足的重要资源。随着城市新阶层居民数量的不断增多,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都应将工作重心向社区下沉,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治理能力。例如北京市委共青团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创建“社区青年汇”项目,选取年轻人聚集的新建社区投放项目资源,围绕青年人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创新活动形式,效果显著。政府相关部门应进一步结合社区实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新机制加大社区治理项目建设力度;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建立多样化的服务方式。
[1] 林尚立.合理的定位:社区党建中的理论问题[J].探索与争鸣,2011,(11).
[2] 景跃进.选举:村庄传统权力结构的裂变[J].中国社会导刊,2001,(2).
[3] 托马斯·海贝勒,君特·舒耕德.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4] 黎熙元,陈福平.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J].社会学研究,2008,(2).
[责任编辑刘蔚然]
TheIsomorphicEffectofPartyandGovernmentinCommunityGovernance——AComparativeAnalysisofThreeCommunityWorkPracticesinBeijing
Tian Dong
(Strategic Research Center,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 Center, Beijing 100007)
community governance; party government isomorphism; governance capability; support mechanism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marke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hina’s urban management system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Unit system” to “community system”,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more vitality and diversity.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rapid establishment of new urban communities,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living space and working space has become a normal phenomenon. These have brought a series of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ontent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in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Governance” instead of “management” has become the basic value goal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ompared with the past,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he utility of the CPC and government isomorphism patter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have changed.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governance concept,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communiti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trying to draw up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Beijing. Through the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seeks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bility,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新移民群体中社区党组织影响力实现机制研究”(项目号:15CDJ011)、北京市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项目“治理能力视野下首都商品住宅社区党组织建设研究”(项目号:15JDKDC12)的阶段性成果。
田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7),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党建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