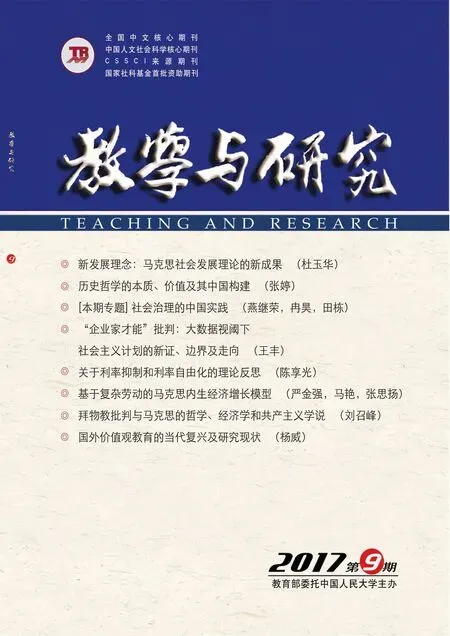拜物教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学说
——对拜物教批判理论意蕴的一种阐释*
拜物教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学说
——对拜物教批判理论意蕴的一种阐释*
刘召峰
Fetischismus;神秘性质;拜物教观念;物的依赖性;拜物教批判
拜物教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哲学理念具体化的重要成果,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新的理论基点。拜物教批判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独特贡献,因为它可以使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在经济理论上区别开来。基于拜物教批判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领会马克思“未来预见”的内容变迁,可以对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作出更为严密的论证,可以对通达共产主义的道路进行更为具体的诠释。所以,拜物教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形态之一。
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是近几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关注的理论热点之一。笔者曾撰文辨析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的具体内涵,建构拜物教批判理论的总体框架*参见刘召峰:《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考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Fetischismus及相关词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话语变迁》,《现代哲学》,2017年第1期。。本文将着力阐发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意蕴。就此问题,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同仁们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他们看重的通常是拜物教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辩证法意蕴。李惠斌研究员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既是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又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是对于旧唯物论的一种彻底的颠覆*参见李惠斌:《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一般方法论意义》,《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对旧唯物论的颠覆及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2期。。孔明安研究员认为,商品拜物教的“物”是集卑俗与崇高于一身,融抽象与具体于一体的,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论蕴含着一般与个别、具体与抽象的辩证方法*参见孔明安:《论商品拜物教中的辩证法意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一些同仁探究了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之于批判当下种种拜物教观念(比如“市场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和“土地拜物教”)的重要意义*参见李建平:《新自由主义市场拜物教批判——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邰丽华:《〈资本论〉中拜物教思想的理论逻辑与时代价值》,《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本文认为,我们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来理解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意蕴——它之于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共产主义学说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一、拜物教批判与马克思哲学理念的具体化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02)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它被我国学者极为频繁地引用。我国不少学者还把“改变世界”视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笔者无意于在此细究马克思这句话的具体所指*对“改变世界”的内涵的详细阐述,参见刘召峰:《“改变世界”:特定的问题语境及其内涵的拓展与深化》,《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只是想指出:马克思对“世界”进行了“层层递进”的具体化剖析。
首先,马克思明确了宗教异化的世俗根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世俗局限性的现象,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宗教局限性。[2](P169)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2](P200)这里的逻辑很明确:宗教异化根源于世俗异化,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即世俗异化是主要任务。
其次,对于世俗生活,马克思明确区分了精神生活领域与物质生活领域,认为后者决定前者,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明确了经济生活相比其他社会生活的优先地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他们的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的形态”。[1](P525、544)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物质实践、生活之于意识、思想观念的基础地位,并为“改变世界”指明了方向。
再次,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也不是平行的,其中生产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经济“问题”的解决要从变革“生产”这一环节入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3](P40)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生产”这一环节的决定作用,从而把实现“生产”环节的根本变革作为“改变世界”的核心任务。
最后,明确区分物质资料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什么)与其社会形式(怎样生产),着力对后者进行考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P520)对于“生产”,马克思是将其具体到“一定社会形式的生产”进行探讨,而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热衷于一般地、抽象地讨论“生产”。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细致地剖析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在生产的“商品形式”中,“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这是“社会关系的物化”);不仅如此,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还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这是“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而“当一般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4](P89、90、112)“虚幻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金银作为物好像天然地就具有可以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的“属性”,天然地就是“货币”。与商品和货币相比,资本具有更加“神秘”的性质——“自行增殖”。其实,只有在“资本—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中,“货币”才是“资本”。可是,资本可以“自行增殖”的假象带给我们的“幻觉”是,即便没有这种“关系”,“物”依然是“资本”,“资本”表现为“物作为物”就具有的属性。在剩余价值被分割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之后,资本、土地和劳动,分别表现为利息、地租和工资的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源泉;这样,“和生产过程的不同物质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各个生产关系已经互相独立化了”(这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5](P940、941)马克思拨开了商品生产与交换(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产生的种种“假象”,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逻辑,展示了“社会关系的物化”、“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的内在机理,揭示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
由此可见,拜物教批判理论是马克思致力于探究生产的特定“社会形式”——商品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形式”所具有的“拜物教性质”而创立的伟大理论。在此意义上,拜物教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哲学理念具体化的重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范式”转换。1961年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认为,哲学作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所研究和所涉及的问题,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普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6](P2、19、200)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理解为探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所共同具有的“最普遍的问题”,实际上内含了把“具体”归结为“抽象”的“下降”逻辑,而为了更为精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我们需要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逻辑。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推广”和“应用”之类的说法,就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意义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以为可以按照形式逻辑的推理原则可以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推论”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错误的。因而,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把“推广”和“应用”理解为马克思语境中的“上升”,而不能理解为形式逻辑的“推论”。二者的原则差别是:形式逻辑的“推论”,当把握了“大前提”和“小前提”时,是不难得出“结论”的,但马克思语境中的“上升”却需要多年的艰苦研究工作才是可能的;形式逻辑的推论,并不能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马克思语境中的“上升”则可以把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改革进程中,肖前和高清海两位先生分别提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等有别于传统的解释模式。肖前先生说:“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他阐述了“另一种自然观”:“我们所面对的自然界是实践地生成的或与实践这样那样联系着的自然界。离开实践的(或为了实践而被人们观察认识着的)自然界,对人来说,虽然存在着,但没有意义。”[7]高清海先生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我们决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用来回答认识的基础、来源和真理的标准等认识论问题的一个原理;而必须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用于理解和说明全部世界观问题、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观点的新的思维方式。”它是“从人与自然的具体统一即从具体的人的现实活动出发去认识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8]突出“实践”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对于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不在其历史的、具体的形态上来把握它,它将面临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物质”一样的命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着重考察了“劳动”这一基础性实践活动。马克思的考察遵循的是从“劳动一般”到“生产商品的劳动”,再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这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逻辑。对于“劳动一般”,马克思说:“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生产商品的劳动,则是“有用劳动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统一”,具有“二重的社会性质”。[4](P56、90-91)“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作为“有用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统一”,[9](P185)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由于马克思这样具体地剖析了特定“社会形式”的劳动,劳动、实践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了丰富的历史性内涵。
20世纪90年代,俞吾金教授提出了如下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在俞先生看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是一种“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适合于社会历史领域,而且适合于其他一切领域,才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而且是全部马克思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仍可以作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同名词而存在,以分别“透显”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与“辩证性”。[10]现代实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可以让人类“推知”人类诞生之前的自然、“观测”人类实践活动触及范围之外的自然。但是,即便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可能“适合于”这两类“自然”所属的“领域”,因为“人类诞生之前的自然”不可能在“实际上”纳入“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而不可能是对于人来说的“历史的自然”(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随着实践与科学的发展会发生变化,这是另外一回事);“人类实践活动触及范围之外的自然”也还尚未成为“人化的自然”。马克思曾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3](P47)对“人化的自然”的实践改造与科学认知的发展,可以使人类提升“推知”人类诞生之前的自然、“观测”人类实践活动触及范围之外的自然的认知能力。但是我们需要时刻注意“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否则,就会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经济学家”那样的错误:“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3](P47)明了“人化的自然”与“人类诞生之前的自然”和“人类实践活动触及范围之外的自然”之间的区别,而不是“把它们等同起来”才是像马克思那样具备“历史性”自觉的表现。
近些年来,“《资本论》哲学思想”、资本批判越来越多地成为科研项目、专著与论文的探究主题。说到“资本”,马克思的如下论断经常被我国学者引用:“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5](P922)孙正聿教授认为,马克思对于“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的揭示,是揭示了“存在”的秘密。[11]其实,对“资本”进行批判的重点和难点并不在于说明“资本”不是“物”而是“关系”,而在于回答如下问题:作为“关系”的“资本”为什么、以及怎样表现为“物”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起来的?[12]这样的追问,就将“资本批判”推进到“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剖析”的理论层面了。杨耕教授认为,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存在方式在于,将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融为一体。[13]笔者非常赞赏这一判断。对此,笔者想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一“形而上学特殊”,揭露了其混淆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把物在社会关系中获得的“形式规定性”归之于物的自然属性,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化、永恒化的理论误区。所以,我们可以把拜物教批判理论看做是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具体化形态。不仅如此,拜物教批判理论也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具体化: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拜物教观念的批判,以一种具体化的形态深化了对意识形态本身的批判;马克思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的批判,是对拜物教观念这一“意识形态的具体形态”的现实基础的细致剖析*对此观点的具体阐述,参见刘召峰:《马克思形而上学、意识形态批判的具体化路径——以〈资本论〉对拜物教观念的剖析为例》,《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
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实践的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而后到“《资本论》哲学思想”,最后到“拜物教批判理论”——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逐步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拜物教批判理论视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新的理论基点。
二、拜物教批判:马克思经济学的独特贡献
我们可以通过解答如下问题来论证这一“独特贡献”: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他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在经济理论上究竟有本质差别?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5](P925)马克思的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论述“本质与现象”之间关系的一般哲学论断。其实,它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评论庸俗经济学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一“三位一体的公式”时说的。在此,马克思想说明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本质”以“歪曲”的(异化的)形式表现自身,而庸俗经济学无法摆脱“歪曲”的表现形式带来的“假象”,陷入了“拜物教观念”的泥潭。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评价要高得多:“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做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5](P940)不过,马克思还补充说: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5](P940)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依然被“拜物教观念”束缚。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如下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斯密和李嘉图就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究其缘由,马克思认为,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的特殊性。[4](P98-99)研究“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追问“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14](P21)就是在探究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而这,正是拜物教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域。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在其《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一文中,通过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四条进行“改写”,凸显了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超越:“李嘉图是从经济上的自我异化,从商品被二重化为价值物(即假想物)与现实物这一事实出发的。他的理论坚持价值产生于劳动。他没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呢。因为,产品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并固定为意识之外的、独立的经济范畴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社会劳动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社会劳动本身首先应当从他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劳动中发现了价值的秘密之后,劳动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15](S52)正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社会劳动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给予了我们需要对“雇佣劳动”这一“劳动的社会形式”[5](P923)“在实践中加以变革”的历史启示。
在马克思看来,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代表人物有托马斯·霍吉斯金、威廉·汤普森、约翰·弗朗西斯·布雷等)也没能逃脱“拜物教观念”的束缚。他们没有把资本看做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没有把资本看做是一种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另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30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还有类似的说法:“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人物,如霍吉斯金,也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经济前提作为永恒的形式接受下来,只是希望消灭既是[这些前提的]基础而同时也是[它们的]必然结果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另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针对“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之类的说法,马克思评论说:“如果他们排除了资本家,他们也就使劳动条件丧失了作为资本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77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另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由上可知,拜物教批判可以使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在经济理论上区别开来,因而,拜物教批判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独特贡献。
三、拜物教批判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
基于拜物教批判理论,可以更好地领会马克思“未来预见”的内容变迁,可以对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作出更为严密的论证,可以对通达共产主义的道路有更为“具体化”的诠释。
1.拜物教批判与马克思“未来预见”的变迁。
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6](P64)马克思是立足于对于“旧世界”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来“发现”“新世界”的,因而,他剖析现存世界的“问题”的视角转换导致了他的“未来预见”的内容变迁。我们可以通过展示《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在“未来预见”上的差别来说明这一点。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特别关注“旧世界”中密切相关的三大“问题”:剥削、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他说:“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主张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私有制、剥削消灭了,阶级对立现象也将不复存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P51、45、5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预见了一种“联合体”的到来: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自觉地把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成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劳动的总产品,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另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直接按照生产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份额的大小分配给个人进行消费;在这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关系,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4](P96-97)对此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得更加明确:“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18](P433-434)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剥削、私有制、阶级对立等视角分析现存世界的“问题”,着眼于这些“问题”的消灭进行“未来预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劳动的“物化”表现形式、“个人的劳动”与“总劳动”之间的“迂回”关系这一视角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性,因而其“未来预见”着眼于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下的商品消亡。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当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时,就“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了。[19](P327)
2.拜物教批判与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证。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0](P163)阐释《资本论》之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不是本文的任务。在此,笔者想集中回答的问题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拜物教批判之于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论证意味着什么?
对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可以诉诸“辩证法”来论证。早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那些“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的“经济学家们”,因为在他们眼中,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1](P598、612)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的相应的社会关系,以及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的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P603)这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辩证”理解:“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P22)秉持这种“辩证的/历史的”态度,马克思也会把资本看作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但是,仅仅运用上述“辩证法”无法说明的问题是:资本作为一种“历史的生产形式”区别于其他“形式”的独特性质和运动规律是什么?
对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还可以诉诸“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论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1](P412-413)但是,这只是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未论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独特规律。
论证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性,需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独特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可是,与封建地租这种“显而易见的”剩余劳动形式不同,剩余价值的存在是被层层“假象”掩盖着的。因而,发现剩余价值规律,需要祛除下列“假象”带来的迷雾:货币作为货币好像就具有“自行增殖”的“魔力”;在“工资”形式上,好像雇佣工人的全部劳动都是有酬劳动;剩余价值好像是在“贱买贵卖”的“交换关系”中产生的;商业利润好像完全是从流通中产生的;生息资本好像是一个能够“自行增殖”的“物神”;作为“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的地租好像是土地的“自然力”的产物;商品的价值好像由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而“构成”。正是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严格地区分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逐步“还原”被层层假象“遮蔽”的“资本关系”,才揭示了资本的拜物教性质的形成机制,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彰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对此问题的更为详细的阐述,参见刘召峰:《拜物教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
3.拜物教批判与通达共产主义道路的具体化。
在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在于:剥削与商品生产的内在结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奴隶主和地主就已经在凭借自身“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来“奴役他人劳动”了,只不过,此时“剥削”的实现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是“外在”的。虽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已经出现,但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并非建立在“商品交换”之上。“剥削”与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实现了内在“交融”: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下,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建立在了看似“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造成的“假象”还发挥着掩盖“剥削”的功能。
剥削与商品生产之间的关系并非“密不可分”,因而,否定了产生剥削的生产关系,并不意味着必须排除商品生产与交换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较低阶段,仍然可以通过商品生产这种“社会形式”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从而为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准备条件。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可以对社会形态的未来演进做如下诠释:从“剥削与商品生产内在结合”的资本主义社会,到剥削被大大限制(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主体”)、但商品生产尚需大力发展的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允许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再到私有制消亡(从而剥削消灭)、但仍存在多种公有制形式(因而商品生产和交换依然存在)的社会(即“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进而再到商品生产消亡的社会(此时才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最后达至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允许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差别的辨析,详见刘召峰:《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当代反思》,《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这样,我们对于通达共产主义的道路的设计就更加具体化了。笔者的这种诠释,既可以避免妄图让私有制在当下中国泛滥的右倾错误,又可避免意欲在当前阶段就消灭商品生产的“左”倾错误。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意蕴做如下的总结:拜物教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哲学理念具体化的重要成果,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新的理论基点;拜物教批判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独特贡献,因为它可以使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在经济理论上区别开来;基于拜物教批判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领会马克思“未来预见”的内容变迁,可以对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作出更为严密的论证,可以对通达共产主义的道路进行更为具体的诠释。所以,拜物教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形态之一。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艾思奇主编.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7] 肖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J]. 东岳论丛, 1983,(2).
[8] 高清海. 论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的意义[J]. 社会科学战线, 1988,(1).
[9]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 俞吾金. 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J]. 中国社会科学,1995,(6).
[11] 孙正聿. “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0,(2).
[12] 刘召峰. 拜物教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4).
[13] 杨耕. 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9).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Hans-Georg Backhaus . Dialektik der Wertform [M]. ça ira Verlag: Freiburg, 1997.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第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孔伟]
FetishismandMarx’sPhilosophy,EconomicsandCommunism——AnInterpretationofTheoreticalConnotationofFetishismCriticism
Liu Zhaof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Fetischismus; mystery of nature; the concept of fetishism; substance dependence; fetishism
Fetishism criticism theory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in Marxist philosophy. It is also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udy of Marx’s philosophy in China. Fetishism is a unique contribution of Marx’s economics, because it can distinguish Marx and vulgar bourgeois economists,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so 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etishism,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tent change of Marx’s “Foreseeing the future”. We can make a closer argument about the inevitability of communism, and we can also interpret it more concretely. So, fetishism theory is one of the specific forms of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Marxism.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中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15CKS00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本论》中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14MGC0207)的阶段性成果。
刘召峰,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浙江 杭州 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