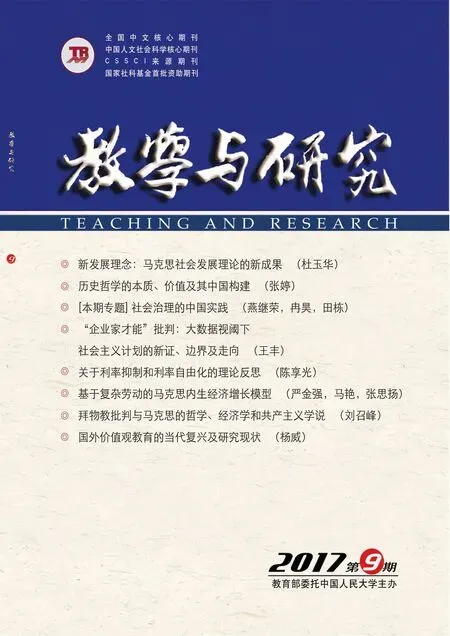以“希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道路的启示*
以“希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道路的启示*
经理
希望;共同意愿;中国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诉求。然而,当代文化的、政治的、国家的认同研究却表明新秩序将受困于民族利益,暗示了不存在多极化力量主导的世界新秩序。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启示我们:新中国的形象正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命运的缩影。作为多民族国家,新中国的成就表明:不同民族间改变世界诉求的相容性与精神中存在的普遍“空缺”密切相关,这种“空缺”来自于对不利生存现状的否定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望(想象),转化为联系各个民族的共同理想,即“民族独立”、“个人幸福”与“民族复兴”。其中,产业工人、农民以及大学生对“梦想”话语的认同及践行,完成了对他人的导引,使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汇聚成强大的行动力量,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因此,展望21世纪,中国道路的启示在于:我国要积极构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完善以发展为主题的希望话语体系,广泛凝聚世界各国力量,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世纪伊始,国际经济形势复苏缓慢,全球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此起彼伏,中国周边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了实现“两个百年”和“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我国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革新,还关系到全球经济产业链的总体布局。当前,发达国家为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所困,发展中国家则身陷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的泥潭之中。持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筑牢互利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已成为本世纪中国亟待破解的政治难题。针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状,我国政府推出了“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等新型经济发展战略,表明了向纵深发展的决心。不过,在拓展区域间经济合作渠道的同时,我国对外政策明显侧重于制定技术层面的经济方案,忽视了以新型意识形态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必要性。因此,建立新型国际政治的关键在于:要着眼于各国人民的普遍意愿,汲取新中国成立后希望政治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国家形象、话语体系与实践主体等方面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希望”政治的理论内涵
随着国家间贸易往来的日趋频繁,商品与资本的跨国流动影响了不同国家的原有产业结构,出现了生产力水平从失衡到再平衡现象。由于国际范围内产业分工链的重新布局,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结构发生了双向调整: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得益于资本输出与落后技术装备的转移,扩大了部分产业的生产规模;另一方面,资本输出破坏了发达国家的原有生产结构,迫使其必须改进现有生产技术,以吸引资本回流,推动本国生产力水平提高。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便会发生改变,使原有的分配关系被彻底抛弃,让位于新的分配关系,引发生产的物质发展与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1](P1000)出于攫取剩余价值的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会依靠制度重建使社会化生产服从于分配的需要。出于维护国内政治稳定,这种由新的分配关系引发的国家内部利益矛盾便被转移到国家外部,表现在国际交往中,就是建立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牺牲他国利益使本国的政治矛盾得以缓解。
在这个时期,不发达国家尚未或正在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重建他国的意识形态体系通常被发达国家视为维护其不合理经济秩序的有效途径。这种话语体系或者表现为“国家—公民”身份,以同构化“劳动者”的身份强化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或者表现为“宗教—信徒”身份,利用“天然的”共同文化强化生命的归属感。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事实上已经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家的生活方式使每个人坚信,合理化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可以实现财产规模的扩大,也使每个人从“此岸”世界看到了救赎的希望。这是因为,节欲正是积累的象征,劳动寓意了肉体的责罚,趋同的生活方式则保证了共同的救赎。基督教神学的祛魅化正是人们将希望寄寓于现实世界的过程。于是,这种希望要求人们合理化自己的劳动时间,同时也要求他们将控制劳动对象的努力转化为管理社会化劳动的方式——科层制,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趋于理性化。[2](P99-102)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扩张也将会在不同民族中间引发相同的结果。在西方中心论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不仅可以将“野蛮”民族纳入“现代文明”的轨道,[3](P141-142)还说明了以资本主义拯救世界的必要性。尽管这种话语体系的建构方式企图消除不同民族的疏离感,但是,它不可能在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形成真正的文化联系。从根源上看,上述逻辑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塑全球空间的政治诉求。
当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显现之后,民族内部的矛盾让位于民族利益。特殊民族利益的普遍化与每个民族利益普遍实现的矛盾愈加凸显。这就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拯救”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在经济“掠夺”的事实中渐趋瓦解。而在此过程中,各种积累的政治矛盾也随着民族利益的伸张,填补了原有意识形态的真空,阻碍了新型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民族间的精神联系需要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被支配、自支配到相互渗透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承受了发达国家流动资本对本国生产方式造成的消极影响。相对于前者而言,他们希望以重申本民族利益获得等同于发达国家社会生产能力。而这就必须否定资本的利润导向,坚持以技术为主导的社会化生产。显然,这就与发达国家追求的对外经济战略发生了冲突,即否定其作为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补充的意图。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文化联系需要相似的经历“表述”。从全球发展史来看,殖民主义经济模式并没有使不发达国家拥有相同的工业结构,而是藉由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完成了增值资本的需要。这就造成了不发达国家同时出现了分别以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尽管这些国家都先后出现了规模化工业生产的事实,但是,劳动力投入量与收入的不对等,不可能使这些劳动者认同发达国家传播的话语体系及其塑造的形象。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消费主义形象的传播也未能弱化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价值判断。这是因为,这种形象不可能完全解决贫富分化、产能过剩(落后的技术产品)、生态恶化等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痼疾,只能唤起人们追溯共同的生命起源,以消除彼此的异质感。对此,安德森就认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4](P7)
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随着各个民族生存状态及其空间结构的改变,对民族文化的追忆已成为各民族主张其自身存在合法性的依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经济联系将受困于文化的差异性。由于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寻求可供借鉴的典型案例已成为上述民族亟待破解的难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情况表现尤为明显。这就表明,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仅是否定了“同质化”发展模式,却没有否定“鉴融化”模式的可能性。所谓“鉴融化”模式,是指围绕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各个国家在选择解决策略方面与参照国的趋同倾向。其中,参照国与本国国情相似度越高,解决策略便越具有相似性。
从文化角度而言,一种新世界秩序的兴起往往伴随着主导这种秩序的国家对外形象及其话语体系的建设。其中,设置形象的目的在于具象化国家发展可被“触及的”前景,而话语体系的传播则充当了国家内部个体对这种“想象的”结果(尚未实现的目标)认同及其与其他社会成员间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便在于它与该民族共同拥有的国家记忆存在显著联系。这种记忆事实上构成了避免民族重蹈覆辙的警示。倘若文化是民族改变生存世界的实践符号记忆的观点能够成立,这就表明文化传统并非不可改变。这是因为,文化传统的中断表明了民族生存境遇的改变引发了文化与现状间的张力,暗示着文化创造活动的开始。这种活动往往伴随着对其他民族实践活动的理解而展开。
那么,这种民族外部的实践记忆(话语)如何转化为民族内部活动的文化要素呢?这只能借助于“希望”。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尔都塞给予了我们以相关启示:首先,希望表现了人与其现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这就表明要使希望的话语表达植根于人们的共同经历,并从对这种经历的拒斥中,唤起人们改变生存现状的意愿。其次,文本(宣言)使隐蔽的想象转化为所能感受到的“现实”,使人们企盼指向未来的实践路径。[5](P296、298-300)在想象的世界中,由于人们始终将避免趋势恶化作为肯定自身存在的前提,这就激发了人们改变不利生存现状的实践欲望,唤起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再次,人们在“先行”的主体实践中确认了自身实践的方式(形象)。由于蕴含普遍意愿的言说者就是它的实践承担者,这就促使其他实践主体,从承担者的实践结果中看到了“先行”的结果。最后,话语使每个人占有了这种“形象”,并促成了共同意愿的形成,得以使集体的政治实践活动成为可能。[5](P311-313)由于普遍意愿的形成不是以任何民族的或文化的主体,作为创造新世界的前提,而是取决于对这种以观念形式表达的意愿认同与否。这种合作方式不仅规避了主体自身的异质性,也消除了主体间合作的异质性,使得塑造世界的“主体”永远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只有经过上述四种转化,希望才能借由人们的价值关切及其实践活动,转化为具有物质性的存在物,才能赋予原有文化以新的结构。简言之,其要义在于:依靠团结共同应对全新问题。
因此,希望的政治就是要以普遍意愿奠定合作的前提,以政治实践主体的存有保障实践活动的结果,形成对其他实践主体的示范与促成效应。在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种合作的观念体系之所以是可能的,便在于:它不仅回应了民族国家保持独立的要求,也承认了民族改变其生存世界的实践诉求,更确认了民族革新自身的生存能力。当然,谈及这种新型的国际合作化道路,它并非没有先行的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道路事实上印证了希望对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巨大改变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后“希望”政治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历经“奠基——转型——再转型”阶段,工业化发展水平无论从规模、速度和质量上都要优于西方发达国家经历的相同阶段,较之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既非出于否定资本主义的本质,也非憧憬于社会化大生产承诺的物质景象,而是依存于生存境遇的转变,在民族独立、个人幸福与民族复兴等理想间实现了转换。这些话语内容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也调动了他们的创造积极性,有效地凝聚了人民力量,更推动了整个社会体系的高效运转,从而使中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1.民族独立之梦。
由于物质生产与人口规模的再平衡能力较强,近代中国并没有出于对外战争或海外贸易的需要,在完成手工工场兼并之后,依靠生产工具的发明或生产技术的改进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主动选择工业化的道路,克服生产力不足问题;而是在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之后,被动地融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体系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这就形成了以下局面:一方面,维持封建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话语体系正在因生产组织的变化而影响力日益减弱;另一方面,这种由外部注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清除封建意识形态统治的政治诉求,而是采取了融合于原有封建统治政治框架的方法,企图为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攫取更多的发展空间。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从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利益出发,各种原有的政治矛盾服从于民族生存,“公平贸易”的话语体系让位于革命的话语体系,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主权独立的新国家。这实际上成为了中华民族相互依存的精神纽带。
建国后,这种理想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初步探索与建设时期发挥着无形的导引作用。中国民众之所以敢于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工业化的中国——的原因在于,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差异表明只有尽快开启中国工业化进程,才能巩固独立的民族国家。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6](P1229-1230)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私人占有与共同占有的所有制矛盾,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们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它们都与独立民族国家存在与否密切相关,解决的办法就是诉诸于各个领域的革命(决裂),从而彻底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
耦合于这种理想,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确立并没有依靠自上而下强制推广合作化的苏联模式,而是采取了从民众试点典型中定型,并逐步向全国推广的模式。比如,在与张玉美的谈话中,毛泽东讲道:“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6](P1209)这种推广模式表面上是注意到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向他人示范了合作化生产的巨大优越性,事实上却是以象征的方式暗示了工业化中国的存在。所谓工业化的中国,就是要中断建立在农业中国基础上各种上层建筑,就是要使国家的面貌与民族的实践联系起来,使现代化的成果打上中国人的烙印,并以劳动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自我确证,即同样拥有发展工业化的能力。
在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这种理想实际上是以建构产业工人的形象予以完成的,比如王进喜、王崇伦等人。这些劳动者的共同特征在于:一方面,他们都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赞成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应中国的工业建设;另一方面,这些人依靠自己的劳动使劳动对象发生了巨大改变,确证了普通劳动者不“普通”的力量。这种公共形象的建构寓意了工业化中国的脚步正在加快到来(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它也吸引了其他人加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有效地实现了劳动者力量的整合。特别是在我国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这种合作化劳动所彰显的力量取得了自身表现的顶峰,它使中国具备了反对外部势力干预与捍卫自身劳动成果的能力,完成了中华民族独立的梦想。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矛盾的转向却中断了新理想的开启——生活方式的变革。在社会秩序趋于混乱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它使人们因难以见到个人生活世界的明显改变,而重新思考自身的生存处境。而这种需要的“空缺”表现为:对科学的推崇唤起了人们运用理性思考生活的热情,然而,集体劳动需要却限制了每个人运用理性规划生活的权利。这就造成了个人与集体两者间的张力,为改革开放时期形成新的理想埋下了伏笔。
2.个人幸福之梦。
改革开放伊始,世界政治力量的均势格局造就了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这不仅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与技术输出创造了有利环境,也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此时,人们对于物质生活改善的要求也变得比以往更加突出。为了顺应国内形势变化,邓小平提出,要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实现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再平衡。他还指出,“我们不参加军备竞赛,总收入要更多地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对世界和平更加有利”。同时强调:“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7](P162、354)这就表明,全党的工作重点从先前的政治矛盾重新回移到经济矛盾的做法,通过政策的执行,获得了积极反馈,表明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呼声。
那么,从民族独立到个人幸福,这种理想的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在这段时期,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应当先以农业为突破口,使广大农民率先确证自己具有实现幸福生活的力量。这是因为,从现实条件来看,经过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农业生产的水利、交通设施与化肥生产的单位规模都已经达到了投入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要求。再从人们的思想条件来看,鬼神文化的退场与科学技术的普及,使得传统的农业生产文化得以祛魅化。此时,不再是人格化的神秘力量决定农业生产的顺利与否,而是理性本身——通过合理地安排生产与控制个人消费,在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不断地追加劳动量来改变生活,以追求自己的幸福。农村“万元户”的出现充分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这种示范有效地促进了其他领域的转变,使人们认可了以劳动量衡量、以税收调节的分配制度,顺利地推动了经济领域的各方面改革。由此可见,这种制度的建立是与个人对自身幸福追求的理想和自我的劳动确证密不可分的。从随后的表现来看,虽然,我国经济制度改革在推进过程中也经历过波折,但是,在各种社会机构之中,正是对个人幸福追求的认同的政治力量超越了其他力量,才维护了经济改革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中国国力在三十年来收获的巨大增长是与这种理想密不可分的。
不过,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加深,我国经济发展在行业内部与不同行业之间,也遇到了和其他国家的相同经济症状。其表现为,生产规模受限于内外部市场而导致产能相对过剩,生产技术受限于高新技术而比较优势不明显,以及企业集中破产带来的劳动力冗余。于是,这就唤起了人们希望以民族身份的承认争取个人生活境遇改变的意愿,它预示了新理想的到来。
3.民族复兴之梦。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正在变得日益紧密,经济产业结构受外部市场的影响愈加明显。由于市场竞争的存在,产业间的产品优势、生产规模与利润水平都出现了较大差异。这样以来,在调整市场布局、改变产业结构与升级生产技术的同时,就必然出现个人劳动力付出与生活境遇不成正比的情形。尽管生活水平的显著差异依旧向人们暗示:个人的幸福取决于劳动本身,但是,此时劳动的认可却是建立在市场交换的基础之上,存在着无法复制、不可持续等问题。从“共存于世”的前提出发,这就使人们感受到运用自身理性的力量,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生存问题,也使其对自身的生存价值产生了怀疑。
正是如此,“中国梦”的提出正是对中国人精神家园的重建。从“中国梦”的个人维度来看,它承认每个人都应该运用理性,以劳动确证自己的力量,实现个人意愿的满足。对此,习近平指出,“广大青年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勇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敢于上下求索、开拓进取……为了创新创造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8](P52)但是,个人的意愿又必须放置在民族意愿中加以考虑。较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归位”与西方文化强调的“争位”而言,个人与民族之间不是要确立何者优先,而是要通过对人们普遍利益的回应,去吸收各自的长处。这种长处在个人那里就表现为“创造”,即个人意愿通过团队的劳动得以实现,而表现在民族那里则是“创新”,也就是不断根据生存现状的变化,诉诸于生产关系的改变,调整已有的关系,优化产业结构。
正是“创新创造”在个人与民族双重维度中各自不同的结合点,当代高校大学生是这种梦想的践行者。这是因为,首先,高校本身是发现新型科学技术的社会机构;其次,大学生是这种新型技术的承载者;最后,在相同的教育环境中,大学生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者共同实现自己的人生意愿。事实上,高校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承认了应当在彼此平等的前提下相互合作,以致力于个人梦想的实现。因此,高校学生创新团队的成功,将能够带动周边更多的人共同融入到这种创新创造的氛围之中,使“中国梦”对更多人具有吸引力。
总之,从民族独立、个人幸福到民族复兴梦想的转换,无论是产业工人、农民抑或高校学生,每一种梦想都是在彼此承认平等能力的前提下,依靠劳动确证了人们的共同理想。正是理想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中华民族的生存面貌才得以发生巨大的改变。当前,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中国道路的启示在于:世界新体系应当在普遍意愿的基础上,确立以“主体示范——共同行动”为核心的新型多核心共建机制。
三、21世纪“希望”政治的展望
进入21世纪以来,回顾世界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的军事干预论、文化普世论、世界政府论等论调,这些主张的背后都试图削弱传统的国家主权,无障碍化资本、商品的流通渠道,遭到了来自民族国家的激烈抵抗。而强行干预的结果是使世界地区形势更加恶化,持“悲观论”的人甚至认为,今后世界将变得比以往更加混乱。应当说,这种论调是对昔日霸权逻辑衰落的心理写照。当今世界并不会落入后西方时代的混沌恐惧,也不会坠入“修昔底德陷阱”,重蹈发达国家的扩张之路,而是在发展中国家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与确立,即从关注民族自身命运转向关注每个民族的共同命运。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将致力于改变民族的生存面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而西方发达国家将以生产力要素的形式参与到发展中国家的进程之中。对此,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9]可见,我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是奠基于发展中国家,面向发达国家的全新共同体。
那么,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形态体系应当如何促成呢?
首先,要结合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历的历史记忆,回应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生存是民族存在的前提,一切民族活动的基础实际上都要围绕经济活动展开。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记忆已经表明臣服于他国产生的“恶果”,而新中国的形象恰好使发展中国家的愿景“具象化”了。因为,这种形象不仅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仅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0]也表明了每个民族在实现发展的过程中,必然经历民族生存(独立)、个人幸福与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必须要从这种形象出发,要使它的内容与这种形象达成一致。由于接受这种形象本身就意味着要改变自身,这就为其他国家鉴融“中国模式”提供了良好契机。
抓住发展的主题,就是对各民族改变落后生存面貌的肯定。同时,我们看到,围绕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教育、文化等领域的问题,都是以合作的方式而展开,这其中便蕴含了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的情况下,如何使规模较小的国家利用大国发展的机遇促进本国发展的内涵于其中。这是一种“同构双向”的发展思路,是与中国对“劳动——改变世界”的逻辑认知密不可分的。从实现发展的前提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架构就是要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与经济发展预期缝合起来,使这种普遍发展的意愿同时具备现实与愿景的双重维度。因此,今后我国应从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入手,加强对各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本着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积极推介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经验,“……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挑战。”[9]
其次,中国应当是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习近平认为,“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所以更珍视和平;中国致力于发展,所以更需要和平;中国期待美好未来,所以更爱护和平。……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理由都不能动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9]建立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实现各国人民的和平相处,这是中华民族的梦想。这种梦想是中华民族从自身逆境中得出的结论,它既不是为了配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是“大国必霸”的逻辑,而是整个近现代史的写照。这就可以有效规避他国对中国发展动机的质疑。而这种承诺也意味着,无论中国发展的经济程度如何,它都将成为理想的践行者。相对于他国民众而言,他们会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上,注意到中国政府实现理想的决心与现状的不断改变,这种“示范”效应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一系列注意与反应。这是因为,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劳动确证了占有世界的能力。中国道路表明:其他民族也可以用劳动确证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一旦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普遍的繁荣,整个民族在劳动过程中对原有文化的重新塑造,便会使其确证民族文化的合理性,获得世界其他民族的承认。而这种劳动的确证以及普遍的承认,正是每个民族希望其他民族对自身所追求文化的、政治的和国家的合理性的承认。
鉴此,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策略上,我国应当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突出中国的成就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对自身幸福与民族富强梦想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只是中华民族理想的观念表达,只是将人民群众所欲言而未言出的东西讲出来,并以经济发展的成就作为这种追求的现实映现。二是要重点突出劳动者的形象建构。每个民族都希望以劳动确认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当前国际关系中倡导的文化包容实质上暗含着对民族劳动成果的确认,这是因为所谓文化就是基于社会劳动的需要,在集体形象建构中,对个体身体使用及他者关系的规制。所以,劳动者的信念是民族前进的动力,劳动者的实践是民族梦想的转化途径。只有在劳动者身上唤起民族梦想的影子,这种方式才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团结,实现各国之间的共同发展。
最后,要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政治结构,使每个参与国家在认同中国形象的前提下,成为这种“形象”的守护者与捍卫者。习近平认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11]面对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事务挑战,回溯文化的或血缘的起源往往是民族国家内部成员联合的普遍方式。而命运共同体则跳出了这种思路,以“首要问题——认同——解决”作为联合的基础。这种新型的政治架构之所以是可行的便在于:中国“形象”包含了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民族自决、民族文化的存在依据、国家现代化的实现能力。而中国话语则在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建立了无形的联系。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在中国话语中确立自身的位置,或者说没有触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那么,这就不会吸引其他国家的注意,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反之,各个国家就必须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履行责任,并将经济的发展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这就表明,命运共同体是在尊重各国主体性的前提下,依靠各国力量的联合来履行职能的。只要联合的力量能够展现出相较于主权国家单独行动的优势,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联合就可以得益于民族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而得以巩固。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双向”合作机制,强化命运共同体——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机制,即实现民族国家与共同体成员身份的有效转换。
总之,中国的崛起给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带来了契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方案是中国道路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自然延伸。在此过程中,构建以发展为主题的希望话语体系至关重要,我国必须以实际行动履行新世纪使命,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1]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 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C].下卷.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6] 逄先知等.毛泽东传(三)[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9]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5/1023/c64094-27730625.html,2015-10-23.
[10]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104/c83846-200830 95.html,2013-01-04.
[11]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5/0328/c64094-26764811.html,2015-03-28.
[12]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5/0903/c64094-27543286.html,2015-09-03.
[13] 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3,(9).
[14]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104/c83846-20083095.html,2013-01-04.
[责任编辑孔伟]
HopeforConstructingHumanDestinyCommunity——EnlightenmentofChinaRoadsince1949
Jing Li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hope; common ideal; China road;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Constructing equal and reasonable order of world is political appeal. However, the current cultural study, political study and national study indicate that new order of world are limited by profits of nationality. It hints that it’s impossible for multi—polarization. The fact of rising of China will terminate this viewpoint. As a multi-nationality state, Chinese achievements expose tha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al void of spirt and consistency of appeal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y. The originality of void is from negation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existence and the hope of a better life. Basing on spiritual needs, common ideal actually becomes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s among peoples, that is,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dividual happiness and rising of nationality, on which, industrial workers, farmers and student are chasing on and guiding each other for regenerating China. Hence,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a road i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should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of hope, realize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 commitment and form new order of world—human destiny community.
*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阿尔都塞晚期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项目号:TJZX16-004)的阶段性成果。
经理,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