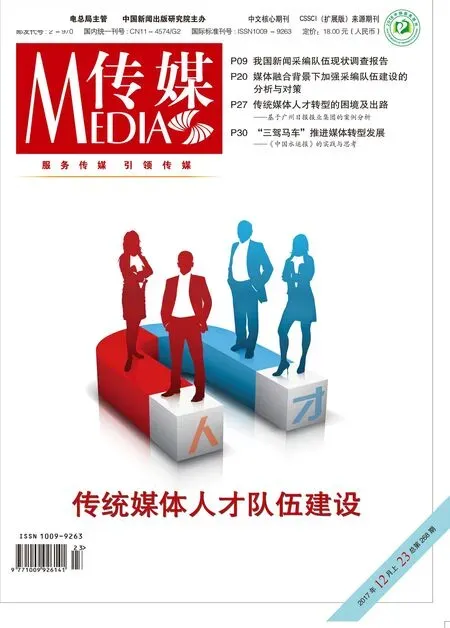少儿音乐类真人秀节目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文/温雅欣
少儿音乐类真人秀节目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文/温雅欣
当前,我国的电视节目将主要市场聚焦于成年人身上,对少儿市场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少儿节目特别是少儿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比较稀缺,远远满足不了少儿的实际需求。而以《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等为代表的音乐类选秀节目和以《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了》等为代表的亲子类真人秀节目的井喷与跟风,导致市场疲软和受众审美疲劳。在这种情况下,湖南金鹰卡通频道、北京卫视等借鉴这两种综艺节目中“少儿”与“音乐”的相关元素,开发出了《中国新声代》《音乐大师课》等非选秀的少儿音乐类真人秀节目。这些节目展现了少儿的童真、童趣与歌唱才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收获了较好的市场回报。但是,节目也存在电视被神圣化、参与者形象符号化和少儿成人化等问题。
电视的娱乐化:功利期待与娱乐化教育
电视自诞生之日起,就由于价格便宜、内容丰富、接收门槛较低等优势,迅速赢得了大众的喜爱。电视本身的巨大威力与观众的超常依赖,以及电视强大的造星功能,导致当前电视的娱乐化趋势愈演愈烈。
电视造星功能与功利动机。电视具有造星与宣传功能,而这影响着少儿参与节目的真实动机,尽管有贵在参与、追寻快乐、结交朋友等好的动机,但在“望子成龙”的传统语境下,以及“出名趁早”“渴望做明星”的浮躁环境下,那些未形成自我意识的少儿参与节目很可能是得到了父母的授意,而非自身的主动选择。诚如美国媒介学家尼尔·波兹曼所言,比赛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如欲望、金钱、身体的训练、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的荣誉。事实也证明,参与《中国新声代》节目的蒋依依,《天才童声》节目的刘宸希等少儿,都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特别是在《音乐大师课》节目中表现良好的向小康,他还借此参加了山东卫视制作的感恩妈妈节目《爱的礼物》。而令人担忧的是,许多选手年虽然年纪小,但已有了丰富的参赛经验,如曾参加过电视选秀节目的棉花糖、胡乔亮、张龙等。可以说,通过电视节目而获得曝光率以及所带来的成名幻象,已经成为家长与少儿参赛的主要动机。越是如此,电视的造星功能越被夸大,越是树立了其神圣的地位。而功利期待造成的电视神圣化,对少儿的健康成长不利。
严肃教育的娱乐化。《中国新声代》和《音乐大师课》等电视综艺节目与教育的结合,导致严肃教育的娱乐化。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以来,除了家庭之外,具有约束少儿行为、传播文化知识与培育道德情操职责的学校就成为少儿最熟悉的地方,而学校最主要的任务便是教育。但是,电视使得原本严肃的家庭与学校教育也逐渐具有了娱乐化倾向。《音乐大师课》《中国新声代》等音乐类节目,模仿学校环境并借鉴学校的教育模式,让少儿产生了熟悉感与亲切感。其中,《音乐大师课》有专门的音乐学院校长、教师和授课教室,里面布置着课桌,师生还需要佩戴校微与红领巾等。同时,节目也有“入学考试”“日常学习”“期中与期末考试”“毕业典礼”等教育板块,而《中国新声代》也有“班内竞歌”“合班精选”等班级元素。
虽然教育离不开娱乐精神,电视也具有传播知识的功能,但学校教育的连贯性与电视的碎片性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打着“快乐教育”“体现个性”旗号的少儿音乐类节目,造成的结果不是培育孩子热爱学校和学会思考的能力,而是鼓励少儿热爱并依赖电视。对此,尼尔·波兹曼认为,在教室里娱乐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在电视上,娱乐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换言之,电视中的教育,其实是以娱乐为目的的。
形象的符号化:苦难叙事与想象性主题
当前,以少儿为参与主体的音乐类节目,以快乐叙事为主,呈现出少儿的天真与童趣,但不可回避的是,苦难叙事与想象性主题,又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参与者形象符号化的问题。
延续了少儿影视剧中的苦难叙事。所谓苦难叙事,便是集中呈现少儿成长的恶劣环境,以及悲惨的现实遭遇与沉重的精神创伤。而这种苦难叙事,又多出现在乡村少儿与残疾少儿中。为了实现节目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兼顾城乡少儿的公平性,肩负媒体的社会责任,节目组不仅选择了城市少儿,还选择了农村少儿和残疾少年作为参赛选手。例如,《中国新声代》里的林志达与傅莹莹、《天才童声》里的张涵与王超、《音乐大师课》里的向小康等农村少儿,以及盲女吴怡铮、成骨不全病的华希、眼球先天性疾病的何陈奕等。这使节目在娱乐的同时,兼顾了社会公平,有利于城乡之间的有效沟通。但节目对乡村风貌与农村少儿和其家长的形象进行了符号化的呈现。
例如,在语言的描述与真实的纪录影像中,节目塑造的农村基本上都是贫穷与落后的。尽管乡村少儿遭遇了多重苦难,但在精神方面,他们又是听话的、懂事的与感恩的。在《音乐大师课》中,节目组选择了湖南乡村的向小康,还请来了她的父亲。为了取得较好的节目效果,节目组有意采用了其母亲生病去世的苦难叙事,也呈现了其父亲与导师杨钰莹教育观念的矛盾。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戏剧效果,但节目并没有顾及到向小康的个人感受,在镜头中的向小康明显有自卑与痛苦的神情。
感恩、励志、爱国等想象性主题凸显,导致参与者形象的符号化。
在《音乐大师课》《中国新声代》等节目中,孝敬与感恩父母成为比较集中的主题。例如,《音乐大师课》中节目组给王亦程、周安信、向小康等安排了感恩镜头,其中诸如“妈妈辛苦了,以后长大后好好照顾妈妈”等话语,明显具有煽情性质。而《中国新声代》节目中,四大导师也频频教育少儿要感恩父母。同时,爱国也是《音乐大师课》中的重要主题,虽然对少儿进行爱国教育是必要的,但节目中导师关于爱国主题的抽象阐释,对于6岁至13岁的孩子而言,是不合实际的。而这种想象性主题的选择无疑也导致节目参与者形象的符号化。
少儿的成人化:价值错位与儿童音乐的缺失
虽然《音乐大师课》等少儿真人秀节目致力于少儿的音乐教育与价值观构建,但其媚俗的语言、抽象的主题与错误的教育方式,无疑造成了儿童价值观的错位。长此以往,会导致少儿与成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童年的消逝便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
语言的夸大性成分。在当前的语境中,“大师”“天才”等称呼,早已广为大众所诟病,因为被媒体包装与炒作并获得大众消费认可的作家、明星等都会被称作为“大师”“天才”,并凭其荣誉进行商业活动。《音乐大师课》节目中将流行歌手曹格、杨钰莹等称为“大师”、《天才童声》中的少儿称为“天才”也具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由于缺乏成人的甄别能力,这些参与节目的少儿很有可能受此影响,造成“大师”“天才”等认识观与价值观的错位。
教育方式不当。为了契合怀旧情绪,《音乐大师课》选择了很多少儿难以学唱的经典歌曲。例如,曹格要求吴文在短时间内演唱难度较大的《外婆的澎湖湾》,导致其演唱异常吃力;韩磊在教孩子爱国歌曲时,充满了政治词汇,而这些是少儿很难理解的;他还让这些儿童现场模拟杀鬼子,直到孩子称“找到杀鬼子的感觉了”为止。这种教育方式显然是非理性的、不合适的。
成人歌曲的选择,加快了儿童的成人化。《音乐大师课》节目包含了“爱国歌曲”“长辈最喜欢的歌曲”“民间歌曲”“影视经典歌曲”等类型,唯独没有少儿喜欢的歌曲或者适合少儿演唱的少儿歌曲。而《中国新声代》节目中,少儿更选择了很多表现爱情的流行歌曲。节目对成人歌曲的选择,显然是成人思维的体现,目的是为了抓住成人市场。无论是少儿参赛者还是少儿观众,都没有获得纯粹的少儿快乐,而这造成了儿童的成人化。
结语
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向往并沉湎于影像娱乐,打造少儿喜闻乐见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无疑是具理想成分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少儿音乐类节目普遍存在着电视神圣化、形象符号化与少儿成人化等问题。广电总局先后下发“限娱令”“限真令”与“限童令”,目的便是为了防止节目的过度娱乐化,保护少儿的切身利益。基于我国少儿群体的巨大市场需求,少儿类节目的制作与创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需要在制作的过程中避免将电视神圣化,避免对少儿参与者的形象进行符号化,以及避免少儿的成人化这些问题,给他们一个快乐而又积极健康的童年生活。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