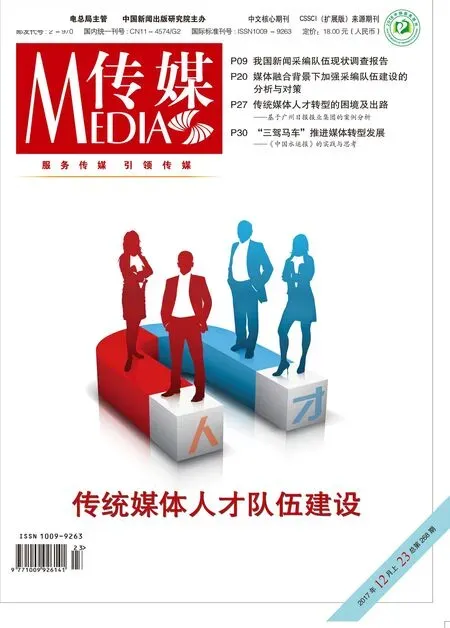和谐社会视域下如何开展舆论动员中的媒体互动
文/王 艳
和谐社会视域下如何开展舆论动员中的媒体互动
文/王 艳
在众多社会议题的舆论动员中,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间的互动及其效果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动员方式和手段,舆论动员中的媒体互动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律,需要以“公共理性”来引导其中的知识生产和意见领袖、以“舆情监测”来把控谣言信息和特殊的社会动员议题。在这一过程中,谋求互动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尽管需要有对等地位和伙伴关系,但在效能上绝不应是等量齐观的,那些真正为时代所认可的“主流媒体”和“权威媒体”要在公共讨论中发挥正向的积极作用,规避由舆论动员带来的可能的社会风险,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和谐社会 舆论动员 媒体互动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是塑造社会共识和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这在众多社会议题的舆论动员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为一种动员方式和手段,“舆论动员”是指“围绕某一特定的社会动员议题,公众、传媒和政治力量等形成公共讨论,并主要由传媒报道和呈现出来,从而影响个人和群体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发动其参与到社会变迁或者社会行动中的过程。”当前,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所在。而对于各类媒体而言,如何参与舆论动员、并与其他媒体开展良性互动无疑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极为重要而且极为敏感的社会实践所在。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要努力寻找在舆论动员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的基本规律,使各种媒体能够在利他或互益中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使社会共识的达成更具广泛性和民主性。而从某种程度上说,推进舆论动员中的媒体互动实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媒体策略和政治智慧,也正是基于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和巩固。
一、以“公共理性”引导舆论动员中的媒体互动
在当前的舆论动员视域中,仍保持高发态势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中的焦点议题之一。面对国家、政府、执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体间的多元价值冲突,身处舆论动员之中的媒体究竟该如何形成社会共意呢?显然,凭借个体的有限性理性是无法完成上述目标的,而只有“为社会共同的善和基本正义问题展开的理性间的交往、对话、沟通”的公共理性才能担此重任。比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地“邻避运动”也随之频繁出现。从2007年至2013年,我国先后发生了十余起重大邻避冲突事件。而在“建”与“不建”的舆论动员中,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互动中的复杂表现其实都围绕着“一种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但负外部效果却由附近的民众来承担”的利益博弈展开。对此,只有凭借“公共理性”才能真正打通不同媒体及其背后的立场壁垒,以良性互动存成社会共识的产生。
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公共理性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因罗尔斯的阐述而广为人知。在罗尔斯看来,“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基于公共理性,媒体能够以互动的形式“有效解决社会生活中共同面临的问题、协调各方立场和化解相互矛盾的问题。”而在具体的舆论动员过程中,公共理性主要由以四种方式显现出来:一是由媒体参与和组织的公共讨论内容应具有公共信息属性;二是包括媒体在内的讨论行为是一种公共参与;三是舆论动员最终达成的共识是为各方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公共价值;四是在舆论动员中运用公共理性引导媒体间的互动体现了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已经在不断涌现出滋长公共理性的舆论动员力量,以公共问题为中介事件,以公共舆论和公开讨论为主要动员方式,以公众参与和平等对话为基本特征的公共理性要素开始大量涌现于网络空间。环顾当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环境,网络“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精神,并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努力方向。这对于传统媒体既是一种补充,也是一种刺激。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讲,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新媒体和传统主流媒体互动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媒体景观下的公共空间本身就是公民社会的组织部分。”
1.对知识生产的引导。在舆论动员中,以主体和载体身份介入公共讨论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究竟应当为公共讨论注入什么样的素质”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换句话说,媒体对成就一个“好的公共讨论”究竟意味着什么。2015年3月,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联合人民网和优酷上推出的关于雾霾调查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议,其中的一个焦点便指向公共讨论的品质和方向。作为一个由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和商业视频网站互动之下生产的作品,有媒体评论其是“一场关于雾霾的科普,是一次公共政策的质询,更是一番公众参与的动员”。从本质上看,这样一种形式的媒体互动对于当前环境保护的最大价值并非是提出了具体的解决路径,而是促使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展开公开的、自由的和充分的讨论,以丰富关于该议题的社会知识。公共论辩最终都是要努力达成某一公共政策的基本共识或者底线共识,而不同的媒体对于知识生产的促进显然是其中的重要推动力量。从舆论动员的角度出发,知识生产的“内在语义是丰富的、是生成的、建构的、解构的,也是批判的。”知识生产可以说是任何公共讨论走向理性的基础。
除此之外,在舆论动员涉及的各种议题领域中,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动员也往往最具难度和挑战性。环顾当下,作为意识形态运作的重要场所,深嵌于制度结构之中的传统主流媒体惯于向公众传达“应当遵守”和“必须遵守”,但对“为何遵守”常常不予重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在“去威权化”的动员模式中,则容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进行“价值解构”。在此情况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需要检视自身在舆论动员中的局限性,积极开展以知识生产、特别是常识生产为核心策略的媒体互动,因为知识和常识通常比空洞的说教更有利于意识形态认同的达成。简而言之,知识生产推动下的舆论动员能够消弭媒体立场的鸿沟,而将可能出现的利益纷争和权力较量框定在知识分歧的视域内。
2.对意见领袖的引导。在公共事件的舆论动员中,活跃在各种媒体上的各类意见领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意见领袖甚至直接成为某一社会动员议程的发起者、组织者和积极推动者,他们通过选择性地关注、选择性地传播信息、选择性地分享和评论,以及发帖量大、在线时间长、表达富有感染力等因素对公众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然而在舆论动员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那些活跃于新兴媒体的以知识分子群体和“新意见阶层”为代表的意见领袖的引导。一方面,要引导其在公共讨论中主动开启自净功能,在提升对有害信息的辨别能力的同时,形成网络意见表达的“制衡机制”,放大理性声音,对冲偏激声音,引导网络话题的均衡分布,从而确保舆论动员能够在多样化信息中保持“航向”;另一方面,则要防止这些意见领袖因意见观点的“派系”之争对社会共识的达成和社会发动的效果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比如说从话语暴力延伸为身体暴力的“约架”等极端表现。这种参与公共事件的方式,以话语霸权取代了交往理性,以人身攻击取代了思想交流,极有可能“成为现实社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在虚拟网络世界的演绎和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兴媒体上意见领袖之间的“约架”已经改变或者说进一步恶化了互联网的辩论生态,因此对其进行理性引导和有效管理意义重大。
二、以“舆情监测”把控舆论动员中的媒体互动
作为技术上把握舆论的一种重要手段,舆情监测能够采集到与各种动员议题相关的社会情绪、意愿、态度、情感和意见,从而有针对性地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舆论动员实践予引导,促进媒体间的协作互动和监督互动的开展,以防范舆论动员的社会风险,降低舆论动员的成本。当前,谣言信息和某些特殊的社会动员议题是舆情监测的重中之重。
1.对谣言信息予以监测。从理论上来看,情感动员策略是新兴媒体的舆论动员“惯习”之一,谣言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社会抗争性事件的舆论动员中,谣言常常诱发舆论造势和舆论审判,而这些都是触发动员客体情感的最有力的工具。大量的网络谣言不仅容易与对抗性解读相伴,也容易与暴力行为相伴、引发群体性事件。网络抗争性谣言往往始于悲情,在愤怒传播中发挥舆论动员的效力,其产生尽管与各种因素的触发有关,比如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和激化、底层公众情绪的被压抑、民主参与的正规渠道资源严重不足等紧密相关,但仍然具有极强的社会负面影响,同时还会对舆论动员中的媒体互动、特别是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产生阻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重点舆情监测。在本质上,谣言是与新闻互补的一种信息形态。因此在对其监测时,不仅要重视对那些一过性的、“暂时新闻”性质的谣言的监测,而要对那些隔一段时间反复出现的谣言予以重点和长期监测,因为与后者有关的社会议题往往出现在现实矛盾根深蒂固的领域,也常常是舆论动员中敏感议题的主要来源,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泛而严密的舆情监测技术是终止舆论动员中各类谣言的前提和基础。
2.对特殊议题予以监测。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中介的跨国动员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各种暴力恐怖事件以及“颜色革命”,这种舆论态势也蔓延到了我国。从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2009年的新疆“7·5”事件再到2014年的云南“3·1”事件,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主要是利用互联网、手机进行暴力恐怖袭击的舆论煽动,从而形成一种需要高度警惕和防范的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不可控性的新型社会风险。在这种态势下,需要通过舆情监测加强对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媒体等的监管,并凸出传统媒体对舆论动员的“把关”和引导、监督等行为,防范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组织利用互联网大肆宣扬暴力恐怖思想,煽动暴力恐怖活动,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近年来,借助互联网开展“舆论动员”的暴力恐怖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损害,其动员主体并不具备合法身份,动员目标更是无法形成“社会认同”。比如在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中,境内外暴力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通过网络等新媒体传播宗教极端思想、造谣惑众,以试图达到蛊惑人心的险恶政治目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非法社会动员议题进行实时舆情监测,从而识别和降低其中蕴含的舆论动员风险,努力净化新兴媒体的舆论动员环境,以有效的社会控制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结语
在不确定性陡增的现代社会中,在舆论动员中谋求互动的不同媒体尽管需要有对等地位和伙伴关系,但在效能上绝不应是等量齐观的,在公共讨论中重新界定出新的、真正为时代所认可的“主流媒体”和“权威媒体”,这不仅有益于社会共识的形成,而且也有益于舆论引导的开展。那么由此就必然涉及如何判断主流和权威的问题。在当前的媒体格局中,只有那些能够“肩负起中国社会改革、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责任,聚焦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和改革难点,突出一些重点的传播领域,广泛集中民智建言献策,用健康科学与智慧有效的信息传播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转型与发展”的媒体,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主流媒体”和“权威媒体”。在今后的舆论动员实践中,传统媒体应继续传播正能量,通过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重拾对主流声音的有效传播力和对主流舆论的掌控权;同时新兴媒体也应不断净化自身所处和参与构建的网上舆论环境,成为舆论引导的积极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就某一社会动员议题展开的讨论,并非是“零和游戏”(Zero-SumGame),应当努力避免二元对立式的价值判断,鼓励讨论的丰富性、层次性、科学性和知识性,特别在一个充满分歧和争议的世界中,既要允许舆论动员中的意见竞争,也更提倡多样性的协商。另一个问题则是随着社会动员主体构成的日益复杂,以及冲突性动员议题数量上的快速增长,传统媒体要深入研究舆论引导方式,避免精英化话语趋势可能导致的居高临下和舆论反弹。
[1]王子丽,吴赋光.公共理性与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J].河南社会科学,2012(08).
[2]张乐,童星.“邻避冲突”中的议程设置——基于R市的实证研究[J].行政论坛,2015(01).
[3]彭剑.社会化媒体舆论:从个体理性到公共理性[J].当代文坛,2014(06).
[4]师曾志,胡泳,等.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郭讲用.微博约架:传媒公共领域的实践困境[J].当代传播(汉文版),2013(03).
[6]童兵,樊亚平.从信息提供者到问题求解者——转型时代传统媒体的角色转型[J].新闻记者,2014(11).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