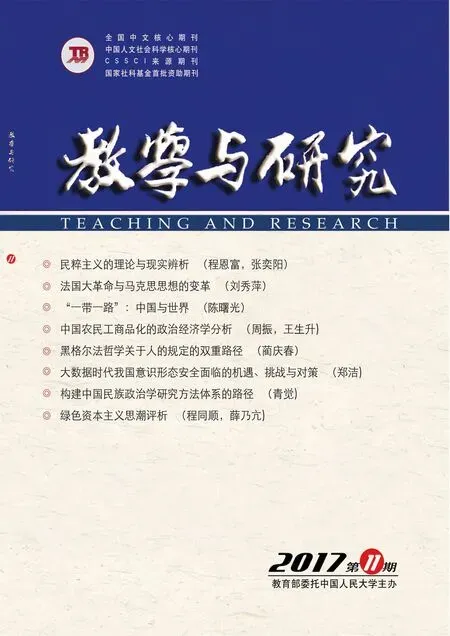法国大革命与马克思思想的变革*
法国大革命与马克思思想的变革*
刘秀萍
马克思;法国大革命;政治解放;人的解放
法国大革命是马克思一生思想建构的重要参照和依凭之一。在思想形成与变革阶段,他从《莱茵报》时期开始关注这一事件,之后通过《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用政治革命与人的解放的视角厘清了法国大革命的短期意旨与长远目标,又通过《神圣家族》借助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批判,对其时代印记、活动方式、民族特征进行了“考察”和“解释”,并且深入到历史细节中对其中的人物更迭、曲折演变及原因进行了探究,最终促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不是思辨逻辑演绎、推论的结果,也不是对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事件进行直观而得出论断的过程,而是通过对思想史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给予持续而深入的考察、追踪、深思而做出的理性的选择。这其中对法国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与思考,构成一条非常鲜明的线索。
在欧洲近代史上,举凡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影响最大、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当属法国革命莫属。爆发于1789年7月到1794年7宣告结束的这场革命之所以吸引众多人的注意,并引起人们的反复思考,并不是由于它发生在占欧洲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的法国,而是因为不论在哲学思想上或政治实践上,它在几十年中一直反映和汇集了欧洲一切“有教养的人”的思想、忧虑和矛盾。“当法国革命者高呼热爱自由的时候,他们用的不仅仅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的声音,同时也是用的1688年英国贵族和1776年美国革命者的声音。”[1](P647)通过这场革命18世纪后期欧洲社会结构的性质所导致的多阶层之间的矛盾得以展现,而启蒙思想和自由观念借助新的手段获得广泛的传播,它所培育起来的自由、平等和民族情感等思想观念和制度在19至20世纪的欧洲甚至是美洲的社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西方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政治革命与人的解放:法国大革命的短期意旨与长远目标
恩格斯在1885年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所写的序言中,曾经说明了马克思之所以青睐法国史的原因:“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2](P468-469)
恩格斯所言确凿。早在1843年1月《莱茵报》停办的时候,马克思就谈到,到国外去就是“想实现自己的写作计划”。9月他在一封写给卢格的信中,又谈到了他即将离开德国时的思想和立场,他写道:未来的情况也许并不十分明朗,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3](P7)本着这样的想法,马克思在10月底迁居巴黎,开始了对于他的思想变革至关重要的一段岁月。
按照卢格的说法,马克思当时“头脑里有一项政治计划”,即“首先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自然法进行批判性的分析,然后写一部国民公会的历史,最后批判所有的社会主义者”。[4](P342)这个说法不无道理。而且,我认为,马克思自己谈及的“写作计划”和卢格所说的“政治计划”实际上是一致的,或者说“写作计划”应该是“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在长期的社会观察和理论创作中,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病,产生了让人们摆脱私有财产关系、回归人的本质的共产主义思想;而在落后的德国,马克思发表自己新的、进步的观点的愿望不能顺利实现,于是,他决心要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法国写作并发表自己的新观点、新思想;这些新思想的建构工作又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从理论上为建立新世界奠定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二是对现实历史进行考察,借鉴历史的经验,思考未来社会的走向。而这两者的结合所产生新的世界观,又必然要同形形色色的社会理论相碰撞、相融合,最后产生合乎理性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
从马克思一贯的工作方式来判断,这样的计划应该是以他前面的研究和思考为背景的,而一旦他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计划,就会着手实施。早在1842年7月到8月,为了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研究现代史(主要是法国革命史),马克思就已经读了一系列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并做了摘录。这其中包括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汉密尔顿的《论北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阅读这些著作的同时,即在《神圣家族》写作之前马克思已经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德法年鉴》上刊出的致卢格的信、《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未完成和未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刊载在《前进报》上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等文献中开始对法国大革命展开了详略不一的论述。特别是从分别写于1843年9—10月和12月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可以看出,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与思考与后来的《神圣家族》是紧密关联的。
(一)《论犹太人问题》
1842年11月,布鲁诺·鲍威尔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了论文《犹太人问题》,1843年又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张》中刊出《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借此考察了德国当时的一个迫切问题——犹太人的解放。随后,他又在布朗施威克出版了《犹太人问题》一书,作为对这两篇文章内容的补充。这些文章和书中的观点引发了人们在报刊上的批评,马克思大致是在1843年秋季在克罗茨纳赫时写下了《论犹太人问题》,来回应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的。《论犹太人问题》分为两个部分:一、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二、布鲁诺·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二十一印张》第56-71页)。显然,马克思这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是对应着鲍威尔的两篇文章之主题一一展开论述的。其中,马克思关于法国革命的论述是在第一部分。在这里,马克思基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分来谈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
布鲁诺·鲍威尔认为,犹太人由于宗教的特殊性,因而不适于解放。犹太人只有首先摒弃犹太教,然后摒弃基督教和基督教国家,才能获得解放。与鲍威尔抽象地谈论人权不同,马克思是从现实历史当中真正存在过的人权出发来分析犹太人能否拥有人权这个问题的。他指出,北美人和法国人是人权的发现者。从他们所享有的人权形式来看,“这种人权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只是与别人共同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共同体,确切地说,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而公民权利,如上所述,决不以毫无异议地和实际地废除宗教为前提,因此也不以废除犹太教为前提。”[5](P39)
显然,如果从政治权力的意义上来谈人权的话,信仰自由就是人权的应有之义。马克思列举了法国1791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10条、宾夕法尼亚宪法第9条第3款等法律条款来佐证他的观点。这些条款均把信仰的权利视为人的自然权利,规定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信仰,即使是宗教信仰,而遭到排斥;任何人的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信仰问题或支配灵魂的力量。所以,“在人权这一概念中并没有宗教和人权互不相容的含义。相反,信奉宗教、用任何方式信奉宗教、履行自己特殊宗教的礼拜的权利,都被明确列入人权。信仰的特权是普遍的人权。”[5](P40)
为了弄清问题,马克思将人权和公民权作了区分。在原始用语中,它们的表述分别是Droits de l’homme 和droits du Citoyen,其中,不同于Citoyen的homme,是指市民社会的成员,不同于公民权的人权,Droits de l’homme 是指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从法国宪法的条款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其中1793年宪法第2条规定,人权是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第6条又将自由规定为“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第16条则规定了“财产权”——财产权是每个公民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的权利;第8条又规定,安全是社会为了维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1795年宪法第3条规定,平等是法律对一切人一视同仁,不论是予以保护还是予以惩罚。
人的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财产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市民社会是以利己主义为特征的,“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5](P42)因此,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对自己自由的限制,黑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把市民社会称为“需要和理智的国家”。
那么,即将扫除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国,为什么要在1791年、1793年两次将人权提上议事日程,而把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贬低为维护这些人权的一种手段呢?是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意识不清醒,把目的和手段弄颠倒了吗?显然不是。1791和1793年的人权宣言明确指出,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保障人享有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可见,法国革命已经认识到,不管在多么急迫的政治事件中,政治生活相对于市民社会生活来讲,都是手段,让市民社会成员享有利己的人权才是目的,这是无可置疑的。也就是说,法国的政治解放是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关系的实质就在于:政治解放是推翻旧的、以封建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在政治国家存在的前提下,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仅限于政治解放并不能完成人的解放的最终任务,而只是人在追求自身解放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显然,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和局限的分析是非常独到和深刻的。而在稍后于1843年末写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接着这个话题,从德国革命的问题、条件和可能性出发,在与法国革命的对比中,表明了德国式革命也必须具有属于“人的革命”的性质,期许德国的社会革命最终彻底带来人的解放。
如前所说,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关注法国革命的初衷。在法国,通过大革命,政治解放已经结出了果实,与此相比照,德国却几乎毫无作为,更有甚者,较之于1818—1820年“开明”的情形,1830—1840年间的德国反而更为“反动”了。因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集中地思考了德国人的彻底解放问题,寄希望于德国也可以产生一场类似法国大革命又超越法国大革命的新的革命。他认为,德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德国犹太人的自私自利和热爱金钱,利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特征。因此,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推翻现代的资产阶级,而并不仅仅是要谋求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就德国来说,正是犹太人的政治解放给1815年后的德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所以,德国未来革命的希望不能诉诸宗教解放。在德国,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德国哲学目前的任务是联系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对德国的法和政治进行现实的批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P4)
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给德国很深刻的启迪,但要走上彻底的革命的道路,德国的具体情况又与法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法国大革命其实是“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的(或者说可以随意获得这些的)资产阶级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他们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试图用自己的金钱和地位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能够使自己被承认为整个社会的等级,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服务。与此同时,他们又成功地把法国贵族和僧侣确立为其对立面,这样,当资产阶级成为解放者等级的时候,其对立面就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公开的奴役者等级。资产阶级代表着解放,有着积极普遍的意义,贵族和僧侣就被看作是整个社会中罪恶昭彰的阶层,显现的是消极的普遍意义。
而德国却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德国旧制度将原则和阶级结合了起来,没有一个阶级处于统治地位,所有的原则和阶级都互相中立,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扮演社会总代表的角色。因此,德国公民就不能用法国的方式来实现,就不能是“纯政治的”革命。“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5](P14)不经过法国式的政治解放而直奔人的解放的终极目标,这也许是理论上的悖论,然而,在德国却可能成为现实。彻底的德国革命,必然是人的解放。
我们看到,马克思参照着法国大革命而对德国革命的现实处境、实现途径和未来目标的思考,事实上把对法国大革命的透析进一步加深了。
二、时代印记、活动方式与民族特征: 超越思辨哲学的“考察”和“解释”
《德法年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集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神圣家族》中,他继续了《论犹太人问题》里对布鲁诺·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的批判,又以法国大革命为议题,抨击了思辨哲学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虚妄而思辨的特征,并以此实现了其思想的变革。
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即使是在研究现实世界、实际的社会历史时,也避免不了将真实的社会历史及其命运归结为“精神”与“物质”、“精英”与“群众”的对立。所以,必然地,无论法国大革命是怎样一个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在他们那里也只能是头脑中的思想活动,是批判的幻想的“象征和虚像”。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主将的布鲁诺·鲍威尔对法国革命进行了新的“考察”,就法国革命的时代背景、现实成果、失败原因等方面展开了分析和解释。显然,在这样的考察活动中,他所自命的“批判家”本身是主体,法国革命是客体,“考察”是“批判家”看待法国革命的手段和方法的展示。“批判家”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的思辨哲学辩护的;同时,“批判家”还别有用心地把这种考察的结论昭告天下,特别是警示愚昧的“群众”。
对于思辨哲学的所谓“批判”,马克思一一予以反驳。
布鲁诺·鲍威尔考察的第一个结论是,“法国革命是一种还完全属于18世纪的实验”。[5](P319)在马克思看来,布鲁诺·鲍威尔用年代学的概念来分析法国革命毫无意义。法国革命爆发于1789年,到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结束,它当然完全是18世纪而不是19世纪的活动。本来,思辨哲学家是最反感事实、真理的,如果非要说布鲁诺·鲍威尔抛出这种年代学上的毫无悬念的真理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还是老一套,即证明以思维为唯一依据的思辨哲学始终占有着“一开始就不言而喻的”绝对真理。所以,与其说布鲁诺·鲍威尔是在考察,倒不如说他是在用“明如白昼”的事实来混淆视听,以给读者造成一种尊重历史事实的假象,好让他接下来的“考察”显得若有其事,实质上是把法国革命当作他的思想活动的幌子自圆其说。另外,布鲁诺·鲍威尔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或许在于,法国革命是18世纪的事情,对于19世纪的德国来讲,其经验已经过期,很难具有启示作用了。
布鲁诺·鲍威尔考察的第二个结论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秩序的范围”。[5](P319)马克思认为,相对于上述第一个结论,这倒是值得去认真“考察”的。
首先,这里的“秩序”指的是国家制度,而“思想”和“制度”属于不同的范畴。由于布鲁诺·鲍威尔把法国革命看作是纯粹的思想的冲突,把法国革命的失败看作是思想的落后,因此,他实际上是把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混为一谈了。在任何情况下,思想都不能超出旧制度的范围,充其量它只能超出旧制度的思想范围;而且,就思想而言,它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而只能通过人的头脑、转化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力量才能得到实现。换句话说,只有当思想摆脱其抽象性而有其现实的内涵,并且越出思想的领域而进入人的社会实践的领域时,才能谈得上是成功还是失败。表面上看,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以平等和自由的思想为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但实际上,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旧制度下的特权阶级之间的一场实际斗争,自由、平等思想的着眼点是资产阶级实际的物质利益,或者说,形式上的平等、自由思想是以实际的物质利益为内涵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而“‘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5](P286)如此看来,一向以思维见长的“批判家”,他们思辨的力量、其对法国革命进行思想方面“考察”的方法,也只是想“自己所想”罢了!布鲁诺·鲍威尔考察的并不是法国革命的思想建树,而是用自己的思想来“建树”法国革命的。
其次,客观地来考察法国革命就不难发现,它在思想方面已经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思想范围的成果,那就是共产主义思想。早在1789年的市民革命中,一个由民主知识分子的代表所建立的社会小组,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萌芽。社会小组的思想家克·福适就主张平均分配土地,限制过多的财产,并主张对凡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给予工作等。虽然革命以中期的勒克莱尔和雅克·卢、后期的巴贝夫密谋失败而暂时遭到失败,但共产主义思想并没有随之而消亡。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并且经过彻底的酝酿,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思想与实践的互动关系。
布鲁诺·鲍威尔考察的第三个结论是,“在这场革命消除了人民生活内部的封建主义界限以后,革命就不得不满足民族的纯粹利己主义要求,甚至煽起这种利己主义;而另一方面,革命又不得不通过对这种利己主义的必要补充,即承认一种最高的存在物,通过在更高的层次上确认那必须把单个的自私的原子联合起来的普遍国家制度,来约束这种利己主义。”[5](P320)按照布鲁诺·鲍威尔的这种理解,法国革命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个人不再受制于共同体,而是像单个的原子一样存在,以至于在社会中产生了个人的利己主义。而普遍国家制度的建立能够将自私的原子联合起来,从而约束和限制个人的利己主义。因此,国家-民族的利己主义就成为个人的最高存在。
在《论犹太人问题》之后,马克思在这里又一次面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与布鲁诺·鲍威尔的理解不同,他认为,法国革命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民族主义的产生,而在于把确立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提到了社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具体来说,法国革命斩断了封建社会中使政治与市民社会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的纽带,随着属于旧制度的同业公会被摧毁,个人与共同体开始出现分离的迹象,表现出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特别是在1793年和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法国革命一方面显示出共同体凌驾于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之上的新观念的绝对统治;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市民社会又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并为利益不受限制的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这意味着社会终将恢复被政治革命临时剥夺的、以利益为纽带的人的个体存在。可见,民族主义是普遍国家制度的必然产物,它否定了封建主义所体现的利己主义,但从封建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获得政治解放的个人,实际上还没有获得作为真正的人得到解放。也就是说,对于人来讲,最高的存在是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存在,法国革命让人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但普遍的国家制度又给人加上了一个束缚,人的存在和发展仍然受到限制,人作为人并没有得到彻底解放。因此,普遍的国家制度想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确认,民族想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确认,就必须以人的解放为前提。马克思再次重申:“人是最高的存在物”,“最高的存在物却必须约束民族的利己主义,即普遍国家制度的利己主义!”[5](P320)
不仅如此,马克思指出,布鲁诺·鲍威尔把现实中的个人比作一个个的原子,这样的理解也是不妥的。原子是个体不假,但原子又不具备个体的所有特征,它的典型特性就是没有任何特性,因此也没有任何由它自己的特性所规定的、与身外其他存在物的联系。这样的存在必然是自我完备的,它没有需要、自我满足,相应地,它身外的世界是绝对的空虚,没有任何内容和意义。布鲁诺·鲍威尔以非感性的观念和无生命的抽象将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设想为原子——与任何东西无关、自满自足、没有需要、绝对充实的、极乐世界的存在物,这只能是想象!现实的社会绝不可能是极乐世界:市民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均是活生生的个体,均有属于自己的活动和特性,是感性的存在物。他们的感觉和特性构成他们的生活——需要及其满足。而恰恰是由于每个人的需要,把个体的存在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必须要建立这种联系。为此,每一个个人都注定要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牵线者。由此可见,在市民社会中,“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纽带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5](P321)
所以,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个人“不是超凡入圣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5](P321)作为利己主义的人,他们不是生活在天堂里,而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像原子那样独立地、自足地存在着,而是必须与别的个体、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而自然存在的、感性存在的个人,其特性和需要——市民生活是彼此连接起来的纽带,政治生活、国家是不具备如此的功能的。这也就是说,不是市民生活必须由国家来维系,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生活来维系的”。[5](P321)这既重申也更深化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见解。
三、革命进程中的人物更迭、 曲折演变及其原因探究
布鲁诺·鲍威尔考察的第四个结论是,“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领袖人物,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和圣茹斯特*圣茹斯特(Saint-Just,1767—1794),罗伯斯比尔的追随者,雅各宾专政的核心成员。关于要造就完全按照正义和美德的准则生活的‘自由人民’的伟大思想……是一种矛盾,人民大众中的卑劣而自私的分子对这种矛盾是以怯懦和阴险的方式作出反应的,人们不可能指望这些人采取别的方式。”[5](P322)简言之,他认为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政府的倒台,是因为他们的美德的理想和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之间的矛盾。具体地说,圣茹斯特关于“自由人民”应该完全按照正义和美德的准则来生活的思想,只有基于恐怖政策才能得以维持一段时间,而且这种思想是一种矛盾,因为在人民大众中总有一些卑劣而自私的人会以怯懦和阴险的方式来利用这种矛盾。此外对于罗伯斯比尔关于将公共的美德当作民主政府的根本原则的说法,他也持质疑的态度。
而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布鲁诺·鲍威尔不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不理解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也就不理解法国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他用民族的利己主义和个人的利己主义的矛盾来说明法国革命的失败,不是“考察”的结果,而是臆想。
首先,与费希特的“自我”的纯粹的利己主义相比,民族的利己主义并不“纯粹”,相反,由于它参与了世界历史进程,因而显示出非常阴暗、掺杂着血和肉、自发的利己主义的特点。布鲁诺·鲍威尔所谈及的民族的利己主义的纯粹性只是相对于封建等级的利己主义而言的,在普遍国家制度建立以后,利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在市民社会中以利益为中介的联合,民族政治必须用市民社会生活来维系,这才是思考现代社会问题的出发点。这样看来,思辨哲学试图证明以民族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比以某种特殊等级和团体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更普遍或更纯粹,并以此作为“考察”法国革命的依据,岂不是太肤浅了!
其次,翻开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们看到,当历史已经由奴隶制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古代的民主共同体就为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所取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为经济基础,商业竞争普遍化,人们以自由地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政府无能为力或者无所作为,人的自然个性和精神个性都被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当然会成为普遍的诉求。但这种诉求的满足无论如何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仅仅从人性出发,着眼于单个的个人的自然特性和精神特性,是万万行不通的。法国“人权”宣言当中的人,由于他们所处历史阶段的国民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迥异于古典古代,他们就再不会是古典古代共同体的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热衷于并且追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形式,完全模仿古典古代的政治形式来建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系,也只能是幻想。归根结底,不能历史地看待国家、不能唯物地分析社会,总之,思想不能与时俱进才是法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布鲁诺·鲍威尔考察的第五个结论是,“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政治启蒙和政治运动就迅速向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这个方向发展,因此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之后不久就能够说:‘有了我的地方行政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可以利用法国来做我想做的一切了。’”[5](P324)
马克思认为,布鲁诺·鲍威尔没有客观地把握法国革命进程,尤其是拿破仑革命的历史作用。拿破仑革命只是史诗般的法国大革命史之中的终结篇,即使他掌握了政权、军队和宗教的力量,也不可能左右和创造法国历史。事实上,无论是罗伯斯比尔,还是拿破仑,任何幻想和暴力,都不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创造历史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
政治启蒙和政治运动并不是法国革命的基础和目的,罗伯斯比尔的倒台、拿破仑政变的历史意义也并不是政治启蒙运动的终结,而是使政治启蒙运动改变了原来耽于幻想、热情洋溢的方式,开始以现实的、实在的方式得到实现。罗伯斯比尔撇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幻想在18世纪的法国建立一种古罗马式的民主制,而当他无法逾越现代民主制所蕴含的抽象平等与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之特征的实际不平等之间的鸿沟时,就不惜使用恐怖和暴力来推动政治对社会的统治。然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在冲破了封建专制的桎梏和恐怖手段的压制之后,取得了符合于它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形式之后,它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大舞台。在热月党建立的督政府统治时期,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迅速兴起,人们纷纷抱着发财致富的渴望创办商业和工业企业,欣喜地享受着新的资产阶级生活带来的鲁莽、放荡、无礼又令人陶醉的感觉;土地得以被查清,封建的土地结构被打破,新的所有者满怀激情在自己的土地上精心地耕作;获得了自由的工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总之,以资产阶级为中坚力量的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生机勃勃的活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宰了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获得和享受人权已经不再是理论的主张,而是成为了现实的任务。
拿破仑打破了罗伯斯比尔不合时宜的政治幻想,意识到了现代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应该对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负的责任,但不幸的是,他仍然没有切实地负起这个责任来。这表现在他既承认现代国家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顺利发展和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为基础的,但与此同时,又不把市民生活看作目的,而是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市民社会仅仅是国家的“司库”、屈从于国家的下属。如此纠结的观念致使他用帝国专制这种行政形式的恐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用对国家本身的膜拜取代了德性。
不可避免地,在罗伯斯比尔倒台、拿破仑政变过程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获得的胜利果实,也因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而进行的不断的劳民伤财的战争又销毁掉了。资产阶级社会最重要的物质利益连带政治利益,都成了拿破仑恐怖主义的牺牲品:拿破仑革命虽然通过对外侵略掠夺,扩大了资本市场,使法兰西民族称霸欧洲,但他的宗旨始终是国家至上、政治至上,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发展在他那里始终只是手段。当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那么牺牲资产阶级的事业、享乐、财富,牺牲资产阶级社会的商业和工业的利益,就成为他必然的选择;不仅如此,拿破仑在鄙视资产阶级社会物质利益的同时,还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把资产阶级社会当做国家的对头。在他那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他曾在枢密院宣称,不容许大土地所有者随便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让国家掌管货物运输进而支配商业。应该说,在拿破仑进行的革命的恐怖主义与新生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争斗中,尽管自由资产阶级占了上风,但它在拿破仑那里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与尊重。正因为如此,法国的商人才策划了首次动摇拿破仑权势的事件,巴黎的证券投机商们人为地制造饥荒,迫使拿破仑把向俄国的进攻几乎推迟了两个月。
拿破仑的对外战争最初具有保卫法国革命果实、反对封建复辟的性质,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拿破仑统治欧洲的野心越来越大,战争的非正义性、侵略性成为主要方面,给被侵略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激起了反法斗争和反对拿破仑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1814年法兰西帝国结束,波旁王朝复辟,法国人民又处在波旁王朝的奴役之下。从以上的事实来看,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的生命史,到1830年并没有结束。可以说,直到1830年,自由资产阶级才真正地明确了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自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在法国开启了发展的历程。
总之,拿破仑革命所俘获的并不是政治启蒙和政治运动,而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新生,以及相应的政治形式。换句话讲,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政变是法国革命的一个历史的分界点,在这一点上,法国革命的两股潜在势力发生了逆转,这之前凸显的是雅各宾党的革命恐怖主义及其政治主张,而这之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主张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主角。
如果说自由资产阶级在拿破仑时代再一次遇到了革命的恐怖主义,那么由于波旁王朝企图重新恢复封建专制制度,它对资产阶级利益的遏制就比拿破仑更加猖狂。因此,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它在波旁王朝时代“再一次遇到了反革命”。所以,马克思认为,到1830年,政治启蒙之后的自由资产阶级,才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这时的他们放弃了实现普遍的国家制度的要求,也不再把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当作自己的目的,而是要力求实现它自己的特殊阶级利益。1830年的立宪的代议制国家,也不再被理解为国家理想,而仅仅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独占权力的正式表现,是对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
可以看出,直面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对法国革命的“新考察”,马克思已然表明了此时的他对法国革命的新的认知:“法国革命史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行进”。[6](P29)而把历史仅仅看作观念的活动而不是群众的经验的思辨哲学,是不能理解历史,也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是持续的、长期的,从《莱茵报》时期开始,一直到去世之前的1881年2月22日致纽文胡斯的信,[3](P457-460)他对法国历史和大革命都有深刻的思考和研究。可以不折不扣地说,这构成他一生思想建构最重要的参照和依凭之一。
[1] 罗伯特·E·勒纳等.西方文明史[M].王觉非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Ruge A.Briefwechselund Tageblätter [M]. Berlin:P.Nerrlich,1886.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M].朱学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孔伟]
TheFrenchRevolutionandtheChangeofMarx’sThought
LiuXiupi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Marx; the French Revolution; political emancipation; human emancipati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Marx’s academic construction. Marx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incident since the period of “Rheinische Zeitung”, wh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thought primitively took place. The French Revolution’s short-term intent and long-term goals was then clarified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al emancipation and human emancipation in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Hegel’sPhilosophyofLawandOntheJewishQuestion. Soon afterwards, with criticizing the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the youth Hegelian school, Marx illuminated the times’, activities’ and ethno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volution inTheHolyFamily, where he went into the details of the history to explore the inconstant personages, twists and turn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volution.The discussion all above eventually led to the maturity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etical research.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文本学研究”(项目号:16BZX009)的阶段性成果。
刘秀萍,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