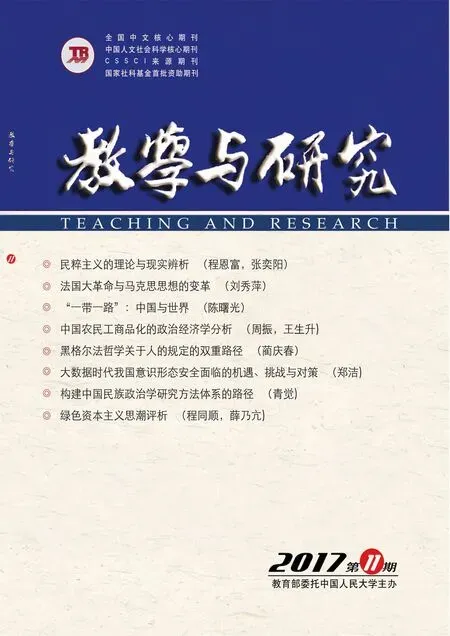隐性网络自组织
——互联网集体行动中的组织状态和治理困境
隐性网络自组织
——互联网集体行动中的组织状态和治理困境
陈氚
互联网集体行动;隐性网络自组织;瞬时结构化;网络社会治理
传统认知中,中国社会是一个缺乏社会组织的社会,但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文聚焦互联网集体行动中的组织形态,提出网络集体行动中存在着“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形态这一理论假设。受到网络社会中速度和时间变迁的影响,隐性网络自组织在特定事件激发之前呈现出一种隐性状态,同时呈现出“个体行动者集合”和“组织”的临界状态。受到特定事件的激发,网络自组织的形成是一种瞬时结构化的过程,时空的压缩和社会互动情境的提前建构,使网络社会中个体行动者完成时间趋近于零的结构化,瞬间发挥传统组织的功能。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存在,模糊了传统意义上个体与组织的边界,是国家网络社会治理的难点和重点,也是网络社会中权力结构变迁的体现。
在互联网发展的初始阶段,互联网上的群体和聚集被视为虚拟空间的产物。学界早期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互联网空间中社群的独特性,将解释的重点建立在网络社会行动虚拟性、符号性、超时空性等独有特征上。而随着现实社会中,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日益融合,尤其是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行动者聚集成功地塑造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推特革命等国外社会运动以及一系列国内的群体性事件之后,曾经的虚拟空间的现实影响逐渐显露,愈发紧密地与社会现实中的实践直接关联。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在这种网络社会的空间融合背景下,社会的自我组织形态产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如何在与传统组织与网络(network)理论框架的对话中解释有可能出现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
一、互联网集体行动中的组织结构
进入新千年以来,世界范围内依托互联网发生的集体行动乃至社会运动不断出现,而进入到改革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阶段的中国社会,与互联网相关的网络聚集和现实空间群体性事件也并不罕见。如果我们按照蒂利和塔罗的概念框架,将集体行动定义为为了共同利益或计划而做出的协同努力,那么上升到政治和抗争层面的互联网集体行动可以被视为互联网抗争政治,[1]而互联网社会运动则是指组织化程度更高,政治或其他目标更加明确的反复运动。中国社会的互联网事件往往介于单纯的集体行动和集体抗争之间,既存在着为汶川地震祈福、为天津爆炸网络募捐等非对抗性集体行动,也存在着为争取地区性环保利益的厦门PX事件、京沈高铁维权等日常抗争事件。这些网络集体行动背后往往并没有传统的社会组织作为支撑,而且大都呈现出“依法抗争”的维权特征。[2]
国内外关于互联网集体行动的研究,大都关注互联网作为中介工具,在社会成员集体行动乃至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社会运动研究的传统中,社会动员机制是集体行动得以成功的重要环节。在网络社会来临以后,这种动员工具从传统的业缘、地缘、亲缘等网络转变为互联网提供的人际关系网络。张文宏等学者提出,互联网提供了一种弱关系,这种弱关系构成的网络可以进行各种资源的动员。[3]也有学者提出,互联网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行动和认知框架,使得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互联网为社会集体行动起到了一种助燃剂的效应,或者在抗争中形成了运动企业家群体,消解虚拟组织进行社会抗争的风险等等。[4][5]卡斯特则通过对突尼斯、埃及、西班牙、美国等地的案例描绘了互联网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首先互联网传递了人们对于某种特定的社会不公正的愤怒,通过互联网为中介的沟通机制,人们开始共享信念和认同,战胜恐惧从而采取集体的行动。[6]但是,笔者认为,互联网的工具论,亦即强调互联网发挥情感传递、价值认同、资源动员这些作用十分必要,但仍然是将互联网视为现实社会之外的技术工具,我们应当意识到,在社会现实空间和互联网空间融合的理论视野下,互联网正在成为现实的生活空间本身和现实的社会结构本身。在这种工具常态化以后,有必要将视角转向结构的层面,重新看待所谓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结合后的新的结构形态,考察这种新的结构形态和集体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
网络集体行动的出现,尤其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种现象,在越来越朝着疏离化、原子化方向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在被普特南等当代社会学家比喻为一人独打保龄球的年代,社会民众因为特定的事件、共同的利益、价值观或者其他诉求,迅速地在虚拟空间乃至现实空间聚集,形成一种行动意义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近似地发挥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却不具备组织的形态。[7]这是在网络化时代后出现的重要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在众多学者看来,中国社会尚且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障碍。而从社区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官方组织的城市社区,往往具有居民参与社区互动意愿度低下,社区活动与社区管理脱离职业群体的趋势,造成了社区社会资本的匮乏。但是,这一传统认知,或许将随着未来网络社会的到来而遭到挑战。互联网带来了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使得社会民众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重新联合起来,这是一种社会组织形态意义上的变革。
二、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形态
面对互联网集体行动中体现出来的组织形态,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组织与网络理论的概念框架审视,则会发现,在一些集体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互联网空间与现实空间结合的组织形态,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组织,也不是仅仅停留在虚拟层面的虚拟组织,同时,相比社会科学中的“网络”概念,又有所不同。
在网络时代,新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网络社会中存在的介于传统组织和传统网络结构之间的一种类组织形式,我们将其称之为“网络隐性自组织”。这种网络隐性自组织,在互联网中生成。在特定的时间发生之前,处于一种隐性的状态,没有固定的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形态和组织结构。但是,一旦特定的事件出现,这些潜在的准组织可以迅速通过互联网转化为一种互联网组织,发挥传统组织的功能,在社会运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中,正式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的互联网集体行动中,正式社会组织的角色往往表现并不明显,推动集体行动的是一个个分散化的、去中心化的行动者。例如,在天津爆炸案之后的网络微公益活动中,真正发挥作用的行动者是基于微博这一社交结构的用户,每一个普通的网友在参与活动前,并不属于某一特定的慈善团体或者组织,但是在特定事件的激发下,每一个微博用户都有一种潜在的可能构成临时性的社会组织。在厦门、北京、江苏等地的环保抗争事件中,也并没有明显的社会组织或者环保组织对所有集体行动负责,或者有能力完全组织起来如此众多的参与者,而是每一个民众通过手机、网络论坛等信息中介,迅速统一了行动的目标和行动的方式,在现实空间中聚集起来。在前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集体行动中,如果没有组织的参与,很难实现集体行动的目标的一致,集体行动资源的整合与调动,往往沦为盲目的乌合之众式的集体狂热。而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在没有传统社会组织在场情况下的集体行动,却可以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惊人的行动一致性,甚至可以通过现有的互联网场景进行各方面的资源调动,并且与现实中的利益诉求或者价值诉求紧密相连。
在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行动中,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功能被一些新的聚集形态所替代。这些通过社交网络、信息平台构成的新的行动者集合往往没有预先固定的组织目标,也没有定期举行的组织活动和传统的组织结构,甚至不能称为互联网之中的组织或者虚拟组织,因为很多聚集在特定的激发事件发生之前并不存在,但却在实践需要的时候发挥了组织的作用,不能用传统的组织概念来概括。
那么,社会科学中的“网络”的概念能否完全概括这种新的组织形态呢?对于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结构问题,卡斯特引入了“网络”这一概念。这里的“网络”并不是特指互联网,而是指代一种特殊的结构,网络状的结构。在卡斯特看来,当代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呈现出网络状态的社会结构,各种资源、要素、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成为社会的重要特征。[8]较早将“网络”与“组织”的关系研究引入到社会学中的是鲍威尔等人,在经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中,鲍威尔提出,“网络”结构是对传统的经济组织结构的一种替代。这种替代体现在从市场交易到国家经济治理的一系列经济行为之中,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9]而格兰诺维特在嵌入性的论述中,也提出与市场——等级制理论相比,社会关系网络同样会在市场交易行为和等级制组织之间发挥作用。[10]阿德勒和本科勒等人进一步提出了对等共创生产的概念,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提升了个人的实际操作能力……令他们可在与其他人的松散联合中做更多事情,却不受价格体系或者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科层制模式的限制”。[11]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实际上将网络的概念更进一步扩展,从人际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物之间的联系上。[12]按照ANT的视角,手机、计算机、信息沟通技术装置与人之间构成了一种网络意义上的联结,成为这个时代的行动者集合。
按照穆勒的总结,我们可以将现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网络”划分两大类别,一类是鲍威尔和本克勒意义上的网络组织,这种网络是人为设计的网络,为了替代组织发挥相应的作用;另一类是事实上的网络,可以称之为关联集群,是指在无边界的行动者集合中形成的一种事实上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11]
概括而言,以往的网络组织和网络关系模式的概念,均是一种静态的描述概念,忽视了一种新的动态变化状况。在互联网社会中的运行速度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在打破了地域、时间、经济等成本的限制后,如果网络的建立可以瞬时发生,网络组织的形成时间可以无限趋近于零,网络社会结构处在一种流变的状态下。
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时,新的通讯技术和社会交往结构可以使这种由网络联通的行动者集合状态迅速转化为有边界的类组织,发挥组织的作用。组织目标、组织的行动方式乃至组织的资源调动都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产生。行动者集群与网络化的组织可以迅速地进行转化,从而发挥出组织的作用。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互联网时代的这种自组织形态呈现出一种在组织与行动者集合之间变化的动态状态,呈现出多重状态,其状态会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而这种在结构的流变中才能确定组织结构的特性,正是鲍曼意义上的流动的现代性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试图将后现代社会理论引入到对网络组织的描摹中的一种尝试。
三、隐性网络自组织形成的速度与时间
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动态流变的这一特性,依赖于以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沟通技术所缔造的新的时空背景。在前互联网时代,行动者集合和组织之间尽管同样有可能相互转化,但是,这种转化的速度与今日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因此,在观察者(作为学者的研究者与作为政府的监管者)看来,作为原子或者作为集合的行动者,与结构分明、目标明确的组织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但是,如果这种从原子到结构的转换可以以近似光速的速度完成,那么对观察者而言,这种结构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当信息无障碍地在光纤中以光速传递时,行动者之间又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连结成组织。在转化速度上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互联网时代的自组织形态,在表面上是一种行动者松散集群甚至完全原子化的状态,但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组织状态。
如果我们把从个体到组织形成的过程视为一个结构化的过程的话,互联网带来的是速度极大加快之后的结构化,可以将其称之为瞬时结构化。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既是对行动者行动的制约,又是行动者行动的产物。[13]在伯格等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社会结构必然是社会行动者在实践中塑造的产物。[14]瞬时结构化则是在新的互联网时空背景下,提出了将时间变量引入结构化理论后(这是现代社会加速发展与时空压缩的必然),这样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当某些具体的社会结构化的过程被无限的缩短后,短时间的结构化何以可能,又如何展开。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沟通技术,以及这种沟通技术背后潜在的缺场行动能力,使得互联网时代的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构成了瞬时结构化的时空背景。我们在这里可以借鉴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中时间的理论概括:“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8]在互联网空间中,行动者面临的时间概念和传统的时间概念相比,也发生了变化,时间与空间密切相关。卡斯特更多地强调互联网之中行动的发生具有一种传统事件意义上的永恒性,事件的痕迹会永久的保持在网络空间之中,无所谓先后的顺序。而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互联网的信息传递以光速为单位,可以瞬间将世界的任何一个空间位置拉近,生产出一种成本忽略不计的跨空间的同时性。正如同张九龄在诗歌中描述的场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样,在前互联网时代,这种同时性的场景不会发生实际意义上的关联,而互联网时代共同发生的跨空间实践活动,可能会具有纷繁的现实意义。
因此,从“无时间的时间”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递速度接近光速,这里的信息不是单纯的信息,而可能包含着意义、信念、态度、情感,更重要的是货币符号、社会资本等流动的资源,这些使得缺场的同时发生的情境具有现实的意义,不仅仅是虚拟空间的意义,而是真实的现实影响力。这种瞬时的速度,在宏观层面上,使得人类社会的运行从未如此之快,以至于产生了哈维所谓的时空压缩,[15]在具体的组织形态上,可以使得行动者从原子化状态或者微弱联结的状态(行动者集合),到组织化的状态的进程从理论可能上无限的缩短。
在时间趋于零的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互联网在空间层面对行动者行动情境的提前建构,这也是时空压缩的重要因素,这也同样构成了瞬时结构化的前提条件。在针对特定事件的互联网集体行动的组织结构形成之前,互联网既有的信息通信技术,以及这种技术创造的交往特点,塑造了一个潜在的交往结构。例如,Facebook、Twitter和微信等技术应用形态,使得每个社会行动者与他人之间先天地产生了一种潜在的组织可能性。在互联网时代,基于这种点对点的社交技术,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交往情境实际上是事先建构的,是一种给定的隐性结构。
在传统的社会行动过程中,行动目的与他人关联的社会行动,都需要发生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情境或者场景之中。而这一情境的搭建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例如,在传统的购物方式下,消费者需要和商品的出卖方共同搭建一个商品交易可以实现的社会场景。在消费者的社会行动中,耗费时间和金钱前往商场,走到柜台旁边,是消费者为了和出卖方搭建交易发生的社会情境的付出,而出卖方则需要为商场的搭建付出租金,为柜台的装饰付出时间和精力,这些都是为了最终的交易行为发生而付出的社会情境搭建成本。同样,对于组织形态而言,传统的社会组织需要为组织成员搭建现实的社会交往情境,需要耗费成本,最重要的是,这种情境的搭建需要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在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中,Facebook、微信、QQ等软件,为每一个行动者提前搭建了一个可以永久利用的社会行动情境,这种社会情境是先在于网络组织的,是在行动者形成组织之前的潜在结构。在某种意义上,瞬时结构化的发生就是将潜在的虚拟空间上隐性结构瞬间现实化和意义化,发挥其现实作用的过程。
四、隐性网络自组织的现实影响及治理
互联网时代的瞬时结构化造就的这种隐性网络自组织,并非仅仅是一种后现代理论意义上的推论,而将真实地影响着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并且这种影响有可能随着民众互联网使用能力、习惯的增强和网络社交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融合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加深。
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存在首先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社会成员的自我组织能力。按照主流观点,中国缺乏社会组织的传统,或者在当前的文化、政治、社会背景下,民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技术发展态势,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一代”将更加适应互联网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一种理想的发展状态下,有可能使得中国未来的社会成员具有更高的自我组织能力。当然,这种自我组织能力如果体现在对群体利益的维护上,在法律的框架以内实行,则有可能产生出更多的合法集体行动,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形成快速结合又快速解体的利益团体。从维护社会民众个体权利的角度,这是一种进步。当然,从另一方面,具有更高的自我组织能力,并不代表具有更高的自我组织意愿。组织化以后的行动者,是否行动还要却取决于一些现实的动因。
从国家网络社会治理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国家网络社会治理的有限性,国家的网络社会治理具有一种理论上的能力限度。现有的社会治理体制中,现实的社会组织与网络社会组织分属于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管辖。民政部门负责现实社会组织的登记和日常监管,而网络社会组织则属于网络管理部门监管。隐性网络自组织恰恰存在于这种日常管理的中间地带。因为,对于民政部门来说,缺乏物理社会互动场景的组织是隐性的,无法监管的。而对于信息工作部门来说,在网络隐性自组织尚未结构化之前,并不是作为互联网上的组织而存在,而是作为松散的行动者集合而存在,具体到每一个行动者上,就更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特点。
随着技术的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对网络社交平台,比如微信群和QQ群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管理的效果,但是这种管理也只能针对业已存在的网络组织,却无法阻止那些尚未存在,有可能瞬时出现的潜在网络自组织。在特定事件激发之前,网络隐性自组织也没有作为QQ群组、微信群组等网络社会组织而存在。只有当特定的事件发生时,例如,京沈高铁的环境保护评估的通过,厦门PX工厂的建立计划的公布等等,现实利益相互关联的行动者才在极短的时间内,借助潜在的互联网社会交往状态组织起来,形成同时具有现实空间行动能力和网络空间行动能力的类组织。而这一结构化的过程和组织化的过程是十分快速的,而且由于信息中介的进一步多元化,从单一技术的角度是几乎无法阻止这一过程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采取传统网络管理模式的国家,在面对互联网的隐性自组织时,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困境。
国家对互联网的治理应当摒弃一种完全掌控的思路,同时,需要具有一种互联网与现实融合的思维,也就是跳出互联网来看互联网。互联网上突然发生的聚集,最终将具有现实的行动能力和影响能力,归根结底是现实中民众利益结构与心理结构以互联网的方式呈现,同时也是来自于现实社会矛盾的影响。互联网中体现的社会矛盾在本质上仍然是现实社会矛盾的映射。互联网中的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形成过程是瞬时性的、流变的和隐性的,而现实的利益结构是相对稳定和可预见的。因此,对互联网的治理应当认识到政府单纯监管和治理互联网行动的能力限度,应当将重点放在现实的矛盾预防和疏导之上。例如,在某些地区性的环保抗争事件中,如果仅从互联网角度进行治理,那么就仅仅会聚焦于一些技术的手段,如防止互联网上的情绪传递和如何过滤信息等等,但是,这就容易忽视这些网络集体行动的现实因素,政府决策信息不透明造成的民众——政府矛盾。只有减少或者避免现实中的直接对立,才能从根本上降低行动者集合迅速演变到组织状态的行动意愿。
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存在,意味着互联网时代的民众,尤其是熟悉互联网技术的城市中产群体和青年学生群体,获得了一种相对的权力地位,并且这种权力是容易被传统管理者所忽视的,具有一种隐性的特质。从国家的角度而言,面对的治理对象似乎是松散的个体,却又是可以瞬间结合成组织的潜在组织。如果轻视这种民众的隐性权力,则有可能遭遇到比前互联网时代更加激烈的负向反馈,这也构成了对国家权力尤其是对国家制定政策的权力的一种正面约束。在具体的政策出台之前,必须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增加与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行动,以共识获得更大的治理合法性。而从更加积极的层面来看,网络隐性自组织也蕴含着社会自我发育和自我治理的潜力。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其中应当“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网络中的民众自我组织现象也应当被充分重视。从正面积极引导和规范这种互联网自组织现象,将是对我国传统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补充。这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自我治理能力增长的重要部分。
[1] 蒂利·塔罗.抗争政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 李连江,欧博文.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A].载吴国光编.九七效应[C].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
[3] 张文宏.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4).
[4] 徐勇.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变及应对研究[J].理论月刊,2016,(1).
[5] 曾繁旭等.运动企业家的虚拟组织:互联网与当代社会抗争的新模式[J].开放时代,2013,(3).
[6] Castells.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M].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7] 朱海龙.网络社会“组织化”与政治参与[J].社会科学,2015,(3).
[8]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9]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J].I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0,(12).
[10]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3).
[11] 穆勒.网络与国家: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政治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12]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4] 伯格.现实的社会构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5] 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李文苓]
RecessiveNetworkSelfOrganization:OrganizationalStateandGovernanceDilemmainInternetCollectiveAction
ChenChuan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Studies, Party School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91)
internet collective action; implicit network self-organization; instantaneous structure; network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traditional cognition, Chinese society is a society lacking social organization. But in the Internet era, social organization has chang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rganization form of internet collective ac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at there exists the form of “recessive network self-organization” in network collective action. Influenced by the speed and time chang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mplicit network self-organization presents a recessive state before the specific event is stimulated. Stimulated by specific events, the formation of network self-organization is a rapid and structured process, and instantly plays the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 The existence of recessive network self-organization,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s the difficult point and focus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al network society. This is also the embodiment of the change of power structur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陈氚,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讲师(北京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