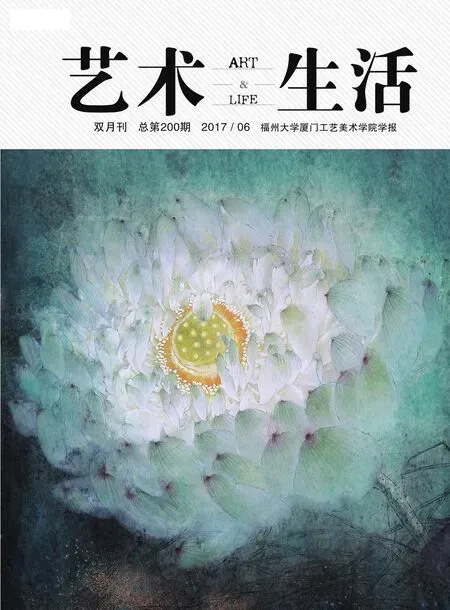美术史研究与高校中国美术史教材的编撰
姜永帅
(江苏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镇江212013)
中国美术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自1917年姜丹书的第一本《美术史》问世,其历史已近百年。中国美术史教材的编撰,正是与中国现代美术史学的独立相伴随。虽然这百年来,中国美术史教材的编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版本数量难以统计(郑岩教授曾经请他的一位研究生进行搜集目前中国美术史教科书版本,居然收获满满两大箱[1](p388),足以见出中国美术史教材编撰的“发达”。)然而笔者翻阅较为典型的高校中国美术史教材,除收录资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外,其编撰模式并不能反映同时期的学术动态,甚至一再重复。有鉴于此,通过对中国美术史教材编撰历史的梳理,研究其编撰的史学观、方法论以及与同期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动态,以揭示中国美术史教材编撰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美术史教材写作的历史及其模式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开始兴办学堂,引入西方教育体制。美术课逐渐成为学科设置的组成部分,美术教材的编撰、美术史的著作也应运而生。仅民国时期就出现了很多版本的美术史,这一时期出现很多版本的美术史书籍,如姜丹书的《美术史》、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等,其中以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书》为代表,且将之成为第一种模式。这些著作基本的方法论并没有发生变化,即对材料进行分门别类地整理。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美术史的分期上,对美术史的分期最能体现出一个艺术史家的史观,例如: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史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则分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代史;而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仍旧保持中国历史分期的观念。正如陈平所指出:这些分期并非直接承袭了古代的传统分法,而是直接受到西方的“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分法的影响。[2](p537)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美术史家意识到传统画学存在的问题,正如郑午昌所指出:
欲求集众说,罗群言,冶融抟结,依时代之次序,遵艺术之进程,用科学之方法,将其宗派源流之分合,与政教消长之关系,为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之学术史,绝不可得。[3](p104)
所以,郑氏的著作和这一时期的美术史写作主要体现在对以往美术的分期上。就拿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书》来说,他将整个绘画史分为四大时期:“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并试图描述艺术的演进过程和流派发展状况。郑氏将美术史的研究纳入文化史的视野,这种模式是艺术史写作的一大进步,并注重美术作品与同时期的政教文化、思想背景相联系。其实,后来许多中国美术史教材的分期大多受到郑氏的影响。即通常把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文化做简要的概括,作为这一时期美术作品的社会背景。然而,不难发现,郑氏的分期,从具体内容来看,又把传统的概述、画迹、画家、画论安排在每章的下面,多有重复。这又受到传统中国画史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的模式制约。这种模式融合画史、画论、画评、著录以及画家传略等诸项为一体,持续一千多年,因此,也被近世学者称为中国画学的一个“超稳定结构”[4](p42-45)。他的主要缺点在于,正如滕固所批评的流于“随类品藻”的弊病,即不成系统,相互之间孤立,缺乏联系,另外前后多有重复。所以,这部著作只是对传统画学的整理,并没有真正揭示美术作品发展的内在联系。
第二种模式,便是以滕固为代表的专业艺术史家。滕固的《唐宋美术史》,以艺术风格的演变为主线,是中国第一部以艺术作品为本位的历史。滕固早年负笈德国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习艺术史,确切时间是1931年4月29日。1932年7月他获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答辩老师是德国著名艺术史家屈梅尔和布林克曼博士。现代艺术史的奠基人沃尔夫林和戈尔德施密特均在该系执教过。滕固曾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沃尔夫林,其著作深受沃尔夫林所提倡的“没有艺术家的艺术史”,即注重艺术史是艺术风格演变史,并通过形式分析揭示艺术作品的风格演变。这一史观强调艺术作品的独立性,强调艺术风格的自主发展。因此,这是以艺术作品为本位的艺术史观。就整个美术史学科来讲,沃尔夫林的艺术史观奠定了美术史学科的内部基础,成为艺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滕固的史观沿袭了沃尔夫林的艺术史观,将风格学的概念引入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领域。打开滕固的《唐宋绘画史》第一章的引论,开头便是:
研究绘画史者,无论站在任何观点——实证论也好、观念论也好,其唯一条件,必须广泛的从各时代的作品里抽引结论,庶为正当。[5](p36)
滕固主张打破历史朝代的束缚,按照艺术风格发展的自律来研究唐宋绘画。他的研究大致如下:
唐初承前代的遗风,山水画还未独立,佛教画仍旧寄迹于外来风格之下,所以叙述初唐,最好和前史——唐以前的绘画,一同叙述,使之占一独立阶段。到了盛唐,即开元、天宝时代,山水画获得了独立地位而往后展开,佛教画脱离了外来影响的拘束而转换到中国风格了。……从此山水画成了绘画的本流,一直发展下去;盛唐以后经历五代迄于宋代初期中期,随着山水画的发达而其他部门绘画亦各露峥嵘了。一直以画取士,流转而产生一种宫廷绘画……院体画发生以了后,浸至末流,为士大夫所厌弃。士大夫欲支撑自己的天下,继续含有“士气”的绘画;及于元代,战胜了院体画,招致了元季四家来装饰近代画史的首章。[5](P39-40)
不难看出,滕固的《唐宋绘画史》打破了朝代顺序,按照艺术内在发展的脉络对各种风格流派的渊源、发展、流变进行了梳理,并把唐宋绘画放置中国绘画史总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平指出:滕固的这本绘画史,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本脱尽古代画论作风的绘画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解释的艺术史。[2](p543)
第三种模式是以王伯敏为代表的《中国绘画史》。建国后,中国美术史教材的编写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影响较大,即强调艺术的外部关系,其分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心态进行划分,将艺术看做阶级的产物,重视“经济背景与政治命脉”和“矛盾是前进的动力”。这一潮流“以王均初开其端,直20世纪50年代以后蔚为主流,王逊、阎丽川、王伯敏等家的通史著作,莫不如是”[6](p453)。这期间,以滕固为代表的专业艺术史家的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在中国沉寂了大半个世纪,直到上世纪90年代,西方艺术史学的引入,滕固的研究才逐渐被人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观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整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美术简史》问世才打破这一研究模式。
第四种模式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美术简史》。该教材系由原系主任薛永年教授主持,原中国美术教研室李树生教授协助主持,1990年9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它的编写集结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研究的大部分精英,参与编写教材的教授、老师,很多都是笔者十分敬仰的学者。所以,该书出版后,十年就发行20多万册,并有韩文、台版繁体中文面世,单从发行和版本也可以看出该教材的学术质量。也正如教材在增订版说明中谈到的:
以中国美术发展的阶段性为纲,以各美术门类在同一时期的演进为纬。注意了四个结合:普及中国美术史知识与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相结合,呈示中国美术各门类的发展演变与阐述重要的美术现象、美术流派、美术家和美术作品相结合,显现中国美术的自身发展与揭示美术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相关因素相结合,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与使用可靠的美术文物(包括新发现的重要作品)相结合。[7]
增订版的说明道出了该教材的研究方法以及美术史观,也正如教材全体编者讨论的第一点那样:
《中国美术简史》(增订本)为按发展过程显示中国美术及其诸品类发展演进全貌的美术通史。力求史论结合,寓评寓述,着重从美术风格发展脉络的条分缕析即其因果关系的阐发中体现具有一定概括性并密切联系历史实际的理论认识,力避脱离历史进程与美术现象的泛泛发挥,并注意在把握美术风格演变中文献与文物二者互证,力戒脱离美术风格及意蕴发展的材料堆砌或作品铺陈。[7]
显而易见,该教材的史观正是建立在滕固《唐宋绘画史》追求美术作品内在的风格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对中国美术史大的风格演变分门别类进行梳理。“说明”中也再三强调打破历史朝代的框架,不依社会发展史划分。足以见出该教材对艺术风格客观发展的尊重。同时,吸纳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将美术现象、美术流派、美术家和美术作品相结合,以及同时期艺术同其他门类之间的联系。这一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对西方艺术史自瓦萨里以来一直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同时也有着中国传统画史的品评的影子。因此,这本教材在当时(2000年)来讲,堪称是一本经典教材。
二、海外艺术史研究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启示
然而,随着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方法的不断进展,对中国艺术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旧有的研究方法很难解释艺术作品丰富的历史问题。尤其是2000年以来,由尹吉男主编,三联书店推出的开放的艺术史系列,显示出海外艺术史界对中国艺术史问题研究的新成果。这些新成果大多从不同的层面揭示艺术作品所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以及对艺术作品含义的探讨问题等等。如图像学的运用、艺术情景的分析、赞助人趣味的分析、艺术作品与消费的关系、女性主义的视角等,这些研究使艺术史的问题变得丰富而复杂。其研究方法都值得中国艺术史研究者深入思考和认真对待。尤其是近年来,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美术史教材的编写提供了不容忽视的视野。即便是拿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与中央美术学院编著的《中国美术简史》相比,仅在材料收集上看,有关史前时期的艺术,前者叙述不到一页的内容,而后者却用了19页,这无疑大大丰富了美术史的内容。但是考古学提供的远非材料,郑岩教授在其论文《考古学提供的仅仅是材料吗》有着明确的阐述,他认为考古学在为美术史提供材料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近年来,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所取代重要的理论成果便是注重物品出土原境的研究,这与艺术史领域的艺术情景研究不谋而合。虽其研究然各有取向,都主张把艺术品放在它最初诞生的情景中研究,强调艺术类别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分类阐述其发展,而不顾及原本整体的情景。比如,在一处寺院既有建筑、雕塑壁画的情况下,郑岩教授十分形象地说:
在“四分法”系统下,我们会在第78页看到壁画被作为绘画史材料加以介绍,但却要翻到第94页的雕塑部分去了解它的塑像,再翻过12页去查看其建筑,至于壁画和塑像的关系、塑像和建筑的关系、寺院和事件以及人物的关系、艺术品与宗教思想的关系等等,就难以写入这部著作了。[1](p360)
郑岩教授也在文章中谈到美术史教材的写作问题,他极具洞察地概括到上世纪的中国美术史的教材是为美术院校的学生所写,而不为综合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而写。只是后来的教材加入了传统以书画为主流以外的考古发现部分,然而在方法论和史观上并没有发生变化。笔者随后又翻阅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教材,由李福顺编著的《中国美术史》(2003),以及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美术教科书,邱振亮编著的《中国美术史》(2007),两本书均是为普通高校非专业的大学生编写的教材,李氏教材意识到普通高校的美术史教材应与美术学院学生的专业教材区别,故在序言中声称“从文化史的视角来介绍美术史”[8]。打开书翻阅,每章按照建筑、工艺、雕刻、绘画、书法,分门别类介绍,并分别在每章第一节概述,章尾附大事记。邱氏本的安排除了缺少每章的大事记外,分类方法基本类同。两本教材均把知识的传递作为主要目标,严格来说,这两本教材并不涉及学术意义的史观,其方法论也只是按照以往的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分类介绍,另加社会环境的铺陈便是文化史部分了。作为普通高校的非专业美术教科书,虽然传递美术知识、艺术史常识是教材的基本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知识的传递不能是孤立无联系的碎片,尤其是更要注意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动态,方能在美术知识传递的同时真正兼顾人文素养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