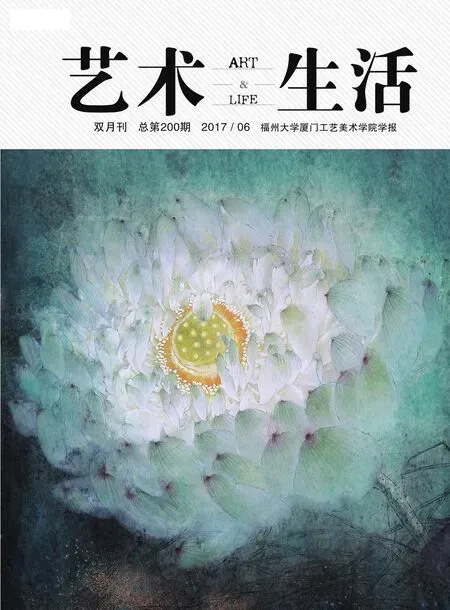试论《写生珍禽图》于当代美术教育之启示
孙琳
(淮阴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淮安223001
美术几乎是与人类文明同时出现的,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发掘中几乎都能找到与美术相关的遗存。美术又几乎是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的,它没有中断过。因而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美术教育也几乎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而出现,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早在《周礼·保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①其中所涉及的六艺虽然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是哪一种解释都包含或包含部分美术教育的内容。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早涉及到美术教育的内容。
这种现象到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改观。谢赫在《古画品录》中首次系统而完备地提出了美术品评的标准,史称“谢赫六法”。谢赫六法虽是着眼于美术批评的著作,然而实际上它还是涉及到了当如何进行美术创作,其中之“传移模写”一条就成为后世众多画家习画、教画的一条重要法则。纵观中国美术发展史,我们还能找到许多关乎美术教育的作品或理论著作。清代龚贤,一生留下了很多的课徒画稿,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给初学者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很有教学实用价值。他所作画诀,言近旨远,精确不磨,现代画家黄宾虹、李可染都从他的笔法中得到了很大的启迪。再有《芥子园画谱》作为综合性画谱,兼具系统有序和浅显易懂的优点,为后世临摹起到工具书的作用,现代的齐白石的花鸟画学习便是从《芥子园画谱》入手临摹前人开始的。不过,古代的美术教育也不尽是临摹,《写生珍禽图》就能给我们多样的启示。
《写生珍禽图》为五代黄筌所作。黄筌,字要叔,成都人。他自幼聪慧,13岁师于刁光胤习花鸟画,又学腾昌祐的蝴蝶,从李升修山水,兼能道释人物,而最擅花鸟。17岁时随刁光胤进入内廷供奉作画,孟昶即位后,迁黄筌为翰林图画院待诏,并主管画院。也因此,黄筌画风主宰了西蜀画院,于是开画艺得官职的先河。宋灭孟蜀后,黄筌随孟昶归宋,入宋朝画院,又被封为“太子左赞善大夫”,西蜀宫廷画风如此入北宋宫廷画院,并成为北宋早期宫廷花鸟画画风之主导。《宣和画谱》:“筌、居宷画法,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②可见黄筌父子的画,对于宋初画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此二者画风趋同,且成为宋初评画之标准。在以画艺得官职的背景之下,黄筌作《写生珍禽图》教子习画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一.《写生珍禽图》之于临摹
在教学方式上,宋代画学极为重视临摹和写生。临摹是工笔花鸟画教学中的基础阶段,宋代的临摹强调严守前人格法。流传下来大量唐代名画的宋摹本,把唐画中精细微妙的地方临摹得不差毫厘,成为了一种艺术精品。如今能看到许多中国美术史早期的绘画作品有不少都是宋人摹本,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烈女传图》,萧绎的《职贡图》,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今天的学者是通过宋人的笔墨看到了晋人的美、唐人的美。这说明宋人是重视临摹的。《写生珍禽图》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需要指出的,宋人不止是重视临摹,他们也是善于临摹的。临摹前先需读画,而后才是摹写和对临,其过程中还必须做到临得其意、摹得其形,从临摹中体会画的意境内涵。
《写生珍禽图》为绢本设色,纵:41.5cm,横:70.8cm。图中绘有各种飞禽、龟、天牛、蜂、蟋蟀、蚂蚱、蝉等。画的右下角有蝇头小楷,署“付子居宝习”字样,书近颜体,是五代楷书流行的风格,由此可知本作品是黄筌给其次子黄居宝临摹用的画课稿。也可以说黄筌创作《写生珍禽图》的目的是展示给其子相关的绘画知识,并提供一个范本可以供其临摹。本作具有超强的写实性,特别是在技法细节上,用线条勾勒轮廓,整体感觉质感坚实,鸟身上细密的丝毛,自然而真实。虽在构图上平铺直叙,但其中展示的绘画技巧和精细微妙、形神兼备的动物形态仍不失为工笔花鸟画很好的临摹素材。对此,还有画家以《写生珍禽图》为摹本开展了一系列工笔画教学案例。[1]
对比宋代画学体制下的工笔花鸟画教学,现代的工笔花鸟画的教学仍然注重临摹,但现代工笔花鸟画的临摹存在很多弊端。其一,大多中国画的教学大量纳入西方基础素描课程,造成国画专业教学的严重脱节。关于这一点目前依然有诸多争议,不少人认为将素描等课程引入中国画教学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和造型能力。对此笔者想说的是,素描可以适当进入中国画课堂,但不可以本末倒置。当中国画之所以为中国画的本质特征都变得模糊的时候,再谈用素描帮助学生来学习中国画岂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吗?
其二,工笔花鸟画的临摹只究其形,而不在乎其意,一味强调技法,使得学画者认识浅薄,鉴赏能力薄弱。关于临摹,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应尽量保持与原作一致。这种一致实际上应该包含有两个层面,即形和意。大多数临摹者在临摹时通常是把注意力放在形似之上,进而忽略了对于原画意的解读和临摹,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临摹。据传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王羲之也曾多次临摹,但都难与初次创作的《兰亭集序》相提并论。究其因,形似较易,神似实难也。在没有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的聚会、没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环境、没有俯仰之间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慨后,即便是书圣本人都难以再现《兰亭集序》的魅力,更何况作为一个一般临摹者,如果不去细心揣摩、仔细体会又怎么临摹到所习作品的精髓呢?故而,作为一个临摹者应该做到形与意二者兼临。
其三,有些教师不能足够重视临摹在工笔花鸟画教学中的价值。在当代美术教育背景下,重新认识工笔花鸟画教学乃至美术教育中临摹的重要性,是《写生珍禽图》能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启发。要知道康有为、徐悲鸿的“中国画退步论”中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当时中国画的写实性远不能到达宋画的高度。虽然不能说写实与否是评价美术作品的标准,但宋人精细入微的笔墨中所传出的神韵不也是我们许多当代的画家和学生所追求的吗?
二.《写生珍禽图》之于写生
宋代理论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评价黄筌的画为“全该六法,远过三师”。六法是谢赫在《画品》中提出的品评标准,在谢赫看来鲜有六法俱全的画家,顾恺之这样的大画家都没有做到六法该备,但郭若虚评价黄筌做到了全该六法,且超越了其三位老师:刁光胤、李升、孙位。能做到这些是极其困难的。如果只是临摹就更加难于超越自己的诸位老师了。这说明黄筌绝不仅仅只会临摹,他还非常善于写生。
事实上,黄筌在当时能够赢得声誉和官职,靠的是高超的写生技巧和生动的造型能力。据《益州名画录》记载,广政年间,淮南与西蜀交好,赠白鹤数只,蜀主令黄筌绘于偏殿墙壁。黄筌绘六鹤于壁上,分别名曰惊露、啄苔、理毛、整羽、唳天、翘足,真实异常,引来飞鹤于画前停立。蜀主及大臣们大为赞叹,便命名该宫殿为六鹤殿。③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黄筌的写生水平是很高的,虽然画史上时常为表现一些画家水平高超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来记载,如张僧繇的画龙点睛、曹不兴的落墨为蝇等典故。但即便如此,对鹤写生于生于蜀中的人来说依然非常困难。
在当时由于四川无鹤,所以四川画家大都不擅画鹤,黄筌只是通过短时间的观察就将鹤表现得栩栩如生,仅凭这一点判断,没有高度的写生能力是很难做到的。黄筌不但做到甚至做得比唐代的画鹤名家薛稷更好。关于薛稷,《图绘宝鉴》卷二记载他:书学褚河南,画踪如阎立本,善花鸟人物杂画,犹长于鹤。④《宣和画谱》卷十五记载:“言鹤必称稷”。②但自从黄筌画六鹤之后,朝野传颂,“贵族豪家,竞将厚礼,请画鹤图,少保自此声渐减矣”。⑤“时人谚云:黄筌画鹤,薛稷减价”。⑥
再看《写生珍禽图》,其名谓“写生”,此图实亦为黄筌之写生作品。画面中20余只小动物均匀地分布,它们之间并无关联,亦无一个统一的主题,但每一件动物都刻画得十分精确、细微,甚至从透视角度观之也无懈可击,显示了作者娴熟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笔墨技巧,令人赞叹不已。比如图中的蓝喉太阳鸟,状物精准,刻画入微,形神兼备;在技法上,淡墨勾勒,因类赋彩,色、墨互不相掩,翎毛骨气尚丰满。如不是黄筌有着丰富的写生实践,又怎么会画出如此传神的作品。联系到今天的美术教育,会发现黄筌对于写生的重视对当下的美术教育依然有很大的启发。
现代教学不重视写生,关于这一点乍听起来似乎是有些耸人听闻,因为在现代美术学院的工笔画教学中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会强调写生的重要性。但笔者这么说是有依据的,有个现象普遍存在,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有些学生在外出写生时,只是拍摄大量的照片,而后再参照所拍照片来进行绘画,且以此为写生。这实在是对于写生的误读。
写生强调的是面对生物,画家通过自己仔细的观察、透彻的领悟,将所见之物以手中的画笔表现出来,其中有着复杂的艺术加工的过程,包括画家将自己见到的三维空间向平面空间转换的过程。很明显,观察真实自然与观察照片是两回事。照片虽然是对于真实世界的记录但照片毕竟是一个不同于真实世界的二维画面,况且这个二维画面是一个定格了的、死了的画面。而真实世界中的一花一鸟、一草一木都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当其遇到春夏秋冬、日升月落、风雨雷电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与情感,这些东西是在照片中看不见的,是要通过真正的写生才能去体味和感受的。世人所熟悉的印象派画家就特别强调户外写生,而且善于发掘同一个场景在不同瞬间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莫奈不厌其烦地去描绘同一个圣拉扎尔火车站,蒙马特大街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在毕沙罗的画笔下。故而,我们的美术教育应鼓励写生,更应懂得写生。对于写生,我们的古人有着贯穿始终的态度。从姚最“心师造化”到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再到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这些都是在强调写生的重要性。
三.《写生珍禽图》之于创作
先需要说明的是,就《写生珍禽图》而言,它并没有包含非常多的创作的内容。这件作品看起来既没有特别的构图,也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可供探索。它看起来就那么平铺直叙,不会让观者觉得画面会富有张力。虽然如此,《写生珍禽图》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关于创作的启示。黄筌作为西蜀和北宋宫廷画家,会吸引我们去探究那时宫廷画院的创作状态。由此我们的视野也不再仅局限于《写生珍禽图》。
宋代的翰林图画院,继承和发展了五代后蜀、南唐画院,结束了唐时宫廷画家分散的情形。北宋前期的画院录用采取“荐入制”和“招入制”,除此之外,画院也从民间画工中招募画匠,崔白就是以此进入宫廷任职的。据《宣和画谱》记载:“益兴画学,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复位博士,考其艺能。”②因此,宋代著名的“画学”得以建立。“画学”体制建立后,画家进入画院必须进行画艺和“经文”等科目考试。故此,我们可以知道宋代的画院考核制度对画家的表现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要求是极高的。比如,有次画院招考的题目就是《踏花归来马蹄香》。就这么一句诗,画家可以有无限种表现的方法,选择何种方式实在是能很好地考量画家的水准,据说入选的作品中没有花,只见一群蜂蝶在马蹄旁飞舞。在当时这一类型的题目还有很多,如《竹锁桥边卖酒家》,也是简单的一句诗,也有无限种选择。结果入选的却是一位没有画出酒馆的作品。画面中小桥流水、竹林茂密,在绿叶掩映之处露出酒帘子,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酒”字。这幅画,画面上不见酒店,却使你似乎看到了竹林后面却有酒店,重点是用形象体现出一个“锁”字来。可见北宋画院的画家都是非常重视创作的。
在今天,我们的画家和美术教育依然重视创作,齐齐哈尔大学的孟德鸿在《工笔花鸟画“三位一体”教学构架探析》一文中提出“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其中讲到:“临摹、写生、创作有机结合、相互渗透、不可分割。”[2]这篇论文就可以作为我们依然重视创作的佐证,况且此论文叙述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普遍性的观点。可见重视创作,不代表今天的美术教育中关于创作的内容没有问题。
在现代花鸟画教学中,由于学生面临着工笔花鸟画课时有限,创作时间仓促,科目多、单位课时量不够、课程衔接不合理等诸多问题,教学浅尝辄止,无法深入,加之原先临摹与写生方面的不足和学生文学素质的缺失,使得学生在工笔花鸟画的创造过程中显得较为被动。如此,在工笔花鸟画创作教学时,注重学生的表现力和创造力的培养便显得更加重要。而表现力和创造力在许多情况下,不仅依赖于画家的绘画水平,同时也取决于画家的综合素养。宋代画院“取士以诗”的考核制度,无疑对画者的文学等其它方面素质的培养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现代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下,众多学生综合素养不高,本已是绘画创作的不利条件。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学生连最基本的美术史、美学类的课程都看作是无用之物。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绘画创作又会有多高的境界呢?想想苏轼、赵孟頫、董其昌等人,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的有识之士呢?故而绘画的创作,不只是与绘画有关,它是关乎一个人的综合修养的。当今的美术教育或许也可以在这一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
小结
黄筌的《写生珍禽图》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的瑰宝。它在给我们带来艺术上的感叹与享受的同时,也对于今天的美术教育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于临摹、于写生、于创作三个方面都引人深思。笔者仅以此文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这些问题,共同推进今日之美术教育。
注释:
①《周礼·保氏》
②《宣和画谱》
③《益州名画记》
④《图绘宝鉴》
⑤《益州名画录》 卷上
⑥《图画见闻志》 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