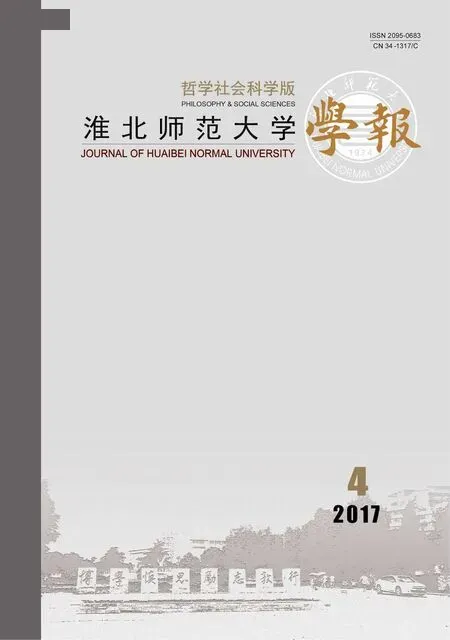深度拓展近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空间
——晚清民国“边缘”女性创作研究的策略
赵慧芳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深度拓展近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空间
——晚清民国“边缘”女性创作研究的策略
赵慧芳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如果将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史视为“中心”,进驻其中的女性创作为数甚少,大量的晚清民国女性创作被“边缘化”,且多处于“消隐”状态。这些“边缘”女性创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基座,其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寻求晚清民国“边缘”女性创作研究的策略与路径,有助于探讨深度拓展女性文学研究对象空间的可能性,发现女性文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使女性文学史写作与当前的“重写文学史”理论和实践形成对话。
近现代女性文学;对象空间;“边缘”女性创作
晚清民国时期,女性文学郁然勃发,众多女作者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然而长期以来,能够进入主流文学史的女性文学仅为少数。近年来,随着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近现代报刊史料的进一步发掘,这些湮没无闻的“边缘”女性创作,也逐渐得到学界重视。深度拓展近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空间,在理论方法和对象资料上都已具备了充分条件。总结晚清民国“边缘”女性创作研究缺失的原因,寻求“边缘”女性创作研究的策略与路径,发现女性文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已成为近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一、晚清民国“边缘”女性创作研究缺失的原因
19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蔚为风气,“性别”几乎成为与“以时期(period)、运动(move⁃ment)或世代(generation)为中心”[1]并列的第四种文学史分析框架。然而,当我们考察那些将“性别”嵌入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或者反过来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剥离出女性文学史的研究,将发现其对象空间相当狭窄,大批女性创作被边缘化,未能进入(女性)文学史。
一是文言写作的女作家作品的边缘化。虽然有许多学者努力将文言写作纳入晚清民国文学研究的视野之中,但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往往还是强调现代文学必须是白话文学。因此,在近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坚持文言创作的女作家以及白话女作家的文言创作,均长期被排斥或者无视。比如被誉为“近三百年名家词之‘殿军’”①转引自李保民.吕碧城年谱[M]∥吕碧城著;李保民笺注.吕碧城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6页。的吕碧城,即使其文言创作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甚至是文学史发展脉络中难以切掉的环节,也难逃被刻意遮蔽的命运。虽然在郭延礼、刘纳等学者的努力下,吕碧城最终得以“浮出历史地表”;而同为南社女作家的徐自华、张默君等,则少有学人问津。再如苏雪林、冯沅君等一批“现代”女作家,其文言诗词写作也几乎无人提及。
二是特殊政治语境、地域的女作家的边缘化。一批知名女作家在事实文学史上曾经引人瞩目,却因政治原因长期被边缘化。比如张爱玲、梅娘、苏青等;另有部分女作家由于地域原因被湮没,如台湾女作家叶陶、杨千鹤、黄宝桃、张碧华等。
三是由于性别身份原因被边缘化。一些优秀女作家,或因身份特殊,或身处名人之侧,其光辉为名人所掩,学术界也关注甚少。如红军女作家、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朱生豪夫人宋清如,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等等。
更多的普通女性作者,彼时仅为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大合唱中的一员,作品未必精良,创作未必持久,虽为那一时代女性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背景”,却从未获得进入文学史的资格。其实,除了发现多样的文学才华和佳构,文学史写作不应摒弃一般的、非杰作的文学样式,因为它们也是构成事实文学史多元与复杂面向的重要因素。[2]
这些晚清民国女作家创作的边缘化,既跟研究者的传统文学史观有关,也源于研究者对于权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模拟,或者未能充分重视近现代中国女性创作的特殊性。如果我们尝试像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那样,对文学史进行批判性审察,即“首先确认在当前的文学研究实践里有哪些研究方式和信仰是司空见惯的,然后问一问这些研究习惯是否都是有效的工具”[3]7,再“把物质、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想象加诸我们习以为常、确信不疑的事物”[3]7,而“最复杂也是最深刻的”,是探询那些文学史写作所围绕的“重要的”作家,“他们是什么时候成为‘重要作家’的,是什么人把他们视为‘重要作家’,根据的又是什么样的标准”[3]7-8,那么,这些“边缘”女性创作就会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并成为我们重新认识晚清民国(女性)文学史的重要史料。
二、已有晚清民国女性创作研究“去边缘化”的努力
事实上,当我们使用“性别”视角重新打量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时,就已经开始了“去边缘化”的努力。在新观念新史料促发下,戴锦华、刘思谦、盛英、乔以钢等大批国内学者,以及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刘禾、刘剑梅等海外汉学家,不断打捞处于以往现代文学史书写边缘或从未进入过书写文学史的近现代女性作家作品,并在新的理论框架内予以重新阅读和评说,使得被遮蔽的部分晚清民国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甚至从文学史的“边缘”步入“中心”。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张爱玲。当夏志清将之单列专章加以论述、重加推崇,我们才看到张爱玲独辟蹊径的创作,及其对于现代小说的重要贡献。中国大陆持续的“张爱玲热”甚至从学术界进入消费领域,愈加巩固了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常常将起始时间划定在1917年或者1919年;清末民初的文学创作则一并归入“近代文学”。而“近代文学”因为已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尾声,多年来一直不被学界重视;其间的女性创作,更是被深深掩压。但仍有一批学者,致力于对于清末民初女性创作的挖掘和研究,并取得不俗的成绩。比如郭延礼即以其对于近代文学持续而扎实的探究,使得一大批女性创作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
而这一批清末民初的女性作家,大都以文言进行创作;研究她们,不可能不重新思考和评价其文言诗文写作的问题。郭延礼、魏爱莲(Ellen Widmer)等学者,都注意到清末民初女诗人及其文言诗文作品,并着手研究单士厘、吕碧城、张昭汉等女作家及其文言创作。
也有学者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挖掘近现代女作家的创作。如宫红英发掘燕赵地区现代女性文学创作史料,陈子善、王羽对民国上海女作家的追寻,萧成对台湾现代女作家的梳理等。这一类细致整理,也让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得以现身。
众多学者如此致力于学术发声,使得大批晚清民国女作家重现于世,面目逐渐清晰,价值得以重估,贡献得到承认,证明了还原“事实文学史”的重要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中“被边缘化”和事实上的“边缘”现象已经得到充分重视。与现代文学研究一样,在近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中,文言与白话的壁垒依然存在;由于史料搜集未能广罗博纳,理论层面尚存深化空间,晚清民国女性创作依然遗漏众多,许多女作家的作品还有待价值重估;更值得重视的是,曾经在民国时期与众多知名女作家一起创作的女作者,她们不甚知名、无大影响,一直被研究界忽略,但她们的作品未必对知名女作家没有启发,她们的存在更构成了那一时代女性文学创作的重要背景。忽视这一点,忽视文学史书写中边缘与中心、支线与主轴的游移和互动,则不可能对当时的女性文学做出深入研究和确当评价。
三、晚清民国“边缘”女性创作研究的策略
研究晚清民国“边缘”女性创作,既出于研究对象的事实性存在,更与近年来文学史观念变更密不可分。新的文学史观更重视文学史的多元而复杂的面向,致力于解构文学史的权力话语,瓦解所谓“正史”的意义。张松建曾经指出:
长期以来,随着五四文学的“经典化”,人们愈来愈相信现代中国写作的主流风格是以白话文为载体、汲取西方形式与技巧的“新文学”,这似乎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换言之,现代文学之“现代”,不但被历史地约定为一个“时间概念”,而且也被想当然地视为一个“性质概念”,在事实陈述之中自然也包含了某种价值判断。五四文学的先驱者通过自己的实践,一方面牢固确立了现代性方案的自我认同,同时也把那些它所判定为“非现代”的文学排斥在这个系统之外,最后形成了“新文学范式”的霸权。[4]315
事实上,这种“‘新文学范式’的霸权”,对于女性文学的压制更突出和严重。因此,在相关研究的策略与路径上,必须结合新史料的发掘、旧史料的重读以及历史现场的还原,有针对性地拆解各种遮蔽与掩压。
我们可以尝试从研究层面打通近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中文言与白话的壁垒。如同郭延礼等指出的那样,晚清民国时期,有许多女作家坚持文言创作,也拥有众多读者。因此,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展示她们曾经对中国文学发展起到的历史作用,指出女性文言创作与白话创作之间的关联,就不失为“边缘”女性创作研究的可行路径。而白话文学兴起之后,那些“现代”女作家除了白话写作之外,也有文言作品问世。研究现代女作家的文言写作,不仅可以捡拾起那些被抛弃、被遮蔽的文言作品,更可以使我们深入认识其文化心理和审美选择。总之,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尽量发掘那些出于种种历史与人为原因“被边缘化”的女性文学创作,恢复被遮蔽的历史记忆与文学/性别想象,尽可能复原中国现代文学史本有的多元化格局,令书写文学史尽量贴近事实文学史。
借助现代女性报刊构成的文学场域,则可以客观复原历史记忆与文学/性别想象。正如贺麦晓(Michel Hockx)所谓“集体作者”,“被当作一个分析单元的杂志期号,不能被视为单一作者的产品。相反,它可以从三个另类的角度来考量:作为一个集体创作的文本;一个编辑的产品;一个没有作者的诸多声音的集合体”;而“水平阅读”则强调“一份刊物的同一期号上的诸多文本在空间上的联系。在多数情形下,这种阅读策略承认单一的小说或诗歌不算是独立的意义单元,不能被称为‘文本’;所谓‘文本’应该指的是杂志期号本身以及它的全部视觉内容”。[4]312在近现代报刊上,我们可以看到众多不知名的女性作者参与了当时的群体性表达,为特定场域、氛围的形成而发声。针对这些不知名而有意义的现代女性创作,我们应该描绘出晚清民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合唱图景。
不以性别关系型塑文学研究中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中心、自我与他者二元模式,转而重视观照这些关系间幽微复杂的互动,勾画其中的对话轨迹,可以重现事实文学史的多元化格局,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形成对话,开敞新的现代女性文学/文化研究实践可能性。
四、深度拓展近现代女性文学研究对象空间的可能性与价值意义
晚清民国“边缘”女性作者,大体有两类,一为晚清民国未成名的女性作者,一为此间已成名但目前被边缘化的女作家。第一大类仍可分为两小类,一为发表或出版过文学作品者,一为私人写作、未公开过作品、但有关于其创作的相关记载者。其地域分布、教育背景、社会身份、经济来源、创作观念、创作实绩与影响,均值得研究者深切关注。而“通过文献和文化的双重功夫”[5],将考证与透视相结合,进行持久而开放的学术探索,正可以深度拓展近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空间,为客观深入的研究提供可能的学术生长点。
近年来,晚清民国报刊电子数据库的开发,使更广泛的研究者群体得以阅览近现代报刊。这些近现代报刊,既为我们呈现了女性创作的历史场域,也为当前女性文学研究对象的拓展提供了资料来源。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五四风潮激荡,大批知识女性被感召、被吸引,常在报刊撰文写作,参与时代大合唱。这个群体中少数女性扬名,成为现代女性文学史(甚而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但大部分女性作者,因创作未持久、作品未臻善,而与文学史高头讲章无缘。但她们是那个时代女性文学书写的大基座、大背景,具有现代性及社会性别革命的精彩意义。当我们将研究对象定位在包括那些未成名的一般女性作者及其文学书写形态在内的“边缘”女性创作之上,我们其实已经完成了研究观念“新定位”以及研究对象“特殊性”的深度拓展。
首先,晚清民国“边缘”女性创作研究基于这样的观念之上,即强调“现代女性文学书写史(或写作史)”不等同于“现代女性文学史”,认为前者远远大于后者,前者所包蕴的社会学内涵亦非后者所能承纳;两者研究的中心指向也应在学术观念上有所区别与分异:前者可以关注包括一般女性的文学写作在内的“边缘”女性创作,后者只关注女性文学家的“经典”文学创作。关于后者的研究,我们已很熟悉并得心应手:关注于作家、作品、流派归属、文学史地位评价等等。但是关于“一般女性作者的文学书写”这一“文化行为”的社会、时代流行史,以及其他“边缘”女性创作,其主要的研究指向应该如何定位?这也正是“女性学”学科尚要构建的分支学科的重要内涵。
其次,晚清民国“边缘”女性创作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可以独立界定的特殊区域。其总背景是现代女性文学书写的历史空间,已有的女性文学研究关注的是其中的部分“成名”女作家的被“经典化”的文学创作,除此之外的广大区域,都因被“边缘化”而在(女性)文学史中呈消隐状态。这些“边缘”女性创作,包括近现代报刊中反映的所有未被关注的“边缘化”女性文学书写,以及大量并未通过报刊形式传播但也留存于世、然亦被边缘化的女性文学书写(如单独印行出版、书信传播、口头传播、家人存藏等形式)。这里,“报刊形式”传播的女性文学书写与“非报刊”形式传播的女性文学书写在属性特点上有分异。前者受“报刊性”(出版时限、办刊宗旨、办刊条件、地点、阅读对象等等)的影响与制约,后者则无。这种“报刊性”的影响也是我们研究中应当特别关注的。
倘能立足于考据与批评相结合,从搜辑整理晚清民国女性文学“边缘”史料入手,考察女性创作产生的内在动因和外部影响,分析边缘与主流间的对话和互动,自然可以阐明其文学史价值与性别文化意义,进而揭示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面貌,丰富并深化女性文学研究,形成与(女性)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对话。同时,也可以建构近现代报刊视阈的“女性”“小人物”的文学书写历史,为现代女性作家、作品史提供一个“基座”或边缘性的参照系。
可以看出,深度拓展女性文学研究对象,并非“去中心”化,而是拾遗补缺,尽可能找回历史现场感,使书写文学史尽可能贴近事实文学史。对于晚清民国“边缘”女性创作的研究,其意义正在于此。
[1]陈平原.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M]∥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7.
[2]季进.多元文学史的书写——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之一[J].文学评论,2009(6).
[3]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 宇文所安自选集[M].田晓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张松建.现代中国文学场的建构——贺麦晓《文体问题》阅读感言[M]∥张松建.文心的异同 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5]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7(1).
责任编校 边之
I206.5
A
2095-0683(2017)04-0093-04
2017-08-01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5D112);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SK2014A091)
赵慧芳(1971-),女,安徽砀山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