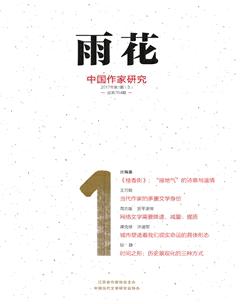江山死否?
杨建兵+徐梦婷
历史和文学作品一样,也是一种文本。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相通性,使文学对历史的改写成为可能,而且,许多历史人物是因为走进文学殿堂,经文学作品的演绎与传播之后,才具有了激动人心的魅力,文学形象的内涵也在诗与史的不断对话中逐渐丰富起来。
在历史穿越小说盛行的近十几年中,一些经典的网络作品已经“黄袍加身”,如桐华的《步步惊心》、李歆的《独步天下》、玄色的《哑舍》等等,它们各自凭借在语言、情节和人物上的特色成为网络文学研究难以绕开的典型个案,也向坚守传统文学研究者们证明,完全不必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而忧心忡忡。那么,以浑然天成的历史想象出彩、敢于涉足穿越小说处女地的《秀丽江山》,是否也会成为李歆继《独步天下》之后的又一经典呢?
一
《秀丽江山》讲述的是王莽新朝末年,南阳刘氏领导的汉军为匡扶经纬,披肝沥胆重统江山的故事。乱世的青年才俊常会成为后人谈论的焦点,这个定律已经被《三国演义》演绎了无数遍。李歆尽管没有罗贯中力透纸背的如椽大笔,却敢于踏足强汉光环下的埋骨青山,去呈现一个病入膏肓的王朝在垂死之时的竭力挣扎。这部主打爱情的历史穿越小说,整体文风严肃,时而带点肆意的活泼,语言平白如话,通达流畅,作者并不效仿一些刻意追求古典意味的网络小说,将穿着现代的人物推到戏台子上,咿咿呀呀唱一出“文不对时”的老戏本,她只有在处理史书上记载的真人真事时,才会像一位引经据典的老学究一样,得意洋洋地吊一吊书袋子。秀丽夫妻的爱情传奇是《秀丽江山》的主音,但小说涉及的内容比“独善其家”的爱情更为广博,并以此区别开其他缱绻妖娆得有些肤浅的网络小说,如被部分读者奉为南朝穿越经典之作的《凤囚凰》。若说《秀丽江山》较之风格绮丽的《凤囚凰》有什么更吸引人的地方,想必除了“小三国”的金字招牌,便是东汉开国时才德韬略概不输容止的能臣强将了。不可否认,容止确实与冯公孙一样足智多谋,但他只看到了南朝承袭的魏晋风流,却没能读懂魏晋的暴力和鲜血,殊不知美色安乐只存一时,政权更迭下的万仞江山才是不朽。
《秀丽江山》小说的情节安排紧贴史实,起笔于新朝建国第十年,即天凤四年,搁笔于永平七年,期间浩浩47年,处处充斥着君臣算计、家族争斗、战争血泪,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对弈时刻在上演。作者在尽可能照顾到所有剧中人物生命轨迹的同时,对目不暇接的节点事件展开了详略得当地叙述,如详写刘秀在刘伯升遇害后的种种怪异行径,略写李轶向刘圣公献计诱杀刘稷和刘伯升的过程。如此富于文学味的情节设置,不仅可以让故事变得张弛有度,而且有利于提高刘秀在一众能人强将中的辨识度,继而顺理成章地在他“温柔好笑语”的性格中增添一笔沉稳多智。对《秀丽江山》一类时间跨度较大的文学作品来讲,详略与虚实是判断作品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情节掌控方面,《秀丽江山》和《凤囚凰》二者相加的分量也敌不过一部《三国演义》,同样以史为骨,同样笔涉乱世,罗贯中在处理纷繁复杂的三国人事时,有意对史料进行适当取舍,从而使小说角色抽枝于《三国志》,却又与原汁原味的历史人物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最终达到“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艺术境界。反观《秀丽江山》,在消化庞大的历史信息方面还稍显吃力,有时更是为了忠于历史强行勒住想象的缰绳,不免有生搬硬套之嫌。如何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是包括穿越小说在内的一切历史题材的文学需要思考的问题。
网络文学不是无根浮萍,它也在学习经典中寻求进步和突破,经过十数年的发展,网络文学的特点愈发凸显,他关注读者的兴趣,但面对新鲜题材也不惧做“吃番茄的第一人”,创作门槛很低,但文笔和故事依旧被读者看重……不过,这些特点仍然掩盖不了年轻作者读者们最看重的两个字:情怀。从历史穿越小说《战起1938》入圍茅盾文学奖开始,文学界就已形成共识,网络文学从来都不是一个贬义词,仅仅是“垮掉的一代”“我手写我心”的最便捷途径,在网络文学日渐成熟的今天,传统文学是时候搁置偏见,躬身去蔡阳刘氏麦浪涌动的田间垄上感受一下这群文学江山的接班人对历史文化的小执念和大情怀,也看一看那位自清廷重回汉家的姑娘,是如何借得故人四分赤心六分才情,凝神细书一段自古名士如美人的茜色传奇的。
二
毫不夸张的说,每个人都做过恣意潇洒走马江山的痴梦,期冀有一天借东风,腾云霄,“扶摇直上九万里”,“温酒赋尽诗酒茶”,我们可以把这梦想笼统地归结为老庄情怀,但比之于隐逸遁世的惯常说法,我更愿意称之为天性——狂妄得令人拊掌笑骂的天性使然。在《秀丽江山》里,女主角阴丽华集可爱与狂傲于一身,以区别于史册里那位美貌端庄的一代贤后,现代思维赋予了她鲜明的人格魅力,而她所有的爱恨情绪又强烈到将她自己烧成乱世里的一滩灰烬。当我们以为这就是“任性”的极限时,小说里另一位更加狂狷傲气的人物简装登场。事实上,东汉名士庄子陵的出场很难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因为作者在勾画庄子陵的形象时笔触略显平淡了些,仿佛水墨画上一个超然世外的背影,始终让人心生一种雾里看花的隔阂感。但正是因为这种难以触碰的距离,赋予了庄子陵令其他角色望尘莫及的夺人光彩。从庄子陵的正式露面到拒绝为官而与主角进行的机智周旋,凡有他出场的情节必定是清风徐徐,水波不惊,一派与世无争的轻松愉悦,也在主线情节波折迭起的时候给读者发热的脑子送来一掬冷泉的清凉。
庄子陵是《秀丽江山》中性情最契合名士风度的人物之一。自古名士皆至纯至真之人,纵使江山几番更迭,真名士迎风踏浪,不退不畏,远有国之名士公孙鞅以青山松柏自勉,千金徙木变法强秦,近有忠义贤侍张骞立身以信持节西度,坎坷远行十三年,他们无一不践行着天意不足畏,舍命谢君恩的处世之道①。千年来,故事里的人物依然颜色不退,德望不减,言名士,必公孙已成共识。那庄子陵呢,他的治世之才比之鞅如何?对此刘玄曾说,“阴识是个人才,朕顾惜人才,也不会滥杀无辜,否则开了这个先例,像邓禹、庄光这般的能人隐士愈发不肯归附,于朕所用了。”可知庄子陵的才能可与云台二十八将高居首位的邓仲华并肩,此后刘秀的屈尊三顾也印证了这一点。可以想见,倘若乱世不平,庄子陵的作为必定与云台诸将不相上下。我很期待作者可以顺着小说的发展,而非历史的进程向读者展现一个可掌理国之大任的庄光。做一介逍遥隐士,富春垂钓等愿者上钩固然是一桩美事,可如若施大才护苍生得名留青史,那未尝不是江山之幸!
事实上,庄子陵不愧为有担当的真名士,他虽远遁方外,却不似魏晋七贤一味地消极逃避世间牵绊。凡人世道他看得通透,自身的才华在刘秀诸位文臣武将面前难免明珠蒙尘,而他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倨傲本性绝对不允许他做出这样的抉择,因此他除了在江山未定时拜请程驭老先生救治阴丽华的腿伤之外,此后数年踪迹不寻。再见时山河已固,庄子陵便顺应本性成全了自己江山钓客的梦想,这梦想看似与七贤别无二致,实际却大相径庭。首先,庄子陵坚持的超然物外,只避俗,不避世。他可以借阴丽华之名在暗处为刘秀的理人治国出谋划策,及至刘秀登门求才,阴丽华从旁苦劝,亦不改初心严厉拒之,也可以收起君臣之礼,从容坦荡赴同窗之约,只谈过往,不论国事,推杯换盏酣睡至天明。这些在后世人看来自相矛盾的言行举止,不过是“发乎其心”罢了,看似极端,实则中正,哪有半点魏晋时期虚无玄远的清高之相?其次,庄子陵与刘秀素来交好,得其赏识,选择淡名薄利大隐于市不过是出于一种难能可贵的自知之明。阴丽华时隔六年再次见到庄子陵时,他曾目不斜视地说,“朝中既有梁侯,又何必非要强求庄某?”此后刘秀请他进宫一叙同窗情谊,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既得阴丽华,何需庄子陵?”不难看出,庄子陵并非不了解朝堂,恰恰是他太了解了,因而他对朝堂众臣的赏罚任用提不出更好的谏言,既然君臣和谐,自己何必锦上添花?第三,七贤隐逸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忠君之志的影响,庄子陵显然没有类似的思想包袱。刘秀待他宽厚有加,在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英雄的动荡时代,以雄才傲骨闻名天下的庄子陵却根本不屑于借刘秀之势封王拜相,他一度改头换姓隐居于富春便是为了避开刘秀的明察暗访,避开纷繁杂乱的凡尘纠葛。“山不就我,我来就山”,刘秀依然以同窗的身份请他进京,尽管求贤无果,他也未曾动过半点“得之我幸,不得除之”的念头。或许在老同学刘秀的眼底,庄子陵最大的缺点也正是他最大的优点。
在数以万计的穿越小说中,少有角色会因为不贵胄、不江湖、不绝世、不救世而被我们记住,庄子陵便是其一,这个角色的个人魅力既来自于历史,更源于作者的再丰富和改造。基于充分的历史考据,作者笔下庄子陵的形象几乎就是从史册上拓印下来的,这种严谨得近乎苛刻的历史考证态度,在众多以历史穿越为噱头的网络小说中实属不易。不管是《后汉书》记载的“狂奴故态”,抑或“士有故志,何至相迫”,作者都一一进行了对合情合理的演绎,而小说另外添饰的更加丰满的情节也足够支撑起庄子陵的恃才傲物,比如庄子陵留京期间,他的旧友大司徒侯霸派人登门拜访,庄子陵箕踞抱膝,极尽无赖傲慢,又含沙射影地嬉笑怒骂侯霸的痴病,一句“如今我人主尚不见,又岂会去见他这个人臣”堵得来使无言以对,让庄子陵这位历史上就不拘形骸的名士在小说里也得到读者们的青睐。
时逾千年,江山几经反复,当年无双国士的画像早就斑驳不堪,辨不出姓甚名谁,唯独名士傲骨依稀有迹可循,在作者有如神助的笔端,见风化尘的冢中骨竟神迹一般重又生出新鲜血肉,于富春山涧高歌一曲“吾本江山一钓客”的名士传奇。
三
政治一个名利场,在一般人眼中,这世间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贤德,什么体恤民情,不过是逢场作戏的假仁义,昭烈帝所言“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在他们眼中也只得一个伪君子的定论。也许历史对我们而言真的太遥远,所谓故人风骨,无一例外全被碾碎做了历史壁画上的落尘。正如天衣有风在《凤囚凰》描绘的美色环伺的景象一样,靡丽得过火几乎让人忘记了刘宋开国初期的青松马革,心底仅存的一丝斗志也因建立在仇恨之上而难以自拔。倘若尽雪前耻,对一个新生的政权而言,谁能堪当大任去持斧劈山建立新秩序?东汉名仕冯公孙用他的切身经历给出了答案,天助自助者,凡修德行,守信义,禮下士者,何愁民心不向,何处不是洛阳?
《秀丽江山》中有精通文韬武略的谋臣良将无数,其中既担得起君子美称,又不失贤德的名士唯有冯公孙一人。冯公孙本是新朝的父城郡掾,文武兼备,学识出众,因出巡属县遇伏,被刘秀的汉军俘虏,得刘秀相护方能保全性命,虽然他有心归于刘秀麾下,但由于牵挂父城亲人,遂与刘秀定下君子协定,征战昆阳的路上由冯公孙护阴丽华一路无恙,刘秀则答应放他归家,此后因缘际会,幸为一世君臣,结刎颈之交,同襟共苦,闯荡江山。作为颍川归顺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刘秀缔造东汉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论领兵打仗,他或许比不上河北归顺派的耿弇,但若论贤德,云台二十八将则无人能出其右。刘秀北上招抚遇挫,逢王郎叛变,并派兵追杀刘秀等人,刘秀率众连夜逃路,行至饶阳芜蒌亭时,因饥寒交迫滞留修整,冯公孙先是杀马,后煮豆粥,从容自若一丝不乱,与狼狈到无暇自顾的其他部下形成鲜明的对比。待众人逃到南宫滹沱河,遇大风雨,还是冯公孙,未雨绸缪,“将私藏的一点麦饼用水泡开,加了些不知名的野草,烧了一大锅麦饭”。如果说刘秀是军队的实际领袖,那冯公孙便是君臣上下的精神支柱。
冯公孙在小说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多,几乎都做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他是良师益友贤臣良官。为人友,刘秀慧眼识人,正是看中他端方君子这一点,才将阴丽华的安危托付于他,公孙果不负所托,竭尽全力护持阴丽华的安全,面对耿弇的无心之过,公孙亦不容有失地说出了“你伤了她,自然就要付出代价!”同样,阴丽华几番向公孙询问他对刘秀的评价,也是因为她心里把公孙视为值得自己信赖的朋友,是刘秀可以同悲共笑的知音。为人师,公孙是阴丽华的“情感顾问”。不管是在出使河北问题上阴丽华因刘秀安排她回新野的决定而产生了信任危机,还是河北脱困之后,阴丽华受制于现代思想一再拒绝劝说刘秀娶真定王外甥女郭氏,把握住阴丽华致命弱点的公孙都是一个有理有据的调停者。为人官,公孙“在关中治理有方,威名卓越,深得人心,外加百姓封冕的‘咸阳王”。为人臣,公孙是“捍卫刘秀利益的坚强后盾”,他在铸造东汉帝国中“功劳显赫,而在论述战功时却总是退避三舍,默默独守树下,不卑不亢,最终荡了一个‘大树将军的戏称”。后驻守关中,遭关中三辅上奏弹劾,称征西大将军冯异拥兵自重,刘秀将奏折交给冯异,“为表忠心,冯异的妻儿作为人质被他先行遣送至京都安顿”。贤德如冯公孙,他江山帷幄的这一生从来以理服人,好比无故不可离身的温润佩玉,总会让人产生浓浓的依赖,仿佛天下无不可退之险,无不可护之人。
时下的作者们甚少有驾驭得了圣贤风度的好腕力,于是读者也似乎忘了,这江山不仅有淡看权势的富春山林天下客,也有志存高远的庙堂贤士阳夏侯,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冯公孙的贤才负得起东汉江山的千钧之重。人说江山日异,历史遥不可及,古人之贤不过明日黄花,读过便弃了。我以为不然,过去虽远,但还未到不可追忆的地步,时间会证明以修身齐家为目标的贤孝精神不是华夏的鸡肋,相反,他会在漏中沙的洗练下历久弥新。江山壮阔,代有人出,毋需夸大其词,若贤仕在世,那必是冯公孙的模样。
四
作为煌煌银汉的中兴之主和定鼎之君,光武帝在东汉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都非比寻常,他完全配得上王夫之“允冠百王”的评价。而作为《秀丽江山》的男主角,刘秀亦是一位堪称完美的兄弟、丈夫、将王和人主,书里书外的温和、幽默、隐忍、多谋、坚韧、仁义、痴情,任意摘取一二,便是穿越小说男性角色的“人设标配”。我们有感于秀丽夫妻亘古传颂的爱情,但在爱情之外,刘秀从搏命百战到偃武修文的心态变化,在封建专制的时代背景下更令人心折。
《秀丽江山》的其他角色设定或许会有争议,唯独刘秀的形象完美得让人无法反驳,但同时,正是因为刘秀温柔仁厚的性情奠定了举国上下温和低调的气质,因此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远不及高祖,麾下本可名声大噪的云台二十八将亦比不上有文学影视作品提升知名度的三国将臣。凡开国帝王,难免会在南征北战中沾染一身戾气,而刘秀则是一个容易让人忽视的例外。身为一个在民间成长起来的帝王,朝代的更替暴露在他面前的是巍巍江山也埋葬不了的血与泪。在硝烟战事中,没人能置身事外,他在马背上的那几年见证了太多的死亡,二姐刘元和三个孩子,大哥刘伯升,这些都是他血脉相连的亲人,是战争带来的血淋淋的教训。他哭过痛过,更多的是无可奈何地忍辱负重,彼时以他偏将军的身份拒绝不了战争,只能提柄长剑以战止战。待戎马闯出了朝堂,创业时骑牛持剑上阵的蔡阳农夫刘秀,践祚后便收刀入鞘,柔道治国,“他对连年的战事感到了厌倦,决定将隗嚣、公孙述这两个大麻烦先搁置一旁,置之度外,下诏勒令所有还朝的将军留在雒阳休养,把军队调防河内,打算暂时休兵”,还太平于天下。不妨作一个假设,凭刘秀的才谋,若有私心,在位期间借抗击匈奴成就千古霸业并非难事,但必然以百姓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为代价。作为深知民生多艰的明公仁主,刘秀最终选择了刀剑入库,休养生息。仁爱天下者必将得天下。于是,江山归刘,民心归汉,善战不好战也成为汉民族最为宝贵的民族根性之一。
相信每一部穿越小说都代表了创作者某一方面的思考,或是爱情,或是亲情友情,再深刻一点,可能还有现代人对历史的思考,但能写到《秀丽江山》这个深度和高度的作品着实不多。很多作者喜欢写小情小爱的萧墙,写勾心斗角的宫闱,反而把人主江山兴亡一肩担的偌大责任视若无物。其实,平安治世时的谈情说爱固然美好,生灵涂炭时堂上君臣整治江山的担当更值得关注。那么,久经沙场百炼成钢的刘秀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是珍惜和平吗?可能是有的。小说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去描写战乱,从汉军起义到昆阳大战,一直写到刘秀从隗嚣、公孙述手中收回汉家江山,若站在读者的角度去看确实是酣畅淋漓,但那故事里也有我们的位置,是你我在乱世走了一遭,对来犯之敌致以迎头痛击,是我们擎着猎猎旌旗,守望红日荣升江山再起。很庆幸这片一度痴迷于忘我厮杀的大好江山被刘秀照拂得很好,他放下屠刀虽未成仙成佛,但当身边有过客絮絮说起那段腥风血雨的青葱岁月时,他也可以眼角酸涩地回一句,那个年代太累了,和平真好!
生长于没有战争的现代,让我们可以心满意足地凝望他的来时路,凝想他未来仍会绵延不息的长久光荣,他以史为鉴的态度让我们明白,不必等浓郁血色熏染得或生气或死寂的眼瞳去告诉他和平二字的分量,跌跌撞撞走过“小三国”的他,血脉中已然揉进了一道不死不灭的传世温柔。
读者总是能在书店的醒目区域找到这样一些畅销书,封面惹眼,书腰直言不讳地标明网络点击量,在作者名前加诸一连串或官方或民间为其量身打造的“镀金王冠”,对作品的评价也毫不吝啬地奉上诸多溢美之词。客观说,这些畅销书的问世是颇不为传统文学所待见的。粗粗翻过几页,不是语言青涩不加修饰,就是人物苍白千篇一律,因此,这群叼着金汤匙出生的文学圈新人总是显得那么不合传统的胃口,除了情节差强人意,其他的小说要素基本都不及格。如果放任自流,那么传统文学坚守了百年的江山不得被这些畅销书糟践得一塌糊涂吗?
我虽然不是网络文学的反对派,但十年前曾写过一篇质疑网络文学作者的文章,对网络文学的发展保持一种既谨慎又开放的态度。时至今日,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网络文学已经撑起了书店畅销区的半壁江山,在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近二十年的竞争对抗中,网络文学丝毫不落下风,网络文学已长成文学家族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江山虽大,寸土不成歌。互联网的影响如此之大,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抱团式取暖不过是个笑话,不管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和读者如何看待网络文学,是心怀宽容还是心存蔑视,在传统文学如雾中姚女顾影自怜的今天,时代也正携扶着网络文学,自鱼龙混杂的作品中摸索到年轻一代不约而同的民族文化认同——愿承先祖风骨,秃笔续千秋,走墨邀故人,扶立起这千年妩媚如一的迢迢銀汉、秀丽江山。
注释:
①此处“远”“近”以故事发生的时间为界。
①杨建兵:《“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吗?——对网络作家身份的质疑》,《文艺评论》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