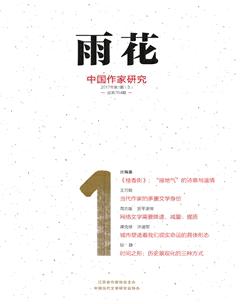当代艺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叶炜(《雨花·中国作家研究》常务副主编):我们以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这个电影为由头来展开这次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当代艺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几天前,我和郝敬波老师在南京参加江苏评论培训班时看了这个电影,很有感触。于是邀请王怀义老师和各位研究生同学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大家都知道,全国第九次作代会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大会上有一个重要讲话,我理解这个讲话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中国文学在重视西方资源的同时,更要立足中国,讲好中国故事。而电影艺术也应该包含其中。像《我不是潘金莲》这种贴近现实的电影,我理解它的实质就是映照中国现实。就冯小刚个人而言,他的这部电影明显在发生转变。他以前所拍摄的《非诚勿扰》等,我认为那种风格也未尝不可,但他对中国的现实没有丝毫的触动。但从《我不是潘金莲》开始,冯小刚对中国的现实有了更好的把握,而且他很巧妙地把中國官场生态给呈现了出来。有些人对这种呈现不满意,说它其实是一种美化,但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其他的导演来表现的话也不一定会比这种方式好到哪里去,因为中国现实是复杂的,有许多限制的因素。因为这是一个上访的题材,并不好拍。我认为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创作,正走在一个正确的路子上。它反映了中国的现实,既叫好又叫座,当然他也有一些不足,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谈。
郝敬波(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一种沉重和沉默,感觉不能一下子给这个作品做一个明晰的判断。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对该作品的解读有很多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促使了我们的讨论。影片显然讲述了一个中国故事,那我们讨论的内容就可以以“当代艺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为重点,大家可以从电影的角度,也可以从其他艺术形式的角度来谈,相互碰撞交流。
一、《我不是潘金莲》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强露(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我的感觉它涉及的方面非常多,一方面是从李雪莲的角度,从普通妇女的角度去写她去上访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从这个过程中去观察官场中的一些状况。但是到最后能给我的思考是一个普通的妇女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二十多年的青春,为了咽不下一口气,为了证明她的离婚是假的、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和别人过不去,也和自己过不去。到最后快要自己和解的时候,又因为别人不信任她说的今年不会去上访,最后又去了。她这样的人生过得太累,我觉得更重要的无论是谁,都要跟自己和解,不要再去瞎折腾。
王怀义(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们要明白李雪莲的丈夫给她戴上潘金莲这个帽子的严重性,如果李雪莲一直戴着这个帽子,在她那个乡村社会恐怕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一辈子要在别人的眼光下生活,而且她还会成为别人谈论的、消遣的对象,这是她想要一个说法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不仅仅是一个离婚的真假问题,最终还会变成一个道德问题。
强露:但是她做不到,这个社会不允许她去做到。
叶炜: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可以变通的,但是也有许多人比如农村妇女,她们的知识层次比较低,许多人活着的理由,是对任何事都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公道的解释。这种人是非常纯真的人,有时候,她们会为了这个合理、公道的解释付出生命而在所不惜。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和《我不是潘金莲》中的雪莲,都是这样,都是性格比较轴的人,在生活中是确实存在的。
郝敬波: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影片用一个幽默的形式来讲述一个当下故事,以一种荒诞的方式讲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精神的世界和中国社会生态的问题。影片有一个叙述人,讲述一个村姑上访的故事,上访的原因就是他丈夫污蔑她是潘金莲。从小说叙述的方式来讲,它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呈现。冯小刚想采取一种冷静理性的方式,提醒观众是在观看这样的场景,提醒大家是在观照这个社会。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本身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能够带来个我们思考的东西。
包素娟(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按照强露同学的见解,如果她跟自己和解的话,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按照我们通俗的说法来说,人活一口气。这个涉及到一个道德和名誉的问题,而且她在上访的过程当中会不断地受到轻视,所以不可能和自己妥协,也不可能和社会妥协。但是在影片的最后她妥协了,她很轻易地跟前任县长谈笑过往,她说到自己事情的时候,就像说其他人的事情,别人笑,她也笑了。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悲哀,她已经忘记了别人说她是潘金莲的冤屈,枉死的孩子的委屈。本来告状是一个的手段,但最后却变成一个目的,为了告状而告状,多么荒诞!后来我自己也有思考这些,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有个旁白,“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不要当真。”故事开端给大家一个很明显的距离,我们观众和导演和故事里的人物是保持距离的,大家在看一场戏。开始是以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去看待,但是看到最后我笑不出来。另外,虽然我们不需要去在意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但是我认为是真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新闻报道某夫妻因想再买套房去离婚,或者因多要一个孩子去离婚,因此这个故事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当代艺术它表现的内容和现实是相接近的,或者是从现实的土壤中汲取养分当作它的表现的内容,在内容上注入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或人道主义精神的关怀。我说人道主义的关怀,是因为我看到最后是非常的同情李雪莲的,很怜悯她。最后,我们能注意到这个镜头有一个方形的,有一个是圆形的,我们可以发现它采用圆形的时候是她在小镇上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是圆的,为什么说是圆的,因为农村小镇是一个人情社会。但是为什么到了北京,就变成了方形的呢?因为北京是有规矩的,是我国的首都,它代表的是一种官场上的规矩,天圆地方。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认为李雪莲的规矩才是真正的方形,而官场的规矩才是圆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讽刺的一点。而且从圆形画幅、扇形画幅、到方形画幅再到旁白等,整个像是听一出戏,可以看出冯小刚导演借鉴了古代的某些艺术表现形式。想要讲好一个故事,我觉得传统东西是不能丢的。也许我们过分强调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反而忘记了传统的表现形式也值得借鉴和欣赏。
二、电影如何讲述“中国式上访”?
叶炜:我们的第一个问题讨论了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接下来我们重点探讨一下电影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的?然后进一步探讨当代艺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张世维(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本科生):
打官司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我们要考虑这个出发点。雪莲觉得他的离婚是假离婚,但是,实际上是真离婚,法律上是真的。但她后来也知道了这个事情,在法律上已经是离婚。但是在结尾的时候,冯小刚为了给她打官司的出发点一个更合理的解释,说她后来已经怀了孩子,后来是出于这个孩子去打官司,这样一个逻辑设计或许是为了找一个更合理的出发点,但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唐突的。
王怀义:我注意到在小说原著里并没有提分房子这个事,这是电影里加的。在原著中,直接讲生孩子的事,生二胎的事,为了生二胎才会有后来的事情,而且孩子是生下来了的。所以原作当时针对的对象是计划生育这个问题。但是在影片中变成了分房子的问题。这样的置换让影片的含义发生了改变。这一点是要注意的。
张世维:我觉得从电影来看的话打官司的出发点有问题的。在结尾的时候,雪莲开了一个店,我觉得这个结尾比较突兀,而且屏幕也从圆形变成了正常的视角。觉得突兀的结尾不符合常理,这是第一点。另外是视角问题,导演是想做成一个团扇的形式,我觉得以我的观点来看,可能更像一个圆形的偷窥视角。他到北京的时候是方形的,然后在小镇上是圆形的,我觉得冯小刚是想把它弄成一个方圆的变幻来表示这其实是一个没有规矩的荒唐事情。
王怀义:这其实是电影的艺术手法问题。要注意电影拍摄的场景是在江西婺源,在我们的印象中这里一直是带有诗意的。然后镜头是圆的,模仿的是宋元时期花鸟山水画的扇面造型。在我们的印象中,上访的人是有苦难的、充满怨气的,但李雪莲是生活在诗意中的。这种表现方式就把尖锐的冲突给削减掉了。在官方事件出现的时候,画面就变成了正方形;而李雪莲在北京生活开始正常生活的时候,画面就变成一个长方形。有人讲这表现的是中国古代的天圆地方观念,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导演使用这种方式把官与民的矛盾冲突给弱化了。有一个细节导演设计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市长和县长在桥上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站了一个年轻女子,她穿着一件非常时尚的大衣,怀里抱着一只小狗。从她的装扮看,她是不从事具体的工作的,而且与市长的年龄差距很大。这个形象说明了什么?值得我们思考。
郝敬波:王教授把电影的画面以意识形态的理论来理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画面的处理理解为冯小刚实施的一种市场推广方式。这就延伸出我们所关注的重点,那就是怎样关注现实,怎样表达现实?从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事情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李雪莲不太可能真的能见到院长、县长、市长,更难见到中央首长。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荒诞的表达,用寓言的方式去讲述一个故事。当然,影片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在这一点上,和贾樟柯的《天注定》很不相同。
王懷义:我认为这两种表达方式都不是很合适,因为这种扇面的山水画的方式拉远了影片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而贾樟柯的方式把偶然事件普遍化,太过真实,唤起的情感也是不能让人平静的,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这两种方式都不太合适。前一种方式是隔离,让人感觉影片与生活太远;后一种方式拉近,让观者融入到事件中去。这两种方式对观众来说都是不合适的,没有达到一种不即不离的表达效果。
叶炜:我们讨论的这部电影,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或许不大,但它是艺术真实。尽管《我不是潘金莲》这个电影起点就是荒诞的,但却呈现出了一种艺术真实。冯小刚从原来的搞笑的风格走向一种直面当代严肃现实的方式,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它是用一种夸张的形式、荒诞的形式来讲述一种“中国式上访”的。而且故事的主线是虽然是农妇上访,其实主要呈现的却是官场生态和社会生态。我理解的冯小刚的意思就是这样。电影所采用的叙事手法,可以让人感受到有一种审美的张力。冯小刚这个人很聪明,他从小在北京跟着一些大院子弟一起玩。冯小刚一方面想要获得一些普通大众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想为平头百姓说点话。但是他还有一种保护自己的下意识。他不会尖锐得像其他的导演一样去赤裸裸呈现现实,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个人很聪明。不但在电影界,在文学界这样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张世维:这让我想到了一些人所评论的,关于江湖和庙堂这个问题。说冯小刚既想做江湖的盟主,又想做庙堂的跟班。这让我想起了另一部电影中的“老炮”,他本来是一个江湖人,他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通过庙堂的方式来解决。
叶炜:是的,冯小刚就是这样一个游离于庙堂和江湖之间的导演。这部电影换做其他任何导演,即便能拍出来也很难通过审查。国家的媒体不会给你做宣传,只有冯小刚这样的一个人物,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说我觉得冯小刚他做的还是不错,其他人不可能做得到、做到像现在这么好。
钱思衡(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本科生):其实电影中所展现的上访这件事情,从法律上来看本来就没有什么冤屈,包括后来法官也说了,如果当初判错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了,就是因为给她的判决是对的,所以才不停上访。包括各级政府其实对她也没有什么太不人道、太不负责的地方,顶多是有些回避、无作为。其实该处理的也处理了,只是处理问题的方法有些问题。
郝敬波:李雪莲没有什么冤屈,只是她不是潘金莲而被叫成潘金莲了。回到叶炜刚才的话题,可贵的是冯小刚关注了现实,而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影片是想反映中国当代现实的,它展开的姿态就是要讲好一个中国故事。再进一步看,冯小刚在这个电影中重点拿捏的东西就是如何表达的问题。我觉得这种表达不是侧重全景的呈现,而是一种抽象的方式。我注意到,影片中几乎没有围观的群众,没有“周围人”,就是没有鲁迅所说的那种“看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抽离的表达方式。
王怀义: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没有看客,没有看与被看的关系。
郝敬波:冯小刚没有采取那种血淋淋撕开的表现方式,这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表达方式呢?值得我们去思考。
叶炜:这个故事实际上是非常紧张,但它发生在一个风景优美的环境里,就把这种紧张关系给稀释了。
卢晶晶(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我是先看了电影再看了小说,所以会不自觉地将电影与小说进行比较,我发现,电影有很多地方是比较尊重原著的。比如说官和民的矛盾没有这么尖锐,小说里面的情节设置也是比较舒缓的,没有大型的冲突和激烈的言辞。其次就是语言,小说里的语言也很幽默诙谐,让人看到非常想笑的状态,只是在电影里这些语言更为集中了,所以带有更为强烈的喜剧质素。因而我觉得,电影效果并不是导演一个人的功劳,他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构建。
王怀义:是的,包括方言的使用也把这种紧张感给消解掉了,使人们在看的时候感受不到这是一件严肃的上访事件。
郝敬波:刘震云的创作,包括《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是非常关注“语言”的,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探讨。
王怀义:其实拿电影来说,不需要完全和小说原著比,就算和小说原著是一致的,但是电影实际上已经另外一种产物了,视角的选择、场景的选择和拍摄镜头的选择都已经使事件发生了变化。现当代艺术和美学在研究“观看的方式”,怎么观看是体现了独特的内涵的。罗兰·巴特分析过一张照片:一个黑人儿童,穿着一身法国军装,在看到法国的国旗时表情很肃穆,很虔诚。这是一个偶然性的场景,但是一旦把这个场景拍摄下来,刊登在杂志上,它呈现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这时它表示的是一个殖民地的小孩对宗主国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尊敬的含义。本来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场景,但摄影师拍摄之后,意义马上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看电影要一定要注意艺术形象的呈现形式、角度;场景是一样的,情节是一样的,人物是一样的,所有的都一样的,但你要看它的角度,拍摄的角度,拍摄的角度就是观看的方式。
郝敬波:我们的艺术家对社会的关注其实还不够。比如乡土小说,对乡村的关注如何?当下乡村的变化有多少作品能够有效地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讲好中国故事首先从对现实深度观照入手。
王怀义:文学作品是落后的,比如说《白日焰火》之类电影,他们就比现在有些文学作品思考得深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能把各方面问题思考清楚。我们现在说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去好好讲述现在中国的现状,而不仅仅是讲好的中国故事。
叶炜:在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现实?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真实的经历或者家乡的现状都可以。《我不是潘金莲》就是冯小刚表现出的中国现状中的一种,他在电影里面展现了一种中国官场生态。在这个故事里,确实没有旁观者,因为他不好表现,旁观者一定是愤怒的。另外还有看客,即使是这些愤怒的人,他也是缺乏行动力的。现实生活还是缺少这样能够行动起来的人。
郝敬波:影片中,李雪莲乘车去北京的情节中有一个邻座的“旁观者”,训斥了警察的无情,但也只是一个促进情节发展场景,其他情节中的“旁观者”很少出现。
张世维:我从先锋文学来谈。现在的先锋文学类似于家族敘事,像莫言、格非等,他们写的都是自己一个家族的故事。现当代文学里面,我比较喜欢的书,莫言的《丰乳肥臀》。他讲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故事,接近史诗。当这个家族叙事变成一种主流的时候,中国故事可能就围绕着以往的边缘叙事来展开了。
钱思衡:我感觉现在家族史诗,好像更能贴合中国现实。我觉得中国发展到现在,我们的问题广泛存在于城市、农村。在农村题材作品中,也并不能仅仅是像以前一样,表现那种家庭和家族为主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们有很多矛盾,但艺术创作还是停留在个人层面,写小事。
包素娟:我家就是农村,现在家家都有无线网,出门就有水泥路,仰头就是蓝天,看见的鸽子麻雀等等都不稀奇,还有电脑、手机等等。但是你看现在当代作家的作品里,能够真正反映这些发展的没有几部,他们一般都是关照到苦难或者宏大叙事,把这个作品表现得更加深入,意义更加深长,但是对于社会现实,对于农村现实发展的现状,我觉得力度是不够的,而且也不是特别及时。当然经济落后的农村也有很多,我觉得可以一分为二。为了让作品更加有意义,就不关注那些新鲜发展的事物,这样有点以偏概全。另外就是心理道德层面,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对于麻烦的事儿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我同情你,不过我也不会为你做出任何的努力,我顶多帮你发一条帖子,那已经是了不得了,但是你要说去采取一些实际行动,那是极少数的。我觉得,中国故事应该涉及对于现代人的心理道德研究。
卢晶晶:我想起外国人来中国拍纪录片的案例,有些中国政府官员,会带着他们到一些提前准备好的地方,比如说放上鲜花啊,打扫干净卫生啊,让百姓注意言行举止啊,完全是一种摆拍风格;但是有些外国人则喜欢在别人安排之外,直接进入到了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去拍摄一些原生态的画面。这两种记录片,我们更喜欢哪一种呢?肯定是后者。所以我觉得讲中国故事,不管是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一定要体现它的真实性,我觉得真实的,才能够表现这个问题的本质。讲故事的方式可以不成熟,可以采用虚幻的甚至荒诞的手法,但是一定要能体现现实生活的意义。有的故事讲得很好,但并不是真实的情感,而是为了唱赞歌,为了表现而表现。
王怀义:你讲的这个情况就是要重视文学创作的多样化,不能仅是单一的表现,这不符合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要求。从文学的功能来看,文学其实不承担褒奖的任务。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文学家和诗人所进行的工作不应是褒奖,这个工作需要政治家或某些政客来完成。就像柏拉图所比喻的一样,诗人和文学家是一个“牛虻”,它让你感受到疼痛,文学的作用也是这样。文学让你产生痛感,然后让你反思。如果你看到作品以后毫无感觉,文学的作用就实现不了。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娱乐的、荒诞的或者是悲剧性的,等等,但是严肃的文学作品都会让人产生一种痛感。痛感并不是揭露,更不是暴露。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的文学还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一部作品,你看过以后,哈哈哈,这类作品并不是文学,也不是艺术。迎合不是文学应该做的。文学应该让我们有痛感、有反思,还要有提升,要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讲这样一些故事还是要有反思性的东西。
郝敬波:中国故事,有两个词,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故事,故事要有中国的现实性,要能反映中国的现实问题,也要能反映人类一些共性的东西。
王怀义:这个提法其实是指“讲好中国现实”。故事一般是虚构性的,我们说的“中国故事”就是“中国现实”,文学和艺术要根据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提出有价值的观点。
张世维:我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比如莫言讲的那个时代的故事对现代又有什么意义?比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对现在有什么意义呢?
叶炜:我们形容中国的词语有好多,其中最常用的是古老中国。我们现在经常说城市中国,其实我们离城市中国还很远。中国的乡土性,尤其是农民的精神面貌没有根本上的改善。所以苏童讲述的《我的帝王生涯》对现在依然有价值,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人们没有什么根本改变,这也是我们立足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国家富了,人民富了,可是精神还没有富,几千年的发展,骨子里的东西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郝敬波:刚才的问题说得很深入。这让我想起新历史主义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新历史”的书写,表现民族面貌和民族性格。比如《白鹿原》通过对家族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书写,反映了我们民族的心理、性格和精神特性,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某种烙印。这当然也是好的中国故事。叶炜老师刚才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艺术表达方式不同,但骨子里在写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民族性格,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这当然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叶炜:如果联系电影的话,我们可以讨论这部电影的优势和缺点。优势是它呈现中国的现实,上访这个问题,起点是荒诞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荒诞的事呢,没有做进一步的反思。它一反思就指向制度层面了。这是不能深入的。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数,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强露:刚刚说至中国农民的劣根性,我们现在没有根本改变,未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变,我觉得这个劣根性恰恰就是中国民族的一个特点,是几千年来发展下来的一个特点,它要改变是非常难的,还有刚刚也说到冯小刚的电影,并没有说到制度方面的,在当下的中国他做不到。
王怀义:你刚刚说的有问题。国民性、劣根性,等等,最好不要用这样的词来修饰农民。你用这样的词,本身就预设了一个立场,认为农民是有劣根性的,需要批判、教育、改正。那知识分子就没有劣根性吗?每个人都有劣根性,人本身就有劣根性。电影《驴得水》里就说“我看,真正需要改造的,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吧!”不是农民需要改造,农民在我们的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创造了这么多文化,劣根性这个词并不合适。
强露:我刚刚用劣根性这个词或许不妥,我想说它的这个特点就带有中国的民族性。
王怀义:对,就是这样,比如说人都要吃饭,你不能说吃饭是劣根性;比如说他喜欢通俗的东西,你不能说通俗的东西就叫劣根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实农民地位是最低的,最无力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上有文化资本,政治家有政治资本,商人有金钱资本,农民没有资本,所以人性的弱点最容易在农民身上体现出来。
强露:我并没有任何歧视农民的意思,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觉得中国就是一个以农民居多的国家,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民族的。
王怀义:我们有一个农业的传统,我们的文化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现在处在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只能讲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精神面貌、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等,发生了变化。现在已经不能居高临下地对农民或者其他阶层采用这种方法去看。如果你要这样去看,你就看不到真实的一面,因为你预先设定了一个价值观。
叶炜:刚刚说到中国国民性问题,劣根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刚刚说农民有,其实知识分子更可恶,为什么呢?农民有时候认识不到问题,所以谈不上改变,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知道问题所在,他也不去改变,这让我想到了近期的另一部电影《驴得水》。这部电影的意义,它批判的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明知道是错的,还在做。我们中国当下的现实其实是很荒诞的,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讲好中国这些荒诞的故事。这个社会的现状就是,农民是不知道自己面对什么困境,而知识分子是知道自己面临什么样的环境的,但他就是不能改变,或者不屑于改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王怀义:所以按照西方知识分子的概念,中国不存在真正的知识分子。
三、当代艺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叶炜:最后我们再探讨一下当代艺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结合冯小刚这个电影,整个情节算是比较好的反映了现实的一个侧面。在目前的现实下,这已经是比较好的去反映现实,而不是一味的迎合或者是批判,有它积极的一面。
郝敬波:对,比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写了“桃花源”,实际上构成了对现实的一种紧张关系,
王怀义:其实这个“江南三部曲”可以讨论一下。看桃花源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最后会变成一个娱乐场所。
郝敬波:不同的作家往往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我曾经问过叶炜,你为什么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写到鬼啊、神啊这些神神秘秘的东西比较多,他给我一个解释,我印象比较深刻。他说现在中国的乡村太荒诞了,荒诞中的变化太复杂了,我用其他的方式不足以表达这种荒诞,那我必须用这种神秘的、魔幻的东西来表达这种荒诞性。我一下子就突然理解了,他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荒诞。一个作家选择用他认为好的方式去表达这种东西。所以说什么是好的表达方式,我认为是根据不同作家的不同选择去表达,不同作家去表达他心里理想的种种故事。电影也是一样。每个导演都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去表达世界。关键是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是否有效表现了作品的主题话语。
叶炜:我今天上课也在谈网络小说,网络小说你看着它离现实比较远,其实它也在呈现现实。
王怀义:網络小说不能作文学解读,只能作文化解读。为什么它有这么多人看?这就是现实。
叶炜:网络小说它现在发展得很厉害。它已经发展到我们不得不直面的地步,全国有两千多万写手在写网络小说,读者数量更是庞大。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它,但是网络文学可能很快就要改变我们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观念。我们现在看网络小说这么漫不经心,好像离现实比较远,其实它也在讲述新历史主义。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当代的艺术都考察一遍的话,它们再荒诞、再夸张、再怎么变形,内里还都是有一种表现现实的欲望。所以艺术表现现实不会因为形式而改变。但是如果有些作品太贴近现实的话,也往往有可能适得其反。
郝敬波:我们最后要强调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当然需要不断的创新,正所谓文学是一种自反的建构。我们有理由对当代艺术讲好中国故事充满信心。
叶炜: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