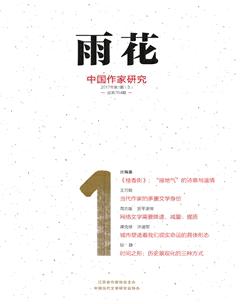作家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的链接
杨晨燕
《富矿》中“轮回”一词非常频繁,既是隐含在文本之中的时间轴概念,又反映了作者向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向往与回归。而《后土》的目录无疑是个亮点:以惊蛰为序曲,以惊蛰作尾声,以二十四节气的变更来串联全文,按照二十四节气的时序推进,惊蛰、夏至、大暑、立秋、白露等节气更迭对应叙事时空的节奏变化,使得麻庄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都随季节和气温的滑移成为真实可感的故事,既超越了传统乡土叙事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又充满着乡土文化气息与中华大地特有的传统文化韵味。《福地》则采用了天干地支作为全书的结构框架,自辛亥卷始,自丙子卷终。充满圆融性与规律性,显示了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即时(时间)空(方位)互动,和“阴”与“阳”的作用结果。因为中国历法本身也包含了阴阳五行的思想和自然回圈运化的规律。叶炜试图将天干地支与乡土日常生活、农民劳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示给读者,书中的超现实的魂灵现象与上帝视角也与生死轮回的天命观相呼应。可见作者是有意在书中彰显“轮回”的生命意识、文化意识和哲学史观。
一、“轮回”的哲学史观与生态理想
叶炜说过:“从《富矿》到《后土》,我在努力试图与生活达成一种‘和解。”现实有时残酷到如果你想继续生存下去,只能选择与现实和解。而在三部曲中,“轮回”与“和解”是不可分割,紧密连结,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原本分离的两端,“和解”促使其成为一个圈型的轮回链。因为不断的轮回,才能回到最初的平静,才算是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乡土中国在长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当强大的自满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与自我修复功能的文化体制,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生活,它们看似弱小,但实际上却相当顽强,从而使中国的乡土生活始终呈现二元并峙的、交融与妥协的局面。“福地”的名称一方面来源于土地的广阔古老,另一方面也包含其“无所不包、泥沙俱下甚至藏污纳垢”“孕育了一切又滋养了一切”的能力,苏北鲁南这片“福地”生命力旺盛且顽强,它和解一切内在的或外来的好与坏,咀嚼转化成所需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造福子孙后代。
“农村,尤其是中国农村,与苦难杂糅在一起的往往还有一种生活和快乐。”①和莫言、赵本夫一样,叶炜打心眼里也不希望自己的故土彻底被苦难与灾祸所笼罩,深爱着故土的作家们往往在本体心理的层面上期待着故土回归生机与活力,所以《富矿》《后土》《福地》三部作品的情感脉络越发柔和平祥。“乡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富矿》主要展现现代化建设中的煤矿工程改变整个麻庄的过程,反映了乡村以“土地”为核心的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劳动人民的困境和挣扎;第二部《后土》中农民们从刚开始的虔诚信仰土地爷,到后期认其为封建迷信,与富矿中过度开发土地的厄运之灵——黑雪有相同的主旨;《福地》中除了时代变迁和历史战争的描写,也通过底层平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保家卫国的誓死决心成功展现了乡村建设的成就——新时期下新乡土世界的新一轮改造。叶炜想传达给我们的是他的土地观——人类并非自然的征服者,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是叶炜所希冀的理想状态。
但叶炜的“轮回观”又是不纯粹的。不似《古里——鼓里》所描述的那个地方“周遭总象有一道屏障,人走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转回来,鸟飞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转来,连太阳和月亮也如出一辙。周而复始,一切终在循环往复,也没有新的东西进来……”②叶炜的新乡土世界与外面的世界是接轨的,是有渠道沟通的,经过村庄内部的自发努力和村庄外部的提携改造,村里的状况也在逐渐好转。甚至可以说,三部曲的这种在反复轮回中又缓慢发展的状态实际上也真真切切地在现实中上演着,因为这正是新时期下整个中国的发展状态,一个小小的麻庄是整个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真实的一个缩影。
二、寻根探求与信仰坚守
叶炜作为具有代表性的70后作家,曾同所有70后作家一样,被学术界赋予“‘被遮蔽的一代”“文学夹心层”的称号。但近年来,不少优秀的70后作家在漫长的沉寂期后爆发出自己的潜能与独特魅力,他们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又结合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进而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开发,创作新气象令人期待。在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曹霞看来,他们也是中国历史上拥有“乡村故事”的最后一代。
“随着全球化发展、城镇化建设节奏的加快,以及网络科技对世界的扁平化处理,乡土中国正面临‘去根的危机。”这样的危机,对作家叶炜而言,既作为一種具有民族隐忧性质的症结所在,又可以说是一次机遇和挑战。在面对席卷全民族的失根病症和传统文化的精华难以延续的状况之下,往往是那黑屋子里最先醒来的国人更加痛苦。于是叶炜在他的乡土三部曲中不断地寻求“根”所。乡村三部曲中有不少的外来户,翠香、曹东风、如意,他们起初或风光无限,或穷困潦倒,但无论过程如何,叶炜赋予他们大多数人的结局多是好的、安定的,如同随风飘荡的芦苇终是扎根在了麻庄这片土地上。
中国农民的土地情节与寻根文化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世间万物的根生长于土地,“人这辈子,再怎么折腾,再什么辉煌,到最后还是得魂归故里。”对于书中没有根的一些人,作者给予的态度,不明多说:“李是凡这样的人,就是没有根的树,枝叶再繁茂,没了根,总站不稳,也活不长。他的痛苦是没有根的痛苦。”(3)没有根是痛苦的,李是凡、王远都是如此,生前风光无限,枝繁叶茂,死后流离失所,树心溃烂,没有故土的依附和遮盖,亡灵们只有飘荡于浩浩荡荡的这人世间,终是无法安息。《?后土》中从麻庄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刘非平回来当了村官,在田边规划村庄未来时遇到了白手起家的个人奋斗者王东周:“你这不也回来了吗,早晚我们都得回来,这里才是我们的根呢。”③如果说麻庄是小说里所有麻庄人的根,那么叶炜的根便是他笔下的苏北鲁南平原这一片乡土世界。作为一个抱有故土富强的愿望和极具时代责任心的作家,叶炜还强调文学干预现实的功能。《福地》里有大量对抗日战争的或细致或宏大的书写,而且书中人民合力抗击日寇的战争在苏北鲁南是有原型的,譬如老万多次带领全村人击退日军的扫荡,枣庄抱犊崮顶与日寇的殊死搏斗。叶炜以抗战史实为原型,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和创造。可见,文学干预现实这一点叶炜确实在做,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书写令人动容,使这些必须铭记的国耻通过文学作品传达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我想这也是他寻根的目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的“寻根文学”热潮。作家们经历了知青和伤痕小说的创作阶段,几乎都陷入了艺术发展的窘境。蔡翔指出:“寻根文学的产生背后潜藏着一种焦虑,一种急于摆脱困境的努力,他们急于找到一个新的思想和艺术的支点,不仅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格本体。”幸而汪曾祺的小說《受戒》以其独特的民风民俗书写承担起了这个跨时代的任务。后冯骥才的《神鞭》,阿城的《棋王》等更使得“寻根”文学名声大噪。寻根文学的“根”多以文学作品中的气韵、情趣、意境传达,使得附着在传统文化意韵上的审美意识在书中复活。
叶炜无意标榜自己的寻根意识,但他对苏北鲁南当地民风民俗民谣的大量刻画,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细致书写,对中国当代现实问题的真实探求都折射出了他对故土“根”文化的依恋与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当然,挖掘中国乡土世界的“根”,除了先天优秀的文化精粹外,还有严峻的现实问题,留守儿童、孤寡妇女,官员的腐败欺压、农村法律意识薄弱等等。《后土》就注意到了乡村留守妇女的问题,麻庄的一个小学教师高翔竟也与多名小媳妇有染,因为农村大批青壮年外出打工,媳妇在家,长期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就给了高翔这样的人以可乘之机。官员的腐败和权色交易也是叶炜重视揭发的一个点。孟美丽原本是一个阳光美丽的女孩子,为了哥哥的婚姻,向王远争取宅基地,结果被王远利用而被迫失身,失身带给她婚姻的悲剧,使得当初那个人见人爱的孟美丽变成了精神失常的疯子。孟美丽悲剧背后既折射出政治腐败的普适性,当下社会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已被调查出有权色交易的倾向或行为,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乡土社会没有法律意识——王远的行为从法律层面已充分构成强奸罪,但却依旧逍遥法外。
叶炜认为“作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文学的方式寻求真理真相,探求和构筑中国的信仰系统。”这也是他在“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创作中所隐含的主题之一。叶炜从小接受的传统观念就是乡土大地万物有灵,长大后接受的教育又告诉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人类对未知的广阔的世界应充满敬畏之情。但中国又偏偏是一个宗教意识薄弱的国家。这不仅体现在虚无性,即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的无宗教信仰的观念上,更体现在不稳定性和多变性上,即农村地区农民的价值观念的动摇和转变上。具体说来,古朴在《中华民族不信邪信道理》一文中阐述:“所谓信仰归根到底也只不过是一种对道理的崇敬与膜拜。”④“我在麻庄这块土地呆了这么些年,看着麻庄雨顺风调,雪落花开,衰极而盛,盛极而衰,一代代一世世,生生不息,绵延不止。麻庄为何这么兴盛?因为麻庄人敬重土地,善待众生。可是现在麻庄的人越来越失去了对土地的敬畏感,我这次来托梦与你,就是想让你告诉麻庄人,不要亵渎土地……”土地神托梦给刘青松的这段引文非常明显地揭示了人的信仰与土地价值的核心问题。庄上原先敬重土地神的人们在改革开放,建设新农村的号召下渐渐失去了所谓的迷信观念,土地爷不再是上帝般的存在,农民正在失去对土地的敬畏感,甚至皈依了基督教。
如今为数不少的中国乡土文学大多表现为立场飘渺不坚定,重“虚”轻“实”,虚的多在精神体验,乡村文化,实的有关土地、当地风俗、家长里短的真实都是建立在与土地紧密联系的基础上,而作家没有真实可感的体验是无法写出震撼人心的乡土巨作的。“当代作家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和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是他们面对现实生活、叙写现实问题的瓶颈。”⑤一部作品的精、气、神来源于作家的信仰追求与意识形态,当下的一些作家生存状态优越,生长于城市,与乡土现实生活想脱离。他们的写作场域与生活场域完全不一致,对于乡土只是回忆或者道听途说。
除了真实可感的乡村体验与丰厚积累,叶炜的乡村中国三部曲中也有大量涉及“信仰”“灵魂”“上帝”这类偏向于神秘色彩的概念思维。对应到文学作品的写作手法上,其实就是超现实主义。用叶炜自己的话:“新乡土写作”离不开“土”“洋”结合、“虚”“实”相生的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此,从《富矿》《后土》中的“梦境”预言到《福地》里的千年老槐树、蚂蚁、鬼魂等非现实化的视角让小说时不时闪现出一种灵动幻象,来弥补纯现实主义写法的单调,可以说是一次超现实主义写作实验,他追求一种先锋与传统现实之间的写作模式。作为压轴之作的《福地》是叶炜“乡村中国三部曲”中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最为契合的最为成功的作品。地域色彩鲜明,写作技巧也愈加娴熟,从清末捻军写到清末民初、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从大跃进,文革再写到改革开放,跨越九十多年的时代长河与历史风云,以一个麻庄上的小人物的家族秘史折射出整个中国的时代变迁的进程,乡土气息更为浓烈,人物语言更为凝练,作者还运用大量的民谣、农谚,从婚丧习俗到节日节气、民风民俗,信手拈来,博古通今。
总体说来,叶炜的“乡村中国三部曲”文学性思想性兼具,但也并非完美充实。作为乡土文学,其方言语感有待加强,思想性方面,道德与现实批评力度不够成熟,人物及情节设计蕴含中庸之道。由于齐鲁文化是主张中庸的文化,也是善于包容的文化,在给写作者带来丰富精神资源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创作的精神自由。
三、回归古典美学的平和叙事与现实品格
叶炜的新乡土写作与韩少功的冷峻叙述和批判完全不同,更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幽默的气质,接地气的语言和情节。“他们不俯视,也不精英,而是将自己置于与之平行的视角,不仅看到了世事的苦和悲,也洞察到其中蕴含的绽放着的光华。”⑥三部曲的整个基调是平和安静的,即使有件件大事依次出现,也毫无堆砌或焦躁急切之感,缓缓而来的却是激烈与平和共存的矛盾。因为相比城镇,农村的现代化是正在进行时,但它依旧是农村,麻庄是个风水宝地,也依旧保持着农村特有的宁静之感,尤其是冬日或是夜里。与之相对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碰撞也是平静如水下的暗潮涌动,譬如《后土》描写的是苏北鲁南平原上一个小村庄的碎片化日常,大多平淡而琐碎,偶尔爆发出一些大事件,但这如同海里的一次小波浪,终被碎片化的平淡抹去,使得这片乡土安静而寂寥,温和而平静。《福地》中大时代下隐秘的家族秘史也围绕老万家的四个孩子娓娓道来,拥有古典叙事的风格特征。这也是叶炜倡导的一种立足村庄言说中国的“大小说”的阶段性特征。
“乡村中国三部曲”中体现出的人性美丑交织,隐秘而复杂,叶炜以不避丑陋的原始再现式写作展现乡土生活的真实面目,因而现实品格也是评价三部曲的一个总体特征。
叶炜打破传统现实主义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手法,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新时代下的“地主”形象——老万。叶炜在《福地》中通過老万这个人物写出了地主的多面性和丰富性。作为“恶”与“财权”的代表,他不乏卑劣与丑恶的行径:霸占滴翠多年,44岁时又娶了13岁的冬菊。而作为土地的保卫者,他又不惧与山上的土匪周旋,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女,导致了女儿欢喜一生的悲剧;面对日军侵略,国民党撤退,老万一方面号召乡亲们坚壁清野,一方面购买军火装备,团结乡民,保卫麻庄;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庚子年间大旱时,早已被赶下麻庄神坛的老万竟然拿出自己家的保命粮,让麻庄的村民择地打井,抗旱自救……以此看来,《福地》中的老万也许比《白鹿原》里的白嘉轩、《生死疲劳》里的西门闹更接近中国历史上真实的地主,可以说,叶炜对“老万”这一地主形象的塑造刷新了传统,实现了创新。
叶炜坦言在写作《富矿》的时候,就有意把人物的命运推向了一种极致,将美好的人物与人性都毁灭了。《后土》中也是如此,与曹东风结为拜把子兄弟的刘青松,因原本两人共同的敌人王远救下淹水的爱女苗苗,无奈出于道义,立场转变,直接导致两人关系的逐渐疏远。而在王远退休之际,曹东风彻底背叛了刘青松,镇党委书记李强欲将刘青松提携为新一轮的村支书,嫉妒和“一股酸楚”让他反将了兄弟一把,将刘青松“超生”的秘密告知李强。如此看来,人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动物,对待相对的弱者,可以迸发出同情与爱心,但若是曾经的弱者突然变强,人就很有可能因为嫉妒与不平衡感,情感突变。
除此之外,叶炜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又一幅令人心寒的农村原始图景:刘青松未抵制住诱惑,与外来户翠香有染并生下一个儿子;王远利用官位权势贪污公款,表面大公无私,捐款爱老,暗下奸污妇女无数;孟疯子贪恋如意美色,如意的男人王忠厚疯狂砍杀孟疯子;小学教师高翔奸杀班里的女学生花花。
现实品格也包含温情的一面。譬如,在《福地》的农会中陆小虎批斗老万,结果因为王顺子的一句“这些年在麻庄为咱们做了不少好”,使批斗大会变成表扬大会,气氛瞬间由肃穆转向幽默温馨。而之后的多次批斗,也多是巴掌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乡民的善意在这里被扩到最大化,批斗不再表现人心相悖的景象,而是团结互助的一种和谐图景,叶炜这样写,使读者看到丑恶与美丽、冰寒与温暖的相溶相生,杂糅并存的一幅幅图像,并由此生成了乡土世界的原始、真实的精神景观。
四、反思生态自然:来自地心的微弱呼喊⑨
生态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英美的批评浪潮,通过文学文本考察文明与自然的关系。它不仅要解救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大自然,而且还要还人性以自然,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它的终极关怀是重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家园和物质家园,天人合一。《富矿》在揭示土地生态危机的同时向读者展示了麻庄人在失去家园后的剧烈阵痛。麻庄不再是以前宁静的村庄,铁路、矿井以及排满整条街道的各色商铺、餐饮和娱乐场所,让村庄变得陌生和诡异。而小说中描写的“黑雪”传说是整个村庄不祥的征兆,这证明了叶炜在总结当代煤矿小说在关照生态危机的同时,揭示出煤矿工业的过度开发所导致的钱权诱惑以及社会冲突和道德沦丧而引发的新一轮精神生态危机。
《后土》中又有这样一段描写:“从地理位置来看,麻庄所在的苏北鲁南处于中间带,四季分明,气候变化明显。但今年似乎有些怪,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一切都没有规律可循了。”⑦可见小说中也隐喻着“生态批评”的主题。刘青松反对大学生侄子刘非平对麻庄进行的部分现代化改造提案,在他看来,大学生的试验过于急躁,会破坏自然环境下麻庄的发展,不适应古老的麻庄。换言之,刘青松是保守的发展派,不过快也不过慢,又是一种中庸思想,对新时期下中国农村改造的脚步与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意识。可以猜测,这是叶炜有意为之的一次设定。从《富矿》中象征厄运的黑雪到《后土》中侵袭麻庄的洪水,生态环境污染的描写与警示意味已足够明显,作者极力渲染的生态破坏问题不仅具有强大的破坏力,惊人的持续性,广阔的范围,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连锁反应……人心的异化。
从“废名的世外桃源”到“沈从文的原乡神话”再到“孙犁的人性乌托邦”⑧,现当代作品中的生态批评视野广阔而长远,叶炜作为一名年轻的70后作家,秉承并发展了前辈们传承下来的故土情结,生态反省的意识也持续在其文学作品中得以展现,值得新一代乡土作家的学习与借鉴。而作为一名合格的现代公民,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应时刻铭记在心。
从叶炜的早期作品来看,也不乏青春校园的记录、职场斗争的呈现,但这只是青年叶炜的阶段性尝试性写作,作为70后作家的典型与代表,他真正的扎根之处依旧在苏北鲁南平原上,叶炜说:“我相信,把苏北鲁南写好了,就等于是把中国写好了,乡土中国的精义就在苏北鲁南——这里是中国最发达板块里的不发达地区,也是原始农村得以完整保留的地方。”⑧作为中国首位创意写作学博士,叶炜的才气与能力令人感动,期待这个70后苏北作家的新一轮创作与成长,为中国新乡土文学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①张闳.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M].林建法.傅任.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15
②蔡测海.《“鼓里”——“古里”》[M].
③叶炜.《后土》[M].青岛:青岛出版社.271
④叶炜.《后土》[M].青岛:青岛出版社.338
⑤郭宝亮:面对现实?当代作家缺少了什么[J].中国作家网
⑥许旸.“70后作家:拥有‘乡村故事的最后一代”.要闻,2016-5-11(1)
⑦叶炜.《后土》[M].青岛:青岛出版社.37
⑧叶炜.“我永远扎根苏北鲁南这片热土”.贵州民族报
⑨张艳梅.《生态批评》.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