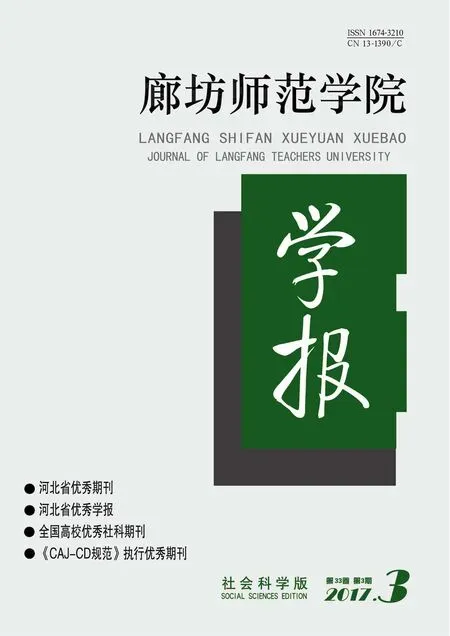现代汉诗的建设策略与方针
——中国现代汉诗研讨会会议综述
(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江苏南京 211189)
新诗专题研究
现代汉诗的建设策略与方针
——中国现代汉诗研讨会会议综述
王珂
(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江苏南京 211189)
现代汉诗是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情感和现代生活,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中国新诗没有造成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断裂,新诗新在创造了一种空前自由的表达情感的方式,百年经验是获得了表达的自由,但是忘掉了诗的精炼和音乐性。对自杀诗人的炒作应该缓行,评论界没有对自杀诗人和自杀现象给予一个冷静的回答。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要培养现代国人和打造现代国家,这是渴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时代赋予新诗的重任,新诗应该绝对现代,但是不能极端现代。建设现代汉诗要重视“汉语诗心”与“汉语诗性”。
现代汉诗;中国现代汉诗研讨会;现代精神;现代
新诗又名“现代诗”,更应该称为“现代汉诗”——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情感和现代生活,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现代国人和打造现代国家。在不同时空,都存在以“诗歌文体建设”为主的审美现代性建设和以“诗歌精神建设”为主的启蒙现代性建设,有必要总结其经验与教训。2016年11月8日至10日,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东南大学中文系及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在江苏南京举办了“中国现代汉诗研讨会”。谢冕、洪子诚、吴思敬、陈素琰、叶橹、傅天虹、郑政恒、章亚昕、沈奇、熊国华、江锡铨、汪政、陈太胜、子张、钱文亮、李润霞、何平、吴投文、张立群、陈义海、陈爱中、宋宝伟、傅元峰、李章斌、杨亮、鄢冬、王珂等30多位新诗学者,子川、胡弦、黄梵等10多位诗人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作家协会、东南大学等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学院的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研讨会。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王珂教授主持研讨会开幕式。北京大学新诗研究院院长谢冕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思敬教授先后致辞。研讨会分三个时段进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傅天虹教授、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沈奇教授、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熊国华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章亚昕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吴投文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陈爱中教授分别担任主持人和点评人。与会嘉宾围绕现代汉诗与现代精神、现代汉诗与现代汉语、现代汉诗与现代文体、现代汉诗与现代人及现代国家,还有现代小诗、现代格律诗、现代散文诗,以及如何界定“现代汉诗”等主题进行了认真研讨,获得了诸多成果。
谢冕教授的致辞点明了此次会议的主题。作为一生都在为新诗奉献的老教授,他的发言充满了激情,他提出的问题更令人深思。他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纪念、庆祝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在这个会上我想起胡适先生在1919年双十节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叫《谈新诗》,他的副标题是《八年来的一件大事》,八年是说从辛亥革命到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的这段时间。八年来的一件大事指的就是新诗这件事,他说与其谈那些无谓的政治,不如来谈谈有意思的新诗这个话题。‘无谓的政治’说的是他对现实的失望,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但现实很糟糕,新诗是他认为八年来最值得谈的一件事。我借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轮到我们来谈论新诗的时候是一百年了。我们是后学的,我们是套胡先生的话来说的,与其谈论那八年来一些‘无谓的政治’,倒不如谈论这件一百年来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中国新诗的诞生与建设。今天轮到我们来谈这件事情,我想就是诞生发展了100多年的新的诗歌形态,或者如王珂所讲的‘现代汉诗’。100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最大的两件事情就是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千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从航空母舰到原子弹都出现了。这100年留给我们的惨痛记忆,那就是废墟、荒原、孤儿和伤残。我想起了台湾的一位作家,在他的笔下菲律宾的一座山下有一万多名美军将士埋在那,那里满是墓碑和十字架,那些都是战乱带来的,是非常惨痛的记忆。现在那么多的墓碑还在那里,还在沉思。我们中国也有惨痛的教训,我们可以到云南的腾冲,那里高丽贡山下有座小山,埋着成千上万的国军士兵,那里竖着的墓碑也让人感到很沉痛,那是无边的死亡在提醒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千年的汉字,百年的新诗,一切都是欲说还休的,我们与其来谈论那些悲痛的历史,倒不如来谈论文化的传承与建设,谈论100年来中国新诗所带来的新气象,谈论新诗这样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谈论战争之后的和平,以及在和平的氛围之下,我们如何将这辉煌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并且建设得更好。诗歌看似无用,其实它是永恒的,它给我们带来希望。我常说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一个做梦的事业,谁都会做梦,做各种各样的梦,诗歌就是让我们做梦的,让我们幻想的,提醒我们要去想象的。谈论诗歌,就是谈论一种非常高远的事情,谈论一种非常恒久的事情。王珂今天让我说一些开头的话,我就想用这些话来回应大家的期待。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庆祝新诗的诞生,纪念新诗的诞生,有许多的诗歌研讨会,我刚从扬州到这里。接连的两个新诗研讨会让我有一种感受,有人文学科的这些学校集合了全国的青年才俊到一起来讨论诗歌的理论问题,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从扬州到这,我看了很多人写的论文,借这个机会来交流我们对于新诗建设的很多意见和看法。我自己读了大家的论文也受了很多启发,得了很多的知识,所以我们是有希望的。诗人们谈论创作,我们谈论理论建设,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都认真地做这件事情,特别是王珂新任中文系主任和东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所长,他是很有抱负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吴思敬教授在致辞中认为已出现了“新诗研究热”:“在大学里边,诗歌研究机构能单独出现,是新时期以来的事情,第一家出现的是原来的西南师大现在的西南大学建立的新诗研究所。此后到了21世纪初,新诗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我们首都师范大学有一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就是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2001年建立。接着就是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现在的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近年也有大学建立了新诗研究的单独机构,像北京师范大学的当代诗歌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现代诗歌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的新诗研究所……人民大学在王家新的主持下也成立了这样的机构。到了今年似乎有加速出现的迹象。今年上半年南开大学成立了穆旦诗歌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上个月河南师范大学成立了华语诗歌研究中心。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参加揭牌仪式的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成立于今年1月。所以一年之内,在四所非常有影响的大学都出现了新诗研究机构,表明诗歌研究受到了许多大学的重视,而机构的成立将会有力地促进当下及未来的诗歌研究。这样一个局面真是让我深受鼓舞。”
此次研讨会还专门开设了“老学者自由发言”专场,由熊国华教授主持点评。虽然每人只有五分钟发言时间,但是四位诗坛前辈谢冕、洪子诚、叶橹和吴思敬的即席演讲都十分精彩。谢冕说:“因为大家的一些焦虑,认为中国新诗造成了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断裂。我觉得问题不一定是这样,从哪些方面来讲呢,我认为语言没有变,使用的都是汉语。就是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从文言到白话,在现代汉语中又保留了很多古典的成分。所以,我们几千年的诗歌之所以能延续下来是其所使用的语言是一个,就是汉语。只不过随着时间的变迁,汉语有一些变化,古代汉语变成了白话,变成了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又有古代汉语的成分。诗歌观念也没变。观念是什么呢?是诗言志,是诗歌对人的情感思想的教化作用。这个没有变,新诗的诞生就是因为它的教化作用嘛。在中国的社会,民心社会有问题,就需要诗歌来振兴,就是所谓‘振兴国运,改造民心,启发民志’。所以几千年下来,中国诗歌发生在‘五四’时期的是一场大变局,这种大变局的原因有很多,改变的地方也有很多,我就不细讲了。从《诗经》的民歌及无名者的创作,到‘五四’新诗的形态,不过是诗歌形态的变化而已。所以,我认为我们新诗百年的焦虑没有必要。诗歌如何向内适应时代,向外走向开放,这才是大问题。唐代长安大街上到处走的就是胡人,一些音乐就是外来的。……今天所说的‘欧化’也好,‘西化’也好,甚至‘全盘西化’也好,这些都没有问题,这是诗歌产生的大格局。究竟新诗新在什么地方,就是新在它创造了一种空前自由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我们一切都可以忘掉,但是诗歌的音乐性不能忘掉。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诗是音乐的文学。我们现在忘掉得相当多,新诗越写越不精炼。……我们现在的诗歌不好听了,不好看了。……百年经验是我们获得了表达的自由、歌唱的自由,但是忘掉了本质的东西,那就是精炼和音乐性。”洪子诚说:“我对新诗一直抱有非常大的信心,即使在90年代大家都在骂新诗的时候,我也一直是新诗的崇拜者,我对新诗一直有敬仰的心情,一直认为新诗是很有前途的。我认为百年来新诗做得非常好,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好。具体内容我就不说了。……但我不同意对旧诗的完全排斥态度,不同意新诗诗人写旧诗就是一种堕落的看法。……我觉得非常绝对化地认为旧诗无用是不可以的。在表达某些特殊的个人经历时,旧诗可能比新诗更合适。”叶橹表示:“我喜欢一些旧体诗,但是不主张在我们这个时代写旧体诗。……旧体诗令人讨厌的一大原因是‘老干体’流行。……新诗的形式应该是自由的。新诗形式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是不长,第二是精炼,第三是音乐。你不要去想建立一种规范的形式。所以那一年我们在武夷山开会时我认为这是一个伪话题。关键是如何把诗写好,现代诗怎么会没有形式呢,每一首诗都有它的形式。……对待新诗的形式问题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谢老师讲的内在韵律很重要,它不一定要押韵,但一定要有内在节奏。旧体诗的形式会越来越走向式微,若不相信,百年后来看,写旧体诗的人会越来越少。”吴思敬说:“我想谈一个沉重的话题,如果要对我的发言列个标题,那就是《向死而生——对自杀诗人的炒作应该缓行》。中国历史上,从古代,到近代,到现代,自杀的诗人是很少的。最著名的是屈原,但他主要不是因为诗自杀的。……并不是因为他写不出诗来自杀的。……现代最著名的是朱湘,1933年他在长江自沉,朱湘的自杀也是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贫困。建国后的一段时间,诗人的政治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也没有哪位诗人自杀,如胡风集团、右派集团的诗人。‘文革’有那么多人自杀,但知名诗人的自杀只有闻捷,他的死因不明。当代海子的自杀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一些诗人的自杀与他有一些相关,一些诗人甚至认为海子后来的诗名是他的自杀带来的。海子今天在诗坛上有位置,首先不是因为他的自杀,而是因为他的文本有力量。海子自杀的原因非常繁复。说海子是‘殉诗’的说法太简单了,这就成了一个神话。这就导致后来有些诗人在写出一些作品之后,希望用自己自杀的行为艺术来提升自己作品的价值。有些诗人去世以后,他的有些朋友就拼命地加以炒作。以致海子自杀以后,不断出现诗人自杀。余地自杀前就在诗中写出‘下一步我就是自杀诗人的王’。大约有近20位诗人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评论界没有对自杀的诗人和自杀现象给予一个冷静的回答,没有启发他们你的诗不会因为你的自杀而变得更有价值。……我们不能人为地自己终止自己的生命,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对青年诗人加以引导,不要去赞美那些所谓的殉诗行为。”
这次研讨会给中青年学者提供了每人十分钟的发言时间,每人都根据自己提交的论文作了精彩的发言,有的话题还当场引起了争论,如洪子诚和沈奇不赞成陈太胜对旧诗的否定,叶橹不赞成王珂的新诗形式需要适度规范、需要建立准定型诗体的诗体重建观,也不太赞同谢冕对诗的音乐性的重视的观点。但是,老中青新诗学者一致赞同王珂提出的新诗要加强现代性建设的主张,尤其是谢冕、吴思敬、陈太胜等人强调了新诗的开放性。
多位学者关注“现代汉诗”这一命名。如子张认为:“我理解的现代汉诗就是现代的或现在的汉语诗歌,它的基本内涵不超出‘新诗’的基本内涵,这也就是说,所谓现代的汉语诗,仍然是区别于传统旧诗的新诗,其主要诗体特征仍然是非定形自由诗。除了诗体上的‘定形化’,它有着一切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就体现在它与现代精神、与现代汉语、与现代文体、与现代人及现代国家的种种关联之中,但这种可能性只能是自然生成的,而不是理论家先入为主预先设计、预先规定出来由诗人们按规定动作操练的。‘现代汉诗’只能从每一个诗歌写作的个体求之。”
作为此次会议的主办者和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的创办者,王珂给本次会议确定的两大主题是:现代汉诗与现代精神和现代汉诗与现代人及现代国家,就是探讨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要培养现代国人和打造现代国家。他认为,这是渴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时代赋予新诗的重任。他说:“现代汉诗是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情感和现代生活,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总方针是:新诗应该绝对现代,但是不能极端现代。新诗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文体,是与政治文化的现代性建设基本同步的先锋性文体。今日新诗与古诗以及不同时期的新诗比较,这种文体在功能、体裁、题材、技法,特别是在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方面都有较大变化,这种变化通常是‘现代性变化’。今日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强调现代性面孔的丰富性,一定要重视现代性中庸甚至保守的一面。21世纪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吸取20世纪新诗革命的教训,只有把它限定为稳健的现代汉语诗歌改良活动,而不是激进的现代汉语诗歌革命运动,才能通过新诗的现代性建设促进中国人的现代性建设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建设。只有通过新诗的诗体现代性建设带动新诗文体现代性建设,通过新诗的文体建设带动整个新诗的建设,通过改善诗歌生态来改善文学生态,通过改善文学生态来改善政治文化生态,才能完成新诗现代性建设培养现代公民和建设现代国家的神圣使命,才能拓展新诗的功能,完善新诗的文体,提升新诗的价值,净化新诗的生态,让现代诗真正‘现代’,让新诗真正‘新’。”①参见王珂:《张志民现实主义创作对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启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陈太胜也认真研究了新诗的现代性。他认为:“无论是西方诗学,还是中国古典诗学,要谈其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都只有放到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现实场域中来才是合宜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个人(诗人)在这当中的创造性作用。完全可以理解,在文化的接受和影响中,并不存在真的原封不动地被接受或影响了的东西。以之对新诗进行贬低或非议的人,首先是违反这一基本常识的。我们所期待于文学的,其实何尝不就是人的问题呢?只有在文学真正揭示了我们的存在境遇和生命境界的某种秘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地谈论‘文学’和‘人性’,才可以说在‘奥斯维辛’之中和‘奥斯维辛’之后仍然还可以有诗。”
一些学者呼应了王珂的现代汉诗的一大任务是培养现代人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新诗已成为“大众”的文体。汪政认为:“诗歌,绝不应该只是诗人与诗歌理论家的事,而可能是也应该是每一个诗歌参与者的事,那些翻开诗歌作品的人,诗歌的受教育者,那些为诗的诞生和传播奉献过劳作的人,都是新诗共同体中的一员。这一中国新诗主体的新认定所意味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意义有待阐释并在现实层面推广。”吴投文认为:“新世纪诗歌的不断升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预示着新一轮‘诗歌热’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中国新诗极有可能重现1980年代的辉煌。如果早前几年诗歌的境遇还显得有些暧昧不明,似乎并未完全摆脱‘边缘化’的困局,当前我们所面对的诗歌现实已经逐步清晰起来,诗歌开始重新回到社会公众的生活之中。新世纪的诗歌升温包含着复杂的文化症结,一方面是公众围观和全民写作的造势驱动,一方面是新诗文化在大众文化语境下面临着实质性的提升。公众围观、全民写作是新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既是新世纪诗歌升温的外在表征,也是新世纪诗歌升温的重要促动因素,同时也是构成新诗文化的群体性基础。在新世纪的大众文化语境下,新诗文化表现出异质性的精神特征,又与公众围观、全民写作纠结着深刻的文化关联。”②吴投文:《新世纪诗歌升温的精神症候与文化透视》,《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
一些学者提出了构建现代汉诗的具体策略。沈奇提出要重视“汉语诗心”与“汉语诗性”,他认为,“笔者生造‘汉语诗心’的说法,在本文语境中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汉语诗人该有汉语自身的诗心所在,不能总是翻译诗歌主导的‘范’;一是说汉语诗人为诗而诗时,多少还得操心点汉语的事。百年新诗,其潜在‘危机’正在这里——屡屡变动不拘,在在创新不断,‘滚动的石头不生苔’(法国谚语),只剩下大众化的、运动性的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如此结果,只能是不断‘下行’而泛化,乃至连‘分行’也只是一种表面性的存在,内里的文体意识亦即诗体意识,已经相当模糊。道成肉身,这‘肉身’之‘体要’,是诗之‘道’所以然的根本属性”。江锡铨从汉语新诗的形式美学建设来探讨现代汉诗,他认为,“诗歌形式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的艺术发展。在汉语新诗百年来的多声部‘合唱’中,格律诗的声音是十分微弱的。这种‘奇特现象’,与近现代国际诗歌文学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也是极不协调的。在世界范围内,在很多国家,尽管一个世纪以来,自由诗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它仍然只是各体诗歌中的一体,好像并没有成为整个世界诗歌的主体,更不是全体”。子川从翻译诗角度来探讨现代汉诗,他认为,“中国新诗创作实践整体上已经跨越对翻译文体直接模仿的练习阶段,在强调现代汉诗的汉语性的同时,诗人笔下已呈现出母语的丰富性,这是在所有文体写作中,诗歌对语言的最大贡献。也许可以这么描述:在学习借鉴翻译文本基础上所诞生的中国新诗文体,经过长达百年的培育,已经渐渐成长为一株树”。陈爱中的论文题目是《论汉语新诗命名的异质性——基于翻译的视角》,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不同语符之间的相互转换,它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内在的语言交际理念,是不同族群之间语词经验的互相应和。囿于语言符号本身的特性,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等值置换的翻译理想很难在实践意义上实现。于是也就存在一个抵制与归依的翻译选择问题。汉语新诗的命名同样是在这种翻译的不均衡状态下自成体系的。汉语新诗将相关的称谓从西方源语言中直接翻译过来,然后寻找到相应的汉语语符,甚至抛弃语词的所指而追求单纯的音译,以此来实现对某一种汉语新诗现象的标示”。
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某段时期的新诗来研究现代汉诗的文体特点。杨亮认为:“‘叙事性’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技巧,还是一种新型的艺术创造,是90年代诗歌有效性诗学命题之一。正是由于‘叙事性’诗学的出现,诗歌告别了80年代‘纯诗’的形式主义追求,从狭小的艺术天地中走出,重新建立同现实人生、经验世界的联系,诗由封闭走向了敞开,呈现出包容的态势,使诗获得了内在的平衡,即艺术与人生、想象与现实、抒情与叙事间的平衡。”张立群讨论了抗战诗歌的正面书写及其复杂化,他认为,“抗日战争(1937—1945)作为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阶段,自然影响了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创作。‘抗战’不仅为诗歌提供了鲜明而集中的国家主题,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诗歌的面貌”。
一些学者还通过具体作品来讨论现代汉诗的现代精神或现代文体。郑政恒的论文题目是《空洞与卖梦——昆南的现代诗风》,他认为,“昆南在新古典风格时期的诗作,并不是对旧式古典文学的全情回归,也不是打着新古典主义的名堂招摇过市,而是追本溯源的一个动向”。钱文亮的论文题目是《词语的镜像——读张枣的〈镜中〉》,他认为,“张枣的成名作《镜中》在当代诗歌经典中是一首望之亲切、即之却远的出色的现代抒情诗。这显然得益于张枣对汉语及其古典诗歌特性的领会与参悟。诗歌巧妙地抓住了抒情诗的特质——音乐性,这一中国古典诗歌最为伟大最为优秀的传统,在重复、迭句与谐音的巧妙运用中获得自我循环的整体感……正是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象征性借用,这首诗举重若轻地获得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如施泰格尔所说的‘情调’,或者是中国古代诗评家所说的‘意境’,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他揣摩透了这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观,一种静观天地人事的道禅审美态度……它仍然是地地道道的现代诗,也颇多西方诗歌艺术资源的征用”。李玫的论文题目是《在四月里如何谈论衰老——西川〈一个人老了〉解读》,她认为,“28岁的西川何以会突然意识到衰老的存在,在无限春光里,一个28岁男人的世界不应该是长空浩荡大地无限地伸向远方吗?……从抒情肌理生成的影响渊源看,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点:中国古典诗歌、西方诗歌和汉译英诗。创作主体的个性化整合,以及由此生成的三种元素配比差异,是不同诗歌个性特征的生成机制。变动中的20世纪中国,在现代性的焦虑中追寻速度和效率,在对旧的恐慌中追赶什么或者被什么所追赶,因而在‘老’中更多地解读出陈旧与过期,需要在对‘老’和‘旧’的不断超越中缓解焦虑和确认方向,时间在这里是单向和单维的,是向前和谋新的”。傅天虹的论文题目是《从〈从俗如流〉看朱寿桐散文诗“汉语诗性”的追求》,他认为,“按照王蒙在序言中的说法,朱寿桐可算是大器晚成的散文家。作为作家,他出版的散文集《从俗如流》,收集较多的是成熟优美的散文诗,而一般散文也都包含汉语诗性的追求,也是‘汉语新文学’这一概念理论运行的体现。通过解读、品味他的散文,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人身上的道德情怀与艺术气质,更体会到了他对归属汉语文化的迫切追寻”。何平的论文题目是《诗人在诗人中间——1980年代汉语长诗写作兼及任白的几首长诗》,他认为,“研究当下诗歌写作,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优秀的汉语诗人都有长诗写作的经历或者正在进行长诗写作实践。应该说,当下汉语长诗在遗忘和记忆中建构个人的精神史方面已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且‘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历史幽灵在许多诗人的文本中徘徊。‘语境’作为对话的基本前提在诗人与诗人之间已经形成”。张娟的论文题目是《渡也诗歌“私密空间”的诗学研究》,她认为,“渡也通过这种私密空间的写作,承载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情怀、男性胸怀和具有日常现代性的情感体验。渡也诗歌中常有私密的日常生活空间意象,看似信手拈来,实际又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汪楚红的论文题目是《从颜色词看梁小斌早期诗歌中的儿童观》,她认为,“梁小斌作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擅长以丰富的颜色词入诗,诗歌具有浓郁的色彩性。颜色词凝聚了梁小斌对儿童的关注和希冀,是打量诗人对儿童认知的一扇窗口”。
一些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视野新颖。李章斌的论文题目是《韵律如何由“内”而“外”——谈“内在韵律”理论的限度与出路问题》,他认为,“‘内在韵律’理念长期主导了学界对自由体新诗韵律特征的认识,有必要开拓一条探讨新诗韵律是如何由‘内’而‘外’的路径,以补充‘内在韵律’说的缺陷。为了回答韵律之‘生于内而形于外’,必须认识韵律的构成基础(重复)、韵律的实现方式(与时间及书面形式之关系)。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后,才有可能为新诗韵律研究开启新的‘范式’”。宋宝伟的论文题目是《新口语写作:智性与鲜活的融汇》,他认为,“口语是一种原生态的言说和语言,最贴近生活。日常生活琐碎、粗粝、凡俗甚至是杂乱无章的状态,与口语的自然、不加修饰、脱口而出的流畅语感,有着一种浑然天成的协调感和一致性,用口语表现日常生活有着先天的独到优势”。鄢冬的论文题目是《新诗中的非诗因素——情感伦理、现实物象与合理化想象》,他认为,“新诗在发展的过程中,文本成熟的魅力与陌生的味道相伴相生。正是由于形式的无限打开,使得新诗诗人拥有无限的话语权,自然而然也就面临着文本现场失控的风险。传统的诗歌观对待新诗文本时越来越迟滞、沉重,以文学性考量诗歌文本也已经是诗人并不买账的手段。情感伦理、现实物象、合理化想象,这三个并不能占据文学文本中心的要素,却有可能成为文化文本的重要标尺,而新诗的每一次突破,有可能昭示着它以文化文本的身份脱离文学文本的开始”。赵娜的论文题目是《意义的瞬间聚集——由长诗〈信札〉解读杨克的现代精神》,她认为,“杨克的长诗《信札》,实现了人的内部生命感受和体验的意义的瞬间聚集。现代诗人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关注埋藏在肉体生命中的灵魂。在这人类被工业和技术不断异化的时代,灵魂需要摆脱更多看不见的束缚”。
Abstract:Modern Chinese poetry is a language art with modern consciousness and modern spirit by using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poetic style toexpress modern emotion and modern life.The newChinese poetry has not caused the break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but in the creation of an unprecedented free way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of experience of obtain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the newpoems forget the poetry of refining and music.The speculation of suicide poets should be delayed,and critics have not given a sensible answer to suicide poets and suicides.The main task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oetry is to cultivate modern people and build a modern country which is the great task given by the great era of the“Chinese dream”.New poetryshould be absolutelymodern,but not extremelymodern.We should payattention to"Chinese Poetic Heart"and"Chinese Poetic Style"in buildingmodern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modern Chinese poetry;seminar ofmodern Chinese poetryresearch;modern spirit;modern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and Polic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WANGKe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1189,China)
I207.25
A
1674-3210(2017)03-0019-06
2017-06-03
王珂(1966—),男,重庆人,文学博士,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