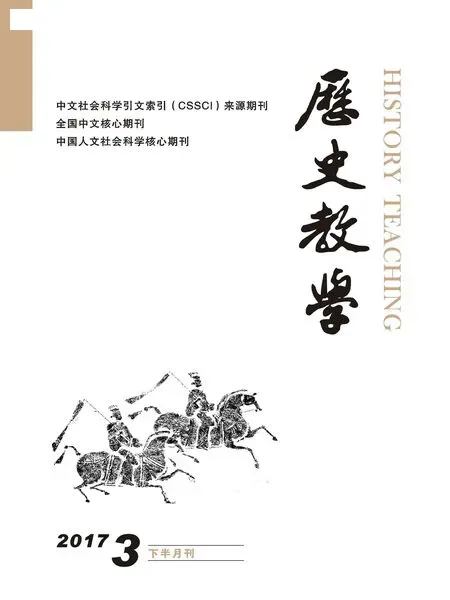教学相长摸索前行
——关于指导学生完成学业的几点心得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教学相长摸索前行
——关于指导学生完成学业的几点心得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教师指导学生完成学业,是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主要环节,是教师的天职和责任。在20多年的博导生涯中,在教学相长的实践过程中,笔者有几点心得:引导学生在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的前提下,制定学位论文的选题;在读书的过程中拓展知识并积累问题;从写读书札记入手不断提高学术文章的质量并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关注评论与鉴识能力的砥砺,以适应专业理论的发展和促进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树立史学自信的精神,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
研究领域,积累问题,札记与文章,评论与鉴识,史学自信
我自1994年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有23年了,第一届博士生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至今也有20年了。而我自己则由壮年步入了老年。
《历史教学》杂志主编杨莲霞女士,要我谈谈这些年来是怎样指导学生完成学业的。这是一个好题目,可以促进撰稿人进行思考和总结。作为杂志负责人,想到这样一个题目,我很钦佩,因为这个题目非常符合这家杂志的名与实,对教师、学生、杂志都有益处,可谓一举三得。
当然,这个题目对撰稿人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一个“挑战”。几十年过去,天天面对学生,许多话从哪里说起呢?我想,就说说自己认为还算是有点心得的话题吧。
一、如何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
这可以从我自己的经历说起。1977年,我正当不惑之年,然学术履历表上仍是一纸空白。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决定着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国史学历史悠久,历史撰述浩如烟海,从哪里着手呢?经过对有关论著索引的查阅,我发现有近300年历史的唐代,今人在唐代文学、艺术、思想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于唐代史学研究则相对薄弱,似有一些空白存在。由于我对唐代历史较有兴趣,于是决定从唐代史学入手研究中国史学史。同时,我也考虑到,在唐代近300年的历史上,史学方面可研究的内容较多,这可以作为一个较长时期的研究对象。1978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唐代史学的文章;①参见瞿林东:《封建史学和封建政治》,《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第5~6期合刊。1987年,出版了一本七万多字的小册子《〈南史〉和〈北史〉》;②参见瞿林东:《〈南史〉和〈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1989年,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唐代史学论稿》。③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我常常跟同学们讲到自己的切身经历,认为只有专注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思想和精力都比较集中,对于这一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才比较容易被发现,一方面可以横向拓展,一方面则可向纵向不断深入。而当有的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甚至受到重视时,自然受到鼓舞,增强自信心,于是学术之路也就越走越宽。
1994年,我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2年,我把自己在这方面的体验和认识,写成了一篇题为《关于如何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几点认识》的文章,④参见瞿林东:《关于如何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几点认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2年第5期。供青年朋友参考。当初在确定研究唐代史学的时候,也曾有这样的想法,即在此基础上,将来或可上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或可下延研究宋元史学。后来的经历表明,我大致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第二个十年里,先后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①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1998年出版了《中华文化通志》系列丛书中的《史学志》,②瞿林东:《中华文化通志》之一《史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这是以中国古代志书体裁撰成的中国史学史;1999年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纲》。③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应当说,这个经历,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设想的“愿景”很是接近。
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些往事,无非是要说明,对一个青年学生尤其是博士生来讲,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概括说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首先是具有明显的学术意义,同时具有创新的可能和较长时期耕耘的空间,以致可以作为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基础。质而言之,博士学位论文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继续研究的起点。
当然,我所指导的博士生毕业后,并非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即使是从事科研工作,但由于工作的需要,未能在原先确定的领域中继续研究,只可把这一思路和能力用于新的工作。有的分配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生,一般都有可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向着横向、纵向开拓,十几年中出版了三四本、五六本专著;有的从学位论文中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扩大了研究领域;有的以研究某一位中西兼通的史学家,进而发展到研究此类史家群体;有的从研究某一时期的中国某一史家的历史思想,进而走向研究与此相近的某一西方史家而两两比较,等等,都存在可持续研究、发展的空间。
不论是对博士生,还是对博士后研究者以及访问学者,帮助他们确定研究领域和具体的选题,都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要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一方面要考虑到研究者的兴趣及知识结构,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学科发展的需要。举例说,有一位名牌大学的文学博士到我这里做博士后,但本人并未考虑好课题,经过沟通,确定以“《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为题。这位博士后出站半年,《〈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一书出版。④参见张桂萍:《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近日,见其主持国家项目“清人文集《史记》评论资料类编与研究”行将结项,我大为感慨:一个文学博士把史学批评与文学评论结合起来,拓展了《史记》研究,我为之高兴。我还带过几位访问学者,他们大都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但由于不明确自己要有一个稳定的研究领域,十多年中,主攻方向不明确,影响研究能力的提高。我如同对待博士生一样,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各自的兴趣和研究能力,建议他们还是要确立一个相对集中的领域,专心地做深入研究。其中有几位访学后一两年中都出版了专著,有的专著还填补了某个领域的空白。⑤如近十年来我处访学的李良玉所著:《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谈家胜所著:《国家图书馆所藏徽谱资源研究——32种稀见徽州家谱叙录》,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
总之,不论是认识上还是教学实践上,我是唠唠叨叨,反复强调博士生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要三思而后定,定后不要轻易改动。同时,我也坦然地建议他们读一读我的《唐代史学论稿·自序》,⑥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1~5页。或许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
二、读书、发现问题与培养独立研究的能力
读书是学生完成学业的重要环节,这不仅是知识储备的路径,也是发现问题和积累问题的路径之一。而发现问题乃是研究的起点,是培养独立研究能力的重要步骤。
史书浩如烟海,穷毕生精力,也难得其“冰山一角”。因此,我建议学生必须划定阅读范围:一是基础理论著作,二是专业理论著作,三是研究领域的主要文献,四是与研究领域相关的著作。关于基础理论著作,我希望学生读《毛泽东选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前者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后者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形态。关于专业理论著作,我希望学生读唐代史家刘知幾的《史通》和清代史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前者侧重于史学批评,后者着重讲史学理论,这两部书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学理论上的成就。关于研究领域的主要文献,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少则数种,多则数十种。至于与研究领域相关的著作,有基础性的,如白寿彝先生提倡阅读“四史六通”,①白寿彝先生说的“四史六通”,“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六通”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三通”,加上《史通》《资治通鉴》《文史通义》。参见白寿彝:《说六通》,见《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85~293页。有扩展性的,即与研究领域相近的其他学科的著作,这要根据阅读者的研究需要而抉择。
上面说的这些,只是理论上的设计,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一般难得按照这种要求去施行。尽管如此,这种设计和要求,有比没有强,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面对这么多要读的书,一是短时间内是无法卒读的,二是根据研究的状态和需要必须分出轻重缓急。我建议学生要对所读之书分成几种情况:一是精读,二是通读,三是选读,四是泛读。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的书,必须精读,三遍五遍亦不为过。当然,与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书,也要精读,使研究得以深入。其他通读、选读、泛读之书,均视具体情况而定。
读书,一方面是拓展知识面,在增加知识储备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改进知识结构。从博士生的研究工作来看,读书的过程又是发现问题和积累问题的过程。我常用白寿彝先生引顾炎武的话说,“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②参见白寿彝:《要认真读点书》,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4页。读书非常重要,尤其是读第一手材料,要能够从中发现问题,问题积累得多了,学术研究才有活力,才可能提出新见解,这就好比“采铜于山”铸造新钱,有所创造。我也向学生介绍我在作“唐代史学编年”的过程中,因接触到一些书而“发现”的问题,如:令狐德棻是较早向唐高祖提出修前朝史的史家,以及他在修“五代史”、《晋书》过程中“总知类会”的作用;在支持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方面尽心尽力;等等,表明他是“唐代史学的开山”。③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157~172页。魏徵是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同时他还主持修撰《隋书》,并撰写了《隋书》纪、传的史论和《梁书》《陈书》《北齐书》总论,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唐初统治集团之历史观与政治观的某种联系,可见《隋书》史论具有突出的重要性。④参见瞿林东:《评〈隋书〉史论》,见《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3~188页。两《唐书》与一些唐人史料笔记中,多有关于谱牒之学的记述,出现一批擅长于论谱牒之学的史学家,这与唐朝政治有何关系,与唐代社会风气有何联系,怎样从历史进程来看待谱牒之学?显然,这是十分有意义的问题,⑤参见瞿林东:《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见《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0~116页。等等。这些问题,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唐代史学的风貌,研究起来,使人兴致盎然,不觉读书、撰述之“苦”。尽管我不能要求学生现阶段都能做到这种程度,但我希望他们应当懂得如何在读书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不断积累问题,这是走向独立研究和撰述的必要前提。
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和学生交谈中,我常用孔子说的话启发他们,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⑥《论语·为政》,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9页。一定要把“学”与“思”结合起来,才能“发现”问题,才能不断积累问题。在这方面,有些学生是做得很好的。如有研究王夫之史论的学生,在读书中发现嵇文甫和林纾对王夫之史论选评上有差异,认为可以进一步探讨;有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的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华覈这个人在史学上有所作为,而几乎被人们所遗忘,应当研究,给他在中国史学史上一定的地位;有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一个明代学者从未有人研究过,但此人有很浓厚的理学思想,故评事论人,都以理学看待而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表明对理学家的相关论述应持分析的态度;有学生在读两《唐书》时,发现唐后期蒋氏史学世家几代人参与修国史,成就突出,值得研究等,于是各写出有关论文,⑦以上参见江湄等主编《时代·师承·史学》一书所载:陈安民:《试论林纾和嵇文甫的船山史论选评》,第454~468页;王姝:《三国吴人华覈的史学批评思想》,第229~241页;于泳:《论〈评史心鉴〉的倾向与得失》,第362~373页;朱露川:《略论晚唐蒋氏史学世家》,第272~28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可见认真读书、思考的重要。这些虽非重大问题,但却实实在在促进了学生们的问题意识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对思考问题的兴趣和独立研究能力也都有所提高。
三、关于札记、文章和学位论文
攻读博士学位,最终是要撰写一份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学位论文,而许多硕士毕业的学生,虽然通过了硕士学位,但一般均未公开发表过学术文章,这就给读博加重了压力。这是因为,撰写文章尤其是学术性文章,必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指导博士生学会撰写文章,实为教学工作的一大要旨。20多年的博导生涯,仅就指导学生撰写论文这一项,我深感压力之大、责任之重。
为了逐步培养和提高学生撰写文章的能力,我提倡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及时把心得写成笔记,或者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其中道理,前人已有明确论述。清代史家章学诚在给自己子侄辈的家书中强调作札记的重要性,他写道:“札记之功,必不可少。”这是十分断然的口气。在章学诚看来,作札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可以提高读书的效果和训练文字表达的能力,他说:“日逐以所读之书与文,作何领会,札而记之,则不致于漫不经心。且其所记虽甚平常,毕竟要从义理讨论一番,则文字亦必易于长进,何惮而不为乎!”这是从“义理讨论”和文字训练两个方面指出“札记之功”的意义。所谓“义理讨论”,当是指对所读之书与文的思想旨趣而言,而“文字”方面的“长进”则是指读者自身了。这真是克服读书“漫不经心”的良方。章学诚进而指出,“札记之功”更在于能砥砺自己的思想见识,他说:“札记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心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则如山径之茅塞矣。”“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①以上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一》,见《章学诚遗书》卷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训练自己的思维、活跃自己的思想之方法和手段,该是多么重要。章学诚还用“山径之茅塞”和“无穷妙绪皆落大海”这样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不作札记的危害和损失,意极深刻。可见,章学诚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对于后辈的良苦用心。
指导学生,理性认识和实践经验都很重要。我在研究唐代史学之初,写过一二十篇札记,有的也已在报刊上发表。但对于札记在治学上的重要性,远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读到章学诚所论后,心有所感,认识提高了,于是写了一篇文章《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发表在《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1984年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从这时起,我就反复地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前人的真知灼见和我自身的感悟,要求学生重视写札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时电脑尚未普及,学生们写札记还算勤快、认真;从90年代后期开始,电脑普及开了,学生们用笔的方式写也逐渐少了,写札记的自觉和热情也渐渐淡了。当然,在电脑上写也可以,只是希望不要忽略,更不要放弃就好。章学诚说的人的思想一旦如“山径茅塞”和“无穷妙绪如雨珠落大海”,那实在是治学上的悲哀,是我和我的学生们都要防止的。除了讲这些道理外,我有时把自己已经发表的札记复印出来发给学生们参考,希望对他们多少有一点启发。
写札记固然重要,但札记毕竟同文章有所区别,有的札记可以进一步发展写成文章,但并非所有札记都可以发展成为文章而发表。章学诚在讲“札记之功,必不可少”的时候,也谈到了文章同札记的区别,他认为:“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札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②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一》,见《章学诚遗书》卷9,第92页。说得直白一点,文章是一个人的“学问”的表现形式,而札记是人们“读书练识”走向“学问”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事情之表现形式。这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并不是说有了“学问”的人就没有必要作札记,更不是说“学问”与札记之间有天然的鸿沟。
说到指导学生写文章,对学生来讲,这应是学生完成学业并明显提高自己的重要环节,而文章则是这个环节的标志。在这方面,我的思想积累和理论认识是很有限的,往往是凭借自己的一些所谓“经验之谈”来指导学生。这里包括几点:一是关于文章的题目,基本要求是平实且与内容相契合,文不对题、文题不相称等均不可取。倘能于平实中略显出内在的分量,或于平实中隐含着某种深意,则更好。二是文章结构力求清晰,或显示纵向脉络,或反映横向关联,或层层推进诉诸逻辑的力量等等,都能井然有序,使人看得明白。三是文章起首要把所论问题提得明白,文章结末要把所论内容作简要小结,倘能在小结中对所述内容有所提升,或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则更好。四是行文平实,不追求华丽,不刻意晦涩,尤其不要生造词汇。五是反复修改,倘能读来朗朗上口,则更好。对于时下所要求的学术规范和遵守学术道德等等,当然必在要求范围之内。
其实,关于文章之道,我向学生讲得最多的还是老一辈学者的学风和文风。我曾概括过白寿彝先生的文章之道,这就是:懂类例,有重点,避枝蔓,戒浮词,讲平实。他说的类例,既是传统意义上的类例思想和体例要求,也是现今所谓学术规范。他说的重点,是不赞成一篇文章中各部分都“平摆着”,面面俱到,读后没有留下较深的印象,于学术无补。他说的枝蔓,是指文章中出现枝枝杈杈,在枝节问题上流连忘返,模糊了文章的主线。他说的浮词,是指引文啰嗦,不够凝练,不仅读来费力,而且还可能掩盖了文章中的精辟处。他说的平实,包含明白、准确、凝炼的要求。①参见瞿林东:《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33~342页。这都是我经常向学生讲述的内容,目的是希望他们都能按这样的要求做。
同时,我也向学生推荐史念海先生的著作,学习史先生史笔的文采,以及文章上下文过渡时的那种含蓄和自然。②史念海先生论历史地理问题,犹如身历其中,娓娓道来,遣词造句亦多洒脱自如,那种“河山之恋”的情绪,溢于字里行间。参见史念海著《河山集》各集自序、《中国的运河》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推荐何兹全先生的论著,③参见何兹全《何兹全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其中,第四卷《中国古代及中世纪讲义》《中国文化六讲》,第五卷《秦汉史略》《三国史》,尤其写得深入浅出,如与朋友论学,如答后学所问,从容、自然。学习何先生平实的学风和文字表述。甚至还向学生推荐郭沫若先生晚年所著《李白与杜甫》,④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这本书的文字表述,可谓炉火纯青,堪称楷模。
我还邀请田居俭研究员来给学生做讲座,题目是我提出来的:“史学工作者要写一手好文章。”田居俭研究员曾任《历史研究》主编,一向讲求文采,他撰写的《李煜传》,⑤田居俭:《李煜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文笔生动,受到读者好评,他“现身说法”,对同学们启发很大。
指导学生如何写文章和改文章,是指导学生完成学业的重要环节,这一环节进行得是否顺利,直接关系到学位论文的撰写及其学术质量。其中最紧要的是帮助学生改文章。改文章的方法是多样的:一般说来,或口头表达要点,或书面写出几条意见,要求学生照着去做,把文章修改出来,这样做是可以的。但经验证明,还是导师亲自动手修改学生的文章,并明确写出何处修改,为何修改,以及尚须注意的相关问题等等,这样做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这需要导师的细心、耐心,也需要导师的思考、真诚和花费大量的时间。
这些年来,我面对学生的文章,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可改,其原因或是论旨不明确,或是缺乏独立见解,都必须要求学生重写。重要的是,导师要告诉学生如何重写。对这种情况,有时甚至要帮助学生列出重写的提纲乃至标目等具体建议。
第二种情况,是略改。所谓略改,是因为文章的基础较好,从立论、内容、结构、论述、文献运用和文字表述,均无明显不妥之处,不需要作较大修改。所谓略改,一是对大小标题再作推敲,看看是否可以改得更贴切;二是看内容是否还可增删,使文章更充实、凝练;三是首段是否可以把问题提得更明确,末段是否可以把所论内容提升一步,或留下可供读者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四是改正或替换引文中不准确的用语,以致个别的错别字、漏字、误书等。
第三种情况,是大改。此种情况的文章,整体面貌与略改的文章面貌相近,它之所以需要“大改”,除其他原因外,是全文文字表述有较多问题,即不够通顺,不够简练,不够规范,是常见的几种现象。对于这种文稿,一方面要概括出来症结所在,一方面是亲自动手进行修改,即使改成“大花脸”,也是必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既要学生从道理上懂得如何讲求文字表述,也要让学生真切地看到什么地方应当怎样去改,以加深理论上的认识,收举一反三之效。我的体会是,疏通一篇需要“大改”的文章的文字表述,比修改文章中的某一学术观点还要艰难。这样做之所以成为必要,不仅仅是为了改一两篇文章,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现代汉语表述水平,因为这是他们将来从事任何工作都不能缺少的基本功。确有不少同学告诉我,被我用红笔改成“大花脸”的文章,他们至今还保存着,一方面留作纪念,一方面是以此督促自己认真对待文字表述。我听到这些,十分欣慰,自己所花费的工夫,是值得的。
不论是略改还是大改,对同一篇文章,一般要改两次到三次。在他们把文章投寄出去之前,我建议他们把改清的文稿认真地朗读或默读一两遍,对于读不通顺的地方,还可以再改一改,同时检查是否有错字、漏字等等。前不久,我们师生有一次聚会,许多学生都讲到我为他们改文章的故事,可见这一环节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
博士学位论文是反映学生读博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每一个导师都高度重视的。论文选题的确定,如同前文所说的如何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有相近的道理。对于开题报告的酝酿,一般不在三五次以下,如讨论写什么,如何写,何处可以突破,何处可能创新等等。开题报告成稿后,如同在对待学术文章一样,也要两次、三次地修改。这种修改不同于一般学术文章,后者所论比较集中,可以修改得精细一些;而前者所论范围要宽得多,修改可能更着眼于大处,细处则要求学生自己多加审视、推敲。
我对学生撰写的开题报告,有两个要求。一是撰写大纲中每章之下要有几百字的提要,目的是把现有的思考成果浓缩其中,以备记忆和进一步考虑之用;二是尽可能列出三级标目,把已经掌握的内容和论点确定下来。这两项,在撰写学位论文过程中都可以修改、补充,而师生从中都可看到这种变化及其得失。
对于成稿的博士学位论文,一般要阅改两遍或两遍以上,除上文讲到的一般要求外、阅改的重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即论点的锤炼、文章的结构、评论的分寸、文风的平实。关于论点的锤炼,主要在于明确和精当:明确是要使人看得明白真切,精当是精准和恰当。关于文章的结构:包含内容的处置是否合理,各部分的内在联系是否清晰,全文的整体性程度如何。关于评论的分寸:时下存在的普遍倾向,是过于拔高、夸大对研究对象的评价,这不仅会损害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而且也有损于作者的学风和学术形象,对此应特别予以重视。关于文风的平实:有些前文已经讲到,主要是戒浮华,戒夸张,戒浮词,戒虚饰,戒晦涩。做到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就好。我以为,帮助学生在年轻时养成此种学风和文风,使其终生受益,这也是导师的责任之一。
勿容讳言,每一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同行专家都会对论文存在的问题以至于错误,提出一些意见和改进的途径和方法,这对学生和导师来说都是一次提高。任何一个导师,都不是万能的,都存在知识上的盲区和理论上的不足,这种盲区和不足都会在论文答辩中或多或少暴露出来,经别人指出后得以自察自省,有所进步。这也是教学相长的一种表现形式。
四、关注评论与鉴识能力的提高
导师为指导学生完成学业所作的各方面的努力,可以取得两个方面的收获:一种收获是现实的,即学生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学位,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走上了工作岗位。另一种收获是潜在的,即他们在完成学业过程中初步培养起来的基本素质和研究能力,而这种潜在的收获不会因学业的结束而结束,它会在伴随着学生走向新的生活历程而逐步发挥出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我在指导学生完成学业过程中,要求学生注意提高自己的评论能力和鉴识能力,这既有益于完成当前的学业,也是在为学生完成学业后寻求新的发展做必要的准备。基于此,我向学生推荐我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①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鼓励他们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用以提高对于评论或批评的认识;同时,提倡学生在读学位期间积极参与史学评论活动,不断提高鉴识能力,这也是继承、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一个方面。
中国古代有史学批评的传统,向学生讲授这一传统,揭示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一,可以提高他们关注、参与史学批评的自觉和热情。比如,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史记》而撰《汉书》,范晔批评《汉书》而撰《后汉书》,唐太宗批评十八家晋史而命史臣撰成新《晋书》,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批评南北朝所修正史而撰《南史》《北史》等。又如,郑樵批评“断代为史”而撰《通志》,马端临批评《通典》而撰《文献通考》,明人王圻批评《文献通考》而撰《续文献通考》等。值得注意的是,每每在批评中撰成新著,其间或多或少都包含着理论上的思考和创见。讲述这些,不仅有助于学生从一个方面对史学发展规律有所认识,对史学批评推动史学理论发展之重要作用的认识,而且激发起学生们对古代史学批评之关注和对当代史学批评之参与的热情。我为我的学生选择史学批评类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方向感到高兴,也因他们能参与当前的史学批评而受到鼓舞。
我也常常向学生转述白寿彝先生有关书评的见解:“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学风:一部著作出版了,有人关心,有人过问。我们研究史学史的人,更要关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自己的提高,而且对作者和广大读者都有益处。”显然,这是从“一种学风”来看待书评的意义和价值。由此我们得到一个启发,即史学工作者的工作,不只是想到自己如何如何,同时要想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对于社会有什么影响和意义。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齐世荣先生所著《史料五讲》一书,我将此书引入课堂,和几位同学共同研讨,并要求大家在研讨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写出书评。这些书评在几家杂志发表,①这些书评包含瞿林东《讲史料论治学——读齐世荣先生〈史料五讲〉书后》、李凯《史料扩充与历史认知——读齐世荣先生〈史料五讲〉的一点认识》、朱露川《博览善择举重明轻——读齐世荣先生〈史料五讲〉的几点启示》,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王姝《史料与学风——齐世荣〈史料五讲〉的启示》,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胡祥琴《私家记载与历史真相——齐世荣〈史料五讲〉读后》,载《中国国书评论》2015年第8期。增强了学生们撰写书评的信心。
对于如何撰写书评,我也引用白先生的见解和学生们共同讨论、理解,就是:对所评之书赞扬,但不捧场;批评,决不挑眼。②参见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27页。这是我们努力遵循的原则。我也结合自己写书评的体会,跟同学讲一些心得,供他们参考。第一,写书评可以评论全书,也可以评其中一个部分或某一个重要论点。比如评《楚图南著译选集》,用了作者的两句诗为题,即《俯仰无愧怍,天地自然宽》,评的是作者的胸襟和精神境界。③瞿林东:《俯仰无愧怍,天地自然宽——读〈楚图南著译选集〉》,《中国教育报》1993年4月14日。评何兹全先生的《读史集》,以《古代政治人物的肖像画》为题,在副题中标明评的是书中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一组文章。④瞿林东:《古代政治人物的肖像画——评〈读史集〉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历史教学》1985年第9期。第二,我也常向学生讲,写书评要仔细琢磨出一个好标题,努力做到准确而能吸引人,如评论一个朋友写的《司马迁评传》,考虑到此书着重是写司马迁的思想,就用了王安石的一句诗作主题《丹青难写是精神》;⑤瞿林东:《丹心难写是精神——读〈司马迁评传〉》,《人民日报》1986年11月7日。评一本名为《中国精神》的书,用了《民族“脊梁”启示录》作为主题。⑥瞿林东:《民族“脊梁”启示录——评〈中国精神〉》,《中国文化报》1991年11月10日。我之所以要讲这些,目的是使学生产生兴趣,同时感到这些并不止是理论上的讨论,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实践。
写书评是训练思维的过程,也是训练文字表述的过程,同时还是提高鉴识能力的过程。这是我要求、鼓励学生写书评的初衷。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史通·鉴识》篇,提出一个命题,叫做“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其深刻的理论意义,是指出了认识主体的不同而对于认识对象的看法、评价必有差异。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⑦刘知幾:《史通·鉴识》,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这几句话的理论魅力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记得有一次,当我分析这话的理论价值时,一个从不提问的学生突然提出问题:怎样判断不同主体对同一认识对象在结论上的差异?于是引发大家一番讨论。而这种讨论,正是我所希望的。其实刘知幾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关键还是在认识主体的学养,这就是“探赜索隐,致远钩深”,庶几近于认识对象的真谛。当然,初学写书评的人远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但让学生们懂得这个道理,树立这样一个追求的目标,把砥砺鉴识作为治学中的大事来看待,进而成为一种自觉的要求,则前途必有大的收获。这是因为,鉴识不仅表现在对评论对象的深刻认识,也表现在评论者在评论过程中,自身被评论对象激发出来的理性火花所照亮而得到新的提高。
史学评论既是同行间交流的纽带,也是史学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是史学工作者融入社会的途径之一,所以我希望学生关注评论,努力砥砺自己的鉴识。
五、关于史学自信
在指导学生完成学业的过程中,导师本身应有一种史学自信的精神,努力把史学的品格和使命传递到学生的思想深处,这是从根本的意义上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不论中外,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学有什么用?看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疑问,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开篇就谈到这个问题,认为此类发问“恰恰是针对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⑧〔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页。我的学生们也不止一人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们或许是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把问题提得很含蓄,比如,说“要是有人问到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对于此类问题的分析和阐述,可以说,贯穿于指导完成学业的全过程。综合起来,我向学生的阐述包含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要相信先贤和前辈的论述。在史学发展史上,司马迁、范晔、唐太宗、刘知幾、杜佑、司马光、顾炎武、王夫之、章学诚、梁启超、李大钊、郭沫若等,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视角指出史学的社会功用,他们说的都是真话,都是真知灼见,如对此有所怀疑,那就是怀疑者自身的问题了。
第二,治理国家需要史学。举例说来,秦亡汉兴之际,萧何特别重视搜集、保存秦朝的文书档案,这同后来他身居西汉相国,协助刘邦治理国家有极大的益处。①参见司马迁:《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唐太宗说的“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②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讲的也是史学与治国的问题。乾隆皇帝评价杜佑《通典》是“亦恢恢乎治国之良模”,③杜佑:《通典》附录一《御制重刻通典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13页。这同唐太宗所说,意甚相近。此类认识与经验,不胜枚举。
第三,史学具有教育人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反复向学生阐明,当人们分不清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的时候,一般都会说历史教育人,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等等。其实,历史已成为过去,它怎么教育人呢?它怎么会成为现实的“镜子”呢?如果人们认识了历史与史学的联系和区别,就一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历史虽已过去,但记述历史的史书可以告诉人们历史上的人和事,使后人受到教育,记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于是成为现实的“镜子”。在现实生活中,懂不懂这个道理,实则已成为是否真正重视史学的“试金石”之一。我向学生强调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感谢刘知幾,正是他用朴素的语言,在8世纪初就阐明了这个道理。他的经典论述是:“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④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0~281页。这段话深刻地表明,当历史已经逝去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史书而认识历史,并从中受到教益,所以史学也就成了“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我们应当大力宣扬这一论述,使今天的人们懂得: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进而真正拥有并运用历史所蕴含的种种宝藏,这是史学最重要的社会功用,正是这种功用确立了它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这就是我说的史学自信的几个方面。
此外,我还向学生们表明,我的史学自信还表现在另一个层面上,即史学的经世与求真的辩证统一关系。
有一种略带普遍性的看法,认为史学的目的只是求真,只是弄清历史真相;如若讲求经世,势必影响以至破坏求真。概而言之,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二者难得两全。
我和学生们讨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必须看到中国史学上存在一些负面现象,如刘知幾《史通·曲笔》篇所揭露的史官曲笔作史现象,如清代学者指出某某史书存在曲笔,等等。这些负面的东西既损害了史学的求真,也无益于史学的经世。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中国史学上,史家的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贯穿于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也贯穿于史学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大致勾勒这方面存在的两条线索,就会发现:这两条线索的结合所构成的史学发展脉络,本是中国史学的主流,这就是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结合。⑤参见瞿林东:《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既向学生阐明我的一些认识,也同他们共同探讨,概括说来,有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实现的,中国史学的发展亦不例外。刘知幾的《史通》一书,既有《直书》篇,也有《曲笔》篇,直书与曲笔同存在于史学之中,成为矛盾的统一体,反映事物的发展的辩证法则。
第二,观察中国史学上的此类现象,既要关注一时一事的发生及其影响,更要关注事物的全局,尤其是事物发展的趋势及主流,不要因有支流的存在而模糊了对主流的认识。
第三,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真实的事物是有生命力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而虚假的东西,迟早都会暴露、败亡。中国史学史上那些曲笔作史和阻碍史学进步的行为,一再遭到时人和后人的揭露、唾弃,正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直书是主流,追求信史目标是大趋势。而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
我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史学自信,是希望真正确立对于史学这个专业的神圣感及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自身有了这种自信,才能更好地去从事与史学有关的各种工作、各项事业,把这种自信传递给更多的人,使史学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功用,以促进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
作为一个教师,指导学生完成学业,是尽其天职;对于学生来说,这个过程或许就是人生与事业的奠基。兹事重大,勿容置疑。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导师,都会选择适用于自己也适用于学生们的方法,做好这件事情。我所做的这些,是在摸索中前行的一点心得。《礼记》中有这样的话:“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①《礼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8~199页。先贤所论,至理名言,乃以“教学相长”标目,以明景仰先贤之心志,并非以此自诩。现应《历史教学》之约,发表此文,意在与同道切磋,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Teaching Benefits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on Educating Graduate Students
Tutor direction is a teacher’s vocation and the key procedure of graduate education.As a doctoral supervisor who has sponsored more than forty student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I have earned great harvest from my teaching experiences,such as:Leading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ir research territory on the basic of choosing their doctoral thesis topics;Helping them to discover problems from reading classical works;Enhancing their writing ability by assigning homework(book reviews);Building their spirit of confidence on History,and Showing them how to apply knowledge toservice the society.
Tutor Direction,Research Territory,Finding Problems,Reading Notes and Reviews,Spirit of Confidence on History
G64
B
0457-6241(2017)06-0003-09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2017-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