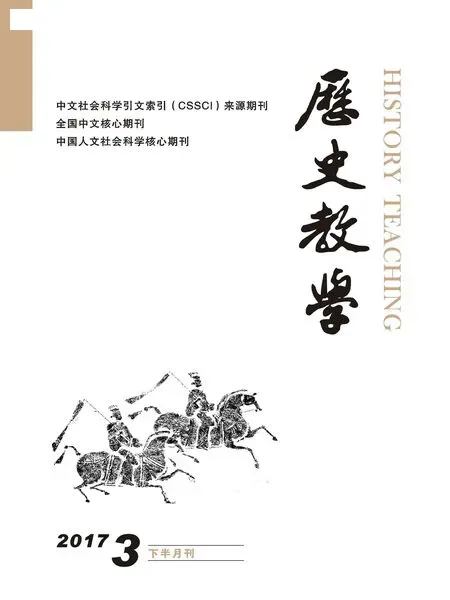1933~1938年英国公众舆论、和平运动与外交决策*
史林凡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70)
1933~1938年英国公众舆论、和平运动与外交决策*
史林凡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70)
20世纪30年代,英国一些典型舆论事件的真相是复杂的,不宜简单地被视为绥靖政策的民意基础。面对接踵而至的国际危机,活跃的英国和平运动出现严重分裂,并成为其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英国和平运动的主流拒绝“绥靖化”,但英国宪政体制的弊端和张伯伦内阁决策的高度封闭使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舆论呼声无法体现于外交政策中。
公众舆论,和平组织,和平运动,外交决策
因《公众舆论》一书闻名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言:
英美两国和平主义者的说教和活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他们导致本国军备建设落后于德国和日本。他们促生了绥靖政策。①Gregory C.Kennedy,“Britain’s Policy-Making Elite,the Naval Disarmament Puzzle,and Public Opinion,1927-1932”,Albion: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Vol.26,No.4,(Winter,1994),p.641.
“二战”后,中外不少学者认为30年代和平运动与英国绥靖政策的形成之间存在重要关联。一些舆论事件被视为民众反战的典型表现,如1933年春牛津大学俱乐部模拟辩论会的决议“本议院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和1933年秋东富勒姆补缺选举结果。②W.N.Medlicott,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Versailles,1919-I963,London,I968,p.xvii;F.S.Northedge,The Troubled Giant: Britain among the Great Powers,1916-1939,New York,1966,p.386;Keith Middlemasand John Barnes,Baldwin,a Biography,London,1969,pp.744~747.徐蓝:《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它们喧嚣一时,在学界却久有争议,其原委值得细心考辨。另外,在保守党政治家的回忆录里,1934年至1935年的“和平投票”也被指责为英国重整军备和对抗法西斯的绊脚石。③Philip Williamson and Edward Baldwin(eds).,Baldwain Papers,A Conservative Statesman,1908-194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351;Robert C.Self(eds.),The Austen Chamberlain Diary Letters;the correspondence of Sir Austen Chamberlain with his sisters Hilda and Ida,1916-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468.〔英〕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风云变幻,1914—1939》,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41页。国内虽有学者指出“和平投票”没能对英国外交产生实质性影响,④梁占军:《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1934-1935年英国“和平投票”的政治影响》,《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史林凡:《1934~1935年“和平投票”与英国政党政治》,《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但仍未充分揭示其体制性根源。
论及30年代英国和平运动失败的原因时,下述看法颇具代表性:当时的和平主义者是空想家,严重脱离社会实际;他们的和平主义信仰与公民权利义务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处于两难选择之中。⑤熊伟民:《30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事实上,不少维护集体安全制度的主张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只可惜被英国政府弃之不用;当国家面临反侵略战争,并非所有和平主义者都会遇到所谓的两难选择,只有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会为了信仰而拒绝履行军事义务。
在此,一些关键问题需更为明确地回答:30年代英国和平组织是否都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若不是,谁是和平运动的主流?代表着民意的主流,它却无力在实质上影响外交决策,体制性原因何在?本文拟围绕公众舆论的复杂性、和平运动的分裂和政府决策的封闭性作一简略探讨。
一、复杂的公众舆论
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有时表达的是多数派的观点,有时却是大事声张的少数派观点,但它很少是全体公众的共同看法。30年代有两种性质迥异的反战舆论:一种是群众自发的对于战争的厌恶和恐惧;另一种是英国的《泰晤士报》《观察家报》,法国的《法兰西行动报》《巴黎回声报》之类的报刊,它们实际上是右派的喉舌,用战争的恐怖恫吓人民,为推行绥靖政策制造舆论。①齐世荣:《齐世荣史学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公众舆论缺乏一致性,常相互冲突,且变动不居,易大幅摆动。因此,严格讲,公众舆论是特定时间和条件下部分公众针对某一具体问题所表达出来的看法。不过,即便如此界定,精确测评公众舆论依然困难,其原因还在于测评手段本身的局限性。当那些未经表达但确实存在于公众心中的看法以行动而非言语体现出来,且这样做的公众足够多时,舆论专家事前的预测很可能出现大偏差。尽管公众舆论有这些特质,但在它被高度重视甚至扭曲的30年代,和平组织、英国政府并未减少对其进行塑造和管控的努力。
首先,1933年2月9日牛津大学俱乐部“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决议与其说反映了民众对战争的忧恐,倒不如说反映了他们对“国王和国家”的不信任、对“一战”正义性质的幻灭感和经济大危机中英国社会空前的怨怼。
本质上,这场模拟英国下院议事规程而举行的辩论会是民众在与政府争夺重构战争记忆的主导权。“一战”中,“为了国王和国家”曾是英国战争动员的响亮口号。1920年,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无名勇士墓落成,墓志铭继续掩盖“一战”是帝国主义之间争霸战的实质,吹捧英国将士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和国家,为了所爱之人的家园和土地,为了正义的神圣事业和全世界的自由。”②Samuel Hynes,A War Imagined:the First World War and English Culture,London:Bodley Head,1990,p.280.但“一战”后长期的经济低迷、大量的失业工人、失望的退伍军人以及动荡的局势使人们逐渐清醒。1930年,在伊尔福德(Ilford)地区的集会上,有人高声演讲:
无论是在停战纪念日里,还是在各种俱乐部里,抑或读报时,只要听到和看到“大战光荣”的论调或字眼,我都会说上一句:“遭天谴的光荣!”③Mark Connelly,The Great War,Memory and Ritual:Commemoration in the City and East London,1916-1939,Suffolk:St.Edmundsbury Press,2002,p.182.
此言一出,掌声一片。在1934年停战纪念日之夜,格林上尉的谴责更为严厉:
1914年,我和数以千计的青年人,情绪高昂,怀着援救可怜的比利时的信念奔赴战场。今天,我们清醒了很多。这都是谎言。更糟的是,我们当时竟然相信了。我们被有权有势的人玩弄了。④Mark Connelly,The Great War,Memory and Ritual:Commemoration in the City and East London,1916-1939,p.182.
以此背景看,“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决议对英国政府掩盖“一战”根源和性质的行为着实是个打击。执掌权柄的保守党政要不但没有自省,反而曲解民众的愤懑和悔悟之辞,将之标榜为绥靖政策的民意基础。温斯顿·丘吉尔虽是绥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但他对“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评论同样暴露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狭隘和自私。丘吉尔认为这个决议“真够丢脸”,使其他国家“深深感到英国已萎靡不振”了。⑤〔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上部第一分册),吴万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25页。在他看来,“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就是不爱国,就是失去了战斗意志。
逻辑上,“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人不一定是反战者,他有可能为了抗击法西斯、不经国家组织甚至违反政府法令而自愿投入战斗。事实上,“萎靡不振”的是英国统治阶级而非那些明辨善恶的民众。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次年2月,英国加入不干涉委员会,明令禁止本国民众参战。但仍有2500名英国人参加国际纵队,并在1936年12月组成英国营,舍生忘死,支持进步的西班牙共和国。他们来自英国各个行业和阶层,不乏社会上层人士。两年内“有1762人受伤,562人阵亡,营长换了11任,政委换了10任。……他们的参战动机其实很简单:不满本国政府的绥靖政策,为了打击法西斯,阻止即将爆发的欧洲大战。幸存者的大量访谈和回忆录足以证明这一点”。⑥赵国新:《英国志愿军与西班牙内战》,《国际论坛》2014年第1期。他们投身西班牙战场,自然“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
据马丁·西代尔(Martin Ceadel)考证,牛津大学俱乐部的模拟辩论本不值得人们关注,只是因为英国报纸盈利的需要才被炒成了重大新闻,进而为解释英国无力约束希特勒提供了简明易懂的辩词;丘吉尔之所以要编造这份决议对希特勒产生重大影响的神话,是为了败坏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声誉。1933年,著名作家和讲师西里尔·乔德(Cyril Joad)的演讲很有煽动性,使“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动议以275票赞成、153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但此后,牛津大学俱乐部多数成员的态度渐有变化。1938年11月10日,初衷不改的乔德再来辩论时,“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时而有正当理由”的动议却得到176张赞成票,反对票只有145张。①Martin Ceadel,“The‘King and Country’Debate,1933:Student Politics,Pacifism and the Dictators”,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 22,No.2(Jun.,1979),pp.418~422.可见,用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决议去指代30年代英国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民意难免以偏概全;拿它去推测1935年后英国绥靖政策的民意基础,会有刻舟求剑的风险。
其次,1933年秋东富勒姆选区的补缺选举结果被不少学者用作英国民众厌战的证据,这与首相鲍尔温的狡辩不无关系。1936年11月12日,他在下院演讲,认为当年这个席位被工党夺去,“完全是因为和平主义者”;他还说,“当时富勒姆选区表达出来的情绪在全国很普遍”,而且随后两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使英国政府得不到重整军备的民意授权。②House of Commons,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Series5,Vol.317,London:H.M.S.O.,1936,p.1144.但实情并非如此。
1933年,东富勒姆的议席只是保守党力保不失的40个席位之一。从全国范围看,不仅大多数议席被保守党重新获得,而且有些选区的保守党候选人恰因支持重整军备而当选。③Martin Pugh,State and Society:British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1870-1992,London:Edward Arnold,1999,p.209.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东富勒姆地区的席位都处在边缘地带,没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时任财政大臣的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有家书可佐证:
富勒姆让首相非常悲伤。但我得承认,此事丝毫没有让我辗转反侧。媒体都把失败归咎于住房问题和关于战争的谎言。无疑,这都是导致保守党失败的因素。我有一位朋友曾在富勒姆和一位街头演讲者聊天。他告诉我真正的攻击是财产调查。④Iain Macleod,Neville Chamberlain,London:Muller,1961,p.179.
英国学者理查德·海勒(Richard Heller)研究了补缺选举的全过程,认为把东富勒姆选举描述成和平主义者的选举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选民之所以抛弃保守党而选择工党,是因为:
在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上,工党给出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对自由主义者和独立选民来说,这可能意味裁军。但对大多数富勒姆选民而言,这几乎肯定地意味着住房、食品价格和就业。⑤Richard Heller,“East Fulham Revisited”,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6,No.3(1971),p.196.
也就是说,保守党败在了民生问题上,而非败在提倡重整军备上。1936年,鲍尔温在下院重提三年前东富勒姆地区的选举结果时,1933年当选的工党议员已经离开下院了。但他为何要重提旧事?用意很明显:掩盖保守党败选的真正原因时不用担心遭到质疑和反对,并让选民充当重整军备不力的替罪羊。
再次,以1934至1935年的“和平投票”为例,来论证和平运动为绥靖政策的形成奠定了民意基础,也颇为不妥。“和平投票”的主要组织者是国联协会(League of Nations Union),其宗旨是力促英国民众衷心支持国联,力促英国政府按《国联盟约》处理外事。但30年代初,因远东危机、日本德国相继退出国联和世界裁军大会屡陷僵局,国联权威受挫,声誉日衰。由于害怕履行盟约义务,英国时常绕开国联,与其他大国私下寻求妥协。此间,对国联感到失望的民众越来越多。国联协会(LNU)会员数量从1932年开始减少,财政收入也从1932年的399931英镑锐减至1933年的29975英镑。⑥J.A.Thompson,“The‘Peace Ballot’and the‘Rainbow’Controversy”,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20,No.2(Spring, 1981),p.151.
国联协会(LNU)试图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唤起民众对国联的支持,改善自身财政状况,并通过舆论来胁迫英国政府改变政策。它的宣传导向性很明显,使“和平投票”更像一场社会动员,而非科学的民意测验,就连其领导人菲利普·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也承认这一点。⑦Philip Noel-Baker,The First World Disarmament Conference 1932-1933 and Why It Failed,Oxford:Pergamon Press,1979,p.138.为了鼓动民众,国联协会(LNU)没有考虑抽样方面的事情。填写问卷并及时交回的都是那些愿意合作的民众。反对者或没有收到问卷,或拒绝作答。所以,投票结果更多反映的是国联协会(LNU)的宣传成效,并非对公众舆论的准确评测。另外,从技术角度看,现代民意测验专家总要把偏见的影响减至最小。1934年时,相对客观的民意测验手段尚处于萌芽状态,直到1937年才初步在英国运用。因此,把“和平投票”视为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或民意调查,①Martin Ceadel,“The First British Referendum:The Peace Ballot,1934-5”,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95,no.377,Oct., 1980.梁占军:《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1934-1935年英国“和平投票”的政治影响》,《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有拔高其意义之嫌。
“二战”后,有政要说30年代英国政府在对外强硬之前,一直在等待舆论转向。②Martin Pugh,State and Society:British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1870-1992,p.208.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和平投票”历经15个月,从宣传的成效看,约有1163万人投票,95.9%的受访者赞成英国留在国联内,86.8%的受访者赞成联合起来对侵略者进行经济及非军事手段的制裁,58.7%的受访者赞成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制止侵略。在军备问题上,90.6%的受访者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现全面裁军,82.5%的受访者赞成根据“国际协定”来实现全面废除各国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③LNU,Headway,Vol.17,No.7(Jul.,1935),p.122.也就是说,在国际协定缺失的情况下,他们不要求英国单方面裁军。
二、分裂的和平运动
从最基本的含义上讲,和平运动是维护和平、消弭冲突、制止战争的社会运动,其参加者是任何以此为目标的个人、团体或机构。但在维和止战的方式上,英国和平运动一直是分裂的。很多人认为反击战争必须使用物质力量,包括最后使用军事力量。他们拥护《国联盟约》和集体安全制度,加入或支持国联协会(LNU),赞成强力制裁和反侵略战争,是“可战派”,如丘吉尔和工党领导人艾德礼。与之相对,有数量可观的英国人信奉古老的和平理念,即基于宗教和伦理等方面的考虑,在任何情况下都谴责和反对战争,而不考虑战争的性质和目的。面对危机和冲突,他们放弃制裁和反击,过于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以致不断妥协退让,是“弃战派”,如政治家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泰晤士报》主编杰弗里·道森(Geoffrey Dawson)以及和平誓约联盟(Peace Pledge Union)。
20世纪20年代,两派之间的分歧潜而不显。但到30年代,面对接踵而至的国际危机,他们的反应如此不同,以致再也不能联合起来,彼此之间开始争夺会员、资金和听众。日本侵华、意埃战争和西班牙内战使国联的性质、功能成为两派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像过去那样,让国联仅仅作为国际合作和谈判的平台?还是在国际舆论之外,让国联拥有更多执行工具,比如强力制裁和武装力量,从而真正地维护世界和平?
鉴于“一战”后轰炸机给民众留下的巨大心理阴影,国联协会(LNU)领导人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es)在1932年创建“新联盟”(NewCommonwealth),专门推动国联拥有空军。1934年,“保卫和平国际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新联盟”提交了建立国际空军的详细方案。在当时英国众多组建国际空军的计划中,影响最大的或许是菲利普·诺埃尔—贝克于1934年提出的构想。他不仅是英国工党重要领导人之一,曾和塞西尔勋爵一起参加国联的创建工作,而且长期担任国联协会(LNU)执行委员。在《挑战死亡》这本文集里,他认为国际空军警察部队(International Air Police Force)应由国联来招募、组建、装备、训练和提供薪水,完全效忠于国联。他还详细规划了这支部队的主要活动区域,指挥官选任,飞行员招募、薪水和退休金等事项。④Brett Holman,“World Police for World Peace:British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Threat of a Knock-out Blow from the Air,1919-1945”,War In History,Vol.17,No.3(Jun.,2010),p.322.
另外,工党领导人艾德礼曾在日本和德国退出国联后说:
如果法西斯国家愿意待在国联之外,那就待在外边吧。但国联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队来抗击任何侵略企图。⑤Waqar H.Zaidi,“Aviation WillEither Destroyor Save Our Civilization:Proposalsfor the InternationalControlofAviation,1920-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46,No.1(Jan.,2011),p.163.
军事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B.H. Liddell Hart)从1935年开始支持组建国际部队,并主张用现代化设备武装起来。1936年,工党重申了上年大选承诺,把推动空军的国际共管作为本党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1937年10月,在国联协会(LNU)全体会员大会上,塞西尔勋爵说:“维护和平需要执行国际法,而国际法需要切实的制裁力量来支撑”。①LNU,Headway,Vol.19,No.11(Nov.,1937),p.212.在他眼中,“切实的制裁力量”除了国联成员国的武装力量外,还包括国联指挥的国际空军。1938年,巴黎和平集会上,大卫·戴维斯、菲利普·诺埃尔—贝克和法国政治家皮埃尔·科特(PierreCot)甚至要组建志愿军,与日本空军作战,使中国大城市免遭轰炸。
30年代后期,扩张最快的民间团体或许是“和平誓约联盟”(Peace Pledge Union)。作为“弃战派”的代表,它的创始者是安立甘教牧师迪克·谢泼德(Dick Sheppard),在1936年5月22日举行第一次集会。1937年10月,谢泼德病逝后,已经辞去工党职务两年多的“弃战派”显贵乔治·兰斯伯里开始担任主席;而这一年,它从12万人那里获得了不参加未来战争的保证。到1939年,它的会员已增至13万人,地方分会在理论上有1150个。②David C.Lukowitz,“British Pacifistsand Appeasement:The Peace Pledge Un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9,No.1 (Jan.,1974),p.116.
谈及和平问题,和平誓约联盟(PPU)的出发点不是具体的外交政策或国际事件,而是必须谴责战争的神圣原则。它认为国联的任务主要是防止战争爆发,而非在战争爆发后惩罚肇事者。机关报《和平新闻》(Peace News)上多数尖锐的批评都指向国联,指责集体安全制度既不道德,也不实用:
所谓不道德,是因为集体安全不过是战争的委婉说法。所谓不实用,是因为在这个空战主导战争和到处都是心胸狭隘的民族的时代里,任何基于利他原则而进行的真诚合作都不可能发生。③David C.Lukowitz,“British Pacifistsand Appeasement:The Peace Pledge Union”,p.119.
批评者甚至反对经济制裁,其理由是经济制裁会带来饥荒,受害者是那些无辜的人,而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很少挨饿。且希望加强国联在道义上的威信,但强烈反对国联拥有制裁的物质力量。
1937年4月,乔治·兰斯伯里以私人身份拜会希特勒。两个半小时的会谈后,他认为德国试图发动欧洲战争的说法是十分荒谬愚蠢的。7月拜会墨索里尼后,他赞同意大利对西班牙叛军的支持是在捍卫宗教和文明。正是这种言行为绥靖政策提供了所谓的民意基础。为了和平,“可战派”已选择物质力量去践行集体安全制度;而“弃战派”仍迷信道义,反对制裁,谴责正义反击,逐渐与绥靖外交合流。
和平组织之间稀薄的黏合剂是维和止战的共同愿望,舆论是它们手中的主要武器。但由于理念与手段上的重大分歧,英国和平运动已然分裂,不能形成足够的舆论压力来改变政府政策。同时,英国政府垄断大部分媒体资源,成功地对和平组织进行舆论压制和利用,放大少数人的声音,使其成为绥靖政策的重要推手。④史林凡:《1936~1938年英国政府的舆论管控》,《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4期。
不过,即便英国和平组织团结一致,仍无望在实质上改变绥靖政策。诚然,“一战”后英国选民数量剧增,使任何党派都不得不争取民意。但大选时机由政府决定,且大选过后选民就无力再约束在下院占多数席位的执政党。1935年6月,“和平投票”结果公布,拥护国联集体安全制度的舆论约束了保守党,使其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拉拢意大利。10月3日,墨索里尼正式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为了做到既赢得大选又不妨碍绥靖意大利,保守党说服英王于10月25日提前重开大选。大选中,保守党假装顺应民意,高举国联大旗,执政后就背信弃义,继续绥靖法西斯。更糟的是,此后直到1940年5月绥靖政策因德国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而彻底破产,选民再无机会用选票影响政府决策。
30年代末,以和平誓约联盟(PPU)为代表的部分和平组织绥靖化了,但它们是和平运动的主流吗?显然不是。规模上,和平誓约联盟(PPU)会员数量到1939年达到13万人的峰值,地方分会在理论上有1150个;而早在30年代初,就已有百余万民众加入过国联协会(LNU);至1936年,付费会员仍约36万,地方分会3000多个。退一步讲,即便和平誓约联盟(PPU)是“弃战派”里最小的组织,国联协会(LNU)是“可战派”里最大的组织,单个对比有失公允,那么以整体论,最能代表和平运动与民众态度的仍是“可战派”。
关于西班牙内战,1937年1月,英国舆情局(British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的民调显示只有14%的受访者把佛朗哥叛军政权视为合法,86%的受访者持否定意见。1938年3月和10月的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仅有7%的受访者支持佛朗哥。到1939年1月,西班牙共和国的巴塞罗那政府在受访者中依然有71%的支持率,叛军政府只有10%。西班牙共和国的高支持率还反映在人道援助的数量上。至1938年中期,英国国内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组织募集了31.73万英镑,支持佛朗哥叛军的组织只募集到了约2.4万英镑。①Hugo García,The Truth about Spain:Mobilizing British Public Opinion,1936-1939,Toronto:Sussex Academic Press,2010,p.203.
关于张伯伦的外交政策,1938年2月英国舆情局的民调结果是赞成者仅占26%,反对者多达58%,不置可否者为16%。②Anthony Adamthwaite,“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1937-1938”,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18,No.2 (Apr.,1983),p.291.9月30日《慕尼黑协定》达成后,英国很多民众一度陶醉于持久和平的幻觉中,但他们很快清醒了。10月19日,著名的盖勒普民意调查公司(Gallup Poll)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份报告:
78%的英国人赞成立即进行全国范围的普查,登记那些能在战时履行军事或民用职责的公民;80%的英国人赞成增加军备开支;93%的英国人不相信希特勒在欧洲已无更多领土野心的承诺。英国人对纳粹政权的性质越来越清楚,必然选择抵抗而非绥靖,即使这样做会带来战争。③Robert J.Wybrow,Britain Speaks Out,1937-87:A Social History as Seen through the Gallup Data,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9,p.5.
三、封闭的外交决策
20世纪里,英国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使首相的权力不可避免地扩张。首相的主张因本党在下院占有多数席位而总能获得通过。他们投身于外交事务,博取公众好感,俨然成了首席外交大臣。在常规外事决策中,英国政府便宜行事的权力很大,而首相倾向于垄断这种权力。不过,首相虽有很大的外事处置权,却并不能像独裁者那样一意孤行。更准确地说,首相决策时的封闭性是有选择的。他会倾听甚至主动寻求支持性意见,同时对批评性意见置若罔闻。
长期执掌权柄的鲍尔温虽对内政的关注多于外交,但也懂得如何减少外交决策时的“杂音”。国防大臣(Minister for Coordination of Defense)一职于1936年初设时,以强硬著称的丘吉尔被多数人视为不二人选,丘吉尔也为它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终出任的却是托马斯·英斯基普(Thomas Inskip),以致非议纷纷。有评论道:“这是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让自己的爱马当执政官以来最具嘲讽意味的任命。”④Graham Stewart,Burying Caesar:Churchill,Chamberlai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Tory Party,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9, p.487.1937年5月鲍尔温退休,未经大选而继任首相的张伯伦决心把英德关系的处置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他对“克莱夫登集团”(Cliveden Set)⑤关于克莱夫登集团,国内外代表性的著作有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辟有专章。Norman Rose,The Cliveden Set:Portrait of an Exclusive Fraternity,London:Jonathan Cape,2000.作者认为“克莱夫登集团”不是被“揭发出来”的,而是被“发明出来”。对其历史作用,作者多有辩词。青睐有加。它得名于白金汉郡的克莱夫登庄园。园主阿斯特夫妇是英国名流。这个政治性沙龙纠集了大量绥靖主义者:
主要成员有菲利普·洛西恩勋爵、《泰晤士报》主编杰弗里·道森、副主编罗伯特·巴林顿-沃德、《观察家报》主编詹姆斯·加文以及“无处不在”的托马斯·琼斯,再加上主人阿斯特夫妇。此外,劳合-乔治、鲍尔温、张伯伦、哈利法克斯等政界要人也都是克莱夫登的常客。他们利用与首相、大臣的亲密关系,往往于觥筹交错或悠然散步之际,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提出种种建议和要求。⑥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第27~28、48页。⑦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第27~28、48页。
1937年底,在科克伯恩的揭露之下,这个活跃的小团体开始为更多人知晓。次年2月,在海德公园的集会上,工党议员巴恩斯激烈指责道:“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再由唐宁街的内阁制定,却在阿斯特夫人的克莱夫登庄园确定。”⑦基于对英国统治阶级的了解,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极力结交那些能影响外交决策的精英,如对《泰晤士报》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洛西恩勋爵(Lord Lothian);又如担当鲍尔温秘密联络人的托马斯·琼斯(Thomas Johns),此人曾用1936年的大部分时间,试图促成鲍尔温与希特勒会晤。同时,利用英国政界精英对《凡尔赛和约》的偏见,利用张伯伦对国内媒体的管控,德国外事部门的针对性宣传获得巨大成效。英国国内“存在反对德国的宣传运动,但效果不佳。因为参加宣传运动的大部分人处在精英阶层之外,或在精英阶层中被边缘化,他们没有建立起与核心精英的联络”。①CharlesChappius,“The British Foreign Policy-Making Elite”,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29,No.1(Jan.,1967),p.139.于是,1938月3月12日,当德军开进奥地利时,英国广播公司却告诉民众:里宾特洛甫受到英王接见,且随后与张伯伦共进午餐!
张伯伦不信任外交部门,时常通过私人渠道与外国政要交流。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英国试图与意大利达成某种协定。张伯伦频频利用私人渠道接触意大利驻英大使格兰迪,还曾用格兰迪的观点当面反驳自己的外交大臣艾登!②D.C.Watt,“Some Post-War British Memoirsand Pre-War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55(1),p.108.由于支持国联、反对绥靖,艾登渐被孤立,终致辞职。张伯伦去罗马会见墨索里尼的决定在1938年10月末才被告知外交部官员,直到11月30日才被通知给内阁。在1939年2月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权这件事上,张伯伦从年初就开始催促阁员这么做。在得到阁员们原则性同意后,他就按照自己的主意采取了行动。外交政策委员会刚准备提出反对意见,就被张伯伦规避了。
多数时候,外交决策都在内阁“四人小圈子”中完成。它由张伯伦、哈利法克斯、西蒙和霍尔组成。英斯基普偶尔被允许参与进来,因为他是真正容易被张伯伦控制的国防大臣。1938年9月,张伯伦在两个星期内三次飞往德国。无论是15日在伯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rten),还是22日在哥德斯堡(Godesberg),张伯伦完全没有表达出内阁成员希望他表达的主张。但正是在这些主张的基础上,内阁成员才同意他飞往德国。张伯伦从伯希特斯加登回来后,海军大臣达夫·库珀(Duff Cooper)记述道:
首相的方案如此成功地拟定出来,且如此详细,但事先从未向我提起过。……希特勒谈起民族自决,并问首相是否接受这个原则。……首相看起来希望我们停止讨论,赶快接受。因为他认为时间已经很紧迫了。③John JuliusNorwich,The Duff Cooper Diaries,London:Weidenfeld&Nicolson,2005,p.260.
张伯伦第三次飞往德国后,不仅库珀不清楚张伯伦的新方案,甚至“四人小圈子”的其他三位成员也不明白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英国史学家瓦特(Donald Cameron Watt)研究他们的回忆录时指出,在相关描述中,张伯伦的个人责任逐渐变得具有压倒性了。④D.C.Watt,“Some Post-War British Memoirsand Pre-War Foreign Policy”,p.109.参与9月30日慕尼黑谈判的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伊冯·克帕塔里克(Ivone Kirkpatrick)写道:
我从未弄明白张伯伦先生的脑海里到底有什么想法。谈判期间,他独断专行;在我的记忆里,采取行动前,他并未提示任何人。⑤Ivone Kirkpatrick,The Inner Circle:Memoirs of Ivone Kirkpatrick,London:Macmillan,1959,p.130.
英国外交决策的封闭性不仅体现在政府内部,还体现在政治精英对社会异见的屏蔽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本党在议会中的优势和严格的党纪。1938年9月,张伯伦向同僚坦露心声:
(他认为)当前时期议会中的争论会摧毁非常微妙的外事谈判。……实际上,在政府做出决定后,议会才会得到通报。⑥Anthony Adamthwaite,“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1937-1938”,p.289.
例如,德国对犹太人的政策早已激起很多英国人的反感。到1938年10月,英国舆情局的民意调查显示85%的英国人反对把“一战”前的殖民地还给德国,其中又有78%的英国人愿意为此参战。⑦British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Public Opinion Survey”,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4,No.1(Mar.,1940),p.78.但在11月13日下院里,张伯伦拒绝透露自己是否准备和希特勒讨论托管领土的事务。⑧Norman and Jeanne MacKenzie,The Diaries of Beatrice Webb,Lond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2000,p.563.可见,在他眼里,舆论或可用来装点外交政策,但决不能成为政府决策的干扰因素。
30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是公众普遍参与的社会运动,其高涨的原因除了连续不断的国际危机让他们对和平深感忧虑外,还在于大量和平组织与英国政府之间展开了对舆论主导权的争夺。当分散多样且变动不居的公众舆论使历史真相变得扑朔迷离时,我们更应该避免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眼光去凝视历史长河表层的浪花。
既然1933年春醒悟的英国公众不再把“国王和国家”视为正义的必然代表,那么是否“为国王和国家而战”也就不宜用作判断30年代英国民众是否反对正义战争的标准,除非“国王和国家”停止掩饰“一战”的性质和根源。1933年秋保守党在东富勒姆选区失败的原因也不是鲍尔温在1936年声称的和平主义。无论从国联协会(LNU)的宗旨看,还是从鼓动民众的成效看,1934年至1935年举行的“和平投票”都与英国政府抛弃国联、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相反。它虽仍是英国最大的和平组织,代表着反对绥靖政策的舆论主流,但在1936年后,其执行委员会里的保守党政要多数已退会,从而无法提前获悉外事动向,更无力影响英国外交决策。
从维和止战的目标看,30年代英国和平运动确实失败了。它之失败,一方面是因为严重分裂,且其主流“可战派”拒绝“绥靖化”,进而被排斥于决策圈外;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宪政体制的弊端和张伯伦内阁决策的高度封闭,主战的公众舆论未能上升为英国的国家意志,从而在客观上刺激法西斯国家的野心继续膨胀,加速了“二战”战火从亚洲蔓延到欧洲。
British Public Opinion,Peace Movement and Foreign Policy-Making from 1933 to 1938
The truths of typical public opinion events in 1930s’Britain were complicated and should not been treated as the social roots ofAppeasement policy.Facingthe successive international crises, the robust peace movement in Britain had deep divisions,which became the primary cause leadingit tofailure.The main stream ofBritish peace movement didn’t cater to the Appeasement policy,nevertheless its cries for resisting the fascist aggression got no echoes from the foreign policy-making elites,as the result of British constitutional defects and exclusiveness of Neville Chamberlain’s cabinet.
Public Opinion,Peace Organization,Peace Movement,Foreign Policy-making
K15
A
0457-6241(2017)06-0065-08
史林凡,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现代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2017-01-1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13CSS02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