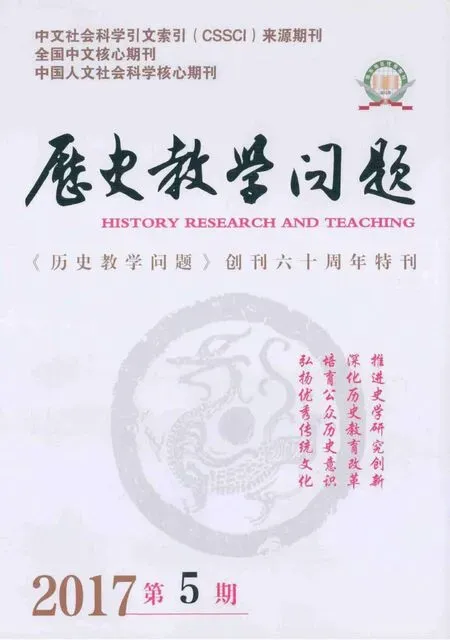史料·叙事·价值的“大问题”思辨
——知识论课程(TOK)与历史教学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蔡乐昶
史料·叙事·价值的“大问题”思辨
——知识论课程(TOK)与历史教学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蔡乐昶
国际文凭组织大学预科项目(IBDP)始于1968年。①国际文凭组织(IBO)全称为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迄今已有分别面向不同年龄段的PYP、MYP、DP、CP等四个项目。其中DP全称Diploma Programme,是大学预科项目,成立最早。国内迄今已有89所承办学校,在上海就有22所。根据IBDP的课程框架,知识论(TOK)、拓展论文和创新行动服务是核心课程,旨在形塑学生作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②徐鹏:《IB国际课程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5页。其中唯一的课堂教学课程是知识论,它围绕八个知识领域和八种认知方式,③八种认知方式分别是:理性(Reason)、情感(Emotion)、语言(Language)、感官(Sense)、信仰(Faith)、记忆(Memory)、想象(Imagination)、直觉(Intuition);八个知识领域分别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社会科学(Human Science)、数学(Math)、历史(History)、艺术(The Arts)、宗教(Religion)、伦理(Ethics)、本土知识系统(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提出并讨论“大问题”,④“大问题”概念来自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C.Solomon),即关涉哲学意义上知识本质的问题。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张卜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目标是培养学生批判思维的能力。
目前学界,关于IBDP,已有不少整体性介绍;⑤顾彬彬:《国际文凭项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李栋:《国际高中阶段课程探析——以IBDP为例》,《基础教育》2009年第8期,第39-42页。张久久:《高中国际课程与本土课程的兼容性探讨》,《教育观察》2014年第3期,第30-32页。徐鹏:《IB国际课程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关于TOK基本理念和考核方式,也有一些大致的梳理。⑥洪光磊:《知识论——一门求知者的新型课程》,《外国教育资料》1995年第5期,第9-18页。李晓波:《知识论课程的新进展》,《全球知识展望》2007年第4期,第37-40页。顾彬彬:《批判性思维与IB知识论课程》,《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69-71页。吴建京:《IB核心课程“认知论”(TOK)及其实施》,《课程教材》2015年第10期,第11-16页。杨少君:《国际文凭高中项目(IBDP)与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比较研究——以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学生评价为例》,云南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这些研究理清了背景信息,为深入讨论夯实了基础。那么,不同的知识领域各有哪些“大问题”?这些“大问题”如何引入与展开?它们对于国内的课程教学又有何借鉴意义?对这些问题,学界尚乏研究。本文拟结合三个版本的TOK教材,以历史这一知识领域为例,尝试作些讨论。
一、史 料
知识论,顾名思义,是关于知识的理论。在导言中,TOK教材开宗明义:我们接受某一知识,往往不是因为我们确定地“知道”,而是我们选择“相信”。⑦Wendy Heydorn and Susan Jesudason,Decoding 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Themes,Skills and Assess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2.因此,真正合理的相信应当建立在“充分的证据”这一基础上。⑧Wendy Heydorn and Susan Jesudason,Decoding 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Themes,Skills and Assessment,p.14.对历史学研究而言,这种证据就是史料。我国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之一是“史料实证”,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①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2016年,第4页。为培育这种素养,国内教材(如华师大版《高中历史》)不仅援引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②余伟民主编:《高中历史》第二分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还将原始史料与二手史料互证的方法融汇于行文中。但是,原始史料会有哪些主观因素?如何审视这些因素?如何在此基础上运用原始史料?TOK对这些问题做了讨论:
从个人角度看,原始史料如当事人口述、日记、回忆等是典型的个人知识。它与个体的“兴趣、期望和文化背景”相连结,③Richard van de Lagemaat,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Seco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426.无法脱离其情感、记忆和信仰等认知方式而存在。当这些个人知识被以文字形态记录下来时,两种障碍产生了:一来文字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还原个人知识;二来文字表述也是一重主观创作,情绪化表达和个人偏见不可能完全规避。
从社会角度看,原始史料的生成是社会背景的产物。如果政治权力等强势因素介入这种生成机制,那么情况会更加复杂。一方面,某些社会群体会失语,比如我们很难了解“希腊奴隶,或封建佃农,或阿兹特克武士如何看待这个世界”;④Richard van de Lagemaat,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Second Edition),p.426.另一方面,某些群体发声受到蓄意操纵和控制,比如斯大林时代为苏联人民“新生活”高唱颂歌的“纪实文学”。⑤Nicholas Alchin and Carolyn P.Henry,Theory of Knowledge(Third Edition),Oxford:Hodder Education,2014,p.301.
那该如何处理这种问题呢?TOK列举了两种处理模式:一是了解创作者及其创作背景。我们要问“书写者是谁?其可能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创作时间距事件发生有多久?”⑥Richard van de Lagemaat,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Second Edition),p.428.二是比较不同的原始史料,通过互相参证,寻找不同记录的错讹。
可史料的数量是否能够让史家如愿地驾驭呢?难度是显见的。在现代报刊传媒推广前,不同社会的记载都较有限。普遍来说,时代越早,原始史料留存越少——不少早期人类文明无论曾经多么辉煌,一旦缺乏史料遗存,只能空留猜想。而在现代通讯和传播技术普及后,甚至到互联网时代,信息体量呈指数级增长。如果历史学家想记述21世纪历史,势必要面对空前浩繁的史料。⑦Nicholas Alchin and Carolyn P.Henry,Theory of Knowledge(Third Edition),p.299.更关键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不单要尝试还原历史本相,还要承担解释历史因果的责任。⑧Richard van de Lagemaat,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Second Edition),p.428.为此,史家需建立有效的史料筛选系统,TOK的下一系列“大问题”也随之而来:有哪些筛选标准?该如何排序呢?进一步来说,史料一旦被筛选和排序,就已超越史料本身,进入新的命题——历史叙事。
二、叙 事
史家写作的第一步是筛选史料,叙事逻辑随之逐节展开,渐成清晰的因果链。本质上,“所有历史叙述都是对历史的解释”。历史教学即要培养学生“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⑨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第4页。但国内教材较少在方法论上系统地讨论如何达成这种素养,这也就留下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学界有哪些经典叙事?TOK在“历史”一章中做了梳理:
三个版本的教材基本都从个体和社会两个面向介绍经典叙事。一个著名的个体角度叙事是帕斯卡从“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不那么高”推导到“我们仍将受罗马统治”的逻辑。⑩Wendy Heydorn and Susan Jesudason,Decoding 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Themes,Skills and Assessment,p.78.这个逻辑试图揭示,历史是有大量变动不拘的偶然细节堆垒而成。个体论的另一位代表是A.J.P.泰勒,他认为“现代欧洲史可以根据三位伟人来书写:拿破仑、俾斯麦和列宁”。[11]Richard van de Lagemaat,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Second Edition),p.434.另一大家是R.G.柯林伍德,他认为推动历史演进的不是“外在因素”,而是“内在因素”,即每个历史人物行动时的内心动机——当他做出某一具体行为时,脑中的想法、情绪、信念等。他由此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①Nicholas Alchin and Carolyn P.Henry,Theory of Knowledge(Third Edition),p.308.
与之相对,不少经典叙事站在社会层面,建立宏大且强有力的因果逻辑。除了介绍在我国已被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之外,TOK还简述了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出的地理因素论。他认为,欧亚大陆文明能在大航海时代后主导世界历史进程,不能被归因为人种差异。应当看到,欧亚大陆可横向交流、具备多种大型可驯化动物和可栽培植物。这些结果导致欧亚大陆形成以农业为主导的集约型社会,而非洲大部、美洲和大洋洲本土文明在公元17世纪依然是渔猎采集形态。②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当然,宏大的历史决定论并非毫无问题。一个有力的反驳来自卡尔·波普尔:如果决定论成立,那未来自然可以预测,未来技术也就可以在当代被悉知和发现,这就改变了未来。③Richard van de Lagemaat,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Second Edition),p.437.TOK通过这些经典叙事的互相碰撞,引导学生思考:这些叙事解释力度和效度各不相同,该如何采信?教材提供了两个角度的反思:
其一,史家不具备“绝对理性”。史家的叙事和口述、回忆、日记相似,都不可能脱离其自身经验世界而单独存在。具备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学者会尽量减少主观因素干扰,避免恶习——比如有意无意地忽略不利于自身论证的史料。但是研究旨趣、史料搜集、国族情怀和阶级立场等因素会影响其历史叙事。④Richard van de Lagemaat,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Second Edition),pp.431-432.
其二,史家不可能真正地站在“上帝视角”。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出“站在月亮上看地球”会获得更客观也更宏观的角度。这个比喻固然指向超越自身桎梏的视野,但是史家终究不可能离开其所处背景。这个背景一方面是社会结构。比如大英帝国在全球鼎盛时期,对本土以外欧、亚、非、美、大洋各洲的文化和文明作了大规模研究。这种研究在客观上展现了多元文明的色彩,但本质是建立在权力话语下的主导体系:世界引领者有必要了解他者的过往,而非反之——阿兹特克已毁于殖民浪潮,无法保留本文明的记录,也就只能处于“被研究”的状态。在这个社会结构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种差异论会交相增长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了。
另一方面,史家离不开所处的时代大背景。比如亨利八世时代的史家不必然能看到国王与安妮·博林的婚姻会意味着天主教在英国的失败。⑤Nicholas Alchin and Carolyn P.Henry,Theory of Knowledge(Third Edition),p.304.又如1918年11月后,史家和人们一样,认为终结所有战争的“大战争(The Great War)”已经结束——而不必然能看到未来还将有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TOK教材援引E.H.卡尔的论述“历史是徜徉于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⑥Richard van de Lagemaat,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Second Edition),p.429.得出结论:我们以看待过去的眼光审视现在,反之亦然。⑦Nicholas Alchin and Carolyn P.Henry,Theory of Knowledge(Third Edition),p.306.
所以,当我们以“重要性”或其他方式来筛选,或为史料排序时,就已建立了历史叙事。但这种叙事不必然是客观且能够久经考验的。在面对任何一种叙事时,都需要探问:它生成于哪位史家?它处于何种社会结构?它处于何种时代背景?它如何对待不利于它的史料?当然,TOK的步伐没有就此停止。上述连续追问和缺乏唯一确定答案的讨论会动摇学生学习历史的根基,会让学生开始怀疑:如果历史叙事如此繁多且不可笃信,那为何还要学历史?这也进入到了最深层次的“大问题”——历史的价值。
三、价 值
国内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在解释历史的价值时提到了“家国情怀”。具体来说,对于本国,“形成对祖国的”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了解并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则是要了解“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⑧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第5页。这当然是种有力的回答,也与TOK所提倡的历史价值之一“帮助我们记忆并提供对国家与世界的认同”相吻合。⑨Wendy Heydorn and Susan Jesudason,Decoding 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Themes,Skills and Assessment,p.73.TOK做了一个类比:假设我们某天早晨,从床上睁眼的瞬间,完全忘记了过去的一切,那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当然是从身边、从房间里找到能证明我们过往的证据,①Richard van de Lagemaat,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Second Edition),p.418.换言之,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从个人类比到国家,如果一个国家不学习历史,那么就很难找到未来的去向。
除认同感之外,对于“历史的价值”这一“大问题”,TOK还给了另外两个角度。其一,学习历史能抵抗洗脑式宣传。比如在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政府控制下的日本、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庞大利益集团都试图以洗脑来形塑大批信众。面对强势权力,大量事实被隐匿、颠覆、甚至虚构。②苏联“大清洗”运动后,所有被斯大林排除的异己(如托洛茨基),都在照片中被“抹去”。TOK教材列举这些材料,提醒学生可信历史在对抗洗脑式宣传时的价值。Richard van de Lagemaat,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Second Edition),p.423.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社会层面缺乏信史,个人层面缺乏批判性的历史眼光,就容易被蒙蔽,盲从利益集团。
其二,学习历史能丰富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理解。国内外历史教学的核心都是人类的历史,因此研究对象是动态变迁中的人类社会,所有“大问题”的问题意识也都围绕“人”复杂的本质特性。TOK藉此说明,深入的历史学习,是要求我们必须从更多的面向来动态观察人类行为,远离简单粗暴的叙事——后者往往是以单向度决定论形式出现的“自我实现期望”,通过粗劣归因推导出某个必然未来,消解努力改变的主观能动性。③Richard van de Lagemaat,The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Ib Diploma(Second Edition),p.424.
以上多个角度可以都被统摄在“面向未来”理念下。TOK和国内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共享统一前提:学习历史不仅要了解过往,还要作用于现在和未来。TOK援引乔治·桑塔耶拿在《理性生活》中的观点“记不得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④Nicholas Alchin and Carolyn P.Henry,Theory of Knowledge(Third Edition),p.312.指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需要不断演进,就必须更加明智地面向未来。为此,就应当时刻警惕与反思脱离时代的现象,比如自诩“文明”的国家为何在20世纪依然会制造种族屠杀。学习历史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获得接近确据与真相的机会,藉此思考最核心的“大问题”:我们从何而来,又该去往何处?
不难发现,TOK课程不试图处理具体事实层面问题,而是通过“证据—反证据”“观点—反观点”“问题—反问题”的来回思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大问题”的能力。具体到“历史”这一章,其教学目标不是让学生了解某些历史人物、事件,也不试图建立具体的历史分析框架。它通过讨论“如何审视原始史料?如何看待历史叙事?如何理解历史的价值?”等历史学科的“大问题”来陶熔学生对于历史这一知识领域的本质关怀。它当然不是具体的历史课程,但能在史料、叙事和价值三个维度上加深学生的理解,也能为国内历史教学课程提供借鉴。
(责任编辑:李月琴)
蔡乐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邮编200241)。
——访陈嘉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