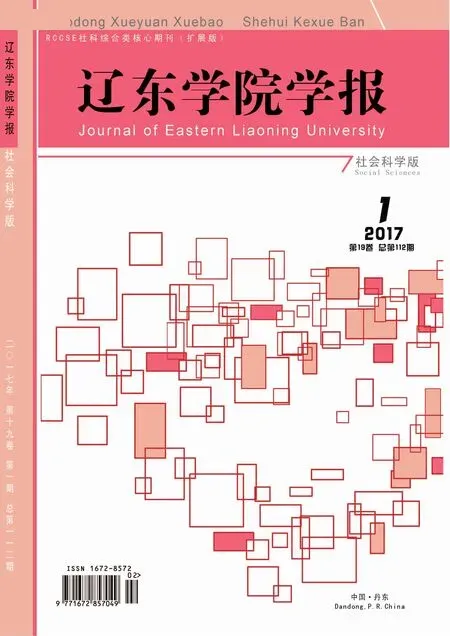“海昏”语源考证
蒋重母,邓海霞
(1.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11;2.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22444;3.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11)
【文史新证】
“海昏”语源考证
蒋重母1,邓海霞2,3①
(1.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11;2.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22444;3.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11)
本文首先对“海昏”是“鄱阳湖西边”一说提出了质疑,并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了其说不可信,接着结合史实重新考证了“海昏”得名缘由,提出“海昏”是“太昏昧”的意思,体现了命名者汉宣帝对被封者“海昏侯”刘贺昏昧行为的蔑视态度。最后指出“海昏”作为侯名,早于“海昏”作为地名,即先有海昏侯,后有海昏县。
海昏侯;海昏侯国;海昏县;语言学;考证
2015年11月前,恐怕除了资深的历史研究者、爱好者,普通公众中知道“海昏侯刘贺”这个名字的人寥寥无几。随着江西大墓墓主人身份的确定,“海昏侯”“海昏侯国”“海昏县”等字眼,开始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然而“海昏”一词究竟由何而来,上述这些词语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至今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一
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 “海昏”是“鄱阳湖的西边”。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周西月《南昌晚报》(2015):
黎传绪:“海”,在古代汉语中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湖”,至今云南、西藏等地还把“湖”叫作“海”,至于“中南海”“北海”更为人们所熟知。“昏”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一个侧立着的伸出一只手的人,手下面是一个太阳,从今天的“昏”字的字形还依稀能辨认出来,所以,“昏”字的本义就是黄昏。古人依据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来辨别东西方向。“东(東)”字的字形是太阳刚刚升起到树干,因此表示“东方”。那么,太阳落到人手下方的“昏”,也就自然而然地表示“西方”了。因此,把“海昏”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湖西”“鄱阳湖的西面”。[1]
随后李峥嵘《北京晚报》(2016年)、黎隆武《中华读书报》(2016)、《中国国家地理》关于海昏侯的专题报道(2016)等也采用了上述观点[2]。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较为随意,值得商榷,试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分析如下:
第一,先秦两汉时期“海”没有“湖”的意思。
在考证某一词语命名缘由的时候,最为简单、也最为便宜的方法就是从词语的表面意思下手,但这种方法也极易犯“望文生义”的错误。特别是在溯源距离我们时代较为久远的古语词的时候,因为古代的语言已经与我们所在时代的语言有了很大的差异,如果不是较为系统地学习或长期接触古代语言(即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古代书面语言),并较为了解古今词义的发展变化,就很容易用现代汉语的词义来追溯古语词的“制名”之源。上文所说“海”在古代汉语中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湖”,是没有从历时角度来考虑词汇的发展变化。翻检《汉语大字典》,“海”字条下共罗列了“海”的17个义项:其中最主要的义项就是“海”的本义,“大海”。《说文解字》曰:“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3]1627。许慎对“海”的说解是天际之水,即邻接大陆而小于洋的水域,和内陆的“湖”“河”“川”有着严格的区别意义。我们知道语言具有系统性和社会性,系统内的每个要素都有着严格的区别和分布特征。一个词语在一定的语言年代,一定有其确切的概念和使用范围,以区别于其他要素。如果“海”和“湖”完全同意,则没有同时存在的必要。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等义词在语言中是不存在的。
我们检索中国古籍基本库先秦两汉部分的文献并没有发现“海”指“湖泊”的用例[4]。我们之所以选取先秦两汉部分的文献作为检索范围,是因为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词义也是在发展变化中的,“海昏”一词的时代背景是汉代,选取时间较为接近的语言材料作为检索范围,体现了语言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原则,从而得出的结论也更为可靠。然而这部分的文献显示“海”不论是单用还是合用,泛称还是专有名词,都是指陆地边缘的水域,而不是湖。
第二,“海”“海子”指“湖泊水潭”是宋以后才出现的语言现象。
虽然《汉语大字典》中确实罗列了“海”指“湖泊”和“大池”的义项和用例。如“里海、洱海、咸海”[3]1627。《汉语大词典》“海”字条下又列有“海子”一词指湖泊。如,“中山城北园中亦有大池,遂谓之‘海子’”(宋沈括《梦溪笔谈》),“海子在县西三里,旧名积水潭,西北诸泉流入都城,西汇于此”(明沈榜《苑署杂志》)[5]1219。
但我们应该科学地看待这些例证。我们知道《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对字义(即语言中的词,字和词在语言学中,不是一个概念,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而词是语言中的单位,古代语言留存到现在只能是书面语的形式,因此这里以字来代指语言中的词,下同)的说解是罗列性质的,并不区分共时平面和历时平面。二书是把某一字从上古到近代所有用法收集整理,并归纳罗列出若干义项,因此人们并不太容易从这两本工具书中完整地了解某字的发展和演变历史。
我们检索中国古籍基本库,发现“海”指“大海义”是其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义项,而“海子”指“湖泊、池塘”的用例最早出现在宋,如上举宋沈括《梦溪笔谈》的例子,而且这一时期用例还很少,但宋以后的元明清时代,“海子”或“海”指称“湖泊、大池”这种用法就逐渐增多。如,《明一统志》“京师四”:(太液池)其上源自玉泉寺,合西北诸水,自地安门水门流入,汇为大池,池上跨长桥,桥北称“北海”,桥南称“中海”,瀛台以南称“南海”[3]1627。这也是上述观点的最主要证据。
另外我们也发现:“海”“海子”称“湖泊、池塘”主要流行于宋以后的北方地区,关于这一点,元代王充耘在其《读书管见》卷上“南北方言”一条下曰:“南方流水通呼为江,北方流水通呼为河,南方止水深阔通谓之湖,北方止水深阔通谓之海子。”[6]49
由此可见“海”“海子”指“湖泊”可能是方言,只通行于部分地区。我们猜测这可能是宋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融合后的一种变异用法。“海”“海子”可能来源于少数民族语言,而借用了汉字的“海”字形。张清常认为“海子”“海”,源于蒙古语,指湖泊水潭[7]31-32。今天在现代汉语中还留存了许多以海命名的湖泊,用汉语“海”之义无法解释,有时特意在后面再加一个“湖”字,以示区别。如,北京:中南海、什刹海(由前海、后海、西海组成)、北海 ;青海:青海、玉石海;新疆:蒲昌海、牢兰海、孔雀海、涸海(都指罗布泊);四川:野人海、五色海; 云南:碧塔海、纳帕海、洱海。因为缺乏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了解,我们不敢确定这种说法是否一定可信,但至少不能根据宋以后的语言事实来确证西汉时期的鄱阳湖就称“海”。而且我们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也没有鄱阳湖称“海”的文献记载。而鄱阳湖古称“彭泽”“彭蠡泽”,“泽”指内陆大水,而非“海”。《汉书·地理志》曰:“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颜师古曰:“汇,迴也。又东迴而为彭蠡泽也,自彭蠡江分为三,遂为北江而入海。”[8]280可见“江”“泽”“海”都是意义确指而区别明显的。
至于现代汉语中的“里海”“咸海”是近代以来才有的国外地名的对译,首译者可能对其是“海”是“湖”的认定并不一定如地理学家一样精确,但沿袭至今,仍以约定成俗为宜,这也不足作为证据。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上文中由此认定“海昏”中的“海”就是“湖”,证据不足。
第三,“昏”不是“西边”。
检阅《汉语大字典》“昏”字条,罗列了“昏”的十条义项:1.日暮,天刚黑的时候;2.暗,昏暗;3.昏愦、迷乱;4.(目)不明;5.昏迷;6.早死;7.结婚,后作“婚”;8.通“阍”,古代守门者官名;9.通“暋”,勉力;10.通“泯”,尽[3]1492。
可见“昏“并没有“西边”的意思,检索中国古籍基本库先秦两汉部分,也没有发现“昏”指“西边”的用例。古代表示西方这个概念的是词语“西”。两者是有严格的词义区别和各自分工的。对于“东”“西”“黄昏”具有些抽象概念的词语,古人只能用具象图画的形式来造字。比如西,字形是一只鸟栖息在树上,表示日落的西方。“昏”字本义,《说文解字》曰:“昏,日冥也。从日,氐声。氐者,下也。一曰民声。”段玉裁注曰:“字从氐省为会意,绝非从民声为形声也,盖隶书混淆,乃有从民作暋者。”郭沫若《殷墟粹编考释》曰:“殷人昏字实不从民,足证段氏之卓识而解决千载下之疑案。”[3]1492可见“昏”是一个会意兼形声的字,其造字理据应是“氐下有日”。《说文解字》曰:“氐,至也。从氐,下著一。一,地也。”[3]2130由此可见昏字的造字理据是日落于地平线下,这是用具象的图画来表示抽象的时间概念“黄昏”,体现了古人朴素的思维方式。而词语“黄昏”和“西方”却不是同一个概念。文字记录了语言,仅从文字的字形上来随意推导文字所记载的词义并不科学,因为在整个词汇系统中,所有的词语必须遵守约定成俗的原则,各自有着确切的词义和分布特征,这样大家才能都听得懂,从而完成交际的目的。硬给“昏”加个“西方”的词义,显然违背了语言的社会性原则,因为在交际中,你把“往西”说成“往昏”是没有人能够听懂的。上文的论证显然是没有区别语言和文字,没有从语言实际中去考证 “昏”的词义,而是从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字形中去想当然地推导“昏”是西方的意思。如果“昏”是“西方”的话,则中国古代的另一个地名“东昏”又该如何解释。关于东昏,《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 集解:徐广曰:“阳武属魏地。户牖,今为东昏县,属陈留。”索隐:徐广云“阳武属魏”,而《地理志》属河南郡,盖后阳武分属梁国耳。徐又云“户牖,今为东昏县,属陈留”,与《汉书·地理志》同。按:是秦时户牖乡属阳武,至汉以户牖为东昏县,隶陈留郡也。正义:《陈留风俗传》云:“东昏县,卫地,故阳武之户牖乡也。”《括地志》云:“东昏故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九十里。”[9]339
又郦道元《水经注》:
济水又东,迳东昏县故城北,武阳县之户牖乡矣。汉丞相陈平家焉。平少为社宰,以善均肉称,今民祠其社。平有功于高祖,封户牖侯。是后置东昏县也。王莽改曰东明矣。[9]339
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东昏”的“昏”绝不是什么西边的意思,其命名来源因为缺乏历史文献的记载,已不可考。但王莽改“东昏”为“东明”,正取“昏”字“昏昧”之义的反义。由此也可知“昏”并没有“西边”的意思。
三
既然“海昏”不能确定是指“鄱阳湖的西边”,那么“海昏”究竟何指?从目前较为有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还不能给出较肯定的答案,或许假以时日,墓中简帛所记载的文字可以给出大家确切答案。然而在墓中文字尚未整理面世之前,我们姑且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结合史实来考证一番。
“海昏侯刘贺”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汉书》中关于昌邑王刘贺的记载无一例外都是负面的。除了《汉书·武五子传》中的《昌邑王传》之外,还散见于《汉书·循吏传》的龚遂部分和《汉书·霍光传》以及《汉书·五行志》中。我们先来看《汉书·循吏传》的龚遂部分:
“贺动作多不正,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国中皆畏惮焉。王尝久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亡度。遂入见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愿赐清闲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胶西王所以为无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闻胶西王有谀臣侯得,王所为拟于桀、纣也,得以为尧、舜也。王说其谄谀,尝与寝处,唯得所言,以至于是。今大王亲近群小,渐渍邪恶所习,存亡之机,不可不慎也。臣请选郎通经术有行义者与王起居,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宜有益。”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宫中数有妖怪,王以问遂,遂以为有大忧,宫室将空,语在《昌邑王传》。会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贺嗣立,官属皆征入。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遂见安乐,流涕谓曰:“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今哀痛未尽,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誖道。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极谏争。”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乱废。[8]889
我们从龚遂的传中可见刘贺素来动作不正,游戏饮食,亲近小人,赏赐无度,胸无大志,不学无术,甚至连龚遂所选的教习也无几日就驱逐殆尽。及至因偶然原因而嗣立为天子,仍旧看不清形势,斗狗走马,日益骄溢,终被废止。
再看《汉书·昌邑王传》所叙刘贺行状:
其日中,贺发,哺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安乐告遂,遂入问贺,贺曰:“无有。”遂曰:“即无有,何爱一善以毁行义,请收属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属卫士长行法。
贺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驺奉乘舆车。王使仆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旦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8]629
刘贺在奔丧路上,先是求买长鸣鸡(一种叫声长的鸡)和积竹杖(一种以竹缕合缠,犹如矛矟的竹杖),又车载女子淫乐。及至长安东都门和城门,仍以咽喉疼痛而搪塞不哭。即将继承大统的刘贺仍如此任性顽劣,不通礼数,后被霍光废弃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书·霍光传》更是记载了昌邑王的海量罪行:
昌邑王即位,好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之中。与孝昭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腰斩。……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8]679
在短短27天中,刘贺就有罪1 127条,平均每天犯错40多条,这里面有没有夸大的成分?我们认为《汉书》的作者班固首先是以私人的身份来修史,后来才得到官方的承认。班固秉承了《史记》的史家笔法,不虚美,不隐恶,甚至为王莽这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也作了传,并且详细描述了他的勤勉与上进。《汉书》中班固对刘贺的描写应该是有历史根据的。《汉书·霍光传》记录的这“一千一百二十七条”应该是有所本,然而制定这“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罪状的人是不是夸大了刘贺的罪行,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罪状却给我们提供了“海昏侯”得名理据的一种可能,那就是“海昏侯”得名于刘贺大量昏昧不当之举,“海”在这里是“大”的意思,而“昏”是昏昧,“海昏”意为“太昏昧”,“海昏侯”得名于刘贺的行为,而不是“海昏县”这个地名,下文我们将展开详细论述。
四
第一、古代王侯的封号不必然以“封地”为号,“海昏”地名不一定早于“海昏”侯名。
上文说“海昏”是“鄱阳湖的西边”,其主观上就已经认定“海昏侯”的侯名来自于其封地“海昏”,这确实也是古代侯王常用的命名法。然而根据现有历史文献,不能证明“海昏”作为地名早于“海昏”作为侯名。
我们首先来看《汉书·昌邑王传》的记载:
其明年春,乃下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侍中卫尉金安上上书言:“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嚣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奏可。贺就国豫章。[8]631
这里只提到“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并未提及其封地在“海昏”,反倒是说“贺就国豫章”。豫章是汉代大郡之一,《汉书·地理志》记载:
豫章郡(高帝置):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一,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县十八,南昌、庐陵、彭泽、鄱阳、历陵、余汗、柴桑、艾、赣、新淦、南城、建成、宜春、海昏、雩都、鄡阳、南野、安平[8]295。
这里明确记载“海昏”是“豫章郡”的下辖十八县之一。但“海昏”这一地名究竟是“海昏侯刘贺”去之前就有了,还是在其去之后才有,不得而知。考察《汉书·地理志》对人口和县域的记载大致以“元始二年”为准,这一点在《汉书·地理志》“京兆尹”条下有说明:
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县十二。
师古曰:“汉之户口,当元始时最为殷盛,故志举之以为数也,后皆类此”。[8]282
可见,班固(32—92)写作《汉书·地理志》的时候,其郡县的记载也应该是他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此时距离汉初高祖时已经二百多年,距离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下诏封故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也已一百多年,而距汉平帝刘衎元始二年(公元2年)则较为接近。《汉书》虽写明汉高帝立豫章郡,班固所在时代也确实有海昏这个郡县,但班固所记录海昏这个地名是否一定就是高帝或宣帝时代却无法确定。因为根据《汉书·地理志》的书写体例和常理,班固记载的天下郡县分布应当是其所在时代的实际情况,而这些郡县的得名和设置历史却是复杂多变的。比如京兆尹下的很多县,设置时代都不相同,比如南陵,文帝七年置;奉明,宣帝置;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又比如左冯翊下的“池阳”,恵帝四年置;云陵,昭帝置;万年,高帝置[8]282。所以班固所记载的郡,有的是沿用了旧名,如太原郡,为秦置;有的则是后来皇帝设置,如弘农郡,武帝元鼎四年置。而郡下所辖的县,是什么时候设置,如何得名的,没有确切的历史资料很难考证。
《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豫章郡下的“海昏”县,是不是就早于刘贺被封海昏侯之前,无法考证。班固虽然在豫章郡的下面写明:“高帝置,莽曰九江属扬州。”只能说明豫章郡为高帝所置,而豫章郡下所属各县设置的具体时间却无法考证。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简要叙述了其所在时代的郡县分布情况,而没有必要对每个县的沿革逐一作出说明。至于“海昏”,《汉书》只点明“莽曰宜生”,而后来注释《汉书》的颜师古则曰:“即昌邑王贺所封”,意思是昌邑王采邑所在之地。因此说“海昏县”在汉初设置为县至少证据是不足的。
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刘贺被废为昌邑王之前,确实存在“海昏”这个地名。因此说“刘贺”因封地于“江西海昏之地”,而名为“海昏侯”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证据。另外我们检索中国古籍基本库也没有在《汉书》以前的文献中检索出“海昏”这个地名,而在汉以后的文献中,“海昏”这个地名就一直伴随着“海昏侯”,直到“海昏侯国”除,这个地名也就彻底消失了。既然“海昏县”无法确定一定早于“海昏侯”,那“海昏县”来自于“海昏侯”就有可能。
第二,在秦汉时期以“海”来命名的侯名很常见。
在秦汉时期,以“海”字来命名的侯名很多。如曹咎,楚汉时期项羽手下大臣,虽然能力不强,但因为对项氏的绝对忠诚而被项羽重用,官至大司马,封海春侯。路博德的校尉司马苏弘因擒获南越末代帝王赵建德而被封为海常侯。海西侯李广利,汉武帝令李广利征大宛国近西海故号海西侯也。海春、海常是否为地名,因古书无记载,不可考,但至少“海”作为侯名用字是可以的。
“海”在古汉语中最主要的意思是“大海”,海纳百川,因其“大”“多”,而在语言的使用中,“海”的词义向“大”“多”引申是极其自然的,由相似性而引申,这是大多数语言中词义引申的主要途径。《汉书·东方朔传》:“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师古注曰:“海者,万物所出,言关中山川物产饶富,是以谓之陆海也。”[8]653这里正取“海”之“大”“多”义,而这种用法仍然留存在我们现代汉语的口语中,如海碗、海量、胡吃海喝等。因此我们认为“海昏侯”中的“海”取其“大、多”的意义也是合理的。
第三,历史上以恶名来命名的“王侯”多体现了统治者对其贬损的态度。
古代王侯的命名,一般以所在封地为名,如安阳侯、襄阳王。但也有根据被封者特色、功绩、秉性以及当权者的心情、意向来命名。如,汉初开国功臣萧何谥号文终侯,曹参谥号懿侯,以表彰其文治武功。据《汉书·萧何曹参传》记载当时民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其命名寓意或许如颜师古所说“讲,和也;画一,言整齐也。”而“懿”正有言行一致、德行美好的寓意,以此名号来彰显萧何曹参的高风亮节。冠军侯霍去病,取“功冠全军”之意,汉武帝于元朔六年(前123年)以此分封名将霍去病。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元朔六年,以击匈奴立功,汉武帝取“博广瞻望”之意,封其为“博望侯”。东汉班超奉使西域,立功封为定远侯等。
而因罪行被削爵者或品行有缺陷者,所得封号则以“恶”字为多。如,孝景帝时,燕王卢绾的孙子它人以东胡王的身份投降汉庭,被封为恶谷侯。齐萧宝卷因昏昧无德而被谥封为“东昏侯”。北宋有“昏德公”和“重昏侯”。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汴京城破,金太宗下诏废北宋徽、钦二帝,贬为庶人,二帝被俘北上。 金天会六年(1128年)八月,金太宗封宋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十月,又将徽、钦二帝发配至韩州。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金熙宗为改善与南宋的关系,将死去的徽宗追封为天水郡王,将钦宗封为天水郡公。第一是提高了级别,原来封徽宗为二品昏德公,追封为天水郡王,升为一品,原封钦宗为三品重昏侯,现封为天水郡公,升为二品。第二是去掉了原封号中的侮辱含义。第三是以赵姓天水族望之郡作为封号,以示尊重。
无独有偶,雍正皇帝执政后,把其弟八阿哥、九阿哥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斯黑”。关于这两个名字的含义,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抄靶子》一文中说:“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10]17“阿其那”和“塞斯黑”究竟何意,至今还没有定论,清史学者王钟翰在《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一文中,对阿其那与塞思黑改名的几种不同字义,改名是自改或他改,改名猪狗之忌讳问题及满汉命名的传统习俗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考证。王钟翰先生指出阿其那与塞思黑体现了雍正在夺嫡斗争中胜利后对失败者的蔑视、轻贱之意[11]77-78。
因此我们认为汉宣帝封刘贺“海昏侯”也应该带有一种“贬损”的味道。这合《汉书》对刘贺的谴责和批评态度是一致的。刘贺被废为“昌邑王”后,汉宣帝继位,刘贺被暂时幽禁于昌邑。宣帝对其仍有戒备之心,并派山阳太守张敞监视其动向,直到张敞报告,刘贺几乎成了废人,宣帝才收了杀心,于元康三年(前63年)效仿舜封弟象于有鼻之国,封故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以彰显其尚念及骨肉亲情。数年后,扬州刺史上奏称,刘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暗自来往,且对现状不满。宣帝就此削除其食邑3000户。不久刘贺就一病不起,愤懑而亡。宣帝也就趁机废除了海昏侯国。
五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海昏侯”得名于其“大量昏昧的行为”,先有海昏侯,后有海昏县。至于海昏侯国与海昏县为两个并行体系。诸侯封地称为侯国,海昏侯采邑所在之地为“海昏侯国”。根据汉制,诸侯王仅得食本国租税,不得干预国政,而“海昏县”是豫章郡下的县,是与海昏侯国同等的县制,后县废。
[1]周西月,贾明.专家解读海昏之谜[N].南昌日报,2015-11-13(06).
[2]李峥嵘.海昏侯真“昏”吗[N].北京晚报,2016-03-04;黎隆武.谁发现了海昏侯墓[N].中华读书报,2016-03-15;海昏侯专题报道[J].中国国家地理,2016(3):1.
[3]汉语大字典[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
[4]刘俊文.中国古籍基本库[Z].北京: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1998.
[5]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6][元]王充耘.读书管见[M].清通志堂经解本.
[7]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社出版,1990.
[8][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汉]司马迁.史记(三家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10]鲁迅.准风月谈[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7.
[11]王忠翰.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J].历史档案,1998(4):77-80.
(责任编辑:孙希国)
Etymology of “海昏(Haihun)”: An Investigation
JIANG Zhong-mu1, DENG Hai-xia2,3
(1.SchoolofHumanities,Suzhou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uzhou215011,China;2.SchoolofLiterature,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22444,China;3.SuzhouArtandDesignTechnologyInstitute,Suzhou215011,China)
The statement that the area of Haihun is located in the west of the Poyang Lake is questioned and proved to be wrong in a linguistics perspective. Besid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海昏(Haihun)” is investigated. It is found that “海昏(Haihun)” means fatuous, showing the scorn of the Xuan Emperor of the Han Dynasty to the Marquis of Haihun Liu He. Finally, it is found that the name of Haihun Marquis came earlier than that of Haihun County.
Marquis Haihun; nation of Marquis Haihun; Haihun County; linguistics; textual research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1.06
2016-04-06
蒋重母(1970—),男,湖南新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上古汉语词汇语法。现在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大学语言学院任公派汉语教师;邓海霞(1976—),女,河北磁县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上古汉语词汇语法。
K23
A
1672-8572(2017)01-0027-07
——海昏侯的“Two Face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