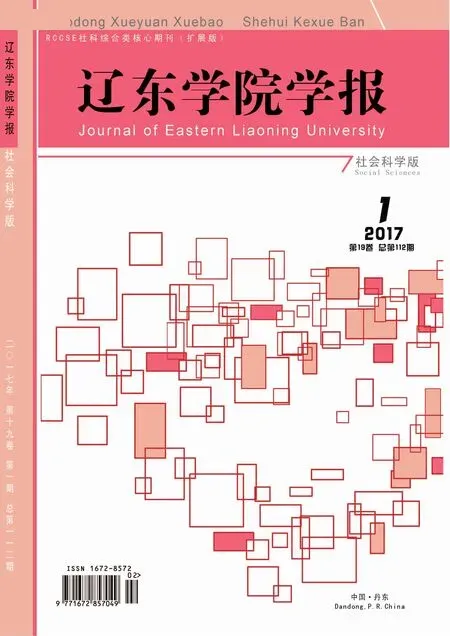论苏曼殊诗歌译介与创作的现代性
季淑凤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文学研究】
论苏曼殊诗歌译介与创作的现代性
季淑凤①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开创鸳鸯蝴蝶派文学之先河的苏曼殊,也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在诗歌翻译和创作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苏曼殊在诗歌译介及创作过程中,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在革命精神和自由意识、悲剧意识、爱情的大胆表达、平等对待女性等若干方面都体现出了现代性特征。这种现代性的发掘,不仅丰富了苏氏文学研究的维度,更为被标签为“封建、旧派”的鸳鸯蝴蝶派外国文学译介及影响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苏曼殊;诗歌;译介;创作;现代性
引言
苏曼殊(1884—1918),广东香山人,他以《断鸿零雁记》闻名于世,也因此被视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鼻祖。同时,他又是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诗人。他一生多才多艺,能诗会画,通晓汉文、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语言,在小说、诗歌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译介与创作的小说、诗歌被柳亚子汇编为《苏曼殊全集》。就外国诗歌汉译而论,苏曼殊可谓中国近代史上翻译西方诗歌的先驱者,以译介雪莱、拜伦、彭斯等人的作品为主,译诗主要收集在《文学因缘》《潮音》《拜伦诗选》之中。苏曼殊的译诗在当时就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鲁迅就曾说“译文古奥的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润色的罢,所以真像古诗,可是流传倒不广”[1]322,罗建业亦持此论。然而,其他学者对苏曼殊的译诗却不吝赞美之词。柳无忌谓其以译诗之功,可位居林纾、严复之后,是为“第三大翻译家”[2]183。周木斋认为“最初致力于译诗的,当推苏曼殊,(译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3]137。由此可以管窥,学界对苏曼殊的译诗评价,莫衷一是。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拟将苏曼殊译介及创作的诗歌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考察,发掘他在异域“他者”诗歌的翻译过程中,建构起自己独特的诗歌世界,在自己创作的诗歌中,很多方面也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体现出现代性的特质。
苏曼殊翻译的众多诗人诗作中,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最为青睐,也受他们的诗学观、诗作影响最大。苏曼殊在《潮音》的序言中,称“拜伦和雪莱,是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中的两人”[4]295。在《本事诗》之三中,写道“丹顿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5]35,诗中把拜伦看作自己的老师,并对拜伦生命的短暂及自己的命运产生一种感伤之情。1909年,在《题拜伦集》中,他写道:“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瓢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4]53,显示出他与拜伦精神上高度的契合。1914年,在《与邓孟硕书》中,他更是表达了要亲自去凭吊拜伦墓的渴望,“欧洲大乱平定后,吾当振锡西巡,一吊拜伦之墓”[4]303,又云:“英人诗句,以师梨最奇诡,而兼流丽”[5]35。1919年,在《与高天梅书》中,他说:“衲尝谓拜伦足以贯灵均、太白,师梨足以合义山、长吉”[6]332,足见拜伦和雪莱在苏曼殊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西方浪漫诗派的译介和推崇源自身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情结,其自身的性格和行为,就是对浪漫主义绝佳的阐释。在译介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歌的同时,他也进行仿拟性质的诗歌创作,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弥漫着西方浪漫气息,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
一、主题现代性:革命激情与自由意识
晚清民初,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形势,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的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积极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尤其在梁启超倡导的“小说以开启民智”的号召下,一时间,小说翻译成为一股热潮。而作为诗人,苏曼殊积极的对诗歌进行译介完全是情理之中。正如英国诗人及译诗家屈莱顿所说“译诗的工作只能由诗人来做”[7]45-47。
苏曼殊是最早译介拜伦作品的译介者之一,他对拜伦的热爱与崇拜,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源自拜伦那光焰灼人的革命精神和自由解放的思想意识。在希腊抗击土耳其的激烈斗争中,拜伦放下手中的一切活动,以超人般的意志前往希腊,积极投身于解放运动之中。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形势和希腊有着非常的相似之处,面对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苏曼殊渴望能有像拜伦一样的无私无畏的斗士出现,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苏曼殊曾在《拜伦诗选自序》中,赞美拜伦“以诗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8]15,并积极译介了拜伦的《哀希腊》《去国行》《大海》等爱国诗篇,以期唤醒国民的革命意识,投入到抗暴抵辱的革命之中,激励民族自强。
事实上,苏曼殊的革命激情,源自于其对正义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和对黑暗力量的反抗。早在1903年,从日本归国的船上,就写下《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8]18。通过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鲁仲连、荆轲的歌颂,表现出诗人忧国忧民的心绪,及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抗议,表现诗人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和追求。1909年,旅日的苏曼殊瞻仰郑成功的诞生地后,曾写下悼念诗词《谒平户延平诞生处》,表现出诗人的爱国情怀和英雄主义。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讨袁声势,苏曼殊写下《讨袁宣言》,表现了诗人的革命热情和对黑暗的反抗。诗中即以拜伦援助希腊的民族独立开头。可见,其受拜伦诗歌的影响之大。“曼殊岂止是一个作绮艳语,谈花月事的飘零者而已”[9]116。
二、诗学现代性:难言之恫与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的确立是近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与中国古典悲剧一般以“大团圆”结束的模式不同,西方悲剧一般都以人物生命或美好事物的毁灭告终,认为把美好的事物粉碎给人看,更能激发人们的同情心,产生共鸣。苏曼殊的身世有着“难言之恫”,加上他亦僧亦俗的身份,使他徘徊于俗世与山林之间,想要解脱又难以摆脱的悲情一生使他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着这种悲情意识。
他诗歌中一方面表现出对人世爱情与温情的渴望,又由于害怕受伤而拒绝,因此他诗歌中相爱之人,要么劳燕分飞,要么一方为爱而死,要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在一起。在《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中有悼念已故日本情人静子的诗:“孤灯引梦记朦胧,风雨邻彦夜半钟。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10]15《樱花落》中有诗云“多情漫向他年忆,一寸春心早已灰”[11]27,表达了苏曼殊对往日爱情的追忆,却又万般无奈和绝望的心理,读来不仅为之动容,催人泪下,透露出强烈的悲剧意识。而在《寄调筝人》中有诗云“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又有“收拾禅心侍镜台,沾泥残絮有沉哀”[10]15。这源于苏曼殊是一个往返于常人与僧人之间的角色,他骨子里的浪漫和风流使他不能放弃世间的情爱,但是出家人的身份,佛教对于情欲的压制又使他处于情爱和佛教信仰之间的尴尬境地。而佛教一直宣扬的“人生本苦”的理论,更加剧了诗歌中的悲剧意识。
他在家国忧思方面的诗歌同样表现出他的悲伤之情。如《东居二》:“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10]16;又如《吴门十》:“故国已随春日尽,鹧鸪声急使人愁”[10]18。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崩裂,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之时的一种救国心切却又无可奈何的感伤之情。
三、情感现代性:崇尚爱情与直率表达
在苏曼殊35年的短暂人生旅途中,他的爱情诗占了很大的比重。据马以军统计,在能够予以确证的三十九题八十九首诗歌中,“言情篇什居十之九”[5]38。例如他为日本艺伎百助眉史而作的具有自传色彩的《本事诗十首》;另有在日本养病时所作的《东居杂诗十九首》,主要描绘了当时与国香、真真、阿可、湘痕、阿燕等日本女子的交往;《樱花落》《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都表达了对已故日本情人静子的悼念。
歌颂爱情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主题。传统诗歌往往把这类题材处理得朦胧隐晦,而苏曼殊在爱情诗中,往往直陈其事,大胆直接地描写了他与不同女子的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并对自我内心进行了大胆的剖析,显然是受了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苏曼殊曾在《潮音·自序》中写道“拜伦和雪莱是两个伟大的英国诗人,两人都把创造和恋爱的高贵情感作为他们诗歌表达的主题”,“雪莱和拜伦的作品都值得每个恋爱者去研究,去欣赏诗歌的美丽,去鉴赏爱和自由的高贵理想”[4]131。可见苏曼殊对拜伦和雪莱的推崇。在《东居杂诗十九首》中写与女子并肩携手漫步乘凉的情景:“兰蕙芬芳总负伊,并肩携手纳凉时”[10]17;与女子偷吻时“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10]18;悼念已逝去的日本恋人静子,感慨物是人非,在《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中写道“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10]15,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无奈。再如,在《本事诗十首》(三)中为日本艺伎百助眉史所做“一杯颜色和双泪,写就梨花付与谁?”[10]14描写了自己失去恋人的凄凉、无助,诗中涌动着凄艳之情。无论是描写诗人对于爱情的沉醉与留恋,还是描写对爱情的无奈和绝望,都是直言其事,言人所难言。对爱情描写之大胆,内心剖析之直白,在中国传统诗歌中,都比较罕见。在爱情表达的直率、大胆和热烈上,苏曼殊大有拜伦之风。他曾在《潮音·自序》里用一种几近崇拜的口吻写道“拜伦的诗,像是一种使人兴奋的酒,——饮的越多,就越觉得它甜美、迷人的力量,他的诗里,到处都充满了魅力、美感和真诚”[11]295。诗词中除了有对拜伦的高度评价之外,还暗含着对自己的肯定,因为他曾说自己师承拜伦门下。
四、性别现代性:重视女性与平等意识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国内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开始追求婚姻自主和爱情自由。苏曼殊中日混血儿的身份以及自幼失怙、多病寡言的性格,加上经钵飘零的境遇使得他能够一视同仁的对待和他相处的女性,而不是俯视他们的不幸遭遇,更多的是以纯真的情感、平等的姿态给予他们以安慰和关怀。
他在《本事诗十首》中“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凝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10]18,表达了自己对百助遭遇不幸身世的安慰,表示能够感同身受。诗人还喟叹“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10]14,表达了自己与百助眉史相见恨晚,不能携手的遗憾与无奈。“华严瀑布高千尺,不及卿卿爱我情”[10]15,感慨他与佳人爱情之深。“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10]15,表达诗人的万般悲痛和感慨携手无期,佳人不再的无奈,其中包含了诗人极为真挚、深沉的感情。苏曼殊在《潮音》跋中曾说自己在积雪的月夜泛舟,“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8]311,刻画出一个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形象。那些抒写离愁别恨、感慨飘零人生、喟叹爱情的诗篇,颇有雪莱式的浪漫主义的风度“其哀在心,其艳在骨”[4]115。实际上,不仅苏曼殊对这些女性以同情和安慰,这些女子也同样对他一往情深。当苏曼殊病重时,与朋友书信中曾提到“近日小病逆旅,旧友都疏,惟女校书数辈过存。不图彼辈缀叶飘花,尚有故人之意”[2]131,从中可见他们感情的真挚,大部分朋友都疏远了,唯有这些女子还能前来探望,足见苏曼殊与这些女子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闪烁着新时代爱情观的光芒。
结语
郁达夫曾评论到“我所说的他在文学史上可以不朽的成绩,是指他的浪漫气质,继承拜伦那一个时代的浪漫气质而言……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4]115。苏曼殊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受拜伦的影响最大,其性格和行为可以说是拜伦浪漫主义精神最好的阐释。他对拜伦极为的热爱与崇拜。而他并不满足于翻译拜伦的诗,还尝试自己创作诗歌。苏曼殊虽然在形式上是古典的,但是在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方面,以及对爱情的大胆、直率表达方面,充满了拜伦式的浪漫主义精神;而其情绪的感伤凄凉,又颇得雪莱的韵味。受西方现代爱情观念的影响,诗歌中的主人公大都多情、真挚、且能在与女性交往中互相尊重。而诗歌时时折射出来的悲剧的气氛则源于作者“僧”的身份。他的落拓不羁、洒脱自由、自然真诚以及感伤怀旧的情调和孤独飘零的身世深得五四之后浪漫青年的青睐,开辟了新时代文学的浪漫主义风气。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柳无忌.苏曼殊传[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3]袁锦翔.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4]柳亚子.苏曼殊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5.
[5]马以君.燕子龛诗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柳亚子.苏曼殊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丰华瞻.试评苏曼殊译诗[J].中国翻译,1989(1).
[8]苏曼殊. 拜伦诗选自序[M]∥苏曼殊文集.广州: 花城出版社,1981.
[9]柳亚子.苏和尚杂谈[M]∥苏曼殊诗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10]柳亚子.苏曼殊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1]马以君.苏曼殊文集(上)[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孙希国)
Modernity of Su Manshu’s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of Poems
JI Shu-fe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uaibeiNormalUniversity,Huaiebi235000,China)
Su Manshu, a pioneer of the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School, is also an outstanding translator and poet in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of literature. He gained a great reputation in poetry renditions and writing.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romanticism, Su’s works take on the modernity features in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 freedom, tragic, forthright love and equality of female. The study of modernity in Su’s poetic activities, not only enriches the dimensions of Su’s literature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influe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by the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School, which was once labeled “feudalism” and “laggar”.
Su Manshu; poem; translation; creation; modernity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1.21
2016-11-20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鸳鸯蝴蝶派外国文学译介及影响的现代性研究”(AHSKQ2015D69)
季淑凤(1982—),女,山东青岛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I046
A
1672-8572(2017)01-0112-04
——岭南历史文化名人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