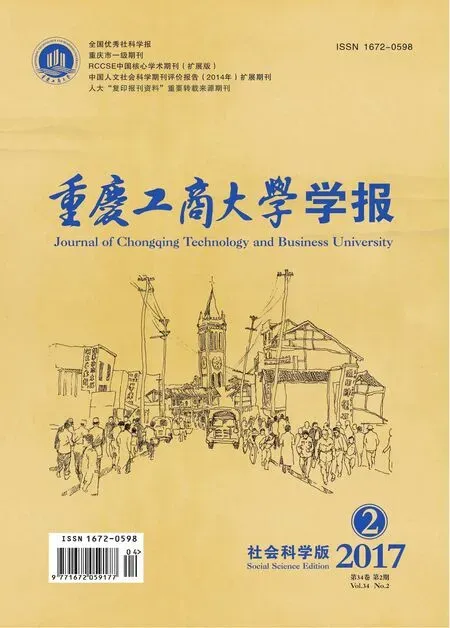发展人类学视野中的渝东南生态保护与发展
谭 宏
(重庆文理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重庆 永川 402160)
发展人类学视野中的渝东南生态保护与发展
谭 宏
(重庆文理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重庆 永川 402160)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是在总结发展经验和教训上提出的,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生态保护区是在当下急剧变迁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对一个特定地区发展的新型定位。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考虑人的存在和发展,这是生态保护区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发展人类学立足于生态区建设过程中因文化引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把发展视为一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过程。运用发展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对于提高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建设效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发展人类学;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保护与发展
2013年9月,中共重庆市四届三次全会通过了《关于科学划分功能区域、加快建设五大功能区的意见》。《意见》根据重庆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综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总结重庆市直辖10多年来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国际国内最新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理念,将全市划分为五大功能区域。即: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对于五大功能区的发展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定位。其中,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基本定位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武陵山绿色经济发展高地、重要生态屏障、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带和扶贫开发示范区,全市少数民族集聚区。” 由此,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目标的实现,确保生态发展区真正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了渝东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生态保护区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种“制度的设置与变迁支配着所有的社会和个人行为,规范着其行为方式的选择,影响着人们利益的分配、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1]生态保护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系统,是带有很大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知识系统的创立总是一种政治行为。”[2](法国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设立,是从一个新的发展视角,为保护渝东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发展规定了一个新的路径。在研究生态保护区建设和发展问题时,发展人类学更关注生态保区发展区的发展意识、倡导保护区民众自觉而积极地参与各种保护和发展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充分考虑和正确处理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利益,以期更好地实现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和谐生活”“和谐发展”。
当人类由“自然共同性”走到“社会共同体”之时,发展问题就成为了地球上不同区域的民族或族群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依据自己所面临的特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选择了自己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不同的人类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更是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以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发展理论逐渐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理论。在传统经济学发展理论中,人类过分注重经济和技术的力量,试图通过加大经济和技术投入,来改变一些特定地区的发展,而忽视对文化生态区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仅仅“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归结为人均收入的逐渐增长。”[3]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向一些落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从总体上讲,这些项目的初衷是好的,力图通过经济援助,改变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促进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事与愿违,反而引起了当地社会的“水土不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些以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目标的项目“引发了许多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 如通货膨胀、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文化冲突等。”[4]这种完全按西方“现代化”为基本标准所设计的“自上而下的以科技为中心的集中投资式干预模式在许多地方都收效甚微。”[5]同时,也试图按照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来重构一个社区或社会,因而,遭到了失败。这种以传统西方经济学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脱离了发展计划所必需的社会背景知识,只一味地想当然把发展对象想象为类似西方社会的背景。因而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科技输入,最终都遭遇重重阻碍和反复失败。”[6]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引起了发展官员和发展专家们的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发展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在此时“派上了用场”,发展人类学“关怀他者”的学科特征,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主要“关注GDP”的学科倾向,发展人类学发现问题出在这些项目的目标设计、目标实施等方面,它们过分地依赖资金、技术的力量,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援助方式”把“所有的地方性知识或实用技术完全排除在外。”[7]西方现代化之发展观“必须经当地性转移”[8]。由此,人们开始关注援助或扶贫对象本身及其所处的文化传统和生态条件,在援助贫困人口或贫困地区时,对当地社会、文化、知识的考证成为制定援助计划的重要参数,也成为援助计划的重要部分。发展人类学立足于“实地解决或解决发展项目中因文化引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 探索利用本土文化提高发展项目实施效果的可能性”。并且,发展人类学“把发展视为一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过程, 关注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权力不平等关系。”[9]由此,使援助和扶贫的计划和项目真正能够取得应有的效果,使当地人受益,得到实惠,其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普遍提高,而不能因这类投资项目“对当地的弱势群体、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等方面造成伤害。”[10]
重庆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是在总结发展经验和教训上提出的,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1997年,为了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后续经济社会发展,重庆成立了直辖市。在直辖市成立之初,根据重庆市“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的特殊市情,形成了“三大经济区”(即:都市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的发展战略。2006年,根据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近10年的具体情况,又提出了“一圈两翼”(即:以主城为核心的都市发达经济区、万州为中心的三峡库区发展区、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发展区)的发展战略。不可否认,这两个发展战略,对于新兴的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过分注重“经济”的导向还是非常明显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重庆总结经验,根据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五大功能区”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特别强调了渝东南和渝东北的生态保护任务和发展,“是站在重庆整体功能布局的高点上,正确处理了加快发展与保护生态的关系。”[11]对此,渝东南地区的各区县领导们深有体会。秀山县委书记代小江说:“多少年来,不少人执着于GDP的增速、增量,在明知不会成功的情况下还不惜一切代价引进工业企业,结果留下了一堆烂摊子。”酉阳县委书记陈勇说:“从工业立县到生态立县,酉阳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在此期间吃过苦也吃过亏。”[12]改革开放以来,渝东南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也一直在不断地向“国际先进经验”和“沿海先进经验”学习,复制它们的模式,走“大工业、大商业”的发展模式,但效果并不理想,最为严重的是经济虽然有一点增长,但生态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面对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的新任务和新目标,我们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既保护又发展的、有特色的、可持续的道路。在保护生态中得到发展,这对渝东南地区是一个由政府倡导下的“指导性变迁”,是由“某个社会的个体或群体积极地、有目的地对其他民族的社会和观念的现实干预。”[13]这种变迁必须会导致一系列的连续变迁。这些变迁也是发展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发展人类学“强调发展要适应当地的自身资源/技术水平。”[14]因此,我们将用发展人类学的视角,来探讨和研究渝东南地区的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我们力图“通过积极参与和介入对将要发生变迁的社区事务进行指导……促进其变迁。”[15]
一、以人为本,促进发展
在当代,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对人类如何认识自己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这样地困惑不解。”[16]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制度性安排”是发展观上的重大转变,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更注重人的发展。任何社会的发展最终都要落实到人自身的发展之上,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文明可视为……迅速提升人类的善良、能力及幸福的一种全面进步。”[17]也就是说发展不能离开“人这一价值原点”,不能把一些发展手段或工具“当作发展本身。”[18]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表述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12年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9]重庆市“五大功能区”的发展战略,就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确立,表现了我们对发展观念的更新,里面是有实质内容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就生态保护区来说,无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还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当下的人和未来的人能够更好生存和发展,这才是设立渝东南生态保护区的目的。在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建设中,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以人为本”的目标。发展人类学也强调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摆脱困境,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像殖民主义那样(尽管是以善意的面目)掠夺当地资源。”[20]让当地人牺牲了自己的发展机会,贡献了自己的资源,而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更不能因此保护项目的实施,而影响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保护是为了使人类更好、更科学地发展和生活,而“绝不是要强迫人们不情愿地像牛一样被喂养,或者永远作为小孩来抚养。”[21]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当代人都不能很好地生存和发展,还谈什么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当代人生存发展得好了,才可能使我们的后代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历史造就人但人们也造就历史。”[22]
在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中,有几个关键词值得注意,即:“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屏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生态民俗文化”“少数民族集聚区”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在新的发展观下,这些都成为了发展的重要要素而得到了重视,“发展应视为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行为转变……此复合系统朝着更加均衡、更加和谐、更加互补的方向进化。”[23]这些生态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达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逐渐全面发挥生态价值的作用”[24],促进当地人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我们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把‘人’的精神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全面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消灭贫困作为发展的目标。”[25]就实际情况而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所辖的武隆、石柱、彭水、黔江、酉阳、秀山6区县(自治县),都基本上是属于“老、少、边、穷”地区,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对于这个地区的人民来说,要完成生态保护的目标和任务,就意味着必然会限制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使这些地区失去一些发展的机会。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为保护而保护,当地民众显然是不会愿意的,难以接受这种“制度性安排”。他们也有享受现代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成果的权利以及与其他的人群或族群一样享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生态保护区的民众,需要脱贫致富,更需要向前发展。小平同志那句至理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还是很管用的,任何生态保护区建设要真正能够有实效,只有在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取得。生态保护不是“机械式”“木乃伊式”保护,这对于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都是如此。生态保护发展区不是为保护而保护,同样肩负着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当地人民群众收入、改善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使命。
生态保护区的设立,从政府的导向来看,是为了保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打造出文化生态、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典范”。就当下来说,由于生产和技术高速发展所引起的自然、社会变化以及导致的文化变迁来说是无比巨大的,生态保护观念的提出,对于维护文化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生态发展区的长远目标是在发展中保护渝东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这不仅是对重庆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对中华民族能够代代相传的贡献。但是,从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来看,由于“保护性发展”更关注长期和未来,其发展的速度表现得比较“慢”,直接的经济数据不一定有那么“好看”,因此,在实际的保护和发展中就可能出一些问题,使“以人为本”的目标发生偏差。在经济力量面前,在经济增长面前,当地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和自然生态保护往往会变成配角, GDP成了主角,生态保护区成为了赢利的广告词和招牌,从而违背了建立生态保护区的目标。因此,在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改变发展观念,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核心位置,把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武隆县委书记刘新宇说:“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追求’。”[26]这样,才能使生态保护的长远目标得到实现。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民众不能在保护中获得自己的幸福生活,那么,保护区建设是不可能长久地进行下去的。
二、积极参与,共谋发展
生态保护区的“制度性安排”最终要落到实处,还需要当地民众的认同和参与。对此,发展人类学提出了 “参与”的概念,建构了“参与式发展”这一描述发展方法论的术语,目前已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和使用, “‘参与式发展’这样一个所谓‘新鲜’的提法已经通过发展干预和实践,从专家学者的文本和话语中,传到偏远山区的不同社会行动者的口语中。”[27]参与“是发展中授权、民主、良好的治理、创新、合作、分权化和能力建设等的基础。”[28]在生态区建设中,发展人类学的“参与”理念和方法,其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理念上讲,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生态保护中民众的力量的。《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是衡量保护区建设成效的决定因素。”[29]让民众参与,并不是我们没有这个传统,也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民能载舟,也能覆舟”这句话,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理念和行为准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更是发动民众,让民众参与的典范。当时的广大民众能够主动地参与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吸引他们,引导的方法适合他们,使他们能够真正参与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在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如何激发更新民众的发展观念,提高保护意识,充分调动他们参与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在实际的生态保护区建设中,这种参与不是一个形式或口号,而是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过程,涉及生态保护事务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当地民众真正参与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在决策及选择过程中的介入、贡献与努力、承诺与能力、动力与责任、乡土知识与创新、对资源的利用与控制、能力建设、利益分享、自我组织及自立等。”[30]这些过程参与实现了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由“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的转变,“走的是一条‘以人为本’、自下而上、全员参与的新的发展路子。”[31]参与式发展可以使生态保护区的民众以主人翁的姿态来认识和把握当地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价值,并变成自己保护和发展的行动。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基本状况是面积1.98万平方千米,常住人口280万人(2012年数据),涉及汉、土、苗等民族,要完成艰难的生态保护和发展的任务,没有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就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中国几亿农民的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若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在空头指标的掩饰下对他们进行剥夺,发展就不可能发生。”[32]对于一个生态保护区的利益相关者来说,无论政府还是学者,或是投资者,他们的角色还是处于“客位”的,他们虽然能够在政策层面、技术层面、资金层面,为生态保护区的发展提供政策、法律、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但最直接的实施保护规划和享用发展成果的还应该是处于“主位”的生产和生活在保护区的当地民众,因此,区内民众对保护和发展的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保护区的建设质量和效果。“参与式发展”就是让当地人在自己熟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按照保护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文化等的具体情况,在政府以及专家们的指导和帮助下,“真正地参与到发展项目的决策、评估、实施、管理等每一个环节”,并且“把所有外部的信息、技术及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变成自然的内源发展动力。”[33]在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实现生态保护和区域发展的双赢局面。
发展人类学的发展观念,强调在发展中必须考虑发展活动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一个社会发展项目的成功,必须要依靠受益群体的广泛参与才有可能,这是一个从“以经济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观念转变。让生态保护区内的民众广泛参与,就目前的“状况”来看,重要的是提高保护区内民众的参与意识。长期以来,渝东南地区都属于国家重点支持和帮扶的地区,其发展基本上是依赖于中央财政的补贴和救济,一直以来,渝东南所在的区县就把争取“国贫县”和各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作为自己的工作任务,以争取更大的外部支持,这种靠“输血”方式进行的“发展”,不仅没有能够推动渝东南地区的发展,反而在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严重的“等、靠、要”的思想,在这些地区“从生产到出售,从柴米油盐到婚丧嫁娶,个人事、家事、村事、乡事,无事不找政府和领导。”[34]这种依赖意识如果不逐渐改变,会严重影响当地人的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精神的确立,更“不能启动其技术创新的过程。”[35]在设立为生态保护发展区后,政府更是考虑和设计了在投入和再分配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措施和政策,因此,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保护区内长期以来被赋予的“弱势群体”“被帮扶对象”的意识。“扶贫政策”往往引起一个重要的负面效果,使当地人慢慢地认为“‘我们属于贫穷和贫困的一部分’——全面伤害了地方族群的自信心。”[36]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参与生态保护和利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要使保护区内的民众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其发展和建设,就要让他们树立起对自己文化和文明的自信,“赋予他们一定的地位、尊严和与外界谈判的能力。”[37]强化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意识。另一方面,外部力量在推进生态保护区建设时,也要克服过分“自信”的感觉,不要认为自己是在做把“落后”“原始”或“奴隶”地区带到“现代”社会的好事,想象着自己是把“先进”“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给当地人,而忽视了当地人的参与。
三、让权于民,推动发展
让当地民众参与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建设和保护,不是一种形式,是实实在在的要求,参与是一种权利,“把参与仅当成是简单的出席这种观点和做法,是对参与极其片面、极其狭隘的理解。”[38]在人类学家看来,发展是“一个知识、实践、技术和权利的关系体系。”[39]当地人在这一体系中的权利享有程度,与自己的发展有极其紧密的关系。“权利关系——表达在政治、宗教、族群和其他样式中,但总是具有经济后果——界定了社会谋划的界限和可能性。”[40]建设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要处理和解决好当地民众在其保护和发展中应该享有的权利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对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是“关爱有加”,而正是这种关爱,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他们的“权力意识”。而外在的政治家、决策者、学者等“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权力’系统。”[41]长期以来,政府领导和专家们极其善意地为保护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希望当地人尽快得到发展,尽快脱贫致富,这种做法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还可能无意中刺激了当地人“等、靠、要”意识的增长,而且由于“发展机构掌握着用于改变现状的主要资源,”从而使得“发展的对象也就不自觉地受到这个外部强力集团的控制。”[42]因此,现在是思考把“发展话语”权交还给当地人的时候了。“如何处理发展中的权力问题主导了人类学发展研究的方向。”[43]在生态保护区建设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学界的指导、企业的支持都很重要,但民众的自觉参与和自主管理更重要。让保护区内的民众享有保护和发展中的一定的权力,才有可能实实在在地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毕竟政府的规划再合理,学界的指导再科学,还得靠当地人来理解和执行,他们才是生态保护区的真正承载者和主体,他们对于当地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状况,比“外来者”更加熟悉和了解,“更加熟悉他们自己的发展限制、发展潜力及发展机会。”[44]因此,在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适当地赋予当地人权力,政府应当改变行政观念,不能像“家长”一样什么都要管,该放手时要放手,该放权时要放权。更多地让保护区民众自己做主,在尊重科学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特有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状况,不断创造和发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状况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让权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态保护区建设过程中主要由“外来者”决策的状况,实现决策和实施“由上而下”向“由下而上”、由“外部”向“内部”、由“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的三个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可以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来进行,“权力可以通过某些制度设计而实现让渡、转移和增减。”[45]在这方面,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根据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对向农村基层放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制度设计。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宪法》中就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3年民政部在《关于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中,把“村民自治”归纳成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994年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提出了完善村民选举、村民议事、村务公开、村规民约等项制度的建设;1994年第十次全国民政会议正式提出了“四个民主”;1997年第十五大会议上,“四个民主”被写进了党章;1998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对村民自治作了定性和评价: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中国式村民自治的探索和实践,已在我国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于扩大基层民主具有重要意义。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建设,每一项工作都涉及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村民自治”的许多政策、经验和做法,完全可以运用到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来。而且,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1区5县大多属于少数民族区县,还享受少数民族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生态保护区当地民众是其生态环境的主人,生态区保护区的设立,为边缘地区的民众或族群提供了“内部”增强凝聚力,“内部”扩大影响力的机会。赋予当地人管理和控制自己资源的权力,保证当地民众依法管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事项,创造自己的特有生产和生活方式,使每一个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都体现出鲜明的特色,为整个社会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提供鲜活的“样本”,这样才能达到建设生态保护区的目的。国内外实践证明:“当社区成员参与发展项目的计划和决策过程、被授权管理和控制他们自己的资源和未来时,平等发展最有可能实现。”[46]在生态保护区建设中,为生态保护区提供指导和服务的外来者(官员、学者、企业家等)一定要转变观念,不要以为我们比当地人更有权力、更有知识、更有技术、更有资金而“高人一等”,可以挥舞着指挥棒指挥当地的发展和建设,可以根据外来者自己的判断来确定大规模的社区发展项目、社区技术推广项目。从实际情况来看,外来者所确定的当地人需求可能与当地人真正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建设中,应该保证当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应该让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公平和有效,应该动员更多的社区成员参与建设活动。在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定位中,文化生态的保护是重要的任务和目标,文化生态的保护任何外来者无法代替完成,必须由当地人完成。在渝东南地区,许多建构在地方性知识体系上的生态保护知识和习惯是值得提倡的,千万不能轻易地以“现代化”的名义而废弃掉,“现代科技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并非世界上唯一的智慧。”[47]事实上,在渝东南地区的一些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就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其中蕴藏的丰富多彩的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具有非常高的一致性和同一性。如秀山钟灵地区的茶—林—农复合生态系统。这些系统都是当地人的智慧结晶,“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48]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其传统文化的活态保护,这种保护更是离不开当地人的参与,必须由当地人来完成,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也应该“让居民获得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权,逐渐实现社区居民文化主导权的回归。”[49]
四、利益共享,和谐发展
从宏观上讲,生态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保护其文化和自然资源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能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这是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但是,生态保护区的设立,并不是把它隔离成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的世界,它的保护、发展还必然和外界紧密联系,涉及相关的团体和人群。生态保护区是一个具体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参与者众多,包括当地人、外来人(旅游者、政府机构、企业集团等等),由他们构成了利益相关者群体。这一群体在建设过程中,必须有各自不同的参与和投入, 客观地讲,这些参与者一方面希望对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希望获取一定的收益,这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我们在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过程中,在追求生态保护整体目标的前提下,厘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划清各自应有的权力和收益,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才能保护各参与者,在为生态保护区建设作出智力、体力、资本、技术等投入之后,获得应有的回报,确保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不受伤害,促进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和和谐发展。绝不能在发展中造成“一些地区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另一些区域却在积累着贫困。”[50]这种“马太效应”会“使经济增长的过程不是把形成的财富和繁荣引向拯救贫困的扩散效应,而是产生扩大贫富差距的回波效应,造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51]这种状况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实践中曾大量出现。本来,按邓小平的设想,是让少部分地区以及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小康”。这个设想对于一个人口、文化、民族都很多、地域很大的中国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也是与不平衡发展理论相吻合的。但是,在强大的资本和技术力量操作下,这一目标在实践中发生了偏离。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任何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资金和技术的参与和投入,“人类进步史上的伟大时代,都被认为或多或少与生产资料的增长直接相关。”[52]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建设,由于其人才、技术、资本的不足,更需要大量地引进外来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现在的问题是,在强大的资本力量面前,外来者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为保护区发展做出最直接贡献(包括为了生态保护而牺牲的利益)的当地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也就是说当地人的付出和收益是不成正比的。实践证明:在文化生态区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当地人能够感到自己明显获得利益时,就会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反之,则会抵制这种开发和利用。在具体的保护行动中,利益最容易受到损害的是当地人。虽然政府的基本宗旨是保护当地人的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可能把生态保护区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政治行为,为了获得外部的资源,不得作出一些妥协,放弃一部分自己和当地人的利益。“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以求得基础设施建设或民俗旅游项目开发的投资能够尽快到位。”[53]在这样的状况下,很显然的是外来的利益集团在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获得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当地政府获取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和很大的政治利益,而当地人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都没有能够得到应该得到的份额。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在生态区新生的“有钱人”,当地人不多,更多的是“外来者”。这是极不公平的,做出牺牲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未做出牺牲者得到了丰富的报酬。
对于生态保护区民众的利益来讲,包括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一些直接从事生态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当地人可获得相应的“一点”利益,如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的导游、饭店接待、餐饮服务、旅游商品经营的当地人,但这些利益在整个利益“大蛋糕”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当地人提供自己的自然资源、贡献自己的文化资源,乃至牺牲自己的发展机会所创造的这部分间接利益,更应该在收益分配中得到体现。“在对经济发展滞后的民族提供外部援助的多元化发展中,立足于相关各方共同利益的基点,以产权关系或其他经济契约关系相联结而形成的稳定的经济支持,应成为主流形式。”[54]针对目前生态保护区利益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政府从政策角度、学者们从学理视角提出了生态补偿的设想。“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部分收益返还给生态保护地政府和居民。”[55]对于渝东南生态保护区来说,应该“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56]生态保护是公益性事业,其服务价值必须具有公益性特征。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生态补偿的原则是:“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这种补偿应该是多元的,政府可以从公共事业经费中拿出一部分,企业应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旅游者应从消费经费中拿出一部分。这些补偿是当地人应该获得的保护经费(资源收益、责任收益),而不是“扶贫款”“救济金”。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还需要进行广泛的宣传,增强民众的生态补偿意识。不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应对自己消费的资源做出补偿。[57]对于渝东南生态保护的建设利益分配,重庆市政府正在探索一些有益的财政政策,主要有:“加大生态财力补偿;按最高比例分配区县各项补助;保持民族地区转移支付逐年增加。”[58]这里要强调的是,补偿不仅仅是促进当地人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在于增强生态保护贡献者的再生产和发展能力,把外部补偿转化为内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形成自我“造血”的能力。
发展人类学所倡导的“发展意识”“参与意识”观念与当下倡导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是完全一致的。“可持续发展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的。”[59]生态保护区就是把这三者纳入一个整体中,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确保在一个区域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后促进一个地方全面可持续发展,使这种发展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需要,同时又尽可能地不损害后代人的生存需要。在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建设中,要确保“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生态目标的实现,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必需的追求。在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建设中,要强化“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渝东南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不是为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而进行的保护,任何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只有在“以人为中心”的前提下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当地人民群众收入、改善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才能取得实效。从生态保护发展区内的区(县)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该地区都基本上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当地人民群众都希望得到快速发展,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因此,在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建设中,应该更加注重群众的增收致富,增加当地人参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活力。只有一切从民众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出发,才能使生态保护区建设得到可持续发展。
第二,要把民众参与作为发展的动力。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动力来自当地民众。虽然,渝东南生态保护区来自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但要真正实现其保护发展的目标,最终得依靠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保护区内民众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保护区的建设质量和效果。因此,在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实际建设中,要提倡“参与式发展”的观念,实现“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的转变,充分调动和发挥保护区民众参与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改变渝东南民众在长期的“扶贫帮困”下形成的“等、靠、要”思想,让外部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资金支持,变成自己的发展助推力,让保护区民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适合当地文化和自然生态状况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三,要把利益分享作为发展的保障。生态保护从长远的目标来看,是为了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但是在短期来看,对生态保护区建设做出最直接贡献的当地人在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牺牲了一定的利益。因此,在渝东南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当地和民众所损失的利益,建立起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重庆市在建立生态保护区时,已考虑到了这种状况,提出了“确保渝东南人均财力增幅高于重庆市平均水平。”[60]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补偿不仅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全社会的支持。也就是说应该在全社会建立这种补偿制度,对于任何涉及生态资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对耗费的生态资源作出一定的补偿,并且把这个补偿的一部分返还给保护区人民。
[1] 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M].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60.
[2] 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M].欧阳敏,邹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52.
[3] 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张景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54.
[4] 杨小柳.发展研究: 人类学的历程[J].社会学研究,2007(4 ):188-189.
[5] 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M].刘珩,石毅,李昌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77.
[6] 杨文英,罗康隆.发展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4 ): 18-19.
[7]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
[8] 侯豫新.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9(2):69.
[9] 杨小柳.发展研究: 人类学的历程[J].社会学研究,2007(4 ):191.
[10] 周大鸣.人类学导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328.
[11] 孙政才.加快建设五大功能区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注入新的动力活力——在市委四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N].重庆日报,2013-09-16.
[12] 吕雯雯.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 环境与经济谋求“双赢”[N].重庆日报,2013-09-25.
[13] 伍兹.文化变迁[M].施惟达,胡华生,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69.
[14] 杨小柳.发展研究: 人类学的历程[J].社会学研究,2007(4 ):196-199.
[15]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621-622.
[16] 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李伯杰,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2.
[17] 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M].欧阳敏,邹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2.
[18] 丁立群.发展:哲学人类学的视野内[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7.
[19]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EB/OL].新华网,2012-11-15.
[20] Arturo Escobar.Anthrop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Encounter:The Making and Marketing of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J]. American Ethnologist,1991,18(4),660-661.
[21] 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7.
[22] 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M].穆尔.欧阳敏,邹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40.
[23] 王军.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30.
[24] 杨庆育.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地方样本:一个直辖市例证[J].改革,2013(12):76.
[25] 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M].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21.
[26] 陈维灯.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重要生态屏障如何守护?[N].重庆日报,2013-10-29.
[27] 郭占锋.走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国际发展项目[J].开放时代,2010(1):131.
[28] 叶敬忠,陆继霞.论农村发展中的公众参与[J].中国农村观察,2002(2):52.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Z].文非遗发[2010]7号,2010-02-10.
[30] 叶敬忠,陆继霞.论农村发展中的公众参与[J].中国农村观察,2002(2):52.
[31] 周大鸣,秦红曾.参与发展: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J].民族研究,2003(5):46.
[32] 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M].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9.
[33] 周大鸣,秦红曾.参与发展: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J].民族研究,2003(5):46.
[34] 何星亮.从人类学观点看中西部的发展[J].民族研究,1997(6):41.
[35] 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M].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85.
[36] 彭兆荣.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3.
[37] 王守丰.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J].广西民族研究,2014(5):68.
[38] 叶敬忠,陆继霞.论农村发展中的公众参与[J].中国农村观察,2002(2):52.
[39] 杨清媚.人类学与发展:一个两难的话语[J].社会发展研究,2014(1):216.
[40] 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M].欧阳敏,邹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65.
[41] 刘晓茜,李小云.发展的人类学概述[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44.
[42] 刘晓茜,李小云.发展的人类学概述[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44.
[43] 杨小柳.发展研究: 人类学的历程[J].社会学研究,2007(4):202.
[44] 叶敬忠,陆继霞.论农村发展中的公众参与[J].中国农村观察,2002(2):58.
[45] 杨小柳.发展研究:人类学的历程[J].社会学研究,2007(4 ):197-202.
[46] Peter D. Little. Anthropology and Development[M]//Satish Kedia and John van Willigen(eds.) Applied Anthropology:Domains of Application,Westport,CT.:2005:47-48.
[47] 王宇丰.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它农业困境[J].广西民族研究,2014(5):68.
[48] 李文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5(1):2.
[49] 秦兆祥.鄂尔多斯盐碱化湖区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研究[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1(1):64.
[50] 李雨停,丁四保,王荣成.中国贫困区域发展问题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9(9):132-139.
[51] 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M].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29.
[52] 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M].欧阳敏,邹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6.
[53] 周霄.民俗旅游的人类学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12-13.
[54] 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M].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86.
[55] 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课题研究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56] 李传宏.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探讨[J].重庆行政,2014(6):4.
[57] 莫延芬.生态旅游中的社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以大山包国家级自然保户区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0(12):50.
[58] 杨庆育.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地方样本:一个直辖市例证[J].改革,2013(12):85.
[59] 袁同凯.地方性知识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东北地区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7(2):118.
[60] 杨庆育.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地方样本:一个直辖市例证[J].改革,2013(12):85.
(责任编校:杨 睿)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t Southeast Chongq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TAN Hong
(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ResearchCenter,ChongqingCollegeofArtsandScience,ChongqingYongchuan402160,China)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zone at southeast Chongqing, which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has important era significance. Under current seriously changing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is new-style positioning for a certain area. In any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must be considered, which ar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construction. Based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zone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regards the development as a process of a kind of culture, economy and politics. The idea and method of the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have strong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zone at southeast Chongqing;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03-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1&ZD12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重点项目(JD2014—002)“传统工艺生产性保护研究”
谭宏(1963—),男;二级教授,重庆文理学院副校长、重庆文化遗产学院院长,重庆市品牌学会会长,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重庆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主要从事人类学、经济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2.010
X17
A
1672- 0598(2017)02- 0076-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