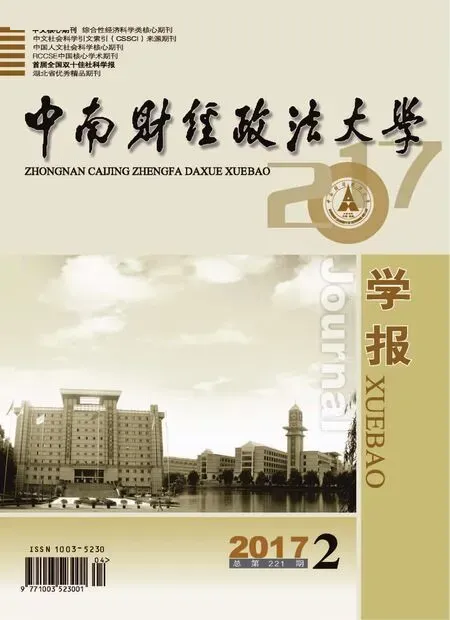“边界”效应下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以贵州岜沙苗寨为例
王子超 王子岚 贾 勤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2.英国剑桥大学 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英国 剑桥郡 CB21QH;武汉大学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2;3.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边界”效应下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以贵州岜沙苗寨为例
王子超1王子岚2贾 勤3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2.英国剑桥大学 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英国 剑桥郡 CB21QH;武汉大学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2;3.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边界”效应多产生于一些省际交界民族地区,在促进原生态文化保护的同时却又制约着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位于湘桂黔交界处的从江县岜沙苗寨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的一手资料,阐释了地域文化、心理防御和农业经济生活“边界”效应对乡村旅游产业的影响。结合这三种“边界”效应,以突破和保护为思路,提出了旅游设施与产品营销升级、有限开发与游客引导、社区参与经营与利益分配等构成的联合驱动旅游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跨越三重“边界”,搭建村民与政府、旅游企业及游客沟通桥梁,对其他省际交界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亦有一定的适用性。
“边界”效应;省际交界地区;乡村旅游;岜沙苗族;旅游业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贫困县要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同步迈入全面小康。要激发贫困地区居民走出贫困的志向和内生动力,“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1]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旅游业是国民经济重要增长点,是带动贫困地区致富的优势产业之一。苗族村寨多处西南偏远山区,贫困人口多,是西部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之一。优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建筑风格、传统的农业景观,是其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围绕民族地区特色,分析“内外结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积极寻找对策,有助于苗族村寨实现科学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乡村旅游产业,是以乡村地域为活动场所,以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景观、聚落景观、经济景观、文化景观、绿色农产品等资源为依托,以旅游设施为条件,以休闲为主要目的,为城市居民或旅游者提供休息、娱乐、观光、旅游、体验的经济活动[2]。中国的乡村旅游产业主要有5种发展模式,分别是:以旅游者需求及偏好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模式”;由乡村来进行旅游资源设计的“供给推动型模式”;以旅行社等来积极推动、促销产品的中介影响型模式;由政府主导基础设施建设、行为管理及扶贫开发的支持作用型模式;由需求、供给、支持、中介等多因子驱动产业发展的混合驱动型模式[3](P113-120)。
“边界”一般是指地区之间的界限。本文所论“边界”将之上升为三个层面:民族村寨所地理环境边界、心理防御边界与经济理念中的边界。这些“边界”产生的效应是,民族村寨的原生态文化得到高度保真,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我国省际边界地区很多是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固守传统的文化心态常常面临旅游发展带来的冲击。通过“边界”效应的突破和保护,可以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省际边界地区由于地理的隔绝性,使其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受限。安树伟认为“行政区边缘经济”空间经济现象,因省际交界地带多被山川、河流等自然屏障分割,容易出现“三不管”现象。且交通不便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桎梏,导致人们安于现状,经济观念无法更新[4](P35-39)。焦世泰指出我国省级行政区陆路边界线广阔,蕴藏丰富的文化资源。但省际边界区域更多地表现为经济的欠发达性,形成了一种具有明显板块性和边缘性特征的“行政区边缘经济”。尤其是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的原因,区域经济的边缘性和分割性更加突出[5]。这些可以总结为地域文化的“边界”性。
一个群体的心理防御边界的形成,往往基于历史上留下来的集体性记忆。Halbwachs指出,基于一个特定的空间范围之内的集体性记忆,可以长久得到保存[6](P192-235)。段会平等认为每个民族有自己特定的经济生活、心理和价值体系,从而产生了边界[7]。赵玉燕指出,基于历史上与封建王朝的冲突,湘西山江苗族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生存状态,形成面对旅游活动时的“惧感”。关于冲突的历史,可以从中国和南亚很多地区的苗民口头记忆中得到佐证[8](P25-49)。和思鹏在最新的研究中指出,政府和旅游公司跨越“边界”的开发与管制,遭遇来自少数民族村寨的抵制[9]。这里谈到的“边界”,可以理解为旅游开发中执行者超越了权力“边界”的同时,也伤害了村民的心理“边界”。
Forster认为,农民倾向于把周边社会、环境甚至自然界看做是“有限”的一个空间,在该空间内,生活需要的所有东西如土地、资产、荣誉、友谊、爱情或安全感,都是短缺的商品,因为他们没有直接的能力增长其数量[10]。同时,McAnany提出,礼仪文化把社会生活和物资条件联系在一起;人们的经济活动过程会超越功利性的考虑,而受到仪式、习俗等构成价值观因素的影响,从而排斥一些即使会带来更多经济收入的活动[11](P1-16)。这些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生活“边界”的“自控”性。
在有关苗寨的乡村旅游研究文献中,吴必虎等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研究,有助于推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有必要加强民族文化旅游理论的研究,目前学界研究有待科学化、系统化[12]。何景明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强调这里位于“三不沿”的内陆边远贫困地区,社会长期较封闭,要审慎地选择旅游开发方法以保护“地方感”[13]。但未就“边远”这一论题做深入探讨。王三北等认为在处理旅游发展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时,应充分尊重民族主体的需求,提倡社区的广泛参与,并由政府扮演好引导角色[14]。赵世钊等分析了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机制,指出旅游开发造成外部力量与信息注入少数民族村寨,造成村寨民族文化异变、管理者与村民矛盾加剧,从而影响了扶贫效果,必须通过处理好扶贫系统与内部发展的关系等措施得到解决[15]。
我国有20个自治州和55个自治县处于内陆省际边界,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壮侗走廊等民族聚居区基本上处于其中,这些地区的经济协同发展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不容忽视[16]。苗族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黔、湘、鄂、川、滇、桂、琼等省区,岜沙苗寨位于湘桂黔省际交界地区,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与这些省际交界地带民族村寨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因其苗族原生态文化的“活化石”称号在国内外游客中知名度极高,因此本文选择其为代表性案例。具体涉及岜沙苗寨的直接研究成果不多,主要分为几个主题。第一,围绕岜沙民俗文化展开。如范生姣研究岜沙衣着头饰、稻作文化、习俗节庆[17]。许星等探讨岜沙村民的着装习俗、审美观念和文化内涵。第二,从旅游产业的社区参与和综合开发入手[18]。卢彦红等从岜沙女性居民较少参与旅游业活动,分析了岜沙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19]。周坚等结合岜沙的聚落形态和地理位置,提出旅游开发是岜沙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必须注重聚落保护、打造民生工程和规范旅游业发展[20]。第三,围绕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观展开。如吴正彪结合岜沙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背景,对岜沙苗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分析[21]。
综观国内外的理论探讨,关于地域文化“边界”、心理“边界”和经济生活“边界”效应的研究比较零散,还不够深入和系统化,但是研究者提出的集体性记忆与空间的关系、民族惧感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值得引起重视和进一步研究。同时,苗寨旅游作为民族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对旅游产业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博弈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到底如何达成两者之间的平衡,探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目前把三种常见的“边界”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新的“边界”效应理论体系的研究还十分欠缺,本文基于这一新视角,探究如何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在2006~2015年间,多次深入苗寨居住和调研。调研发现,岜沙苗寨的乡村旅游产业处于初级开发阶段,贫困状态改善并不显著。而该地存在上述讨论的三种“边界”效应,影响了旅游产业的发展。第一,岜沙苗寨与外界存在的纵向与横向边界,阻碍了游客进入和商品流通。第二,基于苗族在历史上曾被其他部族欺压的传说,岜沙村民存在一种心理防御边界,这使游客无法获得真切的旅游体验。第三,在资源紧缺和民族信仰的共同作用下,岜沙村民形成一种具有控制性的农业经济生活边界,一旦旅游收入分配不公,村民将对参与旅游活动持消极态度。
下文将以湘桂黔边界地区的贵州岜沙苗寨为例,通过实地的旅游产业考察调研,分析如何突破和保护这些“边界”效应,从而对其他省际边界地区的民族村寨发展旅游产业起到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作用。
二、岜沙苗寨“边界”效应对乡村旅游的影响
岜沙苗寨是世界仅存的苗族远古文化完整保持者。村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丙妹镇,地处“黔南门户、桂北要津”[22](P8)。所在地属于西南石灰岩山区,农业资源短缺,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其在有限资源基础上脱贫致富的最可行途径。就从江县而言,2007年以来旅游产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新的主导产业之一(见表1)。

表1 从江县2007~2015年国民收入及旅游相关统计数据
注:根据从江县政府2007~2014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公布的2015年统计数据整理[23][24]。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从江县“旅游活县”政策的逐步推进,2011年开始从江县旅游综合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实现翻倍,2014年以后增长趋缓。借助2014年底开通的贵广高铁,贵州省开始迎来更大的游客潮,岜沙苗寨的旅游产业应抓住新的机遇为从江县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2003~2015年间从江县政府对岜沙景区旅游设施的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陆续修通了岜沙苗寨与从江县城之间的公路、文化宣传中心、生态迎宾表演场,建成了延伸至岜沙几个村寨的青石板游览步道。还以政府为主导,前往广州开展过旅游营销推广活动,但旅游产业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贡献度仍有待提高。
一方面,2012年从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从江县的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为40.7%(贫困人口达13.03万人)。2014年,人民网公布的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中仍有从江县。至今,岜沙苗寨400多户村民的生活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在寒冬季节仍存在缺少生活物资的现象。另一方面,根据笔者的走访与调查,游客们普遍反映旅游体验不足,而岜沙村民认为旅游收入不足以改善生活,游览步道上的游客时不时“失控”闯入吊脚楼侵犯了私人空间。可见,游客与村民之间尚未建立起科学的交流机制,旅游发展方式有待进一步改善,而这与下文探讨的“边界”效应有重要关联。
(一)地域文化“边界”效应促进原生态文化保真
岜沙苗寨原生态的生活与生产方式,1000多年来得到了高度保真,为开发乡村旅游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基础,而这源于当地的地域文化“边界”效应。
就垂直纵向分析,从江县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山地丘陵过渡地带,其所在的月亮山海拔1497米,高俊巍峨,山岭连绵[21](P103)。岜沙苗寨相对下方的从江县城而言,处于海拔较高之处。因此,岜沙呈现的是一种保留在高地的民族文化。就平面横向分析,这里属于过去划分的“生苗”之地。明清两代,与汉族交往少且不服管制的“生苗”,“主要分布在湘西、黔东北的腊尔山脉一带和黔东南的清水江、都柳江流域,封建统治者特称其为‘苗疆’”[25](P52)。从江县处于都柳江中游、湘桂黔交界附近,这里在古代长期是“三(省)不管”的。这对保持岜沙苗寨完好的原生态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树伟提出的“行政区边缘经济”空间经济现象中[4],省际交界地带常表现出区位的边缘性、欠发达性。岜沙苗寨正是如此,湘黔桂三省交界地带有大山等自然屏障,是与外界经济物资及思想交流的严重障碍,长期封闭状态下文化得到保真的同时文化思想亦趋于保守。笔者对岜沙苗寨与外界的纵横边界关系绘制了一张拓扑关系图(见图1)。

图1 岜沙苗寨与外界的平面横向与垂直纵向边界拓扑关系图
(二)心理防御“边界”效应限制旅游发展
在山顶岜沙景区,除了生态迎宾表演场、民族风情区、纪念亭、秋千区,苗族村民的许多文化习俗并未通过旅游开发展现给游客。这里的村民并不欢迎外人打搅,从而使得游客无法获得进一步的旅游体验。
Halbwachs关于特定空间范围内集体性记忆[4](P192-235)和赵玉燕关于苗族对外部世界“惧感”[6](P193-235)的观点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岜沙村民居住在“三省交界的山顶上”这样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严重影响了村民对旅游业的态度。根据笔者在2007年对岜沙宰庄寨贾红仁等老人的访谈得知,无论外面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村民们始终将曾受外来歹徒欺压过的惨痛历史,保留在深刻的集体记忆中。此外,岜沙村民所固守的苗族古老生活方式,也曾经被寨外的人认为是落后和野蛮而受到歧视。即使目前外界对苗族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并认定这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岜沙村民在上述集体记忆与“野蛮部落”历史标签双重影响下,仍与外界形成主动式的心理隔离,长期抵触外来影响,包括新的发展机会如发展旅游业。
(三)农业经济生活“边界”效应加固原有生活模式
Forster和McAnany的理论,可以解释岜沙村民的农业经济生活“边界”。如同Forster提到的“短缺”性[10],在封闭、隔绝的“地域”边界效应下,岜沙村民会时刻觉得资源紧缺,从而控制其使用量。又由于心理的“边界”,他们不愿迁往山下水源丰沛、土地平坦的地方,因而使得他们对生活资源紧缺感更为强烈。他们主要种植抗旱性强的大叶青菜作为主要蔬菜,大部分家庭的粳米、糯米和肉类产量仅容饱腹。
又如McAnany提到的仪式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11],岜沙村民的经济活动深受传统仪式、习俗因素的影响。信仰树神的他们须在特定时间参加祭祀和庆典,例如映山红节、吃新节、折禾、芦笙节、苗年等,参与这些村庄与家族的仪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岜沙村民“幸福感”的重要部分。举办这些活动的物资需要日常耕种、养殖、收集与准备,为此,很多人甘愿在原地维持固有的生活模式而极少外出务工。
因此,岜沙村民刻意维持着古老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不想过多参与到外部社会的市场交换当中。图2展示了这种农业经济生活的“边界”效应,但是这种紧缩性的生活模式逐渐受到不断发展的外界生活方式的影响。

图2 农业经济生活的“边界”效应
可以说,三种“边界”效应是互相促进并融合而成的。偏远的地域与相对封闭的高地生存空间,是集体记忆与心理防御边界能保存数百年的重要条件。岜沙村民的传统经济生活,又正好适应了这样的空间环境,也体现了苗族这个历史上曾经多次迁徙的民族,与其他民族为邻的顽强生存意志与生存智慧。发展岜沙苗寨的乡村旅游产业,必须考虑这些效应,选择科学的发展策略。
三、岜沙苗寨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设计:“边界”效应的突破与保护
岜沙苗寨具有极高的乡村旅游开发价值,但须关注以上三个“边界”效应的存在。这里地处西南偏远民族地区,远离主流及海外客源市场,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需要协调,因此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旅游供需方和中介联合驱动。故以上文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中的第五种为基础,提出“‘边界’效应关注下的联合驱动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见图3)。

图3 岜沙苗寨“联合驱动”下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一)旅游设施与产品营销升级
为使游客获得更多的旅游体验,同时不侵犯岜沙村民的私人生活空间,应由政府部门对“边界”效应实施科学突破与保护(见表2)。

表2 “边界”效应的突破与保护
第一,2014年12月开通的贵广高铁,途经从江县,打通了岜沙苗寨旅游与重要客源地间的黄金路线。随着与广州、桂林进入3小时内旅游圈,若能把握好岜沙苗寨对海外游客极具吸引力这个关键点,抓住契机开通高铁站通往岜沙苗寨的直达巴士,可能获得更多的从广东和广西分流而来的港澳台同胞与国际客源。
第二,应在抵达山寨的游览步道的基础上改建为“景观廊道”,这样既能增加游客文化体验的满足感,又能通过有效管理控制游客的文化“入侵”行为。应高度关注和充分尊重岜沙村民的心理边界,有限地延伸和严格管理这种廊道,用景观栅栏和步行栈道把游客和苗寨生活区隔离开来,并提醒游客绝不能随意走下廊道。
第三,优化现有的营销策略。基于岜沙苗寨受限的地域文化“边界”,岜沙不应满足于“带枪的部落”这一老旧的形象标签。《鸟巢》(2008)、《滚拉拉的枪》(2009)、《岜沙汉子》(2015),这些优秀电影都是以真实的岜沙为背景拍摄的,可作为旅游营销素材充分利用。还可建立专门的网站,以“原生态的苗寨织染文化”、“远古苗疆的农俗再现”等来丰富营销内容,突破地域文化“边界”的空间限制。在海外,岜沙苗寨文化的吸引潜力更大,也可以加强与欧美和东南亚等地旅行社的合作,共同使岜沙农业生态文明这一形象走向全球。
(二)有限开发与游客引导
根据笔者的调查,岜沙村民根据四季节气和劳作规律,有很多乡村文化仪式、农作物耕种方法、纺线、蜡染技术都极具观赏性,可以考虑开发成为旅游景观,突破人们对其“陋俗”的误解,增加其民族自信心。表3列举出的可供开发旅游产品内容,突破了过去的有限景观展示,可满足游客的多样文化需求。

表3 农业旅游景观的开发设计
开发过程中,必须以关注心理“边界”为保护性的前提,与村民做好充分的协调工作。首先由推动县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与村民沟通,使村民充分了解我国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要性及我国各民族和谐发展好状况,实行心理安抚;强调原生态旅游产品开发对改善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其次提醒游客对大部分景观“只参观、不打扰”,如村寨景观和农业生产场景等;对于祭祀仪式实行有限度参观,对于丧葬仪式,按照岜沙村民的惯例,绝不允许外人参观和打扰。
考虑到岜沙村民的心理“边界”效应,政府部门应主导游客文明礼仪培训教育工程。外来游客大部分来自经济水平更高的地区,难免与岜沙村民发生不同文明程度的文化碰撞。应通过旅游管理部门、旅行社导游等提醒进入村庄参观的游客,不能随意拍照或炫耀自己的装备,包括用钱物与村民换取合影。
与此同时,旅游开发主导部门或旅游经营企业,应协助游客理解当地村民经济生活的“边界”效应,这有助于实现乡村旅游的生态教育功能。旅游从业人员应倡导游客向岜沙村民学习其环保理念,这也能提升岜沙村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于旅游业发展的信心。至于在农业耕种与副业劳作中,尊重自然、节约能源的很多其他做法,更应该得到游客的肯定。
(三)社区参与经营与利益分配
基于前述观点,封闭的地域文化“边界”,是岜沙村民产生物资紧缺感,从而产生经济生活“边界”的重要原因,这是发展旅游业并提升扶贫效果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为此,应带动村民扩大旅游收益突破经济生活紧缩的“边界”,保障旅游参与和获利的公平化,减少经济生活“边界”下社区对旅游业接受度的削弱效果。
岜沙的旅游收益可以通过“将蛋糕做大”进行突破。据中国经济网的报道,2014年国庆期间,“岜沙景区接待游客12.36万人次,实现景区门票收入103.5万元”[26],景区从每名游客身上只获得旅游收入8元左右,而景区的门票是80元/人,可见有相当一部分游客并未购买高达80元的门票观看表演,表演的吸引力有待提升。对此,可以借鉴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印第安人参与管理的方式,让当地村民尽量多地参与到景区的文化展示和其他服务中。如在保留现有景区门票的前提下,对于深入景观廊道参观体验农业习俗者,提供更多旅游套票供游客选择。村民可以加入到农俗展示、农家餐饮经营与服务、景区秩序的维护和环境保护中来。
人们在长期的资源短缺和贫困状态下,面对旅游业的冲击,容易对优先接触旅游业并获利较多者产生不良情绪,从而影响当地社区对旅游业的接受程度。因此,必须考虑如何让旅游业的参与和分配尽量公平、公正,可以考虑通过“政府+投资商+社区+居民”利益分配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四、结论与启示
以口述历史为主的苗族历史,是可以被不断更新的,他们向来尝试着吸收与适应周围所发生的变化。苗族人正因为兼有“固守”与“变化”的特点,而拥有强大的适应能力,所以能在千年的“漂泊与迁徙”中,既保持文化的原真性,又不断纳入新的文化因子,适应时代的发展。所以,乡村旅游业与苗族村寨的“边界”之间,随着外来信息的不断注入,同时经过政府、企业和村民共同的协调,终会达到平衡。
偏远地区的苗族村寨,面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的“边界”效应,是中华民族面对全球化时心路历程的缩影。这些“边界”效应,可以通过科学的突破和保护来克服,正如传统文化既要创新发展又应坚守特色。本文研究的少数民族个案,对于众多位于省际交界地区、固守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只要抓住“边界”效应存在的根本原因,深入了解乡村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充分考量村民的心理顾虑、尊重其自我选择,就能逐步地跨越“三重”边界,搭建村民与政府、旅游企业及游客沟通的桥梁,实现通过旅游产业脱贫致富而又保持文化特色的目标。为此,我们必须立足民族地区资源环境条件和民族传统文化特点,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学确定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与实施路径,促进民族文化传承、村民就业增收、生态环境保护、民族地区特色旅游融合发展。
[1] 王子晖.脱贫之战,习近平发出总攻令[EB/OL].(2016—7—25)[2016-12-2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25/c_1119267767.htm
[2] 丁培卫.近30年中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与路径选择[J].东岳论丛,2011,(32)7:114—118.
[3] 张树民.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与政策保障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4.
[4] 安树伟.行政区边缘经济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5] 焦世泰.滇黔桂省际边界民族地区整合发展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0,(4):164—169.
[6] Halbwachs,M.On Collective Memory[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7] 段会平,吕永红.跨越文化边界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2)3:66—70.
[8] 赵玉燕.惧感、旅游与文化再生产——湘西山江苗族的开放历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9] 和思鹏.“国家—社会”视阈中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历史逻辑、边界重构与机制创新[J].贵州民族研究,2016(10):56—60.
[10] Forster, G.Peasant Society and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J].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5,(2):293—315.
[11] McAnany, P.A., Wells, E.C.‘Towards a Theory of Ritual Economy’.In Dimensions of Ritual Economy[M].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12] 吴必虎,余青.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综述[J].民族研究,2000,(4):85—94.
[13] 何景明.边远贫困地区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省思——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中心的考察[J].旅游学刊,2010(2):59—65.
[14] 王三北,高亚芳.理性价值的回归:民族社区旅游发展中文化传承功能的升级演进[J].民族研究,2008,(3):31—40.
[15] 赵世钊,吕宛青.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机制的协同学分析——以贵州省朗德苗寨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5,(1):152—155.
[16] 李俊杰.浅谈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N].光明日报,2008—08—05(11).
[17] 范生姣.岜沙苗寨的民俗文化[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3(4):17—29.
[18] 许星,廖军.黔东南岜沙苗族服饰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0,(4):113—116.
[19] 卢彦红,徐升艳,吴忠军.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以贵州岜沙景区为例[J].民族论坛,2008,(9):51—53.
[20] 周坚,王建平.贵州省岜沙苗寨的旅游开发与经济发展[J].改革与战略,2010,26(8):120—122.
[21] 吴正彪.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典范——贵州省从江县岜沙社区苗族村寨调查报告[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1):103—110.
[22] 政协从江县文史委员会.远古遗风.从江文史资料第五辑(旅游专辑)[M].黔新出(图书),2005.
[23] 2007~2014年从江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信息网)[EB/OL].http://www.tjcn.org/.
[24] 从江县四举措扎实推进旅游扶贫各项工作[EB/OL].(2016—6—23)[2016—11—24].http://www.qdn.gov.cn/ztzl/qdndfpzl/fpcs/201606/t20160623_669447.html
[25] 李廷贵.苗族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26] 吴家辉.从江县百万专款保护民族民间文化[EB/OL].(2014—10—22)[2016—12—26].http://cz.ce.cn/kx/201410/22/t20141022_2013679.shtml.
(责任编辑:陈敦贤)
2017-01-2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我国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生态创新研究”之子课题“文明审视下的中国乡村游之游客行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31541510804)
王子超(1977— ),女,湖南慈利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王子岚(1981— ),女,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研究员,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贾 勤(1963— ),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馆员。
F590.31
A
1003-5230(2017)02-0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