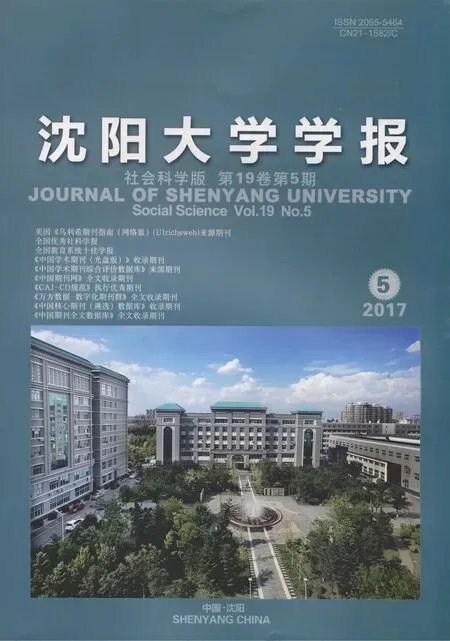论爱与教育超越
谢 桂 新
(惠州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 惠州 516007)
论爱与教育超越
谢 桂 新
(惠州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 惠州 516007)
分析了爱在教育“量”的超越、教育“质”的超越、教育“史”的超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现代社会需要教育超越,爱在教育超越中的作用也尤其需要引起重视。
爱; 教育超越; “量”的超越; “质”的超越; “史”的超越
教育超越是教育的理想追求,是教育超出既有社会现实的规定和束缚,不断地追求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所以论及超越(transcend)而不谈发展(develop),是因为超越(transcend)更强调“超出,胜出,优于”的含义,也就是教育超越内含教育发展,是教育发展的更高层次追求。教育超越在不同阶段、不同时空需要不同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支点才能产生并发挥作用,这个支点就是爱。教育中的爱不仅仅是教师之爱,还是教育决策者、教育管理者、教育组织者、教育实施者等人的爱;教育中的爱不仅仅是爱的情感,更是爱的意志、爱的行动和爱的智慧。爱是教育超越的支点,也就是爱能够超越阶段和时空,始终作为固定不动的一点对教育的超越起着支撑作用。因为教育活动的对象是具有主体性、主动性的活生生的人,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的发展和完善,所以“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发现生命、关怀生命、促进生命培育的社会活动”[1],这种对生命的培育活动,只有以爱为其支点,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生命、关怀生命,从而实现对历史和自身的超越。
笼统地谈教育超越没有太大的意义,人们需要对教育超越有一个结构性的认识,也就是要寻找教育超越的基本维度。谢维和教授认为,教育的发展通常具有两个维度,其一是教育活动的数量与规模发展的维度,其二是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益发展的维度。[2]由之,本文试从教育量的超越、教育质的超越、教育史的超越等几个维度探寻教育超越的支点----爱。
一、 爱与教育“量”的超越
教育“量”的超越可从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发展速度的提升两个方面来考虑。
在学校教育产生以后,教育规模的大小标志着受教育者人口的多少和教育的普及程度。刘庆昌教授认为:“统治阶级的需要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教育规模大小的决定性因素。”[3]也就是说,教育规模要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实现超越,需要统治阶级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理性思考。如果没有对所有受教育者不分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的爱和关心,教育就会沦为只有少数特权阶级才能享用得起的奢侈品,教育的普及更无从谈起。教育规模的重要标志是受教育者的人口数量,扩大教育规模的直接受益人是广大的适龄受教育者,显著标志是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但是,要扩大教育规模,进而实现教育量的超越,其背后隐藏着深刻而复杂的动因和条件,既要有对教育精神上的关注,又要有对教育人力、物力上的投入,还需要“从政策到策略,再从策略到计划的逻辑过程”[4]212,这其中从思想的萌芽到行动的落实,再到超越的产生,对受教育者的爱与责任始终是重要因素与核心力量。当然,统治阶级扩大教育规模也可能是基于政治或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教育始终是面向人的,从扩大规模到量的超越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完成,因此萌芽于人本身的爱是其他各种功利性或工具性需求的支点,没有爱,其他教育发展的人力、物力条件就没有情感支撑和精神动力,教育发展的杠杆将发生倾斜,教育超越不可能发生。
教育发展的速度由于是教育统计特征上的变化,所以也可看作教育发展的量变。教育发展的速度一般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相比较而言的,根据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后,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后行模式,即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再去发展教育;二是并行模式,即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三是先行模式,即教育发展先于或优于其他行业或经济发展的现有状态而超前、提前发展。在古代社会,教育发展的速度较慢,发展的模式是后行模式,孔子周游列国时的一段对话,表明了教育后行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做出的必要选择----当孔子走到卫国时,叹曰:“庶矣哉!”冉由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但是,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教育发展速度的快慢也即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则是社会对教育重视程度的体现。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写的《学会生存》一书指出,“现在,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于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4]35,“现在,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4]36,这即是“教育先行”和“教育预见”,是教育超越的世界之声。教育发展超越于或先于社会经济发展,“替一个未知的社会培养未知的儿童”,这要求教育决策者的远见卓识,也需要教育工作者的深刻思考,但都离不开对教育发展的强烈关注和高度重视。在我国,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了教育先行的思想:“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5]教育优先发展,这是对教育事业的爱,也是对“未知社会未知儿童”的爱,是包括着深刻哲思和远大抱负的爱。也只有这种爱的支撑,才能使教育的地位得以稳固,教育才能成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 爱与教育“质”的超越
教育活动除了数量与规模维度,还包含质量和效益维度。由于教育质量的发展变化是教育非统计特征上的变化,所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还常常带有一定的主观意向。这里我们从教育活动的构成要素来研究教育质的超越,因为要素是构成活动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因素,如果教育活动的各构成要素是真善美的统一,那么教育质的超越则有实现的可能。
1.教育主体的超越
教育活动的主体分别是教师和学生,教师是教育过程中“教”的主体,学生是教育过程中“学”的主体,教师和学生的超越,都与爱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无论是教书还是育人,他的直接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人,那么教书育人的过程就不仅仅是技巧的施展,而应该是心灵的艺术,教师应该对学生充满爱、充满理解、尊重和感染,体现出民主和平等的意识。教育中对教师的价值判定有两种,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正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因此人师是对经师的超越。但凡人师,必定是爱心充盈,名满天下。从孔子的“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到罗素“在教师缺少爱心的地方,无论是品性还是智力都不会得到良好的或自由的发展”,再到苏霍姆林斯基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古今中外的教育名家虽然教育思想、教育风格各有千秋,但都是爱的先驱和使者。但是,在教育过程中,教师的引导、教育是学生成长发展的外因,学生自身需要、认识、情感等方面的变化才是内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教育质的超越归根结底是学生对自身的超越。孔子曾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从知知者到好知者,再到乐知者,就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好知”还是“乐知”,都必定包含着学生的爱,或者是爱老师、或者是爱知识、或者是爱学习这件事本身。因为爱老师,“向师性”才产生了神秘的力量,收到神奇的教育效果;因为爱知识,才能从书中寻找到“颜如玉”“黄金屋”,从而自得其乐,乐在其中;因为爱学习,才可能忍受“头悬梁、锥刺骨”之痛而乐此不疲,乐而忘返。所以,爱是学生超越的支点,没有爱的学生,即使外表看似成功,内心也必索然无味,精神上无所依托,与教育的超越相去甚远。
2.教育内容的超越
教育内容是联系教师和学生的中介,教师通过向学生传授教育内容,使学生从不知到知,从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从继承到发展,从“未完成的人”到“走向社会历史的人”,最终达到教育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内容既是教师和学生知识传递的中介,也是师生情感和价值观传递的中介,还是承载师生之爱的重要媒介。同时,教育内容本身的超越也时时以教育者的爱为依托,闪烁着教育者爱的光芒。在教育的产生之初,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授的内容即是生产生活所必须的技能和技巧,如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神农氏教人稼耕,其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生活得更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生活的丰富,教育内容的组成也日益丰富多彩,满足了学生多方面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正如柳海民教授在其著作《教育原理》中所指出,教育内容从其涉及的范围来说,包括人类社会各种领域活动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技巧;从其价值来说,它具有发展人的智慧、品德、体力、审美能力和劳动能力等方面的作用;就其表现形态来说,有物质的、符号的、精神的、行为的[6]。如何在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中进行恰当的、适合学生发展需要的选择,成为教育内容超越的另一目标和方向,“如何使教育内容更加适合学生特点和社会要求,成为教育负责人、课程设计者和教师们经常关心的问题”[7]166。如根据人的思维发展特点、接受知识的先后次序和科学知识本身的逻辑顺序编排学校教育内容,能够使学生遵循着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到本质的逻辑轨道,高效率地获得人类积累的知识经验;又如“把普通教育的内容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共同的,所有人都必须掌握的最低限度内容;另一部分是各种选修课……这种办法保持了教育体制的基本统一,既保持了机会平等又能更好地满足个人的需求和发展的需要”[7]166。可见,教育内容的丰富、发展、变革和选择,都以学生的发展和需要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种为学生着想和为学生服务的精神实质即是爱,这种爱促进了教育内容超越的同时促进了教育质的超越。
教育手段的超越。教育手段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是指教育者将教育内容作用于受教育者时所借助的各种形式与各种条件的总和。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有人直接将爱即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本文赞同著名教育家、特级教师李镇西的观点:“就是不希望人们把爱心当成一种模式,一种手段,一种技巧……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情感,一种氛围……它自然而然地贯穿于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也不声不响地体现在教育的每一个细节,更潜移默化地浸润着每一个学生的心灵。”[8]这种爱在教育手段的超越中同样作用斐然。物质手段的超越是与教育优先发展密切联系的。优先发展教育,即为教育提供其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宽敞的教育活动场所与先进的教育活动设施,以及现代化的教育媒体等。这些物质形式与条件虽没有思想和情感,表面上看不到爱的影子,但其中必定渗透着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的重视,对学生更好学习条件的关注,愿意为其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以改善教育物质条件,实现教育物质手段的超越。教育的精神手段包括教育的方法、途径等。古往今来,教育方法随着历史的变迁已有千千万万,所以了解每一种方法的长处和短处,正确选择和使用教育方法是教育手段超越的必须。具有超越性的教育方法是以爱学生为出发点,以学生的幸福为最终目的的教育方法。“一堂课就像一首歌,它要由多种教学方法综合演绎而成,它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以适应学生不同器官的需要,使学生既有感官上的愉悦,也有思考中的乐趣,还有通过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享受。各种方法扬长避短,互相补充,错落有致,和谐统一,这样,学生在有张有弛中把全身心都调动了起来,从而体验到全面的幸福。”[9]反之,如果没有爱的情感和氛围,在教育中选取“支配、处置、压制、型塑”等规训的方法,那么就会有“人们听从某种灌输的‘真理’,但独断的‘真理’却压抑着智慧的启蒙;人们都在唱着道德的高调,但是‘道德’或者成为禁锢人们的精神的工具,或者成为掩饰社会各种恶的伪善的外衣”[10]。所以,没有爱作为支点的教育方法是没有走进学生心灵的方法,教育方法和手段没有超越,教育质的超越更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
当然,由于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在分析教育活动的结构时持有的视角不同,对教育构成要素的概括也会有所不同。以上对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的分析很可能也会挂一漏万,但是通过以上的分析,也足以反映出教育质的超越与人类的爱息息相关。
三、 爱与教育“史”的超越
教育“史”的超越即教育“今天”对教育“昨天”、教育“明天”对教育“今天”的超越。纵观整个教育发展的历史,即是一部超越的历史,在这个超越的过程中,教育的境界不断提升,爱的境界也不断发展,教育与爱的结合日益紧密。
关于教育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众多研究者已进行过多角度的探讨,形成了几种各不相同又相互联系的观点。其中,王本陆教授在划分标准中把教育和社会统一起来,以人的解放(发展)为标准,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的阶段划分,为我们考察教育史的超越与爱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有益的纵向线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即人身依赖的社会、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王本陆教授以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为指导,在把握教育、社会和人这三者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以人的解放(发展)为标准,把教育的发展历程分为依赖的教育(古代教育)、独立的教育(现代教育)、自由的教育(未来的教育)[11]11。独立的教育(现代教育)较之依赖的教育(古代教育)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由脱离到结合,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以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由专制、特权的教育走向民主的、大众的教育,教育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形成了系统的教育科学理论等。在独立的教育(现代教育)对依赖的教育(古代教育)的超越中,不难看出教育境界有了层次的提升,其中跳动着更多爱的音符,教育公正、教育人道、教育尊重、教育民主在教育的超越中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自由的教育(未来的教育)是人类教育发展的理想境界,它将“消除现代教育客观存在的物质束缚、认识束缚、文明水平的束缚而真正达到教育的自由王国。”[11]66在教育向自由王国的跃迁中,爱已成为教育超越的唯一也是最高理由。人的发展成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发展人的多方面潜能成为教育存在的最大价值和主要理由,教育成为任何人都享有的、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和侵占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成为所有人的一种不可冒犯的尊严、一种享受幸福的过程。这时,教育真正成了为人的教育,爱与自由在教育的超越中尽情绽放。
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甚至也走过弯路,有过倒退。特别是现代教育片面追求教育的外在价值----教育如何适应社会的需要和教育的社会功能,而忽视了教育的本质属性----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使人成人,使人幸福地享受教育的滋养!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需要教育不断超越,走在社会发展的前沿,并引领社会发展的时代,所以,爱对教育的作用尤其需要受到关注。因为正是由于有了无数教育工作者的爱,才能使教育不断地摆脱各种社会现实的规定和束缚,努力追求发展和完善,从量的扩张到质的飞跃,从依赖的过去走向自由的未来,实现自身的理想和追求。因此,爱是教育超越的支点,爱使教育在走向更高更远的途中始终朝向真、善、美的理想之境。
[1] 王举. 基于“教育”生态的教育政策品格[J]. 现代教育管理, 2013(6):42-45.
[2] 谢维和. 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277.
[3] 刘庆昌,畅肇沁. 论教育的起源、发展与消亡[J].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1999(1):26-31.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1.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75.
[6] 柳海民. 教育原理[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04.
[7] 拉塞克,维迪努. 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M]. 马胜利,等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166.
[8] 李镇西. 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M].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7:205.
[9] 刘次林. 幸福教育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93-94.
[10] 金生鈜. 规训与教化[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3.
[11] 王本陆. 教育崇善论[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1.
LoveandEducationalTranscendence
XieGuixi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China)
It is analyzed that, love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educational transcendence of “quantity”, “quality”, and “history”. Modern society needs educational transcendence. The role of love in educational transcendence particular also needs to pay attention.
love; educational transcendence; transcendence of “quantity”; transcendence of “quality”; transcendence of “history”
2017-05-08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GD16XJY27)。
谢桂新(1975-),女,吉林梨树人,惠州学院副教授,博士。
2095-5464(2017)05-0605-04
G 40-01
A
【责任编辑李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