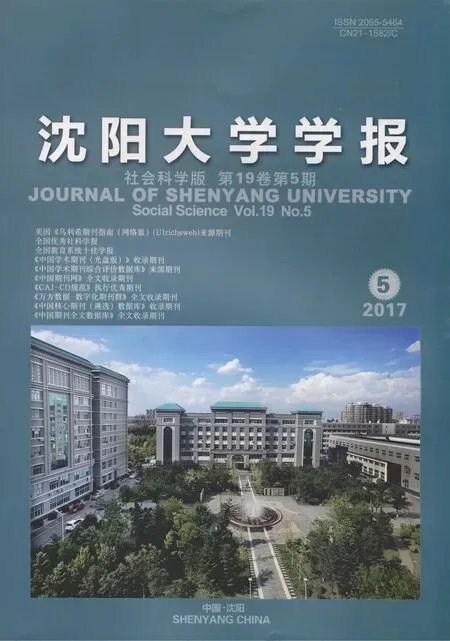方回道德反思的诗学诉求
王 昕, 高览小
(1. 石家庄学院 学报编辑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35; 2.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方回道德反思的诗学诉求
王 昕1, 高览小2
(1. 石家庄学院 学报编辑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35; 2.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主要根据《瀛奎律髓》,分析了方回的诗学思想和创作心态,认为其在诗选中极力推尊诗人杜甫,以“格高”作为评诗的首要标准,倡导诗歌的“熟淡”之美,意在证明自己爱国情怀与人格修养,表现了其自我反思和道德辩解的强烈愿望。
方回;《瀛奎律髓》; 道德; 诗学
方回(1227—1307),字万里,一字渊甫,号虚谷,别号紫阳山人,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因上书劾贾似道、王爚出知建德府。恭帝德祐二年(1276),率郡降元,改授建德路总管兼府尹。七年后罢,闲居终老。方回著述甚丰,今所知名者共二十四种,涵经、史、子、集,现存《桐江集》《桐江续集》《瀛奎律髓》《文选颜鲍谢诗评》《续古今考》《虚谷闲钞》六种*参见詹杭伦《方回的唐宋律诗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6页。詹先生在对方回生平、著作详考的基础上论述方回的诗学思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文多有参考。。方回诗学思想博大精深,学界前辈已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笔者主要据《瀛奎律髓》对其由宋入元后的特殊心态与诗学实践略作观照,以见宋亡之际一降元士人的复杂心理、人生选择和诗学取向。
一、 道德辩解与诗学实践
方回是文学史上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其率郡降元有损大节,为人不齿,甚者谓其品行卑污,巧诈伪劣,“见于周密《癸辛杂识》者,殆无人理”[1]。方回的降元行为与其反复表述的信仰的矛盾悖离成为时人和后学争论的热点,方回的人品与诗品的巨大反差也是宋元诗学和“徽学”研究者难以回避的话题。
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将高兴欲兵取严州。方回时知严州,曾主张以死封疆,并在《桃源行》一诗中慷慨陈言:“楚人安肯为秦臣?纵未亡秦亦避秦!”[2]方回深知降元于己损节、于国助亡,然而在生命和节义的痛苦较量中,方回借助历史学识和哲学变通思想,寻找了一系列放弃信仰和主张的理由,最后选择降元。方回在《先君事状》中为自己的行为作了种种辩解,这些辩解也正是促成他降元的心理依据:①临安已陷,严州于后,其罪可恕。方回自述:“行在所宰执大臣以嗣君名具表纳土,送玺于皋亭山,在正月十八日,军马入临安府易守,在二十日。回犹坚守孤城半月余……彼列阃连城,先下于临安未下之先者,可罪也。此一小垒,临安已下半月而后下焉,恕其罪可也。”②众人所议,严州不降,恐遭灾难。方回陈述当时情境:“王郎中世英、萧郎中郁提兵五千赉诏至郡,合众官吏军民一口同辞,惟恐有如常州之难,议定归附。”③全其郡民,虽非正义,有史可鉴。方回从《三国志·霍弋传》中找到更为可靠的历史依据:“陈寿书谓霍弋、罗宪,各保全一方,举以内附,此虽非人臣之正义,然国亡主迁,土地人民无所归,为小郡者,力不能全国矣,全其郡民可也。”*参见方回《桐江集》卷八,(清)阮元辑《宛委别藏》第10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18-519页。既然投降归叛可以上升为全郡保民的高尚行为,方回由心理矛盾到失衡,从而作出了悖离自己信念的行为。
方回在《先君事状》中进行辩解,意在洗刷自己的罪名,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宽容。然而,方回的辩解没有使人另眼相看,反而招致更多的指责和唾弃。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极诋方回:“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及北军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遍寻访之不获,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3]方回仕元,甚至遭到其女婿和门生的屡屡讦难。其实,方回自己也深感愧疚,他的降元理由能维持一时的心理平衡,但经不起理性深究和情感追问,他在不少诗中真诚坦率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情,如《重至秀山售屋将归》云“全城保生齿,终觉愧衰颜”、《送男存心如燕》云“苟生内自愧,一思汗如浆”*本文所引方回诗,如没有特别注明出处的话,均引自《全宋诗》。。方回后来罢官不仕,反思自己的道德品行,试图以诗文创作化释自己的心理纠结,凭借学术和文学成就重新为自己赢得立足之地,《杂兴》一诗大致表达这种意图:“岂无不朽句,作诗垂万篇。人品虽中中,此心无愧焉。”
至元二十年(1283)方回选编《瀛奎律髓》,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产生的结果。诗歌选本不仅能显示编者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情趣,也能反映其编选意图和内在的心理愿望。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以选、编、评注的方式构建文学赏论世界,自有为学诗者提供理想的教材、以纠正当时创作之弊的显在目的,如其序所言:“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学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参见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下文凡引《瀛奎律髓》者,均据此本。引文出处只标卷数和诗题。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人的现实行为和自然发生的心理过程密不可分[4],方回编著《瀛奎律髓》当亦有开释心理症结、重新确立自我形象的内在用意。从《瀛奎律髓》选诗和评注来看,方回极力推尊杜甫,诗主江西诗派,称赏高健诗格和平淡诗境,这与其说是其鉴于当时文衰诗落、欲救弊扬正的宣言,毋宁说是以诗歌选评方式进行的自我开释和自我表白,尤其是从诗人修养角度对唐宋诗歌思想艺术渊源进行追问和阐释,可称之为一种诗学意义上的辩解和诉求。
二、 尊杜:爱国情怀的表白
杜甫是方回诗学体系的核心,《瀛奎律髓》以杜甫律诗作为选诗和评论的参照和根本。据李庆甲先生统计,《瀛奎律髓》选录诗人385家,五、七言律诗实2992首(去重出之22首)。方回选评杜甫诗达221首,约占所选诗总数7%,居所选唐、宋诗家之首位。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赋予杜甫诗歌最高的评价,对其尊崇可谓无以复加,如下:
诗至老杜,万古之准则哉!(卷十六,杜甫《小寒食舟中作》评)
世间此等诗,惟老杜集有之。(卷十五,杜甫《阁夜》评)
此格律高耸,意气悲壮,唐人无能及之者。(卷十三,杜甫《野望》评)
凡老杜七言律诗,无有能及之者。而冬至四诗,检唐、宋他集殆遍,亦无复有加于此矣。(卷十六,杜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评)
方回又旗帜鲜明地把杜甫标树为江西诗派之祖,并列出宋代师祖杜甫的江西五子:“予平生持所见,以老杜为祖,老杜同时诸人皆可伯仲。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为五,其他与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诗之正派也。”(卷十六,陈与义《道中寒食二首》评)又明确提出“一祖三宗”的观点:“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余可预配飨者有数焉。”(卷二六,陈与义《清明》评)实际上,在方回的诗学体系中,除了江西诗人宗法杜甫,为“诗之正派”,唐李白、王维等著名诗人都属“老杜之派”,宋代的众多优秀诗人也都应纳入“老杜之派”。方回在《恢大山西山小稿序》中具体表述:“五言律、七言律及绝句自唐始盛,唐人杜子美、李太白兼五体,造其极。王维、岑参、贾至、高适、李泌、孟浩然、韦应物以至韩、柳、郊、岛、杜牧之、张文昌,皆老杜之派也。宋苏、梅、欧、苏、王介甫、黄、陈、晁、张、僧道潜、觉范,以至南渡吕居仁、陈去非。而乾淳诸人,朱文公诗第一,尤、萧、杨、陆、范亦老杜之派也。是派至韩南涧父子、赵章泉而止。”[5]卷三三在方回看来,“老杜之派”荟萃众家,阵容强大,是唐、宋诗歌发展主流。除杜甫一派外,方回认为“别有一派曰昆体,始于李义山,至杨、刘及陆佃绝矣”;而嘉定中“祖许浑、姚合为派者”实“江湖晚生皆是也”[5]卷三三。方回对诗歌派别的划分,立足于自己的杜诗研究和两宋以来人们的崇杜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方回的诗学体系是建构在他的杜诗研究之上,其杜诗观既是中国诗学史上杜甫崇拜的极致反映,也浓缩着两宋以来杜甫独尊诗学思潮的精神”[6]。
杜甫的楷范意义在宋代被确立,宋人尊崇杜甫,固然考虑到杜甫诗歌思想和艺术的杰出成就,而更主要是宋人从杜甫身上发现了儒家推尊的道德价值和精神境界。王安石《杜甫画像》云:“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7]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8]《潘子真诗话》记载黄庭坚也有相似表述:“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9]南渡后,经历了国破家亡、流离之苦的文人儒士对杜甫本人及诗歌有了更深的体会,杜甫忠君爱国的精神被高度弘扬。李纲《重校杜子美集序》云:“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句法理致,老而益精。”[10]1320又在《五哀诗》中褒扬杜甫:“平生忠义心,多向诗中剖。忧国与爱君,诵说不离口。饥寒窘衣食,容貌村野叟。自以稷契期,此理人胜否?”[10]248
方回弘扬杜甫罹遭动乱、身在下位却忧时爱国的怀抱和精神,这与宋人逐渐把杜甫典范化的旨向是一致的。如下所评:
老杜合是廊庙人物,其在成都依严武为参谋,亦屈甚矣。……老杜平生虽流离多在郊野,而目击兵戈盗贼之变,与朝廷郡国不平之事,心常不忘君父,故哀愤之辞不一,不独为一身发也。(卷二三,杜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评)
凡十六年间,无非盗贼干戈之日。忠臣故宜痛愤,而老杜一饭不忘君,多见于诗。如“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由来强幹地,未有不朝臣”、“领郡辄无色,之官皆有词”、“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夺马悲宫主,登车泣贵嫔”、“穷愁但有骨,群盗尚如毛”,皆哀痛恻怆,令人有无穷之悲。(卷三二,杜甫《避贤》评)
方回之说几乎是苏轼对杜甫评论的翻版,不过,方回列举出杜甫伤时忧世、忠君爱国的一系列诗句,充分展现了杜甫的精神世界。方回认为南渡前后诗人之忠愤爱国之诗,皆本于杜甫,这也是杜甫作为宋代诗人典范的主要根据。《瀛奎律髓》卷三二选评吕本中《兵乱后杂诗五首》,称赞诗中揭露现实的佳句,以为“老杜后始有此”。同卷评汪彦章《乙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四首》时发表感慨:“靖康中在围城中者,吕居仁、徐师川、汪彦章皆诗人也。居仁多有痛愤之诗。师川以邦昌之名名其婢,而诗无所见。彦章至此乃有乱后诗。岂当时诸人或言之太过,恐忤时相而删之乎?后秦桧既相,卖国求和,则士大夫噤不能发一辞矣!此等诗皆本老杜,亦惟老杜多有此等诗。”
方回推崇杜甫忠君爱国精神,同情其有志难伸的遭遇,还有寄托或表白自己的心志怀抱的用意。《秋晚杂书》一诗云:“窃尝评少陵,使生太宗时。岂独魏郑公,论谏垂至兹。天宝得一官,主昏事已危。脱命走行在,穷老拜拾遗。卒坐鲠直去,漂落西南陲。处处苦战斗,言言悲乱离。其间至痛者,莫若八哀诗。我无此笔力,怀抱颇相似。”诗中对杜甫一生作了总结,感慨杜甫的身世遭遇,敬佩杜甫的胸怀笔力,并且认为自己虽无杜甫之才,而怀抱颇似杜甫。这确实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因为在世人眼中,杜甫与方回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杜甫的爱国之坚贞与方回的降元之妥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方回强调杜甫鲠直有才、屡屡受抑、安史之乱时脱命见新君等,旨在表达自己的心志,其中不无藉此淡化其失节行为的用意。从这个意义上讲,《瀛奎律髓》以杜甫作为忧时爱国诗人典范,极力弘扬杜甫的人格精神,不仅反映了宋代广大士人的呼声,同时也是方回申述自己爱国情怀的诗学表达。
三、 格高:高尚人品的申述
“格高”是方回诗学体系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其根于江西诗派的创作宗旨。陈师道认为“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杜诗“事核而理长”“句清而体好”皆在于“立格之妙”[11]。方回承继其观点,以“格高”作为学诗和评诗的首要标准,并把杜甫之诗作为“格高”的典范。如下所评:
诗先看格高,而意又到,语又工,为上。意到,语工,而格不高,次之。无格,无意,又无语,下矣。(卷二一,《上元日大雪》评)
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学者详之。(卷十五,陈子昂《晚次乐乡县》评)
此格律高耸,意气悲壮,唐人无能及之者。(卷十三,杜甫《野望》评)
然格高律熟,意奇句妥,若造化生成。为此等诗者,非真积力久不能到也。学诗者以此为准。(卷二三,杜甫《狂夫》评)
方回认为诗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即“格”“意”“语”,意为诗脉,语为诗眼,而格为诗骨。*《瀛奎律髓》卷四十二李虚己《次韵和汝南秀才游净土见寄》评:“以意为脉,以格为骨,以字为眼,则尽之。”“格”支撑着诗歌整体,论诗首先须看其“格”;格高方能气足语壮,故“格”相对于“意”“语”更为重要。
方回尤为推崇江西诗人的诗格之高。江西五子诗学老杜,不过又各有特点,如陈与义诗恢张悲壮、吕本中诗趋于圆活、曾几诗清劲洁雅。在方回看来,格高是其共同之处,如下所评:
黄、陈特以诗格高,为宋第一。(卷二二,《和永叔中秋月夜会不见月酬王舍人》评)
简斋诗独是格高,可及子美。(卷十三,陈与义《十月》评)
(居仁)诗格峥嵘,非晚学所可及也。(卷十四,吕本中《西归舟中怀通泰诸君》评)
茶山诗,观其格已高人一头地。(卷十八,曾几《述侄饷日铸茶》评)
除江西五子外,对其他诗人之诗方回也有格高之评。如《瀛奎律髓》卷一评杨万里《过扬子江》:“中两联俱爽快,诗格尤高。”同卷评朱熹《登定王台》:“用事命意,定格下字,悉如律令,杂老杜、后山集中可也。”卷十七评赵蕃《雨望偶题》:“诗格高峭,不妨相犯。”甚至一些不知名者,方回也会称许其诗之格,如卷二十一潘良贵《雪中偶成》评:“潘良贵,字子贱。诗传者不多。风格老练,而缴句皆高古悲怆。味其旨,仁人之言也。”方回还在《唐长孺艺圃小集序》中列举了近世诗人之格高者:“诗以格高为第一。……予于晋独推陶彭泽一人,格高足方嵇、阮。唐惟陈子昂、杜子美、元次山、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韦应物。宋惟欧、梅、黄、陈、苏长翁、张文潜。而又于其中以四人为格之尤高者,鲁直、无己,上配渊明、子美为四也。”[5]卷三三方回推赏的“格高”之诗,涉及了晋、唐、宋代诸多诗人之作,不过,其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即以陶渊明、杜甫、黄庭坚、陈与义诗为最高。
与“格高”相对的诗学范畴是“格卑”。方回认为姚合诗“格卑于岛”(卷十,姚合《游春》评),许浑诗“体格太卑”(卷十四,许浑《晓发鄞江北渡寄崔韩二先辈》评);四灵“学姚合、贾岛诗而不至,七音律大率皆弱,格不高致也”(卷四四,赵师秀《病起》评)。在方回看来,诗格高卑与诗人的品节才学有关,其中又以人品为本。诗格高,创作主体之品节和才学均必高;而人品低下之人,其诗格必不高。方回认为刘克庄“诗意自足,但是格卑”(卷四四,刘克庄《问友人病》评),其诗格卑,并非其才学不富,主要在于其人品不高:“后村初学晚唐。既知名,丞相郑清之奏赐进士出身。贾似道当国,仕至尚书端明。诗文谀郑及贾已甚。晚节诗欲学放翁,才终不逮,对偶巧而气格卑。”(卷二七,刘克庄《老将》评)而对于“江湖”诸生,方回对其才学与品德一概否定,《送胡植芸北行序》云:“近世诗学许浑、姚合,虽不读书之人,皆能为五七言。无风云月露,冰雪烟霞,花柳松竹,莺燕鸥鹭,琴棋书画,鼓笛舟车,酒徒剑客,渔翁樵叟,僧寺道观,歌楼舞榭,则不能成诗。而务谀大官,互称道号,以诗为干谒乞宽之资。败军之将、亡国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阳,刊梓流行,丑状莫掩。”[12]102
方回未具体定义“格”,然就其所推举和批判的诗人及诗而看,可以看出方回所谓的“格”具有多重的含义。首先,“格”不仅指“诗格”,也指“人格”,“人格”决定“诗格”。“人格”并非仅指人的道德品质,而包括德、识、学、才诸方面,即“人品高、胸次大、学问深、笔力健”*参见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二《孙元京诗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9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只有诗人的人格修养和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才能创作出“格高”之作。其次,“诗格”既指诗歌的精神气格,又指诗歌的审美风格,或者说,“诗格”指诗人的道德品质、才学气格等熔铸于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而呈现出的精神风貌和审美风格。诗人的精神气质、道德品格等贯注于作品形成诗歌的精神气格,“格高”之作多给人浑大、高耸、峥嵘之感;诗人的才学识见、艺术修养等凝聚为诗歌的审美风格,“格高”之作主要表现出峭拔、健爽、悲壮之美。
“格”论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命题。以“格”论人汉代已见,南北朝时又以“格”评诗。*如《礼记·缁衣》:“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格”用以论人。《颜氏家训·文章》:“陆平原多为死人自叹之言,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格”用以评诗。宋初有识之士感于士气不振,诗风萎靡,倡导以改造士风来提高诗歌品格,多以“气格”高卑来评论人和诗作。方回立足宋末诗人无行导致诗歌卑弱之现实,提出“格高”之论,在强调诗人的品节气格的基础上,又提出才学识见等对于“诗格”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文坛而言的确具有救弊起危之意义。从方回个人来讲,其极力主张创作主体的“人格”决定其“诗格”,认为人品卑劣必不能创作格高之作,同时,方回本人又创作大量的诗歌来实践自己的诗学主张,这也反映出方回希望以其诗学理论和创作表明自己人品的高尚并渴求人们重新评价自己的良苦用心。
四、 熟淡:和平心境的追求
方回论诗一方面标举“格高”,另一方面又推赏“熟淡”。“熟淡”非方回直接用语,而是笔者对其所论“圆熟”与“平淡”的风格的概括。在方回看来,梅尧臣诗歌平淡有味,自然圆熟;张耒承梅尧臣之诗风,平熟圆妥。如下所评:
若论宋人诗,除陈、黄绝高,以格律独鸣外,须还梅老五律第一可也。虽唐人亦只如此。而唐人工者太工,圣俞平淡有味。(卷二三,梅尧臣《闲居》评)
圣俞诗不争格高,而在乎语熟意到。(卷十六,梅尧臣《依韵和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评)
圣俞诗淡而有味。此亦信手拈来,自然圆熟。(卷十四,梅尧臣《晓》评)
文潜诗大抵圆熟自然。(卷二九,张耒《自海至楚途寄马全玉》评)
平熟圆妥,视之似易。能作诗到此地,亦难也。(卷十六,张耒《寒食赠游客》评)
梅诗平淡已为宋人共识,但在方回之前少有以“圆熟”论梅诗。梅尧臣自云:“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13]梅尧臣认为自己诗歌不仅不圆熟平滑,甚至苦涩刺口,可谓“苦淡”。欧阳修作为梅尧臣知己,也有相似评论:“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14]46缘何方回的审美判断却与梅、欧的感知近乎对立呢?从梅尧臣自身来说,其言有自谦成分,因和宰相晏殊之诗,虽无刻意奉承对方之意,然言己诗之弊从而提升对方诗价值,为交往唱和诗之常识性规律。当然,梅尧臣之言也并非随意自贬,这也正表明其在某一阶段时的作诗情况。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对梅创作进行总结:“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14]881梅尧臣初学王、韦,中兼韩、孟,后效渊明,经历了一个从平淡到雕琢再到平淡的过程。当梅尧臣自觉追求渊明境界而“稍欲到平淡”时,确实不满于自己“间以琢刻”之弊,认为其辞苦硬,未达到圆熟之境。从方回来说,他对梅诗的评价是针对梅尧臣创作总体而言,对古淡有味之作推崇备至;而且,方回站位于纵观唐、宋律诗整体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梅诗与唐诗及江西诗派的比较来论述梅尧臣诗之特色,更为突出梅诗的熟而淡的特征。
方回所言之“熟”有其独特内涵:①“熟”与“活”相通。“熟”的提出,根于吕本中之论,《紫微诗话》载:“叔用尝戏谓余云:‘我诗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诗,只是子差熟耳。’余戏答云:‘只熟便是精妙处。’”[15]吕本中诗“熟”而圆活,在于他对江西诗人创作艰涩生硬之弊的清醒认识,从而把自己提出的“活法”之论运用于创作实践之中。方回以吕本中为江西诗派重要传承者,对其诗也极为推崇,卷四《海陵杂兴》评:“其诗宗‘江西’而主于自然,号弹丸法。”卷十七《柳州开元寺夏雨》又评:“居仁在‘江西派’中,最为流动而不滞者,故其诗多活。”②“熟”与“工”相对。方回在《程斗山吟稿序》中云:“善为诗者,由至工而入于不工。工则粗,不工则细;工则生,不工则熟。”[12]53-54在方回看来,工则粗而生;至工而不工则细而熟,亦即达到无意而工的境界。方回认为“唐人工者太工”,梅尧臣学唐诗又能实现超越正在于其不工,“宋人诗善学盛唐而或过之,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卷二四,梅尧臣《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军》评)。③“熟”与“韵”并在。方回在卷二十张道洽《梅花二十首》评中明确表述:“夫诗莫贵于格高。不以格高为贵,而专尚风韵,则必以熟为贵。”方回认为梅尧臣不争格高,而以韵胜,卷四七僧怀古《寺居寄简长》评云:“宋之盛时,文风日炽,乃有梅圣俞之蕴藉闲雅,陈后山之苦硬瘦劲,一专主韵,一专主律,梅宽陈严,并高一世,而古人之诗半或可废。”
方回所谓的“淡”与“厚”统一,是醇厚而平淡。严羽《沧浪诗话》曾云“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16],方回更进一步指出“圣俞诗似唐人而浑厚过之”(卷二四,梅尧臣《送唐紫微知苏台》评)。方回认为梅诗“淡而有味”,平淡而蕴涵丰富。方回所谓的“淡”与“熟”统一,是平淡而圆熟妥帖,自然而语熟意到。这种熟淡,非陈腐滥套之圆,也非平易通俗之熟,而是“覃思精微”后的“闲远古淡”*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是经历了艰苦锤炼过程后达到的圆熟自如。梅尧臣之熟淡与晚唐、四灵及江湖诗人毫无学术、卑俗陈熟有本质区别;而与杜甫“山高水深”之平淡境界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卷十杜甫《春日江村》评:“老杜诗所以妙者,全在阖辟顿挫耳,平易之中有艰苦。若但学其平易,而不从艰苦求之,则轻率下笔,不过如元、白之宽耳。学者当思之。”梅诗与杜诗美学风格不一,但在这一点上相似,平淡中蕴含着艰苦,圆熟中包孕着历练,这是更高层次的平淡,是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
方回倡导“熟淡”,当然与其审美理想和创作实践有关;不过,方回的心境变化和心理诉求的愿望对于其诗学主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方回晚年深悔以前的行为,希望能平淡生活。方回在卷十三白居易《戊申岁暮咏怀二首》评中云:“予年五十七岁选此诗,深愧之。”白诗云:“荣华外物终须悟,老病旁人岂得知。犹被妻儿教渐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方回当是由此发出感慨。方回不断调整自己,希望能圆通处世,融和为人,评张道洽诗评:“熟也者,非腐烂陈故之熟,取之左右逢其源是也。”(卷二十,张道洽《梅花二十首》评)这与其说是评诗,毋宁说是陈述一种生活哲理。方回推崇程朱理学,尤其深慕朱熹人格,学习其养心治气、内修自身,以求达到中和乐意之境。方回在诗中自言:“诗备众体更须熟,文成一家仍不陈。晚悔昨非思改纪,规随养气省心人。”(《七十翁吟七言十绝》)由此可以推想,方回论诗倡导“活法”“圆熟”“平淡”,不仅是尊重创作规律和审美需求的结果,也是其生活哲学的诗学表达,同时又是方回在时间的流逝和现实的磨炼中,希望摆脱心理愧疚和良心不安、追求“熟淡”心境的曲折反映。
一部具有社会反响的著作能成就作者,这不仅意味着作品给作者带来正面或负面声誉,也意味着读者会根据作品对作者进行重新认识。作品通常“都带有一定的功利指向”[17],读者在阅读消费过程中,很可能受到作品的某些指引而对创作者的人品才学做出与历史不同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能重新体验和经历,不断反思和拷问自身,从而塑造另一自我。方回根于自身的特殊经历和创作经验,立足诗风萎靡的宋季诗坛,放眼唐宋诗歌发展历程,对诗歌创作进行赏析评论和反思总结,同时,方回也对自身进行了道德人格的追问和艺术伦理的教育,从而精神境界得到了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救赎。方回以自己的创作成就和人生教训为宋元诗坛书写了斑驳的一笔,也为后世提供了正负两面借鉴的真切范本。
[1]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1423.
[2] 程敏政. 新安文献志[M]. 合肥:黄山书社, 2004:1077.
[3] 周密. 癸辛杂识[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251.
[4] 邵华,葛鲁嘉. 生态主义视域下的理论心理学研究[J]. 沈阳大学学报, 2011(6):105-107.
[5] 方回. 桐江续集[M]∥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6] 张红. 方回的杜诗观及其诗学体系之建构[J]. 中国文学研究, 2006(3):47-51.
[7] 李壁. 王荆公诗笺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316.
[8] 苏轼. 苏轼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318.
[9] 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112.
[10] 李纲. 李纲全集[M]. 长沙:岳麓书社, 2004.
[11] 张表臣. 珊瑚钩诗话[M]∥何文焕. 历代诗话. 北京:中华书局, 1981:464.
[12] 方回. 桐江集[M]∥阮元. 宛委别藏:第105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13] 朱东润.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368.
[14] 洪本健.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5] 吕本中. 紫微诗话[M]∥何文焕. 历代诗话. 北京:中华书局, 1981:362.
[16] 严羽. 沧浪诗话[M]∥何文焕. 历代诗话. 北京:中华书局, 1981:688.
[17] 贺根民. 中国近二十年来文学道德批评述评[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6(5):681-686.
FangHui’sPoeticExpressionofhisMoralIntrospection
WangXin1,GaoLanxiao2
(1. Editorial Office,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35,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The poetic thought and creation psychology in poetry anthology, Ying Kui Lyu Sui, are analyzed, which is compiled by Fang Hui. He highly praised Du Fu, criticized poetry by the first standard of “style”, and initiated “skillful insipid” beauty. His poetic view also reveals the creation intention to demonstrate his patriotism and personality, and shows a strong desire for self-reflection and moral justification.
Fang Hui; Ying Kui Lyu Sui; moral; poetics
2017-03-23
王 昕(1973-),女,河北邯郸人,石家庄学院副教授,博士。
2095-5464(2017)05-0627-06
I 207.22
A
【责任编辑王立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