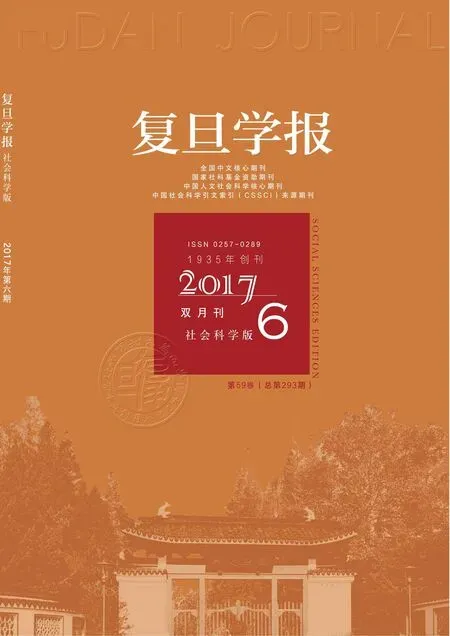儒学的精神性之维及其内蕴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241)
中国哲学研究
儒学的精神性之维及其内蕴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241)
儒学的精神性不能简单等同于宗教性。按其实质,儒学的精神性之维以意义追求为其具体内涵。以人禽之辨为前提,儒学确认了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由此为意义的追求提供了价值论的前提;基于仁道原则,儒学肯定忠与恕的统一,以此避免意义的消解和意义的强加;以自我的提升为指向,儒学注重人的成长,以此区别于可能导向自我否定的“超越”;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之境中,理想意识和使命意识在儒学中获得了内在的统一。相对于“超越”的宗教进路,儒学的意义追求更多地展现了基于“此岸”的现实性品格。然而,近代以来的某些发展趋向在从不同层面消解人的存在价值的同时,也使精神性之维的意义追求失去了前提和依托。以此为背景,便可注意到儒学的精神性之维在今天所具有的意义。
儒学 精神性 意义追求
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系统,儒学包含精神性之维。宽泛而言,“精神”具有不同含义,可以从认识论、伦理学、本体论等角度加以讨论。谈儒家的精神性无疑也涉及以上领域,但其实质内容则关乎价值之维。与之相联系的所谓精神性,首先相对于物质需求和感性欲求而言,其内在指向则表现为意义的追求。
(一)
从形而上的层面看,人的存在与意义追求无法分离。世界本无意义,意义因人而有。相应地,也只有在人那里才形成以意义追求为实质内容的所谓“精神性”问题。人的存在具有多方面性,这一存在境况决定了意义追求的多方面性。意义追求从核心的内容看关乎真善美,就具体的层面而言又涉及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领域。在意义的以上向度中,宗教既非唯一的方面,也不是终极之维,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便把哲学视为“艺术和宗教的统一”*黑格尔:《精神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3页。。按这一理解,宗教仅仅构成了哲学的一个环节,而并不具有至上性。黑格尔关于艺术、宗教与哲学关系的看法是否合理当然可以讨论,但他在精神之域拒绝赋予宗教以唯一性、至上性的思路,无疑值得关注。同样,在肯定“精神性”的实质性内涵表现为意义追求的同时,应当避免把“精神性”简单地等同于宗教性。
意义的追求既不同于意义的消解,也有别于意义的强加。以目的悬置、价值贬弃等为表现形式,意义的消解呈现多样的表现形式。在否定理性的前提下,非理性的情意表达往往压倒了理性的觉解;以确定性的扬弃为形式,意义的追求常常被推向理论关切的边缘;对文明演进、文化延续内在价值的怀疑,则每每使历史本身也失去内在的意义,如此等等。意义的这种消解,在价值观上容易引向虚无主义。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趋向,则表现为对意义的外在强化或意义的强制。意义的外在强化或强制往往以权威主义或价值独断论为其存在形态,它在实质上以外在强加的方式,把某种意义系统安置于人。意义的这种强制或强加,意味着限制人们自主地选择、接受不同的意义系统。如果说,意义的消解导致精神性的失落,那么,意义的强制则引向精神性的异化。
从儒学的原初形态看,其精神性的维度可以从仁道和忠恕之道的统一中加以理解。仁道原则从价值论、本体论等方面为意义的追求提供了前提;“忠”与“恕”的统一则既意味着拒绝意义的消解,也意味着避免意义的强加。
意义基于人的存在,意义的追寻也离不开对人自身的理解和定位。考察儒家对人的理解,首先需要关注其核心的观念——“仁”。从形而上的角度看,“仁”的意义在于肯定人的内在价值,当孔子以“爱人”界说“仁”时*《论语·颜渊》。,便言简意赅地肯定了这一点。对儒家而言,人之外的物固然可以为人所用,并相应地也有其价值,但这种价值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为人所用),唯有人才因其自身而具有价值。孔子在得知马厩失火后探询“伤人乎”,而“不问马”*《论语·乡党》。,便体现了这一点。作为不同于外在对象并不可还原为物的存在,人的价值具有内在性,这种内在价值同时从本源上规定了人的存在意义,并构成了一切意义追求的出发点。
仁道原则的确认,本身又以人禽之辨为逻辑前提。人禽之辨的实质指向,在于通过何为人的追问,揭示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对儒学而言,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格,主要体现于其自觉的伦理意识,正是这种伦理意识,使人区别于他物。荀子曾对人与其他对象作了比较,认为人不同于这些对象的根本之点,就在于有“义”。所谓“义”,也就是普遍的道德规范以及对这种规范的自觉意识(道德意识),后者同时赋予人以前述内在价值,并使之高于其他一切存在(“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人所具有的这种价值进一步为意义的追寻提供了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根据:作为有别于禽兽、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人总是追求有意义的、值得过的生活。在此意义上,作为儒学核心的仁道原则既体现了一种精神性的意义取向,又构成了更广意义上精神追求的前提。
与仁道相联系的是忠恕之道。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内在的趋向是由己而及人,使自己所认同、接受的价值理想同时成为他人追求的目标;“恕”则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包含尊重他人意愿、避免干预他人之意。*《论语·雍也》。就两者与人的关联而言,“忠”主要表现为使之(人)完美,“恕”则更多地侧重于宽以待人。从价值取向看,“忠”展示的是积极的担当意识或责任意识(努力使人完美),但仅仅以此为原则,容易导致强制他人接受自己的理想或价值观念,从而走向意义的强加。比较而言,“恕”则内含宽容的精神。在儒学看来,真正在实践中对此身体力行,便能逐渐趋近于仁的境界。所谓“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便表明了这一点。这种宽容的精神在后来进一步衍化为“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念,后者意味着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价值原则和价值观念。“恕”以及“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主张对于“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可能导致的强人就我趋向,无疑具有某种抑制作用。当然,如果仅仅讲“恕”、单纯地坚持“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可能导致悬置价值的理想,甚而走向意义的消解或意义的相对化。从以上方面看,“忠”与“恕”的统一既通过理想的担当而远离了意义的消解,又通过力行宽容之道而避免了意义的强加。
从形式的方面看,“忠”与“恕”体现的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同时被理解为“仁之方”。*《论语·雍也》。如果说,仁从总的方面规定了意义追求的价值方向,那么,作为实现仁道的具体方式和途径,“忠”与“恕”的统一则使儒家从一开始便与意义的消解和意义的强加保持了距离,儒家以意义追求为实质内涵的精神性,也由此展现了比较健全的趋向。
(二)
意义追求当然不仅仅限于儒家。从比较的视域看,意义追求往往展现出不同形态。这里首先可以关注“超越”和“成长”所蕴含的相异进路。在谈儒学或广义的中国哲学之时,晚近比较流行的观念之一是所谓“内在超越”。后者一方面肯定儒学及广义的中国哲学也有类似西方基督教的超越性(transcend)或超越性的追求,另一方面则认为儒学或广义的中国哲学所具有的这种所谓“超越性”,同时呈现“内在性”(Immanent)。
以上论点尽管试图把握儒学及中国哲学的特点,但从现实的层面看,却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儒学及中国哲学的本来形态。在此,首先需要对“超越”这一概念作一分疏。严格意义上的“超越”,乃是与transcend对应的概念,这一意义上的“超越”概念首先来自西方,并涉及宗教的论域。从以上的“超越”视域看,上帝是唯一具有超越性的存在的,这种超越性非任何其他对象(包括人)所可能具有。当然,后来哲学家如康德也提到过超越性(transcend),而且这种超越性在他的哲学中也与宗教存在相关性。康德区分感性、知性、理性,理性作为超验或超越(transcend)之域,涉及三重理念,其中最高的理念便是上帝。这一意义上的超越,无疑也关乎宗教。不过,在康德那里,超越性同时又主要指超越感性,其意义相对于先验性(transcendtal)而言:先验性(transcendtal)的特点在于先于感性经验,但又可运用于感性经验,超越性或超验性(transcend)则超越感性经验而又无法运用于感性经验。
在以上语境中,“超越”关联无条件的、无限的、绝对的方面,并与内在性(Immanent)相对。这一视域中的“超越”,同时又具有不同意义上的“彼岸”性,而人则无法由“此”及“彼”:在本体论上,“此岸”之人不可能成为“彼岸”的上帝;在认识论上,人不能由感性领域的现象,达到超越于感性的自在之物或物自体。这一类的所谓“超越”,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的限定,事实上,“超越”本身即以肯定人存在的有限性为前提。
这里可以暂且搁置广义的中国哲学,主要关注儒学以及儒学与以上思维趋向的关系。与上述“超越”的进路不同,儒学不同于基督教,从而没有承诺唯独上帝才具有那种“超越性”和宗教意义上的“超越”观念;儒学也并不执著于康德哲学中所谓感性和理性、经验和超验等等的区分,从而也没有认识论意义上(超验意义上)的超越性。进一步看,上述视域中的“超越”(transcend)和“内在”(Immanent),在内涵上彼此悖反,前者(“超越”)是无条件、绝对、无限的,后者(“内在”)则是有条件、相对、有限的。在特殊蕴含普遍或个别包含一般等意义上,也许可以肯定有条件、相对、有限的存在中内含着无条件、绝对、无限的规定。然而,以“内在”(Immanent)规定“超越”(transcend),由此形成“内在超越”之说,则犹言“圆的方”,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事实上,简单地用“内在超越”这类概念去谈儒学,似乎难以避免“以西释中”(借用时下的流行表述),这里所谓“释”具有明显的迎合、附会倾向。
相对于基督教之注重“超越”,儒学更为关注的是为己和成己,后者所指向的,是自我的成长。“超越”隐含着自我的某种退隐,“成长”则以自我的提升为目标。自我的成长或自我的提升一方面意味着在“人禽之辨”的意义上由“野”而“文”,亦即走出本然状态,成为不同于自然对象的文明化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在“圣凡之辨”的意义上,由“凡”而“圣”,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格境界。这里的“圣”不同于“神”:“圣”是内在于“此岸”、具有完美德性的人,而不是存在于“彼岸”的无条件、绝对、无限意义上的上帝。
对“超越”的追求,往往引向自我的否定以及自我发展过程中的间断性:较之绝对的、无条件的、超越的存在,自我似乎显得微不足道,这种自我同时被视为应加以超越的对象。耶稣曾对他的信徒说,“如果有人想跟随我,就让他先否定他自己”。*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64页。这里的“否定他自己”既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否定,也意味着自我发展的中断。比较而言,“成长”侧重于个体的自我实现,后者所确认的,是个体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肯定以及自我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事实上,相对于“超越”的进路,儒学更多地强调形上的根据和人的存在之间的连续性,《易传》的以下论述便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系辞上》。这里的“道”可以理解为价值的形上根据。对儒家而言,这种形上根据与人的成长之间更多地呈现前后相继的连续性:人自身成长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对道的依循和确证。这种依循和确证不同于人的自我否定,相反,在继善成性的过程中,一方面,人的发展有其形上根据,天与人之间呈现前后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人自身的成长过程,也展现出时间中的绵延统一。如果撇开以上表述的思辨形式,从更为现实的层面加以理解,则可注意到,其中同时蕴含如下观念:受道制约的人,其存在规定中蕴含未来成长(包括成就自我)的可能,这种可能构成了人后继发展的根据;成性(自我成长和作为提升)的过程,也就是以上可能的实现和展开过程,其内在向度则表现为前后的绵延相继。
儒学固然也以“克己复礼”规定“仁”,但此所谓“克己”不同于否定自我,相反,其最终的目标是成己:“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5页。这里涉及为己、克己、成己等不同环节,其间的关系表现为从“为己”出发,通过“克己”最后达到“成己”。在此,“成己”构成了终点,“克己”只是这一过程的中介或手段,而个体的成长则相应地表现为一个自我造就,而非自我否定的过程。在“超越”的视域中,既成的“我”和应成的“我”之间往往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应成之“我”表现为对既成之“我”的否定。以“成长”的观念为前提,既成之“我”和应成之“我”之间,则更多地呈现前后的相承:应成之“我”具体地表现为既成之“我”的提升,两者之间不存在否定意义上的张力。
与人自身成长的连续性相联系是过程性、时间性。一方面学以成人,自我的成就构成了个人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按照儒家的理解,“学不可以已”*《荀子·劝学》。,这里的“学”以成人为指向,而“学不可以已”则意味着自我成长是一种无止境的过程。“学”以成人的这种无止境性表明,现实世界或“此岸”中的人,其成长、提升总是离不开历史性。
与此相对,“超越”在本质上并不涉及历史性、时间性、过程性。无论是绝对、无条件意义上的上帝,还是作为超验对象的物自体,都存在于时间和过程之外,具有超时空的特点。康德认为时空的直观形式只能应用于现象界,而无法以物自体为作用对象,这种看法也从一方面强调了物自体超越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将存在与时间联系起来,可以看作是对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思想传统的某种转换,他与康德依然承诺理性之域存在的超时空性颇相异趣,其意义不应忽视。从意义追寻的角度看,“超越”与时间性、过程性、历史性的隔绝,同时也从一个方面突显了以“超越”为指向的意义追寻本身的抽象性,而成长过程的历史性、时间性规定,则展现了与之相关的意义追求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儒家精神性之维的内在特点,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三)
与注重人自身的成长相联系,以意义追求为实质内涵的儒学精神性之维,内在地体现于宋儒张载的以下名言,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页。这既是精神层面意义的追求,又展现了这种意义追求的价值内涵。
如前所述,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在于具有创造力量,这种创造力量使人能够赋予世界以意义。在人没有作用于其上之时,作为本然存在的洪荒之世并没有呈现出对于人的意义,世界对于人的意义乃是通过人自身的参与活动而敞开的。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在表述上尽管具有某种形上的特点,但在实质上却从价值的层面上,突显了人的创造力量以及人赋予世界以意义的能力。
“为天地立心”以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指向,“为生民立道”则涉及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人的历史走向和发展趋向,基于人自身的选择,而并不是由超越的存在如上帝、神之类的对象所规定;人类走向何方,决定于人自身。对历史方向的规定,以肯定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意义为前提,在此意义上,“为生民立道”表明,人的存在和发展并非如虚无主义者所认定的那样没有价值。质言之,一方面,人的存在和发展内含自身的价值意义;另一方面,这种价值意义又源于人自身所立之“道”。
人的存在意义,同时体现于人的文化建构及其绵延发展:“为往圣继绝学”便关乎人类的文化历史命脉。“往圣之学”可以视为社会文化思想的象征,它既凝聚了人类的文化成果,又是文化历史命脉的体现。“为往圣继绝学”的实质意义,便在于延续这种文化的历史命脉。文化积累是人的价值创造力量更为内在的表征,对延续文化历史命脉的承诺,同时也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进一步确认。
“往圣之学”首先涉及过去(以往的文化成果),比较而言,“为万世开太平”则更多地关注于未来。这里首先渗入了人类永久安平的观念,其思想的源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追溯到《尚书》的“协和万邦”以及《大学》“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在西方近代,康德曾以永久和平为人类的未来理想,这一观念在某些方面与张载的思想也有相通之处。不过,在张载那里,“为万世开太平”并不仅限于追求邦国之间的永久和平,其中还包含着更普遍的价值内容,后者具体表现为推动人类走向真正完美的社会形态。历史地看,在不同的时代,人的完美和社会的完美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内容,相对于这种特定的历史追求,“为万世开太平”在展示未来价值理想的同时,又赋予这种理想以终极的意义。
作为儒家精神性的具体体现,以上观念并非玄之又玄、空洞无物,而是体现了理想意识和使命意识的统一,并展示了成己和成物的价值取向,其中同时内含了人自我提升、精神升华的要求。这种精神性追求不同于宗教,无法归入由“此”及“彼”的超越追求,其理想、使命都具有此岸性和现实性,与之相联系的自我提升也基于人的现实存在。
进而言之,以上的意义追求或精神性取向与宗教的分别,还在于它以肯定人自身的价值和自身的力量为前提。前文已提及,从人和世界的关系来说,所谓“为天地立心”,意味着人应当并能够赋予世界以价值意义。从人和自身的关系看,所谓“为生民立命”,蕴含着肯定人的历史发展方向取决于人自身的选择和努力。与之相异,对宗教如基督教而言,人是微不足道的。基督教的《圣经》中即有如下名言:“人算什么?”*见《圣经·约伯记》第七章。如果人试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便难以避免僭越。在基督教看来,人首先应当祈求上帝的救赎,即使注重信徒自身努力的新教,也要求通过这种努力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种以“超越”的上帝为指向的进路,与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旨趣,相去甚远。
(四)
基于人自身价值和自身力量的儒学精神取向虽然不同于宗教,但这并不影响其内在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以近代以来的历史衍化为背景,可以进一步把握这种意义。
如前所述,在儒学那里,人禽之辨构成了意义追求的出发点,儒家对仁道原则的肯定,也以人禽之辨为前提。广而言之,承认人之为人的价值与明辨人与其他存在的区别,可以视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意义追求离不开人,人禽之辨与何为人的问题则紧密相关:人禽之辨所指向的是人禽之别,后者意味着确认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由此,人禽之辨本身也构成了意义追寻的本体论根据和价值论前提。
然而,就中国近代的历史衍化而言,自从进化论引入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类观念一度成为思想的主流,这种观念的兴起无疑有其历史的缘由,它对激发近代的民族危亡意识和自强精神,也有毋庸讳言的历史意义。不过,从人道或价值观的层面看,这一类观念又在逻辑上蕴含着如下趋向,即把人和其他的对象(包括动物)等量齐观,后者不同于传统儒学在人道领域中展开的“人禽之辨”,在某种意义上甚而可以视为“人禽之辨”的一种颠覆:人禽之辨侧重于通过区分人与其他存在(包括动物),以突显人超越于自然的内在存在价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则似乎使人回到自然丛林中的存在形态。从确认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人禽之别),到等观天人(人与物服从同一自然法则),这无疑是观念的重要变化。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商品交换的发展,人的物化和商品化也逐渐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在商品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往往被转换为物与物的关系,商品崇拜、金钱崇拜等各种形式的拜物教则随之出现。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伴随着现代化过程而形成的世俗化趋向,后者往往赋予人的当下感受、感官需要以优先的地位,并以此疏远理想的追求、摈弃精神层面的终极关切。人的物化与物欲的追逐相互关联,使人禽之辨的颠覆,进一步引向了人与物界限的模糊。
进而言之,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技术对人的控制以及工具对人的制约也逐渐滋长,人在某种意义上相应地愈益受制于技术和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手不释“机”(手机或计算机)、网络依赖,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日常景观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技术对人的控制。近时的AlphaGo与围棋高手的对决以及后者的屡屡落败,又使人禽之辨进一步引向人机之辨。就后一方面而言,人工智能似乎从能力等方面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提出了挑战。
从更宽泛的层面看,尼采已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上帝通常被视为意义的终极根据,与之相联系,既然上帝已死,则意义的终极根据也随之逝去。福柯进一步作出了“人之消失”的断言,并冷峻追问“人死了吗”?*福柯:《词与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46页。人是意义的主体,人死了,则意义追求的主体也不复存在。这样,从意义根据的架空,到意义追求主体的退隐,意义都面临着失落之虞。
就现代思想的演进而言,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观念以及理性原则的拒斥,往往伴随着对意义追求的质疑,意义的陨落则是其逻辑的结果。在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那里,这一趋向取得了较为典型的形式。解构强调的是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在强化这一点的同时,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封闭了通向意义之境的道路。
此外,当代世界中还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它们往往将某种片面的宗教观念或价值原则绝对化、至上化,不仅在理论上加以宣扬、灌输,而且力图在实践中推行、贯彻。在实践中推行以上观念往往导致所谓文明的冲突,在理论上对其加以宣扬、灌输则意味着强行让一定共同体的成员接受这种观念。如果说,人禽之辨的颠覆、人物界限的模糊、技术的控制、意义的解构等等在从不同层面消解人的存在价值的同时,也使精神之维的意义追求失去了前提和依托,那么,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则从一个方面表现出意义强加的趋向。
从如上背景出发考察儒学的精神性内蕴,便不难注意到它在今天所具有的意义。以人禽之辨为前提,儒学确认了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由此为意义的追求提供了价值论的前提;基于仁道原则,儒学肯定忠与恕的统一,以此避免意义的消解和意义的强制;以人的自我提升为指向,儒学注重人的成长,以此区别于导向自我否定的“超越”;从“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观念出发,儒学肯定人作为价值主体所具有的创造力量,并确认理想意识和使命意识的统一,等等,这种精神追求不仅在消极的层面提醒我们对前述各种价值偏向保持警觉,而且在积极的层面为我们更深沉地关注人的存在价值、承诺意义的追求、拒绝意义的强加提供了重要的传统思想资源。就意义追求本身而言,相对于“超越”的宗教向度,儒学更多地展现了基于“此岸”的现实进路。从以上方面看,重新回溯、思考儒家以意义追求为内涵的精神性之维,无疑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责任编辑晓诚]
TheSpiritualDimensionofConfucianismandItsImplication
YANG Guo-rong
(InstituteofChineseModernThoughtsandCulture,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The spirituality of Confucianism consists in the pursuit of meaning, which is not simply equivalent to that of religion. Confucianism is based on a premise of distinguishing human beings from animals. It defines the fundamental of human beings, from which derives the premise of the theory of value. With the principles ofren, Confucianism confirms the unity ofzhong(self-fidelity) andshu(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which successfully avoids the dissolving or enforcement of meaning. With the guideline of self-improvement, Confucianism focuses on the human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ng itself from the transcendence which possibly leads to the self-denial. In the spiritual realm of “making a mind for Heaven and Earth, setting up the Tao for human beings, restoring the lost teachings of the past sages, and building a peaceful world for all future generations,” the ideal and the mission found the inner unification. In contrast with the transcending approach, the meaning pursuit of Confucianism reveals more worldly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certain approaches since modern times that aim to dissolve the value of being from variant dimensions. It will deprive of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the meaning pursuit. In this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values of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spiritual essence; meaning pursuit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系作者于2017年6月在“当代儒学发展的经验、现状和方向”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相关研究同时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事与物: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中国现代形而上学的转换”(项目批准号:16JJD72000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冯契哲学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12)的阶段性成果,并同时纳入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以及上海社科创新基地华东师范大学“文化观念与核心价值”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