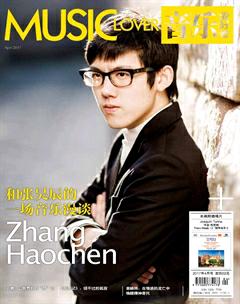《变形记》:绕不过的孤寂
梁晴
入场前,我的内心既期待又疑惑,难以想象将如何“变形”,这实在太具挑战性了。看罢,我被导演亚瑟·皮塔(Arthur Pita)、舞者爱德华·华森(Edward Watson)及舞美的出彩表现所折服。音乐人弗朗克·穆恩(Frank Moon)同样出手不凡,他独自驾驭着全剧的配乐,包揽了从创作到现场演奏演唱的所有细节。



绕不过的孤寂
那天我刚入场,在找座位,周遭是进进出出嘈杂的人群,一抬头发现舞台上格里高尔的父亲已经坐在那儿看电视,妈妈织着毛衣,妹妹趴在地上写作业,格里高尔躺在右边黑暗的床上。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
台下人还没准备好,台上已经入戏。耳旁,模糊地感觉到有声音,非曲调的,只是一丝持续着的声音,飘荡在虚无中,若隐若现的高音区泛音营造出一片不安的气氛。音源不知由何发出,音流入处清出一块孤独的空间。是的,你可以绕过那些喧嚣,但绕不过这孤寂。
大家会对卡夫卡着迷,但是很少人会根据他的作品进行再创作。匈牙利作曲家库塔格(Gyorgy Kurtag)曾经于1966年写下《卡夫卡碎片》,由一些零落的感受碎片组成,而穆恩面对的可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因为是舞剧,导演将格里高尔的妹妹从拉小提琴改成学芭蕾,不过原作中的“小提琴”信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后来看到穆恩站在台下,距离我的位置不远,他只用一把小提琴和一组电声,非常投入。
忧郁的主题
编导皮塔颇具创造性,《变形记》为出演格里高尔的皇家英国芭蕾舞团的首席男舞者华森度身定制,别具特色。华森曾在前两年的新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扮演兔先生,在此他的表演潜力被极大地挖掘。《变形记》获得了奥利弗奖、南岸天空艺术奖、国际舞蹈评审团奖。舞台被分为左右两块,暗示格里高尔与家人分立在两个世界,舞剧故事也在这两边分别进行着,灯光时暗时亮,它们之间仅有“一门”的连接。
开场,格里高尔的母亲出现在舞台右边的客厅,她有点病弱,坐在呼吸机前,主题一出现,曲调忧郁暗淡,节奏缓慢,音程狭窄蜿蜒,线条单薄。
“这是母亲的声音,好温柔的声音。”
后主题二出现,阴暗的小调性曲调,小三度递进上行构成旋律轮廓,音乐忧郁,勾勒出二十世纪初“一战”前西方世界的整体压抑无助感。这两个主题贯穿全剧,形成作品的基调。
“是的,是的,谢谢你妈妈。”

用声音切换日常
卡夫卡《变形记》以荒诞、古怪、变异而夺人耳目。小说开始直指“变形”,而该舞剧却大胆地对小说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原著的开头大家很熟悉: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舞剧以忙碌的格里高尔开场,一上来就让他重复“三天”之日常。在“一天”早晨,闹铃“点亮”了格里高尔黑暗的卧室。他起床,走出自己房间,来到客厅,拿走母亲留的苹果。那绕不过的寂静之声衬托着他,大门关上的声音、轻快的小提琴声、跳跃的拨弦声伴随着他上班的步伐,行人、同事、火车匆匆而过,音乐是如此畅快,节奏摆动。转身到了下班的时间,回家,妹妹的欢呼叫声扑面而来,一家人晚餐。当格里高尔进入自己的卧室,如同进入了自己的内心,那绕不过的寂静声自然又冒出,渗透了整个空间。
从黑夜至白天、从内心至外界、从深厚至泛泛,舞台、灯光、声音同步切割着,借用的是电影般的切换手法,快速而精准,如此循环重复了“三天”,浓缩概括出格里高尔的日常。忙碌的格里高尔曾抱怨过:
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
至第“三”天,那个轻快的音乐已经被忧郁的主题替代,为将来打下了伏笔。第“四”个早晨,当那震耳欲聋的闹铃再次响起时,格里高尔没有起床。
“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
变形一:声音无序,人变虫
“我怎么了?”“我出什么事啦?”
一觉醒来的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有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和许多细得可怜的腿,仰卧着。舞剧中的变形有三部曲,第一步是人变虫。
皮塔的思路和华森的演绎是更多地去捕捉其中无形的东西,而不是在有形处打转。音乐也一样,零零落落的声音在寂静中慢慢地响起,小提琴发出无序的击打声,错乱而没有方向,一改曾经的温情,而变得干冷无情,接着出现一些急促的短小音流加强紧张感。碎裂,裂变。
无序的声音扯断了正常秩序,格里高尔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声音渐强,伴随着家人们、买酒女郎、公司来人等敲门声、叫唤声和催促声,乱成一团。小提琴在低音区不断持续着一个固定音型,几个声部的无序化不断增强,推到一个极致。格里高尔的房门被推开,惊吓的人们离去后,留下孤独的格里高尔。一切安静下来,轻微的滑音营造着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具体声音直用
所谓具体声音,就是指具体物体或人发出的自然音响,它与传统人为创作出来的音响相区别。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出现具体音乐(Concrete Music)这个概念,之后成为早期电子音乐的声音模本。在当代音乐创作中,具体声音的运用极为普遍,因为它的表达更直接。可以思考,《变形记》或其他一些当代作品,为什么没有与成熟大牌的学院派精英作曲家合作,没有弄一个古典式的乐队或组合,而对名不见经传的穆恩情有独钟呢?因为穆恩懂得这部《变形记》需要什么。
在小说中,卡夫卡有很多描写声音的片段:
没错,这分明是他自己的声音,可是却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了出来,仿佛是伴音似的,使他的话只有最初几个字才是清清楚楚的,接着马上就受到了干扰,弄得意义含混,使人家说不上到底听清楚没有。格里高尔本想回答得详细些,好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只得简单地说:“是的,是的,谢谢你,妈妈,我这会儿正在起床呢。”
舞台上,这些声音非常突出,如妈妈用的呼吸机噗嗤噗嗤的气声、上班火车的汽笛声和哨声、咖啡沃特加的叫卖声、妹妹高兴时的尖叫声、老妈子钟点工的唠叨声、电视机节目的声音、开门声等等,它们的出现消解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令作品的表述更为直接而自然。
老妈子无疑就是个次要角色,她每次出场都说很多话,嘴里叽里呱啦地,模模糊糊断断续续,没有一句让人听清楚,但是声音已经将这个人物表现得很准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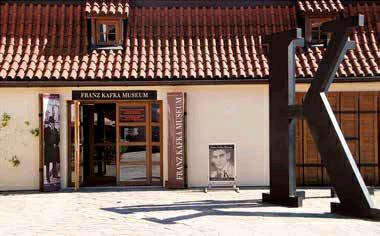
清晨,老媽子来了——一半因为力气大,一半因为性子急躁,她总把所有的门都弄得乒乒乓乓,也不管别人怎么经常求她声音轻些,别让整个屋子的人在她一来以后就睡不成觉——她照例向格里高尔的房间张望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之处。她以为他故意一动不动地躺着装模作样;她对他作了种种不同的猜测。她手里正好有一把长柄扫帚,所以就从门口用它来拨撩格里高尔。这还不起作用,她恼火了,就更使劲地捅,但是只能把他从地板上推开去。
变形二:悲壮的电声,虫灵附体
这是该舞剧的亮点之一,变形第二步,与灵魂相拥,此处的声音也掀起高潮。当与哥哥很有感情的妹妹居然跳起一段虫舞,以示与哥哥沟通的诚意后,一个很强烈的音色瞬间切入,强大隆隆声,释放电声之魅力。此刻,在一种坚定的声音衬托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场景:格里高尔的屋子被翻覆,墙倾斜,床掀起,给人一种颠覆感;另外,由三个黑人演绎的魂灵出现,他们从倾斜的墙后爬进来,向格里高尔走去,非常具有戏剧性;还有,格里高尔自变成虫之后,全身是弯弯曲曲的,扳不回原位,这时,他猛然回头看着黑人,他站立了,在向他的灵魂致敬!
啊!天哪!
声音慢慢扩大,有一种步伐的前进感,又很神秘,基于那一片孤寂的声音同时逐渐放大。穆恩的处理也非常到位,他在此加入人声,托起热烈的情绪。
音乐片段借用
舞剧借用一些其他的音乐,碎片般散落在前后进行中,很多时候是对原创音乐整体灰暗色调的平衡,偶尔给一些协和的过去的美好乐音,如妹妹跳芭蕾时用肖邦的圆舞曲,妹妹想唤起哥哥的记忆时用Wanda Slavik情意绵绵的老歌。
我们家多平静。
这些声音形成过去与现在、温情与孤寂、爱与恨、自然与变形、激烈与舒缓、紧张与释然等等的反差对比。
尤其在舞剧结束前,作为对紧张度的释放缓解,当三位房客住到家里,大家开始放松,先响起了一段爵士乐,然后是一大段犹太舞曲,房客们跳舞,之后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加入了,大家一起舞蹈,非常愉快。同时,一墙之隔的格里高尔也很开心地舞动他的虫爪,甚至全然忘情地爬出自己房间,在欢快的舞曲达到最高嘲时,大家突然看到格里高尔。
萨姆沙先生!
然后妹妹用喊声叫停了舞曲。瞬间,全场寂静,那个孤寂的声音慢慢响起。
变形三:人声颂赞,吾行矣
对《变形记》进行艺术再创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部1977年的动画《山沙先生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 of Mr. Samsa),用沙画来塑型,影像和声音都配合得不错,可惜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尾。而这出舞剧很完整,还有一个与小说不同的结尾。
亲爱的爸爸妈妈,事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你们也许不明白,可我明白。对这个怪物,我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我们照顾过他,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想谁也不能责怪我们有半分不是了。
再次遭到唾弃和拒绝,格里高尔哭了,此刻舞台上出现在一次颠覆,之前翻倒起来的床和墙被归位,声音变得很悠远,空灵。格里高尔看着那扇窗,回过头向着客厅的方向哭泣,但是他的内心依然温暖。
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
第三步变形,他决定离开这个家以及亲人们,今后不再有冲突、反抗或忍受,是又一次艰难的蜕变,但是将回归本来,回到来处。这里没有小说中格里高尔躺在地板上“呼出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的悲哀。格里高尔放弃在世间的所有纠结,坦然走向有光的窗户。穆恩再次运用他极其感人的嗓音,从哼唱到颂赞般的高歌,直至声嘶力竭。电声一同出现,推进、扩展、升腾,舞台整个地黑掉,没有一次亮光,但是那有力的人声,充满整个场子,激荡着每一颗心灵。
“让我们感谢上帝吧。”仿佛这句话不是出自父亲,而是从格里高尔口里流出。
主题再现
当灯光再度从墙内透出时,结尾音乐响起,主题二再次出现,它变得如此温暖而柔美,用考究的复调来装饰和展开,各声部是那么协和。一时间,金光覆盖住灰暗,爸爸、妈妈和妹妹盛装走出,向着格里高尔离去的方向致意。声音传递了很多意思,可以这么说,皮塔抚平了卡夫卡的伤痛,也暂时安置了现代人脆弱的心。主题最后一次再现,还在变形,发出八音盒似晶莹剔透的声音,仿佛什么与远去的格里高尔之魂合一了。你可以绕过卡夫卡,但是你绕不过你自己。
来吧,喂,让过去的都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