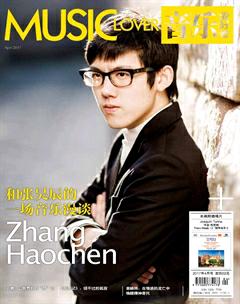圣洁的灵魂
邹彦
恐怕现在知道罗马尼亚钢琴家蒂努·李帕蒂(Dinu Lipatti)的人已经不多了,对他的演奏仍然情有独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然而对那些熟悉并且热爱他的人来说,李帕蒂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录音成为他们缅怀这位钢琴家最好的方式。下面这张照片中的年轻面容永远定格在了三十一岁;他的艺术生命刚刚绽放就戛然凋零,在人世间只度过了三十三个春秋就于1950年死于何杰金氏病(Hodgkins disease)。时间流逝,2017年3月19日,李帕蒂已经整整一百岁了。
1917年3月19日,康斯坦丁·李帕蒂(Constantin Lipatti,“蒂努”是对他的爱称)生于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他的双亲都是音乐家,且生活富足,虽然他们都没有接受过严格的音乐训练,但是在音乐上都有极高的修养。他的父亲曾跟随弗莱舍和伊萨伊学过小提琴,他的母亲被当时的某些评论认为是罗马尼亚最好的钢琴家之一。有罗马尼亚最伟大的音乐家乔治·埃内斯库做教父,加之他音乐家庭的熏陶,我们完全可以说李帕蒂是为音乐而生。四岁的时候,小蒂努就已经在慈善音乐会上演奏,并开始作曲了。
由于李帕蒂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以及自幼便脆弱的体质,他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在布加勒斯特接受了私人音乐教育之后,他于1934年,即十七岁时在维也纳参加了国际钢琴比赛,获得了第二名——这对于李帕蒂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他完全具备了冠军的实力。虽然谦卑的李帕蒂对这个成绩很满意,但评委会的这一决议引起了法国大钢琴家阿尔弗雷德·科尔托(Alfrod Cortot)的极大不满,他以退出评委会作为抗议。比赛获得第一名的人可以去法国继续深造,李帕蒂不可能获此奖励,但他却收到了另一个更令他大喜过望的邀请——科尔托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他请这位踌躇满志的罗马尼亚钢琴家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并且收其为徒。这成为了李帕蒂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巴黎,李帕蒂的老师不仅有科尔托,还有大指挥家查尔斯·明希(Charles Munch)和作曲家保罗·杜卡(Paul Dukas)。杜卡收李帕蒂为徒,授其作曲,然而在看了李帕蒂的作品总谱之后,杜卡迅速得出结论:“我实在是没啥可以教你的了。”刚刚抵达巴黎不久,李帕蒂这位“小巫师”就已经成长为了“魔法师”。后来,李帕蒂投入被恩斯特·安塞美(Ernst Ansermet)称为其“精神的母亲”的纳蒂亚·布朗热(Nadia Boulanger)门下学习,后者成为了李帕蒂终生的良师益友。也正是在布朗热的劝说下,李帕蒂走进录音棚录制了可以令我们后人不断追忆他的珍贵录音。
感谢布朗热这位伟大的音乐教母,感谢录音师瓦尔特·莱格(Walter Legge),这些单声道的录音对当下的意义已然超越了“弥足珍贵”这样的词语,最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让我们听到了一颗“圣洁的灵魂”——这是法国作曲家普朗克对李帕蒂音乐艺术做出的最佳评论。对音乐严肃的态度是李帕蒂追求真理的方式,高贵、优美、真诚是其在音乐中永远向我们传递的信息。
李帕蒂的确是一位艺术上的天才。他的同胞克拉拉·哈斯基尔(Clara Haskil)在信中写道:“我真是嫉妒你的天才。魔鬼带走了它。为什么你有如此多的天才,而我只有这么少?这真的公平吗?”

谦卑的个性和腼腆的外表令李帕蒂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柔弱的。哈斯基尔说他是“一位被自己的天才搞得手足无措的人”。1933年,李帕蒂在布加勒斯特与威廉·门格尔贝格(Willem Mengelberg)合作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当他走上舞台开始排练的时候,门格尔贝格说“那不是一位李斯特钢琴家”(Das ist kein Liszt-spieler);然而,当李帕蒂开始演奏之后,门格尔贝格立即修正了刚刚的断言。的确,从李帕蒂的录音和现场演奏中,没有人会感觉到他是一位童年即体弱多病、青年时代又身染重疾的钢琴家——他的演奏有着非凡的控制力。仅仅在其生命最后阶段的照片中,我们才能在其脸庞看到倦容。音乐是这位苦命却从容的钢琴家医治病痛的良药,这位有着“圣洁的灵魂”的钢琴家的每一次演奏,都是一次通向帕尔纳索斯山的朝圣之旅。他的演奏具有一种特殊的充满力量的柔性。
时至今日,李帕蒂的完美主义已经成为传奇。他说他需要三年时间练习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而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则需要四年时间。对贝多芬的敬畏使李帕蒂很少公开演奏这位“乐圣”的作品,如果不是阿图尔·施纳贝尔的劝说,他或许根本不会学习贝多芬的作品。他练习过《华尔斯坦奏鸣曲》,并且在1949年访问伦敦时为BBC录制了这部作品。他公开演奏的贝多芬的作品还有《D大调钢琴奏鸣曲》(Op.10,No.3)、《暴风雨奏鸣曲》和《热情奏鸣曲》,但是这三部奏鸣曲的录音尚未找到。
“二战”爆发之前,李帕蒂回到了布加勒斯特;“二战”期间,他于1943年和他的未婚妻玛德琳娜·坎塔库泽纳(Madeleine Cantacuzene)辗转来到了日内瓦,两人身上仅有五瑞士法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帕蒂首次出现了何杰金氏病的症状。1944年,二十七岁的李帕蒂被任命为日内瓦音乐学院钢琴大师班的教授,这一职务一直延续到他去世的前一年。

在李帕蒂去世之后发现的一份草稿反映出了李帕蒂对教学和音乐演奏的观点,这是他计划于1951年与布朗热一起在日内瓦音乐学院联合举办大师班的讲稿。他的观点与时下所推崇的基于历史信息的演奏截然相反,认为“一定不要用已经逝去的或是过去的眼光看樂谱,因为这只会给你带来约里克的骷髅”;他所坚信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名言“音乐是当下”。因此,他的演奏会不断发掘钢琴这件现代乐器的优势,这不仅体现在他演奏的拉威尔《丑角的晨歌》之中——其中不仅有令人赞叹的技巧,更是充分探索了钢琴上五光十色的声音;而且像莫扎特《C大调钢琴协奏曲》(K. 467)这样的古典时期作品也被他赋予了强烈的戏剧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李帕蒂没有任何作品传世,但是从这部钢琴协奏曲的华彩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在作曲方面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