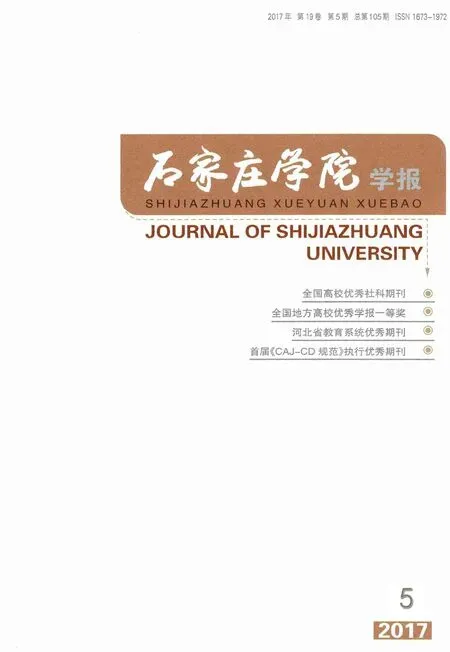群臣上醻刻石赵王遂二十二年说新证
秦进才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群臣上醻刻石赵王遂二十二年说新证
秦进才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群臣上醻刻石自清朝道光年间发现以来,年代问题便成为学者们探索的重点,先后提出了六种主要看法,刘位坦主张的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说逐渐为学界多数人所认同,成为主流认识。为了解刘位坦主张的源流变迁,先移录珍贵而学界稀见的刘位坦跋文,以明其主张的源头所在。然后考察赵之谦、俞樾、陆增祥、徐森玉等人的说法,以观察其流变发展。再收集、归纳50年来新发现的与群臣上醻刻石相关的简牍、石刻、铜器铭文、封泥印章等新资料,以扩展其资料范围,补充其新证据,以见刘位坦主张的可靠性。
群臣上醻刻石年代;刘位坦主张;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新证
考察文物的年代,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有些文物确定其年代,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见仁见智的看法经常存在。从石刻年代的确定来看,有些石刻本身有具体的年代记载,断定年代并不复杂,有些石刻没有具体无疑的年代记述,确定其年代是一项逐渐接近事实的工作,毕其功于一役的期望是不合乎实际的,由一个人盖棺定论也是不现实的。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朱山群臣上醻刻石的年代问题,从道光年间发现以来先后由沈涛、刘位坦、张德容、丁绍基、王树枏等提出了不同的说法。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分歧在日趋缩小,石虎建武六年说认同者逐渐减少,认同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说法者日益增多而成为主流,但任何说法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完美无缺,其疏略处、片面性尚需新资料的发现,逐步完善。王国维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239顾颉刚曰:“新的学问,靠新的材料。”[2]史料的发现、史料的扩展、新方法的应用等决定着史学的发展。笔者曾撰写《群臣上醻刻石年代述论》①论文提交给2014年召开的汉代赵国与邯郸文化国际学术论坛讨论,并在《邯郸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发表。,考察了前贤的六种主要说法,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近来又发现了一些新史料,再次围绕着刘位坦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的主张,提供新证据,以期有助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研究的发展。
一、刘位坦跋的录文与评介
刘位坦(1802-1861年),字宽夫,室名君子馆、叠书龛、甎祖斋等,清顺天府大兴县(治今北京市市区)人。道光五年(1825年)乙酉科拔贡生。六年,朝考一等,以知县用。任刑部贵州司主稿、刑部福建司郎中等。二十四年,授湖广道监察御史。二十六年,署刑科给事中。二十七年,掌河南道监察御史。咸丰元年(1851年),补授湖南辰州府知府。七年,告病回京。十一年,卒。收藏金石书画丰富,精于鉴别,工书善画,兼善篆隶。著有《叠书龛遗稿》②刘位坦撰《叠书龛遗稿》不分卷,其外孙黄国瑾编录,清末抄本,收藏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处,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清光绪年间铅印本,收藏在上海图书馆等处。等。因曾任湖广道、河南道监察御史,人称刘侍御、刘宽夫侍御等。
现代参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讨论的学者,都知道是刘位坦首先提出群臣上醻刻石为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说的,但具体是如何说的,尚未见有人说明白,因为很多参与讨论的学者没有看到过完整的刘位坦跋语原文③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群臣上醻刻石》载:“祥按:沈、刘二说未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96册第84页)即沈涛、刘位坦二说未见到其具体的论述。徐森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言:“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说,清刘位坦考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一五八年)。惜刘说原文未见。”(原载《文物》1964年第5期;又载徐森玉著、徐文堪编《汉石经斋文存》,海豚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19页;还载上海博物馆编《徐森玉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本文用《徐森玉文集》本。)其他人也多是根据赵之谦等人的著述来了解刘位坦的主张。,只是通过赵之谦等人的只言片语,辗转相传知道刘位坦的主张。梁思成讲:“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3]161研究群臣上醻刻石的年代,固然需要观看原石,欣赏早期拓片,也需要了解前人的看法,作为研究者连最早主张群臣上醻刻石年代为汉文帝后元六年的刘位坦跋都看不到,也是一个遗憾。笔者为此苦苦求索,找到了刘位坦的《叠书龛遗稿》,其中虽言刘位坦“生平著作,题跋是第一文字,诗其余事也。”①黄国瑾言,见《叠书龛遗稿》影印本。但《叠书龛遗稿》中并无题跋。书海寻它千百度,方知刘位坦跋语由赵之谦转述,因为赵之谦书法、著述被日本人推崇,很多作品流散到日本,包括赵之谦的《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等。多番寻找,几经周折,方得见到其书,看到刘位坦的跋语。欣喜之余,把刘位坦跋语移录于下,与大家共同分享。
刘位坦跋三则
五凤二年石刻称“鲁卅四年”,与此刻同一例,汉封国得自编年也。考班史《高五王传》:赵隐王如意立止四年,幽王友立止十四年,惟赵王遂立凡廿六年。自文帝元年立国至后元六年癸未,乃其廿二年。是年,匈奴寇上郡,周亚夫屯兵备之,帝亲劳军。越三年丙戌,景帝用晁错议削赵常山郡,遂怨,与吴、楚谋反,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烧杀德、悍。此刻曰群臣上,其时或因出师,或因归国,德、悍纪事勒石耳。
此西汉刻石也。或谓为后赵石虎建武六年刻,窃不谓然。建武六年,即晋咸康六年也,是年正月庚子朔,八月有丙申无丙寅。此刻“八月丙寅”,可知其非是岁矣。且统计其前世为编年之数,近见西洋人或如此,金石刻未有此例也。咸康时遗刻如石如叀,世所不乏,其时字体罕有尚含篆法如此者。位坦既为此刻考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癸未刻,复识数语于右。
又考班史《景十三王传》:赵敬肃王彭祖立六十余年,共王充立五十六年,缪王元立廿五年。范史《四王三侯传》:赵节王栩立四十年,顷王商立二十三年,惠王乾立四十八年。凡此固皆得有廿二年之称。然彭祖之廿二年为武帝元光四年,其时朝廷已有年号纪元,何得不冠于首书之?其不书知为文帝无年号时矣。若充若元,更在彭祖后。若栩若商与乾,则其时字体变隶。此刻绝不在彼时也。世咸重甘泉五凤石字,此更在前,篆法古朴,不益可宝耶!②《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赵廿二年上寿刻石》,载《书苑》第7卷第3号,1943年。赵之谦著、戴家妙整理《赵之谦集·悲盦序跋集存·二金蜨堂双钩十种序跋·赵廿二年上寿刻石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09页),亦收录刘位坦、赵之谦跋文。两者相比较文字有差异者四处,笔者依据《书苑》第7卷第3号本为准,分段亦依据其本。上述刘位坦跋文,是赵之谦从刘位坦之子刘铨福(字子重)处得到,并收录于其书中。
作为一种主张的首创者,一般能够说对百分之五十以上,就很不错了,因为首创者前无借鉴,思虑难周。而后人如有所发展,则需要耗费比首创者更多的时间,才有可能有所推进。而刘位坦对于此问题的讨论,从群臣上醻刻石与五凤二年石刻体例相同入手,以汉封国自得编年为前提,考察汉初赵王在位年限,只有赵王遂立二十六年,其二十二年是汉文帝后元六年,根据其史事,断定“此西汉刻石也”。指出:“且统计其前世为编年之数,近见西洋人或如此,金石刻未有此例也。”③《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赵廿二年上寿刻石》,载《书苑》第7卷第3号,1943年。俞樾撰《春在堂随笔》卷二亦言:“沈西雍观察谓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之年而并数之,故称赵廿二年。然金石刻辞从无此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两人所见略同。从史实、纪年体例与字体三方面否定了沈涛的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为了论述的更全面,又收集了《汉书》《后汉书》中在位超过二十二年的六位赵王,然后从历日朔闰、汉封国纪年款式的变化和东汉字体的变化,否定了六位赵王与群臣上醻刻石有关联的可能性,说明了群臣上醻刻石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的唯一性。说明了群臣上醻刻石的价值——年代久远,珍稀罕见,篆法古朴等。思路清晰,考虑周密,竖起了群臣上醻刻石年代为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主张的旗帜,奠定了年代研究的基础,开创之功不可没。
然首创者难以为工,智者千虑难免有失,刘位坦主张亦有疏漏处。
一是刘位坦言:“五凤二年石刻称‘鲁卅四年’,与此刻同一例。”这种看法亦为陆增祥等所认同④《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群臣上醻刻石》载:“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为赵王,其廿二年为文帝后元六年。是年八月癸卯朔,廿四日直丙寅,刘氏所言盖赵王遂之廿二年也。以五凤石刻鲁卅四年例之,书法正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96册第84页。。确实,群臣上醻刻石与五凤二年石刻,两者的确有相同之处,都是记载汉诸侯王纪年的刻石,反映了汉诸侯王纪年存在的现实,十分珍贵。也应当看到两者亦有不同之处,“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是国号冠于纪年之前,即以国号纪年,反映的是汉文帝时代诸侯王自得纪年的情况。“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4]7300,皇帝年号纪年冠于诸侯王纪年之前,反映的是汉宣帝时代诸侯王纪年的情况。两者不仅有汉文帝与汉宣帝时代的不同,还有诸侯王与汉朝朝廷关系的变化,汉朝初年,诸侯王“掌治其国”[5]741,“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6]2545,“宫室百官,同制京师”[5]394,形成与皇帝“共天下”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5]741,转变成为汉武帝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5]395的富翁,甚至有些“贫者或乘牛车”[5]2002的境地,以至于有的“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5]2681,诸侯王地位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群臣上醻刻石反映了汉初诸侯王纪年特点,五凤二年刻石反映了汉武帝以后诸侯王纪年的特点,正是这种诸侯王政治、经济地位变化的具体体现,因此,两者又有不同之处。
二是刘位坦所言:“然彭祖之廿二年为武帝元光四年,其时朝廷已有年号纪元,何得不冠于首书之?”此话的确有道理,也的确有这一方面的一些证据。如传世文献《史记》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年表列传的年代记载格式,又如山东日照海曲汉墓出土“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汉简[7],是目前所知皇帝年号纪年排列在诸侯王国纪年之前而又相对应最早的汉简[8]。又有“(元康)五年,六安十三年”铭文的阳泉熏炉①此铭文见阮元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九《阳泉使者舍熏炉》(《续修四库全书》,第901册第682-683页)等书。阮元认为是东汉的器物,六安是侯国。陈介祺认为是西汉的器物,六安是王国。其泐文、陈介祺撰《簋斋金文考·汉阳泉使者舍熏炉考释》认为,六安王刘“禄子定立于本始元年,其十三年为神爵元年。《宣帝纪》载是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万岁宫,神爵翔集。诏以五年为神爵元年”。元康“五年三月之始改神爵也”,(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1页。)当为元康五年。又有“钱同人考为元康五年未改元为神爵时”。(《攈古录》卷四《汉》,《续修四库全书》,第895册第312页)。徐正考在《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发表《“阳泉熏炉”泐文考》认为,泐文三个,为“两”字与“元康”二字,汉宣帝元康五年,与六安缪王刘定十三年正好相符。由上述可知,年代泐文为“元康”二字。,还有“建昭三年,鲁十六年四月,受殿中”铭文的铜钟[9]301-302等,其款式与“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4]7300石刻基本一致。刘位坦所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并为后来的考古发掘发现所证实,可见其认识之高明。但亦有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木牍上“卌七年十二月丙子朔,辛卯……卌八年狱计承书从事”的记载②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载《文物》1981年第11期。广陵王刘胥立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四月,四十七年为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汉宣帝本始三年十二月丙子朔,与“卌七年十二月丙子朔”相合,故知为广陵王刘胥四十七年。,还有江苏高邮神居山一号汉墓出土木牍上“六十二年八月戊戌”的记载[10]77,“卌七年”“卌八年”“六十二年”分别指广陵王刘胥在位的第四十七年(前71年)、四十八年(前70年)与六十二年(前56年),相对应于汉宣帝本始三、四年(前71、70年)、五凤二年(前56年)。也就是说到汉宣帝时代,既有皇帝年号纪年排列于诸侯王纪年之前的纪年款式,也有不写皇帝年号纪年、只有诸侯王国号纪年的款式,两者在汉宣帝时代同时并存。因此,不能认为汉武帝时代有了皇帝年号纪年,诸侯王纪年之前就一定冠以皇帝年号纪年。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同一时代的时空下,有着不同的社会现象存在,必须注意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
三是刘位坦言“缪王元立廿五年”,作为有可能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相联系赵王中的一位。稽诸史册,汉武帝征和二年“九月,立赵敬肃王子偃为平干王”[5]209。在位十一年薨。“元凤元年,缪王元嗣,二十四年,五凤二年,坐杀谒者,会薨,不得代。”[5]412又载:“子缪王元嗣,二十五年薨。”[5]2421上述记载,世系无矛盾,时间相吻合,真实可靠。但缪王元,当是平干缪王元。东汉著述记载,有刘秀“至邯郸,赵王庶兄胡子进狗?马醢。故赵缪王子临说上灌赤眉”[11]5,又有“初,河间赤眉大众将至,百姓骚动。[王]郎明星历,以为河北有天子气,素与赵缪王子林善,豪侠于赵,欲因此起兵”[12]15,还有刘秀“进至邯郸,故赵缪王子林说光武曰:‘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李贤注云:“《东观记》‘林’作‘临’字。”[13]11等。从东汉著述来看,平干缪王元又有赵缪王之称,当是因平干王是赵敬肃王之子,故称平干王元为赵缪王。东汉时代,称缪王元为赵缪王无妨,但西汉时不可能称为赵缪王元,因为缪王元在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嗣位,向后推22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又是赵共王充在位的第七年,同时并世不会存在着两个赵王,只能一个称赵王充,一个称平干王元。到新莽更始帝之际,赵国早已绝封,称缪王元为赵缪王元也就无妨了。固然平干缪王元在位超过了22年,也可以泛称为赵王,但汉宣帝神爵三年、缪王元二十二年八月戊辰朔,没有丙寅日。因此,刘位坦把缪王元在位22年作为可能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有关者,无疑有失考察。
刘位坦跋语,从多方面论述了群臣上醻刻石的年代为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否定了沈涛的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否定了赵王遂之外两汉六赵王的可能性,说明了群臣上醻刻石的价值,自成一家之言,不仅为其姑爷黄彭年、外孙黄国瑾等所认同、所传播,而且为学术界诸多学者所认同,逐渐成为主流看法。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刘位坦不可能看到后来考古发现的新资料,更不可能了解后人研究的新情况,受其启迪,完善自己的主张。始创者难为工,认识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说法有些疏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研究探索永远是有遗憾的事业。讳言其过是闭目塞听、掩耳盗铃,苛求古人也是过分认真吹毛求疵,指出其是非功过,明白今后的努力方向就可以了。刘位坦主张的开创之功不可没,他的成就,提高了后人研究的起点;他的疏漏,成为了后人研究的突破点。
二、赵之谦等对于刘位坦主张的认同、补充与发展
刘位坦群臣上醻刻石跋语的主张传世之后,其群臣上醻刻石年代为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的主张,逐渐成为主流的说法,笔者已在《群臣上醻刻石年代述论》中作过介绍,不再重复,而是要提供一些新发现的资料,供大家参考。所谓新发现的资料,是笔者新发现的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相关的原始性资料,或是近来看到的关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新的论述,或者是曾经见到而现在又有新看法的资料等。这里先说近年来新看到的前人的一些看法等。
赵之谦①赵之谦(1829-1884年),字益甫、 叔,号悲盦等,室名二金蝶堂等,浙江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市区)人。咸丰九年(1859年),中举人。官江西南城知县等。诗文务为新奇,绘画富有新意,书法别具一格,篆刻意境清新,将诗文、书、画、印融为一体。著有《悲盦居士文》《补寰宇访碑录》等。是较早介绍刘位坦群臣上醻刻石跋文者之一。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赵廿二年娄山刻石拓本载赵之谦题跋:“此为西汉祖刻,指为石赵者非。详余所述汉刻十种双钩本。”[14]肯定刘位坦的主张,明确否定沈涛的看法。从“详余所述汉刻十种双钩本”中,知道赵之谦还有更为详细的说法,保存在其中。因为赵之谦的《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流落到日本,国内很少有人了解赵之谦在《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中的说法。近来笔者方得以观其详,了解其看法。赵之谦在《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赵廿二年上寿刻石》中,首先抄录了沈涛《交翠轩笔记》的说法,又抄录了刘位坦跋语,然后谈了朋友和自己的看法。
赵之谦言:“余来京师,首见此刻,即断为西汉人作,彼时单据书法及字体得之。”看到沈涛的《交翠轩笔记》和刘位坦跋语后,分析了“颇有和沈说必指为石赵者”的原因,在于“半为观察(即沈涛——引者注)精考证不敢疑,且执世俗之见,以为西汉文字,宋人且不得见之,何况今日,故漫识一金石变例而绝无确证”,因此,感觉“宽夫先生所考最精核,无以益之”[15],认同刘位坦关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的主张。引用胡澍(字荄甫)②胡澍(1825-1872年),安徽绩溪人,字荄甫、甘伯,号石生。咸丰九年(1859年),中举人。后捐升郎中,分发户部山西司。因中年多病,弃仕从医,撰《黄帝内经素问校义》。工篆刻,得秦汉人遗意,所书篆隶,遒劲中多有柔媚,飘逸中带有委婉。赵之谦曰:“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荄甫。”(《赵之谦集·悲盦序跋集存·临嶧山碑题识》,第164页。)对胡澍推崇备至。的说法,“以为‘寿’,犹以‘畴’为‘寿’。《新序》‘尹寿’,《荀子》作‘君畴’。只取声借。‘上寿’乃汉人颂祷常语,《后汉·明帝纪》注所谓‘寿者,人之所欲,故卑下奉觞进酒,皆言上寿’是也。读为答之,而言群臣上,文不雅驯,义亦无取。”[15]赵之谦标明是引用胡澍的说法,博采众人之长,不掩他人之美,并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此刻实两汉祖石,群臣上寿自以为守边归国为合”[15]。既受刘位坦“此刻曰群臣上,其时或因出师,或因归国,德、悍纪事勒石耳”的影响,认为“自以为守边归国为合”,实是推测之词。又提出“此刻实两汉祖石”的新看法,独树一帜,鲜明深刻,为后人所沿袭。
赵之谦又指出:“此汉刻之无可疑者,古诸侯得自书年,不独鲁卅四年也。前则《春秋》书隐公元年,后如《史记·功臣侯年表》书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后四年,简侯奇元年。皆与五凤石刻一例。有先书侯国纪年者,如《绛侯世家》上书建德十三年,下书元鼎五年。及《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地节元年。皆是。其专书年,见于《淮南·天文训》,‘淮南元年冬’。周阳侯甗,‘侯治国五年’。后则文昌殿钟詺曰‘惟魏四年’,见《文选注》。皆可取证。”[15]在肯定群臣上醻刻石是汉代刻石的前提下,又列举证据,以证明“古诸侯得自书年,不独鲁卅四年也”的看法。充实了刘位坦主张的资料依据,丰富了刘位坦主张的内容,所列举的资料,多与五凤石刻体例一致。还指出,“附和悠谬之说,无征不信”,“诸家不之及,率称石赵,疏矣”[15],再次否定了沈涛后赵石虎建武六年说。
赵之谦《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赵廿二年上寿刻石》跋语,收集了当时对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的两家主要看法,从字体、书法、史实、文献、石刻体例等方面,否定了沈涛的看法,认同、充实了刘位坦的看法,探讨了“”的字义,并表明自己的看法,但数量仅有两本,有的流落海外①邹涛编著《赵之谦年谱》载,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九日,《二金蝶堂双鉤汉碑十种》成。九月十八日,装成。正本贻沈均初,副本贻魏稼孙(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07页)。正本后来流落日本,曾收藏在东京全氏家,在1955年9月“赵之谦殁后七十年纪念展”上展出。副本后来曾归罗振玉大云书库,有“《二金蜨堂双钩汉碑十种序跋》手稿本,赵之谦撰。书衣有魏稼孙题记,末有‘稼孙审定’印”的记载。(王国维编《大云书库藏书目》,《雪堂类稿》戊四《长物簿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页。)有的被“称为天壤间唯一仅存残本(真迹原存朝鲜金氏葆华阁)”。(黄苗子《记赵之谦》,《学林漫录》第六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8页。)《书苑》第7卷第3号《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目次下,注明是“全氏葆华阁藏”,似乎全氏葆华阁在东京,而非金氏葆华阁在朝鲜。制作仅此两本,有的流落海外。因此,国人难得见其真容,所以能看到的只能是影印本,或者排印本。。正本以影印的方式1943年开始在日本书道书法类刊物《书苑》上连续登载②《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正本,1943年收入日本三省堂出版的《书苑》中连载出版,包括第7卷第3号等。笔者看到筒子页装订的《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本子,比《书苑》第7卷第3号前面多封面、内封、序言等四页,后面多杨量买山记、莱子侯刻石等12页。其他内容、规格、页码、水渍印痕等均相同,当是《书苑》杂志的抽印本,汉刻十种收录了四种,并非全本。,又作为《二金蝶堂遗墨》的组成部分在日本出版影印本③《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正本,在西川宁编的《二金蝶堂遗墨》中影印出版,一是日本晚翠轩1946年出版的线装四册本;二是日本二玄社1979年出版的精装本。,国内还有魏锡曾抄本④同治五年(1864年),魏锡曾(即魏稼孙)抄本《二金蜨堂双钩十种序跋》一卷,收藏于上海图书馆。魏锡曾跋曰:“同治癸亥秋冬间,见 叔成此书于都门,其正本旋贻均初钩摹跋语,而以双钩初稿畀余。丙寅九月,余访均初吴门,收录此本,至辛未四月十八日始缀成册,续当据初槀重钩入。此序跋俾为副本行世,苦孏惰,不知何日践此言也。十九记。”(《赵之谦集·前言》,第11页。)均初,即沈树镛表字。由魏锡曾跋可知《二金蜨堂双钩十种序跋》正本、副本、抄本的由来。,传播不广,了解者不多。广泛传播刘位坦主张和赵之谦说法影响比较大的是赵之谦编撰的《补寰宇访碑录》卷一《群臣上寿刻石》中所言的“大兴刘位坦考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此汉祖刻。疑为石赵者非”等结论性语言。晚清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一《群臣上寿刻石》、光绪《畿辅通志》卷一百四十八《金石略十一·群臣上寿刻石》、光绪《广平府志》卷三十五《金石略上·赵群臣上醻石刻》等金石著述,引用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的看法。现代《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一册《群臣上醻刻石》、沙孟海《西汉刻石讲稿》等直接抄录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的看法,而《秦汉石刻题跋辑录》等,间接地引用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的观点,即在书中收录了引用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的著述。杨铎说:“据《补寰宇访碑录》云:大兴刘位坦考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之谦案:此汉祖刻。疑为石赵者非。……此称赵廿二年,刘位坦定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与余所见正和。”[16]5020学者们直接看到刘位坦跋语者很少,间接地从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中了解了刘位坦的看法,赵之谦传播之功无与伦比。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必讳言赵之谦所言也有错谬之处,除了缪荃孙所言“惟赵叔之书最草率、最传布”⑤缪荃孙著《艺风堂文续集·外集·答郑叔问书》载:“惟赵 叔之书最草率、最传布,因沈韵初诸人富收藏而不甚读书,为 叔盛气所摄,故推许甚至。”(《缪荃孙全集·金石四》,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41页。)这是对于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的总体评价,既看到了最草率的情况,也说明了“最传布”的长处。而在《金石分地编目》卷四《直隶四·永年县》对群臣上醻刻石的著录,并未指责赵之谦的不足。(《缪荃孙全集·金石四》,第146页。)外,《补寰宇访碑录》卷一《汉·群臣上寿刻石》等还存在着一些错误之处,如说:“左侧有口口判官郁久闾明达题名,乃北魏人书。”《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赵廿二年上寿刻石》亦言:“石右拓本露文尚类文字,闻有北魏人题名一行,俟访。”“左侧题名为‘口口判官郁久闾明达’。”提供了资料线索,又有自己的看法。现代学者孙继民、郝良真、张士忠等到永年朱山考察,弄清了朱山顶上保存有因石而宜镌刻的九行文字是:“监军判官济阴郁久闾明达 侍御史鲁国郗士美 洺州刺史范阳卢顼 冀处士卢叶 监察御史刘荆海 邢州别驾杨审言,口口县尉李嘉同登。大唐贞元(十四)年九月廿八日。”是为了纪念郁久闾明达、郗士美、卢顼等攀登猪山而镌刻的,属于登山摩崖题记。[17]是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时人所书写的,而非北魏人书写。传统金石学家研究资料主要是依据辗转收集的拓片,进行编纂整理与研究,大型书籍全部目验拓片已属不易,缺乏实地调查更是在所难免,著录中出现错谬不足为奇。同样,赵之谦编撰《补寰宇访碑录》也不可能对于所收录的碑刻铭文都到实地考察一遍,以讹传讹的事情也就难以避免了,这也是时代的局限使然,后来者不必苛求于前人。
俞樾⑥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等,室名春在堂等,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至河南学政。以事罢官,居苏州,孜孜不倦于教育,潜心钻研于学术。著有《春在堂全书》《茶香室丛钞》等。对于刘位坦主张的质疑、认同与论证,主要是通过与沈树镛等人往来信函中体现出来。一方面说:“刘宽夫侍御谓汉侯国得自纪年,定为赵王遂之廿二年,较沈说为得之。”[18]18肯定了刘位坦主张比沈涛说法高明,更切合实际。另一方面对刘位坦主张因为没有看到具体的论述而有所怀疑,说:“前示赵刻石文,刘侍御定为赵王遂。然考《汉书》赵诸王享国长久者亦不一人,《景十三王传》赵敬肃王彭祖以孝景前三年立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后徙王赵,以征和元年薨,计在位六十三年。其后又有共王充五十六年薨。未识侍御何以专指为赵王遂?”“然则此碑为何王,固不能臆决矣!”[14]俞樾不了解刘位坦主张的具体内容。看到了沈树镛所言的刘位坦主张后,表示“前示娄山石刻,仆以汉代赵王享国长久者不止遂一人,妄为刘侍御献疑。今承示知侍御君固已博考及此矣。但侍御援五凤石刻为证,彭祖廿二年是武帝元光四年,其时朝廷已有年号,何得不以冠首?知为文帝无年号时矣”[14]。疑虑没有彻底消除,“窃谓此石羌无故实,无可引证,惟‘八月丙寅’四字稍有可探索之处,计前、后《汉书》赵王之得有廿二年者凡六王,吾友汪谢城孝廉方著《廿四史年月日考》,容作书告之,请其考证此六王之廿二年八月,孰是有丙寅日者,庶此事可定乎!”①秦进才《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载《文物春秋》2008年第1期。汪曰桢(1813-1881年),字仲雍,一字刚木,号谢城,又号薪甫,浙江乌程(治今浙江湖州南云巢乡窑头村)人。咸丰四年(1854年)举人,清代以“孝廉”代指举人。上文的“汪谢城孝廉”,即指汪曰桢而言。为了解得更清楚,写信向汪曰桢求教,“鄙见以为,欲知赵廿二年为何王,当求八月丙寅之在何年。足下讲求有素,请详考《汉书》赵诸王之廿二年,何年八月有丙寅日,则此碑庶可定矣”②俞樾著、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致汪曰桢》。(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90页。)正是上文所言的“容作书告之”的书信,语言亦有相重复者。。请汪曰桢帮忙推算,以求群臣上醻刻石年代问题的解决。俞樾不盲目相信刘位坦的主张,而是在质疑、考索中认同,在探讨中深化对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的认识。菩萨是被信仰者的香火熏黑的,真理是被怀疑者的眼光发现的。俞樾的行为体现着学者执著追求真实的风范。
俞樾信函中关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的求索和看法,流传比较广泛的是俞樾致沈树镛函,因收入到《春在堂随笔》卷二中,被光绪《畿辅通志》卷一百四十八《金石略十一·群臣上寿刻石》、光绪《广平府志》卷三十五《金石略上·赵群臣上醻石刻》、《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一册《群臣上醻刻石》、容媛的《秦汉石刻题跋辑录》等著述所引用。《致汪谢城广文》函,或曰《致汪曰桢》函,收录在《春在堂尺牍三》中,[20]574-576亦被王仁俊的《金石三编·通考·汉·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石刻》等引用。而其他两封信函没有变为印刷品则知道的人极少,因此近来方被发现与引用③秦进才《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载《文物春秋》2008年第1期)作了介绍,肖鹏飞《俞樾书学研究》,渤海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引用俞樾此两封信函。。
俞樾的精神令人敬佩,但俞樾所言亦有不当之处。如言“此石羌无故实”,并不准确。长期以来,群臣上醻刻石以字体篆书而有隶书意味,被视为从篆书到隶书过渡的标志,在文字、书法演变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15字,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年代、礼俗等内容,因此为金石家、史学家等多领域的学者所关注,怎会“此石羌无故实”呢?俞樾的方法亦有局限。历日朔闰是判断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的重要内容,并非是唯一因素。因为在两汉诸位赵王当中在位超过22年,按照历日朔闰推算有八月丙寅日的,并非只有一位,而是有四位——赵王遂、赵共王充、赵节王栩、赵惠王乾,这就使得仅用俞樾从历日朔闰上考察不能解决年代问题。刘位坦认为:“若充若元,更在彭祖后。若栩若商与乾,则其时字体变隶。此刻绝不在彼时也。”从时间、字体方面,否定了后来的几位,很有道理。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东汉时代诸侯王纪年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采用了皇帝年号纪年的制度,不再存在单独的诸侯王自有纪年方式④参见秦进才《群臣上醻刻石年代述论》,载《邯郸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也可以证明群臣上醻刻石与东汉诸位赵王无关。也就是要用历日朔闰、字体、诸侯王纪年制度等综合考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不能仅仅靠历日朔闰说事。
陆增祥⑤陆增祥(1816-1882年),江苏太仓人,字魁仲,号星农、莘农。道光三十年(1850年),科举中状元,官翰林院修撰,官至湖南辰永沅靖道,有政声,以疾告归。好学博览,精金石学,著有《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借录张德荣《二铭艸堂金石聚·群臣上醻刻石》的资料,抄录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的看法,了解了“大兴刘位坦考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的观点。陆增祥并非是照抄张德荣等人的资料,而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作了一些修订、删减。如张德荣言:“右刻石拓本,高三尺九寸。”陆增祥以清代工部尺为依据改为“高五尺二寸五分,广六寸”。高度不同,又增加了宽度,更加详实。删去了“尝与潘伯寅论及此刻,伯寅谓容似过求古远,意以为汉初赵刻”及以下的案语。删去了“上醻,即上寿”语,在“犹醻也”后,改为“此刻作上醻,尤足考见古义”。“得辛亥朔”句脱漏了“朔”字。虽然沈涛、刘位坦二说原文未见,还是比较了沈涛的石虎建武六年、刘位坦的汉文帝后元六年说、张德荣的赵武灵王二十二年三种看法,从史实、历日朔闰看,“刘氏所言盖赵王遂之廿二年也”,并且与五凤石刻鲁卅四年“书法正同”。而张德荣的赵武灵王二十二年,“当赧王之十一年,张松坪以此为武灵王之廿二年,亦无不合。惟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丙寅二字转笔方折,全是隶意。仍从刘氏定为西汉时物”[20]84。“亦无不合”,是从历日朔闰方面说的,但从笔势看,仍然认同刘位坦的看法,即“赵廿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当汉文帝后元六年”[20]6。陆增祥综合考虑史实、历日朔闰、碑刻体例、文字笔势等因素,深化了刘位坦的认识。
陆增祥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成为一百三十卷《八琼室金石补正》的组成部分,并未马上流传于世。过了半个世纪,民国十四年(1925年),其子陆继煇校录其书,由吴兴刘承幹希古楼刊刻问世。传播越来越广,影印版本较多,仅笔者知道的版本就有: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六册本,艺文印书馆1966年、1976年《石刻史料丛书》甲编影印线装五十六册本,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1982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影印三册本,文物出版社1982年据刘承幹希古楼刊版刷印线装六十四册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缩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历代碑志丛书》影印三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四册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摘录影印本等,传播日益广泛,对于人们认同群臣上醻刻石年代为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刘位坦女婿黄彭年、外孙黄国瑾信奉其说法。黄彭年主持编纂的光绪《畿辅通志》卷一四八《金石略·群臣上寿刻石》,广收诸家看法,指出:“此摩崖字体,结构与嵩山少室、开母两阙同,晋魏以后篆书皆无此浑朴,决非石虎时人所能造也。”对沈涛石虎建武六年说持否定态度,这一点与刘位坦主张一致。光绪《广平府志》卷三十五《金石略上·赵群臣上醻石刻》引用贵筑(治今贵州贵阳)黄彭年云:“此战国赵武灵王时所刻。其时北伐中山、燕代,拓地千里,胡服自尊,君臣行庆,会饮于此山上理固然也。”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是否真是贵筑黄彭年所言,待查证确实后再说。赵二十二年拓本载黄彭年之子黄国瑾跋云:“此石先外祖刘公宽夫考为汉文帝后元六年刻石,会稽赵氏《续寰宇访碑录》题曰群臣上寿刻石,以冠汉石。家大人及今新城王君考之尤详,信为汉刻无疑。”①秦进才《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载《文物春秋》2008年第1期。黄国瑾跋文中的“《续寰宇访碑录》”当为“《补寰宇访碑录》”。由黄国瑾题跋可知黄彭年父子认同群臣上醻刻石是汉代石刻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说清道光年间沈涛发现群臣上醻刻石以后,研究的重点是年代问题,使用的多是序跋、札记、笔记等体裁。好处是短小精悍、简单明了,不足之处是不利于展开深入的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学术论文逐渐变成了学术研究的重要体裁,详细探讨如同抽丝剥茧,步步深入,有助于把问题论证得更透彻。以论文形式论述群臣上醻刻石年代问题比较系统者是徐森玉②徐森玉(1881-1971年),名鸿宝,字森玉,以字行,浙江吴兴(治今浙江湖州市区)人。参加乡试中举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堂化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博物馆馆长等职。征集珍稀文物图书不遗余力,为国家保存文物善本奔走南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策杖四处走访,为国家征集、鉴定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著有《汉石经斋文存》《徐森玉文集》等。,他在《西汉石刻文字初探》中说:“我认为此刻应定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比较妥当。”并从四个方面论述其理由:
一是“此刻虽为小篆,但已经能看出含有隶书的用笔,特别如‘丙寅’两字转笔处隶意更浓。以其字体和石鼓文相比,固已差距很大,即以秦始皇刻石而论,似亦应在此刻之前,因而‘群臣上寿石刻石’决不可能早到周赧王十一年”[21]141。从字体方面着眼,以群臣上醻刻石字体的小篆带有隶书的因素,比较了其他石刻,判断“决不可能早到周赧王十一年”,语气肯定。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即赵武灵王二十二年,由此而否定了张德荣的赵武灵王二十二年说。
二是“此刻亦不应视为后赵石虎时物,其原因除上述张德容的看法外,更在于以现存晋以后的篆书看,此刻显然远为古拙”[21]141-142。张德荣的看法是:“石虎篡立自称建武,必不仍冒勒之年数为纪。若当时刻石,宜著建武六年,未必概书赵廿二年。”石“虎伐燕不克,由襄国至邺,在是年之冬,而此题八月丙寅,亦与史不和”[22]1748。在张德荣论述的情理、史实的基础上,又以群臣上醻刻石字体比晋以后古拙的理由,否定了沈涛的后赵石虎建武六年(340年)说。
三是“以刻石的字体看,应以西汉的可能性为大。西汉赵王有廿二年以上的,而以历法推算其八月又有丙寅的是赵王遂。《汉书·诸侯王表》:‘孝文元年,王遂以幽王子绍封。二十六年,孝景三年,反诛。’”[21]142运用综合考察的方法,从字体、历法推算、史实记载三方面肯定了群臣上醻刻石的年代为赵王遂二十二年(前158年)。
四是“丁绍基《求是斋碑跋》反对此说的理由有二:(一)‘是年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夏四月复大旱蝗,汉廷君相方切忧劳,而藩国群臣反晏然上寿刻石贡谀,无是理也……似不应狂悖乃尔。’(二)‘赵王遂以幽王子绍封,亦非始封之君,不得云赵廿二年。’第一条反对理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封建统治阶级本来就是不顾人民的死活,刻这几个字又谈得上什么狂悖不狂悖呢?其第二条理由也同样不能成立,金明昌二年发现的鲁孝王刻石,书‘五凤二年鲁卅四年’,按《汉书·诸侯王表》,五凤二年应属鲁孝王庆忌时,但鲁始封的是共王馀,当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距五凤二年(前56年)已百年,鲁卅四年显然也不是鲁始封的年号”[21]142。这里对于丁绍基的群臣上醻刻石年代为汉武帝元光四年、赵敬肃王彭祖二十二年的理由进行了批驳,认为丁绍基反对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的两条理由不能存在。其实这是丁绍基以清朝末年的社会存在来想象西汉社会的情况,虽然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那是现代人解释的历史,而非真实的西汉历史。徐森玉所言:“鲁始封的是共王馀,当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距五凤二年(前56年)已百年,鲁卅四年显然也不是鲁始封的年号。”是针对丁绍基的“且石刻云赵廿二年,必据其立国之始以纪年”“况赵王遂以幽王子绍封,亦非始封之君,不得云赵廿二年”[23]14001-14002而言,与刘位坦跋所说的“且统计其前世为编年之数,近见西洋人或如此,金石刻未有此例也”,异曲同工。徐森玉从情理、史实、诸侯王纪年体例等方面否定了丁绍基的看法。
根据上述四方面理由,徐森玉认为:“此刻应是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赵王遂属下为他上寿献殷勤的刻石。”[21]142这是阐述刘位坦主张群臣上醻刻石年代为汉文帝后元六年、赵王遂二十二年说法的集成之作,论证细致,要言不烦,深化了认识,推进了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研究的发展。
赵之谦以来,针对着群臣上醻刻石年代诸说纷纭的现实,认同刘位坦主张的学者,从群臣上醻刻石铭文所体现的史实、字体书法、历日朔闰、碑刻体例等方面入手,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作了一些补充论证,对于不同时期对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不同的说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明确地认同刘位坦的主张,理直气壮地否定其他说法,进一步完善、深化了对刘位坦说法的认识,为后人研究群臣上醻刻石年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成为学界的主流说法,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群臣上醻刻石的研究,与其他学术问题一样,既是天下的公器,也不可能由任何人来一锤定音,而是一个逐渐深化而日趋明确的问题,也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方法的进步,新资料的发现,而为后人提供继续发展的空间。作为后来者,看不出前人的毛病没有水平,只知道前人的弊端也没有出息,更重要的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克服前人的毛病、弊端,运用新资料,使用新方法,尽力推进认识的发展。
三、50年来新发现的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相关资料
上述对刘位坦跋语的评介,对赵之谦、俞樾、陆增祥、徐森玉等人关于刘位坦主张认同、补充与发展的论述,学者们对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问题的主张、看法,都属于学术史回顾的范畴,是为了搞清楚前人做了些什么,取得了哪些成就,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做。那是前人研究的成果而非研究的依据。推动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研究等问题的发展,不是依据前人的主张、看法,而是依据那个时代真实的资料、新发现的资料。傅斯年讲:“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展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24]5-6史料的发现、扩展,决定着史学的发展。对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研究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新资料的发现,没有新看法的产生,其研究也将陷入停顿之中,而不能与时俱进。幸运的是50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发现了一些与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相关的新资料,笔者收集整理,归纳梳理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与群臣上醻刻石款式大同小异的诸侯王纪年款式的新资料。
这一类的诸侯王纪年款式,可以分为两种。
其一是国号冠于纪年之前的款式。如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很多漆器上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的铭文,[25]183当是昌邑王在位的纪年。又如湖南长沙风篷岭汉墓出土有“铜壶一容五斗,有盖,并重口口斤十二两,长沙元年造第七”铭文的铜壶,以及有“长沙元年造”铭文的铜灯、铜勺(钭)等四件,[26]“长沙元年”,当指长沙王在位之元年等,上述资料都是国号冠于纪年之前,在这一点上与群臣上醻刻石款式大同小异,还有山东曲阜周公庙东高地出土的有“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题字[27]606的石刻,“鲁六年”为鲁恭王刘馀在位的第六年(前149年),比群臣上醻刻石时间仅晚9年。这些都证明“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款式并非是单独的孤证,而是西汉诸侯王纪年系列中的一个,证实了群臣上醻刻石属于西汉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其二是皇帝年号纪年排在诸侯王纪年之前的款式。如山东日照海曲西汉墓地出土的写有“□□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的残简。[7]这里指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城阳惠王刘武十一年。又如“建昭三年,鲁十六年四月,受殿中”铭文的铜钟[9]301-302等,这些简牍、铜器所记载的纪年款式,与群臣上醻刻石款式相比,区别就是在诸侯王国纪年之前加上了汉朝皇帝的年号纪年,形成“上书天子大一统之年而下书诸侯王自有其国之年,此汉人之例也”①顾炎武撰《金石文字记》卷一《汉·鲁孝王刻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707页)。梁廷枏撰《金石称例》卷一《国制类》称:“年号与王封有国之年并称,汉鲁孝王石刻‘五凤二年鲁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成’也。”(《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0册第8页。)两者说法相近,可相互证明。。只是这个体例到了汉武帝时代才开始形成,与《史记》的《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有着相同之处。这种诸侯王纪年款式,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制度的变化和完善,体现出诸侯王纪年款式的变化,可见群臣上醻刻石款式是西汉诸侯王纪年款式继往开来系列中的一个。群臣上醻刻石款式与“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款式的异同,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言。
上述两种与群臣上醻刻石款式大同小异的诸侯王纪年款式,既证明了群臣上醻刻石并非是孤立的存在,是西汉初年诸侯王纪年的典型款式,又证明了群臣上醻刻石款式后来的发展,群臣上醻刻石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诸侯王纪年体系中重要的一环,由此也可以证实刘位坦主张的可靠性。
二是与群臣上醻刻石款式相异的诸侯王纪年资料。
1968年5月,发现保存完整的满城汉墓,出土金、银、铜、铁等遗物1万余件,其中有诸侯王纪年铭文者,铜器有铜钟、铜灯等7种17件,漆器有尊、盘、耳杯等3种24件,总计器物有10种41件。从诸侯王纪年的角度看,可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是明确有诸侯国标志者。如有“中山内府钟一,容十斗,重(缺文),卅六年,工充国造”[28]43,48铭文的铜钟;有“中山内府铜盆,容二斗,重六斤六两,第六,卅四年,中郎柳买雒阳”[28]57铭文的铜盆;有“中山内府,铜鋗一,容三斗,重七斤十三两,第五十九,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28]250铭文的铜鋗;有“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八两,第一,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28]49铭文的铜钫;有“中山内府铜镬,容十斗,重卌一斤,卅九年九月己酉,工丙造”[28]56铭文的铜镬;有“中山宦者常浴铜锭,重三斤十二两,卅二年,第廿五,卢奴造”[28]74铭文的铜灯等,铭文都标明了“中山内府”或“中山宦者常浴”等机构和年代。又因为西汉中山国先后共有10个王在位,只有中山靖王刘胜在位42年,其他9个王在位无过22年者,西汉皇帝纪年更未有达到“卅六年”“卅四年”“卅二年”者。因此,可以确定这些纪年铭文属于中山靖王刘胜在位的纪年。与此种款式相类似的,如山东昌乐县东圈汉墓出土灯盘上有“菑川宦谒右般北宫豆,元年五月造第十五”的铭文[29],当指菑川王在位之元年。再如昌邑食官鼎上有“昌邑食官铜鼎一,容二斗,并重十九斤,六年造,第四”的铭文[9]288,290,昌邑六年,当指昌邑王在位的第六年。还有“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30],当指江都易王刘非在位第十七年。这种款式没有把国号冠于纪年之前,但铭文中有诸侯王国职官等因素,因此可以判断出诸侯王的国号、姓名等,与传世文献、考古资料相结合而解决其纪年归属问题。
其二是未明确标注所属诸侯王国者。如有“椒林明堂铜锭,重三斤八两,高八寸,卅四年,锺官造,第二”[28]74等铭文的铜灯,有“御铜金雍甗甑一,容十斗,盆备,卅七年十月,赵献”等铭文的釜、甑、盆等组成的铜甗[28]52,有“御褚饭盘一,卅七年十月,赵献”[28]150铭文的漆盘等,虽然没有标明是中山国的“椒林明堂”“钟官”等机构,我们根据西汉诸侯王的“宫室百官,同制京师”[5]394的制度和出土陵墓等,可以判断“卅四年”“卅七年”等纪年,为中山靖王刘胜的纪年。与此款式相类似的,如山东沂南阳都故城遗址出土有“廿四年,莒伤(阳)丞寺,库齐,佐平,聝”铭文的铜斧②赵文俊《山东沂南阳都故城出土秦代铜斧》(《文物》1998年第12期,第12页。)定为秦代铜斧,“廿四年”为秦始皇二十四年。,“廿四年”,当是指城阳王刘喜在位的二十四年(前153年)或刘延在位的二十四年(前120年)③裘锡圭认为秦始皇二十四年时,秦的势力也许还到不了这一带。西汉诸侯王及列侯在本国都有自己的纪年。汉初的齐王没有到二十四年的,铭文应当是西汉前期城阳王的纪年。此器仍当为汉物而非秦物。实际上,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才灭齐国,怎会在二十四年就有此铭文的铜斧,裘先生的看法可信。参见裘锡圭《沂南阳都故城铜斧应为西汉遗物》,载《文物》1999年第5期,第54页。。又如河北鹿泉高庄汉墓出土朱雀钮盖鼎上有“廿九年效见,卅年五”的铭文,执炉B型口沿外壁上有“廿九年效见”的铭文。[31]33,37“廿九年”“卅年”,当指常山王刘舜在位的第二十九年(前117年)与第三十年(前116年)。再如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江都易王刘非墓出土的有“十七年二月”“廿二年南工官”铭文的漆盘,有“廿一年南工官造容三升”铭文的漆器,有“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延年大奴固造”铭文的耳杯近百件。[32]亦有北京大葆台汉墓漆盒残底上针刻“宜官 廿四年五月丙辰丞告”的铭文[33]54-55,95-96,“廿四年”当指燕王刘旦在位的第二十四年(前94年)。还有湖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中有“五年七月癸卯朔癸巳,令史援劾敢言之”[34]271,“五年九月丙辰朔壬申,都乡胜敢言之”[34]273,“五年九月丙辰朔丁丑,仓啬夫膚行都乡事敢言之”[34]274。这些简牍都是长沙戴王刘庸在位第五年的记录。这些简牍加上上述所列举的广陵厉王刘胥在位的纪年简牍等,虽然未明确标注诸侯国国号、诸侯王职官等因素,甚至只有纪年等文字,与传世文献、墓葬、地域等结合在一起,但还是可以判断出其所属诸侯王国具体纪年年代的。
上述两种西汉诸侯王纪年款式,既沿袭了春秋战国时代诸国纪年款式的模式,又是汉高祖、汉惠帝、吕太后、汉文帝等在世时所使用的纪年款式,也是诸侯王同于京师的标志。有纪年而未冠以国号,与群臣上醻刻石的款式不完全相同,但丰富了西汉诸侯王纪年款式类型的多样性,有助于深化对于西汉诸侯王纪年的认识。还有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和盱眙县大云山江都易王刘非墓出土器物上的纪年铭文,涉及到了上述两种纪年款式,也就是西汉诸侯王纪年的款式并非是单一模式的体现,丰富了刘位坦主张的内容。
三是与群臣上醻刻石相同均以国号居首的资料。
汉高祖刘邦分封兄弟子侄为王,在疆域上,“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①《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华书局2013年版版,第802页)《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作:“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枉过其正矣。”(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4页。)涵义相同。。并规定诸侯王,在称谓上,后妃、太子、公主、诏令、车舆等名称“拟于天子”②《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第2 104页,参见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 076页。;在官制上,行政机构、职官名称、官吏职权、俸禄等级等与汉朝朝廷“等齐”;在财政上,有独立有自主的财政支配权;还有自己的军队系统等,形成了汉初诸侯王与皇帝“共天下”的格局,[35]群臣上醻刻石就是此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无独有偶,不仅有与群臣上醻刻石款式相同、相异的诸侯王纪年方面的资料,还有诸侯国与群臣上醻刻石相同均以国号居首的资料。
其一是赵国以国号居首的资料。
碑刻,如“赵国易阳南界”石刻[36],与“戍卒赵国易阳侯里李登高”[37]68简,地名先后顺序相同。东汉残碑上的“赵相魏□”[38]等,两者都是以赵国号居首。
铜器,陕西武功县普集镇北显村出土的有“赵内者,容二升,重二斤二两。第八”[39]701铭文的铜豆器,赵内者,指赵国的内者官,证明诸侯国官职与汉朝廷相同。
简牍,如肩水金关汉简有“田卒赵国襄国长宿里庞寅年廿六”“田卒赵国尉文翟里韩□”[40]2-3“戍卒赵国易阳南实里王遂”[37]123“戍卒赵国邯郸平阿里吴世”[41]10“5戍卒赵国柏人广乐里公乘耿迎年卌五”[41]21等,这些戍卒、田卒的籍贯也是以赵国国号居首。
从以国号居首的角度来看,上述资料都是把赵国排列在有关事项的前面,在这一点上与群臣上醻刻石款式有相同之处,也就是说并非只有纪年赵国居首,其他领域中也照样存在,群臣上醻刻石只是这诸多存在中的一个。
其二是两汉其他诸侯国以国号居首的资料。这方面载体种类齐全,涉及领域广泛,按载体类别举例于下。
铜器,如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墓出土的有“齐大官畜粲人“”齐食大官北宫十“”齐食官上米“”齐大官右般“”齐大官右般北粲人”[42]铭文的铜鼎、铜钫、铜罍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清河第三鼎,容三斗,并重卅斤五两”[42]铭文的铜鼎。保利博物馆藏有“昌邑食官鼎容二斗,第五”[9]287,290铭文的铜鼎。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有“昌邑籍田”[25]58-59铭文的铜鼎。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出土有“广陵服食官钉第十”[43]铭文的铜鼎等。陕西西安北郊大明宫乡刘北村汉墓出土有“河间邸”“河间食官”铭文[44]的铜鼎、铜锺、铜扁壶等。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新城乡高庄村汉墓出土有“常山食官钟,容十斗,重□钧□斤”③《高庄汉墓》(第33、34页)。郑绍宗《河北行唐发现的两件汉代容器》亦载:“常山食官锺,容十斗,重一钧十八斤。”(《文物》1976年第12期。)两者形制相同、容量相同,有可能都是常山国铸造的容量标准器。铭文的铜锺、有“常食中般”[31]37-38铭文的铜执炉等,“常食”当是“常山食官”的简称。山西太原东太堡出土有“代食官糟锺,容十斗,第十”“清河大后中府锺,容五斗,重十七斤,第六”[45]铭文的铜锺等。江苏徐州铜山龟山一号西汉崖洞墓出土有“楚私官,重一斤一两十八朱,第二”[46]铭文的铜量。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出土了刻有“江都宦者,容一升,重三斤”[30]铭文的铜行灯。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汉墓出土有“菑川西宫中官”[47]铭文的铜盆等。咸阳博物馆藏有“汉与鲁王为虎符”“鲁左五”[48]铭文的鲁王虎符等。上述这些不同类型的铜器铭文,涉及到齐国、清河、昌邑、广陵、河间、常山、代国、楚国、江都、菑川、鲁国等11个诸侯国,都是以诸侯国号居首,标明了铜器的所有者,证明了诸侯国的职官制度,证明了诸侯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不是虚言,而是真实的存在等,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印章封泥,如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出土了有“广陵王玺”[49]铭文的金印,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了有“中山御丞”“中山祠祀”字样的封泥等[28]214-215,335,河南商丘市永城县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出土了有“梁后园”铭文的印章[50]65等,湖南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出土了有“长沙丞相”铭文的铜印[51]24等,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了有“楚御府印”“楚武库印”“楚宫司丞”等字样的印章[52]114-115,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出土了有“楚太仓印”“楚司马印”“楚都尉印”等字样的印章[53],安徽天长三角圩一号汉墓出土了有“广陵宦谒”铭文的印章[54]等,山东临淄新出土了有“齐内官丞”“齐都水丞”“齐铁官印”“齐太仓印”“齐乐府印”[55]52-57等字样的封泥,传世有“淮南邸”[56]991-992封泥等。据不完全统计,传世与出土的国号居首的职官印章封泥涉及到齐、楚、赵、梁、代、鲁、泗水、广陵、六安、定陶、北海、中山、菑川、长沙、河间、城阳、东平、衡山、真定、广川、广阳、胶东、淮阳、淮南20余个诸侯王国。不仅同姓诸侯国官印上首刻国号,而且异姓诸侯王也是如此,如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了“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吕大行印”[57]等封泥,属于吕太后所封的吕氏诸侯王国,也是以国号居首,证明了汉代诸侯国的官制,体现了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的时代特色。
简牍,这些年发现的较多,如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中,有“鲁御史”“鲁中大夫谒者”“鲁郎中”[58]87-88,是以国号冠于诸侯国官职名称前面,以便与汉朝朝廷官员区别开来。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简中登记戍边戍卒、田卒等的籍簿中,如“戍卒梁国睢阳东方里上造赵害,年廿四”[37]156,“田卒粱国睢阳汴阳里牛充”[37]41,“戍卒淮阳国陈莫大宰里陈山,年卅一”[59]72,“鲁国大里大夫王辅,年卌五岁,长七尺五寸,黑色”[59]70,“田卒平干国广平泽里簪褭李田利里年廿六”[40]5等,数量众多,不胜枚举。上述肩水金关汉简登记的诸侯国戍卒、田卒等籍贯、年龄等,都是以诸侯国号居首,不仅证明了诸侯国人也有戍守边境的任务,也证明了诸侯国号就是他们的身份标签。
瓦当,如河北石家庄市元氏常山故城出土有“常山长贵”“常山长昌”[60]字样的瓦当,并且“常山长贵”瓦当不止一种类型,文字排列位置不同,读法不同[61]。常山当指常山王国而言。传世的“真定长乐”瓦当,真定当指真定国。三者都是寓意美好追求的吉祥语。关中出土有“淮南”[56]232-233字样的半瓦当,有“□□王当”字样的残瓦,当为“淮南王当”四字[56]936,当指淮南王所言;有“梁宫”[56]921字样的瓦当,当是指梁孝王长安邸遗物。三者当都是诸侯王在长安建立的国邸建筑的瓦当。上述六种瓦当均是以诸侯国号居首,体现着汉代诸侯王与皇帝共天下的特色。
漆器方面,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出土有朱书“长沙王后家杯”[26]字样的漆耳杯,与此相似的有“杨主家般 今长沙王后家般”铭文的漆盘,在湖南长沙城东五里牌杨家山汉墓发现过[62],既证明了墓主人身份及墓葬等级,也表明款式是以诸侯国号居首。
上述两种类型,体现着以诸侯国号居首纪事方式的广泛性,“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与上述器物铭文有相同之处,也由此而体现出群臣上醻刻石款式的时代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西汉大一统国家与诸侯王制度带来的。在战国时代,“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63]757-758。各国不同的职官制度和各具特色的名称就已经显示出特殊性来了,因此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国号居首的词语来区别。汉承秦制,国家一统,皇帝与诸侯王有着许多相同的职官设置,有着诸如太后、太子、公主等相同的人际称谓,也就需要有区别其存在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采用以国号居首的办法,既区别了朝廷与诸侯国的不同,又区分了各诸侯国之间的不同,也区别了诸侯国与汉郡的不同,还区别了诸侯国官职、地名的不同等,因此,也就出现了两汉时代呈现的国号居首的特色。从这个角度看,“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的国号居首款式体现出汉代的特色。
上述所列举的新资料,类型齐全,涉及领域广泛,均是以50年来为限,如果扩大时间断限,将会有更多的新资料发现。其中有些是前辈学者所未曾看到、也未曾运用过的新资料,扩展了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研究的资料范围,增加了其类型与数量,丰富了其内容,具有“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64]619的作用,新材料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将会促进深化与细化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的研究。与群臣上醻刻石款式相同者,证实了其可靠性,相异者丰富了其内容,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从总体上支持、印证了刘位坦主张的正确性,完善了刘位坦的主张,进一步证明了群臣上醻刻石所体现的西汉初年的时代特色。
刘位坦提出的群臣上醻刻石年代为赵王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的主张,至今已经历时150余年,虽然期间又提出了四种其他看法,但刘位坦的主张,不断地被赵之谦、俞樾、陆增祥、徐森玉等人所认同,并加以补充与发挥,日趋完善,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成为主流性的看法,显示出其蓬勃旺盛的学术生机。同时,不断发现的汉代简牍、碑刻、瓦当、铜器铭文、封泥印章等新资料,不仅为证实刘位坦主张提供了新证据,扩展了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研究的资料范围,而且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为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研究的与时俱进、深化与细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笔者根据新发现的资料,综述刘位坦主张的内容,介绍赵之谦等前辈学者的新资料与看法,提供新资料的线索,期望抛砖以引玉,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推动群臣上醻刻石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
[1]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2]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J].文献,1981,(2):18-25.
[3]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4]翁方纲.两汉金石记[M]//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冀介良,许姗,王站琴,等.山东日照海曲西汉墓(M106)发掘简报[J].文物,2010,(1):4-25.
[8]秦进才,李艳舒.海曲汉简“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简探微[J].四川文物,2016,(6):53-58.
[9]保利艺术博物馆.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G].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
[10]赵化成,高崇文.秦汉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11]刘珍,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袁宏.后汉纪[M]//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
[1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4]秦进才.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 [J].文物春秋,2008,(1):44-53.
[15]赵之谦.二金蜨堂双钩汉刻十种·赵廿二年上寿刻石[J].书苑,1943,(7-3).
[16]杨铎.函青阁金石记[M]//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六册[G].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17]孙继民,都良真,张士忠.河北永年朱山唐代石刻考察记[J].文物春秋,2003,(6):48-52.
[18]俞樾.春在堂随笔[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9]俞樾.春在堂尺牍三[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四一四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20]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M]//续修四库全书:第八九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1]徐森玉.徐森玉文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22]张德容.二铭艸堂金石聚[G]//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三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23]丁绍基.求是斋碑跋[G]//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十九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24]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2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26]何旭红,黄朴华,马代忠,等.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7,(12):21-41.
[27]山东省曲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曲阜市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3.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9]迟延璋,曹元启,李学训.山东昌乐县东圈汉墓[J].考古,1993,(6):505-513.
[30]李则斌,陈刚,盛之翰.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J].考古学报,2012,(7):53-59.
[3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高庄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2]李则斌,陈刚,余伟.揭开江都王陵——盱眙大云山汉墓发掘纪实[J].中国文化遗产,2012,(1):76-83.
[33]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4]郑曙斌,张春龙,宋少华,等.湖南出土简牍选编[G].长沙:岳麓书社,2013.
[35]秦进才.汉初与皇帝“共天下”的诸侯王 [J].历史教学,2004,(4):66-70.
[36]孙继民,郝良真,马小青.“赵国易阳南界”石刻的年代及价值[J].中国历史文物,2004,(1):69-76.
[37]甘肃简牍博物馆等.肩水金关汉简(贰):下册[M].上海:中西书局,2012.
[38]郝良真.邯郸新见东汉建宁二年残碑考释[J].邯郸学院学报,2015,(3):21-24.
[39]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40]甘肃简牍博物馆.肩水金关汉简(壹):下册[M].上海:中西书局,2011.
[41]甘肃简牍博物馆.肩水金关汉简(肆):下册[M].上海:中西书局,2015.
[42]韩建武.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几件汉代刻铭铜器考释[J].考古与文物,2014,(4):63-67.
[43]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 [J].文物,1991,(10):39-61.
[44]王长启,孔浩群.西安北郊发现汉代墓葬[J].考古与文物,1987,(4):39-42.
[45]山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员会.太原东太堡出土的汉代铜器[J].文物,1962,(4、5):66-72.
[46]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J].文物,1973,(4):21-22.
[47]曹元启,王学良.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汉墓[J].文物,1987,(9):76-83.
[48]刘晓华,李晶寰.鲁王虎符与齐郡太守虎符小考[J].文物,2002,(4):81-82.
[49]纪仲庆.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J].文物,1981,(11):1-11.
[50]阎根齐.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51]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52]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53]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J].考古,1998,(8):1-20.
[5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长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J].文物,1993,(9):1-31.
[55]刘创新.临淄新出土汉封泥集[M].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05.
[56]陈直.关中秦汉陶录·慕庐藏瓦·汉淮南邸印章门观监两泥封[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7]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J].考古,2004,(8):3-16.
[58]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59]甘肃简牍博物馆.肩水金关汉简(叁):下册[M].上海:中西书局,2013.
[60]胡海帆.河北民间藏汉代“常山长贵”、“常山长昌”瓦当[J].文物春秋,2012,(4):71-72.
[61]杨双秋,王巧莲,杜平.河北汉常山郡故城址出土建筑材料[J].考古与文物,2001,(6):92-93.
[62]考古研究所湖南调查发掘团.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J].科学通报,1952,(7):493-497.
[63]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4]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A New Proof for the Inscription Requited by Officials about the 22th Year of Prince Liu Sui
QIN Jin-cai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24,China)
Since the discovery ofthe inscription requited by officials in the Daogua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the dating has become a research focus.There are chiefly six kinds of views in which Liu Weitan's proposition,that is,22th year of Prince Liu Sui and the sixth year of Emperor Liu Heng,is almost approved.Liu Weitan'spostscript testifies the origin of his proposition.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atements from Zhao Zhiqian,Yu Yue,Lu Zengxiang,XuSenyu and others can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Liu Weitan's proposition.And the new data from the bamboo scripts,inscriptions,bronze brass and lute seals relating to the inscription requited by officials in the past 50 years can enrich the data scope and supplement new proof to observe the reliability of Liu Weitan's proposition.
the dating of the inscription requited by officials;Liu Weitan's proposition;the 22th year of Prince Liu Sui;the sixth year of Emperor Liu Heng;new proof
K207
A
1673-1972(2017)05-0052-13
2017-09-02
秦进才(1953-),男,河北衡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秦汉史与历史文献研究。
(责任编辑 程铁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