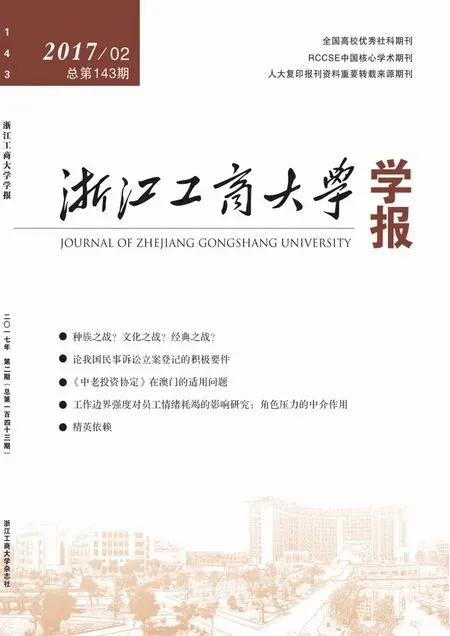论屈原心理情结和诗歌创作的美学关联
刘 奕,颜翔林
(1.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江苏警官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31;3.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15)
论屈原心理情结和诗歌创作的美学关联
刘 奕1,2,颜翔林3
(1.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江苏警官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31;3.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15)
主体的心理情结和文学创造存在着潜在的美学关联。屈原的心理情结主要构成因素是孤独情结、恋美情结、痴狂情结和死亡情结,它们之间存在着时间性的历史关联和逻辑递进,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诗人的审美意识形态和诗歌创造活动。换言之,楚辞文本即是诗人的心理情结和审美创造的互动性显现。
情结;孤独;恋美;痴狂;死亡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称赞屈原“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楚辞》文本所寄寓的诗性情怀、审美理想和伦理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链条的延伸和全体成员的审美精神,引导着后代对人生与艺术的审美判断和创造欣赏。《楚辞》既是古老东方诗国的第一株浓荫常绿的神话树,也是华夏民族“共时性”(synchronical)的审美崇拜的艺术丰碑。
1898年,德国学者西奥多·齐亨创立了“情结”(complex)一语。荣格较早运用这一话语并赋予丰厚的理论内涵,提升为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荣格看来,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念形成的心理结丛即是“情结”,它是个体无意识的重要的和有趣的特征之一。荣格认为,情结“并不一定成为人的调节机制中的障碍。事实恰恰相反,它们可能而且往往就是灵感和动力的源泉,……例如一个沉迷于美的艺术家就不会仅仅满足于创作出一部杰作。他会执著于创造某种最高的美,因而不断地提高其技巧,加深其意识,并从而创作出大量的作品来”[1]。他又认为,对美的追求必须归因于强有力的情结,而微弱的情结则会限制一个人,使其只能创作出平庸低劣的作品,甚至无法创作出作品。“情结”可能具有非正常的略有变态的心理性质,但对艺术创造却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对屈原心理情结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审美分析,进而阐释这些“情结”的文化学、心理学、美学意义并揭示它与楚辞文本创作的潜在关联。
一、 “独穷困乎此时”:孤独情结
史上诸多艺术家呈现出明显的孤独情结,孤独成为附依在他们内部的一种特殊心理簇丛。尤其是那些追求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艺术创作主体,更容易滋生孤独的心理情结。孤独情结对人生而言可能具有悲观和消极的作用,却有助于主体达到虚静空寂的审美境界,从而获得审美与艺术的自由领悟和灵感发现。从《楚辞》来看,屈原具有强烈的孤独情结,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诗人借助创作活动来宣泄被压抑的心理,又有助于激发诗人强烈和奇异的想象力,并使其进行深刻的精神反思和审美创造。
屈原常在文本中表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我灵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孤独者形象。一方面,诗人的孤独情结受到群体无意识影响:楚国自古是独立而相对封闭的区域,中原诸国对这个远离文化中心的荒蛮之地怀有先天的冷漠与敌视,这使楚民族成为一个孤独的族群。另一方面,屈原的孤独情结更多地来源于个体后天经验,主要源于政治与情爱的失意这两个因素。
1. 政见孤独。屈原的政治理念主要包括“民本思想、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等内容,然而,君王沉湎于集权和享乐而不思进取,奸佞弄权,结党营私,楚国的政治生态严峻。诗人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又招致君王疏远和群臣排斥,最终被放逐于偏远的沅湘之间。“忳郁邑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离骚》)作为一位贵族官员,政治生活给予屈原孤独无助的体验。屈原与楚王、群臣的政见不合而滋生强烈的孤独意识,在偏僻的沅湘,诗人思念故土而不得归返,使孤独情结达到极致。政治生活给屈原带来的孤独,可包括政见孤独、怀乡孤独和节操孤独等内容。《离骚》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政见孤独:“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九章》可能是屈原再次被放逐时的系列作品,有的距离自沉时间不远,它的政见孤独情结显露得更为鲜明:“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行不群以巅越兮,又众兆之所咍。”(《惜诵》)“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哀郢》)“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屈原是一位爱国思乡之人,在独自流放之中又听闻国破家亡的噩耗,怀乡之孤独可谓痛断愁肠:“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涉江》)“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静幽默。”(《怀沙》)“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哀郢》)诗人的孤独境遇,一方面是社会的外在逼迫,另一方面是自我的内在选择:“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为了保持美好的节操,诗人宁可选择孤独:“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卜居》)心灵的忧郁以及廉贞的德行无人能够理解,只有孤独地守望着精神家园,借助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去排遣内心的痛苦:“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显然,有关政见的孤独情结交织于屈原的主体,它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人生与创作。
2. 情爱孤独。屈原的孤独情结亦起源于情爱失意、欲望被压抑而产生的痛苦。如果说《离骚》和《九章》主要显现了屈原政见上的孤独,那么,《九歌》则更多显现了屈原情爱上的孤独。屈原是个生性浪漫、情感灼热的诗人。他诗意而浪漫地对神话中的女神产生了爱情冲动,她们是诗人潜意识中所寄寓的生命本能的原欲对象和审美幻象。
《九歌》之中,《云中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以及《礼魂》所祭祀、歌咏的神灵,其外在形象属于女性,诗人对她们的迷恋不排除本能的因素,但更多纯粹的审美崇拜。尽管屈原对美女的迷恋或许残留着“里比多”的原欲冲动,但已超越了“本我”制约而升华到宗教信仰和审美超越的境界。如诗人对云中君的爱慕之情寄寓在对女神朦胧飘舞的描摹之中:“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篇末表露了惆怅失意、无缘相聚的哀婉之情。《湘夫人》借助景物的象征,暗示了爱情的不完满结局:“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之潺湲。”哀伤的情调注定这必然属于一场空幻的单相思,因为人神之恋注定不会有花好月圆的结果。《少司命》勾画出司职子嗣的女神,诗人在“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的时刻,产生极其快乐的幸福感。“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这时诗人沉湎在短暂的爱情体验中,但笔锋一转,又叹息“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让人疑心所写的一切均不过是审美幻觉而已。对《山鬼》中的山野女神,诗人的倾慕虽然并未直接表白,但凭借诗歌意象的暗示溢于言表,可惜最终的结果仍令人叹息:“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湘君》和《河伯》所写的也是离别的忧思和情爱无果的感慨:“采薜荔兮水中,褰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邻邻兮媵予。”诗人借此表达出情场失意的孤独意识。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往往“抛弃了与真实事物的联系;他现在用幻想来代替游戏(spiel)。他在空中建筑城堡,创造出叫作白日梦的东西来”[2]。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被压抑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心理产生白日梦的幻觉,而这种幻觉包括一定的爱欲成分。
依此,我们发现《楚辞》中许多作品属于生命本能被压抑所产生的白日梦,体现了性爱欲望与艺术活动的潜在联系。《九歌》中诗人对女神的爱恋,完全是精神性的幻觉活动,虚无而飘渺,可望而不可即,无法获得实体性的接触。所谓“女神”,只不过是一种直觉化的心理意象。她们与《浮士德》中的“海伦”属于同性质的存在,是爱与美之理想的虚无象征。因此,诗人处于孤独无助又无法逃脱的爱情陷阱之中。
纵观楚辞文本,诗人的所有爱恋均是徒劳无果的梦幻,孤独始终缠绕着他的心灵。然而,情爱所带来的孤独情结,直接派生了诗人从事艺术创造的精神势能。这也契合了精神分析理论的“转移”和“升华”的概念:情爱绝望导致诗人将负面的心理张力“转移”到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中,“升华”为一种比较崇高的精神活动。诚如乌纳穆诺所言:“爱本身就是深入到精神中的某些肉欲。由于爱,我们才得以感觉:凡是精神的必有属于它的实质的肉欲成分。性爱,它是其他所有形式爱的创生典范。在爱中,而且透过爱,我们寻求自身的永存之道”[3]。从《九歌》文本中,我们隐约感觉到诗人对爱情的渴慕和追求中不乏原欲的成分,但诗人超越本能的欲望寻求“自身的永存之道”,这就是诗意和审美的生活,它包括对崇高人格的求证,也包含着诗人对治国安民的执著追逐。
处于孤独状态的诗人主体,凝神观瞻万物,运思人生哲理,进入逍遥以游的审美境界,想像力和创造力获得高度的提升,从而将包括孤独在内的诸种审美意象表现于诗歌文本,构筑了华夏诗歌史上一道奇瑰浪漫的景观。
二、 “求宓妃之所在”:恋美情结
屈原的恋美情结由孤独情结演生,而爱恋的失败又反作用于之,将诗人进一步推入孤独的深渊。屈原对美富有超常的敏感,审美体验与审美直觉的能力亦非常人能及。诗人迷恋一切美之存在:从大地之美到天宇之美,从物质性之美到精神性之美,甚至心灵中虚拟的美之意象,诗人都痴狂地爱慕。无疑,屈原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对美产生强烈迷狂情结的诗人。屈原的恋美情结,可分为“自恋”与“他恋”两方面。
1. 自恋。屈原有一定程度的“自恋”倾向,它并非变态,而不过是诗人自我尊重、强烈自信的超常表现而已。屈原对自我形象是极为珍惜的,它又可以分为“外美”与“内修”:
诗人尤其注重仪表的风度气韵,对自己的衣著装束尤为注重,甚至到了刻意修饰、追求奇装异服的地步: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离骚》)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涉江》)
屈原心仪外表的卓异打扮,一则为其自恋情结因现实挫折而向外转移的某种结果,二则也是为了标举与众不同,显示自我独特的审美观念。从“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的视野上看:“身体化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特征,身体意识也是如此。我所理解的‘身体意识’不仅是心灵对于作为对象的身体的意识,而且也包括‘身体化的意识’;活生生的身体直接与世界接触、在世界之内体验它。通过这种意识,身体能够将它自身同时体验为主体和客体”[4]。显然,屈原具有这种鲜明而强烈的身体化意识。在《楚辞》的多个文本中摹绘自己身体的诗人,既迷恋自己的身体,也通过其建立对世界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意识。
屈原的自恋情结更深层地指向“内美”。诗人注重内在品性的提升,致力达到内外齐修、两美合一的境界。屈原的“内美”主要呈现在:第一,先天的高贵。屈原在《离骚》的开端就表明自己生辰的特殊和出身的高贵,他坚信着受命于天的神话。此外诗人有不同凡响、具有高度审美观念和伦理精神的命名。这一切无疑令其产生自我爱恋的情结。第二,后天的修养。它更为屈原自我推崇。首先是忠君之德。《离骚》主题之一即是忠君意识,诗人对君主几乎到了宗教虔诚的境地,即使是“灵修数化”“哲王不寤”,他也不忍指责和背弃,甚至为其“殉情”自杀。《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悲回风》中,屈原均表现出强烈持久的忠贞君王的意志和行为。其次是爱民之心。屈原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真切、灼热地同情民众苦难。如《离骚》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此外,《少司命》《抽思》《天问》里,均可发现屈原对民众的深挚之爱。再次是爱国之情。《离骚》凝聚着诗人对故土、故国的深切眷恋。诗人云游天地四方,“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而《哀郢》作为一篇诔文,倾诉着国破家亡、迫离故土给诗人带来的巨大痛苦。在《惜往日》里,屈原回忆“国富强而法立”的美好时光,对故国充满情愫。而《橘颂》则借橘比德,它成为诗人自我人格的写照,寄托着对故土的热爱。最后是以死殉节。屈原效法古代贤哲,最终以死达到“内修”的极致。这显示了屈原继承儒家精神,实现了伦理学和美学合流的完美人格。诚如所论:“屈原关于君子人格美修养的思想在后世的影响不弱于孔子”[5]。尼采推崇“超人”具有的高尚品格:“他把自己的道德变为自己的偏爱和自己的宿命:因此他甘愿为自己的道德生存或死灭”[6]。显然,屈原具有尼采所心仪的超人的内涵,可说是一个古典主义的“超人”形象,具有道德偶像价值。因此,屈原完全有自恋的理由和权力。
2. 他恋。诗人既执着地迷恋自我,又狂热地迷恋非自我的所有美之存在对象,甚至迷恋非实在的虚拟化对象。由此而导致诗人的性格出现乖戾、怪癖、疯狂的意向。然而,正是如此,主体的审美创造的冲动和意象的营造机能才得以产生,由此建构起一系列奇异瑰丽的艺术图景。屈原的“他恋”有如下方面:
其一,是美人之恋。作为“他恋”对象的“美人”,在不同的《楚辞》语境有不同含义。这个意象,有时可能指君王(怀王或顷襄王),有时也指异性美女:“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离骚》)“与美人之抽怨兮,半日夜而正。……结微情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抽思》)“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思美人》)屈原对君王的恋美主要导源于君主崇拜意识,其实,无论是怀王还是襄王,可能内外两方面都不符合“美”之标准。屈原将他们升格为“美人”,实属为专制政治下文化心理的折射。诗人对美女的迷恋也投入了同等热情。《思美人》一诗,其“美人”的符号能指是双重的:既指君王,又指美女。它一方面寄托了政治愿望,另一方面寄托了审美愿望和爱情愿望。而在《招魂》中,诗人对美女的迷恋则更为显明和富有冲动色彩,这里的“美女”完全与君王无涉,全然为世俗生活中的异性:“肴羞未通,女乐罗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
诗人对美女的欣赏还扩展到历史传说人物。这些人物,有的可能是信史,有的可能是传说中的虚构性存在。如《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诗人对历史上的这些美女怀有强烈的审美幻觉,尽管她们有些也不一定符合屈原的审美理想,但诗人却是借此来达到对现实界对象的审美否定,以实现对世俗情爱的超越。美人之恋还包括美神之恋。前文提到屈原对《九歌》女神们的情爱追求,这源于女神们的内外之美。《九歌》以诡异浓烈的色调,描摹了沅湘民间的女神及扮神的女巫。在诗人的笔触下,她们外形显得香艳灵秀,娉婷袅娜,内心呈现媚态缠绵、柔婉真淳的风致。那种忧郁、孤独、空灵、虚无、怪诞、朦胧、迷幻、灼热、清莹、浓烈的美之神韵令人回味久长。而这一切,均深挚地寄寓了诗人对美神的爱恋——正是这种强烈的爱的势能和冲动,才使屈原写出了千古不朽的瑰奇诗章。
其二,是美物之恋。王逸、刘勰均注意到《楚辞》和自然界对象的密切关系。的确,屈原的恋美情结,还含有对“美物”的爱恋。南国楚地的自然物本来丰富,在自然宗教意识的作用下,屈原对自然的审美冲动极度扩张。诗人将自然之物领悟成为具有生命的对象,甚至将之作为宗教化的图腾对象来对待。他迷恋山水草木、飞禽走兽、云霓飘风、日月雷电……这些自然物象被广泛描绘,赋予神话思维的色彩,借助于文学修辞方法,使之生成为充盈美感和灵性的诗歌意象。又多赋予了象征、移情、比兴、隐喻等艺术技巧,从而升格为具有丰富意蕴的审美符号。诗人还将自然附加以人格内容和伦理概念,这也反映了先秦时代“比德”的美学观念对诗人的潜在影响。
《楚辞》写到多种植物,如有:江离、薜芷、秋兰、木兰、申椒、菌桂、蕙茝、留荑、揭车、杜衡、芳芷、秋菊、胡绳、芙蓉、幽兰、琼枝、荣华、杜若、芳椒、石兰、疏麻、瑶华、女罗、辛夷、幽篁、三秀、松柏、橘树……屈原并未遵守现实逻辑,而采用了神话思维的方式对其加以表现。春兰和秋菊共时,冰雪与芙蓉同舞:时间的顺序被审美需要所切割,季节的更替被艺术目的所征服。《楚辞》还表现动物之美。它描绘的动物十分丰富,其中很多现在已经灭绝,有些则属珍稀物种,还有一部分是现实界根本不存在的虚构形象,寄托着诗人的信仰、崇拜和审美理想,如:虬龙、凤凰、玉鸾、青虬、蛟龙、文鱼、夔等。《楚辞》喜爱表现楚国风物。诗人在屡遭放逐的情形下,由于时空的阻隔,更为眷恋楚地的自然景观,这是诗人灵魂和生命的最终寄托。《招魂》一诗夸张地渲染了其他国家的严酷与恐怖,而将楚国描写成为富饶美丽、宁静安详的乐土。《离骚》《九章》《九歌》诸篇,也广泛抒写了楚国山水景色的秀美,倾注了对故土的无比深情。《楚辞》还表现出对日月星辰、云霓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审美意识,显示了超常的审美感受能力,它也有助于释放审美创造的能力。
其三,是美政之恋。和前两者不同,屈原的“美政之恋”属于抽象的观念,缺乏感性的外在形式特征。但是,它却代表了诗人最高的利益追求和价值核心。因为,他对楚国的爱恋、对民生的忧思,都集聚在对“美政”的渴望和期待之上。在先秦时代,“美”与“善”的概念往往互相融合。作为一位诗人政治家,屈原把政治与审美联系起来,从而把“美政”当作人生最高的生存目的和价值尺度。屈原的“美政”内涵包括:民本意识、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国富平乐。在《离骚》《哀郢》《抽思》《怀沙》《惜往日》《九章》等诗篇中,均可看出屈原对“美政”的殷殷向往之情。兹不细述。
总之,“自恋”和“他恋”这两个心理层面相互联系,有机地构成了屈原的恋美情结。屈原则将对美的爱推向极致,甚至达到超越理性的地步。这种心理情结促使他在艺术构思、艺术写作的状态,滋生出审美体验的神秘感悟和超人的想象灵性。它最终演进为一种美学精神,并转化为一种影响深远的“骚体”美学思想。
三、 “迷不知吾所如”:痴狂情结
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等人早已发现疯狂、迷狂对于创作的作用。屈原由于孤独情结的作用,自然滋生“迷狂”的心理。意大利精神病学家隆布罗索坚信天才与精神病的相关性,“试图证明许多天才患有神经病、神经官能症或者发育充分的精神病”[7]。据他认为,许多大艺术家都有精神病症状。美国现代心理学家阿瑞提也认为痴狂心理、精神病与创作力有潜在的联系,可能刺激心理机能的创造活动。因此,我们认为屈原也有轻度精神病态,尤其在放逐后和自沉前比较明显。
一方面,楚民族是一个充满神话思维和诗意情怀的文化集体,所谓浪漫楚风,狂放骚人,隐士众多。另一方面,从个体而言,由于孤独情结的主导性作用,屈原的心理平衡渐趋失调而产生了痴狂的迹象,这种心理有效地拉开了主体和日常生活的距离,使其进入一种“迷不知吾所如”(《涉江》)般如痴如醉的诗意与审美的境域。
1. 前期痴狂。诗人前期的痴狂情结较为轻微,此时死亡的黑色魔影尚未呈现,痴狂情结偏重于艺术化的存在,这使其诗歌(如《九歌》《九章·橘颂》《天问》《招魂》等)空灵幽远,意在言外。创作主体进入神话思维和自然宗教的神秘体验状态,在想象力的作用下,主体幻想与万象融合,主体从自然获取灵性和美,而自然物也被赋予了主体的美感与诗性。诗人恋花恋草,奇装异服,性情古怪。但是,文本中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主题还趋向积极健康。诗歌里对生命、美、情爱的眷注之意向十分明显,对国家政治的权力争夺还抱有希望。因此,诗人对生命还不愿捐弃。
《九歌》有学者认为是屈原被放逐后所做。通观其十一篇,诗人处于“焦虑”状态,精神有所失衡,乃至变态。但痴狂情结强化了神话意识,万物有灵观被进一步激发。从比较神话学来看,希腊神话中人与神的界线相对明显,而《楚辞·九歌》,人与神没有严格的逻辑区分,人神相恋,精神与身体可以贯通,亲密无间。在诗歌境界,人与神、人与自然万象自由交往,相遇相亲,心会神往。例如“东皇太一”,在诗人的审美体验中,假定为整个世界的本体结构,属于绝对精神的象征品,也是心灵对象的最高存在,被放置在祭祀之首,地位至尊。《九歌》三个唯美的女神形象,少司命、云中君和山鬼,诗人对她们有着痴狂的迷恋,达到审美崇拜的境界。诗人对她们的崇拜和沉迷,实乃一种因现实缺失而产生的一种幻想。在神话思维和诗意思维的共同作用之下,时空被超越,春兰秋菊同时开放,鲜花于冰中娇艳含香。《九歌》隐匿着浓厚的女神崇拜意识,在这种意识中,花草与女神同体,女神是花草灵魂的升华,她们之间有着神秘的生命轮回。
《九歌》之外,《九章·橘颂》里的比德与体物言志,和后世的咏物之辞有所不同。后者清醒地意识到自我是在进行比喻、象征的艺术活动,而屈原在写作过程中处于痴狂状态,他真切相信物象具有人格和灵性,与人同一,渗入了人的生命与情感,并自认为并非在写作,而是在和自然物象进行心灵的对话。《招魂》是屈原初次流放后的痴狂产品。屈原被放逐到荒蛮之地,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物质条件的艰辛又损伤他的肉体,“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疾病附身,因此诗人怀疑自我的灵魂逸出到一个恐怖的遥远世界,所以他期盼灵魂回归故土。诗人描写了一些狰狞的神话意象,如天象、气候的严酷,妖魔、猛兽的可怕,意在竭力要将自己迷失的灵魂从这个死亡空间拯救出来,回归故土。他以铺陈的手法展现故土的博大华丽,场面气势恢宏,又不乏绚烂柔婉,无不竭尽繁华奢侈、浓墨重彩,精思妙想之能事。然而,此种“竽瑟狂会”的描摹多为虚构,是诗人的迷狂幻觉为痴狂情结打通宣泄路径。
《天问》表面上荒诞无稽,然而却充满怀疑论的思想色彩。它将思辨与想象、逻辑与幻觉完美地结合起来,生成了哲学化的诗。据王逸诠释:“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疲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8]。王逸这种猜想的美学意义在于:它说明了创作主体处在生存环境的强烈刺激下,想象力和领悟力达到极大的扩张和释放,激动情绪使主体展开审美体验和艺术幻觉,以神话意识来反思自我和追寻真理,存疑客观存在和以往历史。于是,这种心理活动就具有怪诞虚幻的性质,审美体验距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正缘于此,才构造出一个有审美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神话世界。
2. 后期痴狂。在被放逐尤其是临近自沉汨罗的时期,屈原滋生明显的死亡动向,痴狂情结则偏重于现实人生。此时他更大程度陷入孤独,而想象力更为活脱、奔放,对于国家、历史、政治、伦理、人生等问题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和领悟,在创作上达到顶峰状态。《离骚》《九章》(除《橘颂》外)《哀郢》《渔父》诸篇便是后期痴狂的产物。
在《离骚》中,诗人称自己是高阳帝的后裔,又逢寅年寅月寅日所生,且“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及写上天入地,各种神灵为自己引路、驾车、侍卫,确有狂人的味道。但诗人最终拒绝了巫师明哲保身的“忠告”,坚持“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这是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精神痴狂。没有痴狂的精神信仰和意志力量,诗人既写不出《离骚》这部传世之作,也无法实现崇高的道德人格。
对《九章》诸篇,刘勰说:“朗丽而哀志。”(《文心雕龙·辨骚》)李贺说:“其意凄怆,其辞瓌瑰,其气激烈。”(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九章》均是在诗人精神痴狂并有所失常的心态中创作的结果。与《九歌》充溢爱与美的柔情幻想相比,死亡意识在《九章》占据了上风。诗人逐渐坚定了以死来殉理想、殉信仰的决心。
概言之,诗人的后期痴狂走向君王崇拜和圣贤信仰,其心灵意识也超越对美与生命的眷恋。他写死亡、鬼魂、幽都、古贤,“魂一夕而九逝”(《哀郢》),感悟到死亡的意义价值及其神秘的美感诱惑,并认为他的“内修”内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获得现实性。于是,他的日常行为的痴狂程度也超过前期。他形容枯槁,颜色憔悴,奇装异服,行吟泽畔,求卜问筮,拒绝“渔父”的劝告。他的最终陨落正是痴狂情结的驱使;然而,也正是痴狂情结,使诗歌的想象力更为奇峭,悲剧气氛更为浓烈,情感更为震撼。
3. 神游。屈原被流放沅湘险境,加之听闻整个楚民族的生存危机,心理上受到极大程度的压抑。他梦见三后、楚国的先王,梦想重建前贤们所创造的理想的生存空间。于是,诗人的痴狂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形式:神游。作为此时唯一救渡自我的方式,幻觉的神游成为《楚辞》一个重要的艺术标志和美学主题。它使诗人的想象力格外地充沛和飞腾。
《离骚》写三次“神游”,境界博大华丽,最为后人称道。它是屈原的生命意识受到压抑后的心理狂想,具有如下特征:超越时空束缚,寻求绝对自由;眷注审美愉悦,具有艺术情怀;守望真理和正义,乃至于达到痴迷完美的地步;以理想破灭,追求失败,走向死亡作为终结。处于迷醉诗的生命体验中的诗人以热情的狂想,进行伟大生命的诗意独游。在痴狂情结的支配下,“神游”天宇与大地,沟通历史与现实,渴慕宓妃佚女,回忆先王贤哲,与巫师鸩鸟对话……其实质,乃是以神话与寓言双重象征的方法,描绘美丽心灵和黑暗现实之间绝望抗争的悲剧。这类同于人本主义心理学马斯洛所言的“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的“时空莫辨”(disorientation in time and space)的心理状态。屈原的“神游”与庄子的“逍遥游”有精神相通之处:他们都追求超越现实的绝对自由和审美化生存方式,力图撇弃思维、真理等被遮蔽的状态,从而获得心智之路的澄明。但由于屈原富有庄子所缺乏的痴狂情结,因此,他比庄子的想象更为奇绝,信仰更为执着。
《天问》《九章》《九歌》《远游》《招魂》诸篇都程度不同地描摹“神游”的内容。此皆为屈原生命受到压抑所采用的逃避方式,均包含着非理性的痴狂心理。这种“神游”的表达手法也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后世的文艺。我国古代文学中后来出现了诸多神游、求仙、幻化的经历,以及桃花源、太虚幻境等审美意象的创造,与屈原的“神游”境界不无潜在的关联。
屈原本着生命自由的目的去神游,结局却以弃生赴死作为归宿。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理解?这是因为,死亡虽是对生命的否定,然而在屈原的意识里:死亡也是对生命的超越,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根本性证明。屈原决心“限之以大故”(《怀沙》),“毕辞而赴渊”(《惜往日》),这是他将死亡当作领悟人生真谛的方式,试图以此走向生命的神秘彼岸。自杀是屈原无可选择的选择,是现实痛苦、理想破灭的最终悲剧性解脱手段。叔本华说:“悲剧,也正是在意志客体化的最高级别上使我们在可怕的规模和明确性中看到意志和它自己的分裂”[9]。屈原的悲剧意识正是自我意志之分裂的表现和结果。
总之,屈原在群体与个体的双重情境下,由孤独感导致心理痴狂。诗人行为怪癖,偏执骚动,甚至思维有所混乱。然而,这直接加强了感性冲动和直觉意识,使诗人进入到神话思维的境界,《楚辞》也由此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魅力。当然必须指出,屈原的理性始终是健全的,他在痴狂的同时,仍坚守着“忠信仁爱”的信念,维护着自我的道德尊严。理性与痴狂这两个矛盾的对立体共存于屈原的心理结构中,不可思议地和谐而不抵触,共同影响着艺术生产。
四、 “从彭咸之所居”:死亡情结
梁启超曾言:“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屈原惟自杀故,越发不死”[10]!的确,《楚辞》内容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死亡的眷注。《离骚》是屈原谈论死亡最多的诗,至少有七处谈到自己的生死问题。《九章》九篇大部分是屈原晚期的作品,无不牵涉到死亡主题:仅从字面上统计,屈原言及自杀有十五次之多,至于谈到古代自杀和被杀的事例则更多。这一特点导源于孤独情结引发的死亡情结。可以说,《九章》是死亡冲动占主导地位时所催生的艺术奇葩,其中,《惜往日》《怀沙》《悲回风》诸篇距离诗人自沉时间不远,可以视为屈原求死冲动的临终之笔。
屈原对于生死的反思是诗意的和神话式的,没有现代的抽象思辨,所以文本没有晦涩的逻辑外壳。但令人惊异的是,诗人几乎类似西方现代哲学家那样将死亡提升到本体论和存在论的地位,并将它与人的本质和价值联系起来,以此说明其审美意义。这使作品呈现出深刻的形而上学因素。
概括而言,《楚辞》中展现了屈原死亡情结的三方面内涵:畏惧死亡、不畏死亡、灵魂不死之信仰。
1. 畏惧死亡。在屈原看来,死亡确实是可怖性的,否则他不至于将此意象作为最终极的痛苦反复歌吟。《九章》中所笼罩着的阴森氛围,便是诗人畏死情绪在文本中的折射。如《涉江》:“露申辛夷,死林薄兮。……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哀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抽思》:“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这些象征性的死亡意象,无不浸透悲凉恐怖的感觉。
从表层上看,屈原对生死是豁达超然的。然而,透过这些悲剧性的诗歌意象来看,可以瞥见诗人对死亡的痛苦与畏惧,因为人在本能上毕竟是恋生畏死的。此外,《天问》较多涉及历史上众多的死亡现象,在指责残暴势力对圣贤生命的无理剥夺时,诗人在深层心理上隐约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情绪和情感排斥,明显表现出珍惜生命和人生价值的倾向性。
2. 不畏死亡。“按照弗洛伊德晚年发展的一套理论,每个人只有两种基本的本能。他把其中之一叫作生命本能,而给另一种命名为死亡本能。这两种冲动的目标和欲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11]。据此,屈原的心理结构里隐藏着这两种本能,如果说生命本能在《九歌》里体现最为充分,那么死亡本能在《九章》里体现最为强烈。而《离骚》,则综合了两种本能,呈现二者激烈的冲突。从现实来看,最后是死亡本能占据了上风,尤其在屈原流放沅湘之后,痴狂情结进而诱发求死的心理冲动。屈原战胜死亡恐惧的原因有二:
其一,以死亡解脱自身痛苦。屈原在现实世界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政治上“美政”失败,情感上“美人迟暮”,乃至国破家亡,流浪荒蛮……诸种无法解决的痛苦长期作祟,发展为孤独绝望,它最终引导诗人自杀。屈原的绝望情绪主要包含这几个方面:一是对昏君感到绝望(《悲回风》:“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二是无家可归的绝望(《哀郢》:“惟郢都之辽远兮,江与夏不可涉。”……),三是无人理解的绝望(《怀沙》:“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这三重的绝望情绪,在《离骚》《九章》中表现颇为明显,它必然地促使诗人走向死亡。
其二,以自杀实现道德理想。加谬认为自杀是人生荒谬、空虚的副产品。然而屈原并非做此种理解。《离骚》所言的自杀,均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理性选择,而不是非理性的盲目冲动。屈原充满了对生活的肯定和对理想的追求,故而在他看来,自杀恰恰是向真理接近,是成就道德和审美境界有意义的实践。因此,诗人对历史上取义成仁的圣贤(伯夷、彭咸)逐渐产生亲近之感(尤其是在生命后期)。诚如叔本华所言:“当认识力占得了上风,人们因此能够勇敢、镇定地迎向死亡时,人们会把这种态度和行为尊为伟大和高贵。我们因而就会庆祝认识力战胜了那构成我们本质内核的盲目的生存意欲。[12]”屈原的认识力使他对于君王、政治、国家等对象彻底失望,为了维护自我的道德与理想、人格与尊严,他逐步理性地选择死亡。
屈原的自杀倾向在《离骚》中便很明显地流露了出来:
虽不周于今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贤之所厚……虽体解吾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而《九章》中描写的死亡意境,都贯穿这样的意识:死亡不是对生存空虚的厌倦和为逃避社会责任而采取的消极行为,它必须被注入人的存在本质的意义,必须具有道德和审美的意义。屈原最终借助有意义的死亡来实现对人生价值的高扬。死亡是恐怖的,但诗人最终毫不犹豫地踏上死亡之旅,自沉汨罗,以道德信念和理性勇气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因此,《楚辞》文本更能体现人格的刚强和伟大,呈现理想的人物性格,更加臻于较高的艺术美境界。
3. 灵魂不死之信仰。《九歌》是屈原生命意识充盈时刻的作品,言死不多。唯有《国殇》一篇,为祭祀为国捐躯的鬼魂而作,所言乃他杀而非自杀。“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借此可以反映出屈原对死亡的另一种看法,即灵魂不死观念。在诗人看来,“首身离兮心不惩”,死亡只是对肉体的否定,而精神生命是轮回和循环的。这是典型的神话思维对于死亡的审美超越(因为神话在本质上是否定任何死亡和死亡观念的),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坚定信仰。
此外,《楚辞》涉及“魂”的篇目有:《九歌·国殇》《九章·惜诵》《九章·哀郢》《九章·抽思》《招魂》《远游》《九歌·礼魂》等。而《九章》三篇所言的“魂”和《招魂》所招之“魂”,是指屈原自己的“魂”。这些文本无疑表现出:诗人相信自己死后,其灵魂是不朽的,它暂时离开身体去进行“神游”。屈原迷恋生命、迷恋香草美人,它与求死情结的形成内在矛盾。李泽厚特别强调了屈原选择自杀是一种“理性自觉”。当然,这一“理性”原则是屈原自沉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屈原精神结构中还存在着“灵魂不死”的诗意,死亡对他既是一种痛苦的道德意志的实践,也是幸福和充满美感的精神升华。求助于神话思维的灵魂轮回观,可能也是屈原解脱死亡之畏的一剂良药。
总之,屈原的诸种心理情结形成辩证的逻辑关联,对诗人的精神结构和实践意志均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影响他在政治活动中的选择和决策,另一方面影响他在诗歌创造中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再一方面影响诗人在生活世界的人生态度和具体行为,最终导致诗人自沉汨罗而走向诗意的审美永恒。
[1]霍尔·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38-39.
[2]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张唤民,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30.
[3]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M].段继承,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164.
[4]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序1.
[5]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11.
[6]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10-11.
[7]S·阿瑞提.创造的秘密[M].钱岗南,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54.

[8]王逸,洪兴祖.《楚辞章句》补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83.
[9]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54.
[10]梁启超,王国维.楚辞二十讲[M].胡晓明,选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9-20.
[11]J·洛斯奈.精神分析入门[M].郑泰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33.
[12]叔本华.叔本华美学随笔[M].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08.
(责任编辑 杨文欢)
Aesth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Qu Yuan’s Psychological Complex and His Poetry
LIU Yi1,2, YAN Xiang-lin3
(1.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Nanjing 210031, China;3.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15, China)
There is a potential aesthetic relevance between psychological complex and literature creation. Qu Yuan has 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s of loneliness, love for beauty, insaneness and death. There is temporal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d logical progression among them and they influence Qu Yuan’s aesthetic awareness and poetry cre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In other words, Chu Ci is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Qu Yuan’s psychological complex and aesthetic creation.
complex; loneliness; love for beauty; insaneness; death
2016-11-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审美范畴研究”(15BZW026)
刘奕,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警官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颜翔林,男,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美学原理、中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研究。
I01
A
1009-1505(2017)02-0040-10
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