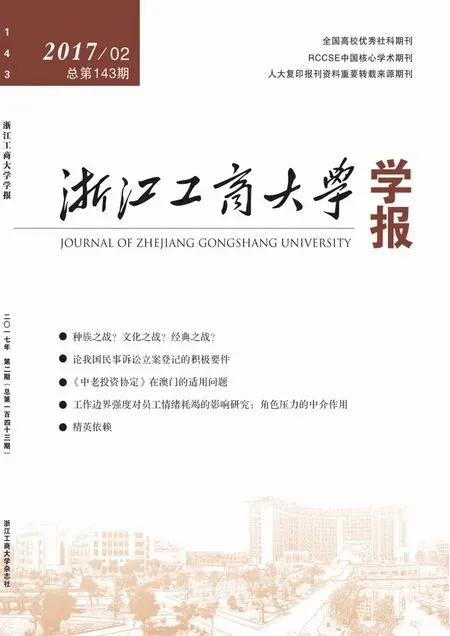论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的积极要件
——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19条
肖建华,王 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38)
论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的积极要件
——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19条
肖建华,王 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38)
以往学界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的立案登记积极要件“门槛高”,然而,在现行立案登记制模式下,这种解读已不适宜。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上的立案积极要件是可以解释的,也是可以适用的。司法现实中的“立案难”问题并不能归咎于立法。未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立案登记积极要件修订时,立法者应考虑到尽早过滤无法律利益的诉、兼顾诉讼解纷的固有界限、秉持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的外部因素。由此留下的解纷真空,则可通过讼外解纷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来填补。
立案登记制;立案积极要件;诉权享有要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为全面贯彻落实立案登记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30日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度。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2015年5月1日正式施行《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登记立案规定》),由此,立案登记制在我国法院系统全面推开。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登记的积极条件并没随之改变,先前学界对其“门槛过高”“起诉条件高阶化”的解读,在立案登记制下是否仍然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特别是立案积极要件)有无可能作适应立案登记制的解释?在立法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以往关于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高阶化问题有无化解的途径?本文拟重新阐释《民事诉讼法》第119条,透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度中的立案积极要件,并且尝试回应前述问题。
一、 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积极要件的规范基础
民事立案登记积极要件是指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具备的要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该四项要求就是立案积极要件,《民诉法解释》和《登记立案规定》对此还进行了具体化的规定。应当说,当前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运行的立案登记制还是有规范依据的,并且有具体程序作保障的。
(一) 立案登记制度中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
在立案登记制实施之前,我国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的立案积极要件法律依据是旧《民事诉讼法》(1991年制定,2007年修订)第108条。然而,现行《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第119条并没有改变旧法规定的立案积极要件。*从字面上看,新、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积极要件并没有任何区别,二者文字表述基本一致。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原告的起诉要满足当事人资格,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法院主管和管辖方面的要求,法院应此进行审查之后才能确定是否立案。先前有学者认为,该立案积极要件立法“门槛过高”,对原告的起诉提出这样的要求明显苛刻。这或许会让我们产生疑惑:司法政策确立了立案登记制度,为什么现行法上仍适用立案审查制所确立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呢?如果二者是冲突的,这又如何让我们在规范文本与立法意图之间取舍、衡平?
在笔者看来,立案要件与立案模式并不是一回事,立案要件是对诉的成立提出的要求,而立案模式要解决的是“法官审查民事立案积极要件的范围和程度”问题。尽管现行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依旧延续着立案审查制时期的规定,但我们不能认为这些规范只能作立案审查制立案要件的理解。不管民事诉讼立案是“审查制”,还是“登记制”,现行法只是对立案积极要件做了原则性规定,其与立案模式无关。通过司法政策以及司法解释的发展,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中的规范内涵早已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将其看作对以往立案审查制时期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替代和扩张,却也并非不合情理。
此外,我们不妨对此从比较法的角度反观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关于民事立案积极要件的立法。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33条,起诉状应当载明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包括原告和被告——如果有——应当列明当事人的法定监护人);(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三)诉讼理由(诉讼理由是法律所要求的用以证明原告对被告请求对的事实)[1]。差不多相同的规定也出现在德国民事诉讼立法中,起诉状的内容部分是必须记载的或应当记载的:当事人和法院是必须记载的;必须对标的和所提起请求权的理由进行具体说明,应当说明诉讼主张的证据手段[2]687。类似的规定也出现在法国民事诉讼法中,《法国民事诉讼法》第648条规定,“如果申请人是自然人,文书上应当写明其姓名、职业与住所及常用名、国籍、出生日期与出生地点;如果申请人是法人,文书上应当写明该法人的法律形式、名称、总机构住所地以及法定的代表法人的机关,但并不要求指明组成该机关的自然人的身份。”《法国民诉讼法典》第56条,“除规定执达员文书的应载事项外,传唤状应载有以下各项内容,否则无效:1.指出已向哪一法院提起诉讼;2.诉讼标的并陈述理由……”[3]41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早就实行了“立案登记制”。尽管上述域外关于民事起诉状应载事项的立法例略有不一,但将我国立法与它们稍加比较,就足以留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立案积极要件并没有离奇的“门槛过高”。
(二) 立案登记积极要件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
在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时期,法院依职权对原告起诉进行实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口头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4]。这种更多强调法官“权力中心”的立案程序构造往往会造成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不周延。基于这种认识,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应是对以往法官职权主义特征的立案审查程序构造的修正。
此次民事立案登记制度改革中,更具突破性和实质性的发展,应是其完善了对原告程序诉权保护的制度。具体体现,首先,《民诉法解释》和《登记立案规定》确立了保障原告程序诉权的程序规则,即实行当场登记立案,对不能确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法院应接受书面材料并出具书面凭证,且应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这种“当场立案或处理”的程序要求,可以有效防止法院以各种法律外的理由推诿甚至不接收起诉材料的现象发生,充分保障了原告接近司法的权利。其次,对不符合形式要件的起诉,实行一次性全面告知和补正,这将从技术操作层面为原告起诉提供便利,规避了以往法院故意拖延立案或刁难原告的现象。再次,对不符合法定要件的起诉,应当依法作出不予受理或不予立案的裁决,出具书面文书并载明理由,这意味着法院应对不予受理的起诉要出具书面裁定,从而抑制了以往法院以口头方式作出不予受理裁决的恣意。第四,当事人可依上诉或申请复议的形式对不服的不予立案裁决进行救济,该规则强化了原告在立案阶段的程序参与,完善了原告对程序诉权救济的权利。最后,司法解释建立了以上级法院内部监督和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检察机关、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立案监督机制,同时也完善了对违法滥诉行为的制裁措施。
依上所述,现行关于民事立案要件的立法明确了立案登记积极要件规范;立案登记程序规范又把立案环节纳入到了程序保障范畴,充分保障了原告的程序诉权。换言之,规范民事立案积极要件与加强对原告程序诉权保障是相辅相成的,即只有在对原告程序诉权保障的基础上规范民事立案积极要件才是立案登记制的应有之意。
二、 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积极要件之重新阐释
学界以往对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的批评,主要是立案积极要件设置不当。学者认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既涉及到起诉要件,又涉及到诉讼的形式要件,还涉及到诉讼的实质要件[5];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揉合在一起,事实上为当事人行使诉权设置了相对较高的“门槛”[6];高阶化的立案受理条件严重阻碍了当事人诉诸司法权利的可能性[7]。如果能够将诉讼要件从起诉条件中剥离出来,司法实践中的立案难顽疾将大为改观。我们先不问这种思路是否真能解决立案难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学者的论述并没有明确回答要将哪些要件剥离出来,哪些要件应作为起诉受理(立案)审查的内容,以及审查的理论依据等重要问题。学界认为起诉要求中夹杂着诉讼要件,是立案难主要症结。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仅从立法文本字面上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忽视了对立案积极要件规范的理论基础和立法依据的考察。立法从当事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与法院管辖方面对立案积极要件作了大致轮廓性规定,与法官审查这些要件的尺度无关。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积极要件,需要在立案登记制的背景下进行具体化的解释。
(一) 当事人方面要件的分析
当事人的状况对诉讼法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法院必须在程序开始时对此予以确认,不能允许“不明之人”或者“有关人员”提起或者对他们提起诉讼。对此,法院在起诉阶段一般按照原告在起诉时提交的诉状和其他诉讼材料中双方当事人之表示对谁是当事人问题确定[8]146。
先前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一)项中“有直接利害关系”是对原告适格的要求,但原告适格与否因涉及到案件实体因素,法官须在诉讼系属后经当事人实体辩论才能判定。“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中的有直接利害关系,是要求原告是正当的当事人”[7];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是要求法院在审査当事人的资格时对原告采“适格说”[9];“《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要求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涉及到对实体法律关系的审查,在立案阶段很难查明”[10],都是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上述“原告适格须在诉讼系属后才能判定”的论述,笔者甚是赞同。实体资格是表现了当事人与诉讼标的的实体关系并且回答了当事人是否正确的问题[2]251-252。不过,在笔者看来,在立案阶段,“有直接利害关系”并非是对原告适格的要求。当事人在发生法律争议后提起诉讼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行为,诉权是进行诉讼的自由,是一种法定权力的体现[3]99。但这种诉权不能与实体权利相混淆,实际上,实体权利是诉权的客体[8]279。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呢?笔者认为,“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解释为“原告在起诉时需具备诉权享有要件的要求”,即原告在起诉时需证明自己因诉讼可能获得的“利益”。按照法国民事诉权理论,诉权是否受理有两项基于诉讼当事人本身的条件,即诉讼“利益”与“资格”。“利益”必须是“正当的利益”,而诉讼“资格”则是“受到损害的权利”与“诉权”结合起来的联系[3]150-151。法国学者对诉权享有要件中的“利益”要件进行了具体解释,当原告行使诉权可以为其受到的“损害”进行“救济”,则该人具有诉讼利益。这里所说的“诉讼利益”包括各种性质的惠益:财产性的,非财产性的;或金钱的,或仅仅是精神的。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种类的利益都可以成为诉讼利益。只有那些在行使诉权之日即存在的一定特征的利益,才能成为诉讼利益[11]299-300。如果不具备享有诉权的条件,“向法院表达诉权的行为”不予受理,即诉讼请求不予受理[3]99。不予受理抗辩既没有触及到权利的实体(“不经实体审查”),也不是皆在推迟争议的了结(“皆在使原告的请求被宣布为不可受理”)。不予受理抗辩所针对的是当事人的诉权本身,其目的是对不具备诉权的当事人予以惩罚[11]362。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利益”只是原告观念上认为的利益,至于这种利益是否确实满足实体法上“实体利益”的要求,法官无需在起诉阶段审查确定。在这个意义上,若将我国法上的“有直接利害关系”要件诉诸于诉权享有要件中的“利益”要件理论,那就没有将其解释为“原告适格”留下太多的空间。至于学者对“有利害关系即是对当事人适格要求”的解读,在司法实务中可能确实存在,或者说这是法官审判逻辑的理所当然。事实上,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在立案阶段要求原告主体适格。但我国理论和实务均强调原告应当具有当事人适格[12]。假设该论述成立的话,上述学者对“有直接利害关系”系立法上不当设置的批评就有失偏颇。
(二) 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要件的分析
诉讼请求是指明诉讼尺码基本单位的概念,法院可依其为标准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是否发生请求合并、诉的变更、是否构成二重起诉等问题进行判断[13]。相应地,原告在提起请求时只说被告有责任,却不提供任何识别的线索,总归是不大像乎是真的;易言之,起诉状中没有关于争议事实的叙述,以致被告不明白怎样诉答,也是不大可能的。由此,原告在起诉材料中必须载明请求的趣旨及请求的原因,以使原告对被告提出的权利主张与其向法院提出的胜诉判决之要求获得明确表示[2]690。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三)项“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规定,要求原告在起诉时必须明确诉讼请求。若原告的主张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无法要求对方当事人合理地构建应答文状,法官应通过释明要求原告补正。通过释明后仍然不能明确的,法官将依法作出起诉不合法的裁决[14]。对此,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17条,可能造成诉讼行为无效的实体不合规的情形还包括,传票未载明任何请求[11]347。《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第2款第2项规定确定的请求是诉状中必须记载的[2]690。在笔者看来,原告在起诉时主张的请求只是观念上享有的权利,而不应是实体意义上的胜诉请求权。胜诉请求权属于请求的实体权利的本体问题,但是,诉权本身并不包含实体权利。因此,即使法官判定原告的请求不具有正当性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却不能在起诉时就剥夺原告提起诉讼的权利[15]。在未实行强制律师主义的诉讼制度下,要原告在起诉时就对案件作出恰当的法律评价并向法院作出明示,应当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些案件是伴随着庭审的进行,诉讼请求要件才能得以特定[8]118-119。
诉讼请求不仅应当根据其语句解释,而且也要借助整个理由说明进行解释[2]690。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三)项“有具体的事实、理由”的规定,就是要求原告应在起诉时就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予以大体明确,我国民事司法解释中也已有相应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条“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的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应当提交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然而,我们不能对此予以过高的期待,因为只有那些最为简易的案件才有可能做到严格遵守这样的要求,但凡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诉讼案件,最好还是由原告的律师在其提出的最终陈述准备书中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的理由做出详细的补充说明。要求原告从对抗一开始就把“全部战线”都暴露出来并不恰当[3]705。要求原告在起诉时应尽可能提交证据(事实、理由的主要内容),但并能在立案阶段要求其切实做到这一点,原告在起诉时是否提交了适当的事实、理由,法官不妨采取相对弹性的审查理念。当事人在起诉阶段提交的证据不同于庭审中定案的证据,起诉证据的证明对象是以起诉权和管辖权为基础的待证事实。相较于庭审中的民事诉讼证明对象而言,它的内容较为狭窄且侧重于程序性[15]。法官在起诉阶段对证据的审查重心,应是现有事实、理由是否有利于程序的推进,而不应是原告主张的实体请求权是否具有充分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原告提供的证据符合如下条件即可:能够证明争议的事实存在、原告与被告存在一定事实和法律上的关系、属于法院主管、本院有权管辖,即要求原告提供起诉证据即可,不要求提供胜诉证据,对证据的审查,也只限于程序审查[16]。
(三) 法院管辖要件的分析
在发生诉讼系属前,案件依原告的申请不拘形式地交付法院,但在法院审查确定管辖权前,原告提交诉状的行为对法院不产生管辖效力。根据《民事诉讼法典》第119条第(四)项关于对法院管辖方面的立案要件规定,法院在原告起诉时应从两个方面对管辖方面立案积极要件审查:首先,原告提起的诉是否属于法院主管范围,即法院是否整体有权对该纠纷裁判;其次,若纠纷属于法院主管,接下来要确定具体的管辖法院,这须经过若干管辖规定的组合才能确定。
有学者认为案件主管、管辖法院的确定,只有经过实体审理,才能知道是否属于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范围,是否属于本法院管辖[12]。在该文看来,法院在起诉阶段审查管辖方面要件的依据是决定管辖权的实体因素,而非决定案件实体问题的因素。管辖权问题所要求的并不是就诉讼的实体本身作出判决,而仅仅是对“直接决定管辖权的实体因素”作出判决[3]440。通常法院根据原告提交的起诉材料中诉讼标的额、纠纷发生地、被告地、当事人的身份特征、争讼标的的性质等主要因素予以确定。很显然,这里论述的确定管辖法院因素,不同于上述学者主张的决定案件实体问题的因素。考察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关于管辖方面立案要件的立法例,可以佐证我国法上的规定并非孤证。德国民事诉讼中,法官不需要在庭审或等到实体裁判阶段,就可以判断案件因管辖权错误造成原告起诉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裁判权的存在是诉讼有效性的前提条件[17]176。法国法也有类似立法例,若原告的起诉状中没有管辖的记载事项,则该诉讼文书无效。现在,这些规定比过去更加具体。按照《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6条规定,传唤状还应当载明以下各事项:指出已经向哪一级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有必要具体说明法院的性质(职权管辖)以及法院所在地(地域管辖)。有时由于两个或多个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所以指出向哪一级法院提起诉讼尤为重要[3]704-705。通过对这些域外立法例的研读,可以让我们对管辖法院方面的立案要件获得一个大体统一的印象:法官在起诉阶段可依职权对管辖法院方面的立案积极要件审查;若该要件不具备形式性要求,则原告的起诉行为无效。不过,按照大陆法系民事诉讼通行理论,法院管辖又具有诉讼要件的性质,因此,法官仍可在诉讼审理阶段对其审查。
上述对我国民事立案登记积极要件的分析表明,尽管现行法中关于立案积极要件的立法并不完善,但这也并非是立案制度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换言之,我国立法上的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并没有给原告起诉带来太多的“障碍”。立案积极要件理论和诉权享有要件理论密切关联,诉权享有要件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立案积极要件的实质性依据。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说,原告在起诉时对立案积极要件的说明是否充分没有严格的评判标准,因此,这又是一个由法官自由裁量的“事实问题”。
三、 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积极要件的发展理念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说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的立法不仅是能够解释的,而且是能够适用的。不过,相比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民事诉讼立案要件周密和精致化的立法,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的立法还有进一步发展和细化的空间。在笔者看来,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积极要件在发展和实施中应当秉持三个基本理念,具体表现如下:
(一) 尽早过滤无法律利益的诉
立案登记制度改革旨是为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立案难”问题。这在立法者看来,对符合法定立案要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不过,一项法律规则常不只要实现一个目的,毋宁常以不同的程度追求多数目的[18]。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度也是如此,对民事立案制度立法目的的认识,我们不能局限于立法者公开表达的意图。更恰当的是采取一种“客观目的论”的分析方法,即在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基本价值功能下还需引入影响立案制度运行的司法环境之类的考量。因为,我们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而非原则上毫不限制的“极端法立场”。立法者可以对这种权利进行“非根本性限制”[3]152。仅仅有某种“可能的利益”不足以作为提起诉讼的依据。我们要避免受到“讲歪理精神”鼓励的“防御战”来剿杀法院,并且“诉诸法院”也要有某种道德观念,同时还要对“司法流量”进行调节……因为法官人手不足[3]157。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关于立案积极要件的设置也表明,立法者从来不打算将立案制度的功能局限于保护当事人诉权,而是宁愿在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时对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做出限制。立案登记制并非是绝对的形式登记,强化法院对立案要件的审查管理,摒弃法律范围之外的利益诉求才是该制度的理论精髓。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滥用诉权或就法律外的利益诉求向法院缠讼等现象尚还存在。因此,基于保障司法资源合理利用的考量,法院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管理以尽早避免无法律利益的诉进入程序,这对节约司法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二) 兼顾诉讼解纷的固有界限
作为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审判机关,法院的受案范围受制于诸多客观因素,合理划定法院的受案范围是司法良性运行的关键,相反,如果法院受理了超出其审理能力的案件,则会严重损害法院的社会地位及权威[19]。更有一些社会转型期制度、政策层面改革的负面残留,若对这些纠纷径直以诉讼方式解决并非都能得到公正有效的处理,稍有不慎可能还会引发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提醒我们:在讨论民事立案积极要件规范时,实际上无法回避民事诉讼解纷的固有界限。法院并不具备从根基处全面解决社会纷争的资源和条件,为此,对真实世界里的纷争进行某种裁剪,就成为法院为实现自身功能而不得不做的选择[20]。有些纠纷因牵涉到政府政策调整而在司法上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是诉讼制度设置的不合理。相反,这些纠纷由行政机关以灵活、弹性的行政方式解决反而更加高效和全面,更能实现法律保护的需要。在我国,许多社会关系还依赖于行政性、政策性的规范加以调整;司法机关的现实地位也使其还不完全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21]。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的设置是在保护当事人诉权与尊重审判权固有界限这两种利益间寻求平衡。这也不得不让我们重新理性审视立案登记制度的价值功能,那就是,仅仅指望立案制度层面上的改革来解决现实中的立案矛盾,这种期待是不现实。当然,这并不是说,排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相反,保障司法对法律范围内利益诉求的解决正是立案登记制度的价值功能。过去存在很多非法集资、企业破产等按照法律本该受理但因涉及面较大,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而被法院不予立案的情形,施行立案登记制后“放行”这些案件进入法院,势必有巨大的进步意义[22]。
(三) 秉持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
立法者的选择从来不是抽象的、理想主义的,而必定是具体的、从实际出发的[23]。立法者引入的某项制度须有其特定的功能预设,我国立案登记制度也是如此。随着社会法治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要求法院抱积极态度的呼声颇为高涨,司法积极主义正逐显头角。立案登记制度的功能预设正是要着力清除当事人接近司法的障碍,扩张司法解纷的范围,彰显司法的担当。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对原告的起诉审查时应基于对原告诉权尊重和保护的原则,秉持一种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让法律范围内的诉求进入诉讼程序中来。在实行立案审查制时期,由于立案积极要件立法的原则和抽象,法院往往在法律范围之外私设各种立案“土政策”,并以解决案件实体问题的思维方式对立案积极要件过度审查,这从而导致了本该受理的法律纠纷被拒绝在诉讼外。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后,基于原告在起诉时提交起诉材料的局限,法院应按照最有利于原告的原则审查起诉材料,当可以判定原告提交的起诉材料间存在的逻辑关系能达到一般生活经验所确定的程度,且这种简明扼要的陈述又能给被告一个平等的通知即可,除非它毫无疑问地显示原告不可能提出任何事实来支持其提出的诉讼主张。现行立案规范也并不要求原告一开始就详细地陈述和提交所有涉及诉讼主张的诉讼材料。
四、结 语
本文以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规范为研究出发点,以立案登记制度改革的意旨为分析主线,并借助域外成熟的诉权享有要件理论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下的立案登记积极要件规范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分析得出,随着保护原告程序诉权和司法积极主义的立法理念确立,学者先前关于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立法“门槛高”的解读在现行立案登记制模式下已不适宜。不过,这只是一个解释论上的中立判断,未来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规范的设置应融入尽早过滤无法律利益的诉、兼顾诉讼解纷的固有界限和秉持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对此,留下的解纷真空,应通过讼外解纷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来填补。
[1]阿德里安·A·S·朱克曼.危机中的民事司法——民事诉讼程序的比较视角[M].傅郁林,陈湘林,唐桂英.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31.
[2]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M].李大雪,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3]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4]傅郁林.中国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J].法学家,2011(1):99-113.
[5]毕玉谦.民事诉讼起诉要件与诉讼系属之间关系的定位[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4):60-69.
[6]宋朝武.民事诉讼受理制度改造的理性视角[J].法学论坛,2007(3):41-46.
[7]刘敏.论裁判请求权保障与民事诉讼起诉受理制度的重构[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2):44-50.
[8]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9]黄新华.对我国民事立案受理制度修改的思考与完善[J].司法改革评论,2013(1):55-70.
[10]徐昕.解决"立案难"要立足中国国情[J].中国审判,2007(1):10-11.
[11]罗伊克·卡迪耶.法国民事司法[M].杨艺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2]张卫平.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J].法学研究,2004(6):58-68.
[13]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18.
[14]张卫平.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法商研究,2015(3):3-15.
[15]王福华.民事起诉制度改革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6):1-9.
[16]宋旺兴.论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度[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2):83-90.
[17]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M].周翠,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76.
[18]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9.

[19]许尚豪.“立案登记制”后如何审查立案[N].人民法院报,2014-12-24(5).
[20]吴泽勇.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性原理[J].法学家,2010(5):81-101.
[21]张卫平.起诉难:一个中国问题的思索[J].法学研究,2009(6):65-76.
[22]禹爱民,李明耀.立案登记制如何穿越现实屏障[N].人民法院报,2015-05-04(2).
[23]吴泽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适格[J].法学研究,2014(3):148-167.
(责任编辑 陶舒亚)
Positive Requirements of Filing Registration of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and a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19 of Civil Procedure Law
XIAO Jian-hua, WANG Yong
(School of Law,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8, China)
In the past, academics used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high threshold” of the legislation on civil action filing requirements. However, in the current case filing register system, such interpretation is no longer appropriate. Positive case filing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civil procedure legislation can be explained and also can be applied. The problem of “being difficult in filing a cas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judiciary cannot be the reason of blaming the legis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applying civil action filing requirements in the future, legislators should consider filtering the lawsuits without legal interes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 inherent limits of litigation mediate and adhere to tolerant concept for filing. The vacuum of dispute resolution left thereafter can be supplemented through building and perfecting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besides litigation.
case-filing register system; initiate an active requirement; requirements of enjoying litigious right
2017-02-21
肖建华,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王勇,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DF72
A
1009-1505(2017)02-0050-08
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2.006
——以民事诉权的合法要件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