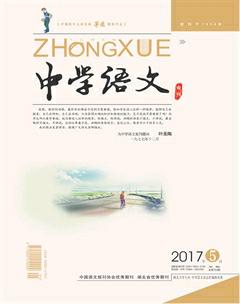大自由
王澄宇
自由是什么?无数的作家、哲人都曾试图给“自由”下一个定义,却总是发现,不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将其完美地表述出来。这种境界似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于是便只能退而求其次,从一些侧面展现它,犹如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侧面間接描写有时候远比正面刻画更余味无穷。《逍遥游》中,庄子也没有一上来便高喊“逍遥就是无所依凭,自由就是无拘无束”,而是首先以大鹏“水击三千里”这样的壮阔场面撼人心魄。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鲲鹏尽可鄙夷学鸠的浅薄——它甚至都未尝从云间鸟瞰人世,又哪里有足够壮阔的情怀去迎接自由?可真到了变得足够“大”时,就能冲破一切桎梏,逍遥游于天地么?即便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终归还是“去以六月息者也”。可以说,所至越远,所依越多。而现实中,却有那么多人对此误解连连。有多少“热血”“励志”的作家,总以为“大自由”就是通过个人卓绝奋斗、苦心经营登上权力的颠峰后,便再也没有什么权威能压制自己,由此就可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事实却证明,这种观点何其肤浅与荒谬:在权欲之海中浮沉的人物,有几个拥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权杖如魔咒,看似给予人无拘无束的无限风光,实际上,史册中又有多少因它而生的兴衰成败、爱恨情仇,它又断送了多少原本可以长存的希望与可能?汲汲于世,高居庙堂,真得能抵达“大自由”的境界么?庄子摇摇头,说他甘愿做一只在泥水中摇尾的鱼;心性率真洒脱的五柳先生,也终因折腰之恨愤然解印,在农事与饮酒中追寻自由的真谛。
庄子感叹到,并不是让自己更“大”后就能真正实现逍遥。诚然,楚之冥灵远胜于晦朔不知的朝菌,上古的大椿更胜于百岁的南冥。可我们想要游的是无穷啊!变“大”确实是一种进步,可不管是“五百春”,还是“八千秋”,这数字再大,对于“无穷”来说是有意义的吗?“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生命注定要终结,那我们为何还要在这有限的时间欲壑难填,百般挣扎?为何还要忍受那么多自己看不过眼的东西“数数然”不已?
叔本华说“自我与永恒结合的唯一方式便是死亡”。庄子亦在妻子离世后欢快地击打着木盆,庆祝其妻回归自然。即使伟大如鹏也需凭六月大风,我们这些渺小众生又如何逍遥?恐怕答案只有一个,放空一切,看开一切,“无所待”于这纷乱的尘世。如果我们真能炼出一颗静水般的心,无所依,无所为,无所欲,甚至看淡生死,那还有什么能困扰我们,阻止我们通向至境?
恕我不恭,这种潇洒的哲学对现在的我们而言至多是一种心理的抚慰与憧憬,于现实生活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死亡的确是难免的,生命的确是有限的,可我们却正年轻,满满的激情和愿望正如种子要突破地层,是那样的不可遏制。“大自由”在当下该是如那解牛的庖丁,反复训练、精益求精之后目无全牛,游刃有余。
还记得我读过一篇科幻小说《上帝骰子》。它讲到:一些人类无法容忍“宇宙间不可通”的金科玉律,觉得自己被囚禁在这个宇宙中,便制造了一个连接两个宇宙的黑洞。他们每个星期日随机抽中一个“幸运儿”,将其送入黑洞,看他被吞噬。日复一日,只为那根据量子学说“一切都有概率发生”的不足万亿分之一的可能性……
用有限追求无限,其结局注定是悲剧的,可这并不代表小大的差别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小说中新来的人不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争着去“送死”,“幸运儿”们都笑着说:“我们不去,就永远是不可能;去得人越多,概率的分子也就越大。”怀着这样一种精神,我想,他们在被吸入黑洞的一瞬间,心灵一定是无比澄澈通透的吧。
[作者通联: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二(29)班 指导老师:文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