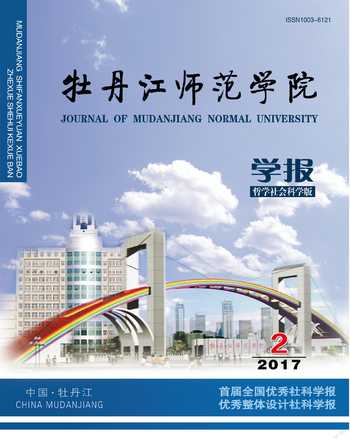结果补语对动词的选择限制探析
[摘 要] [+可变]和[+他控]是动词充当结果补语的充要语义条件。非自主达成类动词具有充当结果补语的天然语义优势。由于词类的连续统性质,少量弱动态状态词、具有非自主用法的活动动词,以及具有非自主特征的弱动作性动宾式、并列式合成词也能充当结果补语。可用排除法鉴别结果补语动词,能够进入“ +了”格式,同时不能进入“在\正\正在+ ”和“去+ ”格式的动词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结果补语动词具有双重时间结构,在整个词类系统中呈连续统分布。
[关键词] 结果补语;动词;达成;非自主;形式鉴别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2010706
结果补语主要由形容词充当,也有少数动词,到底哪些动词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王红旗(1995)、陈巧云(2000)、何元建等(2002)、辛永芬(2003)、刘芬(2011)曾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统计,但各家的统计结果出入较大,统计标准也不够明确。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充当结果补语的动词主要是单音节的;语义上具有可变性、非自主性特征;认知上具有非持续性、有界特征(马婷婷,2016)。而这些描写性特征不具备排他性,因此仍然无法获悉结果补语选择动词的区别性特征。
为了帮助界定、厘清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动词的特征,从语义、句法、情状等三方面对充当结果补语的动词展开多维考察,并从情态角度对这些词进行了分类,发现有三类动词可以充当结果补语:
(1)达成动词:败、爆、崩、绷、病、丢、掉、到、滚、毁、卷、见、开、落、破、撒、散、输、睡、死,等。
(2)状态动词:怵、懂、疯、服、够、惯、会2、乐、明白、毛(1)2、恼、怕、忘、习惯、瞎、哑、晕、肿,等。
(3)活动动词:飞、混、活动、哭、趴、跑、笑、翻2,等。
上述三类动词充当结果补语的能力呈递减趋势,即:达成动词>状态动词>活动动词。结果补语主要由达成类动词充当,但不限于达成类动词,少数状态动词和活动动词也能充当结果补语。由此,结果补语对动结式的动词还有哪些限制,结果补语的选择、限制条件的动因是什么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1)为什么有的达成动词能够充当结果补语,有的却不能?各有什么样的特征?(2)什么样的状态动词能够充当结果补语?为什么?(3)什么样的活动动词能够充当结果补语?为什么?
一、动词充当结果补语的基础语义特征
(一)达成类动词充当结果补语的语义基础及动因
“达成”是动词情状类型之一,情状分类影响最大的是Zeno Vendler(1967)的四分法,即将情态划分为四个类型:活动(activity)、完结(accomplishment)、达成(achievement)、状态(state)。邓守信(1986)将时间结构分为起点(inception)、过程(duration)、终点(termination),并据此将Vendler提出的四种类型进一步阐释为:
活动:表明纯粹的动作过程。开始以后动作本身便是目标,别无其他目标。表示活动的开始或进行。
完结:表明达到了動作的目标。达到目标之前不存在,发生于瞬间,指明活动完结的终点。
达成:表明情况的出现(状态的发生或转变);指明状态变化的起点或终点。
状态:表明一个情况的存在,恒久不变。
目前关于情态类型划分的语义特征主要有[±动态] [±完成] [±持续]三组,其中,活动、完结、达成三类情态具有动态特征,状态具有静态特征。我们将前人(Dowty,1979;邓守信,1986;陈平,1988;杨素英,2000等)关于这四类词的主要语义特征总结如下:
(1)状态词:[-动态][+持续]
(2)活动词:[+动态][-完成]
(3)完成词:[+动态][+完成][±持续]
(4)达成词:[+动态][+完成][±持续]
其中,[±持续]这一组语义特征难以将完成词和达成词区别开来。达成词强调动作完成后呈现的状态及状态的持续;完成词则强调动作的瞬时性,强调动作本身的结束。本文采用是否具有[结果实现]的语义特征区别达成类动词和完结类动词。
动结式所表示的复合事件是一个过程结构,要求包含事件发生的起点和终点。一般情况下,原因事件由述语动词承担,表示事件的起点;结果事件由补语承担,标志动作事件的结束、动作结果的产生,即状态的开始。因此,能够进入动结式补语位置的词必须是一个有界的动词,包含动作的终点。由于状态的改变和驱使力是致使结构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状态的改变”要求动结式的补语谓词必须是可变的、动态的变化动词。[+可变]这一语义特征是谓词能否充任结果补语的前提,而结果补语本身就表示动作或状态引发的结果,即施事或受事者状态的改变,蕴含结果的实现,因此,达成类动词和结果补语具有相同的语义基础,达成类动词充当结果补语具有天然的优势。
然而,并非所有的达成类动词都能充当结果补语,其限制因素为动结式的另一核心要素——“驱使力”。“驱使力”的存在表明,结果补语谓词所表状态必须是在外力作用下形成的非自主状态,自主的达成类动词都不能充当结果补语。因此,[+他控]性是结果补语谓词的另一核心特征。至此,我们将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达成类动词的语义特征描述为:[+动态] [+他控][+结果实现]。
经考察,杨素英(2009)统计的包含结果的达成类动词中不能充当结果补语的单音节自主性达成动词主要有:撤、等、冻、赶、关、滚、害、合、还、交、解、戒、碰、起、惹、删、逃、停、吐tǔ2、推、退、谢、变、放、降、夸。而双音节达成类动词都不能充当结果补语,如“摆脱、报销、暴露、爆发、拆除、偿还、打倒、打破、答复、达到、到达、稳定、颠倒”,等。
(二)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状态类动词的语义特征
谓词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一个重要前提特征就是动态性。从理论上看,状态类动词的主要语义特征是静态性,不具备充当结果补语的语义基础。但是,词类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动态词和状态词之间存在着过渡地带,少数状态词具有弱动态性,如“怵、懂、疯、服、够、惯、会2、乐、明白、毛2、恼、怕、忘、习惯、瞎、哑、晕、肿”等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究其原因,仍可归结到结果补语的核心特征上,即这些词具有[+可变][+他控]的特征。
上述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状态词是表示心理活动的感觉类动词,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弱动态性,处于活动词和状态词之间。陈平(1988)曾将静态的状态动词分为表示属性或关系的动词、表示心理或生理状态的动词、表示处所位置的动词三类,认为它们的静态性质有程度强弱的区别。杨素英(2009)也将表示心理或生理状态的词看作弱动态词。因此,少数状态词仍具有一定的弱动态性,满足结果补语要求的[+可变]性特征。
这些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状态词也是少数,并非所有的表示心理活动的状态词都能充当,对其起限制作用的语义条件便是[+他控]性。也就是说,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状态词所表状态都必须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不能由自发而产生。同时,这些词不能是有意识的动作行为,即不能是自主动词。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心理活动动词要么不能由动作的主体自由支配,如“懂、会、瞎、晕”等,要么既可以受动作主体支配的自主能力也能表示受外力影响产生的非自主特性,这类词具有双面性。
(三)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活动动词的语义特征
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活动动词数量更少,本文统计的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活动动词只有“飞、混、活动、哭、趴、跑、笑、翻2”等少数几个词。它们之所以能够充当结果补语,是因为同时具备[±他控][±可变]的特征,即这些词兼有自主和不自主的双重含义,可以用来表示结果补语要求的非意志控制状态。此外,这些词本身是强动态动词,但也可以用来表示动作持续的状态,表明状态变化的起点。这些特点满足了结果补语对谓词自上而下的语义要求,进而获得充当结果补语的可能。
(四)少数动宾式、并列式合成词充当结果补语的语义动因
除了上文分析的非自主的达成类动词、弱动态状态词及少数具有非自主用法的活动动词能够充当结果补语外,还有少量双音节动词或短语能够充当。主要有以下三类:
(1)动宾式合成词:变形、岔气、出名、出格、出圈儿、出神、到手、到头、断气、动心、动情、掉队、掉色、感冒、流血、卷口、入迷、散架、上当、上门、上瘾、脱皮、生气、走眼、走调儿、走样儿、走嘴,等;
(2)并列式合成词:残废、混淆、成熟、习惯、颠倒、活动,等;
(3)动趋式合成词:趴下、剩下,等。
这类成分数量非常少,根据所阅读考察的材料,尽可能穷尽列举,也仅有上述少量词语。这些词在充当结果补语时,与动词搭配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有些甚至是单一搭配。如,“走眼”只与“看”搭配;“走调”只与“唱、弹”等搭配;“掉色”只与“洗”等搭配,这类词构成的动结式搭配不自由,具有熟语性。吴为善等(2008)认为,这些动宾式合成词之所以能够充当结果补语,一是因为其“动性”很弱,虽有动态性,但可用于表示结果或状态;二是这些词都具有非自主特征,所表结果状态都是由外力作用或环境刺激造成的,满足结果补语的语义要求。同理,根据张国宪(1997)关于双音节动词“动性”强度等级序列排列:“前加\后附〉偏正〉补充〉陈述〉支配〉联合”,并列式合成词的动性最弱,具有充当结果补语的语义基础,而且这些并列式合成词都是偏义词,其语义主要由其中一个语素承当,且这个语素单独成词,能够充当结果补语。如,与“残废”对应的“残”;“混淆”对应的“混”;“成熟”对应的“熟”;“习惯”对应的“惯”;“颠倒”对应的“倒”;“活动”对应的“活”等,都能单独充当结果补语,所以这些词有充当结果补语的语义基础。但是,由于能够被同义的单音节词替代,因此上述并列式合成词充当结果补语的频率较低。
二、结果补语对动词的其他限制
[+可变][+他控]是结果补语谓词的两个核心语义特征,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谓词,在理论上都具有充当结果补语的可能性。但在语言现实中,结果补语谓词还受其他条件限制。
(一)双音节达成类动词几乎都不能充當结果补语
结果补语对谓词的选择除语义要求外,便是音节上的限制。即便满足了结果补语语义要求的达成类双音节动词也不能充当结果补语,如:“摆脱、传达、传染、达到、打倒、打破、得到、防止、改正、纠正、看见、满足、埋没、明确、破坏、碰见、改进、改良、改善、说服、夸大、扩充、扩大、放松、养成、减少、降低、消除、消灭”,等。这种双音节词之所以不能充当结果补语,理由有三:第一,从外因上看,受汉语双音节化的影响,动结式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事件结构,结果补语优先选择单音节谓词充当。这种倾向性表现与形容词结果补语一致。第二,从内因上看,这些动词的构词方式都是“动词性语素+动词性语素”的格式,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组合性结构,包含一个动作及指示该动作结果的行为(连动式)、状态(动补式)、方向(动趋式)、方式(偏正式)等,已经蕴含了动作的各种附加成分,无法再由某一外力致使形成一个新的联系紧密的复杂结构,这是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此外,还有部分词是自主动词,不符合结果补语要求的非自主特性。
(二)独立性差,不能单独成词
有些结果补语谓词所表状态的外在致使力规约性高,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单独表义的范围逐渐缩小,丧失了独立性,整个动结式已凝固成词,结果补语以合成词构词语素的形式存在动补式合成词中。如:
没:淹没、埋没、隐没、吞没、沉没;
明:申明、说明、阐明;
变:改变、蜕变、演变、嬗变;
合:糅合、配合、融合;
退:击退、打退、撤退。
三、动词充当结果补语的形式鉴别标准
(一)动词[+可变]特征的形式鉴别标准
动词的[+可变]性就是其动态性。[±动态][±持续][±完成]是以自然的时间流逝为参照点,根据动词在时间轴上各时点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归纳出来的三组语义特征。它们是划分动词情态类别的区别性特征。动态和静态是一组对立的概念。静态是“在时间轴上所有时点呈现出相同状态的情状,是一种均质的时间结构”(陈平,1988:152)。动态则相反,要么在时间轴上只占据一个时点,不能容纳时段,如瞬间动作动词“死、断、熄、明白”等;要么“情状在时段的各个时点上呈现出来的性质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陈平,1988:152)。通俗地说,动态性指动词所表示的活动、变化、感觉、状态等是运动的、变化的。根据Comrie(1976:49)的定义,静态情状的维持不需外力作用,而动态的活动或时间的维持则需要外力的持续作用才能保持。
静态动词不能用于进行体。Vendler(1967)、Dowty(1977)都是用能否进入进行体作为动态和静态的区分标准。汉语没有时态,一般用表示行为进行的“在”作为测试标准,检验动词的动态性(陈平,1988;郭锐,1993)。杨素英等(2009)认为,动词的静态、动态情状是一个渐变的系统,没有截然二分的区别。动态性有强弱之分,很多弱动态动词并不能用“在”检验出来,他们倾向于用“在”检验强动态动词,用“着”检验弱动态动词(杨素英,2009)。如,“爱”和“姓”一个是心理活动动词,一个是属性动词,两者都是静态动词,但是“爱”蕴含有弱动态性,其所表状态有中断、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爱”能与“着”连用,表示状态的持续,而“姓”则不能。
结果补语本身表示由动作引起的状态的变化,蕴含着“状态的产生与持续”两个不同的时间节点,要求充当结果补语的谓词具有弱动态性而非强动态性。因此,活动动词都不能充当结果补语。而用于检验强动态动词的类体标记词“在”也不能作为检验结果补语动态性的标志。我们更倾向于语言学界已形成的共识,即:“着”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持续或动作造成的状态的持续,而非判断动态性的标准。
结果补语强调的是一个状态的发生或转变的过程,本文用动词之后能否加“了”的方式鉴别结果补语动词的动态性,用句法槽“ +了”表示。能够进入该句法槽的动词具有动态性,否则不具备。这样就可以排除属性或关系动词,如:“姓、是、属于、好像、当作、值得、等于、配、显得、以为、认为、算、允许、标志、意味”等。试比较:
(1)结果补语动词:断了、败了、重了、丢了、见了、卷了、变形了,等;
(2)属性或关系动词:*好像了、*以为了、*是了、*等于了、*标志了,等。
由于结果补语动词的动态性较弱,所以用能否进入“在+”的格式检验结果补语动词的动态性强弱,来排除强动态动词。也就是说,能够进入该句法槽的动词都是强动态动词,不能充当结果补语。我们用“在\正\正在+”句法槽的方式排除活动动词、表示复变情状的强动态动词,如“吹、拉、打、跳、听、看、弹、吃、喝、带、抓、爬、闹、散步、探望、提倡、想、思考、考虑、关心、注意、体会、改良、提高、变化、恶化、减少、推翻”等。
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结果补语动词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弱动态状态了,因此没有重叠形式。结果补语谓词不需要再通过重叠的方式弱化其动态性。所以,是否有重叠形式也可以作为判断结果补语谓词动态性特征的一个参考形式。
(二)动词[+他控]性的形式鉴别标准
[+他控]即为动词的非自主性。马庆株(1988)研究了一套完整的动词的“非自主”性的鉴别方法,即用动词单独使用能否构成祈使句及动词前后能否加上“来\去”的方法鉴别。具体为:不能进入以下8种格式中任一格式的动词为非自主动词:①V+(祈使语气);②V+O+(祈使语气);③V+来\去;④V+O+来\去;⑤来\去+V+来\去;⑥来\去+V+O+来\去;⑦来\去+V;⑧来\去+V+O。
将其简化,以能否进入“去+”句法槽构成祁使句作为判断结果补语谓词是否具有“非自主性”的标准,藉此可以排除自主的表示心理活动的弱动态状态词及自主的达成类动词,如“爱、喜欢、恨、轻视、害怕、等、赶、关、逃”等。动词必须同时满足上述三个句法条件才能充当结果补语。下面用图表简要概括三个句法槽的功能:
表1 动词充当结果补语能力的形式鉴别方式
句法槽功能
能够进入“在\正\正在+ ”过滤出活动动词及复变类动词等强动态动词
不能进入“+了”过滤出状态动词(包括属性动词)等静态动词
不能进入“去+”过滤出自主性达成类动词及弱动态状态词
四、结果补语选择动词的总体特征
[+可变]和[+他控]是动词充当结果补语的最基本的语义条件,也是结果补语选择动詞的充要条件。除此之外,充当结果补语的动词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结果补语动词具有双重时间结构
结果补语动词具有双重时间结构,一种是内在的,一种是外在的。外在的时间结构有终点,对动结式的动词所表动作事件起“界化”作用,表明动作事件所表动作的结束;内在的时间结构具有起点,表明动作事件结束后所引起的结果或状态的开始。因此,充当结果补语的谓词必须包含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但是,这两个时间结构的位置却属于不同的层次。或者说,汉语动结式是一个有界的结构,包含着起点和终点,述语动词所表动作有终点,结果补语所表状态有起点,而结果补语的状态不一定有终点。这与当前学界“述语位置的动词包含动作的起点,补语谓词包含动作过程的终点”(徐丹,2000;施春宏,2008)的观点有所不同。结果补语重在表现由动作引起的状态的起始,强调状态的起点。而结果补语谓词的动态性则重在说明结果补语谓词所表状态有“可变”的潜质。但并不能就此认为,结果补语谓词本身包含过程的终点。当单独考察结果补语谓词的特性时发现,由于强调状态的转变,而不是“动作”的变化,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谓词“动性”较弱,具有一定的状态性;这些词必须具备状态变化的起点,并且作为一种实现后的新状态,可能会持续下去,不一定有状态变化的终点。所以,结果补语既可以是持续的也可以是非持续的。具体地说,结果补语谓词具有“界化”作用,标志述语动词所表动作的结束,但并不能表明自身是否蕴含过程的终点。当由动词充当结果补语时,动词本身所蕴含的过程终止,状态起始;当由形容词充当结果补语时,由于形容词本身的动态性弱,状态性强,结果补语表示新状态的实现或新的程度量的实现。但是,该状态或该程度量并不一定结束。
(二)结果补语谓词(包括形容词)在整个词类系统中呈连续统分布
可以看出,“动性”较强的活动动词和完成动词不能充当结果补语,只表静止状态的形容词也不能充当结果补语,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有“动态”特征,又能表示状态起点的谓词才能充当结果补语。“状态”表明一种情况的存在,状态动词则表现为“一种较稳定较恒久的心理或生理状况。”(邓守信,1986:35)如,“喜欢、知道、认识、了解、明白、生气、烫”等词。但状态动词中有一部分词具有弱动态性,也能充当结果补语。因此,从结果补语谓词的时间性特征(动性强弱)的角度看,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在整个词类系统中是连续分布的。
[注 释]
(1)例词右下角的序号为该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所属义项顺序。
[参考文献]
[1]王红旗.动结式述补结构配价研究[A].郑定欧主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5:144167.
[2]王玲玲,何元建.汉语动结结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7071.
[3]陈巧云.动词做结果补语情况探析[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3):3942.
[4]辛永芬.论能够做结果补语的动词[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8789.
[5]刘芬.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词作结果补语的综合考察[D].上海师范大学,2011.
[6]陈平.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J].中國语文,1988(4):152.
[7]邓守信.汉语动词的时间结构[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4):2837.
[8]郭锐.过程和非过程——汉语动词的两种外在时间类型[J].中国语文,1997(3):162175.
[9]郭锐.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J].中国语文,1993(6):410419.
[10]张国宪.“V双+N双”短语的理解因素[J].中国语文,1997(3):176186.
[11]徐丹.动补结构中的上字与下字[A].语法研究和探索(十)[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2120.
[12]杨素英.当代动貌理论与汉语[A].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九)[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1104.
[13]杨素英,黄月圆,王勇.动词情状分类及分类中的问题[A].陆俭明主编.语言学论丛(第39辑)庆祝乔姆斯基教授获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专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78505.
[14]施春宏.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68.
[15]马庆株.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1346.
[16]马婷婷,陈波.结果补语“到”使用的语义条件分析[J].临沂大学学报,2014(3):5558.
[17]马婷婷.结果补语谓词计量统计研究现状[J].文教资料,2016(16):2628.
[18]吴为善,吴怀成.双音述宾结果补语“动结式”初探[J].中国语文,2008(6):498503.
[19]Dowty,D.Towards a Semantic Analysis of Verb Aspect and the English Imperfective progressive[J].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1977(1).
[20]Comrie,B.Aspe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M].1976:49.
[21]Vendler,Z.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责任编辑]李献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