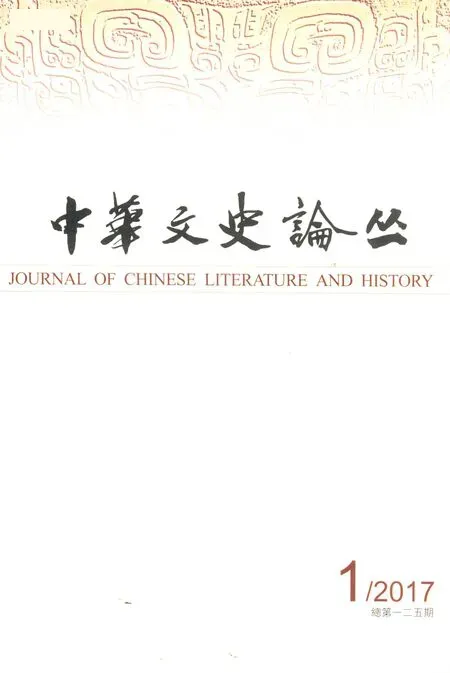“畫諾”問題縱横談
——以長沙漢吴簡牘爲中心
王素
“畫諾”問題縱横談
——以長沙漢吴簡牘爲中心
王素
“畫諾”作爲漢唐長官批閲公文典制,傳世文獻記載甚夥,向無疑義。但由於出土文獻未見明確例證,研究者對其形制並不清楚。長沙走馬樓吴簡和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都見有長官草書批字,該字是否“諾”字,曾引起激烈爭論。直到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出土,見到長官所批規整“諾”字及減省“若”字,“畫諾”之爭纔告一段落。本文回顧相關爭論經過,結合早年高昌郡國公文“畫諾”問題的討論,對“諾”的字形演變及其符號化過程進行了梳理,爲“畫諾”問題討論畫上圓滿句號。
關鍵詞:公文畫諾長沙漢吴簡牘高昌郡國文書諾字符號化
2016年是長沙走馬樓吴簡出土二十周年,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無疑是一項十分重要的紀念工作。曾有專家回顧早期吴簡研究成果,認爲:“其中,胡(平生)、王(素)二氏由於研究視角的差異,文章中的觀點多有商榷,經逐步發展後形成21世紀初學術界一道靚麗風景。”①王琦《十五年來長沙走馬樓吴簡研究進程綜述》,《羣文天地》(半月刊)2012年第2期下,頁191。這裏就以這道“靚麗風景”中的第一個景點——“畫諾”問題,作爲本文縱横談的主題。
一 關於長沙走馬樓吴簡“畫諾”之爭
1996年10月至11月,長沙走馬樓出土一批總數超過十萬枚的三國孫吴紀年簡牘,轟動了國内外。1998年春,主持吴簡發掘工作的宋少華先生發表《大音希聲》文章,介紹吴簡總體情況,首次刊佈一枚後來定名爲《録事掾潘琬白爲考實吏許迪割用餘米事》的木牘圖版,並對該木牘的形制和内容進行了簡略的解説。②宋少華《大音希聲——淺談對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的初步認識》,《中國書法》1998年第1期,頁9(解説),36(圖版)。這枚關於“許迪割米案”的木牘,是一件臨湘侯國録事掾潘琬請求將重新考實“許迪割米案”的結果上報長沙郡府的公文。該公文最特異之處,是左上角有一濃墨草書(圖一)。而我與胡平生先生的爭論,就是圍繞該草書展開的。
1999年5月,我與宋少華、羅新二先生聯名發表介紹吴簡整理工作的文章,談到該公文,特别指出:
該公文左上,有一濃墨草書“若”字。按:“若”即“諾”。《後漢書·黨錮傳序》記汝南太守宗資(南陽人),信任功曹范滂(字孟博),郡人爲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當時太守批閲公文,結束時,照例均需“畫”(即草書)一“諾”字(意思同於今之畫圈),以示知道和通過。説明該公文
還經當時的長沙郡太守看過。①王素、宋少華、羅新《新出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簡介》,《書品》1999年第3期,頁79。林小安在兩篇文章中都談到:“若”與“諾”本爲一字,“若”是“諾”的初文,“諾”是“若”的本義。見《殷契六書研究》(一),《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4;《殷契本義論稿》,《出土文獻研究》第5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10—11。同月,胡平生先生發表吴簡三文書考證的文章,談到該木牘,只説:“在木牘左上部有一草書的‘曹’字,應爲長沙郡有關曹府收到後所批。”没有解釋“批曹”原出什麽典制。②胡平生《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吴簡牘三文書考證》,《文物》1999年第5期,頁48。按:《書品》當時爲雙月刊,單月20日出刊;《文物》爲月刊,每月20日出刊。也就是説,此二文係同一天推出。作爲“畫諾”問題的學術史,從開始時的各説各話,到成爲是“畫諾”還是“批曹”的爭論,無疑算得上是一件趣事。其中,有一場“口頭”爭論不能不提,因爲這是這場“筆頭”爭論的最直接的導火索。

圖一長沙走馬樓吴簡許迪割米案“畫諾”木牘
同年6月,《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的第一卷《嘉禾吏民田家莂》排出校樣。這是長沙吴簡整理組預定9月出版的向國慶五十周年獻禮的首部圖書,參加工作的各單位都十分重視。因爲該卷首附《發掘報告》,主持發掘工作的宋少華先生專程從長沙趕到北京審讀校樣。當時審讀校樣的工作在中國文物研究所(現改名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三樓的會議室進行。《發掘報告》中附有該木牘的圖版和釋文,而釋文中這個濃墨草書是空缺的。我剛進會議室,就聽見文物出版社本書責任編輯蔡敏先生指着該木牘的圖版和釋文,對宋少華先生説:“這麽大的一個草書字,釋文空缺,又無説明,恐怕不妥。”宋少華先生見我進來,就問我:“這是一個什麽字?”我回答:“這是‘若’字,也就是‘畫諾’的‘諾’字。”胡平生先生在一旁聽到,説:“我已經釋出來了,這是個‘曹’字。”我説:“你的釋讀是錯的。”李均明先生走过來,一邊説:“確實是個‘曹’字。”一邊要將《漢代簡牘草字編》翻給我看。我年輕時不僅學過書法,還特别練過章草,知道“曹”的草書怎麽寫,便没等李均明先生把《漢代簡牘草字編》翻開,就説:“不用看了,‘曹’的草書筆畫是往上翻轉的,與這個‘若’字末筆往下折完全不同。”李均明先生翻開《漢代簡牘草字編》一看,果然如此,想了一下,説:“‘曹’的草書筆畫也是可以往下折的。”胡平生先生對宋少華先生説:“《發掘報告》不用我的‘曹’字,也不能用王素先生的‘若’字。”宋少華先生没有辦法,只能在木牘釋文後補加了一行字:“本文書末行上方頂格處另有一草書字。”①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少華、何旭紅執筆)《長沙走馬樓22號井發掘報告》,《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頁33(圖版)、34(釋文)。我感覺:已有正確釋讀,卻要裝着不認識,未免令人遺憾。在此情況下,我纔決定正式撰文談“畫諾”問題。
我撰寫的文章,全面針對胡平生先生前揭吴簡三文書考證的文章,因爲他對吴簡三文書的考證,絶大部分觀點我都是不同意的,而“畫諾”問題不過僅爲其中之一。我在文章中列舉了大量傳世文獻記載的漢唐間各級長官“畫諾”的例證,説明“畫諾”原是一項漢唐間各級長官批閲公文的制度。①王素《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吴簡牘三文書新探》,原載《文物》1999年第9期,收入《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頁163—165。此後不久,胡平生先生寫了三篇文章,在《光明日報》連載,對我的文章進行了全面回應,其中第三篇專門談他釋“曹”的根據,特别説“我和李均明同志都認爲此字應是‘曹’而不是‘若’”,並舉了幾個下部從日的字“也可以寫作向下的折筆”的例證。②胡平生《讀長沙走馬樓簡牘劄記(三)——釋“曹”的根據》,《光明日報》2000年4月21日第3版《歷史週刊》。本文需要先交代前揭“口頭”爭論蓋源於此。因爲如不交代前揭“口頭”爭論,胡平生先生的這篇文章一般人是很難看懂寓意的。又不久,我也寫了三篇文章,在《光明日報》連載,對胡平生先生的文章進行了全面回應,其中第三篇仍是批評他釋“曹”的根據的。③王素《“若”即“諾”可以作爲定論——長沙走馬樓研究辨誤(三)》,《光明日報》2000年8月25日第3版《歷史週刊》;又見《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辨誤》,原載《考古學研究(五):慶祝鄒衡教授七十五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收入《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頁171—172。這場關於“畫諾”和“批曹”的爭論,從“口頭”到“筆頭”,從學術刊物到大衆傳媒,在當時的學術界形成了廣泛的影響,稱之爲“靚麗風景”自不爲過。然則,學術界對這個問題是怎樣看的呢?
第一位支持“畫諾”説的是張小也女士。她現爲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當時在《光明日報》工作,正是發表我與胡平生先生爭論文章的責任編輯。我的三篇文章發表後,她給我寫了一封信,對我糾正該報文章錯誤表示感謝,並稱:這場爭論到此爲止,該報再也不會續發相關文章了。
第二位支持“畫諾”説的是王子今先生。他對該木牘的釋文有不同看法,曾撰文進行商榷,但談到該濃墨草書,説:“最後一行‘若’字批文的釋讀,王素先生所説至確,應理解爲‘諾’。”①王子今《走馬樓許迪雕米事文牘釋讀商榷》,《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頁111。按:關於該木牘釋文的最新成果,參閲王素、宋少華《長沙吴簡〈録事掾潘琬白爲考實吏許迪割用餘米事〉釋文補正》,《文史》2015年第1輯,頁279—282,218。
實際上,在此之後,隨着長沙走馬樓吴簡的不斷整理和公佈,特别是“君教”簡多有“若”字批語,還有由“若”字蜕變爲“雙勾”(W形)的批准符號(另參本文第三節),我的“畫諾”説就已經成爲了定論。值得關注者有二:一是日本學者都支持“畫諾”説。最近的成果,出自伊藤敏雄先生。他引用該木牘,釋文作“若”,或括注“諾”,或解説作“諾”。②伊藤敏雄《長沙吴簡中の生口賣買と“估錢”徵收をめぐって——“白”文書木牘の一例として》,《歷史研究》第50號,2013年,頁100;同作者《長沙吴簡中の〈叩頭死罪白〉文書木牘》(日文),《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頁46—47;《長沙吴簡中的〈叩頭死罪白〉文書木牘》(中文),《魏晉南北朝史的新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一届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頁628—630。二是李均明先生也轉而支持“畫諾”説。他主持整理的《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肆〕,第1289號簡頂格處有一濃墨草書,他釋作“諾”,出注曰:“‘諾’字爲草體濃墨批文。”③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頁159(圖版),652 (釋文)。因此,儘管胡平生先生後來仍在自己編著的《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等書中堅持他的“批曹”觀點,但那已經不重要了。
二 關於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鳳尾諾”之辯
2004年4月至6月,長沙東牌樓出土一批東漢靈帝時期簡牘。這批簡牘的時代雖然較走馬樓吴簡稍早,但内容和典制可以與走馬樓吴簡銜接,故十分重要。其中有一件定名爲《光和六年(183年)李建與精張蟵田自相和從書》的木牘(圖二),末有草書一行,文曰:“九月其廿六日若。”《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在“九月”下注曰:“此二字墨色甚淡,似爲廢字。”在“其廿六日若”下注曰:“此五字爲濃墨草書。最後一字‘若’,字形除末多一捺筆外,與同地所出孫吴簡牘《録事掾潘琬白爲考實吏許迪割用餘米事》所見‘若’幾乎完全相同。而加此捺筆,即爲後世所謂‘鳳尾諾’之一種。”①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王素、劉濤主持整理)《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頁34(彩版二),頁73—74(釋文、注釋)。

圖二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蟵田自相和從書“鳳尾諾”木牘
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正式出版之前,我就曾對該木牘所見“鳳尾諾”做出過解説。首先指出:這個“若”字寫法爲章草。宋高似孫《緯略》卷一〇“鳳尾諾”條云:“齊高帝使江夏郡王學鳳尾,一學便工,帝以玉騏驎賜之。蓋諸侯箋奏,皆批曰:諾。諾字有尾,若鳳焉,蓋花書也。”①高似孫《緯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52册,頁370下。按:此段記載前半原出《南史》卷四三《齊高帝諸子傳下·江夏王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悦,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尾矣。’”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088。又,宋吴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卷一〇“畫諾”條云:“‘若’字有尾婆娑,故謂之鳳尾諾。”②吴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253册,頁898上。明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三“晉·江左十一帝都建康”條云:“晉以後有鳳尾諾,亦出於章草。……按章草變法,‘若’字有尾,故云鳳尾諾。”③陶宗儀《書史會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14册,頁664下。均可爲證。④關於“鳳尾諾”,還可參閲陸龜蒙《甫里先生文集》卷一九《説鳳尾諾》、《文苑英華》卷三六二《説鳳尾諾》,又見《玉海》卷四五《晉鳳尾諾》、《困學紀聞》卷一四《考史》“《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條、《六藝之一録》卷一七〇《古今書體二》,不具注。接着指出:這種有尾的章草“若”,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並非僅此一例,還見於1150號(背)私信、1159號(背)公文、1092號(正)私信,⑤前揭《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頁49(彩版一七,1092號)、61(彩版二九,1150號)、64(彩版三二,1159號)。區别僅在於“鳳尾諾”尾長,其他“若”尾短而已。⑥王素《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選釋》,原載《文物》2005年第12期,收入《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頁153—154。然而,儘管證據十分充分,研究者卻未必都有同感。支持者固然不少,如黎石生、葉玉英、鄔文玲等專家先後撰文,引録該“自相和從書”,均照寫此字爲“若”。⑦黎石生《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李建與精張蟵田自相和從書〉初探》,《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3輯,長沙,嶽麓書社,2006年,頁345—349;葉玉英《東漢簡牘〈和從書〉所見東漢若干制度探索》,《廈門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頁101;鄔文玲《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光和六年自相和從書〉研究》,《南都學壇》2010年第3期,頁11。但質疑者也不乏其人。
裘錫圭先生最早對“鳳尾諾”説進行質疑。他認爲:作“若”之説“難從”,從字形看應是草書的“發”字,最後一行是説“這份文書在九月廿六日打開”。⑧裘錫圭《讀〈長沙東牌樓7號古井(J 7)發掘簡報〉等文小記》,原載《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3期,長沙,嶽麓書社,2 0 0 6年,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 0 1 2年,頁5 2 8—5 2 9。侯旭東先生認爲“此説可從”,稱:“查《簡牘帛書字典》,‘若’字各種寫法中均可見到‘口’或‘口’的變形,與此字形不同;而與‘發’的草書一致。另外,從唐代官府上行文書看,上級官員的批覆雖位於文書的末尾,具體位置較爲自由,但很少見到置於左下角的,東漢時期亦理應如此。長沙出土的走馬樓吴簡J22-2540‘吏許迪割米案’木牘上的‘若’字就是位於左上角,即是一證。”①侯旭東《長沙東牌樓東漢簡〈光和六年蟵田自相和從書〉考釋》,《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2012年,頁247—275。黄樓對吐魯番文書所見北涼解文進行復原與研究,引録該“自相和從書”,直接將“若”寫作“發”。②黄樓《吐魯番文書所見北涼解文的復原及相關問題研究》,《敦煌研究》2016年第3期,頁71。雖然“發”字作爲簡牘文書收發詞語使用不乏其例,③高村武幸《“發(ひら)く”と“發(おく)る”——簡牘の文書送付に關わる語句の理解と關連して》,《古代文化》第60卷第4號,2009年,頁102—119。但用在此處仍讓人感覺有些匪夷所思。首先必須指出,不僅《簡牘帛書字典》,還有《漢代簡牘草字編》,其中“發”字的草書均與此“若”不同,並非質疑者所認爲的“一致”。④陳建貢、徐敏《簡牘帛書字典》,上海書畫出版社重印,1994年,頁567;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年,頁241。其次,也是最重要的,這批簡牘中有四個間架結構相同的“若”字,要是“若”就都是“若”,要是“發”就都是“發”。這應該屬於常識。爲什麽只説一個尾長的“鳳尾諾”之“若”,不管另外三個尾短的非“鳳尾諾”之“若”?我想,原因應該是:尾長的“鳳尾諾”之“若”是孤立的一個字容易解説,尾短的非“鳳尾諾”之“若”在公文和私信中有上下文關聯不容易解説。姑且不論這種回避問題的治學態度是否可取,就是孤立地將尾長的“鳳尾諾”之“若”解釋作“發”,也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有二:
(一)將此“自相和從書”之“若”與“許迪割米案”之“若”進行比較是很不合適的。因爲“許迪割米案”末行“二月十九日戊戌白”的書法與前面正文書法相同,爲同一人所寫,僅“若”字爲草書批字;而“自相和從書”末行“九月其廿六日若”的書法與前面正文書法不同,均爲另一人的草書批語。二者没有可比性。因此,“許迪割米案”之“若”字批語孤懸在木牘左上角是合乎情理的,“自相和從書”之“若”字批語接寫在“九月其廿六日”批文下也是合理的。
(二)當時開啓封檢並不稱“發”而是稱“開”。東牌樓東漢簡牘中有一件定名爲《兼主録掾黄章上太守書》的木牘(1128號),其末行爲草書批文,原釋文作“十月十一日□”。①前揭《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頁53(彩版二一),頁75—76(釋文、注釋)。此“□”不太清晰,又僅此一例,故當時不敢釋讀。但現在可以肯定,是一個“開”字。因爲新出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有一件“永元十五年(103年)府君教”,末行亦爲草書批文,釋文爲“五月九日開”。②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39(彩版),99(掃描版),202—203(釋文、注釋)。前“開”的寫法與此“開”完全相同。這兩個“開”相隔八十年,用法相同,寫法一樣,自然不會是巧合,而應是典制的要求。據此可知,將“自相和從書”之“若”釋作“發”,指開啓,與同時存在的“開”牴牾,是違反典制的。
總之,將“自相和從書”之“若”解釋爲“鳳尾諾”之“若”,是完全没有問題的。近年,李洪財對漢簡草字進行整理與研究,所輯《漢代簡牘草字彙編》,其“若”字條下,將“自相和從書”之“鳳尾若”與前揭1150號(背)私信、1159號(背)公文、1092號(正)私信三個“若”字並列,是很有見地的。③李洪財《漢代簡牘草字彙編》,《漢簡草字整理與研究》下編,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頁17。
三 從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到吐魯番高昌郡國文書
2010年6月至8月,長沙五一廣場出土一批東漢和帝至安帝時期的簡牘。這批簡牘的時代雖然又較東牌樓東漢簡牘稍早,但内容和典制可以與東牌樓東漢簡牘銜接,故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其中有很多“君教”簡,“君教”二字下多有長官所批規整“諾”字(圖三)及減省“若”字(圖四)。①這樣,對於當時存在長官批閲公文的“畫諾”制度,大家終於没有異議了。

圖四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減省“若”字
如本文第一節所説,走馬樓吴簡中也有很多“君教”簡。當時的“君教”之“君”,指的是縣令長或侯相。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説過:東漢三國時期,州郡縣三級長官都有尊稱:州刺史稱使君,郡太守稱府君,縣令長或侯相稱君。他們發佈的告諭稱爲“教”。按:“教”與“令”原爲一詞,統指命令。如《晏子春秋·内篇問上》:“明其教令。”①吴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21。《漢書·文帝紀》十四年(前166)冬條:“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②《漢書》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25。後將“令”作爲諸王與皇后、太子之言的專用語,“教”就只能作爲比他們地位低的“諸侯”的命令的專用語了。③按:《文選》卷三六“教”李善注:“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77年,頁505下。此處“諸侯”主要指地方長官。如縣令長號稱“百里侯”。故姚華在所著《論文後編·目録上》中就“教令”分開使用,推測:“秦法,后及太子稱‘令’,至漢王赦天下,淮南王謝羣公,皆曰‘令’,殆‘令’隆而‘教’殺耶?”④姚華《弗堂類稿》(十五卷本)卷一,據上海,中華書局,1930年影印聚珍仿宋版三十一卷本改編本,頁14。汪桂海先生統計漢代官府往來文書,第二類即爲“教”。⑤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49—51。日本佐藤達郎先生對“教”進行過多方面研究。⑥佐藤達郎《漢六朝期の地方的教令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68卷第4號,2010年,頁575—600;又《魏晉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地方長官の發令“教”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儀禮と刑罰》,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基盤研究(S)“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儀禮と刑罰”研究組織,2011年,頁21—55;又《關於漢魏時代的“教”》,《法律文化研究》第6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58—365。這裏無須贅言。
從文獻記載看,“使君教”較爲少見,但並非没有。《後漢書·傅燮傳》記耿鄙爲涼州刺史,用人不當,燮諫言云:“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⑦《後漢書》卷五八,頁1877。知“使君”應該有“教”。“府君教”很多。《太平廣記》卷三八二“李旦”條引《冥報記》記劉宋李旦死而復蘇事,稱先“有一人將信幡來至牀頭,稱‘府君教’喚旦”云云。①李昉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3043。東漢《張景碑》有“府君教,大守丞印,延熹二年八月十七日甲申起”語;東漢《邛都安斯鄉石表》有“言到日,見草,○行丞事常如掾,○主簿司馬追省,府君教諾”語。②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京都,同朋舍,1994年,頁136,228。《邛都安斯鄉石表》“府君教”下也有“諾”字,值得關注。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有“府君教”已見本文第二節。走馬樓吴簡也有“府君教”(貳·3620),從殘留墨痕看,“府君教”下也應有“諾”字。至於“君教”和“君教諾”,走馬樓吴簡就更多了。
關於走馬樓吴簡“君教”的性質,本文第一節已有交代,日本高村武幸、谷口建速、關尾史郎等先生和徐暢女士也都分别進行過討論,③高村武幸《秦漢地方行政制度と長沙走馬楼吴簡》,日本長沙吴簡研究會報告,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學文教育學部棟8階演習室,2002年10月26日;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楼吴簡にみえる“貸米”と“種粻”——孫吴政權初期における穀物貸與》,《史觀》第162册,2010年,頁43—60;徐暢《走馬樓簡所見孫吴臨湘縣廷列曹設置及曹吏》,《吴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310;關尾史郎《從出土史料看〈教〉——自長沙吴簡到吐魯番文書》,“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一届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2014年10月12—15日;徐暢《釋長沙吴簡“君教”文書牘中的“掾某如曹”》,《簡帛研究》2015(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24—237。這裏無須多説。值得關注的是“君教諾”的“諾”字的變化。當時的郡縣長官,雖然不一定“日理萬機”,但也是事務繁雜,每天要“畫”很多個“諾”字。④《三國志》卷一六《魏書·杜畿附子恕傳》注引《魏略》記孟康爲弘農太守,“郡領吏二百餘人”,而康之工作“事無宿諾”;卷五五《吴書·黄蓋傳》記蓋爲石城縣長,因軍務繁忙,無暇顧及縣務,“乃署兩掾,分主諸曹”,“兩掾所署,事入諾出”。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506,1284。可以窺視當時郡縣長官之忙碌。而規整的繁體“諾”字,左“言”七畫,右“若”九畫,共有十六畫,寫起來很費工夫,如何減省,勢必成爲長官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根據上文介紹,可以看出: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已經存在一個從完整的“諾”向去掉“言”旁單寫“若”字的變化。到了東牌樓東漢簡牘,章草“若”字开始出現,且將下面的“口”字三畫減省爲“乂”字二畫,具備了“鳳尾”的早期形態。這一點極爲重要。而到了走馬樓吴簡,如前揭“許迪割米案”所見,章草“若”字下面的“口”又由“乂”字二畫減省爲“丿”字一畫。不僅如此,幾乎同時,有的章草“若”還減省爲“雙勾”(W形)批准符號(圖五),①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故宫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木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待刊)。開始向符號化方向長足發展。

圖五長沙走馬樓吴簡雙勾“若”字符號
實際上,在我們整理吴簡之前,就有過一場關於“畫諾”問題的討論。這就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業師唐長孺先生領導的“吐魯番文書整理組”,關於吐魯番高昌郡國(327—496年)文書所見“勾勒”是否就是“畫諾”問題的討論。當時,整理組發現,高昌郡國文書中,常見“事諾奉行”、“事諾注簿”、“事諾班示”、“奏諾紀識奉行”等要求長官“畫諾”的用語,卻從未見到長官批覆“畫”的“諾”字,只見到一個大的粗筆“勾勒”符號。②參閲《西涼建初二年(406年?)功曹書佐左謙奏爲以散翟定□補西部平水事》、《殘文書一》,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86,101。不具舉。按:這兩件文書的時代,我曾作考證和調整:前件爲高昌張氏王國建初二年(490),後件爲高昌闞爽政權緣禾四年(435)後。見《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第144、283號,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頁106,142—143。這種“勾勒”符號,與走馬樓吴簡“雙勾”(W形)符號比較,我認爲可以稱爲“單勾”(√形)符號。這些文書均從墓葬出土,且被剪成鞋樣,顯然是經過批覆,最終作廢的文書。整理組認爲:既然要求長官“畫諾”,而經過長官批覆卻未見“諾”字,那麽這個大的粗筆“勾勒”,就一定是符號化了的“諾”字。①按:這場討論,由於缺乏記録,並不爲外界所知。僅唐長孺先生在介紹高昌郡國文書中的“勾勒”時曾説:“有的同志認爲這就是‘畫諾’,也有可能。”見《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縣行政制度》,原載《文物》1978年第6期,收入《唐長孺文集·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359—360。稍後,祝總斌、白須淨真等也就吐魯番高昌郡國文書中的“畫諾”問題發表過見解,不具録。最後,柳洪亮經過研究,正式斷定:“公文上的勾勒,顯然就是太守批閲時畫上去的,等同於‘畫諾’。”見《高昌郡官府文書中所見十六國時期郡府官僚機構的運行機制》,原載《文史》第43輯,中華書局,1997年,後改名《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官僚機構的運行機制——高昌郡府公文研究》,收入《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87。我懷疑:這種“單勾”符號,從左筆昂立似鳳頭、右筆摇曳似鳳尾來看,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鳳尾諾”(圖六)。

圖六吐魯番張氏王國文書單勾“若”字符號
這種定型爲“單勾”形態的“鳳尾諾”,實際上一直延用至今。柳洪亮先生曾經指出:我們今天在現實生活中仍然使用由“諾”字演變的“勾勒”,大自人民法院發佈對罪犯判決的佈告,小到教師批閲學生的作業,都用“勾勒”表示同意和批准。①前揭柳洪亮《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官僚機構的運行機制——高昌郡府公文研究》,頁287。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此外,還有選舉投票、填寫表格等很多需要用“√”形符號表示選擇的事例,也都是漢唐時期“畫諾”的遺留。從追尋“畫諾”符號化“源流”來看:走馬樓吴簡出土之前,我們只找到了“單勾”符號在高昌郡國乃至在今天使用的“流”;走馬樓吴簡出土之後,我們則找到了“單勾”符號的前身“雙勾”符號在三國孫吴時期已經使用的“源”。因此,談到走馬樓吴簡的價值,不能忘記它對“畫諾”問題研究的貢獻。
(本文作者係故宫博物院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