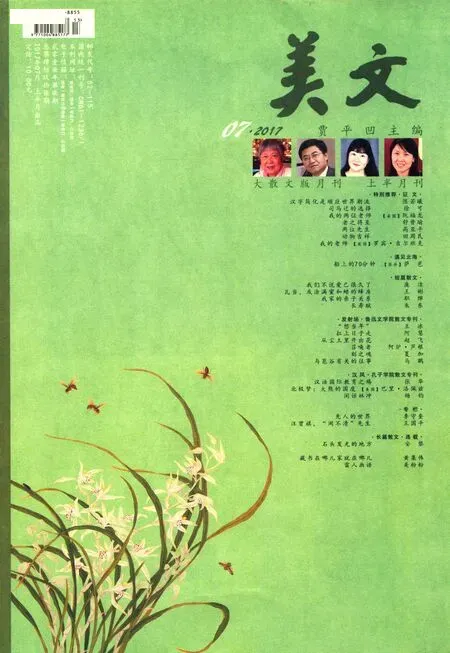石头发光的地方(七)
——回望耀州
◎安黎
·长篇散文·连载·
石头发光的地方(七)——回望耀州
◎安黎

安 黎 男,1962生,出生于陕西耀州,现定居于西安。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散文集《丑陋的牙齿》《我是麻子村村民》《耳旁的风》等。
16
耀州城地处陕西交通中轴线的咽喉地带。从陕北以及更北的塞外南下西安,或从西安北上陕北塞外,耀州为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过客,走累了,走困了,马要吃草,人要吃饭,于是就歇息下来,在耀州城里住上一宿,逛逛店铺,逛逛“窑子”,厌腻了,就去东街看看斗鸡,去西街看看赛狗,去南街看看拳客抡大刀,去北街看看大户门前舞狮子。或者,就去庙里烧香,一遇佛像就跪地磕头。
傍晚时分,是耀州城最热闹的时候,各种杂耍都从小巷的隐蔽处蹦跶到了街面,花样百出地吸引人的眼球,以求得人的施舍。捏泥人的,吹芦笙的,耍猴的,下棋的,卖狗皮膏药的,扭捏卖唱的,等等,这儿叫,那儿吼,这里几声铜锣响,那里一阵鼓点急。一盏盏高悬的汽灯,或挂在一根木桩的顶端,或悬于某株树的树杈,人在微弱的亮光中,像一团模糊的云影在晃来晃去。表演者表演一阵子,便端起摆放在地上的瓷碗,转着圈向围观者讨钱。讨钱开始,人墙松动,围观者后撤。对于一般人,讨钱者并不过度索要,只是走走形式,给不给无所谓。讨钱者为扎场子的领班,走南闯北,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他的眼珠子骨碌一扫,就能大致猜测出在围观者当中,哪些是本地人,哪些是外地人,哪个人兜里有钱,哪个人兜里没钱。面对外地客,讨钱者显得很不客气,他不但拽住他们的衣襟,而且还要从袖筒里抽出一根钢鞭,带有威胁意味地舞动着,以逼迫他们消财免灾。外地人到了异乡的街头,比起在自家的门口来,胆也怯,气也短,腰不硬,腿不直。无奈之下,他们便转过身去,遮遮掩掩地从捆绑的腰带中,取出几文钱来,递给舞鞭者,然后扭身逃窜。对于那些衣着阔绰的人,讨钱者则改变了策略,用祈求代替威逼。领班递来一个眼色,两个或三个女人,就扑通一声,齐刷刷地跪在了某个貌似“老爷”者的面前。身着绸缎,肥头大耳,摇着蒲扇,一副逍遥游的架势,能不是“老爷”?下苦力的,日子紧巴的,能养出那样一身厚墩墩的肥膘?女人们跪在“老爷”面前,除了捣蒜一般地磕头,还嘤嘤地哭,边哭便诉说自己的不幸。这个说她妈去世了,无钱安葬,到目前为止,已在自家的庭院里躺了七七四十九天。妈呀,妈呀,你咋就那么命苦呀?活着吃的是猪狗食,死了竟连张席子都卷不起。另一个说她丈夫是个赌徒,输光了所有的家当,还把她一个宝贝儿子抵押给了别人。为赎回儿子,她才四处流浪卖艺的。她一个女人家,本来脸皮就薄,却被逼成了讨饭的。儿呀,儿呀,你咋就这么倒霉的呀?咋就偏偏遇上了这么一个豺狼爹爹呀……女人们这么一哭一叫,一磕头一伸手,“老爷”挺不住了,便想溜之大吉。但此时的他,不是想逃就能逃走的。他脚跟刚一拧转,女人们便扑上前去,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腿。许多条胳膊,像藤蔓一样紧紧地缠住他,使他欲罢不能。领班对这等状况起初佯装不见,等闹腾了一阵子,才转过身来,以调解者的口吻,打起了圆场,说好我的老爷哩,你能忍心让两个女人给你下跪?跪了,磕头了,哭了,诉说了,你一个有头有脸的老爷,好意思不予赏赐就离开?你还是行行好吧,大大方方地给上她们几两银子,权当少喝了两盅酒,让她们葬埋母亲赎回儿子!人在做,天在看,天有一亏,地有一补,你怕啥呀?你行了善,上天都在账本上给你记着呢,到时候还能不加倍地报偿你?
一番说辞之后,“老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从衣兜里摸出一块铜板来,扔进领班顶住自己下巴的碗里。“老爷”走后,两个女人站起身来,掸掸衣服上的尘土,脸上笑眯眯的,一扫哭诉葬不起母亲和儿子被抵押时“黑云压城城欲摧”般的伤悲。领班觉得差不多了,就收拾摊子,打算回去休息。他们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决然不敢得陇望蜀。“老爷”胆敢一怒,他们恐怕想溜都溜不掉了。
围观者观赏他们的卖唱或耍猴,纯粹是为看热闹,而讨钱讹钱,则宛若一幕戏剧的高潮部分,数人在演,百人在看。事实上,演员事先都进行过模拟演练,每一场演出,不过是按照剧本背诵台词而已。
街头的杂耍,表演者大多不是耀州本地人,而是从外地流窜而来的客户人。这些人一路行走,一路表演,看到哪里相对富裕,人气又旺,便会在哪里多待一些时日,但不会永久驻扎。耀州在渭北一带,算得上是一个人流熙攘之地,于是这些客户人来了去了,不外乎于紧盯耀州人的钱袋打转转。比起这些带有坑蒙性质的谋生伎俩,耀州本地人却显得过于老实本分。他们大多依靠苦力来赚钱,即使涉足商海,也规矩经营,不欺不诈,不缺斤不少两。最重要的是,耀州人的观念普遍很正统。说好听一点,就是只沿着正道走,不受岔路的引诱;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认死理,脑子是榆木疙瘩。
耀州的旅馆业很是兴隆,其客源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商人,一是信徒,一是脚夫。其他如杂耍卖艺的,人数算不上很多,可以忽略不计。乞讨者也不少,但他们不会住客栈,甚至连骡马店的麦草铺也睡不起,而是在富户人家的围墙外,占据个角落,窝着身子,凑凑合合地过夜。对乞讨者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野狼。一到半夜,狼就钻出洞穴,溜进城里寻肉吃。但狼一看见火红的灯笼,就畏缩不前。富户人家几乎家家都要悬挂红灯笼,灯笼一夜不熄,就是为了辟邪和驱狼。乞讨者眠于灯笼之下,相对要安全许多。
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歇息处。比如商人,常常都聚集于各自家乡的会馆里。四川人有蜀馆,安徽人有徽馆,山西人有晋馆,山东人有鲁馆。会馆可能很奢华,一个大院子,前楼后楼的,一派雕梁画栋;也可能很简朴,仅一处小院,几间瓦房。这些会馆,都是由各地商人集资建造的,类似于驻扎当地的“大使馆”。入住其中,说着乡音,吃着家乡饭菜,满目皆是熟人,有一种回到家的温馨感。商人在外,一怕官府找茬,二怕土匪打劫。一群家乡人住在一起,彼此照应着,有个三长两短,人多力量大,集体抱团行动,不像独自面对可能遭遇的危险那样,身单力薄,孤立无援。
并非所有的商人都能在耀州找到自己家乡的会馆。没有会馆的商人该怎样安顿自己?首要的选择,就是“蹭馆”。别人的会馆,自己混迹其中,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人引荐,且引荐者对其知根知底,如此才能避免引狼入室。举例说,河南某人在做某个生意时,和某个山东商人结识,并发展成朋友关系,于是他就去鲁馆蹭馆。经他山东籍朋友的游说,大家基本同意他来下榻,于是他就以缴纳茶水费的名义,支付少量的费用,便可以把自己融入进一群山东人中间。会馆不对外营业,哪怕钱再多,只要不是它的人,都叩不开它的大门——会馆的大门只对自己人敞开。
无馆可蹭,那只好住客栈了。商人们下榻的客栈,条件不知要比骡马店好出多少倍。客栈里除了房间干净,还配有酒肆、茶室以及赌博室等。当然,躲在暗处的女人是免不了的——人与人或许身份不同,但在生理的需求上,并无太大的差异。
客栈里住有很多商人,也住有很多信徒。信徒很多,其来源也很芜杂,远至南洋,近至周边的州县。南洋一带的信徒,去年的十月就从家里出发,今年的三月初,才抵达耀州。他们不远千里万里地来耀州,不过是要去观音菩萨的修身地香山烧一炷香。香山每年过两次会,农历三月十五和农历十月十五,一个春会,一个秋会。春会是正会,比秋会在规模上更宏大,盛况更浓烈,原因在于,春会的日期,恰好是观音菩萨的生日。
耀州境内的香山,从北魏开始就一直香火旺盛,且名声远扬。凡为信徒,都把这座隐于密林深处的山脉视为心目中的圣地,似乎不亲临朝拜,就难以获得修行的圆满。于是他们从各自的家乡结伴出发,络绎不绝地赶往耀州。信徒有男有女,而以女性居多。女性中,又以中老年妇女为主。这些女人,被整个社会视为不祥之物,除了去寺庙,平时总是躲于屋檐下,拘于灶房内,是极少走出家门的。每个女人,自小都接受过一次惨无人道的酷刑,那就是裹脚。不裹脚,非但嫁不出去,沦落为猪嫌狗不爱的剩女,而且还被人指指点点地看不起。
有人调侃说,中国人不但发明了指南针、造纸、火药和印刷术,还有第五大发明,那就是女人裹脚。女人裹脚的确算得上是中国人的一项创举,也独为中国人所拥有。不过,这样的发明,实在是太过恶劣,太过变态,太过耻辱了。它不是中华文化脸上的光泽,而是雀斑。它的出现,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目睹到含情脉脉掩映之下的青面獠牙。
小脚女人尽管行走不便,但千难万险,也阻止不了她们向观音菩萨靠拢的决心。她们有的是从福建海边的某个渔村起程,有的从浙江的某个山坳里出发,有的从陇东的某个荒野里起步,有的从川南的某个山寨走出,背着干粮,挪动着鸡蛋大小的小脚,晃晃悠悠,颤颤巍巍,朝着耀州的方向汇聚而来。她们知道,在耀州,有一座山叫香山;在那座山上,观音菩萨的肉身虽然已经圆寂,但她遗留的仁善之光,弥漫于山林,闪烁于峰巅。
小脚女人们从家里出来,迎风而行,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布囊里的馒头吃光了,随身携带的水也喝干了。饿了,就到沿路的一些寺庙,寻找一口饭吃,或到一些施主的家里寻求施舍;渴了,就在某一条溪流旁,蹲下身去,双手捧起一掬水,吮吸而饮。沿途的虫狼虎豹,时时都在威胁着她们的生命,但她们无所畏惧,因为她们心中有神,坚信神的保佑。观音菩萨,是这些小脚女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灯盏,照亮她们的暗夜,牵引她们的前行。
耀州在哪里?她们不知道。香山在耀州哪里,她们也不知道。她们只是按照大致的方位,依据日月星辰的移动,来确定脚步的方向。
观音菩萨也是女人,可她坐于山巅,供万人朝拜。她们也是女人,却是卑微的女人。她们虽贱若草芥,但依然向往一种高度。她们执着而虔诚地相信,信仰能赋予自己以力量,能给自己带来幸运,能保佑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耀州香山,是她们此行的目的地,也被她们视为灵魂得以升华的圣殿。
香山,同名同姓者甚多。单中国境内,就有八座香山。如果把香山看作同胞兄弟,那么耀州香山,则是兄弟中的老大。有一种说法,说耀州香山是诸多香山的鼻祖,而其他香山,不过是它的分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就昭示着这样一个逻辑关系:耀州香山是总根,其他香山是根须。
耀州香山,年岁最高,资历最老,因寺而兴,因观音而旺。它的盛名,蜚声海内外,其知名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绝对不输于山西的五台山和福建的普陀山。
曾几何时,一到农历三月初,从各省远道而来的香客,就挤爆了耀州城乡。寺院里住不下,就找驿站;驿站没有床位,就打地铺;地铺容纳不了,就叩击信徒的家门;信徒的家里消化不了,人群漫溢而出,流落至大街的屋檐下。街道两旁,店铺墙外,一到夜里,全睡满了从异地而来的香客。
远路上的香客爬上香山,跨进寺门,除了磕头烧香,还要布施。因为路途遥远,他们很难将实物带来,因此,从自己的口袋掏出并塞进布施箱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硬通货。但本地的香客却与之不同,要么吆着一头肥猪,要么赶着一头山羊,要么捉着两只公鸡,要么背着一袋玉米或半袋土豆。这些活物或食物,就是他们将要捐给香山的布施。当地的香客捐献何种东西,是由前一年上山时在神面前的许愿所决定的。许什么样的愿,就还什么样的愿,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出尔反尔。一旦有所偏差失信于神,据传就要遭到报应。神报应人,比人报应蚂蚁还要简单。蚂蚁钻进地缝里,人未必就能找见;但人不论藏于哪里,神都能尾随而至。在闭塞的乡村,人们极其迷信因果报应之说。村庄里或周围村子的某个人,或遭雷击而亡,或被毒蛇咬伤而故,在口口相传中,总是把他的厄运,与去寺庙许愿却不还愿挂起钩来。这样的传说,营造出了一种恐怖的气氛,使任何一个曾对神许过愿的人,都骇然惊悚,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于是送猪送羊,送小米送豆子,送棉花送布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寺庙里的出家者,多达数百之众。一次过会,差不多够这些剃发和尚和削发尼姑吃喝半年,不足的部分,则有赖于大户人家的捐助。
人越是富足,越是胆小,越是睡不着。一无所有的人,牵挂少,恐惧亦少,纵然灾祸突降,丢失的最多只是性命。但大户人家则不然,他们要为粮仓会不会失火而担忧,为埋藏的钱罐是否被贼惦记而惶恐,为孩子能否“学而优则仕”而愁绪满怀,为大老婆小老婆的争风吃醋而身心俱疲,为家庭是否永远保持兴旺而面目憔悴。牵念多了,恐惧也就多了。很多大户人家身穿老虎皮,脖缀着象牙骨,但内心就像浮冰一样脆弱。大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在信佛,且大多都建有家庭式的微型佛堂。即使没有佛堂,也要摆一张桌案,将佛供奉起来。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佛堂里向佛报到,并插上三炷香,说一些求佛保佑之类的话;晚上睡觉之前,也要去佛堂,跪在佛像前,又插上三炷香,并念念有词一番“阿弥陀佛”。其他时间里,则是该收账时收账,该放贷时放贷,想去青楼就去青楼,想去赌场还去赌场。大户们深信,单靠家丁,是不足以保卫家业与保护家人的。家丁最多能抵挡土匪,却无法抗衡命运。而要让命运姹紫嫣红,必须借助于佛的力量。佛高居尘世之上,左右着人,支配着人,人不过是其掌中的浮尘。佛轻嘘一口,人就四处飘散。于是,大户人家不但要和官府搞好关系,还要和佛搞好关系;不但要竭力讨好官府,还要竭力取悦于佛。基于这样的理念,大户人家向香山捐献起财物来,格外地主动和慷慨。他们在神像之前,一许愿,动辄就是十头猪十石麦子。
许愿,源自于心中有愿。有愿望却无法实现,于是就想着假借神之手、神之力、神之能,帮自己实现愿望。许愿者中,有的妻子跑了,遍寻不见;有的养鸡鸡死,养牛牛病,日子过得很不平顺;有的孩子耳聋眼瞎,中药喝了不顶用,偏方服了没作用;有的赌博手气很背,输得很惨,想偷邻居家的银器卖钱还账,不料被邻居扭住了胳膊……凡此种种,都希望万能的神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每逢过会,香山的几个山头,总是人山人海。几口大锅,摆放在中峰的空旷之处,数十个男女信徒,劈柴的劈柴,挑水的挑水,拉风箱的拉风箱,搅勺把的搅勺把,揉面的揉面,一派忙碌的景象。一口一口的大锅冒着蒸汽,一摞一摞的瓷碗堆叠成山,他们要蒸出很多很多的馒头,要擀出很多很多的面条,以满足所有上山者的口腹之需。他们做的饭食,被称作善斋,只要有人伸手,就有馒头和面条递来,且无须缴纳费用。这种善斋,很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产队的大锅饭,谁都可以吃,但油水不大,且场面有些混乱。人太多,又不排队,很容易出现你拥我挤的状况。香客们已经够多了,其他的谋生者还要蜂拥而至。摆抽签摊的,摆测字摊的,卖祭祀用品的,卖字画的,卖古玩的,牵着毛驴驮运人的,赶着牲口送补给的等等,凡进山者,都希冀用善斋喂饱自己。
蹭饭者中,最多的还是乞丐。乞丐们老老少少,一手拄根柳木棍,棍子上绑道白布条,一手端个瓷钵,瓷钵里扔一些钱币做诱饵。柳木棍和瓷钵,是乞丐的行头,犹如清朝时官人戴的顶珠,外人打眼一瞧,不用搭腔,就知道他们是干啥的。乞丐们上山,主要受两样东西的吸引:一是过会期间,香客出手都较为大方;一是有免费的饭菜,不用叫叔叫婶就能吃个肚儿圆。乞丐们乞讨累了,便跑来吃喝,他们围住几口大锅,眼巴巴地盯着将要揭开的锅盖。既然为免费的餐食,那就松开裤带,放开肚皮,端起碗不肯丢手,不吃八个馒头三碗面条,决不罢休。平时干瘪瘪的肠胃,哪能装填得下这么多东西?哪能受得住这等优待?吃不了,就兜着走,但肠胃不听话,兜不住了就闹别扭。一些乞丐蹲着吃饭,吃完后竟然站不起来了;还有一些乞丐突然肚子剧痛,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每年过会完毕,清理丢扔的垃圾时,都能从山上抬下几具乞丐的尸体。这些可怜的人,十之八九,不是被饿死冻死的,而是被吃得撑死的。
香客们对待乞丐是宽容的,宽厚的。他们兜里只要还剩下一个馒头,都要给乞丐掰上一角,因为他们相信,香山上的神灵在俯瞰着他们。佛心怀慈悲,不会嫌弃乞丐的。佛都如此,作为佛的信徒,他们能对乞丐踢一脚或唾一口吗?香客们把对乞丐的施舍,当作积德。付出一文钱,或一角馒头,他们积德的账本上,就会加上一分。倒是乞丐,才不管佛不佛的。他们不信那一套,只关心碗里的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