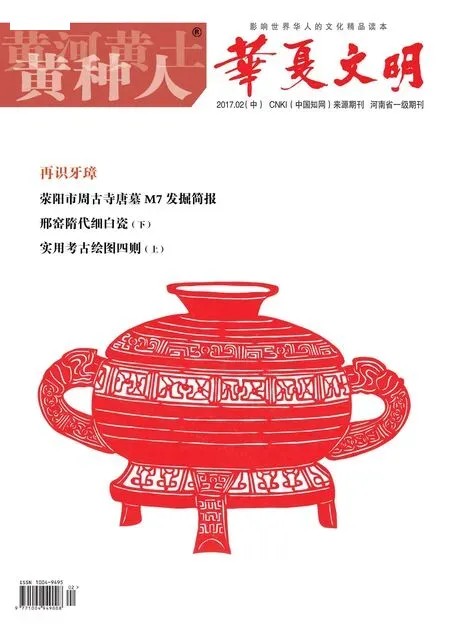北宋汝窑的文化内涵浅析
——以河南博物院藏天蓝釉刻花鹅颈瓶为例
□刘子宁 贺佳琪
北宋汝窑的文化内涵浅析
——以河南博物院藏天蓝釉刻花鹅颈瓶为例
□刘子宁 贺佳琪
在河南博物院的展示厅里,静静地放置着一只天蓝色的北宋时期汝窑瓷瓶,其口径5.8厘米,足径8.4厘米,高19.6厘米,敞口细颈,腹部向外鼓起,造型丰满圆润。瓷瓶自颈部至腹下刻有缠枝莲花,简约的花纹在天蓝釉色的映照下若隐若现。纯净的天蓝色釉通体泻下,犹如湛蓝的天空,莹润的质感使人观之有“似玉非玉胜似玉”的感觉。釉面上的冰裂纹更是浑然天成,古朴之中透出天然之美。它就是被称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的北宋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一、北宋汝窑瓷品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 《历史研究》一书中,说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在谈到自己的愿望时,他竟然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这是为什么?汤因比自有他的道理。
1.宋代的文化积淀
唐代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世逐渐走向衰微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由前期转向后期的起点;而从文化上看,唐朝处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则处在由中唐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成熟期。因此,类型的划分比单纯的朝代划分,更具有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文化中的艺术门类发展到宋代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到奴隶社会的青铜,再到后来的碑刻、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艺术史上人们津津乐道王羲之的 “书换白鹅”,顾恺之的“三绝”,吴道子的“吴带当风”,颜真卿、柳公权的“颜筋柳骨”……都说明一代代才子对文化与艺术的贡献。
特别应提到的是唐诗。唐诗的大繁荣是在封建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思想比较开放,艺术文化普遍高涨的推动下,诗人们继承和发扬《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广泛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结果。它不但说明中国古典诗歌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达到了诗歌艺术的顶峰,同时也意味着文化的理论形成也有了日程表,但唐代尚不足以有此“功力与学养”。不过,唐诗的发展所经历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阶段,历尽盛衰荣辱,使文化备受煎熬。这为后代艺术理论的提炼、使之上升到哲学高度做了充分、必要的准备。
2.宋代文化艺术高屋建瓴:站在历代艺术巨人的肩膀上
北宋时期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这一时期,不仅有处于中国诗词文化巅峰的宋词,而且也有取得非凡成就的金石、书法、绘画等,更有以关、洛之学为代表的宋代理学——这一集大成的哲学体系。说到宋代,总是有人拿宋代“不堪一击”的国防实力来说事,以论之成败。但我们不妨从另一角度想想:“上帝”关上了宋代军事的“门”,却为之打开了艺术高峰的“窗子”。

北宋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已为后代学术名家所公认。当今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
两位学术大师对宋代文化的一致评价,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已达到一个空前繁荣和高度成熟的地步。
3.“天下名瓷汝窑为魁”——文化高地上的艺术明珠
在宋代的文化艺术成就中,汝瓷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北宋五大名窑“汝、钧、官、哥、定”中,汝窑居其首。因汝瓷稀少,李苦禅先生曾言“天下博物馆,无汝(瓷)者,难称尽善尽美也”;在民间,更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件)”之说。
汝窑创烧于北宋晚期,因其窑址在汝州境内(今河南汝州、宝丰一带)得名。以烧制青瓷为特色,有天青、豆青、粉青等品种。汝瓷,为宋代汝窑烧制的青瓷的统称,多为宫廷御用瓷器。金灭北宋后,汝窑也随之消亡。
南宋叶宾《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说明汝窑是受命于宫廷烧造窑器,而且北方青瓷的技术是全国之冠。一位古陶瓷专家推论: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
以前人们往往只把汝瓷归于 “工艺品”,而没有将其视为文化艺术珍品。这显然大大低估了汝瓷的艺术特点与文化成就。
宋徽宗赵佶是北宋历史上第八位皇帝,在位26年。赵佶在艺术上极具天赋,特别是他的书法绘画创作,其成就彪炳千秋。汝窑烧造的时间,在北宋中晚期,有20年左右。按时间推断,大部分是在宋徽宗赵佶亲政的时期,因此跟赵佶的审美有很大的关系。北宋出现“弃定用汝”,可能与赵佶个人的审美观有关。宋代艺术家对理学倡导的“格物致理”有深刻认识和观物察己的真知灼见。艺术家在观照山水自然形态的观念中,其自然精神的价值取向从“物理”的层面引申到精神的层面,即从客体自然再现到主体精神表现的统一。这在汝瓷精品中有完美的体现,让人感受到其具有的气息或气韵是形而上的,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超越视觉精神抽象的气象。因为赵佶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青色的幽玄,正合徽宗之意,“弃定用汝”也正是这种崇尚青色的审美观的反映。由于汝瓷贡器以玛瑙为釉,形成特殊色泽,故有“汁水莹泽,含水欲滴,釉如膏脂溶而不流,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之誉。汝官窑烧制的瓷器,内置玛瑙末,土质细腻,骨胎坚硬,与天一色,含水欲滴,釉带斑斑小点,在光线下观察“七彩纷呈,灿若星辰”。
作为艺术家,赵佶对汝瓷除了有釉色(色彩)的要求外,还有造型、纹饰、材质、肌理的要求……他的这些审美要求,也决定了北宋宫中汝窑用瓷必须符合 “青如天,面如玉,蟹爪纹,晨星稀,芝麻挣钉釉满足”的标准。“青如天”,即釉色如雨过天晴。“面如玉”,即器表有玉石般的质感,釉光莹润如玉。“蟹爪纹”,是指器表的开片犹如蟹爪,呈不规则状交错,且裂纹很细。“晨星稀”是指釉中的气泡稀疏,犹如晨星一般寥寥无几。“芝麻挣钉釉满足”,即满釉裹足、足底部用细如芝麻点小的支钉支撑着烧。汝窑瓷这些胎釉特征,有文献记载,又为出土物所证实,是鉴定汝瓷的要领。由于使用玛瑙末为釉,汝窑瓷会出现文献中所说的有“八种颜色之多”的釉色,有天青、天蓝、豆青、卵青、粉青、月白、虾青、艾青等。其中,最成功的颜色为天青色,最好的为天蓝色。釉色较深似蔚蓝色天空者为天蓝,釉色较淡如雨后初晴的天空者称天青,更淡的似夏夜的皓月者叫月白。粉青则犹如倒映在清澈湖水中的苍穹,在淡青中微带绿色,呈现出一种青绿翡翠交融的迷人光泽。虾青中往往略带黄色。同时,汝官窑青瓷釉还是一种复色釉,这种釉对光极为敏感,在不同的光线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釉色会随光变幻,在暗光下出现清澈湖水般的翠绿色,在明亮时则会看到如雨过天晴的湛蓝天空色,并泛着点点星光,显得流光溢彩。
二、汝窑瓷品反映北宋社会的审美情趣
从宋代理学指导国家思想秩序的角度而言,皇权最高阶层介入艺术领域无疑给山水画创作注入了新的内涵。所以,开国之初即设翰林图画院集天下之画士,并授予官职。宋代皇家权威对艺术形态的直接参与,是中国美术史上绝无仅有的,而把艺术家的身份抬高到授予官职的地位,这对绘画艺术的发展无疑是件幸事。从设置画院、网罗画家、建立规范的考试体制至授官取仕,皇家制定的一系列的制度,无不说明皇家对艺术形的态积极参与和高度重视,这一举措相应提升了社会层面的审美情趣。这也许是北宋成为中国历代 “文化高地”的制度原因。
1.宋初审美与艺术的生活化、休闲化转向
宋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的世俗化、文化的平民化,教育由贵族到平民,艺术由殿堂走向民间。在美学上的反响是,士大夫的审美兴趣呈现出多样化、精致化及世俗化、休闲化的特点。在士大夫审美趣味的背景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美学精神凸显休闲旨趣,追求一种平淡天然的“逸”的境界,一种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闲”的趣味,一种在入世与出尘之间无可无不可的“适”和“隐”的态度,美学更深地融入了生活,表现了休闲的旨趣和境界。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呈现出由汉唐气象向宋元境界的转化。两宋文化艺术在臻于精致、典雅的同时,为平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俗文化也随之兴起,并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这一切都在汝瓷上集中地体现了出来:汝瓷的造型简而精、朴而实。汝瓷胎薄壁坚,无流光溢彩之姿,有淡雅清幽之美,沉实大度、静穆高华、淳朴敦厚、充满神韵。
2.社会审美情趣影响下的北宋文化艺术门类
从北宋诗文革新开始,宋诗更多地开始表现诗人琐细平淡的日常生活(如梅尧臣、苏轼等),注重从这些生活内容中格物穷理、阐发幽微(如邵雍、程颢、朱熹等),由此感喟人生,嘲弄风月。理学奠基人程颢也以“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秋日偶成》)的名句表现在平凡生活中的理趣与闲情。宋代绘画,无论山水、人物还是花鸟,都充满了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审美趣味。最具生活气息的绘画代表作,要算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简直就是把北宋城市生活的一角呈现在画面之上。
可以肯定的是,汝瓷艺术与诗词、绘画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与绘画艺术的联系达到高度的契合:在汝瓷器皿上,不仅彼此之间的艺术融合为一体,在制作时窑工、工匠与诗人或颇有成就的画家之间也有着亲密无间的联系,每件汝瓷珍品上,都凝聚有多人的智慧和汗水。
汝瓷的色泽青如天,面如玉;汝瓷的质感润如肤,堆如脂;汝瓷的开片丝如发,质如金,形似蝉翼纹。这些艺术特色,都与当时的社会审美情趣息息相关。
三、汝窑瓷品中宋代理学思想的内涵
1.理学要旨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而后,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理学直接承继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同时理学思想体系也选择性地吸收了道家、玄学、道教及一些佛教的思想。
理学的主要命题,是研究人在自然天地之间、社会人伦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使命,重视人“与天地参”的自主自觉性。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邵雍《乾坤吟》(《伊川击壤集》卷十七)云:“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谁能天地外,别去觅乾坤?”《自余吟》(同上卷十九)云:“身生天地后,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其余何足言?”周敦颐的“追贤希圣”乃至“跃然与天同一”之学,在他本人身上形成了“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的崇高风范,备受时人仰慕。
2.理学主题与精神在汝瓷上的表现
一个瓷瓶表现的是物质景观,经过适当的艺术处理,融入思想与感悟,物质景观就变成了精神景观。当把一堆泥胎变成精神景观时,就不再侧重它是什么特质,而是通过瓷瓶跟社会、历史、人生、文化,以及整个时代、大自然的沧桑变化联系了起来,特别是融进了当时的主流思想——理学的意念。
包括汝瓷艺术家(我们姑且这样称呼为人类制造出汝瓷这一稀世珍品的人们)在内的宋代艺术家在表现自然与人物的创作中,展示自然生命生存的意义。一大批艺术造诣高深的宫廷和布衣画家,在研究自然形态的过程中“以法致道”,探究“穷理尽性”的理论,并从精神理念的高度使自然物象深入透彻,掌握艺术传承中的精华。这些精神都凝聚在汝瓷的传世精品中,为后人在欣赏中不断感悟。
宋代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的出现,在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把传统的青釉系瓷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青釉系瓷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釉色、造型和装烧方式上,更重要的是,汝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瓷器的审美情趣,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瓷器外部的表现形式,而是更加重视器物内在的韵味,创造了一个审美新境界。这正是理学思想所追求的。
[1]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2期。
[2]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作者单位 河南省实验中学)
[责任编辑 孟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