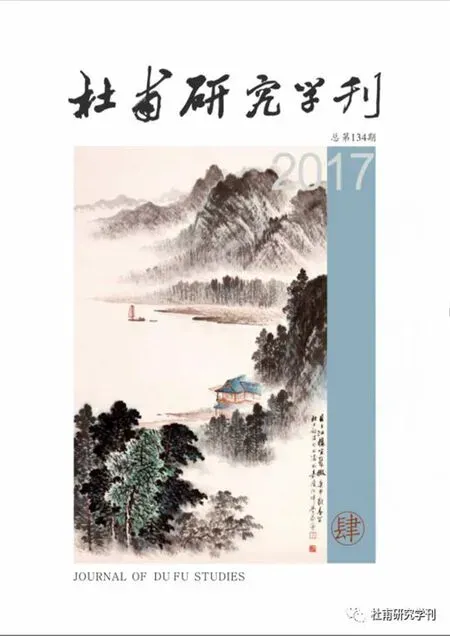杜甫《滕王亭子》诗旨解读
——兼评杨慎对“诗史”的非议及其它
张广成
一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春,杜甫流寓四川阆州,写了《滕王亭子》诗二首。其中一首七律为: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
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
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
人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还。
滕王亭为唐初皇子滕王所建。清钱谦益《钱注杜诗》曰:“滕王亭即元婴所建,在玉台观”。元婴即李元婴,系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爵封滕王。据新旧《唐书》本传载,滕王其人系一骄奢淫逸﹑秽行多端、劣迹昭彰的皇室贵胄。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的好友、成都尹严武奉召离蜀还朝。七月,杜甫陪送严武至绵州,遂依依惜别,意欲折返成都。适值成都少尹兼侍御史徐知道举兵叛乱,“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遂暂为滞栖。杜甫有“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之句,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邵注曰:“三年奔走,谓往来梓、阆之间。”流寓虽则艰辛,诗人杜甫依然具有“处困而亨”“不失山水之乐”的襟怀,期间不乏挥笔描写梓、阆山岳胜迹的诗作,《滕王亭子》诗便是其中之一。
二
关于《滕王亭子》诗,历来对其诗意主旨的诠解,颇有岐义。主要有“美”“刺”之释。
仇兆鳌《杜诗详注》曰:“江石丽而伤心,抚遗迹也。花蕊斑然满目,逢春色也。来不知还,就滕王出牧时言之,讥其佚游无度也。”“末二句,一气读下,正刺其荒游,非颂其遗泽也。”浦起龙《读杜心解》曰:“此为风人之极轨,正始之遗音。”此解可谓“讥刺”之说。
明杨慎《升庵诗话》曰:“杜子美《滕王亭子》诗‘人到于今歌出牧,来到此地不知还。’后人因子美之诗,注者遂谓滕王贤而有遗爱于民”“其恶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称之,所谓‘诗史’者,盖亦不足信乎?”显然,杨慎认为《滕王亭子》诗是赞美颂扬滕王的,此解可谓“美颂”之说。仔细玩味,无论探求微言大义的“讥刺”说或搜瑕求疵的“美颂”说,均有一个相同的解读基点,这就是共同认为此诗的“标的”是滕王,这是解读此诗形成如此牴牾的疏解的要害!
其实,《滕王亭子》诗原本就是杜甫因兵乱流寓梓、阆时,诗人本于“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之诗家天性,以“处困而亨”“不失山水之乐”的情怀和心态,描摹山川胜迹的写景之作;是咏叹春光美景、抒写游人即目所极、秀色可餐而沐浴于大自然之美境中,展现怡然自乐而流连忘返的场景的诗篇。正如当代学者郑文先生在《杜诗管窥》一文中所说:“《滕王亭子》全诗写景,正由景景可爱,故游人乐游之甚,以至忘返,此全诗一贯之意也。”此说可谓切中肯綮!这样,诗中“不知还”者,非指滕王,而是旅人游客群体,当然也包括老杜自己。至于诗名《滕王亭子》,只是一种历史常规承袭的沿用,因亭为滕王始建,故因以命名之,仅仅是一般因承的称谓符号,是亭子这座建筑物外壳式般的称谓,老杜抒写此诗时的情怀,与滕王这个人毫无内在实质性的关联!
此诗作如是观,自然就否定了本诗与滕王的“质”的关系,诚然也就抽掉了“讥刺”说的本事,同时也就消解了“美颂”说的本体。
对于本诗中引起岐义的一些相关干系句义,仇氏把“伤心丽”中之“伤心”按照“悲伤”义项诠解,而郑文先生释义为“好看的要命”。郑说很有见地。如此,则诗句全义当为:江水、奇石绚丽润目得美不胜收。这就冰释了仇氏“抚遗迹”之说强加于诗人与滕王之瓜葛。但郑文先生对于“伤心”不作悲伤释解,言之嫌略。故此,何容先生与笔者曾撰写了《漫话“滕王亭子”美刺之讼——兼释“伤心”一词》一文,对于“伤心”可做“至爱至美”“很爱”“爱怜”“爱的要命”等等义项,作了较详述证,故不赘叙。但对于杨慎“美颂”说及其诟疵“诗史”之见,彼文虽有驳议,但未作深层次疏解;对于杜诗研究中的相关其它涉及问题,犹觉意犹未尽。时至今日,虽为陋识,应一吐为快,故略为文叙之。
三
明代杨慎因杜诗中“人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还”句,而认定杜甫美颂滕王,进而否定杜甫的“诗史”地位。如此惊世骇俗的翻案之论,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杨慎是把诗句中的“歌”,释读为歌颂之义,其实是囿于常套,未必尽然。从“歌”字的原始本义考查:《说文》:“歌,咏也。”《释名》:“人声曰歌,以声吟咏有上下。”《说文系传》徐锴曰:“歌者长引其声。”显然,“歌”字的初义是指声腔节拍的长短抑扬,就是唱的声腔或调子,仅为“载体”,与所唱的内容或抒发的情感毫无关涉,更无论“颂扬”“赞美”。现仅举《诗经》中的篇章为例:《召南·江有汜》“其啸也歌”之“歌”是抒发女子的哀怨;《陈风·墓门》“歌以讽之”的“歌”是一唱三叹,对贵胄的谴责和讥讽;《小雅·白华》“啸歌伤怀”之“歌”是抒发弃妇的怨愤;《大雅·桑柔》:“既作尔歌”之“歌”是芮良夫刺厉王,责其暴政。
于此可见,在古汉语中,“歌”字也具有与赞美、颂扬等相反的讥刺、怨愤等义项。所以“歌出牧”就未见得必是颂扬滕王,反倒也可为仇氏“讥刺”说张本。即在后来,“歌”字的义项有所嬗变,也并未专指“颂扬”“赞美”。迨至唐代,白居易诗“惟歌生民病”句中之“歌”,仅从此单句理解,也是既无讥刺之义,也无颂扬之义,只具有为歌陈述之义。如联接下句“愿得天子知”句,方才显露陈述中约略具有婉转规谏之意。而其《秦中吟·序》曰:“因直歌其事”之“歌”,其义项与上近似。故尔,杨慎以“歌”为颂扬义项,实难成为唯一性诠释。但是,关键还在于“出牧”之指代。
那么“出牧”何所指呢?前面说过,此诗标题为“滕王亭子”,仅仅是“亭子”这一建筑物,差似德·莱辛所言:“对建筑品的赞赏并不一定就是对建筑师的赞赏。”况且,此诗以其为题,仅是因历史的沿袭被如此命名的特定空壳称谓,是一名称符号,与滕王这个人物毫无内在的实质性关联。在此基点上把握全诗,则“出牧”非指滕王,而实为借代仅仅指其所建的“亭子”这座建筑物,“歌出牧”者,实为以此建筑物——亭子托物起兴,作为打头引子,而真正歌咏的内容,当为亭子所处周遭环境的秀美景色,绝非关涉滕王——“出牧”其人!正如诗人杜甫《越王楼歌》“君王旧迹今人赏”句,所言其意极是,今人赏的是“旧迹”,并非“旧迹”的建造者!同理,来游“滕王亭子”此地者(包括诗人),欣赏的是山光水色之自然美景,只此而已。《滕王亭子》诗作如此赏析,则“来游此地不知还”句,当自然承上有所贯通,游人沉浸于春光美景之中,模糊了对时间流逝的关注,以至于流连忘返,方为入情入理。
倘若,来游此地的人们,仅囿于“讥刺”或“美颂”滕王——“歌出牧”,则定然思绪尘杂、形役心累,顿失山水之乐的淳朴情趣,游兴大减,何由亢奋如此而“不知还”呢?如此狂热之态,也绝非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散客”游人在无外力支配下所能为,实在悖逆游人的至情至性!诗人杜甫也不会笔书如此“无厘头”的虚无场景!再说,滕王恶声远播,民非不知,将此恶人牵入游踪,实在大煞风景,何由为之?这样,“不知还”句将何以坐实?只有游人心无旁鹜、沉浸于山水美景之中,“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乃至其“肉体和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方为流连于自然美景之中而“不知还”!
总之,无论是“讥刺”说,还是“美颂”说,都是对此诗的曲解!本来就是一首谱写游山玩水之怡情冶趣的诗篇,却被硬要索引挖掘其意蕴,弄得背上了历史的负重,笔墨聚讼不息,实为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一桩趣事!
四
杨慎是有明一代颇有成就的学者,为什么偏激地以《滕王亭子》这首诗为口舌,否定杜甫的“诗史”地位呢?值得寻踪究考。

首先,“诗史”之称,并非如杨慎所云,是“鄙哉宋人之见”。唐孟棨《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又《新唐书·杜甫传》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足证杜甫“诗史”之号缘于唐代,且足属实至名归!无疑倒是杨慎疏察欠审,草率出论,反之,如清陈僅所言:“升庵博极群书,然不免好奇之过。……则杜撰欺世矣。”

再则,杨慎还不屑地说:“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如果把“诗史”之内涵仅仅界说为只能泛泛的以韵语纪时事,当年缘起“诗史”尊号之“世人”也绝非如此低能和村俗!杨慎如此率尓持论,即或慧目存翳,也或眼中无物!此公委实难脱“英雄欺人”“特好臧贬先辈”之嫌!
杜甫之所以被尊崇为“诗史”,是他的诗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矛盾剧变的一个完整的社会时代断面,高度艺术精湛地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重大历史现实,是一面时代的镜子,且在诗歌苑域达到了前无古人﹑炉火纯青的境界,在我国古典诗史上成就了一座令人仰望赞绝地巍巍高峰!《新唐书》本传《赞》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注意!“善陈时事”,就绝非普通人所能为的“纪时事”﹔“律切精深”也更非是常人所能作的普通“韵语”。《赞》又曰:“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唐元稹也赞曰:“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如此精当之论,杨慎何以漠然视之,硬要“执一格,囿一偏”“为通人所不取乎”!

杨慎不喜宋人说,从而持否定“诗史”之论,更进而在杜诗中爬梳寻疵,怀着“疑罪从有”的心态,以己对杜诗的错解,以“类于讪讦”“以韵语纪时事”等出格不逊之语贬辱杜诗,力图为否定“诗史”之论张本,实在有失学者大家风范!倒是清人吴乔一语中的地指出:“用修不喜宋人之说,并‘诗史’非之,误也。”不喜宋人说,就玷辱杜甫,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且宋人在杜诗的整理辑集、疏解诠释、付梓刊播,以及对杜甫的慧眼定位和高度认知,都是举世皆知、成绩斐然而功不可没!何可谓宋人“不可论诗”“鄙哉”之有?杨慎倒可反观于己、审视考量,其狂异之论,实难为训!
五
其实《滕王亭子》诗,也并非是杜甫诗作中的上乘代表篇章,居然引发“讥刺”和“美颂’两种对立的赏析及评论。表象察之,也无非是关于一首诗的疏解和释读,无关宏旨,实则未必如此。其中投射出了对杜诗整体评价的基点的偏视和成见。即是“讥刺”或“美颂”都是由于以“诗史”为旨归,无论肯定或否定。
历来,对于杜诗整体的认识和评价,存在着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弊端,以为杜甫是“诗史”,其诗就应该首首有来历,句句有所指,杜公举首张目必是“满目疮痍”,展卷挥毫定然“笔底波澜”,非“刺”即“颂”,岂有它哉!显而易见,“粘着一事,明白断案,此史论,非诗格也。”因而,倘若“注杜者全以唐史附会分笺,甚属可笑”“句句附会实事,殊失诗人温厚之旨,窃恐老杜不若是也。”前人此论,言简意赅,足可令人反思和深省!
究其弊端之源,在于我们如何把握对“诗史”这一尊号内涵的定位、认知、理解和运用。下面掠美于蒋寅先生《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一书中的一些论断,夹以自己的粗浅理解,予以阐述。
其实,“诗史”的涵括界量是有边际限度的,其意义绝不能被无限放大、极度强化和曲解。“诗史”是就杜甫一些诗作艺术的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和深刻性而言,“诗史”也只有在这一层面上才有鲜活真实的意义!故尔,诗的本质功能和价值并不是一丝不苟地记录和实述历史,否则,就会“从诗与史的一致性出发,作出一些世间最粗疏的结论来。”因此,我们不能把真实的反映历史作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和最高价值判断标准,不能以史定诗。钱锺书先生说:“‘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也就是说,诗绝非是史的附庸!
显然,杜诗之所以伟大辉煌而不朽,绝非仅仅是能以诗写史或诗中蕴史为旨归。对此,一些学术大家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究和阐述,诸如,梁启超大师说因为诗人杜甫是“笃情圣手”、是“情圣”;许思源先生说因为杜诗最能表现中华民族“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民族感情;袁行霈先生说因为表现了诗人崇高人格的成长和诗人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如此等等。
综上,诸说纷纭,可继续探研。但认定用“诗史”来一味推崇和定位杜诗确乎有失偏颇而不尽人意、实有探骊未得珠之憾,当是共识。如此,无疑对杜诗作出更符合文学、美学、诗学规律的本质揭示和阐释,是有启迪之益的!
六
上述表叙,并非要对杜甫的“诗史”地位有所质疑和否定,仅是对“诗史”这一尊号的外延和内涵予以廓清、界定和净化,以免过分拘泥固守、无限放大,以致误导我们以为只有真实的反映历史,才是诗歌唯一的至高的鉴赏、判断标准;而要遵循文学的艺术和美学特质及规律,视诗歌作为一门独立艺术,应予以诗性本体回归的认定,多角度多元化的给予评价和解读。而杨慎恰恰是既要否定“诗史”(“六经各有体”反对以史入诗或以诗写史),又反以其为标准对杜甫诗作爬梳寻疵(鄙薄“以韵语纪时事”),导致陷入谬误的泥淖而作出了谬误的持论!
诗人杜甫,究其本质他首先是一位自然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尔后方为一位诗人,一位才情横溢、卓迈亘古的伟大诗人。故尔,他兼有人之真性和诗人天才的情怀,所以方能以“喜怒哀乐,亦心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为旨归,以其为至人的崇高操守、其为至情的博大胸怀、其为至性的纯真禀赋、其为至文的卓绝诗才,以自然、社会缤纷之万象滋润着自己的诗笔,纯朴率真地抒写着妙幻的自然、万象的社会,也抒写着自己的人生。惟其如此,诗人杜甫方能成就其为“诗圣”!为人类留下“高、大、深俱不可及”的宏伟篇章!

其实,关于杜甫的山水诗,前人也有所注视和评价。清朱庭珍《筱园诗话》曰:“山水诗,以大谢老杜为宗。”大谢当指东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又谓“康乐善游,精于独造,其写山水诸作,千秋绝调。”而“永嘉山水奇丽,康乐诗境肖之;西蜀山川雄险,工部诗境肖之。”“所以山水诗,以大谢、老杜为宗。”将杜甫与谢灵运并宗,可见杜甫山水诗的成就和地位!清陈僅《竹林答问》曰:“游山水者,秦、蜀诗学杜老。”可以予人为学山水诗作之法,足见杜甫山水诗非同凡响、岂可忽觑!基脉于山水诗的天才禀赋和深厚功力,杜甫的山水题画诗,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等诗篇都可谓是出神入化的佳作!对于杜甫的山水题画诗作,前人曾推崇备至。宋许顗曰:“画山水诗,少陵数首后,无人可继者。惟荆公《观燕公山水诗》前六句差近之,东坡《烟江叠嶂图》一诗,亦差近之。”宋胡仔曰:“少陵题画山水数诗,其间古风二篇尤为超绝。”其诸篇积思独造,遂为此体之祖!

在诗人杜甫流寓梓州、阆州期间,颠沛凄惶,生计苦踬,但依然正如明张綖所言:“公当远离之时,而不失山水之乐,亦足见其处困而亨矣。”这恰恰是诗人不为俗累而持续着诗情的超凡特质和痴情于家国山川的本色。清沈德潜曰:“诗人不遇江山,则虽有灵秀之心,俊伟之笔,而孑然独处,寂无见闻,何由激发心胸,一吐其堆阜灏瀚之气。”德国诗人席勒说过:“自然仍然是燃烧和温暖诗人灵魂的唯一火焰。”诗人杜甫,正是以此“生命灌溉”而葆有经久不衰的诗情,谱写着辉耀千古的卓越诗篇!
诗人杜甫在梓、阆期间,除了《滕王亭子》外,委实也留下了一些颇有特色的山水写景诗篇,诸如《牛头寺》《阆山歌》《阆水歌》《越王楼歌》《涪城县香积寺官阁》《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等等,这些诗作,艺术成熟,独具特色,表明杜甫山水诗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其特色在于“纯然是梓州阆州的山水图,我们不但由此看得出那些山川的特殊的形势,而且好像还感到它们的色彩和声音。有如当年吴道玄在长安大同殿的壁上画嘉陵江边三百里的风景一般,杜甫也用他的诗笔勾画出一幅川北百里图。”诗作能绘形、绘色、绘声、绘神如此,且与‘画圣’吴道子的山水丹青相媲美,杜甫也确为山水诗作巨匠!
总之,《滕王亭子》这首七言诗作,的的确确就是诗人杜甫“处困而亨”“不失山水之乐”的一首游览山水、现场即景的抒发其怡情乐趣之作。现据其诗意仅以现代语词迻绎于下:
滕王亭子座落于巴山之峦,拾级栈梯尚可登临攀援。
春光明媚,竹林里莺啼不断,犬声远传,白云深处的人家恍若仙境一般。
江水清澈,怪石嶙峋,美丽悦目的景色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山花遍野,生机盎然,万紫千红映入眼帘。
游人如织,歌唱着这旖旎的风光,其乐无边,沉浸于融融春景中,怡然自乐而流连忘返!
平心而论,《滕王亭子》诗在杜甫诸多山水诗作中也非上乘的代表作,就此居然引起了“美”“刺”之讼争,且涉及到‘诗史’称号的一些相关问题,故率尔为文,琐议冗论,略陈固陋于上,望方家赐教。
注释
:①(清)钱谦益:《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47页。
②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万卷出版公司 , 2015年,第169页。
③④(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340页、第1136-1137页。
⑤(清)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77年,第631页。
⑥(明)杨慎:《升庵诗话》,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二),齐鲁书社,2005年,第1056页。以下见于此书者不再出注。
⑦张广成:《漫话“滕王亭子”美刺之讼——兼释“伤心”一词》,《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1期。
⑧朱光潜译:《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5页。
⑨(明)王世贞著、陆洁栋,周明初批注:《艺苑卮言》,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43页。以下见于此书者不再出注。






——评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研究》
——以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辑录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