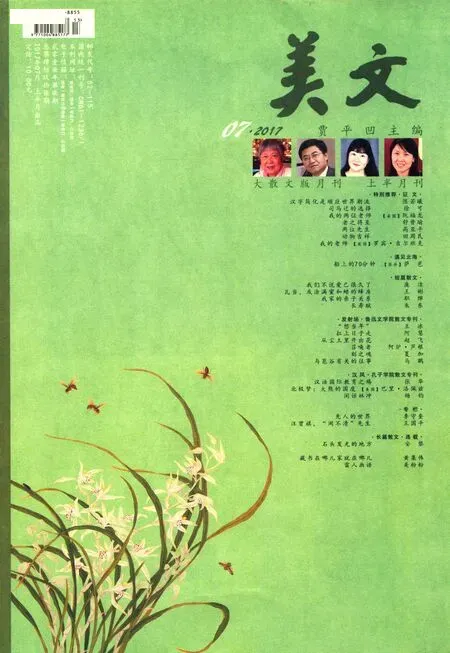汪曾祺,“闹不清”先生
◎ 王国平
汪曾祺,“闹不清”先生
◎ 王国平
王国平 江西九江人,供职于光明日报社。著有报告文学 《一枚铺路的石子》、人物传记合集 《纵使负累也轻盈》,曾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中国报纸副刊学会年度银奖等。
一问三不知。
这怎么行?
《论语·公冶长》,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这个当老师的,闲来无事,就找点事,让子贡自我评估,你跟颜回,哪一个要更厉害一点?
这一问,子贡不仅回答了,而且还颇为得体:“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知二。”
闻一知十,自是高人。闻一知二,也不错。凡夫俗人,闻一知一,足矣。
不管怎么说,先要“闻”,才有“知”。
哪能不闻不问、不思不想、不清不楚?
有这样的人么?
有的。有请汪曾祺先生!
《藻鉴堂》,这是颐和园西边的一个偏僻去处,汪曾祺跟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歌剧《江姐》作者阎肃,在这里住过一阵,闭关弄剧本。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里曾经圈禁过一个亲王,“我于清史太无知,把亲王的名字忘记了”。
《玉渊潭的传说》,写的是北京一个公园的事。如今这里春季怒放樱花,京城早春一景。他听老人们讲,玉渊潭原本是私人的产业,是张家的,“他们把这个姓张的名字叫得很真凿,我曾经记住,后来忘了”。
《罗汉》,例举了自己中意的彩塑罗汉,有一处就在泰山后山的宝善寺。后边缀上一个括号,内容是“寺名可能记得不准确”。
岁月不饶人,记性跟不上,只好作罢。
《沙岭子》,写“我”下放劳动的事儿。真的是劳动,“大部分农活我差不多都干过”,还在果园喷波尔多液,画《中国马铃薯图谱》。1983年,故地重游,走访了工作过的地方,见了一些人,知道了一些事。文章尾部总结:“重回沙岭子,我似乎有些感触,又似乎没有。这不是我所记忆、我所怀念的沙岭子,也不是我所希望的沙岭子。”但所希望的沙岭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也说不出”。
要我说,道理很朴素,相见不如怀念。
《戴车匠》,对车床的运行原理描述了一番,又说这是用语言说不清楚的,“《天工开物》之类的书上也许有车床的图,我没有查过”。
幸亏是写小说,要是搞研究,这态度可不行。
《老董》,这是“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相识的一位工友,他平常的工作就是掸办公室的尘土,拔拔石缝中的草。老董说北京的熬白菜比别处好吃,因为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没有考查出来”。
《塞下人物记·俩老头》,有个耿老头,唱过二人台,艺名骆驼旦。“骆驼”和“旦”怎么能联系在一起?也许他小名叫骆驼?汪曾祺坦白:“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楚。”
《故里三陈·陈四》,说“我们那个城里”有迎神赛会。所迎的神,有“都土地”,地位相当于一个区长。“我”所居住的东城,“都土地”是唐代名将张巡。张巡为何会到这里来当“都土地”?他又不是战死在这里的,“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弄明白”。
再说张巡是太守,死后为什么倒降职成了区长了呢?“我也不明白”。而且“都土地”还被称为“都天菩萨”,这是怎么来的?“这一点我也不明白”。
疑惑一个接着一个,在脑海中盘旋。劳神费力。老爷子真是辛苦了。
《我和民间文学》,老爷子对民间文学的妙处做了述说。不过,要问他从民间文学那里得到了什么具体的益处,“这不好回答”。
《鸡毛》,西南联大新校舍里住着一位文嫂,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这些学生中有个金昌焕,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把鸡毛藏在床下,一声不吭,了无痕迹。直至毕业了,文嫂替他打扫宿舍才大白天下,“他怎么偷的鸡,怎么宰了,怎样褪的鸡毛,谁都无从想象”。
《侯银匠》:“银匠店出租花轿,不知是一个什么道理。”
《夏天的昆虫》,说家乡有一种蜻蜓,大家都称之为灶王爷的马,“不知道什么道理”。
《故乡的食物》,说小时候一到下雪天,家里就喝咸菜汤,“不知什么道理”。
还是这篇,说昂嗤鱼,背上有一根尖锐的硬骨刺,用手捏起这根骨刺,就发出昂嗤昂嗤小小的声音。这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我一直没弄明白”。
没弄明白的事还有不少。
《大淖记事》开篇,说这地名很怪。“淖”字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而且全县的地名用这个“淖”字也是独一份。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至于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什么,“就无从查考了”。
《小姨娘》,章叔芳为了爱情,与家里决裂了,后来又和好了。战乱年代,家人变卖田地,到南洋发财,“他们是否把章叔芳也接到南洋去了呢?没听说”。同是校花的胡增淑的命运,听说过一些,但不清晰、不完整,“后来不知怎么样了”。
《职业》,巷子里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一个孩子,眼看着长大起来了,叫卖的声音也变了,可以听得出一点嘲讽、委屈、疲倦,或者还有寂寞,混在一起的东西,“种种说不清”。
《异秉》,王二的熏烧摊子,为何要摆在保全堂药店的廊檐下?“都说不清”。
《小学同学》,说之所以记得王居,主要是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玩,但要细说有什么好玩的,“说不出个道理”。至于他初中毕业后,是否升学读了高中呢?“我就不清楚了”。
《笔记小说两篇·捡烂纸的老头》,这个老头穿戴不齐整,烂棉袄油乎乎,腰里系着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多大岁数?说不清。六十岁?七十几岁?
《风景》,“我以为坛子里烧的肉根本没有什么道理”。一众朋友想去东福居打牙祭,补充营养,唯独他投了反对票。原因是自从注意上了那儿的一个堂倌,就不想再迈进那个门了。“也许现在我之对坛子肉失去兴趣与那个堂倌多少有点关系。这我自己也闹不清”。
《道士二题》,说这个叫五坛的道观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医生请五坛道士去给父亲亡魂超度。法事进行中,经案上的烛火忽然变成蓝色,而且烛焰倾向一边,经案前的桌帷无风自起。这是异象。法事结束,道士问医生:令尊是怎么死的?医生问道士看到了什么。答:一个人身着罪衣,一路打滚,滚出桌帷。医生只得实话实说:父亲犯了罪,在充军路上,被解差乱棍打死。
汪曾祺说这故事让他很不舒服,“为什么使我不舒服,我也说不清”。
左思右想,也探不到底,反而跌入雾中。还不如不思不想。干脆,不知道。
《昆虫备忘录》,提及一种硬甲壳虫,是个大力士,被唤名“独角牛”,你要问学名叫什么,“不知道”。
《泡茶馆》:“昆明的茶馆分几类,我不知道。”
《年红灯》,说走到室外,总要抬头看看,“为甚么要看看呢?看甚么?——不知道”。
《塞下人物记·陈银娃》,说片石山就是采石场。那本地人为何都叫它片石山呢?“不知道”。
《八千岁》,说当地把不讲理的人叫作“舅舅”,他们讲着胡搅蛮缠的歪理,这就是“讲舅舅理”。为何对舅舅这么有意见?“不知道”。
《礼俗大全》,说孙小辫请名士宣瘦梅教全家男女老少背一篇东西,文体很怪异,说古文不是古文,说诗词不是诗词,说道情不是道情,不俗不雅,不文不白,“这算是什么东西呢?是谁的作品?不知道”。是孙小辫的思想,还是宣瘦梅的?“不知道”。
《草巷口》,说老家有个普通的巷子,用砖铺的,这个巷子和别的巷子不同之处在于,巷口嵌了一个相当大的旧麻石磨盘,“这是为了省砖,废物利用,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文末,说再往北还零零落落有几户人家,要问这几户人家都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
《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说詹大胖子是县立第五小学的斋夫,也就是后来的校工、工友。至于“斋夫”什么时候废除的,“谁也不知道”。
《昙花、鹤和鬼火》,李小龙上学要路过傅公桥。为何叫这个名字?傅公到底是谁?“谁也不知道”。
《日规》,说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蔡德惠做了一个很简单、很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为了好玩,增加一点生活情趣,这是否也表达了“寸阴必惜”的意思,“那就不知道了”。
《星期天》,有位史先生,是首饰店学徒出身,“至于他怎么由一个首饰店的学徒变成了一个教史地的中学教员,那谁知道呢”。还颇有所指地捎带提一句,“上海的许多事情,都是蛮难讲的”。
《三圣庵》,这里住了一个风流和尚铁桥,相貌堂堂,双目有光,会写字,会画画,有相好的女人,跟俗家人称兄道弟。小说《受戒》里的和尚石桥,就是以他为原型的。笔走至此,另起一段,汪曾祺写道:“高邮解放,铁桥被枪毙了,什么罪行,没有什么人知道。”
近期水库溃坝率较低,反映了强化水库防汛负责制与安全管理责任制的作用。但仍有部分小型水库溃坝的现实也反映出存在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管理不到位,工程质量差,或防洪标准不能满足要求,技术认识不到位。更深层次上反映的是小型水库产权、管理权不清、管理模式僵化、工作不实的问题。
从三圣庵回到五坛道观。
说这个道观,正名是“五五社”,坛的大门匾上刻着这三个字,但大家习惯了叫“五坛”。为什么要这么叫?“不知道”。
进一步说,“也许这和‘太极’‘无极’有一点什么关系,不知道”。
还要补上一句,“我小时候不知道,现在也还是不知道”。
有点躁了。
歌唱:“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
都叫喊了起来。
《牙疼》,说“我”就要离开云南,只身前往上海了,S则回福建省亲。上海既不是老家,而且与生活了七年的昆明大不同。那为何要到上海?
“你问我,我问谁去!”
嚯!还挺横的。这位同志,这是什么态度?这可有点不讲理,你说是不是?
转念一想,牙疼缠绕了半年,又要离开落下满满回忆的春城,紧要的是眼瞅着要跟女友S小别,一身子的感伤,也就原谅他了。
《历史》中的童阿杏,不识字,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她到处做报告,事先有画家把她想说的意思画出来,所以她的讲稿很特别,都是小人、小鸟、小河、小桥之类。
汪曾祺问:“具体的东西好画,抽象的概念怎么画呀?”
汪曾祺答:“我也不知道!”
竟然是个叹号!没见过的,不知道的事,还这么理直气壮!
…………
这么一条一条地连缀起来,不由得想起萧红《呼兰河传》的结尾: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就着记忆开中药铺,一一列举出来,感觉很详尽了,但没有一项是稳定、可靠的,是可以坐实的。“这是一个除了‘无’之外一无所有的世界。”《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6年第10期刊发论文《“潜能”、动物与死亡——重读萧红〈生死场〉》,作者王钦说。
这就怪了。按道理,作家的能耐就是“无中生有”。有个说法,作家是自己文学世界里的国王,“皇上的旨,将军的令——一口说了算”。也就是说,作家应该是全知全能的,就像现在的高清摄影,形成“技术俯视”,领着读者更加清晰明了地“看见”过去、现在和未来。怎么能动不动就不知道呢?还这么大面积的不知道。
萧红是在着力营造一个纯粹而又无望的世界。就汪曾祺来说,有些事,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知为不知”。这不是露馅,也不必藏拙。世界广袤无垠,世事错综如麻,哪能总是三下五除二般爽利干脆,水一落,石就出?更不可能像是打了鸡血,亢奋异常,以为真理在握,所向披靡,铿锵铿锵。
王蒙说,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般一清二白,皆不可信。
汪曾祺说,不能像《阿诗玛》里所说的那样:吃饭,饭进到肉里;喝水,水进了血里。
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因为底气不足、信心不满。21岁时,他写有《匹夫》,其中有这么一句:“我派定他姓荀,得他姓荀了。我居然能随便派定人家姓氏,这不免是太大的恣意。”
姓荀就姓荀了!怎么着吧!
磨磨叽叽,受不了!
——1948年11月30日,他在给老友黄裳的信中写道,自己到了北平,买了一包“中国烟丝”,囤积了“华芳”牌。感觉这在北平是很奢侈的事,每抽上一口,颇有些不安,“婆婆妈妈性情亦难改去也”。
挺有自知之明的。
还得承认,有些事,原本是应该知道的,但故意说不知道,属于艺术处理。
《小学同学》,写了个叫徐守廉的,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子承父业,在棺材店里学手艺。“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事,“为什么不好呢?我也说不出来”。
“汪曾祺或许认为以徐守廉的聪慧,将来必可大有作为,在村镇里当一名棺材匠,简直是把他埋没了。但是作者没有把这些话写出来,只是让文中那股淡淡的忧伤来感动读者。”方星霞在《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中是这么分析的。
不过也只是揣摩,“或许”而已。
歌唱:“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作家的心思怎么猜得着?
不过,有些事,想想法子还是可以“闹得清”的。比如,《我的家乡》,汪曾祺说高邮为秦代始建,故又名秦邮。外地人或以为这跟秦少游有什么关系,“没有”。
很干脆,不含糊。
但这算是特例。多数时候,还是懒汉持家,真心不想往深处探路,用不上,也犯不着,没有多大的必要,干吗要较哪个劲,吃饱了撑的,人生苦短,难得糊涂,姑且这般,你说怎么着,何必呢,井水犯了河水,河水也犯了井水,哪是井水,哪是河水,傻傻分不清楚,就这样了吧,爱谁谁。
“?”,为何总是想着要拉直,成一个“!”?就不要用蛮力、用巧劲了,人家好好的,干吗要大动干戈?
依照汪曾祺的性情,恨不得蹲下身,闲聊起来:小问号同志,今年多大了?
《紫薇》,白居易有诗云:“紫薇花对紫薇郎。”紫薇郎是唐代官名,即中书侍郎。这句诗,使人觉得有点罗曼蒂克,汪曾祺说,“其实没有”,如果还是产生了一点罗曼蒂克的联想,怎么办?汪曾祺的态度是,“也可以”。
不拦着。
《〈茱萸集〉题记》,说他取茱萸为集名时,脑袋里想着的是“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有点儿怀旧的情绪,但这和小说内容没有直接关联。不过,如果读者于此有所会心,“自也不妨”。
悉听尊便。
这个态度在汪曾祺这里是渊源有自的。
1940年的小说处女作《钓》,讲了一个传奇故事。说有个画画的,“画个麻雀就会叫,画个乌龟就能爬,画个人,管少不了脸上一粒麻子”。临死时,画了一张画,交给新娶的媳妇,让她到城里交给他的师傅,再送到京城的相爷家,如期送到,必有重赏,小媳妇一辈子的生活费不用愁了。关键是事前不要拆了。媳妇好奇心重,途中没有憋住,拆开看了,不过是一片浓墨,当中有一块白的。一阵大风,把画儿吹到了河里。原来是一轮月亮。从此这月亮便不分日夜地在深蓝的水里放着凄冷的银光。
“你好意思追问现在为甚么没有了?看前面那块石碑,三个斑驳的朱字‘晓月津’,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儿。”汪曾祺自问自答,温静平和。
《天山行色·伊犁河》,说伊犁一带有不少关于林则徐的传说,有的不一定可靠。惠远城东的一个村边,有四棵大青枫树,传说是林则徐手植的。这大概也是附会。林则徐为何要跑到这样一个村边来种四棵树呢?
难道那时的人也有植树的义务?
想多了。人家汪曾祺就很淡定:
“人们愿意相信,就让他相信吧。”
又说:“这样一个人,是值得大家怀念的。”
《苏三、宋士杰和穆桂英》,他听说洪洞县曾经禁演《玉堂春》,因为戏里有一句“洪洞县内无好人”。有人著文考证,苏三根本不是历史人物,故事是小说家编造的,关于苏三的遗迹也是附会。
汪曾祺觉得,洪洞县的人和有考据癖的先生都很可爱,“何必那样认真呢?”
规劝的姿态。
潜台词是:“你好意思追问是假还是真?”
桐庐有个严子陵钓台,在山顶上。
这怎么钓鱼?
各种考证,各种说法,不亦乐乎。
这回,老爷子有点恼了,“我的我要爆了”,摆出上阵“约架”的姿势:
死乞白赖地说这里根本不是严子陵钓台,或者死乞白赖地去考证严子陵到底在哪里垂钓,这两种人都是“傻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