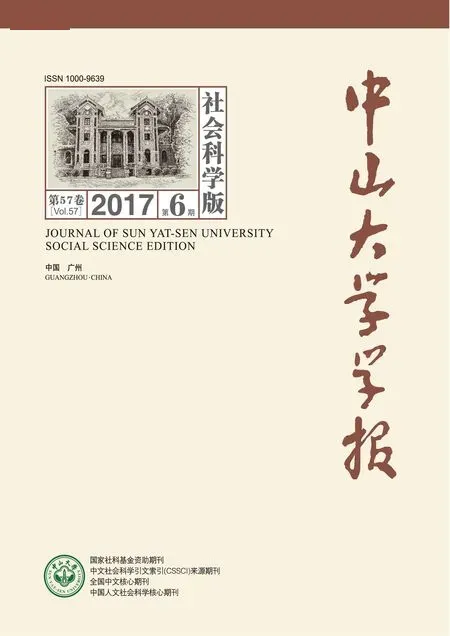圣人年谱:立志与成圣*
——王阳明与季本《论语》“志于学”章辨释
郭 亮
圣人年谱:立志与成圣*
——王阳明与季本《论语》“志于学”章辨释
郭 亮
明代中晚期,《论语》“志于学”章一度有“圣人年谱”之称,如此解释在王阳明及其弟子季本那里已见端倪。阳明在解释此章时提倡“亲切简易”,特别揭示“立志”贯穿于整个为学成圣过程的重要性,伸张立志成圣之“吾”的“主体性”,辨析经文中“志”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以“四时”的观念统摄成圣之阶段。由此,阳明提出“尽心”的成圣路线,而与季本“节节分疏”的释经路数有诸多不同。对比阳明与季本对“志于学”章的解释,既可以为考察阳明及其后学因经典诠释而产生的思想差异与分化提供方便,亦能成为进入阳明释经学的一个通道。
王阳明; 季本; 《论语》“志于学”章; 圣人年谱; 释经学
自古迄今,历代释经家对《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以下简称“志于学”章)之深意多有揭橥。有明一代的释经家如李贽、顾宪成、刘宗周多认为此章是叙述夫子一生成圣之经历,故而一度有“圣人年谱”之称。实际而言,阳明之后诸家对“志于学”章的解释取向可以直接追溯到阳明本人。本文拟以阳明写给弟子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的一封书信为中心,附及阳明在其他情境下对“志于学”章的解释,力图完整地展现出阳明对“志于学”章的心学式解释图景。在此基础上,考察阳明及其后学因经典诠释之不同而产生的思想分化,并为进入阳明释经学提供一个方便的通道。
一、圣人年谱与从吾之学
明代中晚期,“志于学”章一度有“圣人年谱”之称,李贽快评此章时直呼:“孔子年谱,后人心诀。”*[明]李贽:《四书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页。其后,顾宪成进一步发挥推演:“这章书是夫子一生年谱,亦是千古作圣妙诀。试看入手一个学,得手一个知,中间特点出天命二字,直是血脉准绳一齐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顺曰从心,证境也。即入道次第亦纤毫不容躐矣。”*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页。刘宗周则更径直点出:“此夫子一生求仁年谱。”*[明]刘宗周:《孔孟合璧》,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与以上三子不同,阳明在解释此章时直接挑明“立志”的核心地位*日人北见吉弘曾指出阳明“立志”论与“志于学”章有内在的关联。参见氏著:《王阳明的立志论》(上),《鹅湖月刊》2001年第5期,第44页。。他在《示弟立志说》中勉励胞弟时说:“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明]王阳明:《示弟立志说》,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7页。“三十而立”是志立,“不踰矩”亦是此志之不踰矩,由此“立志”成为贯穿成圣各个阶段的事情,这种对“志于学”章的解释为阳明一贯所坚持。阳明在回答弟子唐诩问及“立志”与“善念”关系时说:“‘从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处。”*④ [明]王阳明:《语录一》,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第21,5页。
重要的是,“志于学”是“吾”志于学,“吾”之一字张举的是立志学做圣人的“主体性”。没有了这个“吾”,或者说埋倒了这个“吾”,“志于学”就无从谈起,后面的成圣之阶段便无法真正地展开。阳明曾言:“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④显然,以阳明之见,子夏之学“博学而笃志”是“笃信圣人”,而曾子之“三省”是“反求诸己”。“笃信”虽好,但总不如“反求”切己。因此,对于常被为学所困的弟子,阳明总是一再强调“自求其志”“自许自志”,立“吾”之真志。对年近七旬,曾经笃志于诗文,后转向圣学,从师于自己的董萝石,阳明喟然叹曰:
夫吾之所谓真吾者,良知之谓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笃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笃敬焉,斯恶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恶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从私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恶之矣,将心劳日拙而忧苦终身,是之谓物之役。从真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将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入而不自得;斯之谓能从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尝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从吾之始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则从吾而化矣。*[明]王阳明:《从吾道人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第266页。
“吾”有真假之区别,而阳明所倡导之“吾”即是一己之“真吾”,“真吾”便是“良知”。“从吾之学”便是从吾良知之学,“从吾所好”便是从吾良知之所好。具体而言,吾良知之所好,是《礼记·礼运》中的“父慈、子孝”,《论语·卫灵公》中的“言忠信,行笃敬”。“从吾所好”就是“好”吾良知之所好,“恶”吾良知之所恶,由此,阳明把“名利物欲之好”看作“从私吾之好”,把“良知之好”看作“真吾之好”“天下之所同好”。至此,孔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志”于“从真吾之好”的“从吾之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是“志”于“从真吾之好”的“从吾而化”。
二、志与学:其心一也
关乎“志于学”章中“志”与“学”的关系,持朱子学立场的清儒陆陇其解释此章时说:“通章先要认这个‘学’字是学个恁么。讲家有以‘心’字贯者,有以‘天’字贯者,有以‘矩’字贯者,然这三字先难认,若认得时,随拈一字皆是实理;若认不真时,随拈一字皆是外道。”*[清]陆陇其撰,周军、彭善德、彭忠德校注:《松阳讲义——陆陇其讲〈四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144,144页。又曰:“认得这‘学’字了,方可去看‘志’字。”*[清]陆陇其撰,周军、彭善德、彭忠德校注:《松阳讲义——陆陇其讲〈四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144,144页。显然,陆陇其在“志”与“学”的关系上偏重于“学”之优先性。
然而,到底是“志”为先,还是“学”为先?对此问题,弟子朱守谐曾问学于阳明。其问学语如下:
守谐问为学,予曰:“立志而已。”问立志,予曰:“为学而已。”守谐未达。予曰:“人之学为圣人也,非有必为圣人之志,虽欲为学,谁为学?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为之,虽欲立志,亦乌在其为志乎!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明]王阳明:《书朱守谐卷》,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第293页。
这里,虽然阳明对“志”与“学”之间关系的看法很圆融,但是,细究之,如果非要对两者排出一个顺序的话,无疑是“志”为“先”。对于此“志”,阳明说得极为斩钉截铁:此“志”是“必为圣人之志”。这是因为,阳明把“志”看作与为学之“吾”息息相关的事情,它体现的是“为学之心”,是为学的那个“真吾”所在;而“志于学”之“学”,是为学的“领域”,代表的是“为学之事”。如此一来,“志”与“学”就在“此心”层面达到一如之境地。
三、王阳明对季本释经之拨正
“志于学”章展现的是夫子立志为学成圣之经历。对于阳明及其弟子而言,这样的人生道路,不仅对生而异质之人有效,对常人而言亦是可能。只不过,对如何立志为学成就圣人之地位,阳明和弟子的理解有所不同。嘉靖丙戌(1526),阳明55岁,看到同乡弟子季本信中对“志于学”章的解释后,回应曰:
承示:“立志益坚,谓圣人必可以学而至。兢兢焉,常磨炼于事为朋友之间,而厌烦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极!又谓:“圣人之学,不能无积累之渐。”意亦切实。中间以尧、舜、文王、孔、老诸说,发明“志学”一章之意,足知近来进修不懈。居有司之烦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辈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奋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则可矣;必欲如此节节分疏引证,以为圣人进道一定之阶级,又连掇数圣人纸上之陈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条例之中,如以尧之试鲧为未能不惑,子夏之“启予”为未能耳顺之类,则是尚有比拟牵滞之累。以此论圣人之亦必由学而至,则虽有所发明,然其阶级悬难,反觉高远深奥,而未见其为人皆可学。乃不如末后一节,谓:“至其极而矩之不踰,亦不过自此志之不已所积。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学可进,圣人岂绝然与人异哉!”又云:“善者,圣之体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无。去其本无之人欲,则善在我而圣体全。圣无有余,我无不足,此以知圣人之必可学也。然非有求为圣人之志,则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论,自是亲切简易。以此开喻来学,足以兴起之矣。若如前说,未免使柔怯者畏缩而不敢当,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无弊也……其云“善者,圣之体”,意固已好,善即良知,言良知则使人尤为易晓。故区区近有“心之良知是谓圣”之说。其间又云:“人之为学,求尽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为一,而未免反离而二之也。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明]王阳明:《答季明德》,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第227—228页。标点略有校改。
阳明对弟子季本的解释既有赞同之处,又有批评之意。要之,阳明赞扬弟子季本从孔子的自道中体味到圣人亦有常人之面向,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并非凭靠天生异质,而是由于有了此“志”坚持不懈之累积所致,并且,圣人即使达到“从心所欲不踰矩”之境地,亦有继续用力为学之余地。职是之故,阳明和弟子季本都高扬“圣人必可学而至”的论调。
阳明批评弟子季本之处在于:第一,季本“节节分疏引证”式的解释,以及引用一些古圣先贤犯有过错的例子,来说明已经达到圣贤地位之人,仍然有可能堕入低阶之境地。如此的解释,让人感到圣人进道需要不同之阶级,迈进圣人之门墙非常人所能及。第二,季本“善者,圣之体”,以及“人之为学,求尽乎天而已”的说法不够恰切、留有弊端。对阳明而言,“善”是圣人之本体本来无错,但是不如“良知”更易为人接受;对季本“求尽乎天”的说法,阳明则认为容易产生天人为二之流弊,因此,不如说为学之道“求尽乎心而已”更为“亲切简易”。
四、节节分疏:季本的释经路数
季本写给阳明的书信已经缺失,我们不能看到他如何具体解释“志于学”章。不过,季本所写的《论语私存》对此章有着详细的解释,且与阳明写给他书信中的内容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不妨引录:
十五者,入大学之年也。志,则心之所主而念念不忘者也。学以尽性,性之则即下文所谓矩也。尽性工夫,谨独而已。独不谨则矩踰矣。立即志之不颓处,不惑即立之有定处,知天命即不惑之主于天明处,耳顺即天命之随感而应处,从心所欲不踰矩即感应之合则处。自志学以志于所欲不踰矩,皆此学之渐进以造其极耳。非如《集注》可分知行为两事也。当其志学必亦立矣,但十年之中犹有未立之时,故至于三十而始可以言立。当其能立必亦不惑矣,但十年之中犹有惑时,至于四十而始可以言不惑。当其不惑必亦知天命矣,但十年之中天命犹有不知之时,至于(四)〔五〕十而始可以言知天命。当其知天命时必亦耳顺矣,但十年之中犹有不顺之时,至于六十而始可以言耳顺。当其耳顺必亦不踰矩矣,但十年之中矩犹有或踰之时,至于七十而始可以言不踰矩,此其安且成而言矣。故学者学此矩也,立者此矩之立也,不惑者此矩之不惑也,知天命者此矩之知也,耳顺者此矩之顺也。至于矩之不踰,则亦不过安于所志之学耳。圣人之学本无异于人,惟其工夫不息,则非人所能及,所以为圣也。然则此章所述进德之序,岂假设其辞以示谦哉?*[明]季本撰、朱湘钰点校、钟彩钧校订:《四书私存》,台北: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年,第144—145页。
整体上看,季本解释此章,主要修正的是朱子的解经范式。朱子解释“志于学”章时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古者十五而入大学。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顺,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4,55页。
又曰:
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讬也。后凡谦辞之属,意皆放此。*[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4,55页。
无论是朱子,还是季本,都对关键词汇如“十五”“志”“学”“不惑”“天命”等进行了详细的疏解。即使他们对这些关键词的理解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二人在解释此章时的大体思路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对比来看,季本开宗明义,把所志之学理解为“尽性”之学,而“尽性”的方法便是“谨独”,并把孔子之自道看作他本人的进德之序。这与朱子所认为的“圣人生知安行”“无积累之渐”的说法迥异。
问题的关键是,对夫子自道成圣阶段的理解,朱子认为每一个阶段必然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超越为基础,即是说十五岁有此志,三十岁此志已立,而后“守之固”则不必“事乎志”;四十岁已经不惑,而后“知之明”则“无所事守矣”;“知天命”之后则不必言“不惑”……季本认为成圣工夫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后亦会有堕入前一个阶段的可能。此外,从知行关系的角度来看,季本认为朱子把“耳顺”之前看作“知”的累积阶段,而把“从心所欲不踰矩”看作“致知”工夫熟后的“安而行之”阶段,故而朱子以六十岁为界限,把“耳顺”之年看作达到“知行合一”的临界点*陆陇其对朱子解“志于学”章分知行为二有一辩护:“通章依《大全》朱子,‘志学’是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顺’是知之至;‘立’是行之始,‘从心’是行之至,总是愈久愈熟,若更加数十岁,境界必又不同,不是至七十便画住了。或疑‘知’、‘行’不应画开,然论工夫则‘知’、‘行’并进,必无十年一‘知’,十年一‘行’之理;论得手,则‘知’、‘行’有辨,有得力于‘知’之时,有得力于‘行’之时。朱子之说不可易也。”([清]陆陇其撰,周军、彭善德、彭忠德校注:《松阳讲义——陆陇其讲〈四书〉》,第145页)徐复观亦看出朱子在解释“志于学”章时有分知行为二的倾向。参见徐复观:《有关中国思想史中一个基题的考察——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氏著:《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422页。。
撇开对文义的不同理解,与朱子和季本对成圣阶段的解释不同,阳明没有过多强调学做圣人需要一定的阶级,他只是以人生之“四时”观念来统摄成圣之过程。阳明在给弟子郭善甫的信中曾经说道:“夫农,春种而秋成,时也。由志学而至于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于不惑,去夏而秋矣。已过其时,犹种之未定,不亦大可惧乎?过时之学,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犹或作辍焉,不亦大可哀乎?”*[明]王阳明:《赠郭善甫归省序》,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253页。阳明把“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与天地之“四时”相配,立志者如农夫,春天播种,秋天自然会有收获,由此从立志到成圣便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
五、王阳明与季本释经的“规矩”之辨
季本的“志于学”章解释有来自经典之中的“证据”。子夏之“启予”,出自《论语·八佾》第8章子夏问诗,孔子称赞其能够启发相长于自己之学问。这在季本看来,孔子还未达到“耳顺”之境地。关涉“尧之试鲧”,《史记·夏本纪》有详细的记载: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鯀可。尧曰:“鯀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鯀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鯀之治水无状,乃殛鯀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鯀子禹,而使续鯀之业。*[汉]司马迁、[刘宋]裴骃、[唐]司马贞、[唐]张守节:《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0页。
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圣王尧因一时听信群臣之建议启用鯀治水而导致失败,因此,季本认为圣王如尧者亦有所惑之处。拆穿来看,这里涉及“圣人有过”之问题*陈立胜对王阳明“圣人有过论”做过详细而全面的考察。参见氏著:《“圣人有过”:王阳明圣人论的一个面向》,《学术研究》2007年第4期,第72—77页。。关乎此,阳明曾在写给胞弟的信中表明过自己的立场:“成汤、孔子,大圣也,亦惟曰‘改过不吝,可以无大过’而已。人皆曰人非尧舜,安能无过?此亦相沿之说,未足以知尧舜之心。若尧舜之心而自以为无过,即非所以为圣人矣。”*[明]王阳明:《寄诸弟》,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第185页。儒家圣人不是“超人”,更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全知、全能、全善之“神”。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圣人常怀戒慎恐惧之心,一有过错,便会察觉,一觉即化,不滞于心,如此而已。
面对弟子季本提供的“证据”,阳明亮出自己释经的“规矩”:“圣贤垂训,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觉者矣。”*[明]王阳明:《答季明德》,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第228页。阳明引用《易经·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为自己的解释背书,认为读书释经之法在致吾之良知,如此就能激活经典,为我所用,而一旦拘滞于文义,反被其所束缚,虽或偶能发明经义,时或窥见经文之“妙诣”,但终究不能摆脱 “意必”之窠臼,使“良知”陷于“障蔽而不自知觉”之境地。
六、结 语
为了对比阳明与季本释经之异同,我们不妨列一表格。由于季本的解释牵涉朱子,所以有必要把朱子《论语集注》中的解释也位列其中。

朱子季本王阳明“志于学”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古者十五而入大学。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顺,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论语集注》)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讬也。后凡言谦辞之属,意皆放此。(《论语集注》) 十五者,入大学之年也。志,则心之所主而念念不忘者也。学以尽性,性之则即下文所谓矩也。尽性工夫,谨独而已。独不谨则矩踰矣。立即志之不颓处,不惑即立之有定处,知天命即不惑之主于天明处,耳顺即天命之随感而应处,从心所欲不踰矩即感应之合则处。自志学以志于所欲不踰矩,皆此学之渐进以造其极耳。非如《集注》可分知行为两事也。当其志学必亦立矣,但十年之中犹有未立之时,故至于三十而始可以言立。当其能立必亦不惑矣,但十年之中犹有惑时,至于四十而始可以言不惑。当其不惑必亦知天命矣,但十年之中天命犹有不知之时,至于(四)〔五〕十而始可以言知天命。当其知天命时必亦耳顺矣,但十年之中犹有不顺之时,至于六十而始可以言耳顺。当其耳顺必亦不踰矩矣,但十年之中矩犹有或踰之时,至于七十而始可以言不踰矩,此其安且成而言矣。故学者学此矩也,立者此矩之立也,不惑者此矩之不惑也,知天命者此矩之知也,耳顺者此矩之顺也。至于矩之不踰,则亦不过安于所志之学耳。圣人之学本无异于人,惟其工夫不息,则非人所能及,所以为圣也。然则此章所述进德之序,岂假设其辞以示谦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示弟立志说》)“从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处。(《传习录》)中间以尧、舜、文王、孔、老诸说,发明“志学”一章之意,足知近来进修不懈。居有司之烦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辈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奋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则可矣;必欲如此节节分疏引证,以为圣人进道一定之阶级,又连掇数圣人纸上之陈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条例之中,如以尧之试鲧为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为未能耳顺之类,则是尚有比拟牵滞之累。以此论圣人之亦必由学而至,则虽有所发明,然其阶级悬难,反觉高远深奥,而未见其为人皆可学。乃不如末后一节,谓“至其极而矩之不踰,亦不过自此志之不已所积。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学可进,圣人岂绝然与人异哉!(《答季明德》)夫子尝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从吾之始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则从吾而化矣。(《从吾道人记》)夫农,春种而秋成,时也。由志学而至于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于不惑,去夏而秋矣。(《与郭善甫归省序》)七十岁之后 至其极而矩之不踰,亦不过自此志之不已所积。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学可进。 与季本同
对比以上三家的解释,撮其要,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圣人年谱问题。“志于学”章是否属孔子本人成圣之经历?从以上三家的解释对比来看,后人对此问题的看法确实产生了分歧。朱子认为圣人生而异质,自当生知安行,在成圣道路上不需积累之渐,故而夫子自道实属谦辞,其真正之目的是为学者立法。相比而言,阳明及其弟子季本,因秉持圣人亦常人的观点,特别是阳明有“心之良知是谓圣”之说法,均认为此章即夫子叙述自家学做圣人的渐修之过程,因此,属于孔子之“自传”。
第二,为学成圣的路数问题。阳明及其弟子季本都看重“立志”在成圣过程中的作用。阳明殊重十五岁之有志、三十岁之立志,以及七十岁之“志熟”,从而把“立志”看作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成圣过程。此外,比孔子更进一步,阳明与弟子季本认为在“从心所欲不踰矩”之后继续有 “立志”工夫可做。这与朱子志立之后“无所事志”的解释路数殊为不同。当然,虽然阳明及其弟子季本对“立志”的作用有一共识,但这并不能消弭他们在为学路数上的分歧。阳明认为成圣工夫要在此心上做,而季本则倡导“尽性”的工夫*有论者指出晚明王学思想中逐渐有一“宗性”派别开发出来。其实,“宗性”思想在阳明第一代弟子季本那里就已经有其发端。对晚明王学“宗性”思想的系统研究,参见侯洁之:《晚明王学宗性思想的发展与理学意义——以刘师泉、王塘南、李见罗、杨晋庵为中心的探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博士论文,2011年。。
第三,成圣之阶段问题。朱子把成圣之过程分为六个阶段,然而,阳明和季本对此的理解已经超出按照经文所显示的成圣阶段,特别是阳明把成圣之过程与“四时”相比配。除此而外,朱子认为在成圣的六个阶段中,后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超越,只要进入了一个高阶工夫之境地就不会有堕入低阶之可能;与此相反,季本站在朱子的对立面,认为成圣之工夫进入了高阶亦有可能堕入前一阶段。与朱子、季本不同,阳明既不完全站在朱子之立场上,认为众理洞明之后,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不完全与弟子季本同在一个战壕,认为到达成圣工夫之高阶后又会堕入前一个阶段。
第四,知行合一的问题。按照季本对“志于学”章的理解,朱子在解释此章时有分知行为二的倾向。对照朱子之解释,他确实把六十岁理解为“知之之至”阶段,七十岁为“安而行之”之阶段。阳明则把“立志”看作贯穿于从“志于学”到“从心所欲不踰矩”整个成圣之过程,由此“立志”成为保障“知行合一”的关键性工夫。因此,以阳明之见,知行合一贯穿于成圣的不同阶段。
总之,《论语》“志于学”章是反映孔子人生成长经历的重要篇章,阳明对此章之解释彰显出其在释经学中所倡导之一贯宗风:在释经的形式方面,与朱子、季本一流“专题化”的释经方式不同,阳明或是在与弟子的对谈之中,或是在写给亲人、弟子的书信中,或是在写给同志的序文中,以“非专题化”的方式来解释,如此的释经方式自然给受教者更为切己的指点,经典之中的文字在一个个新的语境中被具体地活化*为了方便对阳明释经著述体例进行分类,这里借用海德格尔(Heidegger)的一对术语:thematic是指一种对象化、系统化的研究,unthematic是指非对象化、非系统化的研究。参看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p.21、pp.414—415。;在释经的内容方面,阳明在尊重经典之原文的基础上,根据自家之体味,以一种“亲切简易”的方式解释经文,使得受教者能够有更切己的理解,为成就自家之神圣人生提供铺垫。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赵洪艳】
2017—03—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15ZDB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09);石家庄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7BS005)
郭 亮,石家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石家庄050035)。
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6.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