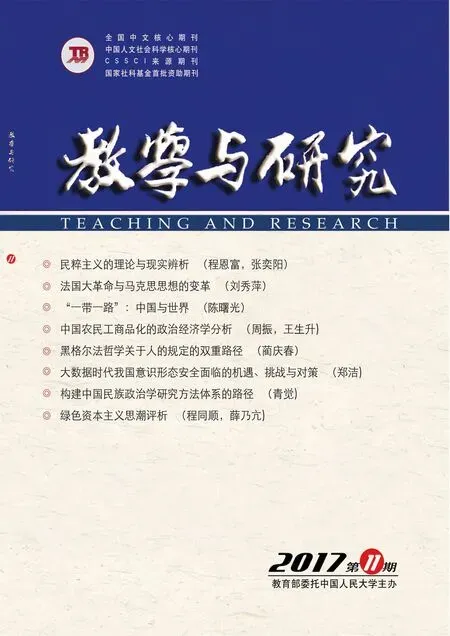绿色资本主义思潮评析
,
绿色资本主义思潮评析
程同顺,薛乃亢
绿色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市场中心主义;技术失灵
试图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绿色资本主义”思潮认为,利用市场手段和技术的进步可以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而没有必要对当前的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体系变革。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矛盾,在现实中基于市场中心主义的解决方案在资本主义的现有框架下是低效的,旨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创新也不能完全奏效,这些都使得“绿色资本主义”实际上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已经成为悬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有没有必要进行彻底的体系变革以解决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其中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流派便是“绿色资本主义”,该思潮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可以实现环境和生态危机的全面解决。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起源和理论特点,第二、三和四部分将分别论证绿色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市场中心主义的解决方案效果有限,新技术的进步也不足以完全解决环境问题。
一、什么是绿色资本主义?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迅猛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恶化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现代环保运动如星星之火一般蔓延开来。伴随着《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于杀虫剂滥用的反思,环保主义运动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本石破天惊的著作将保护环境的信条深深地刻在人类社会中。1970年4月22日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游行在全美扩散,这一天成为第一个地球日。20世纪70年代中期,面对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压力,美国政府为展现其强硬的态度,面对环境污染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不久以后,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正统的理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得到了加强,“命令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型的监管方法受到了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冲击。[1](P1314)此外,哈丁(Garrett Hardin)发表的《公共地的悲剧》一文也促进了环境治理的市场转向,他认为,当稀缺资源成为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公共财产时,就会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开发,只有通过市场手段对于产权进行明晰界定并通过市场进行激励和约束才能避免“公共地悲剧”的发生。[2](P1243-1248)1991年,世界银行发起的旨在解决成员国内部和全球范围环境退化问题的“全球环境基金”,标志着“绿色资本主义”式的全球性环境计划成为主流。[3](P3)
首先,绿色资本主义认为经济增长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有利的条件。
绿色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来自于环境经济学,它是基于经济角度来分析和解决一系列环境问题的一门交叉学科,其基本理论形式由外部性公共产品、产权和其他微观经济学理论构成。[4](P282-297)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环境和生态系统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拆分的机械系统,生态系统的任一部分出现的环境问题都可以被独立处理,人们能够运用经济价值的可分离性来分析“绿色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环境问题。[5](P129-155)相比之下,批判这一“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的生态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往往集中于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它强调经济系统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之一,任何一个环节必须放在生态系统这一整体之下处理才是正确的路径。[6](P13-14)
环境经济学和“绿色资本主义”把增长放在第一位,声称经济的扩张可以实现最佳的社会福利状态。这些学者的逻辑是,较大的蛋糕比较小的蛋糕更容易分配。然而,这种逻辑排除了生态系统本身的极限会将蛋糕的大小限制在某一阈值以下的这一重要前提。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评论说,环境经济学忽略了有限物理规模,实际上无限的增长和利润永远不会发生。[7](P193)
其次,绿色资本主义提出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市场原则来保护世界自然资源。
绿色资本主义宣称人类可以成功地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主要做法是对于地球上的所有资源进行合理的定价来反映它们的实际效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市场可以确保采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资源从而减少环境的恶化。[8](P1884-1885)
由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公共产品、外部性和其他经济理论,其判断标准是利益成本分析,强调效用和效率的概念,所以在“绿色资本主义”理论中所有的环境问题都可以转化为对效用增减的研究。其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导致的市场失灵,这意味着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未能有效地分配资源,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通过界定产权归属以及恰当的经济组织形式将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利用市场机制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碳交易的基本思路便来源于此。
最后,绿色资本主义对于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非常自信。
绿色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霍肯在《绿色资本主义:创造下一个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了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的概念,他认为全球经济是在一个包含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更大的经济系统里,自然资本支撑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赫尔曼·戴利明确了自然资本的概念,认为自然资本是能为经济系统输入可供生产的自然资源以及向社会成员提供服务的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将人类社会的资本存在形式概括为五种: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生产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9](P1-11)经济的增长由这五者的组合所决定,某一形式资本的低效率或者减少可以通过提高其他资本的效率或者增加其数量来解决,材料和资源的消耗会由于更先进的技术和创新而得以控制。总之,支持绿色资本主义的人认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对于环境和生态问题的解决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绿色资本主义”可以定义为以市场和技术创新为工具,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结合的旨在纠正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绿色资本主义忽略了资本主义 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
“绿色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对于市场和技术的力量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在市场和技术创新的作用下,资本主义能够与环境保护共存,没有必要对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体系变革。然而,“绿色资本主义”这一解决方案是不成功的,因为资本主义同生态环境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关系,这种根本性的矛盾表现为两点,一是增长的极限与追寻无止境利润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生态系统对立的矛盾。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追求永恒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对于资本积累病态的渴求将资本主义制度与人类历史上之前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环境可以被视为进行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者奥康纳(James O’Connor)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外,还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里的生产条件指的就是自然环境。[10](P18)
生态马克思主义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在于资本的本质是不停地追逐无限的利润,当代资本主义的“反生态”社会便来自这个逻辑。在这个社会中,技术、劳动、日常生活、消费模式和发展模式的实质都是追求最大的利润。[11](P87-90)为了使利润最大化,除了不断地扩大生产以进行资本增殖外,资本积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化趋势。[12](P3)通过金融化产生的资本积累不论是速度上还是总量上都远远超过从前在商品和服务行业的积累。绿色新政组织(Green New Deal Group)在其报告中清晰地论证了这种关系,认为全球债务规模的高速扩张不仅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最重要诱因,也助长了能源及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的不可持续型消费。[13](P2)由于资本的特质是无限积累和不断地追求增长,那么增长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因而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会无情地碾压阻碍其扩张道路上的一切东西。
罗马俱乐部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模拟实验,他们使用计算机模拟经济和人口增长与有限资源供应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实验最明显的结论之一是增长具有源于地球空间和资源有限性的极限。该增长模型有五个变量,即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枯竭,其中世界人口和工业化属于无限系统的指数级增长,而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枯竭是属于有限系统的线性增长方式,因此人口过度增长和工业化产生了粮食短缺、环境退化和资源不足等严峻的问题。根据模拟计算结果,如果这五个变量的当前增长趋势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将在一百年以内看到增长的极限,到那时全球性的系统崩溃将发生。[14](P10-12)基于对增长具有极限的理解,赫尔曼·戴利发展了零增长理论,提出了旨在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稳态经济理论。要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物质系统与人口系统之间要达成一种动态平衡状态,这两个系统只有都保持较低的流量时,稳态才可能实现。[7](P185-193)稳态经济所隐含的抑制财富增长速度的前提条件,与资本主义追求无限利润的本质是无法一致的。
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生态系统对立的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攫取和对经济增长的不懈追求往往会产生一种物质变换裂缝(metabolic rift),使人类同生态系统逐渐对立起来。[15](P372-373)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到,“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P95)
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紧密,那么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就不应该被仅仅视为单纯的环境问题,而应该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去考量。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的理解深受李比希提出的物质变换(metabolic)观点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17](P919)福斯特指出《资本论》批判的就是“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并将其概括为物质变换断裂(metabolic rift)这一概念。[18]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其客观呈现就是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物质交换过程在人和自然之间的表现则为劳动,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物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然而在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是异化的,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从而将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19](P274)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0](P579)资本主义通过土地圈地、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控制了生产资料,也掠夺了土壤的养分,不断地强化和深化人类和地球之间的物质交换的断裂。[21](P477-489)由此带来的物质变换断裂在全球层面上蔓延,使得人与自然的对立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三、绿色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心主义解决方案效果不佳
基于市场中心主义(Market-based)的解决方案在资本主义的现有框架下是低效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根据已观测到的气候统计数据撰写的《气候变化2014综合报告》,深入分析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对于地球气候的影响。其核心观点是,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是明显的,更为严峻的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业已达到历史最高值;温室效应气体所造成的近期的气候变化已对人类和自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如不加以控制,将导致生态系统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普遍和不可逆的危机。[22](P3-5)事实上,对于温室气体的限制措施早在《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签订时就开始实施,但是该计划的执行却举步维艰。美国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不过2001年上台的小布什政府却拒绝执行,使得美国成为最早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2011年12月,加拿大也正式退出该协议。此后,俄罗斯、日本和新西兰也明确反对《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欧盟和澳大利亚态度暧昧。世界银行在《全球气候体系中的整合发展》报告中批评《京都议定书》对抑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收效甚微,该条约于1997签订,但到2006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增长了24%。[23](P233)
《京都议定书》的失败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和环保人士开始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去寻找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些人认为该协议的缺陷在于其“自愿”的命令控制缺乏约束力,这一缺陷在“无政府状态”的全球体系中会被放大。因为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供给的碳排放限额势必会造成搭便车现象,而市场激励可以克服“京都议定书”的弱点。[24]碳税和“总量控制和交易”(cap and trade)是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的两种最主要的市场激励调控机制。碳税所解决的是化石燃料使用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问题。[25]利用碳税定价碳排放,是政府鼓励企业和家庭通过投资清洁技术和采用更环保的做法来减少污染的最有力激励措施之一。同碳税相比,“总量控制和交易”计划更为复杂,政府为特定的污染行业设定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限(cap),每一单位二氧化碳减排量都有一个“许可证”,公司可以在将来购买、销售、交易或存储这些“许可证”。在这个计划下,使用大量化石燃料从而产生过量排放的公司必须拥有额外的排放许可证,才能被允许进行超额排放,而能够控制排放量或者大规模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企业却拥有剩余的排放许可,这就使得这些过度排放的公司必须向能够控制排放量的公司购买排放许可证。与此同时,政府将逐步降低总排放量的上限,增加过量碳排放的公司购买排放许可证的成本。最后,随着污染许可证价格的上涨,使用化石燃料的成本将超过可再生能源,致使化石燃料逐渐退出市场。该方案的支持者认为,如果碳税和“总量控制和交易”计划能够实施,温室气体所带来的全球变暖问题就能够被有效遏制。
从表面上来看,“总量控制和交易”计划与碳税是可行的,环保主义者对于方案的成功满怀信心,但其自身存着致命缺陷。首先这两项计划方案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绿色税,从而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26](P213)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一国企业成本的增加会使其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从而直接削弱本国产业的竞争力。[27](P8)对于碳税来说,其最大的问题是碳税税率无法确定,具有很大的弹性。[28]这就给予大型的工业公司和利益集团相应的操作空间,他们可以通过游说要求维持低水平的碳税。煤、天然气、石油等行业组成的利益集团为国家提供数百万的工作岗位和上百亿的税收,如果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限制,政府的财政收入便会受到影响,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压力也将逼迫政府停止进一步的行动。除了工业公司之外,其他的社会团体也会要求低碳税的实施,例如,工会可能因为就业岗位面临削减而抵制碳税,消费者也会因为企业会将成本转移到自己身上而抵制新的税收。所以,通过多方谈判,碳税率在最终实施中会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这对于气候变化未来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来说,显然达不到人们的预期水平。如果要将整个21世纪的地表温度的升高幅度控制在2°C以下,则需要205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0年减少40%至70%,2100年保持排放零增长。[22](P20-21)而维持原有的碳税税率水平是不可能达到这一要求的。
“总量管制和交易”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税。[29](P118)很多国家和企业尽可能地不参加这一计划,而即使同意了这一方案,也会把排放上限设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的推行被誉为美国环保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但实际上该法案仅仅承诺在2020年之前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而不是京都协议书中所要求的1990年)降低17%。而如果与1990年的排放量相比,则仅仅下降了5%。[30]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总量控制和交易”计划中规定的总量上限仅仅在2020年下降1%,而且85%的许可排放量都被免费发放出去而不是在碳交易市场上拍卖。[31](P315)在德国,来自工业的压力集团通过失业和工业转移的威胁游说政府以谋求更高的排放总量上限,并且成功地得到了3%的额外排放量。[29](P118)日本和韩国则于2011年宣布放弃实施应当在2013年执行的限额和交易计划。日本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称,64家相关的大型企业中有61家反对引入碳交易,这些公司认为这个计划大大增加了企业经营的成本,日本的优势产业面临着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环境政策的“负担”只会在全球竞争中拖后腿。[32]2014年,澳大利亚则放弃了一系列的碳税政策,因为它对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有负面影响,碳税导致了企业的成本急剧上升,使得资源开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消失了。[33]
市场中心导向计划的失败不应归咎于利益集团与政府的沆瀣一气,即使政治领导人有改革的勇气,他们也不能扭转局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各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因为只有经济的增长才能支持人类目前的生活,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化石燃料的消费最大化。作为一个理性的政治行为体的政府,其首要目标必定是寻求最大化的政治支持,当政府发现这些计划和行动可能对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时,便会继续在宽松的化石燃料政策上前进。总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性民主中,政党和政府没有更多选择,为了实现连任,得到民众和企业财团的支持,其竞选纲领和执政政策只能专注于民众的短期福利,提高就业率。
四、绿色资本主义推崇的新技术也不足以完全解决环境问题
支持“绿色资本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新技术的诞生和发展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和资源利用率,能够减少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者在生产过程中每单位产生的废物和有害排放物的量。然而,创新和技术进步仍然不能完全解决资源消耗增加的问题。
智能手机对于固定电话、MP3播放器、相机、传统便携播放器具有极强的替代效应。但是对智能手机需求的急剧增加,必然导致必要的资源投入从原来的电子设备转移到智能手机上。即使每单位的能耗由于技术的进步而下降,制造手机所需要的材料和能源总消耗也可能远超从前。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刚刚发布的题为《失控的创新:智能手机十年全球影响》的报告,2016年用于智能手机的制造能耗是2007年的250倍,如果用于制造液晶屏的铟的开采速度不加以限制,那么14年内便会枯竭。由于越来越多的手机采用一体化设计,使得旧手机的拆解异常困难,由此产生的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废弃物回收处理将成为一大难题。[34]

图1 2007年以来世界能耗 [34]
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种状况被称为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19世纪经济学家杰文斯在研究煤炭的使用效率时发现,技术进步使得煤的使用效率提高了,但煤的消耗总量却反而更多。[35]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所使用的特定资源的效率,但是效率的提高却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该资源的消耗。[36](P1)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更多的利润,更多的利润使得资本家能够扩大再生产并且增加这种资源的消耗。斯默(Kenneth A. Small)和丹德(Kurt Van Dender)研究了美国车辆里程燃料效率提高的反弹效应,他们发现车辆燃料效率提高5%只能使燃料消耗降低2%,这其中3%的差距是因为效率更高的燃油发动机使得美国人能够驾驶得更快和更远。[37](P25-51)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安托万·德谢兹莱普雷特(Antoine Dechezleprêtre)、大卫·荷莫斯( David Hemous)、拉尔夫·马丁(Ralf Martin)和约翰·范里宁(John Van Reenen)研究了汽车和交通运输业中影响技术变迁的因素,并将结果发表于顶尖期刊《政治经济学》,他们的研究发现,汽车工业中技术创新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如果某一企业更多地接触偏向清洁型创新(clean innovation)的外部环境(技术溢出表现为偏好清洁环保的技术),则其对于清洁技术的创新和使用有更强的偏好;反之,具有污染型创新(dirty innovation)历史的公司在未来也更倾向于污染型的创新。[38](P1-51)目前完全从事量产电动车生产的汽车厂家只有特斯拉,电动汽车项目在其他的传统汽车制造商,例如大众、丰田、奔驰和宝马等公司的生产计划中仅仅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因此,由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它们投身于制造更加清洁环保的汽车技术的意愿值得怀疑。2015年曝出的大众集团“尾气门”事件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那年美国环保署查出大众公司涉嫌在58万辆柴油发动机车辆的车载电脑中安装一种可用于尾气测试作弊的软件,允许车辆正常行驶时的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法定标准的40倍以上。[39]
因此依赖新技术去完全解决环境问题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技术发展盲目狂热的错误,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同样可能不会沿着人类预先设计的路线前进。[36]
结 论
“绿色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试图利用市场和技术将“绿色”和“资本主义”拉到同一条战线上。他们坚信,不需要进行彻底的体系变革就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妥善处理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
首先,他们认为经济的增长就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好的福利,但是他们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自身的有限性。资本主义的逻辑在于资本的本质是不停地追逐无限的利润,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和发展模式的标志是追求最大的利润,这与生态系统有限性是矛盾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物质交换裂缝的产生,人与自然也逐渐地对立起来。
其次,“绿色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坚持认为,利用市场这一强有力的工具,可以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根据这一逻辑,这些学者提出了碳税和“总量控制和交易”计划等措施。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各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发展经济,大型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不能受到损害,同时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性民主中,政党和政府都专注于民众的短期福利和就业率来讨好选民,因此,碳税和“总量控制和交易”都得不到有效执行。
最后,“绿色资本主义”认为,新技术的诞生和发展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并且使得少量的资源生产更多的商品。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进步又使得人类面临着杰文斯悖论,效率的提高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该资源的消耗。除此之外,技术创新所具有的强烈的路径依赖的特性也使得污染企业欠缺研发清洁型技术的动力。因此,人类应该摒弃绿色资本主义对于技术发展的盲目信念。
[1] Michael Watts. Green Capitalism, Green Governmentality[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ume 45, Issue 9, 2002.
[2] Garrett Hard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Vol. 162, Issue 3859, 1968.
[3] Zoe Young. A New Green Order?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M].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4] Robert U. Ayres, Allen V. Knees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Externalit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 3, 1969.
[5] T. Weis. The Ecological Hoofprint: The Global Burden of Industrial Livestock[M]. London: Zed Books, 2013.
[6] Jeroen C. van den Bergh. Ecological Economics: Themes, Approaches, and Differences with Environmental Economics[J].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2, Issue 1, 2001.
[7] Herman Daly. Allocation, Distribution, and Scale: Towards an Economics that is Efficient, Just, and Sustainable[J].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ume 6, Issue 3, 1992.
[8] J. Alper.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with the Power of the Market[J]. Science, Volume 260, Issue 5116.
[9] Neva R. Goodwin. Five Kinds of Capital: Useful Concep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03-07, 2003.
[10] Evangelia Apostolopoulou, William M. Adams. Neoliberal Capitalism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Post-crisis Era: The Dialectics of “Green” and “Un-green” Grabbing in Greece and the UK[J]. Antipode, Volume 47, Issue 1, 2015.
[11] 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2.
[12] Paul M. Sweezy. 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J]. Monthly Review, Volume 49, No. 4, 1997.
[13] Green New Deal Group (GNDG). A Green New Deal[M].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008.
[14] D. Meadows. The Limits to growth[M]. New York: Universe Books,1972.
[15]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 105, No.2, 199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8] 刘仁胜.约翰·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的阐释[J].石油大学学报,2004,(1).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0]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1] Ivan Scales. Green Consumption, Ecolabelling and Capitalism’s Environmental Limits[J]. Geography Compass, Volume 8, Issue 7, 2014.
[22] IPCC.气候变化2014综合报告[R].2015.
[23] World Bank.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into the Global Climate Regime[EB/OL]. 2010,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WDRS/Resources/477365-1327504426766/8389626-132 7510418796/Cha-pter-5.pdf.
[24] 朱京安,宋阳.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失败的制度原因初探——以全球公共物品为视角[J].法治与社会发展,2014,(2).
[25] 娄峰.碳税征收对我国宏观经济及碳减排影响的模拟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10).
[26] James Hansen. Storms of My Grandchildren: The Truth About the Coming Climate Catastrophe and Our Last Chance to Save Humanity[M]. New York: Bloomsbury, 2010.
[27] S. Chang. Cap and Trade or Cap and Tax?[J]. IEEE Spectrum, Volume 46, Issue 4, 2009.
[28] 蔡博峰.碳税PK总量控制-碳交易[J].环境经济,2011,(6).
[29] Richard Smith. Green Capitalism: the God That Failed[J].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Issue 56, 2011.
[30] Brian Tokar. The Problem with Climate Legislation-Politics-as-Usual While the Planet Burns[EB/OL]. 2010, http://www.greens.org/s-r/51/51-02.html.
[31] Ashley Dawson. Climate Justice: The Emerging Movement Against Green Capitalism[J]. Climate Justice, Volume 109, Number 2, 2010.
[32] S. Keidanren. Korea Business Lobby Oppose Start of Carbon Trading[EB/OL]. The Japan Times News, 2011,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1/01/15/business/keidanren-s-korea-business-lobby-oppose-start-of-carbon-trading/#.WNadgmR96Uk.
[33] Telegraph, Australia Abandons Disastrous Green Tax on Emissions[EB/OL].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commodities/10972902/Australia-abandons-disastrous-green-tax-on-emissions.html.
[34] 绿色和平组织.失控的创新:智能手机十年全球影响[EB/OL].2017, http://www.greenpeace.org.cn/global-impact-of-10-years-of-smartphones/.
[35] William Jevons. 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EB/OL].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66. 2nd edition, revised. 2017/4/7.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jevons-the-coal-question
[36]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Richard York. Capitalism and the Curse of Energy Efficiency: The Return of the Jevons Paradox[J]. Monthly Review, Volume 62, Issue6, 2010,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0/11/01/capitalism-and-the-curse-of-energy-efficiency/.
[37] Kenneth Small, Kurt Dender. Fuel Efficiency and Motor Vehicle Travel: The Declining Rebound Effect[J]. Energy Journal, Volume 28, Number 1, 2007.
[38] Philippe Aghion, Antoine Dechezleprêtre, David Hemous, Ralf Martin, John Van Reenen. 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4, No. 1, 2016.
[39] 李雯.“排放门”大众到底是怎么作弊的[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auto/2015-09/23/c_128259769.htm.
[责任编辑刘蔚然]
AnalysisofGreenCapitalismThoughts
ChengTongshun,XueNaika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green capitalis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rket centrism; technical failure
The “green capitalism” thought believes that the use of market mean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effectively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a thorough system reform of the current capitalism. However, due to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olution based on market centralism in the reality is inefficient under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capitalis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imed at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not entirely effective. All this makes the “green capitalism” thought in fact a self-contradictory situation.
程同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薛乃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